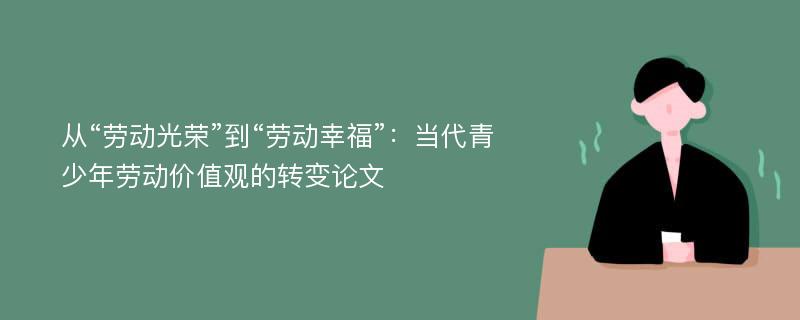
从 “劳动光荣 ”到 “劳动幸福 ”:当代青少年劳动价值观的转变
王绍梁①
[摘 要 ]当代青少年的劳动价值观发生了实质性转变,即从“劳动光荣”转向“劳动幸福”。这一转向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包括社会从小农生产转向资本全球化时代,以集体主义为价值底蕴的计划经济转向以个人主义为原则的市场经济以及脑力劳动成为社会劳动的主导形式等。相比过去,当代青少年更愿意接受挖掘潜能、表达个性、开发创造力等劳动教育形式,这些劳动教育形式使得青少年从自身的劳动之中获得本质力量的确证和肯定,同时也发挥了他们的自由和个性。
[关键词 ]劳动幸福;劳动光荣;劳动教育;青少年;价值观
关于青少年的劳动教育问题,近十年流行着一种消极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当代青少年越来越不热爱劳动了,他们更喜欢沉浸在休闲的游戏或者娱乐之中。这种观点是否正确,我以为是值得商榷的。青少年是国家的希望和未来,他们是否朝气蓬勃、是否热爱劳动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我们社会未来是否充满活力、是否具有创造力。因此,我们需要研究的是青少年不热爱的是什么劳动,他们热爱的又是什么劳动?不同的劳动倾向背后实质上说明了当代青少年的劳动价值观在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即由“劳动光荣”传统价值观转向“劳动幸福”的现代价值观,而这种价值观转变的基础正是不同时代青少年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差异。
由于工程总承包方对项目调查研究的局限性和收集资料的影响,错误地得出项目特点和项目实现的条件,编制计划脱离实际,导致停工待料和相关工序脱节;松散的设计、施工以及采购导致工程总承包方没有克服由于设计和施工的不协调而影响建设进度;另外,设计工作不及时,施工组织不力,劳动力和施工机械调配不当,施工技术措施不当均会引起质量事故导致停工;作业人员未按方案施工导致较大安全事故引起整个工程长时间停工;平面布置不合理等因素致使工程受阻,施工方缺乏基本的风险意识,盲目或野蛮施工而导致工程被迫中断,施工单位旧的管理模式,施工队的核算方式等导致的效率低下等,以上内容均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工程进度。
一、两种劳动价值观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
笔者认为,应当从社会历史变迁的角度理解当代青少年劳动价值观念的变化。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告诉我们,“劳动光荣”和“劳动幸福”这两种不同价值观的生成背后一定包含着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这些历史条件作为社会意识的生成土壤恰是辩证而科学地理解看似冲突和矛盾的价值观的现实基础。社会生产的转向、经济关系的变迁以及劳动形式的变化是理解青少年价值观由“劳动光荣”转向“劳动幸福”的三个重要的社会历史条件。
在脓毒症的免疫抑制阶段,由于胸腺萎缩及外周血中T淋巴细胞减少可导致机体免疫监视功能减弱,对病原体的易感性增强,增加二次感染的可能性[32]。在多细菌诱导的脓毒症动物模型中,炎症早期使用S1P类似物(FTY-720)抑制T淋巴细胞从淋巴器官迁出,对小鼠生存率无显著影响[33]。然而,在柠檬酸杆菌诱导的脓毒症小鼠中,FTY-720长期治疗的小鼠体内病原体清除延迟,且其脾内的细菌含量显著增加[33-34]。
第一,社会生产从传统的小农生产向现代资本主义全球化生产的转变。从社会形态的转变来看,西欧大体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几种社会形态的转变。相比较而言,中国并不存在西方式的“奴隶社会”。总的来说,我们的历史是以封建社会的存在形态为主体。对中西方来说,社会形态都可以分为两种:前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封建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就“劳动光荣”这样的价值观来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下具有不同的指向,“奴隶社会中的劳动光荣被统摄为奴隶对奴隶主的忠顺;封建社会的劳动光荣是对自然经济中男耕女织自食其力劳动生活的赞美。”[1]长达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其社会生产主要是以小农经济或小农生产为主导。恩格斯指出:“小农,是指小块土地的所有者或租佃者——尤其是所有者,这块土地既不大于他以自己全家的力量所能耕种的限度,也不小于足以养活他的家口的限度。”[2]这就是说,小农生产的特征是自给自足,只能保持家庭的继续生存和劳动力的再生产。这种生产是以使用价值的生产作为目的和追求,所以反对懒惰、褒扬劳动,反对不劳而获、赞美勤劳致富。正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食衣足而知荣辱”。“劳动光荣”是对我们过去积极、美好和高尚的生存状态的一种价值观上的浓缩,这种价值观一直延续到“小农生产”的历史完成。由此,中国也卷入现代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之中,我们社会的生产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即从个体小农生产转向工业生产、商业生产。这样,我们一改从前“民以食为天”的自给自足观念,我们的生产目标也不再只是“使用价值”,而慢慢转向“交换价值”。这种转变决定了以前靠着劳动获得物质财富的历史已由“工资多少”“经济收入”以及资本大小为财富象征的时代所替代。以前劳动光荣的价值取向也就慢慢发生了变化,劳动是否光荣已经不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人们关注的是能否通过劳动获得幸福。
李正江等[10]建议对甲状腺被膜侵犯和Ⅵ区淋巴结转移的cN0甲状腺癌患者,常规行颈部Ⅲ、Ⅳ区淋巴结清扫, 能及时发现和清除侧颈隐性淋巴结的转移。SLNB能有效发现早期转移的颈部淋巴结,特别能反映Ⅵ区淋巴结的转移情况,再结合肿瘤大小、是否有包膜侵犯,对于临床是否行侧颈区(Ⅱ~Ⅳ区)淋巴结清扫起到了指导作用,因此,纳米碳示踪前哨淋巴结活检能有效地评估cN0分化型甲状腺癌颈部淋巴结转移情况,同时在保证Ⅵ区淋巴结清扫彻底的同时,还有助于甲状旁腺的保护。
第二,经济关系从上世纪的计划经济向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经济转变。社会生产的变化只是一切社会意识形态转变的大基础。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主要是计划经济的退场和市场经济的出场,并且后者在社会资源配置方面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经济问题讲究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为谁生产,从我国的社会性质看,计划经济是为人民生产。这种经济关系变化所带来的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表现为集体主义向个人主义的转变,穷者越穷、富者越富的贫富分化以及“劳者不获、获者不劳”的异化状态。计划经济是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前经济关系的主要形态,这种经济形态在一定时间内为集中力量办大事、国家力量快速增长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这种经济关系所塑造的社会价值观更倾向于“集体主义”。为谁生产的问题就是为谁劳动的问题,在计划经济时代,为集体生产就是为集体劳动。因此你的劳动是否有价值、是否是正义的、是否是道德的以及劳动所得多少,其评价标准都来自“集体”。我国历史上的“公社运动”时代的劳动就是如此,为集体的劳动优先于为个人的劳动、为集体劳动的多少决定所得“工分”的多少,甚至为集体劳动的贡献决定了从集体获得的赞扬和荣誉的多少。反观之,在市场经济的时代,一切方向和顺序都发生了大转弯,评价劳动的标准和原则都转向了个人。尽管在价值观的倡导上,仍然是强调每一个人的劳动应当是个人与社会的统一,但每一个劳动者的真实出发点已经转变为了个人,即为自己而劳动。集体劳动的优先性也向着个体劳动转移,这种转移或变化所象征的是当代人的价值观的转变。青少年作为这个时代的主要受影响群体,自然也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我们不得不承认,当代青少年对集体主义的信仰已经让位于个人主义。但是这种转变并不代表着社会集体利益服从于个人利益,而只是每一个人思考和行为的出发点发生了变化。集体和个人并不是绝对对立的,马克思早就说过:“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前提和条件。”[3]这样,“劳动幸福”价值理念的形成并没有绝对否定“劳动光荣”价值理念,而是前者扬弃了后者,是“劳动”价值观念在更高发展阶段的表现。
第三,劳动形式从非创造性的体力劳动向创造性的脑力劳动的转变。劳动价值观的变化一定离不开对劳动本身的认识和理解,可以这么说,有什么样的劳动形式就有什么的劳动价值观。大体来说,社会劳动的主要形式经历了从体力劳动向脑力劳动、非创造性劳动向创造性劳动、简单劳动向复杂劳动的转变。这主要体现在蓝领工人的白领化、机械劳动逐步为智能机器人所替代以及现代社会对创造性劳动需要的增长。所谓的“劳动光荣”在过去时代所赞颂的主要是体力劳动,主要表达了对劳动者辛苦劳作、默默奉献的尊重。也是在体力劳动主导社会发展、推动社会进步的历史长河中,逐步使得“劳动”一时间成为“体力劳动”的同义词,这种对劳动的“体力劳动”的理解也深深影响了当代青少年。在价值观的倡导上,我们固然要倡导“劳动平等”观,尊重一切劳动的价值理念,但我们又不得不说,社会的主要劳动形态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青少年的劳动观念发生相应转变也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尤其随着脑力劳动的普遍化,社会价值创造的主体也由体力劳动转变为脑力劳动,对现实劳动的认识和评价不得不受这种转变的影响,所以“坐办公室”成为人们就业一时的“向往”。尤其是社会对创造性劳动的需求越来越大,你的劳动是否有意义、是否更有价值取决于劳动的创造性的大小,而不同于过去“体力劳动”的简单“量”的大小。这是对当代青少年影响最大、价值观形塑力量最强的一个社会条件。
二、当代青少年价值观从“劳动光荣”向“劳动幸福”的转变
第二,当代青少年对“劳动光荣”的真实认同感越来越低,劳动光荣成为一种表面上的“应然”认同,即“劳动应当是光荣的”,而实际在职业选择的时候,他们往往更认同“不劳而获”“关系致富”等错误的观念倾向。
但是使得曾经成为一时风尚的“劳动最光荣”的价值观蜕变成了一种口号的根源还在于资本主义异化劳动的出现。异化劳动是当代社会一切病症的根源。同样地,使“劳动者不再光荣”“勤劳难以致富”的病原体也是“异化劳动”。所谓“异化”在这里指的是本为人所创造出来的对象,反过来危害、统治和奴役主体自身。今天的社会里充满着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佛系”犬儒主义错误价值理念。反观现实社会的劳动阶级,他们作为当代青少年的父母,不仅很难从劳动中获得真正的赞扬和肯定,而且深深体会到劳累、痛苦和压迫感。不同时代的“劳模”评选即反映了劳动价值观的变化。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像杨富珍、杨怀远、蔡祖泉等老一代劳模在上海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4];而在当代社会,一方面充斥在青少年面前的是娱乐界的明星偶像如“小鲜肉”,另一方面劳模中的一线劳动者越来越少,越来越多的却是成功人士、领导干部,乃至资本家。今年9月1日,教育部联合中央电视台推出了一时间成为“网红”的《开学第一课》。在批判的浪潮之中,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央视节目推迟了十多分钟,而在这十多分钟里充斥的不仅是与教改相反的教育机构广告,更令人无法理解的是,开播之前满屏传达的不是男性的阳刚之气、一线劳动者的辛勤工作,而是“小鲜肉”的“不男不女”。客观地说,“小鲜肉”可以是任何个人审美和追求的对象,但作为青少年价值观引导的重要媒介却“反其道而行之”,这怎么能不让青少年的劳动观发生扭曲?怎么能不让他们“像逃避瘟疫一样逃避劳动”[5]?怎么可能让他们秉持“劳动光荣”的价值信念?
厅直水电站大都承担着江河的防洪、灌溉、航运等社会责任,承担的这些社会责任都无法得到相应的补偿,要争取政府相关部门对水电站的支持:①免征或减征水资源费和库区扶持基金;②逐步提高上网电价。因厅直水电站建成较早,资产未重新评估,资产账面价值严重偏低,折旧少,导致物价成本调查中资产部分成本小,人工成本所占比重大,更新改造隐性成本无法真实反映,补偿时间严重滞后,以致账面上的生产成本不能真实客观地反映现实成本,以致电价难以提高,水电站没有更新改造的能力。水电站要争取物价部门的理解和支持,逐步提高上网电价。
谈到当代青少年的新劳动价值观,也就不得不追溯至马克思哲学中的“劳动”概念。在马克思那里,劳动并不单单指狭隘的“体力劳动”,也不是劳累和痛苦的代名词。相反,在哲学的意义上,劳动关涉的是人的本质。劳动在人类社会中起着非常大的积极作用,劳动创造人本身,劳动是财富和幸福的源泉。那么这个“创造人本身”指的又是什么?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中就大胆地提出,正是在劳动的过程中,猿才逐渐转变为人类。手脚、语言等都是在劳动的过程中被创造出来的。这固然有一定的科学性,但是马克思所说的“劳动创造人本身”并不只是生理学意义上的“创造”,即创造了我们的手和脚,使人在劳动过程中慢慢学会站立,实际上,这种“创造”是哲学意义上的创造。
第一,当代青少年越来越不热爱“劳动”了,并将劳动与劳累、痛苦的消极理解联系起来,视之为休闲、享乐的对立面。
“劳动光荣”是一种对劳动的褒扬,是劳动阶级通过劳动成果从外部获得的一种赞扬和荣誉。“劳动幸福”不是一种从外向内的赞扬,相反,它表明的是一个人从自身的劳动成果之中获得一种本质力量的确证和肯定,这种确证和肯定是一种潜能的实现、能力的表现以及由此而获得的愉悦和幸福感。
这就是马克思“劳动”概念的哲学基础,它指的是劳动是属人的感性的对象性活动,在劳动的过程中我们不断地创造出属于我们的对象,这种对象反过来创造人自身。因此,正是在这样的对象性关系之中,人的本质力量获得了确证和肯定。简而言之,所谓的“劳动幸福”就是劳动对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和肯定。这种肯定有别于从外部收获的荣誉和赞美,它本质上是自己对自己的一种肯定,自己对自己的潜力实现而获得的一种愉悦和快乐。这种在劳动之中获得的快乐并不是“劳动光荣”,而是“劳动幸福”。马克思认为,“我的劳动是自由的生命表现,因此是生活的乐趣”,“我在劳动中肯定了我自己的个人生命,从而也就肯定了我的个性的特点。”[10]劳动(感性的对象性活动)是人的本质,而不是动物的本质,因此劳动是人类与动物相区别的特有的活动之一。动物尽管也有吃喝拉撒,但是人不仅是吃喝和繁殖,而且有自己的精神生活。离开劳动,也就不可能有精神生活的存在,因为离开了劳动,人的本质力量就得不到显现。
一项实证调查研究[7]发现: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青少年越来越认同“劳动很累,所以痛苦”这种观念;青少年享乐主义倾向越来越强;青少年对“不劳而获”劳动价值观的否定倾向在下降;青少年越来越认识到“人际关系”对于获取个人财富的重要性;青少年对劳动应然性即“人生在世就该劳动”的赞成度逐步降低。这就是说,随着青少年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他们的劳动价值观念并没有得到强化,对待劳动的态度越来越消极。另一项调查[8]发现,青少年“应然”价值观念与“实际”价值观念存在矛盾和冲突:一方面,有72.6%的受调查学生认为“社会上没有低贱的劳动岗位”;另一方面,却只有9.5%的学生愿意从事“有技术的工种或劳动”,相反有高达35%的学生想成为“企业家”。从这些调查中,我们可以得出几个结论:
这些结论都真实地反映了当代青少年劳动价值观的变化。“劳动光荣”的价值取向在现实中也慢慢远离青少年,逐渐成为一种价值纠偏的“口号”。这就是说,“当我们研究价值观念时,需要区分实然和应然两个方面”,[9]当社会处于小农生产、计划经济以及以体力劳动为主的时代,“劳动光荣”曾经作为社会以及青少年劳动价值观的真实基础存在过,这是“实然”的阶段;但是当社会转向资本全球化、市场经济以及以脑力劳动为劳动主要形式的今天,“劳动光荣”作为人的价值层面的实体就逐渐为社会现实消解,再谈“劳动光荣”就会成为一种软弱无力的口号,因为现实处处充满着对“劳动光荣”的否定。由此,“劳动光荣”开始从“实然”的现实层面转向“应然”的理想层面。这就是当代青少年劳动价值观转变的内在机理与逻辑。
概括来说,当代青少年从“劳动光荣”的传统价值观转向“劳动幸福”的现代价值观,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与过去相比,当代青少年在生活、学习以及实践等方面关注的焦点从集体转向个人,由从外部获得对劳动的肯定转向劳动本身是否能够肯定自己。“劳动光荣”与否已经不是青少年关心和认同的焦点,他们关心的是能否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幸福。关注自身,是当代青少年的一大特征,所以往往被冠以“特立独行”“独来独往”以及“个性鲜明”等特点。从这些性格的变化就可看出,当代青少年不再是以“集体主义”为活动、思考以及表现的优先原则,更多是从自身出发,敢于表达、表现自己。在劳动价值观方面同样也是如此。学校开展的活动、开发的劳动如果还停留在过去那种单纯“体力劳动”和简单劳动基础上,青少年势必会有排斥感和厌恶感,对劳动的天然亲切感也会随之降低。相反,他们更加愿意参加具有挑战性,能够发挥他们潜能和表现他们智力的劳动,在这些活动或劳动之中,他们能够将自己的想法、主意以及创意表达出来。
马克思把劳动异化归结为四个方向:一是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的异化。在现实中表现为“劳者不获,获者不劳”;二是劳动者与劳动本身相异化,劳动者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6];三是劳动者与类本质相异化,概括地说就是劳动原本是人本质力量展现的活动,但是在异化劳动中这种力量被压抑了,得不到体现,这也是人的理想世界和精神世界的丧失;四是人同人的异化,这些异化的结果就是人与人之间关系变得越发紧张、对立。在处于“异化状态”的社会中,青少年如何看待劳动呢?
第二,与过去相比,当代青少年越来越愿意参加创造性的活动或劳动,也越来越排斥繁复、简单和机械的劳动。在上个世纪的中小学中,学校组织的劳动一般都属于“体力活”,如打扫卫生、做家务活。这些体力劳动固然重要,依然是学校劳动教育的必修课。如苏联著名教育实践家和理论家苏霍姆林斯基指出体力劳动在“促进动作协调,塑造优美体态”“平衡心脏和神经系统,改善健康状况”“培养坚强意志,完善个性”“达成有效休息,调节精神状态”[11]等方面有着十分积极的作用,但是就价值观的真实基础来说,已经不是当代青少年劳动教育的轴心和目标。我们应当顺应时代的潮流,与时俱进,将当代青少年的价值取向与劳动教育结合在一起。创造性劳动不仅是我们社会得以发展、国家得以强大的根本动力,而且也是培养青少年符合时代的劳动价值观的根本途径。创造性劳动包括智力开发型、社会参与型、动手操作型、团队合作型等方面的劳动。苏霍姆林斯基也同样指出了“创造性劳动”的重要性,他指出,“只有当孩子从事那种必须经常进行思考和操心的长期劳动时,劳动活动的创造性质才会在他面前展现出来”[12],体力劳动就只是作为这种劳动创造性发现和锻炼的基础。
三、用马克思劳动幸福理论指导青少年的劳动教育
列宁曾指出:“没有青年一代的教育和生产劳动的结合,未来社会的理想是不能想象的。”[13]马克思也早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在按照各种年龄严格调节劳动时间并采取其它保护儿童的预防措施的条件下,生产劳动和教育的早期结合是改造现代社会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14]问题在于,当代青少年的教育应当与怎样的生产劳动结合呢?这是我们应当关注的方向和研究的课题。
第一,当代教育应当围绕学生的兴趣、爱好和性格特点开发相应的生产劳动形式。马克思批判的是现代社会的异化劳动,异化劳动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必然会经历的一个阶段。但对于青少年来说,学校所设计和开展的劳动教育并没有这样的生产制度的约束,因此一般来说劳动都是非异化的。对于劳动教育而言,更重要的是设计和开发怎样的劳动教育。与过去的社会相比,学生更加欢迎具有生活性、享用性、体验性和人文性的劳动教育。[15]
第二,积极开发具有创造性,更能够挖掘当代青少年的潜力、展现青少年的创造力的劳动教育类型。这些劳动教育就受教育的主体来说,更具有可行性,对于他们的核心价值观的形成、实践能力的加强以及内心需要的激发都是至关重要的。马克思认为,“人之所以是活生生的,只是因为他进行生产活动”,人是以“运动原则”为其特征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弗洛姆由此认为,“对运动的原则不能作机械的理解,而应把它理解成一种趋势,一种创造性的活力、精力。”[16]
第三,将劳动教育的范围从体力劳动拓展到脑力劳动,从劳动本身杜绝当代青少年对“劳动”的片面排斥。在很多的调查研究中,都是一味强调青少年不再热爱劳动、排斥劳动,甚至在潜在的观念中把劳动视作非但不光荣而且“脏乱累”的代名词。对当代青少年进行劳动教育,首先应当对“劳动”本身作反思性、批判性和时代性的理解。劳动不只是体力劳动,劳动不等于劳累。由此,劳动教育应该是培养青少年实践操作能力、健康的生命观以及为学生与社会建立起时代关联而必须修炼的一门功课。
认知科学家泽农·派利夏恩(Zenon W. Pylyshyn)进一步指出,认知就是一种计算。[1]他认为,认知有机体能以自己的行为方式对自己的心理活动进行表征,而后对这些表征进行操作——展示出某种认知行为,这与电子计算机的工作原理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因此,把认知有机体的认知行为看作是一种计算行为是可行的。简言之,认知就是计算。另一位认知科学家萨迦德(Thagard P.),以更为简洁凝练的语言把认知即计算概括为“计算-表征的认知理解模式”简称CRUM)。[2]
对于改革的评判标准,丁声俊等[6]把客观实践作为衡量改革成败的唯一标准。具体表现为五个“是否有利于”:是否有利于稳定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农民收入、是否有利于保持粮食市场基本稳定、是否有利于保证国家粮食安全、是否有利于完善粮食流通新体制。因此他认为对国有粮食企业的改革促进了国有粮食企业更好的发展。董玉红等[7]认为评价国有企业是否充满生机和活力,重点要看其在决策效率和市场竞争力方面是否适应市场发展需求。
参考文献 :
[1]李凯林.与时俱进地理解“劳动光荣”的科学内涵[J].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2(2).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86-487.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3.
[4]王大犇.“体面劳动”是“劳动光荣”的基石[J].工会理论研究,2013(5).
[5][6]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50.
[7]龚为纲.当代青少年劳动价值观念变化的研究——对1146名青少年的调查[J].青年探索,2006(6).
[8]鲍忠良.青少年学生劳动教育现状的实证研究[J].教育探索,2013(8).
[9]张庆熊.“劳动光荣”:以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5(1).
[1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38.
[11]孟欢欢.体力劳动对青少年健康促进的作用及实现机制——苏霍姆林斯基“体力劳动的健康促进”思想探略[J].运动,2015(21).
[12]蔡汀,王义高,祖晶.苏霍姆林斯基选集(第4卷)[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456.
[13]列宁.列宁教育文集(上卷)[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40.
[1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4.
[15]戴家芳.论青少年社会核心价值观培育与践行的劳动载体[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15(6).
[16](美)E·弗洛姆.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A].吴晓明,王德峰.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C].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44.
From “Labor Glory ”to “Labor Felicity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ntemporary Youth Labor Values
Wang Shaoliang
Abstract : The contemporary youth’s labor values have undergone a fundamental shift,from “Labor Glory” to “Labor Felicity”. This turn is due to the social and historical changes.The society has shifted from small-scale farming to globalization. The planned economy featuring collectivism has turned to a marketeconomy based on individualism and mental labor has become the dominant form of social labor. Compared with the past, contemporary adolescents are more willing to accept the way of labor education that gives full play to one’s potential, individuality and creativity. The form of labor education enables young people to get strength and confidence from their labor, and also provide them with opportunities to show themselves.
Keywords :labor felicity; labor glory; labor education; adolescents; values
[中图分类号 ]G40-0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7947(2019)01-12-05
①[作者简介] 王绍梁,男,上海师范大学知识与价值科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编辑: 陈 宁)
标签:劳动幸福论文; 劳动光荣论文; 劳动教育论文; 青少年论文; 价值观论文; 上海师范大学知识与价值科学研究所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