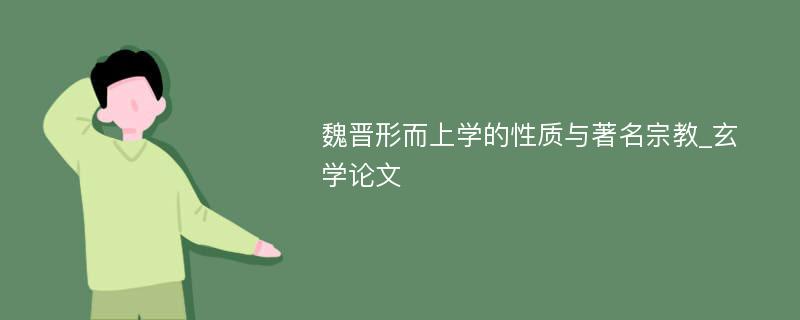
魏晋玄学之自然与名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名教论文,玄学论文,魏晋论文,自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1999)12-0090-07
汉魏时期独尊儒家经典,以名教治天下,唐长孺与汤用彤在名教问题上见解一致,认为名教包括政治制度、职官、名分、人才的配合以及礼乐教化等。(注:参见汤用彤《汤用彤学术论文集·魏晋玄学论稿·魏晋思想的发展》,中华书局1983年298页;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魏晋玄学之形成及其发展》,三联书店1955年312页。 )这种定义似乎泛指了占社会主流的文化体系,此所谓职官名分不外儒家所讲的“正名”和法家所论“综合名实”皆指向一套合乎“道”的政治制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性,汤先生就以“致太平”为名教的目的(同上书)。理想化说,月旦人物,设官分职,各尽其分而兼顾全面,如此可得无为而治。实际上,名教一经外化为规范,便有了脱离其“实”而异化的成分。而涵盖于名教中并居于基本地位的则是儒家的一套伦理规范,本文即是侧重于在直接体现儒家思想并蕴于儒家文化整体中的伦理—域商量自然与名教的关系。
唐先生在上引文中论说当时因名选才之风气,致使入世求仕之人沽名钓誉,而终使名实不符。在此,“实”不外指名背后的东西,这正是本文所谓的自然,对自然具体的理解魏晋玄学家各有不同,下文有说。而近人对自然的理解也有不同侧重,从贺昌群对儒、释、道极致不二观点看,其倾向——超验本体,(注:参见贺昌群《贺昌群史学论著选·清谈思想初论》,中国社科1985年。)陈寅恪则把经验的存在也归入自然的范畴,他在引述《后汉纪》卷二三灵帝建宁二年述李膺、范滂诛死事论略后讲到,文中虽无自然二字,但“保生遂性”即主张自然之意,名教本来是准则自然而设的,李、范虽为名教杀身,也无妨自然,因自然为本,名教为末。(注:参见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上海古籍1980年191页。 )所谓保生无非是重一经验之肉身;遂性乃指心中之性体,可与“仁”相通,陈先生没有再深究性体,与郭象相似。而唐长孺更重经验,视思想之变迁乃统治之需要,似有以偏概全之嫌。总之,对“实”的不同态度成为理解“自然”的分歧所在。
一
孔子上承周公,基于三代以后的伦理宗教,系统化了儒家思想,提出了其核心观念“仁”,仁内在于人心,作为先验的道德范畴是儒家自然观架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仁”与经验肉身之关系,至孟子才深入人性作了考察,其“四心说”划定了人与动物的界限,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寻出根据,人性虽本善,但喻于利本身无所谓善恶,乃为人与动物所共有,小人者,其善常为动物性所遮蔽。后来朱子以“理”“气”之说深究了这一看法,“性,形而上者也,气,形而下者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莫不有是气……以理言之,则仁义礼智之禀,岂物之所得而全哉?”(注:朱熹《四书集注·孟子集注》卷十一。)气即为动物性之源,人又禀有仁义礼智,人之两重性由此而明。至于人何以得如此关爱?早至三代时期“天命”观念便充斥于文献之中,似乎来自神秘力量的安排。周以降,敬德、保民成为天命的主要特征,孔子亦继承天命说,如在《论语》中有“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的说辞。正是在天命与人道之间,孔子强化了伦理内蕴的路向,也蕴育了魏晋玄学名教的思想以及宋明理学天理与人性的显在关系。传统儒家如此双重确认为后来哲学思想留下了回旋之地,魏晋玄学自然与名教问题正以此为契机。
名教在规范上偏离其根本意旨,在人表现为拒斥,是为异化。名教异化问题自东汉末年的突显在经验层面大致可归为两点,其一是当权宦官与党人名士之争触动了儒家人伦规范,“部分名士为了剪除宦官,已不惜为‘非常之谋’,即使冒易代废帝那种越出儒家道德规范的大风险也不妨干一下。”(注: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东汉末期的大姓名士》,中华书局1983年34页。)其二是选才用人制度所招致的种种弊端,《晋书》卷四十五有刘毅对曹魏始行的九品中正制的精彩批评,道出了当权者不顾才实,欲求进者货赂自通,计协登进的情状。如此弊端除与制度的不合理不健全外,在人本身应有更深层的原因。司马氏集团虽倡导名教,但其立意为一己之私与名教相去甚远,名教异化且为当时某些名士所不齿不无根据,儒家伦理本体的失落致使人们对存在产生困惑以及部分人欲为统治者的合理性寻求辩护,玄学对本体的重建便在所难免了。在学理上,杨雄作《太玄》显其后玄学思想踪迹,张衡作《玄图》以通玄远。玄学真正发端于东汉新旧经解的问题,马融开义理解经之风范,郑玄以“老”解“易”直指玄学主题,与当时章句训诂之经学的繁琐相映成趣,其内容也渐由宇宙观弥散至社会人生之域。再者,由先秦名家的名实之辩到魏晋名理学家开出的考察人物以求正名,而上溯及道家的“无名”也是一条理路。这正暗合了汤用彤先生对学风殊异的原因所作的论断:时势促成和学理的自然演进。(注:汤用彤《汤用彤学术论文集·魏晋玄学论稿·读〈人物志〉》,同上206页。 )逮荆州之学,学风更加自由,到王弼因时际会而集玄学大成。本文将就魏晋几位代表人物,侧重自然和名教问题作一讨论。
二
对名教的异化,王弼直接切入问题实质,以外儒内道的表现方式重建其本体论。
对存在论之本体和发生学意义上的本源,魏晋玄学家往往混而说之,基于老子,王弼首先明示了他对“无”和“有”的双重看重。他在《老子指略》中说“无形无名者,万物之宗也”;(注:《王弼集校释》楼宇烈校释,中华书局1980年,下引王弼话皆出此书。)而对于有形之具体经验物与无形而有名者之关系,他认为“象而形者,非大象也,音而声音,非大音也”,且大音大象有名而无形,必须借助有形之物才得以可能,“四象形而无所主焉,则大象畅矣,五音声而心无所适焉,则大音至矣”。在此,象与大象,音与大音皆属于有之域的存在,其与“无名”是一种对待关系。无与有,绝非共相与殊相的关系,而只是发生关系,王弼《老子》一章注有云:“凡有皆始于无,故未形无名之时,则为万物之始,及其有形有名之时,则长之、育之、亭之、毒之,为其母也”,以母子为喻即是发生之意。“无名”是不可言说的,但它有作为万物之源的根据,同是在《老子》一章注中说“两者皆始于母也,同出者,同出于玄也……玄者冥也”,玄冥虽名为无却非nothing。 王弼对“无名”的体认暗示了作为有名而无形之名教底蕴的终极根据。
在“有”之域,王弼认识到概念的内涵越多则所包含的事物越少,为达到对本体的认识,他认为应减损概念的内含,他在《老子》二十二章注说“转多转远其根,转少转得其本,多则远其真,故曰惑也,少则得其本,故曰得也”,对此汤一介先生认为王弼的本体“无”是把事物一切属性抽空了的无,把无内容的概念作为本体,即把没有内容的抽象存在形式作为本体。(注:参见汤一介《郭象与魏晋玄学》,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47—48页。)汤先生如此阐释是根据王弼在《老子》四十二章注说“愈多愈远,损则近之,损之至尽,乃得其极”。细考察之,此“尽”应为尽头之意,而非穷尽,因为在对概念抽象中不可能抽空一切属性,即便如此,就是取消概念而走向连形式也没有的极端,既得不出王弼的“有”也得不出王弼的“无名”。而把“尽”理解为“尽头”,概念的极致就是包罗一切的“有”了。王弼在《老子》注中也有体、用的说法,但似乎与现在体(nature)、用(function)的用法有别,如他在《老子》三十八章注说“不能捨无以为体则失其大矣,所谓失道而后德也,以无为用,则得其母,故能己不劳焉而物无不理”,在十一章注说“言无者,有之所以为利,皆赖无以为用也”。在此以无为用之“用”只能作根据解,其表现形式就是无为而无不为。
以上王弼的有无之论为其深入分析名教作了铺垫。
余英时先生把名教更简明地概括为“整个人伦秩序”,(注:参见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名教思想与魏晋士风的演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正契合于本文侧重点,王弼对此阐发了形上的根据,在《老子》三十八章注中他提出——“德”,“何以得德?由乎道也,何以尽德?以无为用,以无为用则莫不载也……故灭其私而无其身,则四海莫不瞻,远近莫不至”。显然,“德”是一种至上的人格,人由乎道而具有之,冯友兰认为“天地万物所由之宗是‘道’,人类也有它的所由之宗称为德”, (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四册, 人民出版社1986年66页。)与本文看法一致,《荀子·王制》也说“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究义之本就是德。道(无)与德的关系又究竟怎样?据王弼的有无之论,德属“有”之域,其根源非“无”莫属,二者是发生意义的关系,德在经验界借名教而显示自身。“以无为用则莫不载也”指向一无措的境界,即下文的“上德”之境。冯友兰在上引书中把无分别、混沌之境视为以无为用的极致,其根据仅是从逻辑上把有作为本体,而未达有背后的无。然而德在实践中何以可能?
王弼认为德分上下,上德无为而无所不为,即是无待。然而在社会人生中却有不能无为而为之者,表现在伦理一域就是向善,而善名生则有不善相对,下德即是仁义礼节。如他在《老子》三十八章注曰:“是以上德之人唯道是用……故虽有德而无德名也”,“下德求而得之,为而成之,则善以治物,故德名有焉……善名生,则有不善应焉,故下德为之而有不为也”,“凡不能无为而为之者,皆下德也,仁义礼节是也”。照王弼的逻辑思路,上德以无为指归,下德是有题中之义,所谓名教乃为下德的外显。下德为而成之,则善以治物,可知王弼是把下德作为治物的工具,有着很强的目的性,这与周公为保周朝的统治而上承天意开出重德、尚民意似乎一致,但在学理上经过孔孟的人文转向,下德(主要指仁)已成人内在之性体,既如此,下德亦是顺性而无为,下德中的礼较特别,往下再说。他继续提出“上仁”的概念“极下德之量,上仁是也”,上仁是王弼极力使下德合于上德的关键,由下德顺性无为一路,便成就上仁,然而此与王弼指向无名的无为有本质的不同,因上仁并无表现出对有的超越。在此义上上仁仍是有为,在伦理一域王弼并没有真正圆融有无,便退而求其次,在上仁的形式“无偏私”上做文章“爱之无偏私,故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也”。
对于义、礼,王弼在《老子》三十八章说“爱不能兼,则有抑抗正直而义理之者,忿枉佑直……故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也……尚好修敬,校责往来,则不对之间忿怒生焉,故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所谓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故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义是有以为,礼更是,王弼如此诽薄礼,却又列礼于德之域,其根据无非是礼以修敬为内容,修敬则是仁的外显,自有其神圣性。然而礼—经外显便因人经验层面的影响而可能背离“仁”。“乱之首”、“吃人的礼教”正可说明经验形式的杂染对礼之内蕴的亵渎。面对下德,王弼在《老子》三十八章注曰:“守母且存子,崇本且举末……母不可远,本不可失”。问题是,在实践之域崇其本何以可行?王弼对此也已交待,对仁,已从无偏私极其量以趋本,对已含有偏私的义,只能同仁一样退而求其次使其偏向儒家最高的仁的境界。而礼之以无为用是建立在其意蕴趋于上德的契机之上,不泥于其表形而重其内蕴,礼之以无为用才得以可能。
三
与王弼不同,嵇康、阮籍不拘礼法,《晋书》及《世说新语》多有描述,其貌似取法老庄之学,实则远没有那份洒脱,时司马氏以孝治天下,名教趋于支离,文饰虚伪,容肇祖说“阮籍的破坏礼教,亦是因为当日礼法过严,才生出这种反动的行为呵!”(注:容肇祖《魏晋的自然主义》,东方出版社1996年37页。)而嵇康除懊恼伪饰的名教外亦因于魏室有姻在先,不愿与司马氏为伍,其“非汤武而薄周孔”周遭环境是一重要原因,二人越名教而任自然(自然主义的)果真反名教吗?鲁迅也看破了此点,他说:“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渎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注:鲁迅《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见《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502页,参见《晋书》卷四十九, 中有二人“性孝”的说辞。)但二人并不驻足在忿懑与困惑,同时在学理上为自己寻找安身立命的根据。
二人虽承道家,本体论却与“道”的旨义不同,嵇康在《答难养生论》有云:“乐长生之永久,任自然以托身,并天地而不朽者”,(注:《嵇康集》殷翔、郭全芝注,黄山书社1986年,下引嵇康同此。)可见其重于“长生”、“天地”等有之域物事。阮籍更明确地在《达庄论》中说“故至道之极,混一不分,同为一体,得失无间”,(注:《阮籍集校注》陈伯君校注,中华书局1987年,下引阮籍同。)在他们,自然就是万物的整体,相当于王弼的有,而在此有与万物又只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如《达庄论》又说:“自其异者视之,则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则万物一体也”。在二人本体倾向于作为整体之有的基础上,与名教关系甚密的是其人性与人格说。嵇康认为自然就存于欲望中,故要从人性之欲,他在《难自然好学论》中说“六经以抑引为主,人性以从欲为欢,抑引则违其愿,从欲则得自然,然则自然之得,不由抑引之六经,全性之本,不须犯情之礼律,故仁义务于理伪,非养真之要术,廉让先于争夺,非自然之所出也。”显然,嵇康人性论中没有儒家的人性与动物性的区别,人之内所有的皆为自然,如果当然之德在人性中,自然也要遵从,虽然他没有明言人性是否有先验的六经之蕴。在此,他贬抑的只是犯情之礼律,异化之名教,那么,人在环境中所形成的后天之欲是否也应遵从?从他对道家的看重及对名教异化的厌弃看,他当反对。人因盲从而致的后天之欲不是自然的, 关于盲从, 约翰·密尔(John Stuart Mill)指出“现在流行着的许多意见,必将为未来时代所排斥,其确定性正像一度流行过的许多意见已经为现代所排斥一样。”(注:约翰·密尔《论自由》,程崇华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19页。)而出于自然的东西是不会流行或终结的,密尔所谓集体的暴虐即是非出于自然的公众意见对个人或少数人出于自然东西的扼杀。
复观王弼,既然其有外儒一面,亦内在认可了人的诸多应物之欲,他多次提及圣人有情,如他注《老子》二十九章说“圣人达自然之至,畅万物之情,故因而不为,顺而不施。除其所以迷,去其所以惑,故心不乱而物性自得之也。”何劭《王弼传》也有相似说法,认为圣人有情,应物又无累于物。(注:参见《三国志·魏志》卷二八,钟会传裴《注》引何劭《王弼传》。)与嵇康自然观有一致处,后来王守仁沿此一路将有情之心作为本体加以提升,开辟了与王弼“有”之层面类似的圣人之境。同为反名教异化,王弼重内道,嵇康重经验而从欲任自然,但嵇氏从欲非纵欲,如他在《释私论》中提出“心无措乎是非”,“情不系于所欲”,在《养生论》中又有“导养得理,以尽性命”之说。一方面明示了这一点,又合了道家无为而指向—“无措”的气象。
阮籍则基于—整体“有”的自然观在《达庄论》中提出了一种境界,“廓无外以为宅,同宇宙以为庐”,达到了我即万物,万物即我,浩荡恢宏,正合了冯友兰所指的无分别混沌之境。据王弼的本体论体系,这界于上德与下德之间。然而理想非现实,在现实层面,阮籍对六经作了明确的认同,《达庄论》中又有“别而言之,则须眉异名,合而说之,则体之一毛也,彼六经之言,分处之教也。”他之所以又反对名教,着实因名教在现实中支离舍本,如他接着说:“然后世之好异者,不顾其本…残生害性。”《晋书》卷四九阮籍传说他本有济世志,因当时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便不与世事。可见,阮籍纵酒以避俗世重要一点无非是以自然主义方式与黑暗秩序作抗争罢了。他这种自然主义的观点的形成除源于他当下的内心体验外,老庄之学可能是其学思的另一由来,嵇康也同样。在学理上先秦道家何以能开出魏晋的自然主义,非在此所能说清,亦与本文论题无直接关涉,暂搁一边。
四
嵇阮之放达不拘自有其特别之处,然而后来者不明其意旨,仅盲从其表面的颓废放荡而弃人性中名教之根据于不顾,与侯外庐总结魏晋清谈从谈中之理到理中之谈再到谈中之谈而趋于流弊一样,(注:参见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3卷,1957年版82页。)也必走向末流, 似有满街皆是狂禅之趣。对此,裴頠和郭象以“崇有”为进路以纠偏(其世界观或许是根本原因)。
裴頠作《崇有论》,认为无不能生有,有乃自生,“虚无是有之所遗也”,将无仍归于有的层面,“济有者皆有也”,反对以无为用。在上书中对贵无论者也有一段文辞精彩的批评,继之,以否无崇有为基点,在既化的有之域对名教加以体认,如他说:“居以仁顺,守以恭俭,率以忠信,行以敬让……斯则圣人为政之由也。”(注:《中国哲学史教学资料选辑》上册,北大哲学系中哲所注,中华书局1981年。)比之裴頠、郭象之论则精致得多,他从其独化论为入口论有无,与裴頠一样,他认为无不能生有,有自生,如其《庄子·齐物论》“夫吹万不同”注说:“无既无矣,则不能生有……然则生生者谁哉?块然自生尔”。(注:郭象《庄子注》(唐)陆德明音义,四部备要袖珍本,上海中华书局1927—1931年,下引同。)又如其注“景曰:……又得而然者邪”说:“言天机自尔,坐起无待……若责其无待,而寻其所由,则寻责无极,卒至于无待,而独化之理明矣。”所谓寻责无极,即找不到一“物”为宗,显是独化了。郭象确也在《庄子·知北游》“有先天地生者,物邪……”注中用责其所待之法,由“阴阳”、“自然”到“道”一路责寻,得出至道乃至无的结论,在此他一方面降“无”为“有”,失庄子本意,再者也回避了自尔的可能性问题,物何以自生?并且就是那个样子而非别的样子?万物独化又何以彼此相关?对后一问题,郭象也作了显示,他在《庄子·秋水》“以功观之……”注中仅把万物相关喻为“彼我相与为唇齿”,“唇亡则齿寒”,虽指出济有者乃有,却未给出本来究竟。同嵇、阮、裴一样郭象摒弃了经验存在之外的思辩,得之在末,失之在本。
这就是郭象的自然观,万物自生自性,名教因而有了存在的根据,就是人的自性,如其《庄子·齐物论》“如是皆有为臣妄乎”注说:“故知君臣上下,手足内外,乃天理自然,岂直人之所为哉?夫时之所贤者为君,才不应世者为臣……岂有违哉?”郭象也从其价值倾向性来论名教的合理性,对于人,依郭象观点可因自性中德之多寡或者说德被动物性一面所遮蔽的程度而为圣人和普通人,既然如此,名教作为圣人行为典范来规范寡德之众的道理何在?对此,郭象在《庄子·胠箧》“天下之善人少……圣人之利天下也少”注说“然则有圣之害虽多,犹愈于亡圣人之无治也”,一种紧张关系也随之凸现,即把名教理解为存在者时,名教成了化自然为合理的媒介。汤一介先生总结郭象自然观也有“天人之所为皆‘自然’”的看法。(注:汤一介同上书303 页。)而理解名教为制度或治术时则又不合于“自性”,这一紧张同样存在于王弼的体系,但依王弼本体论,此紧张可归之于经验的残缺,就郭象残缺即本体的自性说而言,这一紧张作何归属?究其原因只能是其自性说本身的问题。或可继续退让说,紧张即自然,郭象基于价值倾向,为经验社会辩护竟可作如此容忍。在民众之“自性”和社会之治之间,密尔在《论自由》中则提供了一个群己划界的思路。
进而,郭象也指出有关名教的两点不足,其一如他在《庄子·天运》“死生相与邻……”注说:“夫先王典礼,所以适时用也,时过而不弃,即为民妖,所以兴矫效之端也”,在“彼知美矉而不知矉之所以美”注说:“夫礼义,当其时而用之,则西施也,时过而不弃,则丑人也。”其二,他在《庄子·大宗师》“二人相视而笑曰……”注说:“夫知礼意者,必游外以经内,……若乃矜乎名声,牵乎形制,则孝不任诚……岂礼之大意哉?”在此,德作为人自性的一方面,其经内的根据是不变的,所谓先王典礼的根本依据也正在这里,这与成为“民妖”“丑人”的礼义也并无冲突,后者只是异化的背离其内蕴的礼义,这一点上郭氏与其他几位玄学家并无不同。如果同时他有为存在之合理性作论证的倾向,则他在《庄子·人间世》“臣之事君,义也”注所说:“千人聚不以一人为主,不乱则散,故多贤不可以多君,无贤不可以无君。”既合于他的自然观又合于此倾向,至于一人为主的种种弊端,却在他的考虑之外。
郭象扬弃了外在超验的本体“无名”而强调“自生”“自性”、“礼义之经内”,使其在人格之域呈现出一种宏扬名教的精神气象,正如他在《庄子·逍遥游》“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注说的:“夫圣人虽在庙堂之上,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乐广所谓“名教中自有乐地”正合此意。
到此,魏晋玄学虽然似乎“解决”了长久困扰着人们的自然与名教问题,但在嵇、阮二人身上所浸润的更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的东西仍在纠缠着本文的余思,“思长林而志在丰草”(嵇康语)仅仅是佯狂避世,或者仅是动物性的强势在作怪吗?当我们说它或许提醒了人的异化之时,一切又显得那么苍白,舍此,其更深的蕴义究竟在哪里?
标签:玄学论文; 魏晋论文; 人性本质论文; 老子论文; 读书论文; 国学论文; 人性论文; 晋书论文; 王弼论文; 郭象论文; 魏晋南北朝论文; 魏晋时代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