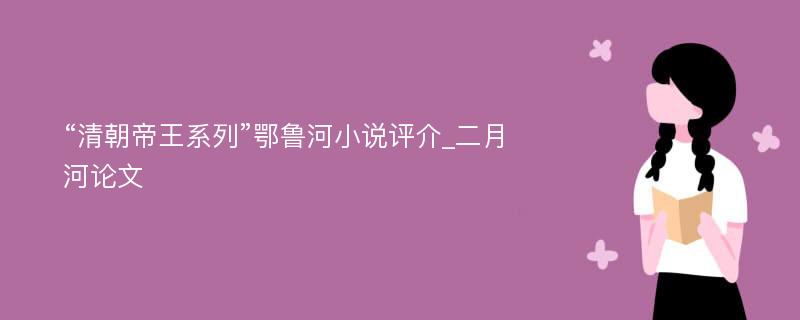
评二月河“清代帝王系列”小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清代论文,帝王论文,系列论文,二月河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时期以来,长篇历史小说的创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家作品。在这些作家作品中,二月河及其“帝王系列”有其特殊意义。二月河自80年代中期开始历史小说创作以来,迄今已出版了以清初社会历史为背景的“帝王系列”《康熙大帝》(四卷)、《雍正皇帝》(三卷)、《乾隆皇帝》(五卷)共计五百余万字,显示出其不凡的创作实力。“帝王系列”全面再现了清朝初年的三位有为皇帝康熙、雍正、乾隆的政治生活。由于作品以“正史”为基本线索,而在一些非主要人物和非重大历史事件的塑造和描绘上,作者发挥了自己独到的重构能力,并辅作品以大量的社会风情和人文景观的描绘,这就使作品既具备了“史诗”的品格,又呈现出“平民化”的特质,表现了雅俗合流的倾向。
一
中国是一个“史官”文化高度发达、历史积淀异常深厚的国度,每一历史时期都留下了许许多多宝贵的历史资料和文献,这些所谓的“正史”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宝贵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众多历史小说家进行创作的材料来源和创作准绳。近年来,人们的历史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历史的“真实性”问题在小说创作中也遭到了更多人的质疑甚至颠覆。这一现象的出现缘起于西方“新历史主义”理论的影响(这一问题将在后文论及)。不过一般来说,历史小说应该以“正史”为依据,尽可能地还原历史的真实。
既然历史小说必须遵守历史的原则,在作品中最大程度地还原历史的真实,摆在二月河面前的最大问题就是,到底以一种什么样的创作观念切入清代历史的深处。清代自康熙至乾隆历时一百三十余年,在这百余年里,清王朝经历了众多的内忧外患,政权由飘摇到稳固的艰难时期,最终把我国几千年的封建政权统治推向了最后一个辉煌,史家称之为“康乾盛世”。怎样把“康乾盛世”这一百多年的辉煌在作品中再现出来,对二月河来讲无疑是一项艰巨而又浩繁的文学工程;此外,相对于汉民族而言,清代是一个外族当权的王朝,特别是它后期的腐败和无能,给整个中华民族带来了不尽的灾难和耻辱,面对这样一个表现对象,是用狭隘的大汉族主义观点对之审视和批判,还是以历史的眼光,开放的心态进行客观的评价和描绘;如何对三位封建皇帝——康熙、雍正、乾隆——进行塑造和定位;尤其是作为历史小说,如何摆脱历史资料的规定,更深层次地去挖掘有利于展示当时社会风貌的素材,以避免小说只是干巴巴的史料堆砌,等等。这些都成为二月河“帝王系列”创作所要面临和解决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处理得合理与否,不仅关系着作品艺术品位的高低,而且也关系着作品是否具备了“历史小说”的品格。
从一定意义上讲,一部历史小说的气势是否宏大,是否具有“史诗”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是否能准确、逼真地再现当时的社会历史场面,能否在庞杂零乱的历史事件中筛选出决定未来发展方向的重大历史事件加以表现。“帝王系列”在这方面的艺术处理应该说是相当出色的。我们仅从《康熙大帝》一书中即可领略到二月河历史小说的这一特点。历史上的康熙自八岁登基(1661年)至六十九岁猝死(1722年),历时六十一年,在这六十一年时间里,尤其是其青少年时期,正值满清初定中原,政局不稳,内忧外困的时期。内有鳌拜的觊觎朝政(康熙元年),以吴三桂为首的“三藩”之乱(康熙十二年),北京“朱三太子”杨起隆领导的八旗家奴起义(康熙十二年),等等;外有内蒙察哈尔布尼叛乱(康熙十四年)、准噶尔首领噶尔丹的多次叛乱(康熙二十七年、三十五年)和俄罗斯的进犯(康熙二十二年);此外还有康熙二十年的收复台湾,等等。这些都是康熙早年在政治上、军事上的一系列重大行动。这些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作品中都有精细的刻画和描绘:无论是第一部《夺宫》中的智斗鳌拜集团,还是第二部《惊风密雨》中的平定“三藩”和与“朱三太子”杨起隆的斗争;也无论是第三部《玉宇呈祥》中的东收台湾、西平噶尔丹,还是第四部《乱起萧墙》中的皇位之争,对于这些重大历史事件,作品或正面描写,或侧面叙述,都能做到剪裁合理,腾挪有致,调度有方。小说这种在“正史”基础上的对宏大历史场面的描绘,再现了清初壮阔的历史图画,也展现出“帝王系列”的“史诗”风范。
如果说对重大历史事件的真实再现显示出“帝王系列”的“史诗”风范的话,那么对作品主要人物的精细描绘和塑造则表现出二月河对历史真实的尊重态度和开放心态。康熙、雍正、乾隆是清代,也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三个有作为的皇帝。康熙、乾隆在位都达六十余年,做了许多稳固国防,奖励生产,有利于社会安定的大事;雍正虽只做了十三年皇帝,但他在位期间国力也得到极大的加强,为“康乾盛世”的最后辉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从另一方面说,他们却是那个腐朽没落的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对于这些人物,作者以历史的、辩证的态度,充分展示和肯定了他们对国家和民族所做出的积极贡献;而且,更多从生活中入手,从多个侧面对他们的思想、行为进行描绘;同时,也不避讳存在于他们身上的种种弱点和不足。正是这些立体化的描绘,最终构成了人物鲜活的艺术生命。比如康熙这一人物,正像《雍正皇帝》中所说:“他精算术,会书画,能天文,通外语,八岁登极,十五岁庙谟独运智擒鳌拜,十九岁乾纲独断,决意撤藩,四下江南,三征西域,征台湾,靖东北,修明政治,疏浚河运,开博学鸿词科,一网打尽天下英雄——是个文略武功直追唐宗宋祖,全挂子本事的一位皇帝!”(注:《雍正皇帝》卷一《九王夺嫡》,长江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83页。)对于这样一个“一代令主”,作者除了细致地表现了他在军事上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武功外,还以较多的篇幅描绘了他政治上的文治韬略和生活中的明爽豁达。他招民垦田,修治黄淮,蠲免钱粮,厉行节约,特别是开“博学鸿词科考”,为自己网络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当然这些都是作者对他的正面描绘,为康熙这一人物形象打下了一个明亮的底色。在第四卷《祸起萧墙》中,在围绕废立太子和夺嫡谋位的问题上,作者展示了康熙性格中的另一方面:多疑猜忌、阴险狡猾、手腕多变、心狠手辣的性格特点。这种对其性格的多方面描绘和展示,也符合康熙这个有着超人才华和胆略的封建皇帝性格发展的内在逻辑。
雍正在历史和传说中是一个争议最大的人物,是一个有着“谋父、逼母、弑兄、屠弟”的骂名,和“心胸狭窄、刻薄寡恩、深沉狡诈、心口不一”的两面派作风的“伪君子”,但同时他又是一个励精图治、锐意改革、勤于政务的封建皇帝。他在位的十多年里,采取一系列措施:整饬吏治、严禁党争、废除“贱民”、发展生产、巩固边防、加强中央集权,基本上铲除了康熙末年产生的党锢之争和官吏腐败现象。他曾自言:“朕立志以勤先天下,凡大小臣工奏折,悉皆手批”。对于这样一个褒贬不一,莫衷一是的人物,作者不囿成见,以充实的历史资料为依据,不仅厘定了雍正为合法皇位继承人这一历史疑问,而且也从多个侧面塑造了雍正这位心机颇深、办事干练、腹有雄才大略,外表却又沉稳镇定、不苟言笑的“冷面王”的形象。乾隆皇帝可以说是目前影视及文学作品中出现最多,也最上镜的一位清代皇帝。他那英俊潇洒、风流倜傥、狂放不羁的品行在读者的脑海里早已形成了定势,这就为二月河塑造好这一人物带来了许多不利的因素和创作上的局限。二月河却能独辟蹊径,扬己所长。他的《乾隆皇帝》不以野史为据,不随意点染生发,不戏说历史,而是以史实为据,表现了乾隆在处理政务时的机智果断、潇洒自如,为读者塑造出了一位正如纪晓岚所言的“圣学渊深,精明强干,历世练达,都是经天纬地,一点也不亚于圣祖世宗。若论勤政,精力打熬,千古帝王没一个及得上”的帝王形象。(注:《乾隆皇帝》卷三《日落长河》,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6页。)
对重大历史事件和三位帝王的真实再现和描绘,显示出二月河“帝王系列”不凡的大气之象。但这只是支撑“帝王系列”得以站立起来的骨架,它还必须由充裕的内在“肌质”的填充才能充实活泛起来,这些“肌质”的材料同样来源于作者对清代历史资料,包括《清史稿》、《清圣祖实录》、《清世宗实录》、皇帝《起居注》等一些正统史料的深入研究,以及对《清稗类钞》之类的稗官野史的搜罗。在“帝王系列”中,作者显示出其对清代皇家宫廷生活知识的全方位掌握,诸如君臣的衣帽服饰、官廷礼仪、典章制度、食膳规律、嫔妃进御,其它还有政权机构设置、官员配置方法、权限职责范围,等等,作品都有详细交待和表现。所以,读二月河的“帝王系列”,有时犹如在读一部专业性很强的清代历史文化研究著作,这也显示出二月河自称的“半个历史学家”的深厚学养。
二
既使是作家严格按照史实来进行写作,也只能是其在“接近”历史状态下对历史的自我重构。因为历史是不可能“复制”的,所谓“历史的真实”也只是小说家在一定的历史史实基础上的文学操作,它永远也摆脱不了作家主观意识的规范和制约。钱钟书先生讲的“史家追叙真人真事,每须遥体人性,悬想事势,设身其中……庶几入情合理”(注:《管锥篇》,中华书局1979年8月版第166页。 )。便非常形象地说出了历史真实与作家主体意识参与创作之间的关系。而且小说之所以是小说而不是科学报告或历史著作,也就在于作家可以运用历史提供的有限知识和资料,进行艺术形象和社会生活的重构和创造,以使作品达到“艺术的真实”。
历史小说说到底是小说家根据一定的历史资料进行的虚构和创造。虽然二月河的“帝王系列”在总的特征上是对清初重大历史事件的再现,但在一些细节方面,诸如对一些有争议的历史事件的结论和评价上,对次要人物的塑造上,以及对小说文化品位和深层意蕴的表现上,仍然显示出其独到的见解和重构力。在历史传说中雍正是一个“矫诏”夺位,恶贯满盈,终被江湖女侠吕四娘所杀,身首异处的暴君形象。即使是在目前国内史学界,对于他的评价也是毁誉参半的,特别是他在谋得“大统”之位的方法和手段上,即他是勾结隆科多篡改康熙遗诏,还是如遗诏中所言:“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的正当皇帝,更是说法不一。在《雍正皇帝》一书中,作者通过对诸多正史、野史,以及民间文学和传说的条分缕析,探幽烛微,艺术地再现了康熙临终之即那惊心动魄的一幕,并把作者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结论形象化地展示了出来。作品不仅得出了雍正合法皇位继承人的结论,而且也使这一结论在具体历史场景的演示下显得更加真实可信。这是作家发挥自己的艺术想象力,对历史进行自我重构的结果。虽然目前史学界在谁为康熙合法继承人的问题上仍然分歧较大,有关康熙“遗诏”的真伪也是见仁见智,不能统一,但《雍正皇帝》对此事件的形象描绘和分析,从文学的角度上对史家也是一种参考。
二月河在他的“帝王系列”中,除了对重大历史事件进行自我认知的重构外,还以独特的方式,在自己擅长的领域表现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和重构力。他的这种对传统文化的重构主要体现在他所塑造出的一大批“士”人形象上,其中包括伍次友、周培公、高士奇、熊赐履、张廷玉、刘墨林、邬思道、方苞、曹雪芹、贾士芳,等等。作品细致地描绘了这些封建文人,在儒道释三种人生哲学的长期培育下所形成的思想和行为方式。他们都是在几千年封建正统文化的熏陶培育下成长起来的,一个个满腹经纶,才力过人,诗词歌赋无所不能,圣传义理无所不精。在他们身上鲜明地体现着传统文化的精髓和实质,出将入相,佐君勤王的儒家积极“入世”思想成为他们人生意义的最高准则和目标。然而,这些文人,他们大都是汉人,在一个外族当权的时代,他们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他们虽都有积极“入世”的愿望,却又时常处在“伴君如伴虎”的旦夕危险之中。因此,儒家文化中积极“入世”的进取精神与道释文化中消极“出世”的明哲保身态度的矛盾一直在他们身上鲜明地体现着。当他们在生活上、政治上一帆风顺的时候,“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就占据上风,他们不甘寂寞,努力进取,意欲在险恶的政治舞台上一展英姿;当他们在生活上、政治上失意时,往往或退避山林、修身养性,或浪迹江湖,追求自我与自然的和谐;有的甚至皈依佛门,万念皆空。作品中的伍次友、周培公、高士奇、邬思道、曹雪芹等人,无不在他们的命运到达极致时,走上“宁静”、“无为”的“出世”之道。
儒与道是支撑中国传统文化主体的两大柱石,也是中国古代文人处理政治事务,应对猝然巨变的理论依据。这种进可攻,退可守的圆滑哲学也培养出了一代代封建政治的牺牲品。二月河在作品中对这种文化特征的理解和表现是颇有见地和深刻性的。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二月河以自己的眼光和标准对儒道学说作了自我新的阐释和再现。像熊赐履、张廷玉、邬思道、方苞、曹雪芹等都是有稽可查的,但基本上只是只言片语的记载,其生平事迹大多都语焉不详,这恰恰给二月河提供了充分发挥自己艺术想象力的机会和条件。作品中的这些人物,他们处事精明,机敏过人,本该在政治生活中大显身手,但最终都摆脱不了命运的捉弄,过早地退出了政治舞台。这是否也代表了二月河的人生态度和世界观呢?其他人物像伍次友(无此友)和高士奇,这两个完全虚构的高“奇士”,都是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文人形象。一个沉稳持重,一个狂放不羁,他们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类型的封建文人形象,并且都深得皇帝的厚爱与恩宠,也同样没能摆脱退出江湖,归隐山林的结局。应该说这些文人形象只是二月河对传统文化认知和再现的心理符号,从这些文人的最终遭遇不能不说是二月河的“心性”使然。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二月河这种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形成?二月河有段自述颇能说明问题:“我确实有‘出世’的思想……这种意识在作品中不可避免要流露出来,作品中那个人物一旦红极了,我就‘宰’他,或让他掉下来。这种意识也是道释两家的那种自我超脱,我在这里寻求一种精神上的安慰,一种超意识的情感。”(注:《卧龙论坛》,1993年第4期。)二月河的这种“超脱”意识,使他在作品的政治权力斗争中看到的更多是人与人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这种意识也决定了二月河“帝王系列”的基调是沉重悲惨、鲜血淋淋的。
众所周知,二月河的“帝王系列”主要以场面宏大,描写社会时代风云的诡谲变幻见长,它更关心对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的再现与刻画,但作品对政治斗争的险恶、人际关系的淡薄、权谋机变的微妙、君臣兄弟的倾轧等方面的描写也可谓是玲珑剔透、惟妙惟肖。尤其是对宫廷之内的皇储皇位之争的再现与重构,不仅表现出二月河在处理重大题材方面手法的老到和成熟,也显示了二月河对这一问题所包含实质的思考。因此,我们在作品中看到的皇储皇位之争,时时处处隐含着险恶、阴谋、欺诈。这固然是作者依据历史事实创作的结果,但我们也不能忽视了作者主体意识进入作品后对作品基调的制约作用。在这些宫廷斗争中,康熙为了保全自己的皇位不受侵犯,可以将亲儿子——太子允礽再废再立,最终使其“复以罪废,锢于咸安宫”;允禔为谋得太子之位,以镇魇之术加害与他构成威胁的兄弟允礽;而雍正在夺得皇位之后即囚禁了与他同为兄弟的政敌允禵、允祀等人。这一如作品中康熙所讲“天家本无骨肉之情”。这些事件本身来源于史料,但在这些史料的加工处理,和具体细节的操作上,我们不能不把它归因于二月河丰富的艺术想象力和创造力,这也是二月河“帝王系列”对历史文化进行重构的具体表现之一。
概而言之,“帝王系列”对一大批封建文人的行为、心理、思想特征的表现和描写,体现出二月河对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深刻理解和把握,这是这一系列作品颇具文化品位的支点;作者通过对宫墙之内、帝王之家皇储皇位之争的描写,更是把自己对历史文化的认知和重构延伸到造成这种文化特点的根处,从而揭开了罩在生活于那个社会环境里的人们脸上的那层温情脉脉的面纱。从这一意义上讲,二月河对这些历史文化特征的揭示与重构具有“醒世”的作用。
三
二月河是一位旗帜鲜明地声称自己是为了大众写作的历史小说家。他在谈到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时讲:“我认为两者是可以统一的。如果必然要得罪一边的话,我得罪资料,在不违背大的历史史实的原则下,那些小的历史史实我并不拘泥,因为我必须讨好我的读者。”(注:《卧龙论坛》,1993年第4期。)不拘泥于历史史实并不等于不尊重历史史实,而是说出了二月河对艺术真实的自我建构能力,也反映了他“必须讨好我的读者”的“平民化”写作倾向。不善于“包装”自己,也从不写“创作谈”的二月河以作品与读者展开了对话。他的这种“平民化”写作与那种生怕一旦沾上个“俗”字就会坏了自己一世的英名,更怕有损于自己作品品位的思想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在这种“平民化”艺术观念的支配下,二月河在“帝王系列”中,以独有的方式向读者展示了他的“平民情结”。
中国的历史小说缘于古代的“讲史”,是从史传中衍生出来的通俗文学形式。虽然作者有时一再声称自己所写的故事是有根有据的,但小说仍然被看成是稗宫野史,不能加入到诸如诗词歌赋之类的所谓“正统”文学中去,它的阅读对象和范围多被限制在市井百姓之中,这就决定了历史小说从一开始就是大众的、通俗的。这种小说形式的最大特点就是采用章回体制,每章有回目,以概述该章内容,结尾有套语,以起承前启后的作用,很适合大众的阅读欣赏口味。二月河“帝王系列”的“平民化”写作特点之一,就是作者能根据大众欣赏习惯的需要,适当地采用章回体这种大众喜闻乐见的,也更能显示自己创作个性的艺术形式。
鲁迅先生认为小说源于休息。他说:“人在劳动时,既用歌咏以自娱,借它忘却劳苦,则到休息时,亦必要寻一种事情以消暇。这种事情,就是彼此谈论故事,而这谈论故事,正就是小说的起源”(注:《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1月版第302页。)。鲁迅先生的这段论述很明确地提出了小说的娱乐消遣功能,也说出了小说源于生活的平民化、大众化特质。作为这种平民化、大众化特质的特点之一的章回体制,也是为适应这种特质的要求而出现的。心系大众的二月河对于在市民阶层中耳熟能详的传统形式不会熟视无睹。从一定意义上说,是章回体这种传统化的艺术形式选择了一直坚持“平民化”写作的二月河。这种艺术形式在现当代的小说创作中已很少见到,这不能不说是二月河“帝王系列”“平民化”写作的特色。
以细腻的笔法在作品中描绘出一幅清初社会的市井风俗画,是二月河“帝王系列”的另一特点,也是二月河“平民化”写作的又一特征。虽然二月河的“帝王系列”是以展示“康乾盛世”的百年辉煌历史见长,但作品并不拘泥于对历史的再现与重构。在二月河看来,如果小说仅以展示历史为主,势必会使作品成为枯燥乏味的历史演绎,这也会削弱小说的可读性,必须配之以大量庞杂的其他东西和材料。因此,他在再现与重构历史的同时,还不惜笔墨精心描绘当时社会的市井民情风俗。庙堂之高,江湖之远,无不被他尽收笔底。他力图在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多侧面地展示出“康乾盛世”的社会历史和人文景观。作品这种波澜壮阔的历史场面描绘与生动逼真的社会风俗画卷的融合,使“帝王系列”又带有“世情小说”的某些特点。这一特点在《康熙大帝》和《雍正皇帝》中已有所展示,在《乾隆皇帝》中,随着清代国力的增强和社会的安定,以及城市化、市俗化的出现,小说的这一特点也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作品对清代的饮食服饰、里巷杂业、蓬门荜户、宫廷庙堂、典章文化、礼仪乐章、青楼红粉、勾栏瓦肆,五花八门无不展示,三教九流、七行八作无不涉及。因此说,读二月河的历史小说,既是一定清代历史知识的学习,有一种历史的苍凉感和纵深感;又是在欣赏一幅清代的《清明上河图》,给人以审美的享受。
对众多知识性素材的展示和运用,显示出二月河的丰富阅历和多才多艺,这也是构成二月河“帝王系列”“平民化”特征的主要因素之一。曾经是军人出身的二月河,在对待作品的态度上并不像一些“科班”出身的作家那样,非要将自己多年的学术研究成果赋之以形象,写出一部专业性很强的历史小说。他的知识大多来自“课外”,来自他多年的刻苦自学和积累。他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自己是个“杂家”,这也算是他的夫子自道。这种“杂”就表现在对知识性素材的运用上,由研究《红楼梦》起步,最终闯入小说创作领域的二月河,在从事创作之前的数年里进行了大量的阅读准备工作,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学名著和《二十四史》、《清史稿》这样的正统历史著作自不必说,就连一些枯燥乏味,让人望而却步的论著,如五经四书、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医学棋艺、天文地理、麻衣神相、奇门遁甲,等等,他也都广泛涉猎。这些材料和知识在他日后的创作实践中都能适时地予以表现,而且不给人以生硬突兀,卖弄才情之感,反而给作品增添了可读性和无穷的趣味性:《雍正皇帝》中对贾士芳法术的描绘,作者俨然是一位道行高深的气功大师或武林高手;《康熙大帝》中对康熙病理的分析和药方的处置,作者又像是一位医术高明的江湖郎中;对皇家膳食的配料和制做过程的详细介绍,使作者又像是一位能做宫廷大宴、满汉全席的美食家;而作品对诗词歌赋、散曲的穿插运用,以及对高士奇歪诗戏诸儒的描写,使作者又像是一位才高八斗,却又怀才不遇的落第文人,等等。这些描绘亦庄亦谐,令人时而捧腹,时而叹息。
当看惯了那些板着面孔却又振振有词的历史说教之后,再回过头来看二月河的“帝王系列”,确实有一种赏心悦目的轻松感。这种轻松感是非常适合大众的欣赏心理的,也符合二月河“必须讨好我的读者”的创作思路。这并不是作者媚俗或从众,而是他抓住了从来历史小说的平民化、通俗化的特点,并把这一特点发挥到极致。而且,作者对这些知识性材料的运用,并不是把它们与整个作品割裂开来,孤立地铺陈演绎,而是时时刻刻把它们放在与作品情节发展有必然联系的内在逻辑之中,使之与整个作品融为一体,使整个“帝王系列”产生出举重若轻的情韵。
这一特点的出现,是二月河广泛吸收借鉴古今中外优秀文学遗产,尤其是我国古典文学遗产,并使之与当前社会生活紧密统一的结果,使读者在阅读时产生借古鉴今的审美心理效应。如作品中诗词歌赋的大量出现显然是受古典名著《红楼梦》的影响和启发;《乾隆皇帝》中对新科状元庄友恭中状元后喜不自禁,以致痴迷颠狂的传神描写,使我们马上想到《儒林外史》中的范进中举后的丑态;《雍正皇帝》中盐漕两帮追杀争斗又有金庸小说的影子;而《乾隆皇帝》(卷一)对贺露滢被害案的描写,又使作品带有公案小说的特征,等等。这些情节与事件的加入是作者对正史资料的补充和延伸,也是作者对古今优秀作品的借鉴与“戏仿”,为“帝王系列”增添了无穷的阅读乐趣。如果读者再对作品深入理解的话,还会轻易地发现“帝王系列”对诸如马踏宴席,贺道台死因等一些事件和场面的描写中,还蕴含着更深一层的意蕴。
四
二月河的“帝王系列”,既尊重历史,尽量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书写,又不为历史所局囿,在一些非主要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上敢于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更主要的是,尽可能多地借鉴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学传统和文学遗产,在作品中展示所反映时代的社会历史文化和人文地理景观,从而使作品产生出雅俗共赏的艺术效果。这也是本文总结出的二月河“帝王系列”的三个主要特征。与时下某些以一部作品一炮走红的作家不同,80年代末就已出齐《康熙大帝》四卷的二月河当初并未能得到国内文学和评论界的青睐,只是当他的作品在几年内十几次再版,盗版更是铺天盖地,他本人也被港台评论和新闻界誉为“文坛一杰”之后,他才真正引起国内评论界的注意。这种“墙内开花墙外香”的情形可谓是国内文坛的“二月河现象”。这一现象从另一方面讲也是“帝王系列”雅俗共赏品格的反证。“帝王系列”所以能受到读者和评论界的好评和厚爱,主要是因为作者在创作中较好地处理了以下几组关系。
第一,历史与艺术的关系 毫无疑问,历史与艺术的区别主要在于,历史是历史学家根据有限的知识和史料进行的理性判断和认识;而艺术则是艺术家根据有限的知识和史料进行的形象创造,并由此勾画出艺术家自己心目中的图像。两者都是从“知识”和“史料”出发,依据不同的手段和思维方式达到了再现历史的目的。历史与艺术的这一不同特征决定了历史著作与文学作品之间相辅相成,互相依托的关系,同时也决定了文学作品是与历史属于不同的体系,有各自相对独立性的特点。
应该看到的,是在“新历史主义”“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观点影响下,近年来历史小说的创作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历史的真实性遭到质疑,创作前必要的历史资料准备和考订工作被潇洒地略去,历史仅仅成为作家精心制作节目时的帷幕和道具,作家们凭借这一道具,在历史的帷幕上任意地涂抹出一个个由血与泪、刀与光、情与仇共同交织而成的现代图画,历史的严肃性与庄严性在这种颇具当代意识的言说过程中被消解殆尽;而另一方面,一些作家“固守”历史的阵地,在创作中严格按照历史的真实书写,即使是一些次要人物和事件也不敢稍加穿凿,这种历史小说固然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历史的真实,却失却了文学作品应具备的艺术的光辉,使作家作品成为了史料的附庸。
对以上两种创作倾向的得与失,我们不能在此妄下结论。不过,除此之外历史小说创作还有没有第三条路可走?即除了再现与重构之外,作家是否还有所作为?二月河的“平民化”写作为这一问题做了回答。也可以说,“帝王系列”的“平民化”特征是沟通历史与艺术的桥梁。它吸纳了历史小说以“正史”史料为依据的历史小说本质,又接受了历史小说源于民间,为大众服务的特性,结合作者自己多方面的深厚修养,为历史小说的当代性提供了存在的依据。历史的真实在“平民化”的激发下不至于呆滞,艺术的想象在“历史的真实”的规范下更显出生机,形成历史与艺术之间的张力。
第二,雅与俗的关系 雅与俗是文学创作的一对矛盾,但也决非水火不容。恰恰相反,它们是互为依托相生的关系。没有雅就没有俗;反之,没有俗更何谈雅。当然,它们也并非"1+1"的简单相加,而是相互渗透,互为融合的一体。很难想象,失去了俗的支撑的所谓雅文学的面目会是什么样;同样,没有雅的存在的俗文学又会走向何方。
既然雅与俗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的,在创作中就没有理由将它们割裂开来,对某一方面做片面的追求或夸大。这种情况在当代历史小说创作界还是普遍存在的。作家大多对“俗”讳莫如深,为避“俗”甚至不惜牺牲历史小说的大众化特性,更注重在小说的艺术形式和表现方法上寻求变化。这固然是小说“雅”的表现,但也容易使历史小说走上“雅”的极端。
历史小说的“雅”并不只表现在采用何种表现方法和艺术形式上。譬如长期以来被公认为通俗小说的标志的文体——章回体,也并不一定都是俗文学的专利,决定其文学价值的关键还要看作品所反映出的思想内容如何。我国古典名著《红楼梦》采用的是章回体。从内容讲,它讲述了发生于宝黛钗之间的一个凄迷哀伤的三角爱情故事。俗人爱看俗故事,它适应了大众的阅读欣赏口味,具有俗文学的特点。但《红楼梦》所反映的决不简单是一个才子佳人式的恋爱悲剧。它的深层意蕴在于,通过这一爱情悲剧,揭示出了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封建统治阶级必然崩溃的历史命运,展示了封建家长对青年人理想和爱情的毁灭与摧残,也表现了青年人崇尚自然、追求个性解放的民主主张和要求,等等。这就不是通俗小说故事曲折、思想浅显的特点所能涵盖的。反观二月河的“帝王系列”,作品在章回体形式的包裹下为读者设计出了一个个惊心动魄的故事和场景,并通过这些故事和场景,反映出了作者对发生于宫墙之内的倾轧(封建政治的残酷与险恶),人与人的勾心斗角(对人性的展示),以及作者对传统文化支柱儒道释互补现象的理解与认知,等等。而且,作者在作品中对古典诗词歌赋及散曲的大量运用和穿插,使作品更具文人气息。有论者称“帝王系列”有“《红楼梦》笔法”,原因概出于此。“帝王系列”最值得称道和总结的,也就是它在艺术上雅俗共赏的品格。
第三,历史与现实的关系 历史小说如何与现实沟通,如何表现当代意识,是历史小说必须面对和回答的问题,也是历史小说创作中必须处理好的关系。创作界对此也是有深刻教训的。“文革”前十七年历史小说创作受到时代政治的影响和局限确实很大,一些作品在极力表现现代意识的同时,却不自觉地淹没了自己的思想及其艺术个性;与此相反,80年代中期崛起的“新历史小说”派又走上了另一个极端,作家在尽心展示作品的现代意识和自我思想时,却忽略了历史小说最基本的品格:历史的真实。把历史只是当作一块橡皮泥任意地扭捏把玩,这种对历史的真实可以忽略不计的颠覆行为,使历史小说的历史意识完全失去了意义。
二月河对历史与现实关系的处理是从他的历史观念入手的。在他看来,“一个朝代的兴衰与它的‘气数’有关”(注:《卧龙论坛》,1993年第4期。)。他的这个多少有点“唯心”成份的思想,实际上也包含了辩证法的物极必反,盛极必衰的观点。所以,他的创作更多的是关注历史的深层内涵,以及人作为一个生命实体的存在与意义,更注重从历史的深处揭示出其文化的内涵。他在尽可能尊重历史真实的同时,更希望借历史以回答今天的事,给人以历史的借鉴。他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如果各个阶层看了(“帝王系列”)都有一些自己的感受,那对社会就是一种贡献,我的用心是善良的。”(注:《卧龙论坛》,1993年第4期。)二月河历史小说的这种“镜子”说,是他在作品中真实再现历史的基础上,广泛研究了大众阅读心理之后得出的结论。它既与现实有密切的联系,由于有历史真实的规范和制约,又使这种联系之间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从而产生出艺术美感。
标签:二月河论文; 康熙论文; 历史小说论文; 文学论文; 艺术论文; 文化论文; 康熙帝论文; 历史知识论文; 乾隆论文; 雍正皇帝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