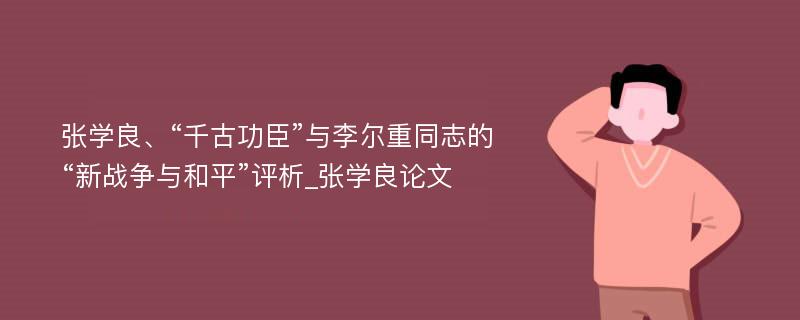
“千古功臣”张学良——兼评李尔重同志的《新战争与和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争与和平论文,功臣论文,千古论文,同志论文,张学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品评论
李尔重同志的《新战争与和平》,是一部正面描述中国抗日战争的恢宏巨著。
中国的抗日战争,正式的提法,始于1937年的“7·7事变”。实际上,自从1931年“9·18事变”,日寇不宣而战,迅速占领我东三省,中国人民抗战的序幕已经拉开。从“9·18事变”到“7·7事变”,中间相隔6年,与8年抗战一起,两者相加,共是14年,构成了一部完整的中国抗日战争史。
李尔重同志的《新战争与和平》即是从1931年“9·18事变”写起的,这符合历史的真实。至1937年“7·7事变”,一共写了4大部,占全书总篇幅的一半。后面又写了4部,正面描述中国的八年抗战,前后相加,共8大部,构成了一幅完整的中国军民抗战图。
在《新战争与和平》的前4部中,即从1931年“9·18事变”到1937年“7·7事变”的这6年当中,有一个关键性人物始终活跃在作者的笔下,这个人物就是张学良。
历史上的张学良,绝不是一个单一的、平面的人物:他是土匪出身的大军阀的公子,习过武,又进过洋学堂;当过割据一方的“东北王”,又是国民党军队的一级陆军上将;打过日本兵,又围剿过红军;冒死向蒋介石实行“兵谏”,又自动放虎归山,甘愿身遭囚禁。这样一种复杂的经历和矛盾多变的性格,正是文学家所钟情的写作对象,因为它最具典型性,又是文学家最感棘手的描写对象,没有高超的技艺,驾驭不住人物,就极易走偏。对李尔重这样的具有很高的政治修养和文学素质的作家来说,这种复杂的经历和矛盾的性格却正是他施展才华的地方。对中国抗日战争历史的深入研究,决定着他对这段历史中的风流人物的关注和偏爱,张学良便是其中的一个。在《新战争与和平》中,他那支如椽巨笔始终追寻张学良的行踪不放,并在他的身上倾注了极大的热忱。尽管自1936年12月25日,张学良从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消失了;尽管自第4部以后,张学良从李尔重的《新战争与和平》中消失了,但是,张学良的影响仍在,“西安事变”的余波仍在,这个人所一手制造的历史事件,震惊中外,甚至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从而使他与事件一起脱颖而出,成为《新战争与和平》的众多历史人物中力透纸背的一个。
这就是张学良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这就是张学良在李尔重同志的《新战争与和平》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历史唯物主义与爱国主义
张学良作为一个历史性人物,注定是要与重大的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的。在《新战争与和平》中,张学良的性格成长与历史事件的进程同步展开,在历史事件中刻划人物性格、塑造人物形象是作者应用的主要写作方法。作为历史题材的小说,它首先要求作者对人物大量的历史实践活动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筛选,即作出自己的正确判断,其判断的标准有两个,即“价值判断”和“艺术判断”。支配价值判断的是作者的政治修养,它决定着人物形象的最基本特征的建立。李尔重在对大量的史料进行价值判断时,始终坚持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它的分析方法。这种观点和方法,使他可以从哲学的高度,对历史做整体的、辩证的、合乎逻辑的观察和梳理,可以说,历史唯物主义是李尔重美学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过这样的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价值判断,作者得出的结论是:张学良艺术形象的基本特征,应该是,也只能是爱国主义的,即面对张学良复杂、矛盾的性格,必须突出地将他作为一个正面人物来加以描写和刻划。恰恰是在前几年,在一片“张学良热”中,那些专写张学良情场艳史、官场角逐、军阀交恶的作品争相出现时,作者不为所动,牢牢把握自己的创作原则,坚持自己做出的价值判断,没有丝毫放松,这是难能可贵的,它表现出了作者政治上的坚定。“艺术判断”,即艺术地把握历史,这是一个将客观的历史加以审美意识化的过程。在这里,作者赋予不同时期的张学良的爱国主义以不同的内涵。同样是爱国主义,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条动态的、发展的曲线,作者对张学良的性格描写和形象塑造,是在这样一条曲线中得到最完满的体现和最终完成的。
张学良爱国主义的发展曲线,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即依次经历了从“保家”,到“卫国”,再到“事变”这样三个不同的层面。
“保家”是张学良爱国主义发展初级阶段的主要特征。作者集中描写了张学良的三件事:1、易帜换旗(由五色旗换成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归顺南京中央政府。2、摒退东北军中的日本顾问,阻止日本人依据“二十一条”在东北境内铺设铁路。3、诛杀前朝重臣杨宇霆、常荫槐。这三件事,历史有载,件件具实,是对日本军国主义者依靠满蒙,挥师南进,鲸吞中国的战略的沉重打击。但作为东北军的最高将领,此时的张学良还未能充分地、自觉地意识到自己肩负的历史重担,面对虎视眈眈、步步紧逼的日本侵略军,他主要顾虑的还是祖上传下来的偌大一片家业。为保护自己的领地不受侵犯,他只是被动地虚与委蛇,层层设防,不敢有丝毫懈怠。这时,张学良的爱国主义还处在自卫本能的层面,基本属于“保家”的范畴。
在第二发展阶段上,张学良从初期的“保家”,逐渐走上驱逐日寇,收复失地的爱国主义道路。在这个阶段,与其说作者重点写的是历史活动,不如说更多描述的是人物的心境:张学良率30万大军,不战而退,置东三省和三千万同胞于日寇铁蹄之下而不顾,自觉心中有愧,终日遭受着良心的责难;他顶着“不抵抗将军”的恶名,遭国人唾骂,替蒋介石背黑锅,但又感到极大的委屈,时刻忍受着精神的折磨。这如同一柄双刃剑,每一面都在刺着张学良的心。但这一刺,刺出了张学良对爱国学生运动的同情、支持和保护,对围剿红军、进攻苏区的抵制和抗拒,刺出了他打回老家去,拯救父老乡亲于水火的强烈要求和坚定信心。历史的巨变将张学良从一个单纯“保家”的地方军阀变成一个怀有“家仇”和“国恨”的国民党爱国将领。这既是历史的成因,也是张学良的性格使然。从“保家”到“卫国”,张学良的爱国主义经历了一个飞跃。尽管在这一阶段作者没有更多重大的、典型的历史事件的记叙,但对张学良心境的细微刻划,却预示着历史更深刻和惊人的演进。这里作者运用了一个细节描写,写的是一个皮夹子,里面深藏着蒋介石向张学良下达的“力避冲突”、“不予抵抗”的两纸电令。张学良将皮夹子贴身而放,时刻不忘撤兵失地的耻辱,每当委屈难平、激愤难忍时,便取出看上几眼,又咬紧牙关,再揣回去。这种借用物件所做的细节描写,在全书并不多见,这里是仅有的几处之一,但从一个薄薄的皮夹子所反映出来的张学良的内心世界,却是极其丰富的,它形象的告诉我们,屈辱之心蕴含着巨大的能量,一旦爆发出来,便可酿成惊天动地的大事件。
“西安事变”爆发了。“西安事变”是张学良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也是他的爱国主义精神最完美、最充分的体现。尽管从“保家”,到“卫国”,直至“事变”是这条爱国主义曲线发展的必然轨迹,可谓瓜熟蒂落,但这个事件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所占有的重要地位,比及它那戏剧性的进程和结局,却一直为历史学家和文学家所津津乐道。历史学家关注的是它的结果:由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蒋介石被迫停止和放弃了在全国范围内对苏区和红军的大规模武装“围剿”。以全面内战的基本结束为标志,国共两党实施了自十年内战后的第二次合作。历史在这里出现了一个转折,中国的抗日战争从此开始了一个新的局面。文学家关注的是它的过程:这个充满戏剧性的事件是张学良一手导演的,从始至终都涂抹上了强烈的张学良个人性格的色彩,是张学良性格最集中、最完整的显现,以至可以说,没有张学良,就没有“西安事变”,张学良成了“西安事变”的代名词。作为政治家和作家的李尔重,是从历史的和文学的双重角度对这一事件加以关照和表现的。他将张学良这样一个艺术形象,放到“西安事变”这一典型的历史事件中去加以塑造,从而使张学良形象中的基本特征——爱国主义得到了更鲜明、更丰满、更具有特色的表现,成为区别于其他众多国民党高级将领的“这一个”。作者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来叙述事件的全过程,并为事件的爆发做了充分的行动上的铺垫——浓墨重彩地描写了张学良在事变前的半年之内连续向蒋介石做出的“四谏”:桂林诤谏、洛阳(大寿)直谏、洛阳苦谏,最后破釜沉舟发动了西安兵谏。如果说从“保家”到“卫国”再到“事变”是一个大的循环圈,那么这“四谏”则是大循环圈中最后时刻的小循环圈,大环套小环,环环相扣,水到渠成,“西安事变”就是在这样历史的、逻辑的进程中完成了。在对张学良艺术形象的塑造和性格的刻划中,“西安事变”占去了一半以上的篇幅,是作者花费笔墨最多、耗费心血最多的地方,在《新战争与和平》中,它是一个重点,一个高潮,无疑也是全书写得最精彩的地方之一。
恩格斯说过:观点应该隐蔽起来,倾向应从场面和情节自然流露出来。李尔重善于选择最重大的场面和最关键的情节来刻划人物性格,塑造人物形象,把人物放在历史的、命运的转折关头来加以表现,因此,他笔下的人物具有深沉的、真切的历史感,显示出厚重、沉稳的特色。对于《新战争与和平》来说,这种厚重、深沉的历史感是必不可少,甚至是须臾不可或缺的。它带给读者的,是对战争与和平这一永恒主题的思考,是对人类命运和个人际遇的追寻,它使这部巨著具有了“史诗”的品格。同时,在这深沉的历史氛围中,又始终高扬着一种精神,这就是爱国主义精神。这种爱国主义精神是张学良艺术形象的基本特征,又是贯穿全书的一条主线,没有了这条主线,李尔重的《新战争与和平》便失去了灵魂;背离了这条主线,张学良便不再是《新战争与和平》的张学良,不再是李尔重笔下的“这一个”,而是野史的张学良,演义的张学良,戏说的张学良了。可以说,对张学良爱国主义形象的塑造,集中体现了作者对历史所作的正确思考和对《新战争与和平》主题的准确把握,具有着历史的和现实的双重意义。
二、阶级本性与历史真实
人类发展的历史屡屡证明,一个人性格的形成和发展,终究是与阶级出身、所受的教养和社会影响联系在一起的。张学良也不例外。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时刻,爱国主义是张学良性格的主体,也是作者塑造张学良艺术形象的基本特征。但是对张学良这样一个复杂的人物,那种单一的表现、静态的描写、切刈的刻划已不能完满地解释存在于张学良性格中的各种矛盾现象,用这种方法塑造出来的人物形象难免是苍白的、单薄的。因此,作者在以正面人物为基准塑造张学良的爱国主义形象的同时,也不回避他的性格的矛盾多变的一面,并注意揭示他性格中的弱点、缺陷和消极的地方。
张学良出身大军阀家庭,从小养尊处优,颐指气使。成年后,长期周旋于上流社会,并以东北最高行政长官和军队高级将领的名份跻身国民党上层统治集团。这样的出身、经历和社会影响,必定要在他的性格中留下深深的烙印。这是阶级的烙印,是很难将它轻易抹掉的。在张学良的命运的关键时刻,在他的性格与生活撞击时所迸发出的火花中,它总要顽强地显现出自己的影响力来。这就使张学良的性格带有了一种局限性,这是历史的局限性,阶级的局限性,是一些带有根本性质的局限性,是人物难于超越的。在《新战争与和平》中,作者对张学良性格中所固有的这种局限性进行了直接的、明确的展示,其中比较典型的有这样几个:
作为同一阶级、同一营垒的人,张学良对蒋介石尽“忠”尽“义”,行君臣之礼。从国外考察归来,是他第一个提出要效仿意大利法西斯的作法,用“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统一中国,拥戴蒋介石为领导全国抗日的“伟大领袖”。
张学良奉命“围剿”我陕甘边区,亲率10万大军进犯,被红军吃掉两个装备精良的主力师。消息传来,他痛心疾首,气急败坏,大骂败逃而归的军长无能,扬言要“枪毙”他。
对蒋介石封官许愿、拉拢利诱、恩威并用、软硬兼施的两面派手法,张学良始终未能认识清楚,虽然有所警觉,却一直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以至他对蒋介石的认识,在许多地方甚至不如赵四小姐,不如杨虎城,不如他的幕僚和下属来得更清醒和深刻,最终,他未听从周恩来的劝告,怀着一腔热血伴蒋而去,遭受终身监禁。
在这些地方,出现的是另一个张学良,是与正面的张学良形象相抵触、相冲突的。它们所表现的,是张学良性格中带有局限性的一面。作者所以选择这样的内容,不仅仅因为它们是历史的真实,也是出于塑造人物形象的需要。对张学良这种出身和经历的人物所具有的复杂性格,应当有一个全面而有说服力的展示,对他性格中的矛盾现象,应当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阶级的分析。阶级观点还是要讲的,不讲,有时候,一些历史现象就无法解释得通,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极其尖锐的时期尤其如此。作者深知这其中的道理,因此,他不是静止地、孤立地去看待张学良身上存在的矛盾、甚至是冲突的现象,而是将它们作为一个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充分揭示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确定它们的性质,分析这些历史活动的主流和支流、偶然性和必然性的辩证关系,在这个基础上对它们加以合理的、科学的布局,艺术地运用到人物形象的塑造中去。经过这样一番处理的张学良形象,性格矛盾而又合乎逻辑,面貌驳杂而又不失统一,它比任何一种单一的形象更符合历史的真实,并因此更具文学意义上的“真实性”。
三、白描手法与记实风格
《新战争与和平》是一部以中国抗日战争为题材的历史小说,它以大量的、真实的史实作为依据,艺术地描绘了中国抗日战争中的众多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体现出一种记实性的风格。文学语言是表达艺术内容,构成艺术形象的手段,《新战争与和平》的语言,简洁平实,朴素无华,是一种直陈白描式的叙述语言。历史记实性的风格与直陈白描式的文学语言的结合,构成了《新战争与和平》在写作上的主要特点。具体来说,它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历史记实性风格,主要体现在对中国抗日战争所做的全面、真实、全景式的描写上。这种描写,是对历史从上到下的鸟瞰、从始至终的扫描,无论是对战争的全局,还是对战场的局部,无论是对某一战役的实施,或某一事件的展开,均力求描写其全貌,即主要进行正面的过程的叙述,舍弃侧面的枝节的描写。仅以侵华日军为例(在以往的以抗日战争为题材的文艺作品中,对他们做系统的、正面的介绍和描写的小说寥寥无几),若将在《新战争与和平》中出现的日军指挥官的姓名、职务、官阶及指挥过的战斗、战役制表列出,便是一部完整的侵华日军高级将领一览表,它的详尽和真实,即使是历史学家也会对它感兴趣的。
最能体现这种历史记实风格的,莫过于作者对张学良一手导演的“西安事变”的叙述了。作者居高临下,取俯视的角度,将这一事件的最高层参与者一一划入笔端。张学良方面,写他与杨虎城,与阎锡山,与王以哲、于学忠等实力派军阀和东北军高级将领谋划、实施事变的详细过程。国民党方面,蒋介石是当然的主角,何应钦、陈立夫、宋子文、孔祥熙、陈诚、宋美龄等军政要员尽相露面,依据各自的身份、地位及所代表的政治、经济利益集团做充分的表演。共产党方面,以周恩来为代表,毛泽东、朱德等高层领导均出场。另外,日本驻华大使川越,美国顾问端纳,以及代表美、英等国利益的美英大使等,无一不在。可以说,能够决定中国抗日战争的进程和命运的关键性人物大都出场亮相了。在作者笔下,历史得到了完整的、真实的、艺术的再现,再现的不仅是一般的发展过程,而是其中最核心、最本质的部分。虽然这种以展示过程和全貌为主的记实写法,有时难免使小说的描写失之平直和简约,欠缺丰满和生动,不过,以作品宏大的主题和作者着意营造的深远的历史氛围来说,这种平直和简约在许多地方又是必要的,细节描写过多,有时候反而会冲淡作者对历史整体进程的把握和感悟。
2、历史记实风格,绝非对史实做严格的、一丝不苟的复述,而是在依据和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进行艺术的再创造。文学创作需要作家发挥艺术的想象力,它允许虚构和杜撰。但在历史记实风格的制约下,这种虚构和杜撰既不能脱离开历史的真实,同时又要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则需要高超的艺术功力。据作者自己讲,在小说中,周恩来应张学良之邀,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参加西安事变的谈判,赴西安前,在延安的土窑洞里,周恩来与毛泽东、朱德曾有一段边吃烤土豆,边商讨谈判对策的场景,这个场景,就是作者虚构的。但是,这场谈话表现出的高度政策水平,所显示的政治家的战略眼光和宏伟气魄,以及风趣幽默的对白,极其符合中共领袖人物的身份和地位,而后来西安事件的历史进程,基本上印证了这场谈话的内容,因此,这个场景尽管是虚构的,仍不失是“真实”的,它是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想象相结合的产物。
3、直陈白描笔法的显著特征之一,便是作者很少做大段的、细致入微的心理描写。即使运用了一些心理描写,也是简洁的、坦露的,其直白程度,有时甚至象人物在自言自语。更多的时候,对人物的心理活动,作者用人物的形体动作来加以表现。以外观的、可见的形体动作,替代内心的、隐密的心理活动,以大段的人物间的对白,替代人物的内心世界,是作者普遍使用的一种写作方法。
在刻划张学良的矛盾性格时,作者有几处动用了心理描写:当张学良的两个装备精良的主力师被他所认为的弱小可欺的红军一举歼灭时,百思不得其解;在张学良向蒋介石多次进谏而屡遭拒纳时,苦闷而无奈;在张学良即将实行兵谏而兴奋得夜不能寐时,思绪纷沓、姿肆汪洋。但这些地方的心理描写,至多三、五行,百余字,点到即止,惜墨如金。这样的写法,在中国古典小说中常可见到。如果说,李尔重同志有着丰富的中国古典小说的知识和深厚的中国古典小说的功底,那么,在写作《新战争与和平》时,他首先有意识加以借鉴的,是中国古典小说在写作上的技巧。
无可否认,心理描写在深入开掘人物丰富而复杂的内心世界,塑造丰满而生动的人物形象时,是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的,它为读者开辟了更为广阔的联想天地。但心理描写的具体运用,不能统而划一,用与不用?何时用?怎么用?均要视情节的发展而定。《新战争与和平》以直陈白描笔法为主,偏重于事件的展开和过程的描述,在这个总的写作原则下,作者不以过多的心理描写来阻断历史事件进展的节奏和顺序,形成连续贯通、一气呵成的气韵,又是与全书的记实性风格相统一的。
4、直陈白描笔法,并非是站在一个旁观者的地位,对历史做纯客观的、自然主义的叙述和描写,而是在简约、冷峻的笔法下,时时有作者鲜明而强烈的感情流露。这种感情的流露是多姿多彩的:在描写张学良置个人名利和安危于不顾,毅然发动兵谏逼蒋抗日时,是赞美;在描写蒋介石临潼被捉的狼狈相时,是轻蔑;在描写周恩来面对张学良伴蒋而去的飞机渐渐飞远时,是感叹。有时候,作者抑制不住自己情感的迸发,甚至脱离开对事件进程的叙述,直接插入简短的、鲜明的评论性或赞叹性词句,将作者的立场和感情表露得一览无余。尽管这种写法与全书叙述体的直陈白描风格不相协调,但每读至此,总令人怦然心动,受到极大的感染,仍可见出这种写法在艺术上的魅力。相形之下,在另一些地方,作者所做的某些游离于情节之外的说明性文字,却给人以生硬之感,例如在描写舞会的场面时,有这样的句子出现:“当时跳舞并不象现在这样流行”。例如在刻划日本情报机关的头目土肥原时,这样开头:“直到现在为止,没有一本书能够明晰地介绍日本特务机构的全貌”。在这里,作者直接以一个现代人的身份出现,对历史进行时空倒错的对比和外加的说明,应当说,即使是在历史记实风格的总体把握下,这也是要十分注意加以避免的。
四、文如其人
“文如其人”,指的是作家的人品与他的作品所表达的道德精神的一致性。李尔重同志与他的《新战争与和平》便极好地体现了这种一致性。
李尔重同志早年投身革命。1929年,在中国革命尚处于低潮时,他毅然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这一年他才16岁。1932年正式转为中国共产党。1937年“7·7事变”后,日军大举进犯中国,中国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李尔重离开大学,投笔从戎,参加了八路军。从此,在革命军队这所新的大学里,他驰骋疆场,征战南北。抗日战争期间,李尔重同志历任冀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武装部长、冀南第五军分区政委兼地委书记。解放战争期间,历任牡丹江省民运部长、铁道兵团宣传部长。十几年出生入死的战斗生涯迎来了新中国的曙光。全国解放后,李尔重同志长期担任武汉市、湖北省、中南局、陕西省的重要领导职务,1983年从河北省省长的岗位上退下来。
笔者所以不厌其详地列举出李尔重同志的详细履历,是要说明,它与《新战争与和平》的创作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作为一名抗日战争的亲身经历者,李尔重对战争本质的认识,要较之一般作家更真切、更深刻、也更生动。这种被鲜血和生命浸润过的战争体验,刻骨铭心,终身难忘。它为李尔重同志所独有;它为李尔重同志的文学创作提供了自由驰骋的广阔天地。对一个作家来说,这种经历是无可替代的,也是最可宝贵的。如果说李尔重同志在创作上存在着什么优势的话,它首先就表现在这种无可替代的、丰厚而深刻的战争生活积淀上。在《新战争与和平》的众多人物形象中,无论是真实的历史人物,还是虚构的小说人物,我们时时可以看到李尔重同志的身影在闪动:既有他作为热血青年投身于抗日洪流的英姿飒爽的身影,也有他作为成熟的领导干部,精于谋略、指挥若定的身影。这种生活积淀的闪现,在许多时候,对一个作家的创作可以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新战争与和平》的创作便是证明。
这种优势还表现在,李尔重同志是作为正义的一方投身到这场伟大的抗日战争中去的。他的爱、他的恨,他的一切情感,都与战争中正义一方的利益休戚相关。因此,在《新战争与和平》中,正义的事业受到了最大程度的褒彰,爱国主义精神得到了最充分的表现,字里行间始终扬溢着一股浩然正气。李尔重的为人与为文,在小说的创作上实现了高度的统一。可以说,作者是以自己的生命熔铸了《新战争与和平》,同时,《新战争与和平》也为我们提供了一条更深入地了解作者、认识作者的最好途径。
结束语
李尔重同志历经十载写就的这部恢宏浩大的历史长卷——《新战争与和平》,以真实、厚重的史实为依据,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武器,以爱国主义为主线,运用白描记实的艺术手法,形象地再现了中国人民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并取得辉煌胜利的历史进程,塑造出这段历史中众多的风流人物形象,张学良是其中突出的一个。对历史上的张学良,周恩来同志用“千古功臣”四个字来评价。这是政治的评价,是对他的盖棺论定。在《新战争与和平》中,李尔重同志借用了这四个字,作为他描述“西安事变”那个章节的总标题,可见,他是完全赞同周恩来同志的这个评价的,并将这个高度概括性的政治评价,化作了具体可触的张学良的艺术形象。在这一点上,李尔重同志是成功的。
标签:张学良论文; 西安事变论文; 战争与和平论文; 李尔重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抗日战争论文; 历史论文; 中国形象论文; 蒋介石论文; 世界大战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