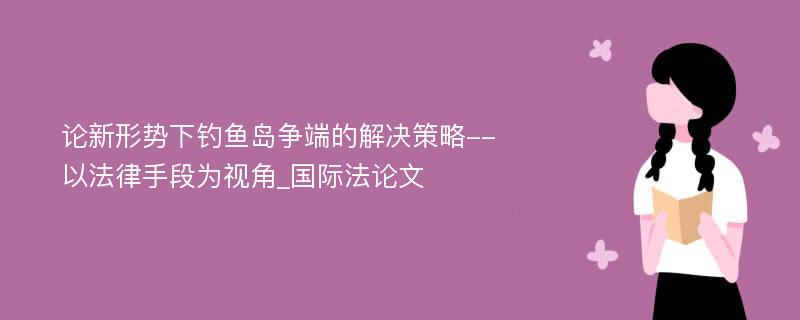
论新形势下钓鱼岛争端的解决策略——以法律手段为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钓鱼岛论文,争端论文,新形势下论文,视角论文,手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F93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8-4355.2011.04.10
钓鱼岛争端并不仅仅是指岛屿本身的主权归属问题,还涉及其在中日东海划界中的地位,以及与之相关的资源开采等问题。当前,钓鱼岛争端日趋复杂化,涉及三国四方。日本近年来动作不断,试图加强对钓鱼岛的控制,有意造成既成事实。同时,围绕中日钓鱼岛主权争端的“美国因素”日渐突出,美国成为影响钓鱼岛争端的重要外部因素。面对日本、美国对钓鱼岛的步步进逼,台湾当局在“一个中国”和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逐渐蜕变。2010年9月7日的“钓鱼岛撞船事件”更致中日关系陷入危机。
现阶段和平解决钓鱼岛争端的途径主要有二:一是政治手段,即通过外交谈判,协商解决;二是法律手段,即将争议提交国际仲裁或者诉诸国际法院。
我国一贯主张通过友好协商等政治手段解决钓鱼岛争端,然而当下形势表明,政治手段解决钓鱼岛争端已面临困境。以法律手段解决钓鱼岛争端是日方背弃中日共识的情况下需要采用的方法。
一、政治手段解决钓鱼岛争端面临的困境
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政治手段是指法律手段以外的争端解决方法和争端当事国以外的第三方解决方法,主要包括谈判、协商、斡旋、调停、和解、调查。对于钓鱼岛争端,我国一贯主张通过友好协商等政治手段求得解决,具体体现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政治战略,并希望在此之前双方都能保持克制,任何一方都不要制造事端。然而,在当前的形势下,“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能否全面解决钓鱼岛争端,值得加以反思。
钓鱼岛列屿由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南小岛、北小岛和3块小岛礁,即大北小岛、大南小岛、飞濑岛等8个无人岛礁组成,皆为中国固有之领土,这一点早已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据考证,明朝永乐元年(1403年)的《顺风相送》为记录有关钓鱼岛的最早文献,是书条记钓鱼岛列屿“福建往琉球”之路[1]。清末时期,国势衰微,钓鱼岛于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被日本占领,二战后日本理应根据《开罗宣言》将其归还于中国,但囿于诸多因素的干扰,钓鱼岛仍未回归中国。为避免中日在钓鱼岛和东海划界问题上的分歧影响两国关系,中国政府积极倡导以“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针来处理这一问题。① 双方同意在该问题上达成谅解,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缓和钓鱼岛和东海划界争端紧张局势的发生。
然而,近年来的种种事实表明,钓鱼岛争端并未因此得到根本解决,日本并未保持自我克制,仍在一己之私的驱动下乘机加紧制造既成事实,以期通过“实际占有”谋求有利于日本的解决途径。中日通过“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方针缔造的互信机制已面临困境。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右翼团体多次登上钓鱼岛,设置灯塔、神社等设施,日本政府对此却采取了纵容的态度,试图造成钓鱼岛是日本领土的既成事实。1990年,日本青年社在钓鱼岛建灯塔,再次引发“保钓”风潮。1996年7月14日,日本青年社在钓鱼岛再次新设置了灯塔。中国外交部表示对这一事件“严重关切”。1996年10月15日,日本外相重新声称日本对钓鱼岛享有主权,并否认曾和中国达成任何搁置钓鱼岛主权问题的协定。2000年4月20日,日本右翼团体日本青年社在钓鱼岛上建立了一座小神社,意在寻衅破坏中日关系。2003年1月1日,日本《读卖新闻》报道,日本政府已与声称拥有钓鱼岛所有权的国民签订了正式租借合同,以年租金2 256万日元的价格租下了钓鱼岛及附近的南小岛、北小岛三个岛屿。2005年2月,日本政府正式宣称管理钓鱼岛上的灯塔。同月25日,日本海上保安厅首次将这座灯塔正式记载在其新印制的海洋地图上。2008年6月10日,日本海上保安厅一艘巡逻艇在钓鱼岛近海与一艘台湾渔船相撞,并导致该渔船沉没。② 2010年9月7日,一艘载有约15名船员的中国渔船在钓鱼岛附近海域被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船冲撞,中国船长被日本非法扣留17天后回国[2]。
“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主张的提出充分显示了中国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国际争端的诚意,有利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但从上述事件可以看出,中国此重大善意举措不仅没有得到日本的积极响应,还促使日本乘机对钓鱼岛进行事实控制。为了否定负面因素的出现,在历次中日外交会谈过程中,日本政府刻意回避并不使中国政府有机会商谈解决钓鱼岛争端问题,至今有关谈判尚未开展过[3]。更为甚者,日本政府不断声称日本对钓鱼岛享有主权,认为钓鱼岛一直是日本实效管辖下的领土,从来没有与其他国家谈判过这一领有权问题,将来也不会与他国谈判钓鱼岛的主权问题。⑧不难看出,日本政府断无诚意与中国政府通过和平的外交途径解决钓鱼岛争端。
日本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正在实现对钓鱼岛的渐进实际控制。“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前提是“主权在我”,但从目前形势观之,如果中国继续坚持“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不仅会造成日本事实上对钓鱼岛的控制,还会造成如下为国际社会所默认的既成事实:钓鱼岛为中日双方“共同所有”,甚至为“日本所有”。到时“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犹如鸡肋,不仅无助于钓鱼岛主权争端的解决,还会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产生连锁反应,这些国家也纷纷以事实的先占行动来回敬“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导致这项主张成了约束中国自己的“君子协定”[4]。因此,有必要在新形势下重新探讨中日钓鱼岛争端解决的途径。
二、法律手段解决钓鱼岛争端的可行性
面对上述困境,我们有必要反思解决钓鱼岛争端的新策略。法律手段解决国际争端是指采用仲裁或司法判决来解决国家之间的争端。其区别于政治手段的最重要特点是:仲裁裁决和司法判决对争端当事国具有拘束力,争端当事国有义务诚实地执行裁决或判决。综观学界有关研究情况,我国大部分学者提出的解决钓鱼岛争端的途径与政府的主张相同,即“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对于采用法律手段解决钓鱼岛争端多持保留意见,主要是认为选择国际法院进行诉讼存在一定的风险,在很多没有法律规定或规定不明确的情况下,裁判的结果可能缺乏明确的预见性和稳定性,中国会在维护利益的轨道上失控。此外,钓鱼岛争端涉及东海大陆架划界问题,中国沿海邻国的情况各不相同,某一区域大陆架纠纷的有利判决标准适用于我国和其他国家的大陆架纠纷很可能会变得对我国不利,而我国作为当事人的某一案件的判决对于其他类似争议可能会产生联动效应,不一定符合我国的整体利益与长远发展[5]。有学者还提出,我国可考虑像韩国一样就《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98条发表声明,排除三类争端的管辖[6]。其目的是将钓鱼岛争端问题等排除在有拘束力裁判的强制程序之外,即拒绝用法律手段而只用政治手段解决争端。笔者认为,在日方当前无诚意与我协商谈判时仍拒绝使用法律手段解决钓鱼岛争端,实不可取。相反,运用法律手段解决钓鱼岛争端,势在必行。
首先,钓鱼岛已处于日本的实际控制中,若仍长期搁置主权争议,将对我方不利。有效控制原则是国际法院解决国际领土争端经常适用的基本原则之一,它是指国际法院在权衡诉讼双方提出的进行了有效统治的证据之后,将有争议的领土判给相对来说进行统治更为有效的一方[7]。钓鱼岛争端不应适用有效控制原则,因为有效控制原则只针对难以确定合法所有者的争议领土,对于主权明确但领土被他国控制的情况是不适用的[8]。但从目前的有关情况来看,国际法院有在解决领土争端中运用有效控制原则的趋势。例如,在2002年喀麦隆诉尼日利亚的“领土和海洋边界案”④、2002年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之间的“利吉坦岛和西巴丹岛主权争议案”⑤ 以及2003年马来西亚诉新加坡的“白礁岛、中岩礁和南礁的主权归属案”⑥ 等案件中,有效控制原则均有所体现。由于国际法院的判决对国际习惯法的形成有重要作用,此种情况将使我国陷入不利的境地。从日本1972年于美国手中接管钓鱼岛开始计算,不管其理由是“先占取得”或“时效取得”,只要日本在相对长的一段时间内对该岛屿实施有效控制,中国再提出收复钓鱼岛,恐怕会贻笑大方。换言之,钓鱼岛争端可以搁置不谈的期间是有限的[3]77-83。因此,在钓鱼岛已被日本长期实际占有的情况下,中国如不采取有效的法律步骤,不仅会被国际社会认为中国已经放弃对钓鱼岛的主权权利,而且在国际法上也将处于被动。
其次,中国对钓鱼岛之主权,实有充分理据,将钓鱼岛争端诉诸法律手段,乃明智之策。日本虽然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第36条第2项和第5项的规定,接受了国际法院的强制管辖权,但由于现阶段其实际占有钓鱼岛处于有利地位,绝不会主动将争端诉诸国际法院。这是因为日本一直意图通过长时间的“实际控制”来弥补其合法性的不足,如果主动提出诉讼,相当于中断了其对钓鱼岛的管辖效力。另一方面,中国主动向国际法院提起诉讼,如日本拒绝应诉,则会在国际舆论上处于不利的地位。对中国来说,在事实较清楚又有国际法根据的情况下,用法律手段来解决钓鱼岛争端是明智的选择。
或有多人存疑,若将钓鱼岛争端诉诸国际司法途径,会对南中国海争端产生不利的联动效应,实则不然。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第36条的规定,国际法院对事管辖权有三类,即自愿管辖、协议管辖以及任择性强制管辖。⑦ 到目前为止,中国并未声明接受国际法院的任择强制管辖权并在事实上拒绝了国际法院自愿管辖权和协定管辖权。事实上,国际司法或仲裁的管辖权来自当事国的自愿,中国在钓鱼岛争端中采取国际司法途径,并不是说中国在解决南中国海争端的方法上也必须采用同样的方法。除非中国接受了国际法院的强制管辖权,否则,国际法院不具有管辖权。中国可根据南中国海的具体情况,于争端之继续存在足以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之维持时,以谈判、调查、调停、和解、公断、司法解决、区域机关或区域办法之利用,或自行选择之其他和平方法,求得解决。⑧
最后,中国主动将钓鱼岛争端诉诸法律手段,有益于中国展示大国风范以及“和平崛起”战略之实施。迄今为止,中国尚未接受国际法院的强制管辖权,也未曾利用过国际法院来解决国际纷争。所以,从总体上说,中国对国际法院的管辖权仍持比较消极的态度,中国有必要对此作更为积极的考虑[9]。其一,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此种消极态度不利于发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作用。⑨ 其二,虽然很多国家不一定有能力或有意愿出面阻挡或纠正日本违背国际法之乖张行为与主张,但如果中国诉诸国际法甚至寻求司法解决(尤其是当国际法站在中国这边之际),一定会在很多不愿意看到国际法被日本蹂躏践踏的国家中得到共鸣与支持。这也是中国要走独树一帜大国外交之一大途径[10]。其三,中日一衣带水,通过法律手段和平解决钓鱼岛争端,更有利于两国的长远战略友好发展,是中国展示大国风范以及“和平崛起”的应有之义。
三、法律手段解决钓鱼岛争端的应对策略
一如前述,“搁置争议、共同开发”钓鱼岛已面临困境,以法律手段解决钓鱼岛争端是在当下日方背弃中日共识的情况下需要采用的方法。我们应为法律手段解决钓鱼岛争端作好充分的准备。
(一)分析双方不同立场,收集有意义的证据
中日钓鱼岛争端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钓鱼岛等岛屿的主权归属;二是与之相关的东海海洋权益分割。目前我国学者多偏重于从历史和地理角度论证“钓鱼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在国际法角度则从原始发现、行政管辖、经济活动、自然延伸等原则为基础,论证钓鱼岛的主权属于中国[11];以及主张在东海划界中忽略钓鱼岛的效力,即给予其零效力[12]。与此相对,日本官方和大多数学者从国际法的先占、时效取得以及根据日美之间的条约和协定主张日本拥有钓鱼岛主权[1]109-120;同时坚持以钓鱼岛等岛屿为基点与中国在东海划界,即给予其全效力。比较中、日双方的主张,可以看出钓鱼岛争端的关键问题有四,即:(1)中国能否在法理上证明钓鱼岛自古属于中国;(2)日本的“无主地先占”结论是否成立;(3)战后美日之间的条约或协定能否作为日本拥有钓鱼岛主权的依据[13];(4)钓鱼岛在东海大陆架划界中处于何种地位。
针对上述争端分歧,我国应着力从以下几个方向收集证据。第一,继续从史料中挖掘能够证明中国对钓鱼岛行使主权的国家行为,如1893年慈禧太后曾下诏书将钓鱼岛等3个岛屿赏给臣民盛宣怀作采药之用的类似证据。尽管中国最早发现和命名钓鱼岛,并在明清两代用作往返琉球时的航向标,但这些行为并未强有力地证明中国的有效占领。⑩ 第二,驳斥日本“无主地先占”的谬论。在国际法上,取得领土的“无主地先占”必须是“有效先占”,它要满足五个方面的基本条件才能成立:领有的企图;无主地的确认;占领的宣告;占领的行动;实效管辖[14]。因此,我们应从这五个方面论证日本的主张不能成立。第三,论证战后美日之间的条约或协定不能作为日本拥有钓鱼岛主权的依据。主要是从条约相对性的角度说明1951年的《旧金山和约》和1971年的日美《归还冲绳协定》不能变更中国对钓鱼岛的主权,日本应遵守其在1945年接受的《波茨坦公告》及《开罗宣言》,将钓鱼岛归还中国。第四,搜集翔实的科学数据,证明钓鱼岛在东海划界中为零效力。尽管钓鱼岛等岛屿不过是弹丸之地,但如果获得全效,就可以为主权者带来11700平方海里的海域[15]。从相关国家实践和国际司法仲裁有关海洋划界案例来看,岛屿的划界效力一般是通过权衡它对界线的影响程度与其自身重要性之间是否成比例来决定的。分别给予全效力(full effect)、部分效力(partial effect)或加以忽略(ignored)。(11)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21条规定,岛屿的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应按照本公约适用于其他陆地领土的规定加以确定。但不能维持人类居住或其本身的经济生活的岩礁,不应有专属经济区或大陆架。钓鱼岛并不能维持人类居住或其本身的经济生活,因此其在东海划界中的效力应被忽略。为此,我们应着力收集钓鱼岛有关地理、生物等方面的数据资料以证明其不能维持人类居住或其本身的经济生活。
(二)加强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研究,完善相关国内立法
在目前我们无法通过谈判等方式收回钓鱼岛主权时,可以通过研究《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完善相应的国内海洋立法,为将来运用法律手段解决争端争取主动权。
我国迄今为止颁布了多部海洋法律法规(12),为维护国家的海洋权益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仍存在很多不足之处。第一,规定过于原则化,不具操作性。如《领海及毗连区法》、《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基本上照抄《公约》的内容,全文不超过20条,缺乏相应的或配套的实施细则或办法。第二,立法混乱,缺乏整体性,条块分割严重。我国现行海洋法律、法规和规章相互交织,立法层次和立法部门繁多,各法律法规的海洋活动只涉及各自管辖的范围和区域,缺乏部门间配合和协调。第三,没有专门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的法律或法规。虽然每部单行海洋法律法规都旨在保护国家海洋权益,但在海洋权益斗争日趋激烈的今天,将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的责任分到各个单独法律法规中去承担,未免显得势单力薄。另外,有关钓鱼岛的法律规定仅在1992年的《领海及毗连区法》第2条第2款有所体现(13),其他法律均无涉及。
值得关注的是,2007年4月20日,日本国会审议通过了《海洋基本法》,该法于2007年7月20日正式实施。(14) 日本《海洋基本法》的颁布实施,是其“扩疆争利”、“夺岛圈海”海洋策略的集中体现,必然对我国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海洋权益维护以及海洋安全保障产生极大冲击,引发沿海各国的摩擦和争端。日本可能借《海洋基本法》之机升级钓鱼岛事件,会依据《海洋基本法》对钓鱼岛采取更加积极的实际控制行动。《海洋基本法》对远海孤岛的保护规定,其目的性很明显,日本企图用国内立法方式为其争夺钓鱼岛营造合法依据,从而为其争夺钓鱼岛的主权问题谈判增加政治筹码[16]。透过2010年“钓鱼岛撞船”事件,其立法意图可见一斑。
为此,我国应以钓鱼岛争端为契机,完善我国相关海洋法律。第一,要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制定有关法律法规的配套实施细则,增强其可行性和操作性。第二,制定《海洋基本法》,主要应明确该法的立法目的、原则、我国海洋的基本方针、基本政策、基本措施以及海洋综合管理。第三,制定《海洋安全保护法》,完善海洋安全保护与资源开发使用的法律体系,为我国的海洋安全保护与资源的开发与使用提供法律依据[17]。第四,进一步宣布我国的领海基点、领海基线及明确我国管辖海域的界限。我国政府于1996年宣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领海的部分基线和西沙群岛的领海基线,共宣布了77个领海基点。随后并未宣布其他岛屿的领海基线,为切实维护我国的海洋权益,我国应进一步宣布其他所属岛屿的领海基线,以明确确定我国有权管辖的海域界限[18]。钓鱼岛为中国固有领土,应将钓鱼岛作为我国的领海基点,其拥有12海里领海,但不享有大陆架及专属经济区。(15) 第四,可考虑效法韩国制定的“独岛开发方案”(16),制定《可持续利用钓鱼岛法案》,规定与钓鱼岛有关的利用开发方案、政策,以宣示我国对钓鱼岛主权的领有。
(三)完善海上执法体制,形成高效行政执法力量
根据国务院“三定”方案和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我国现行的海洋执法体制是海监、渔政、海事、边防及海关等为主的分散型执法体制,形成了一幅“五龙治海”的景状。(17) 这些执法力量在海上执法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维护了国家利益和海洋秩序。
进入2008年以来,围绕钓鱼岛主权争端、管辖海域划界问题,中国海监、渔政等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海上涉外维权行动,并取得一定成效。但从整体上看,中国的海洋维权斗争仍存在诸多问题。这其中,既有海洋大国与周边国家不断“侵权”所造成的外部维权压力,更有我国维权力量、维权能力相对薄弱所形成的内部“瓶颈”[19]。我国现行的分散型海洋执法体制存在诸多弊端。各部门建立的海洋管理队伍,条块分割、自成体系,协调工作难以进行;部门分工困难。对有些任务,各部门争夺管理权,而对另一些任务,各部门又互相推诿。此外,执法机构及其武装重复建设和多功能利用问题难以解决。
随着各国海洋权益的不断扩展,组建独立的综合性海上执法力量已经成为趋势。例如,美国的海岸警卫队、日本的海上保安厅、韩国的海洋警察厅等。特别是日本海上保安厅,已经成为日本与中国争夺海洋权益的“利器”。近年来,日本海上保安厅在争议海域的活动日益频繁,特别是在钓鱼岛水域,海上保安厅通过暴力驱赶我国作业渔民以及民间“保钓”船只的方式,逐渐掌握了钓鱼岛水域的实际控制权。同时,海上保安厅在其所辖的灯塔上大规模装备监视雷达、红外线夜视装置及高倍数照相机,并进一步完善危机管理综合情报系统[20]。因此,我国应改变目前海域管理和海权维护工作中的多部门参与却缺乏协调的局面,形成一支较为统一并高效运转的行政执法力量。在现阶段,中国海洋维权力量分散于多个部门,要将它们从职能部门中分离出来并实现整合,短期内存在一定的困难。当前可考虑先着手加强海军与海监、渔政、海警等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机制,发挥海军的主导作用。另外,应加强对钓鱼岛周围海域的巡航,形成定期巡航制度。
(四)加强实际控制,寓维权于开发之中
从有关的历史资料来看,中国早在15世纪就已经发现并命名了钓鱼岛,比日本早五百多年。然而日本如今在钓鱼岛上设灯塔、建神社、向国民“租借”、议员巡视、军事演习、常驻巡视船,武力阻止我各方的“保钓”行动、无端指责我正常科考活动、阻扰我维权执法行动等,使我国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究其主要原因,就是我们过去一直缺乏对钓鱼岛的实际控制。我们多次强调“最早发现论”,却难以举证对钓鱼岛进行实际行政管理,一些单纯的私人渔民行为并不具国家性质,在现代国际法语境中并不占优势。我们应当从过去比较强调历史性权利转化为当下的实际控制。
有学者精确地观察到了国际社会中的一个现象:“近年来的海域划界实践和判决都倾向于避免干扰已长期存在的资源开发行动,当许多国家都在同一地区有开采行动时,解决问题的办法往往就是大家来分享资源。时间是站在那些不顾历史传统活动径自进行开采的国家这一边。一旦海洋资源的经济开发行动已经发生了,就很难再依靠谈判或第三者裁判的办法,将这个国家从该地区完全排除。因此,现况(status quo)可能对某些相关国家是不利的。”[21]这一现象也是对我国钓鱼岛问题的精确概括。
从国际领土争端解决的实践来看,实际控制争议地区是最常见的宣示主权的方式。根据国际惯例,实际控制的时间越长,解决争议时就越有优势。因此,加强在钓鱼岛的现实存在,有利于增加我国日后通过法律手段解决钓鱼岛争端的筹码。在现阶段,国家应当采用寓维权于开发之中的政策来宣示对钓鱼岛的主权,充分利用法律、政治、经济、外交、科研、文化、旅游等各种手段来强化中国主权在钓鱼岛的实际存在,以打断日本对钓鱼岛的治理控制。此外,应加强对一些私主体开发活动的管理。从近年有关国际判例来看,渔民、民间团体等私主体的行为并不代表国家的实际控制行为,因此,政府可通过审批的方式批准私主体在钓鱼岛从事开发活动,以实现国家对钓鱼岛的实际控制。
(五)全方位准备,为通过法律手段解决钓鱼岛争端争取主动权
基于钓鱼岛争端的历史和法律问题复杂性,通过法律手段解决钓鱼岛争端,还需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作为:
首先,应强化在战略高度将钓鱼岛问题与台湾问题解决相关联的思维。从当前的国际形势观之,钓鱼岛问题与台湾问题存在密切关联。当前,台湾当局试图利用日本牵制中国,而日本国内由于跟台湾的特殊关系,也希望在台湾问题上起一定的牵制作用。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某些别有用心之士以为台湾“正名”为由,提出“台湾为主权独立国家”,试图跳脱一个中国的思考方式,来解决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22]。台湾当局在“一个中国”和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逐渐蜕变,使得钓鱼岛争端解决前景更显复杂性,实为引人担忧与警惕。因此,应强化在战略高度将钓鱼岛问题与台湾问题解决相关联的思维。一方面,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正确战略,保有对钓鱼岛的主权,有助于中国的和平崛起,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对钓鱼岛的开发利用将促进大陆与我国台湾地区的经贸、政治、文化发展,缩小两岸的认知差距,从而推动台湾问题的成功解决。另一方面,始终坚持在“一个中国”的框架下解决台湾问题,也有助于钓鱼岛争端的解决。一旦所谓“台独”实现,则表明中国实力不足,这将为日本提供乘虚而入之机,同时,其中的“美国因素”更为甚嚣尘上,无疑使钓鱼岛争端的和平解决举步维艰。
其次,应加强对相关国际判例的研究。国际法院已成立近60多年,受理的案件逾百件,绝大部分案件涉及领土主权、陆地边界、海洋划界问题,这些判例影响巨大且意义深远。从国际法院的相关判例入手,研究国际司法实践,认真分析、总结国际法院在领土主权尤其是岛屿主权争端方面的判例及其确立的一般原则、规则和方法,归纳国际法院审理领土争端案件的基本态度,将法院的相关判例与中日钓鱼岛争端相联系,分析各方的主张能否在相关或相似的国际法院判例环境下得以成立,从而有利于对将钓鱼岛争端提交国际法院做出初步的预期性结果分析。从钓鱼岛争端所涉及的国际法问题来看,对英国和法国敏基埃群岛和艾克荷斯群岛案(1950-1953年)、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领土、岛屿和海洋边界争端(尼加拉瓜参加)(1986-1992年)、卡塔尔与巴林的海域划界与领土问题案(199l-2001年)、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利吉坦岛与西巴丹岛主权争端案(1998-2002年)、尼加拉瓜和洪都拉斯岛屿归属与海洋划界案(1999-2007年)、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白礁岛、中岩礁和南礁主权归属案(2003-2008年)等典型判例进行深入研究,对钓鱼岛争端解决有重要启示。
最后,应加强对国际法人才的培养。近年来,随着国际法学的发展,这一领域的人才培养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我国现有的国际法人才,无论在数量还是水平上,都远不能独立应对国际官司。应着力培养一批学术造诣高深、能够把握国际法发展趋势和我国对外政策、具有较强处理国际法事务能力的国际法专家学者,为钓鱼岛争端的法律解决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
四、结语
综上所述,中国对钓鱼岛之主权,虽有充分理据,中国对钓鱼岛争端的解决亦表现出相当大的善意,但政治手段解决此争端所面临的困境已然表明中国有必要采用法律手段解决纠纷,避免事态的进一步升级,以维护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时下,中国应为通过法律手段解决钓鱼岛争端作好充分准备。在这一努力过程中,中国应分析双方的不同立场,收集有意义的证据,注意完善相关国内立法;同时,要改革海上执法体制以形成高效行政执法力量;加强在钓鱼岛的实际存在,重视其与台湾问题的关联;积极培养高水平国际法人才,深入研究相关国际判例。
收稿日期:2011-05-06
注释:
① 1979年5月31日,邓小平同志会见来华访问的自民党众议员铃木善幸时表示,可考虑在不涉及领土主权的情况下,共同开发钓鱼岛附近资源。同年6月,中方通过外交渠道正式向日方提出共同开发钓鱼岛附近资源的设想,首次公开表明了中方愿以“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模式解决同周边邻国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的立场。
② 参见:钓鱼岛大事记[EB/OL].[2011-1-4].http://news.qq.coM/zt2010/diaoyudaozc/.
③ 对1972年中日领导人关于钓鱼岛问题的搁置争议之说,日本外务省与日本的大部分学者都是不予承认的。邓小平在1978年访问日本时提出的搁置争议给下一代解决的主张是在记者招待会上讲的,日本人认为这是中国方面一厢情愿的想法。(参见:张植荣.日本有关钓鱼列屿问题研究评述[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2,(1):101-103.)
④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Land and Maritime Boundary Between Cameroon and Nigeria (Cameroon v.Nigeria:Equator Guinea intervening),judgment of October 2002.
⑤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Case Concerning Sovereignty over Pulauigitan and Palau Sipadan (Indonesia/Malaysia),judgment of December 2002.
⑥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Sovereignty Over Pedra Drancha/Pulau Batu Puteh,Middle Rocks and South Ledge (Malaysia/Singapore),judgment of May 2003.
⑦ 《国际法院规约》第36条规定:“(1)法院之管辖包括各当事国提交之一切案件,及联合国宪章或现行条约及协约中所特定之一切事件。(2)本规约各当事国得随时声明关于具有下列性质之一切法律争端,对于接受同样义务之任何其他国家,承认法院之管辖为当然而具有强制性,不须另订特别协定:……”争端当事国提交的一切案件,不限于法律性质的争端,即所谓的“自愿管辖”。《联合国宪章》和现行条约中特别规定的事件或争端,即所谓的“协定管辖”;国家事先声明接受国际法院管辖的一切法律争端,即所谓的“任择性强制管辖”。(参见:王铁崖.国际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5:590.)
⑧ 《联合国宪章》第33条第1款:“任何争端之当事国,于争端之继续存在足以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之维持时,应尽先以谈判、调查、调停、和解、公断、司法解决、区域机关或区域办法之利用,或各该国自行选择之其他和平方法,求得解决。”
⑨ 在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中,英国是全面接受国际法院管辖的国家,美、法是有保留地接受,就连一向对法院管辖权持反对态度的苏联,也于1989年就6项人权公约承认接受国际法院的管辖。(The Soviet decree of 10 February 1989 is published in AJIL 83 (1989),p.457; T.Schweisturth.The Acceptance by the Soviet Union of the Compulsory of ICJ to Six Human Rights Conventions [J].EJII,Vol.2,1991:110-117.转引自:梁咏.从国际法视角看中日东海大陆架划界争端[J].法学,2006,(8):122-128.)
⑩ 如在1931年的克利伯顿岛仲裁案(clipperton island arbitration)中,该案仲裁员指出:不论此岛曾经用过什么名称,1858年的时候是不是无主地,是本案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即使此岛是西班牙国民发现的说法得到承认,还须证明西班牙不仅拥有占有这个岛的权力,而且还实际行使过这个权力。(参见:曲波.有效控制原则在解决岛屿争端中的适用[J].当代法学,2010,(1):144-151.)
(11) 全效力,即把岛屿当作该国领土的一部分与本国领土一样享有大陆架。部分效力,即不把岛屿作为基点但要视具体情况允许其享有适当的海域。零效力,即不把岛屿作为划界基点,也无适当海域。(参见:高建军.新海洋法看中日东海划界问题[J].太平洋学报,2005,(8):71-78.)
(12) 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领海的声明》(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1992年);《关于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决定》(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基线的声明》(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1982年,1999年修订);《海岛保护法》(2009年)等。此外,还有很多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实施细则,如《远洋渔业管理规定》(2003年);《无居民海岛保护与利用管理规定》(2003年);《海洋行政处罚实施办法》(2003年);《渤海生物资源养护规定》(2004年);《海域使用权登记办法》(2006年);《海域使用权管理规定》(2006年);《港口规划管理规定》(2007年)等。
(13) 1992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第2条第2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陆地领土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及其沿海岛屿、台湾及其包括钓鱼岛在内的附属各岛、澎湖列岛、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以及其他一切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岛屿。”
(14) 日本《海洋基本法》共分为4章以及附则,分别为总则(第1条至第15条)、海洋基本计划(第16条)、基本对策(第17条至第28条)、综合海洋政策本部(第29条至第38条)、附则。
(15) 但也有学者认为,“可将钓鱼列岛的主权之争予以搁置,且以其不拥有相应的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同时,也以不作为测算伪劣的基点为妥。”(参见:金永明.东海划界争议解决路径研究[J].上海经济研究,2008,(8):24-30.)
(16) 韩国议会于2005年制订了《可持续利用独岛法案》。根据这一法案,于2006年编制了《独岛可持续利用基本计划》,主要包括在独岛设立研究基地、建设独岛纪念馆、鼓励国民赴独岛旅游等方面的内容。
(17) “五龙”指的是国土资源部下属中国海洋局及“海监”系列执法船,农业部渔政局下属的“渔政”船,交通部下属的海事局“海巡”船,同时还有公安部边防局下属的“海警”,以及海关部门的缉私艇。
标签:国际法论文; 中日钓鱼岛争端论文; 中国钓鱼岛论文; 日本中国论文; 钓鱼岛论文; 法律论文; 日本政治论文; 国家部门论文; 岛屿论文; 国际关系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