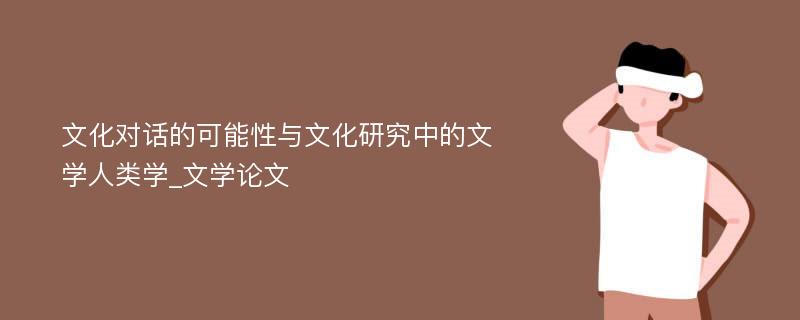
文化研究 文化对话与文学人类学的可能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论文,人类学论文,可能性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对20世纪的文学研究——特别是比较文学发展脉络的历史回顾,提出在文化对话的广阔背景上建立文学人类学的可能性,以期为未来的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确认中远期目标。从文化人类学对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的双重影响着眼,比较文学作为通向文学人类学的必由之路,作为加强文化交往与沟通、克服民族中心主义心理障碍、确立文化相对论平等对话观的有效途径,已日益变得明确和必要。随着后殖民时代多元对话的展开,文学研究本身获得了发掘文学艺术的人类学价值,促进人类文学经验的会通和整合的新使命。
关键词 比较文学 文化对话 文学人类学 人类文学经验整合
一、引论
回首20世纪的文学研究,比较文学的长足发展十分引人注目。然而,比较文学学者常常为自己的研究算不算一门学科、有没有“嫡传合法性”而忧虑,许多自我正名和辩护的努力人们已经耳熟能详。化用精神分析的语汇,或可称为比较文学的“无根情结”。11年前,乌尔利希·韦斯坦因套用高更的一幅画名来质问自己的比较文学生涯:《我们从何处来?我们在哪里?我们向何处去?》(D'où venons— nous? Que sommes—nous? Où allons—nous?)这三个相关的问句恰切地表达了由“无根情结”派生出的自我质询。其实这种叩问历史根脉、寻找立足点、确认方向感的迫切需要并不只是比较文学学者特有的神经过敏之产物,而是文学研究乃至所有人文学者处在迅速变化的世界格局之中都不得不明确的自我认同问题。当今的文化变迁(culture change)所激起的文化震撼(culture shock)足以使那些过去名正言顺的学科和有着根深蒂固传统的人文研究规范(norms)都发生动摇,受到挑战。只是由于地基不深,立足不稳的比较文学在这场大变局中震感更强烈,危机也更明确的缘故,才会有频繁的“生存焦虑”以及相应的自我治疗、自我慰藉的顽强需要。
如今,距韦斯坦因的自我叩问不过10年多,却仍有必要重新考虑何去何从的问题。因为冷战结束,信息高速公路的开通和世界性市场的形成已经对比较文学学者的自我定位产生了根本性影响。随着文化交往升级和文化对话的空前扩大,一种以多元取代一元、边缘挑战中心为特征的超学科的文化研究正方兴未艾,预示着新世纪人文社会科学新趋势和新格局的到来。我们在此时提出文学人类学的可能性,作为比较文学发展的中远期理论目标,或可借此消解“无根情结”和方向困惑,使比较文学继续发挥促进文艺学总体变革的先锋作用。
二、比较文学作为通向文学人类学的必由之路
比较文学在文化对话方面已经做出了有目共睹的业绩,但比较既不是理由,更不是目的,而毋宁说是一种手段,一种过渡和中介,它的未来的理论目标将通向文学人类学(或称人类学诗学)。
从文学研究本身看,比较文学比国别文学的封闭研究传统是大进了一步,但如果参照一下文化人类学的进展,就不难发现比较文学学者仍不免有作茧自缚、划地为牢之嫌。把一国文学同另一国文学比较,或把一个语种的作家同另一语种的作家相比较,充其量只能看作通向对人类文学的本质与功能认识目标的一个起点,一种过程,因为世界上有数千个民族和一千多种语言,其中的每一种都毫无例外地应视为“世界”或“人类”总体的有机组成部分。
就在比较文学学者大声疾呼、著书立说、成立组织、召开会议,试图把这一研究作为合法学科或至少是合法学派确立下来,并在莎士比亚和汤显祖、伏尔泰与《赵氏孤儿》之间寻找平行的或影响的关系时,人类学家已在从容不迫地整理来自世界各个角落各种社会和文化的民族志材料,并以此为基础去思考人类文化的普遍规律问题了。19世纪作为欧美人类学之父的泰勒和摩尔根试图概括人类进化的程序,都是建立在300多个社会的样本上的。相形之下,19世纪末提出《文学的比较史》的戴克斯特所预期的文学理想也只不过是“欧洲的”而已。而本世纪初洛里哀著《比较文学史》(1903)欢呼世界大同之到来,译者傅东华亦随声附和地称扬此书“把从最古时代直到现在的世界上每一角落的文学纤屑无遗地用不过繁重的篇幅统统都收摄起来”[①]。细览其书,只是被迫接受了东方学的历史成果,在一部欧洲中心的欧洲文学史的框架上点缀了若干“东方”民族文学的花絮。全书二十章,除首章讲欧洲文明之前的四大文明背景,第二章讲印欧文明的分化,第九章讲到中古亚洲文学及其对欧洲的影响外,其余十七章绝大部分篇幅都在讲欧洲文学,这样一部文学史在当时已经让人感到视界大开、登泰山而小鲁了,却实不知“世界上每一角落的文学”在哪里。仅以第九章提到中国文学的一段来做例子,总共不过几行字,说到的作家仅四位,却把王维和骆宾王二人说成是李白、杜甫的后继者和劲敌。一段空洞的赞叹之词竟以如下一句作结论,更令人感到痴人说梦一般的迷惑:
然而看它种种的刻画功夫,看它对于日常生活的真际的观察,也再没有一种文学比它更和我们自己的文学相似。[②]
从比较研究方法的发展来看,文化人类学也较比较文学大大领先了一步。众所周知,人类学的成立便是以跨文化的比较为方法论背景的,在那里,比较不需要正名和辩护,因为它不仅是“人类”这一大旗之下天经地义的方法,而且也是赋予人文研究“科学性”的重要依据:
人类学家必定要跨越某一特定文化的界线而比较人类行为。大多数人类学家都同意,比较分析是文化人类学的必需的因素。
超越背景之外,比较方法或交叉文化研究方法与物理学或化学之类的自然科学使用的实验技术相似。人类学家能建立假说,控制可变因素,并检验接受或抛弃假说。人类学家在得到大量的民族志材料后,能够借这些材料来建立或检验假说。其他人类学家能再检验对其这些假说的检验。因此,交叉文化分析达到了科学的方法的基本标准之一——能够检验和再检验假说。[③]
人类学中除了简单的一对一比较法,还发展出了更加成熟的“有限比较法”(Controlled Comparision)和“统计比较法”(Statistical Comparison),使比较作为建立和检证假说的方法更加精确有效,近似于自然科学中的实验和取样技术。在这方面,屡次陷入名分危机的比较文学显然还有很大差别,那种已显得有些陈旧的一对一的比较模式在比较文学论文中仍占据着很大的比例。
40年代问世的文学理论国际性权威教科书——以渊博和丰富著称的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虽然也为比较文学开辟了专章,但西方中心的格局没有多少改变;同一时期的人类学家却在着手建立旨在覆盖全球文化的《人类关系区域档案》(The Human Relations Area Files,HRAF)。耶鲁大学的人类学家为此编出了根据800多种文化的民族志资料并覆盖一千多个社会的《文化资料通览》(Outline of Caltural Marterial,OCM),研究者可以分门别类地获取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化的系统资料,这无疑大大刺激了具有高度概括性的大规模横向比较研究。比阿特丽斯·惠廷借助于《人类关系档案》去验证她研究印第安派尤特人(Paiute)社会中巫术功能得出的假说,完成了《五十个社会的巫术》这样的跨文化统计比较法的典范之作。
相对而言,比较文学研究的现状因受到学历、视野和资料等方面的限制,还远远不能达到人类学的那种纵横四海的统计比较程度。不过,比较文学从西方扩展到东方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许多森严的壁垒已经打破,中、印、日、阿拉伯等亚洲主要文明同西方文化的交汇与对话业已展开,这也就为未来的文学人类学开辟了道路,提供了可供局部概括和演绎的基本素材。假如我们还没有足够的条件和自信将比较方法用于大规模检验假说的尝试,那么在目前阶段,至少可以把比较作为促进文学交流和加强相互理解的一种“边界游戏”方式。如倡导双向文化人类学的比利时学者J.雷米所说:
不同文化的交流过程中存在着共同的文化因素,而各种文化又包含着各自的特色。文化交流中的这种“共性”与“个性”的结合导致这样一种结果:边界这个概念不再被视为一条鸿沟,而被看成是各种文化的边缘。边界成了一个中性地带,在这里,文化交流得以顺利进行。
使边界和边界会晤的价值得到增值。我们应该努力发现一种能够激起我们对于边界游戏产生兴趣的感情,这意味着一种人人都能从中获益的相互交流。[④]
从这种打通边界、填平鸿沟的意义上看,比较确实充当了促进文化间交流的使者和中介人的作用。当人们的心态由闭锁转向开通,比较也就无须为自己证明合法性了。
三、比较作为文化对话的一种形式
比较方法不只和跨文化分析的技术有关,而且也直接影响到处理异文化问题的情感和态度。斯梅尔塞在回顾社会科学中比较方法的兴盛时指出:“在人类思想史上,人类集团歪曲他们对‘不同’集团的认识的倾向,只是在最近才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同样,为克服这种歪曲而进行的严肃努力,相对也是在最近才出现的,其途径是超越单独一个集团的实践范畴去认识社会生活的差异。大部分这样的努力都是在社会科学领域进行的,尤其是在人类学、社会学、政治科学和历史学领域;对于这种努力的定名各不相同,例如‘比较研究’,‘交叉文化分析’,以及‘跨国分析’。”[⑤]对于闭关锁国了几十年的中国学界来说,由于“歪曲”早已习惯成自然,最初倡导比较就需要相当的勇气。而平心静气对待异文化的态度则需要时间来培育。
当詹姆逊80年代在北京大学讲出如下话语时,学者们确实感到跨文化阐释原则的启发作用:“为研究某一种文化,我们必须具有一种超越了这种文化本身的观点”[⑥]。但随着一个世纪以来的人类学文献的大量汉译,人们不难发现这早已是老生常谈了。马格丽特·米德1928年就说:
以往我们习惯上认为属于我们人性中固定成分的行为的诸多层面,现在一个接一个地被发现只是人类文明的一种可能的结果。一国居民所有的行为,另一国居民可能并不具有,而这是和种族的差异无关的。人类学家了解到,即使像爱慕、恐惧和愤怒这类人类的基本情绪,也不能归咎于种族遗传或所谓共同的人性,它们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⑦]
这种虚怀若谷的文化观念和态度终于在美国人类学家中首先达成理论的共识,这就是20世纪的文化人类学为全球一体化进程而提前准备的思想礼物——文化相对主义。伯克(Philip K.Bock)在《文化震撼》一书导言中精辟地指出:
既然文化震撼总是让人感到不适应和不愉快,那么为什么世界上的人还应当去寻找此种体验呢?对这一问题的答案已如前述:直接面对一个陌生的社会是学习相异的生活方式和反观自己文化的最佳途径。这正是为什么对每一个文化人类学家的训练都少不了至少一年的“田野作业”之缘故。[⑧]
受人类学的重要启示,文学批评家和文学史家难道不也应该补上异文化田野作业这一迟来的必修课,以便“通过揭露他自己的我族中心主义之根源,从而达到自我认识”[⑨]吗?在这方面,倒是敏感的作家和艺术家先觉一步,把人类学的启发化作个人体验的实践。这在诗人庞德回答学诗者关于创新诀窍的一句名言中体现得最为充分:你应去寻找别人没有写过的文化。
詹姆斯·阿克曼(James S.AcKerman)在谈到现代人文知识对于高等教育的挑战作用时则说得更加激进:“……我们必须牢记下述原则:产生于过去的和异文化中的知识对于我们的生存是至关重要的,因而决不能任其失落。”[⑩]
在人文研究领域寻求与异文化的对话成为本世纪以来学术创新发展的一个重要源泉,而且越来越趋向于普遍的自觉选择。
保加利亚裔的法籍批评家茨维坦·托多洛夫总结自己的学术生涯,倡导“对话批评”,可以看作是文化对话通过个人经验而凝结出的杂交优势成果的典型案例。托多洛夫回顾他在索非亚求学时所接受的文学理论教育,称之为“教条论”,因为它可用两个概念(人民性与党性)概括出来。后加入法国籍,学习了俄国形式主义等“内在论”,最终又获得了超越这两种对立理论的边缘立场。他自述说:
自从我取得法国籍后,我就强烈地感到我与其他的法国人不同:我同时属于两种不同的文化。内在与外在的两种归属,既可理解成一种缺憾也可理解成一种优越,但它却使你对文化的相异性、对“他人”的感受更加深刻。……它涉及伦理范畴中普遍与相对的对立。是否应该听从统治我们思想的宽容精神,放弃对与我们的社会不同的另一个社会的评判?或相反,如果我掌握着某些普遍的价值,我还能够避免在一个既定的(我的)模式中压倒他人吗。[①①]
文化间的边缘体验和个人的流放经历使托多洛夫获得了反思自己原有的单一立场和偏执态度的可能,这种反思终于使他克服了“普遍与相对的对立”,站到所谓“对话批评”的高境界之上。由此出发去俯视以往的问题,对话产生的觉悟效果竟是始料不及的:“我们也可以不完全拒绝普遍价值,把它当成一种与他人交流的共同点,而不是一种先验的知识。我们还可以发现我们无法占有真理,但我们却不能放弃对真理的探索。真理可以是一种相通之处、一个期望的终极。我们并不放弃真理的思想,但我们可以通过人际交流的调节原则而不是通过真理的内容来变更真理的法规及功能。总之,不同文化代表(或在我身上的不同文化成分)之间的相互理解是可能的,假如这种互相理解的愿望存在的话。”[①②]在这里,比较作为异质文化对话的形式导致了认识论上的突破,而文化相对论的态度则引发出新的真理观:真理不在形形色色的自我本位者和民族自大狂的手中,真理就在对话中的“相通之处”。托多洛夫就这样以现身说法的方式帮助人们理解他所主张的“对话批评”的产生。这种在个人学术经历中实现的文化对话不是以缩影的形式预示了文学人类学的可能性吗?
四、后殖民时代多元对话与人类文学经验的整合
文学人类学的真正建立有待于全人类各民族文化的文学经验之整合与会通,在这方面要走的路还相当长远。并不是简单地收集汇编起各国的国别文学史就能实现整合人类文学经验的目标,事情还不是这么简单。文化研究的新进展启迪我们,现有的文学批评和文学史因受到各种形式的沙文主义、我族中心主义和权力话语的宰制,实际上充满着历史偏见和文化盲点,在所谓的世界文学的版图上还存在大片的受压抑的沉默区域。也只是到了本世纪的末期,借助于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消解中心的重大功绩,各种边缘的声音和非主流话语才第一次受到学界的重视。而后殖民主义的批判潮流正以空前的广度和号召力在世界范围内唤起“弱势话语”,“少数文学”、“第三世界文学”的众声喧哗新局面。只有经过这一番风雨之洗礼,文化的多元主义才有可能从有限的多元走向为真正的多元,人权和民主的目标才能在文学话语世界得到相对的认可,从而为文学人类学的构想开启大门。
就此意义而言,文学人类学的建构绝不仅仅是笼统的所谓“东西方对话”就能完成的,文化对话实际上意味着丰富得多的层次,包括东方内部的对话和西方内部的对话,一国之内不同民族和地区的充分对话,等等。
以中国为例,迄今尚没有一部名符其实的体现多元与对话的《中国文学史》,56个民族中有55个民族的文学尚未被纳入汉族中心主义者的文学史视野,更不要说台湾文学、港澳文学这样一些新近被分离出中国大陆主流文化的边缘地区之文学了。而台湾文学自身的主流话语又是把世世代代生息在这个岛屿上的原住民文学排斥在外的。只是到了最近几年,原住民文学的可能性问题才被正式摆到了比较文学研究的议事日程上来。[①③]从大背景看,这种值得注意的寻找盲点的尝试,是在80年代文化研究中异军突起的美国原住民(印第安人)文学的再发现和再阐释浪潮波及之下的远东激起的连锁反应。20世纪以来,“重写”美国文学史的呼声已经在不同时期留下了三代人的实绩。1988年问世的艾利奥特《哥仑比亚版美国文学史》便是多元文化时代的“重写”标本:作者以强调歧异性、丰富性和异质文学的共存而自豪,标举出美国文学的四大源头:美洲印第安人、英国人、西班牙人和清教徒。尤其值得夸耀的是,该书将由印第安奇奥瓦(Kiowa)族作者司各特·莫马迪(N.Scott Momaday)撰写的《本土之声》(The Native Voice)作为全书首章,因为这本土之声在时间上比殖民者的到来早得多, 在空间上也是名符其实的本土的。
然而,从长远的眼光看,不妨把时下正热的“后殖民主义”和“民族批评”看成是和“比较文学”一样的过渡时期的文化现象,其历史使命一旦完成,退潮后所留下的将是相对平和、丰富的多元文化之声,或者就是19世纪先见智者们所期待的“世界文学”——文学人类学的新时代。
曾经充当解构主义冲锋陷阵的主将,现今又走入文化批评阵营的米勒,在回答关于第三世界文学和少数文学的问题时说出如下富有预见性的见解:
“少数文学”、“第三世界文学”、“后殖民地文学”现在使用起来也许是正确的字眼,但我认为很快就会过时了。我们一般正进入文学研究的新时代,在这个新时代中,传统西方国家文学对于一般学校和大学文学研究的宰制,将被改变为更宽广的多语言、多种族的研究模式。在这个研究文学的新方式中,问题将不是少数对抗多数,或边陲对抗宰制、霸权,而是以不同的研究方式,一起研究来自许多不同文化的许多不同语言的文学。我认为在所谓的文化研究的发展中,那种情形已经发生。所有这类研究的名称,都带有帝国主义或欧洲中心的的回响。一提到“后殖民研究”或“民志学研究”,本身就已经造成许多问题了。目前我们还没有更好的名称。[①④]
在中心和霸权受到质疑而日益消解的后殖民时代背景中,文化与文化之间追求平等对话已不是梦想。而平等对话的实质是一种互为边缘化的尝试,其结果必然是我族中心主义价值观的打破,以及各自话语性质的调整和改变。人类各族文化数千载以来形成的“唯我独尊”观念和“远方异人”观念,正面临着彻底瓦解。半个世纪以前,韦勒克所忧虑的那种构成对总体文学认识障碍的“国家主义的感情和民族主义理论”也开始走向瓦解,只爱自己的国家,而害怕别的国家的普泛心态终将得到改观。廖咸浩先生在为《中外文学》杂志“国家文学专辑”所写的编辑报告中写道:
每一个社群都有某种程度“自主”的欲望。但是这种自主的欲望经过浪漫时期以来的合理化、神圣化与图腾化之后,却形成了“国家”或“民族国家”(nation)的观念。“国家”的观念虽然有瓦解“帝国”的历史性正面意义,但是,它在此后历史中却一再地重复帝国的企图,而且由于国家机器的形成与精致化,国家对封闭与一致的讲求所加诸人民的压迫甚至更大于帝国。因为,当国家被奉为终极意义的时候,所有“异常”的砂粒都不由自主地被吸入了国家多泪的眼中;它们最后总会被揉出来,或者自己流出来。所以“国家”的观念出现之后,也就注定了“国家散裂”(dissemi nation)的接踵而至。[①⑤]
一旦国家的图腾被去除神圣化,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在现实生活中尚不具备破除国家间隔的实际条件的情况下,靠什么样的途径去培养一种超离狭隘的文化集团利益的、世界公民所应具备的肚量和心态呢?从历史的经验来看,人类学知识的传播和各国文学之间的国际贸易都曾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文学史家发现,以进化论为主的人类学思想曾在中国现代作家中培育出空前的“世界主义意识”。在鲁迅、茅盾、周作人、郑振铎等人着手编辑“世界文学大系”或收集、翻译、研究各国神话、童话和小说的背后,可以看到受进化论影响而孕育的世界一体的观念:
历史、人类学、心理学领域中新理论的发展,都有助于鼓舞这个信念:把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比之将人类作为一个个特殊的种族或者民族来判断,是一种更进步、更明智的思想方法;这是20世纪西方知识分子的普遍信念,并且在中国反映出来了。[①⑥]
与文学家受到人类学思想启蒙的情形相对应,人类学家把文学经验的跨国界传播视作世界公民教育的最好教材。伯克便这样认为:“伟大的文学作品,借助于读者的想象,常常能够比数月的实地体验传达出更多的有关异文化生活方式的经验。如果你在适当的年龄读了《艾丽丝漫游奇遇记》,并在某种程度上进入到艾丽丝的好奇与挫折之中,那么你便已经有了一次文化震撼的生动体会。某些人类学家,如马格丽特·米德、奥斯卡·李维斯和伊丽莎白·托马斯,也都因为善于捕捉和传达其它社会的文化精髓而著称。然而,对于美国社会却很少有像纳博科夫的小说那样具有穿透力的认识。只要你通过《洛丽塔》中主人公汉勃特·汉勃特那惊异的眼光去观测,你就会获得这种认识。”伯克在如此强调文学作品的人类学价值之后,做出了以下论断:“事实上,对任何艺术作品的敏锐思索——从荷马史诗到毕加索绘画,都能扩展我们的人性观念,并加深我们对自身的理解。这正是人文主义的人类学所追求的宏伟目标。”[①⑦]
可以预期,在下一世纪中,随着跨学科交流的发展,文学艺术的人类学价值将会得到更广泛的重视和更深入的开掘与利用,而人类学的影响也会进一步拆除文学经验的国别和文化界域,把诸如《北京人在纽约》、《日本人在巴黎》之类的猎奇式体验引向人类文学经验整合的总体目标。
五、结论
通过对20世纪的文学研究——特别是比较文学发展脉络的历史回顾,笔者提出在文化对话的广阔背景上建立文学人类学的可能性,以期为未来的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确认中远期目标。
从文化人类学对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的双重影响着眼,比较文学作为通向文学人类学目标的必由之路,作为加强文化交往与文化沟通的有效途径,作为克服民族中心主义心理障碍,确立文化相对论平等对话观的有益工具,已日益变得明确和必要。随着后殖民时代的真正多元对话的展开,文学研究本身获得了发掘文学艺术的人类学价值,促进人类文学经验的会通和重新整合的重大使命。而文学经验的世界性整合将成为先期破除国族的和地域的疆界,培养具有世界主义人文素质的新时代国际公民的最佳教育手段。
在通向文学人类学目标的理论话语建构方面,笔者主张本土话语与外来的话语的对译、互动和再阐释。并把未来的世界话语的形成视为绝对的目标,而把本土话语的封闭自足视为相对的历史遗留现象,并力求析解纯粹本土话语神话背后的狭隘偏见和民族自大心态。
本世纪中叶以来西方文学理论家和人类学家在尝试文学人类学研究方法和绘制新的超学科理论体系蓝图方面,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并通过多种视角和学科背景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①⑧]如何从第三世界的边缘视点出发对这部分理论遗产加以清理和综合,消解其欧洲中心主义的架构,纠正其盲点,并发扬各种弱势话语的互补优势,建构真正多元对话基础上的文学人类学,已成为即将到来的新世纪摆在中国比较文学学者面前的重要理论课题。
注释:
① ②洛里哀:《比较文学史》,傅东华译,商务印书馆1930,上海书店1989,译序第5—6页;第98页。
③尤金.N.科恩等:《文化人类学基础》,李富强编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78页。
④J.雷米:《自我表现与边界游戏》,王宾等主编《狮在华夏:文化双向认识的策略问题》,中山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74—275页。
⑤斯梅尔塞:《社会科学的比较方法》,王宏周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2页。
⑥《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陕西师大出版社,1986年版,第11页。
⑦马格丽特·米德:《萨摩亚人的成年》,周晓红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页。
⑧ ⑨Philip K.Bock ed.,Culture Shock—A Reader in Modern Cultural Anthropology,Alfred A.Knopf,Inc.,New York,1970,P.xi.
⑩James S.Ackerman:"Two Styles:A Challenge to Higher Education",Daedalus,1969,Summer,p.861.
①① ①②托多洛夫:《批评的批评》,王东亮等译,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73页;第174页。
①③参看孙大川:《原住民文化历史与心灵世界的摹写——试论原住民文学的可能》,《中外文学》第21卷7期,1992年12月。
①④单德兴:《米勒访谈录》,《中外文学》,第20卷4期,第108页,1991年9月。
①⑤廖咸浩:《编辑室报告》,《中外文学》,第22卷4期,第6页,1993年9月。
①⑥B.S.麦克道格尔:《西方文学思潮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见《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潮》,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1页。
①⑦Philip K.Bock:Culture Shock,p.xi.
①⑧参看拙作《西方文学人类学研究述评》,《文艺研究》1995年第3—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