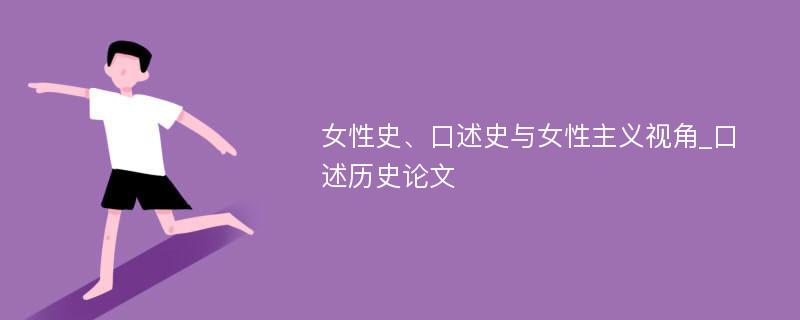
妇女史、口述历史与女性主义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角论文,妇女论文,女性主义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让女性发音:女性口述历史的重要性
综观各个历史时期,人类历史的另一半——妇女基本上被排除于战争、经济、政治、文化、科学与艺术的领域之外。女性成了人类历史的“缺席者”,她们的历史地位与作用得不到应有的反映与呈现,她们的经历被忽视,她们的贡献被淹没,她们成了名副其实的“沉默群体”。即便偶然写到女性,也是因为她们的活动与经历与男性有关。
20世纪初,随着新史学运动的蓬勃发展,一部分西方激进的历史学家号召彻底摆脱传统史学只注重男性精英人物的历史观,而要求重视下层平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并撰写有关他们的历史。在这股“自下而上”的史学运动中,西方女性主义史学家倡导的妇女史成为史学界中最具活力与创新精神的领域之一。
但是,妇女史研究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女性史料的匮乏。于是,妇女历史学家便提倡一种让每个妇女都有机会说话的方式来撰写女性的历史,而当时口述史学的兴起与发展正好迎合了妇女史研究的需求。正如中国20世纪妇女口述史计划主持人李小江教授所说的,“妇女史与口述史具有天然的盟友关系。……而妇女史的崛起和口述史的重新启用,几乎是在同一个时间段上(20世纪中期)同步进行,两者相互推动,成为近代以来史学革新运动中比肩行进的战友。”(注:李小江:《女性的历史记忆与口述方法》,《光明日报》2002年8月16日。)于是,挖掘女性口述历史便成为让女性进入历史叙述的重要手段,从而实现第一次女性主义运动中女性主义者所提出的女性与男性共创历史的观点,肯定妇女在历史发展中的能动作用。
口述历史在妇女(史)研究中的意义首先在于发现了被传统历史学家认为“非官方非正式”因而无关紧要的社会经历,通过“让女人说话”来填补历史空白,丰富历史内容,女性口述历史学家强调女性口述历史的第一位在于“挖掘,挖掘,挖掘”。(注:Susan Armitage and Sherna Berger Gluck,Beflections on Women's Oral History:An Exchange,Frontiers:A Journal of Women's Studies,Vol XIX,No.3,1998,pp.8,10.)
通过女性口述历史挖掘沉默的声音虽然部分地改变了女性“缺席”的处境,但是口述历史的意义不仅仅在于“让女人说话”,而在于“用女人自己的语言说话”。传统历史学造就的女性“失语”的原因就在于女性了解与表达自己与对世界看法的方法都来自那些占据特殊位置的男性话语,所以要真正实现女性重回历史,必须坚持从女性的经历出发,倾听女性自己的声音,让女性成为自己经历的发言人,正如肖娜·格拉克(Sherna Berger Gluck)所说的,“不再保持沉默,妇女们正在创造一种新的历史——运用她们自己的声音和经历……运用与人类记忆同样古老的口头传统,我们正在重建我们自己的历史。”(注:Sherna Berger Gluck,What's So Special About Women?Women's Oral History,Frontiers:A Journal of Women's Studies,Vol.II,No.2,1977,p.3.)
第三,女性口述历史有助于促进妇女研究的跨学科发展。最能反映这一特点的是由格拉克与达芬尼·帕特(Daphne Patai)主编的《女性的话语:口述历史的女性主义实践》一书。该书集中了一大批来自历史学、人类学、交际学、语言学、民俗学、文学、社会学、心理学等领域的专家写就的。正如两位主编在前言中所指出的,传统的口述历史方法已经不能很好地满足女性口述历史的兴趣,我们必须利用跨学科视角,只有如此才能更为深刻地理解女性主义口述历史的复杂性。(注:Sherna Berger Gluck and Daphne Patai eds.,Women's Words:The Feminist Practice of Oral History,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Introduction,pp.1-5.)
对于女性口述历史学家来说,从事女性口述历史不仅仅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学术成就进而为自己获得提升的机会,更为重要的是,女性口述历史是一项兼具学术性与政治性的伟大事业。这一宗旨为中外的女性主义学者所深信并坚持,李小江教授指出,“‘让女人自己说话’,是建构妇女史的基本原则;发出‘女性的声音’,在今天社会中兼有政治的和学术的双重使命。找回和重建女人的历史,不仅是史学的需要,更是女人找回自我,确立自主、自信的人生的必要基石。”(注:李小江:《女性的历史记忆与口述方法》。)美国加州州立大学长滩分校历史系鲍晓兰教授通过她的女性口述历史实践也深刻感到,“妇女口述不仅是一种重要的研究手段,而且是一种政治手段,即通过对妇女经历的肯定,增强妇女的自信心,从而赋权于妇女。”(注:鲍晓兰:《西方女性主义口述史发展初探》,《浙江学刊》,1999年第6期,第85页。)
口述历史过程不仅对于访谈者或使用这些资料的人来说是重要的,而且对于受访者本身也是同样如此,让女性自己说话,是对于长久以来被传统的精英历史所忽略的普通妇女的生活经历的认可,有助于提高女性的自尊心,并且促进女性群体的团结以及对于女性集体记忆与认同感的追寻。通过对于女性经历的认可并因此帮助她们挑战在日常生活中遭遇的男性至上主义,挑战现存社会性别观念,争取社会平等。
二、学术史回顾:中外女性口述历史的历史性考察
西方女性口述历史(主要谈美国女性口述历史)最先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初,它的动力主要来自于一些基层计划,比如1972年由格拉克主持的“女性主义历史研究计划”、1973年由科基·布什(Corky Bush)主持的“爱达荷州农村女性口述历史计划”和1975年由苏珊娜·哥特(Suzanne Gott)等人主持的“蒙大拿女性历史计划”等等。在这些计划的影响下,根据妇女研究杂志——《边缘》(Frontiers)1977年“女性口述历史专题”统计,到1977年全美总共有18个州开展了大约30余个集体性女性口述历史计划,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个人女性口述历史计划。(注:Women's Oral History Resource Sections:Projects and
Collections,Frontiers:A Journal of Women's Studies,Vol.II,No.2,1977,pp.125-128.)70年代女性口述历史主要处于发现被忽略的女性生活经历的“挖掘过程”,而且访谈的对象主要集中于著名白人女性。作为这一阶段女性口述历史实践的学术成果,就是1977年《边缘》杂志的“女性口述历史专题”,该专题主要集中分析了女性口述历史学家参与具体计划的实际经验,不过并没有集中地探讨口述历史的深层次问题。
进入80年代,女性口述历史计划继续发展,据1983年《边缘》杂志“女性口述历史专题Ⅱ”统计,全美总共有27个州开展了大约50余个涉及妇女的集体性口述历史计划。(注:Nancy D.Mann,Directory of Women's Oral History Projects and Collections,Frontiers:A Journal of Women's Studies,Vol.VII,No.1,1983.pp.114-121.)而到80年代中期,女性口述历史领域发生三大转变:(1)访谈的焦点迅速转向普通女性和有色人种女性;(2)一些大型女性口述历史计划的财政支持迅速减少。(3)由于赞助资金减少,女性口述历史计划开始从社区转入学院,大型合作性集体计划几乎消失,不过由从事妇女研究的研究生与学者主持的小型口述历史计划迅速增加。这种学院式操作促进了女性口述历史理论的深层次发展。而80年代末以来,集中体现西方女性口述历史学界努力的成果便是上述提到的《妇女的话语:口述历史的女性主义实践》。
在中国大陆,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女性口述历史计划是由李小江教授主持的“20世纪妇女口述史计划”。该计划从1992年9月正式启动,它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次将妇女这一主题与口述历史方法相结合的尝试,参与者逾千人次,遍及全国20多个省市和少数民族地区。(注:杨洁:《妇女口述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历史研究》1999年第2期;屈雅君:《妇女口述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评述》,《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年第4期。)
目前,大陆出版的利用口述历史进行妇女研究的比较有影响的专著有贵州省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张晓的《西江苗族妇女口述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定宜庄的《最后的记忆》和李小江教授主编的《20世纪中国妇女口述史丛书》。(注:张晓,《西江苗族妇女口述史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定宜庄:《最后的记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李小江主编《让女人自己说话:文化寻踪》、《让女人自己说话:民族叙事》、《让女人自己说话:亲历战争》和《让女人自己说话:独立的历程》,三联书店,2003年。)另外,从90年代中期开始,大陆一些期刊也开始关注女性口述历史这一主题,不过数量很有限。
在台湾,女性口述历史开展最为活跃的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该所于1992年出版了第一部女性口述历史的专书《贾馥茗先生访问纪录》(注:游鉴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1996年第4期。)此外,还有一些基于女性口述历史的故事集,目前已出版的有《阿妈的故事》、《阿母的故事》与《消失中的台湾阿妈》。(注:叶汉明:《口述史料与妇女研究:从〈走过两个时代的台湾职业妇女访问纪录〉说起》,载游鉴明:《倾听她们的声音:女性口述历史的方法与口述史料的运用》,台北左岸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2年。)值得一提的是,台湾女性口述历史不仅在实践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而且在理论研究方面也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其代表性成果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游鉴明研究员的《倾听她们的声音:女性口述历史的方法与口述史料的运用》一书。(注:游鉴明:《倾听她们的声音:女性口述历史的方法与口述史料的运用》。)
在香港,女性口述历史也开始受到学界的重视,香港新妇女协进会分别于1998年和2002年推出两部女性口述历史——《又喊又笑:阿婆口述历史》和《16+—少女口述历史》。(注:《又喊又笑:阿婆口述历史》,香港新妇女协进会,1998年。《16+—少女口述历史》,香港新妇女协进会,2002年。)
三、女性主义口述历史如何可能?
在这里,之所以强调女性主义口述历史,是为了区别于一般的女性口述历史。因为随着女性主义的发展,其理论与方法不断被女性口述历史学家所借鉴,尤其是“社会性别概念”与“差异理论”大大地影响了女性口述历史访谈过程以及对于口述历史的分析。
社会性别概念是当代西方女性主义学术和理论的核心概念。它的产生来源于对传统妇女史写作弊病——单纯地把妇女填补到历史中去,没有把妇女置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进程中来研究,没有把女性与男性的认识结合起来进行考察——的反思。(注:琼·凯利—加多:《性别的社会关系——妇女史在方法论上的含义》,载王政和杜芳琴主编《社会性别研究选译》,三联书店,1998年,第82-100页。)女性主义口述历史学家对于社会性别概念的敏感,必将提醒她们更加重视女性口述过程中所展现的与社会各方面的复杂关系。
差异理论的产生来源于女性主义者对“妇女”这个范畴的反思。到底“妇女”是一个单一的范畴,还是一个具有极大差异的范畴?到底“妇女”是先历史而存在,还是历史所形成的社会范畴?女性主义者出于政治目标,为将妇女动员起来,组成一个具有共同政治纲领的社会群体,便极力强调女性之间的“姐妹情谊”,就这样,女性主义的历史成了一部削减女性之间差异的历史。这些差异(即阶级、种族、政治、宗教以及经济状况等差异)被缩减成一个妇女的共同身份。(注:琼·W·斯科特:《女性主义与历史》,载王政和杜芳琴主编《社会性别研究选译》,第365页。)
而差异理论给予女性主义口述历史学家的启示是:作为女性口述历史访谈的女性受访者,她们的社会身份是多元化、多层次、多方位的,除了阶级、种族、社会性别的差异外,还有教育、年龄、信仰、政见、自我意识与价值观等等的差别。而且,在不同的背景中,这种多元化又表现出很大的不稳定性。
什么是女性主义口述历史?直到今天学术界也没有给出一个准确的定义,唯一可能的是如何在女性口述历史过程中更好地体现女性主义视角。限于笔者专业以及实践经验所限,只能结合国内外同行的实践经验来分析如何在女性口述历史过程中贯穿女性主义宗旨,建立访谈者与受访者之间的平等互动关系,通过让女性(所有弱势群体)自己发言,挑战现存的包括性别、阶级、种族等在内的所有不平等观念与现象,真正实现个人自由、民族自决与社会平等。
1.确立女性受访者的主体地位,弱化访谈者的居高临下的解释权威。
女性主义口述历史的目标就是让女性受访者发出自己的声音,改变访谈过程中访谈者以客观主体自居并企图驾驭受访者的“主客”二元权力模式,重塑女性在认识上的主体地位。女性主义者认为,让女性发音,不仅要聆听她们的生活经历,更重要的是聆听她们对于那些经历的看法与感受,因为后者更能体现男女价值观的差异以及女性的独特视角。正如有些学者指出的,“因为我们希望听到的是女性们用自己的话讲述的事而不是为了验证我们自己的预先假设,特别是我们的计划还包括了许多处于不利地位的与被人遗忘的妇女,她们的认知与学习方式、认同感转换以及道德观点很少受到学术界关注。……仔细地聆听妇女的心声与视角,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聆听那些听不到的与无法想象的来自女性的心声。”(注:Shulamit Reinharz,Feminist Methods in Social Research,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pp.19-20.)
为了鼓励受访者讲述自己的主观感受,女性主义口述历史学家主张应该提问一些能够自由回答的问题,而不要过分关注自己对于访谈进程的单方面控制,而且尤其关注访谈中那些能够集中反映女性情感的个别词语。(注:Kathryn Anderson and Dana C.Jack,"Learning to Listen:Interview Techniques and Analyses",in Sherna Berger Gluck and Daphne Patai eds.,Women's Words:The Feminst Practice of Oral History,pp.12-18.)
2.建立访谈者与受访者之间的平等互动关系。
口述历史是访谈者与受访者之间合作的产物,女性主义者认为,要建立访谈者与受访者之间的平等互动关系,首先要对访谈这一形式中所潜在的不平等关系有所认识。黛安娜,沃尔夫(Dinae Wolf)总结了访谈中的不平等关系,主要反映在以下三个方面:1、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社会身份的差异,包括种族、阶级、国家民族、生活际遇、城乡背景等等差异;2、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权力的行使,包括确定其本人与研究对象的关系、与研究对象不平等的交换、甚至对对方形形色色的剥削等;3、田野调查后权力的行使,包括研究者对研究结果的撰写和对访谈内容的“再现”。(注:转引自鲍晓兰:《西方女性主义口述史发展初探》,第86页。)
在认识到访谈中的不平等关系形式之后,那么如何在实践中建立平等互动关系呢?笔者借鉴了相关女性主义田野研究的经验做一总结,以供参考。
(一)在正式访谈之前,访谈者应清楚地向受访者呈现足以影响访谈过程的个人信息以及整个研究计划信息。
访谈者的个人信息不仅影响访谈者对于受访者信息的再诠释,而且使得受访者的叙述具有高度的“表演性”。香港社会学研究者周华山博士在云南摩梭山区进行母系文化研究时遇到的一个例子很好地说明了这种“表演性”。他曾走进摩梭家屋火塘,与风乌结梳一起喝酥油茶,吃饭时其侄儿车独支端上两块猪膘肉,并且吃了两块。后来才知道这位阿乌因为胃病已多年不喝酥油茶,但因研究摩梭文化的研究者到访,令他认为必须展示传统摩梭饮食习惯,才同周博士喝上一些;而这位侄儿也表示他其实嫌猪膘肉太腻,只在春节才象征性尝一点。周博士的出现令这些摩梭人自觉到自身的“摩梭身份”,感到有必要把传统摩梭文化展示出来,因而忽然变得“非常摩梭”。更有趣的是车独支打酥油茶时,竟忘记“初夺”敬锅庄,要由他阿乌提醒,这使得这一次“初夺”变成了一种“表演”。(注:周华山:《女性主义田野研究的方法学反思》,《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5期,第59-60页。)
此外,访谈者必须告知受访者正在进行的研究计划的目的和程序,以及该计划所要实现的目标与预期用途,并由受访者自己做出是否愿意被访谈的决定。
(二)对于反映受访者社会身份多元性的阶级、种族、民族、社会地位、信仰等因素保持高度敏感,并注意这些因素的不稳定性。
有些学者发现,如果女性主义口述历史只是表现单一的女性主体意识就是一种失败,女性主义者应该关注女性受访者社会认同感的多样性与关联性。
美国丹托克社区学院(Dundalk Community College)历史学与人类学教授卡伦·奥尔森(Karen Olson)在一项关于马里兰州钢铁制造社区丹托克的种族、阶级和性别的民族志研究中发现,她自己既有的女性主义成见深刻地影响着对于女性历史的理解。
该研究的起始目的,在于了解在蓝领阶级社群中,女性主义意识如何被经历与表达,因此计划访谈三十至四十岁的成年妇女(没有访谈男性工人的打算)。然而,妇女受访者坚定的告诉奥尔森她不可能得到一个与以她们为主的与男性分离的女性生活世界,因为现实情形是——她们的生活不可避免的与其丈夫纠结。为了能体会这些妇女如何在现实状况中妥协出令人满意的婚姻(以达到其女性主义的研究目的),奥尔森察觉她对这些男性有更多的了解。
因此,她访谈了这些钢铁工人丈夫。在访谈过程中,她了解到他们的环境如何塑造出所谓的“男子气概”。而且,她发现在钢铁厂中,白人钢铁工人如何在充满不满的氛围中抱怨监工与黑人工人。而黑人工人也必须在充满敌意的白种工人竞争工作下中,不断地设计各种策略以求生存。综观该口述历史访谈,奥尔森意识到妇女研究必须是个关于双向性别关系的研究,并且不可避免的与阶级和种族因素联系在一起。(注:Karen Olson and Linda Shopes,Crossing Boundaries,Building Bridges:Doing Oral History among Working-Class Women and Men,in Sherna Berger Gluck and Daphne Patai eds.,Women's Words:The Feminist Practice of Oral History,pp.189-191.)
而且有些女性主义研究者提出有些女性受访者也许本身并不具有“女性意识”或者按照研究者预设的“女性主义意识”。她们认为如果研究者以自己的女性主义偏见来引导受访者,可能会误导受访者的回忆。
(三)在访谈中,坚持以地方性语言与特定言语模式为本,挑战传统学术中所形成的话语霸权机制。语言作为反映历史意义与诠释过往经验的符号媒介,它深刻地影响着语言主体的自我意识、思维模式与价值取向。作为试图希望了解另一种文化的“局外人”,研究者必须学习其语言。
周华山博士警告,“……研究者永远只是从自身文化价值观和语言体系出发,把她族文化与思维化约成自身文化的符号以,“我”观物而物物皆着“我”的色彩,把她族文化削足适履而不断复制和强化既有的价值观。”他在云南摩梭山区进行母系文化研究时就深刻体会到了解被研究群体语言的重要性。但是,因为他只能进行简单的摩梭语交流而必须借助翻译者,不过他担心翻译者自身的价值取向、性别偏见与表述模式会影响原叙述者的本来意思。譬如,摩梭语没有一妻一夫、妒忌、寡妇、妇女、情人、生母、养母、继母、失贞等专有词汇,因此当翻译者用上这些汉语时,就必须搞清楚是她自己强加这些语汇于原话上,还是原话正好表述这种含意。(注:周华山:《女性主义田野研究的方法学反思》,第58页。)
虽然翻译者对于研究者的理解与最终的学术性表述是至关重要的,但是也有研究者提出为了保存语言的地方性,在采访中或整理口述资料之时,不应随意删除或更换古音、方言、俚语。只需从旁作读音和意义注释。
口述历史作为一种会话(conversation)形式,受访者口述叙事中所体现的言语模式可以显示地位、人际关系、语言的知觉理解力、自我认同以及认识世界的方法。对于言语模式的关注,对于那些很少有机会向公众社会表达心声的特殊群体来说,他们的言语模式能够深刻地揭示造成他们在公共领域“沉默”的深层次社会原因以及背后所潜藏或伪装的真实情感。西密歇根大学(Western Michigan University)英语系教授Gwendolyn Etter-Lewis在一项利用黑人女性口述历史来分析黑人女性自我意识的研究中发现黑人女性叙事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频繁的掩饰”(frequent understatements),即避开第一人称的叙事观点,很少提及个人的成就与掩饰个人权力欲望的声明。而这种叙事特点可能与长久以来社会并不鼓励黑人女性自由公开地表达她们的傲慢与自信有关。(注:Gwendolyn Etter-Lewis,Black Women's Life Stories:Reclaiming Self in Narrative Texts,in Sherna Berger Gluck and Daphne Patai eds.,Women's Words:The Feminist Practice of Oral History,pp.44-49.)
(四)重视口述历史访谈中访谈者与受访者之间的权力关系,实现口述历史成果的共享。这种权力关系表现为两个方面,即访谈者把受访者当成“工具”与受访者把访谈者当成“工具”两个方面,因而口述历史过程就成为双方相互角逐权力的舞台。毫无疑问,在整个口述历史过程中,访谈者设计研究计划、寻找受访者、设置问题、编辑访谈、撰写总结报告以及最后以某种形式公开发表,这一切都是以访谈者的预先目标安排的。这种不平等尤其是对那些处于弱势群体的妇女来说更加显得是一种赤裸裸的剥削。
当然,我们也应该警醒受访者潜在的权力,即同样的,受访者是否把访谈者当成“工具”?这种“工具性”尤其体现在访谈者是受访者雇佣的。受访者的潜在权力则体现在在访谈中,他完全可以根据访谈者的现场反应作出自己的回答,即经过所谓的“听其言,观其行”后,受访者会对访谈者的意图、能力以及某些预设作出判断,进而决定自己口述的内容以及内容的深度与广度。如果受访者意识到访谈者的某些对他的不利意图,他会最终离开访谈者的既定轨道,又或是使访谈者仅仅成为了受访者的“发泄对象”。
关于如何做到成果共享?女性主义者还做了许多具体的尝试。比如,在与访谈对象接触的过程中,尽可能为其及其所在社区提供可能的服务。有的访谈者还和访谈对象平分成果的经济报酬和同注为作品的合作者等。(注:鲍晓兰:《女性主义和倾听妇女的声音——意义、方法和思考》,第10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