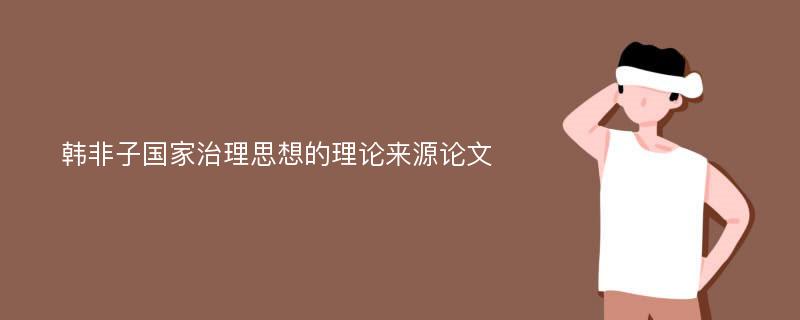
韩非子国家治理思想的理论来源
张茜倩
(苏州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苏州215400)
摘 要: 韩非子国家治理思想的形成,受到了诸子的深刻影响。韩非子从儒家思想中借鉴了有关人性的看法以及制度主义,从墨家借鉴了专制主义,从道家借鉴了世界观及方法论。在此基础上,以商鞅为代表的法治、以慎到为代表的术治、以申不害为代表的势治,对韩非子思想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 韩非子;国家治理;理论来源
韩非子为韩国贵族,与李斯同求学于荀子。司马迁认为其“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韩非因劝谏韩王而不用,悲愤下留下了大量作品。在这些作品中,韩非子在批判继承既往学说的基础上,创建了自己关于治国理政的学说体系。韩非子思想既是对前人学说的综述,又开启了下一世代的理论学说,而对韩非学说的阐述,乃至对于韩非学说的实践,则一直延绵到近代。因此,梳理各家学说对韩非子的影响,是有必要的。
一、儒、墨、道思想对韩非子的启迪
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底色。延绵两千年的君主专制自战国酝酿成熟,而围绕如何治理国家的思想碰撞则尤为激烈。韩非子作为战国末期最为重要的思想家,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诸子学说的影响。他的治国理念是对此前诸学派的重要发展。
(一)借鉴儒家有关人性以及制度的看法
韩非子师从荀子,其思想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儒家烙印。韩非子的国家治理思想,与荀子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荀子思想中包含有“性恶”而“崇礼”的逻辑。荀子在《性恶》篇中鲜明提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1],并对孟子的性善论进行了批判。他更从国家治理层面讨论了性善论的错误。他反问:“凡古今天下之所谓善者,正理平治也;所谓恶者,偏险悖乱也。是善恶之分也已。”[1]以现实中政治纷乱的格局为反证,荀子认为,假设人性本善,那么政治一定天然地可以获得和平,而不需要人为因素,但现实情况却并非如此。由此,荀子推论出一个重要的国家治理原则,即需要按照既定的礼对国家进行治理。其礼治思想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礼来源于对人性恶的认知与抑制,二是礼的制定者与实施者为君主,三是礼的内容实际为客观制度。
虽然我国开始推行素质教育,但是传统应试教育还是影响着教育的发展。初中学生依然摆脱不了英语中考的命运,所以老师无法真正给小组合作学习模式留下足够的学习时间和讨论时间,无法真正让学生通过小组合作学习来达到提升自己英语素养的目标。小组合作学习模式在中考升学压力面前就变成了摆设和形式,小组学习模式的自由性被极大的限制。
承认人性恶而以确切的制度治理国家,是荀子思想之于韩非子的重要影响。韩非子进而把礼阐释为法,明确了以法治国的基本思想。这是对儒家思想的继承与发展。韩非子认为,人都有“自为心”,人人都为自己着想。他以医生、车夫、匠人为例说,医生为病人吸吮伤口是因为有利益,车夫希望人人富贵是因为那样人人都可以乘车,匠人希望人人都死是因为那样可以顺利地卖掉棺材。人的行为动机都与利益相关联。通过这些例证,韩非子说明了人性为利益而存在。这种自利心对于荀子的性恶论主张是一种扩展。韩非子所主张的性恶论与荀子类似,都是从人的自然欲望出发以满足人自然欲望的需求,即为生而有之的“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的人类属性。正是这种自然追求,使得人不可能自然而然地实行仁爱。值得注意的是,韩非子不仅仅将自然欲望视为正当,更将所有人类欲望合理化。在韩非子看来,社会需求与自然需求一样十分正当。例如他认为“霸王者,人主之大利”,“富贵者,人臣之大利”。[2]对于君主而言,成就霸业是其利之所在;对于大臣而言,富贵是其利益所在。这两种利益显然都超越了温饱的基本生存需求,而扩张到了个人价值的实现。韩非子还认为“利之所在,民归之;名之所彰,士死之”[2]。名则属于一种精神利益,显然大大超越了温饱的自然需求。因此韩非子对于个人所欲的认识,实则在内涵上远比荀子更为丰富。不仅如此,韩非子还把人对各种利益的追求视为人之常情,认为人们应当顺应这些追求,即其所谓“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2]。以此对比韩非子与荀子的主张,可见二者实则对于人之欲望的承认,有着不同的限度。首先,二子均承认人内在的欲望,并认为这是一种恶。但在荀子看来,人性虽恶,最终可以通过教化而使其归于善。也就是说,在荀子看来,这种人性,归根到底可以通过制度运行进行修正,从而实现人性之善,即所谓化性起伪。而韩非子却认为,这种欲望属于人之常情,不需要去矫正,只需要认同并利用这样的人性就行了。正因此,韩非子的人性论,并没有简单的善恶区分,而是客观承认个人趋利避害的个体需求。基于人性的趋利避害,韩非子在国家治理方面,认为所有人都是可控的。在他看来,这种控制手段,就是通过惩罚与奖赏对人进行诱导,从而实现国家富强的目的。
韩非子的法相较于商鞅,更具有抽象与普遍的特点。商鞅谈及法时,不仅仅明确了法的平等性、普遍性与公开性等特征,更指一种鼓励农战的军国主义法令。他主张“圣人之治国,作壹抟之于农而已矣”[5],乃至后世有学者认为“商君之道,农战而已矣”[5]。这是战国中期面临的严峻情势而带来的必然选择。韩非子则站在更高的理论立场上,将法的作用提升到君主掌握权力以稳固秩序的高度,而不仅仅将其视为推动国家强盛的工具。“法分明,则贤不得夺不肖,强不得侵弱,众不得暴寡”,“立法,所以备曾、史也,所以使庸主能止盗跖也”。[2]在韩非子看来,只要明确了法律,普通的君主同样可以实现社会治理,而不只是简单地为国家在战争中赢得胜利。细究商韩之别,商鞅“欲举一国之学术文化而摧毁扫荡之,使政治社会成为一斯巴达式之战斗团体”[6],但是韩非子则注重建立起国内稳定的政治统治。萧公权先生认为:“孕育长养此诸观念之历史环境,一言以蔽之,即封建天下崩溃过程中之种种社会政治事实而已。就政治方面言,封建崩溃之直接结果为天子微弱,诸侯强盛。然强盛之诸侯非旧日分土之世家,而每为新兴之权臣所篡夺。……于是君权之扩张遂同时成为政治上之需要与目的,而政治思想亦趋于尊君国任法术之途径矣。”[6]客观地说,在实现统一,恢复天下和平秩序后,韩非子的思考更加具备普遍性,实际上为后世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做了思想准备。
(二)借鉴道家的世界观及方法论
在韩非子看来,“法、术皆帝王不可一无之具”。术与法对于国家治理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师也。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2]可见韩非子认为二者不可偏废。申不害重术而轻法,导致“不一其宪令则奸多故”,缺乏稳定的标准,于是“奸臣犹有所谲其辞”,导致韩国无法强盛。在刑赏执行上,韩非子吸收了申不害的术治理论,以刑名为刑赏依据:“人主将欲禁奸,则审合刑名者,言异事也。为人臣者陈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专以其事责其功。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罚。故群臣其言大而功小者则罚,非罚小功也,罚功不当名也。群臣其言小而功大者亦罚,非不说于大功也,以为不当名也害甚于有大功,故罚。”[2]他还以韩昭侯兼罪典衣、典冠二臣故事,对其加以说明。韩昭侯醉后就寝时,典冠担心其受凉,于是为韩昭侯添加衣服。韩昭侯醒后得知情况,认为典衣未履行好职责,同时典冠越权行事,同时惩罚二人。在这一故事中,可以看到韩非子刑名为本的刑赏策略,是严格按照职务所定权限考核官员,并以此为赏罚的根本依据。韩非子的刑赏思想,其所欲达到的效果是“独制四海之内,聪智不得用其诈,险躁不得关其佞,奸邪无所依。远在千里外,不敢易其辞;势在郎中,不敢蔽善饰非。朝廷群下,直凑单微,不敢相逾越”[2]。可见相较于申不害,韩非子治理群臣,实则是更加偏重于刑奸,即藉助除掉奸臣从而实现大权在揽。从政治理论上看,其是为建设新的君主专制国家做理论准备。
(2) 提出了基于库水位运行工况概化,通过GeoStudio软件SEEP/W模块获取各工况下的滑坡渗流场,并依次将其导入FLAC3D获取滑坡位移场的水库型堆积层滑坡位移预测方法。
(三)对墨家专制主义的借鉴
墨子的学说以“兼相爱,交相利”为本。墨子认为,天下大乱的原因就在于不相爱。人性复杂,往往不能以同一价值观要求所有人,于是墨子构建了集权政治体制,以在集权政治中实现兼爱。墨子从人性上认识到人与人相互间的不同是不相爱的缘起,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提出建立“尚同”的政治制度,将全国上下之“义”同归于一。每个人都有相同的价值取向,则不会发生相互争夺(“交相恶”)的乱象,而能够使天下人都同为一义的人,则是天子。墨子主张:“明乎民之无正长,以一同天下之义,而天下乱也,是故选择天下贤良圣知辩慧之人,立以为天子。”[4])即择贤者为天子,而天子则负担起同天下之义的责任,以推动社会大治。墨子学说开启了战国至后世的一元政治格局,为君主制开先河。这一政治体制应当为墨家对后世政治学说的重大贡献,即树立绝对政治权威以弥合社会分歧,治理国家。
这些思想同样为韩非子所接受。在《主道》篇中,韩非子认为:“道者,万物之始,是非之纪也。是以明君守始以知万物之源,治纪以知善败之端。故虚静以待令,令名自命也。虚则知实之情,静则知动者正。”[3]在这段话中,可以看出,韩非子认同道为世界的本原(万物之始),并引申到伦理规范(是非之纪)。基于此,他提出治理国家的法则为“虚静”。这都是对道家学派尤其是黄老学说的继承与发展,但韩非子摆脱了过去神秘主义的天降圣人说。他认为统治者的出现,是因为个人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而成为圣人:“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近古之世,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2]有巢氏、燧人氏、尧舜禹汤这些上古圣人,并非天生,而是人为。在韩非子看来,统治者是行动在人间的智者,他们运用自己的能力推动社会进步,进而构建了合法的统治基础。
申不害思想的内核主要为“君人南面之术”,即君主如何控制臣属的策略。申不害的术治思想,在根本上以“清净”为指导,在具体实施上以“刑名之术”为策略。就道论而言,申不害的哲学本体论、生成论与黄老之术一脉相承,倡导君主在统治上实现守静的自然姿态与制衡的能动精神的统一。[7]在具体执行上,他认为,一方面要深谙“南面之术”去智弃心,另一方面要积极运用权术以管理官员。申不害主张“为人君者操契以责其名”,即君主用以选拔、监督和考核群臣的方法,所谓“名者,天地之纲,圣人之符”[8]。名即是法律所规定的职责,官员应当严格按照名所规定的内容行事。申不害发扬了这种名学思想,主张君主“以其名听之,以其名视之,以其名命之”[9]。这样可以有效控制臣下,从而实现治理。申不害的术治以黄老清净思想为根本,为君主维护权力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法家理论以法治为核心,与儒家的礼治形成鲜明对比。站在时代发展的角度看,社会形态由过去的奴隶制度向封建制度过渡,是必然的变革。这一变革在商鞅变法中展现得淋漓尽致。根据《史记》记载,商鞅为卫国公子,“少好刑名之学”,对法律很有兴趣。入秦后,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商鞅主持变法,使得秦国迅速成为战国七雄之一,为兼并六国,建立统一国家奠定了基础。商鞅对法的崇尚,是先秦政治学说法治理论的最强音。商鞅的法治理论包含以下三方面内容。一是法自君出。这里明确了君主立法的必要性,即为了消弭纷乱,必须通过立法以“止乱”,维持社会秩序;而为了保持法的稳定性,则需要维护君主权威,“君尊则令行”,否则“虚君位而令不行则危”[5]。二是法以时定。法不能一成不变,需要有变化。这是对君主立法权的发展,即所谓明君应当制定怎样的法律。商鞅认为“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所有称王称霸者,都经历过变法,所以变法并不意味着紊乱,反而是富强的前提。他进而提出“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文、武,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法以时而定”的立法观[5],强调时与法的关系。三是壹刑重刑。商鞅赞扬重刑主义,并强调法的统一性。商鞅主张“圣人之为国也,壹赏,壹刑,壹教。壹赏则兵无敌,壹刑则令行,壹教则下听上”。在壹刑的主张下,商鞅同时强调应当重刑。其目的在于充分强调惩罚的意义,以普遍性的刑罚适用,推动国家治理的实现。
二、集三派而成一家
在韩非子之前,先秦法家的代表人物为管仲、商鞅、申不害、慎到等政治家。他们在自己的政治实践中,积累了相当的政治理论,为韩非子的理论构建,提供了直接的思想源泉。韩非子糅合法、术、势而成一家之言,实则是对先秦法家学派的继承与发展。
(一)对商鞅“以法治为核心”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重庆九院院长阳光介绍,成研中心汇聚了全市的医学管理、卫生经济、经济管理、医学教育等专家。中心下设9个研究室,在实践过程中,中心形成了院内、院外、医改三个重点工作方向:院内主要为标准化成本核算与医院DRG任务联合工作开展方案、BSC+RBRVS创新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方案;院外重点研究民营医院医疗质量安全与成本消耗的内在规律、国有企业医院转制重组的理论与实践等内容;医改方面重点研究标准化成本体系建立问题。
在圈定的注浆加固范围之内,以1×1m的间距对注浆孔进行布置,呈梅花形布置。孔位布置完成后,监理工程师应对其进行检查,确认无误后进入下一道工序。
(二)对申不害“南面之术”的继承与发展
韩非子赞赏墨家的专制主义,但是墨家的专制基础,来源于天的命令,即君主的权威性来源于天,是上天在人间的反映。墨子认为文王之所以获得天下,是天赏赐:“《皇矣》道之曰:‘帝谓文王,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不长夏以革,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帝善其顺法则也,故举殷以赏之,使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名誉至今不息。”[4]因此墨家的专制主义,有一层浓厚的神权主义色彩。韩非子则不同。他在吸收墨家理论的基础上,更在哲学层面秉持原始唯物主义。他认为客观的道是世界的主宰,这使君主更具备客观性,君主是事实上的主宰。他所构建的君主权力,直接来源于君主自身,在政权中理所应当然处于最高地位,因此他提出的法治理念是为专制君主服务的。韩非子的国家治理逻辑在于国家政局紊乱,必须要有一个稳定的治理核心,而这一核心即君主。君权稳固,则所有人的行为都可以有确定的目标,又因为君主是政治核心,因此韩非子设计了一整套理论来维护这一君权。典型如政治制度的演进,其所有出现的分权制衡理论,实则都是服务于君主擅权的。由此可见,韩非子的君主至上理论,是法家政治理论的总结,强调了现实政治中君权的正当性、合法性。
《史记》将韩非子与老子并入同一列传记载,可见在司马迁的观念中,韩非子的思想与道家非常接近。韩非子著有《解老》《喻老》二篇,以阐释《老子》思想。事实上,对韩非子国家治理思想影响最为显著的,是以老子学说为基础,于战国时期形成并发展的黄老思想。道家以道为世界形成的源泉。道作为世界发生的源泉,同样是世界发展的依据。所以在国家治理上,道家认为同样要顺从于道。老子认为:“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3]可见道是道家学派政治理论的核心。黄老学派在这一基础上进一步阐发,主张道与法同一。换言之,道即是法。道家学派在后期发展过程中,逐渐认识到了道与法的辨证关系,使道家思想更贴近于统治需求。在方法论上,道家学派同样以道为尊,即以道之运行规律来指导人类活动。道家学派认为,道的运行规律为清净无为,所谓“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3]。可见道如流水,清净不争。基于此,老子主张“致虚极,守静笃”,反对统治者过多“为”,认为统治者应当“歙歙焉,为天下浑其心”[2]。基于此,黄老具体提出了两项政治主张:其一,统治者应当少干涉社会生活,君主治理国家时,应当重视习惯,尊重社会本身,再依据社会实施统治;其二,统治者应当加强自身修养,清心寡欲。
(三)对慎到势治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慎到的势治主义与战国时所流行的君权观一致,都强调君主的重要性,而且同样从稳定性上论证:“立天子者,不使诸侯疑焉;……臣疑其君,无不危之国;孽疑其宗,无不危之家。”[10]由是,在慎子看来,立天子是稳固国家秩序的必然要求,否则“国必乱”。在赋予君主以稳定秩序的重要意义后,就需要确定君主的绝对地位,而用以保障这种地位的,便是势。“腾蛇游雾,飞龙乘云,云罢雾霁,与蚯蚓同,则失其所乘也。故贤而屈于不肖者,权轻也;不肖而服于贤者,位尊也。”[10]慎到将君主比喻为飞龙,而势则是飞龙借以翱翔天际的云,以现代政治学理论类比,则应当是政治权力,只有掌握这一权力,君主才可能发布命令,执行惩罚。他论证道:“尧为匹夫,不能使其邻家。至南面而王,则令行禁止。由此观之,贤不足以服不肖,而势位足以屈贤矣。”[10]尧当然为圣人,但即便是圣人,在没有成为王的时候,就连邻居也无法指使,于是慎子得出结论,使尧能够指挥其他人的奥秘,并不在于他的智力或者道德修养,而在于政治权威。这一理论在当时有着巨大的时代意义,突破了传统政治理论中伦理与政治不分的情况,明确将权力这一因素作为国家治理的核心要素予以讨论。
输入信号经过输入匹配网路进入第一级放大器,该级放大器的主要目的是保证尽可能低的噪声系数,再经过级间匹配网路进入第二级放大器。第二级放大器的目的是保证宽频带特性和高增益特性,最后经过输出匹配网络输出信号。将噪声系数和增益分别置于两级分开设计,有利于降低设计难度,保证二者均取得较理想的值。同时,为了尽可能的节省芯片面积,降低芯片的成本,该设计的第一级和第二级放大器共用栅极和漏级电源偏置网络。
在掌握权势以后,慎子认为君主应当少做事:“君臣之道,臣事事而君无事,君逸乐而臣任劳。”[10]以无为为要,乃至有学者认为其有着虚君的思想。[11]但无为是有为的辩证对立面,是道家思想中“无为而无不为”思想的体现。他的论证逻辑在于:“君人者,好为善以先下,则下不敢与君争为善以先君矣,皆私其所知以自覆掩,有过,则臣反责君,逆乱之道也。君之智,未必最贤于众也,以未最贤而欲以善尽被下,则不赡矣。若使君之智最贤,以一君而尽赡下则劳,劳则有倦,倦则衰,衰则复反于不赡之道也。”[10])这里慎到进行了一次逻辑推演,假设君主并不是最贤明的,以及假设君主是最贤明的两种情况。前者做事过程中一定会出错,出错以后就会降低权威,从而影响君臣关系。而后者事无巨细,必然导致疲倦,因而发生失误,同样影响君臣关系。因此慎到主张君主不必做事,应当默然守法,“不多听,据法倚数以观得失。无法之言,不听于耳;无法之劳,不图于功;无劳之亲,不任于官。官不私亲,法不遗爱,上下无事,唯法所在”[10]。
韩非子“抱法处势则治”的思想就是继承了慎到势治的思想,强调君主应当守住权势,并且应该严守法度。韩非子认为,治理国家不应片面强调统治者的个人因素,应当以普通人资质为标准:“尧、舜、桀、纣千世而一出,是比肩随踵而生也,世之治者不绝于中。吾所以为言势者,中也。中者,上不及尧、舜,而下亦不为桀、纣。”[2]尧舜与桀纣都不是治国者的主流,因此他强调了有迹可循的客观规律性,即法结合势以治理国家,从而提出了“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的主张。“夫弃隐栝之法,去度量之数,使奚仲为车,不能成一轮。”[2]他以此说明如果舍弃法律,贤人也无法治理国家。“无庆赏之劝,刑罚之威,释势委法,尧、舜户说而人辩之,不能治三家。”[2]这又说明如果离开权势,同样会导致大乱。
这些法家代表人物所提出的观念,构成了先秦法家政治理论的基石。正是在这种理论基础上,韩非子提出了法术势结合的治理思想,为君主执政设计了具体的方案,形成了关于国家治理的理论体系。
牛顿说如果说我看得比别人更远些,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先秦诸子学说之集大成的韩非子,正是在吸收众多思想资源的前提下,才形成了其极具特色的国家治理思想的。
参考文献:
[1]方勇,李波,译注.荀子[M].北京:中华书局,2011.
[2]高华平,王齐洲,张三夕,译注.韩非子[M].北京:中华书局,2010.
[3]饶尚宽,译注.老子[M].北京:中华书局,2006.
[4]孙诒让.墨子间诂[M].北京:中华书局,2001.
[5]蒋礼鸿.商君书锥指[M].北京:中华书局,1986.
[6]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7]马腾.申不害刑名法术思想及对传统治道德影响[J].政法论坛,2015(6).
[8]柴永昌.申不害思想新论[J].宁夏社会科学,2013(3).
[9]魏徵,褚亮,虞世南,萧德言.群书治要[M].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2012.
[10]许富宏.慎子集校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 2013.
[11]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2.
收稿日期: 2018-12-27
基金项目: 江苏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一般项目“城镇化视域中的乡村政治文化变迁研究”(2017SJB1404)
作者简介: 张茜倩(1987-),女,江苏太仓人,硕士研究生。
分类号: D9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395 (2019)04-0089-04
责任编辑 韩玺吾 E- mail: shekeban@ 163.com
标签:韩非子论文; 国家治理论文; 理论来源论文; 苏州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