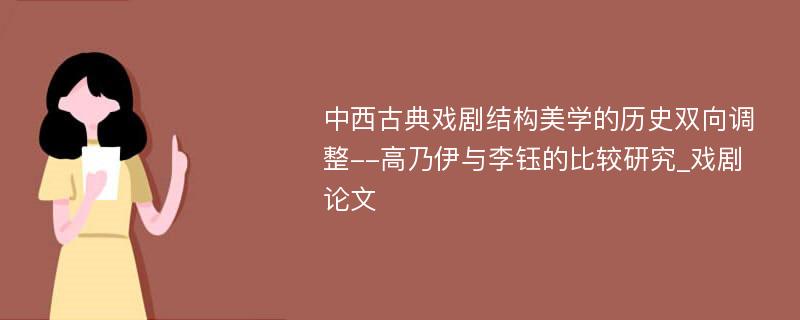
中西古典戏剧结构美学的历史性双向调节——高乃依、李渔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李渔论文,历史性论文,美学论文,双向论文,中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历史的角度看,世界各民族的文化发展历程总有这样或那样相似的时期,文学艺术是时代的精华,自然也不例外。美国学者J.刘若愚认为:“文学理论的比较研究可使我们更好地从整体上理解文学。”[①]戏剧曾经是西方古典文艺最流行、最高雅的文学样式;在中国,诗、词、音乐、绘画、歌、舞、动作熔为一炉,也构成了灿烂的元明清戏剧。在文学四大家族之中,由于表演手段及表现时空的舞台制约,戏剧实际上成为当今创作中自由度最小的一种。在电气化时代,由于影视文化的迅速崛起,戏剧曾有的灿烂光辉逐渐暗淡下去(影视手段处理的戏剧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戏剧了)。但是,中西古典戏剧都有过自己的辉煌,戏剧文学所积累的美学经验依然有着不可磨灭的生命。因此,中西戏剧结构理论的比较便具有文化学意义与美学价值。李渔、高乃依几乎是同时代的戏剧家,他们从各自的传统出发,对戏剧美学传统作了一次双向的调节。这种调节直接影响到了东西方“写实与写意”风格的互相贴近与转化,到布莱希特时,西方已经面对面领悟了“虚实相生”的中国艺术精神。而李渔、高乃依二人的创见,无疑是东西方20世纪尤其是当代文化转型的先声。本文主要通过高乃依的“三一律”观与李渔的“结构第一”论的比较,探讨中西戏剧理论在写实论与写意论中的一次双向自我调节,从中透视中西戏剧理论的差异性与趋同性。
写意与写实:中西戏剧美学的结构重心
作为一种综合艺术,中西戏剧因历史发展、地理环境、文化传统和审美习惯等方面的不同而构成了种种差异性。一般认为,西方戏剧重写实,强调摹拟再现,注重反映现实的矛盾和斗争;中国戏剧美学则重写意,强调虚拟性表现,与现实生活的联系不甚紧密,在戏曲中取材于现实生活的少,而取材于书本典籍的多。然而,二者的走向并不是平行前进,而是呈现某种不规则调节乃至趋同态势。中西戏剧美学史中具有开创意义的戏剧批评家吕天成(1580—?)与莱辛(1729—1781)可为一例。前者强调情节和事件的营构应符合艺术意境的创造,而莱辛则主张情节和事件的铺陈应从属于人物性格的塑造。二者的相似点在于,他们都将情节、事件视为戏剧的重要因素,也就是艺术结构所表达的艺术真实性;他们都注重道德教化作用,要求戏剧的道德作用必须契合戏剧的审美特质。但是,他们一个主张通过艺术意境的创造、一个主张通过人物性格的塑造来达到这一点,表明了二者的歧异;而且,东方哲学偏于“价值—实践论”,西方则偏于“本体—认识论”,因此,吕天成流露出传统的儒家伦理功用观,而莱辛则张扬了近代启蒙主义的审美的宗旨。
本世纪德国现代主义先锋派戏剧家布莱希特与中国戏剧大师梅兰芳戏剧美学思想的贴近,是上述相似性的又一例,是东西方戏剧在20世纪的相互寻找。1935年梅兰芳到苏联访问演出,布莱希特那时正受希特勒迫害,在莫斯科政治避难,他看了梅兰芳的表演,深深地着了迷。1936年他写了著名论文《论中国戏曲与间离效果》。布莱希特第一次把中国戏剧的结构(当然含有动作、音乐、唱、念、白等小结构)所表达的接受美学效果之谜揭示出来。在布莱希特之前,一般西方理论家都强调结构的重要性,由此上溯到两千多年前的亚里斯多德,就有着与李渔结构观一致的类似论断。亚里斯多德在《诗学》中总结了希腊悲剧、喜剧的艺术经验,在第6章中指出戏剧的六种基本成分是“情节、性格、言词、思想、形象、歌曲”,在这6种成分中,最重要的是情节,“情节乃悲剧的基础,有似悲剧的灵魂”[②]。
狄德罗在《论戏剧艺术》第7节中说,戏剧作家“特别要对自己立下禁条:绝对不在布局尚未确定以前就把任何一个枝节的想法落笔”,“应该先有布局再写各场”。到布莱希特时代,一方面,他从表演艺术上发现中国戏剧的间离效果;另一方面,他同样强调结构布局的重要。他说:“布局是举足轻重的部分,它是一出戏的核心。”[③]同样强调情节与布局、结构的重要意义,东西方戏剧毕竟表现出不同格调的美学风范。两者在形式及内容上的差异与趋同,依然展现着一种不规则的曲线运动。
“三一律”的扩展:西方戏剧由写实美学到写意美学的走向
亚里斯多德在《诗学》中曾论及希腊悲剧情节的“整一性”和演出时间对戏剧创作的限制,他的观点对西方戏剧的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可以说,西方戏剧美学的写实主潮经过亚里斯多德的弘扬,到文艺复兴时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莎士比亚(1564—1616)戏剧的蔚为大观。但稍前的卡斯特尔维屈罗(1505—1571)还未领略到莎士比亚剧作的新面貌,以至于他出于对当时某些剧作结构松散、地点更换频繁、时间拖得过长这些问题的失望,僵化地诠释亚里斯多德的戏剧美学,规定了戏剧的“三一律”,即时间的统一(剧情不能超过一昼夜)、地点的统一(要在同一个地方进行)和行动的统一(事件在单一意向下发展)。这个规定后来成为17世纪新古典主义戏剧的一种创作原则,由于它成了创作上必须严格遵守的清规戒律,过分强调戏剧艺术对生活的刻板摹仿,就把戏剧逼进了死角。当然,并不是所有的题材都能被“闭锁式”结构嵌定,正是在“三一律”盛行的17世纪,高乃依率先以他的代表作《熙德》一剧进行反抗,并从理论上对“三一律”进行了变通与扩展。
应该看到,17世纪的中西方戏剧都面临着一个转化,即由古代形式向近代形式的转化。西方文艺复兴时期,歌、舞因素从戏剧中分出,17世纪前后,歌剧、舞剧形成于意大利,西方戏剧开始向以“散体正剧”为主流的剧种多元化转化。中国戏曲就总体而言,偏重音乐、歌唱、舞蹈,有修养的欣赏者往往是在欣赏歌舞表演的基础上了解剧情内容的,所以歌、舞、白三合一的形式在17世纪左右得以继续发展,但开始由承接海盐腔、余姚腔、弋阳腔线性发展而来的昆山腔逐渐发展为多种地方剧种繁荣并存的格局。在这些转换过程中,出现新的探索是正常的。
令人惊奇的是,高乃依(1606—1684)与李渔(1611—约1680)大致同年,而且,二人都既是剧作家,又是戏剧理论家;既有创作戏剧的经验体会,又有戏剧理论的深刻探讨;二人在戏剧史上引人注目,主要不在于他们对各自传统的继承,而在于他们的那种创新精神,那种对各自传统的一定程度上的偏离或者调节;他们都反对拘泥于古人的规则,都要求从时代和实践出发,批判地继承和发展前人的理论,两个年龄相仿的戏剧家于世界的一东一西,不约而同地对不利于戏剧艺术健康发展的理论与创作的偏离进行了必要的双向调节。
在《论戏剧的功用及其组成部分》中,高乃依强调对“行动、时间、地点的一致”规则的扩展。在《论三一律,即行动、时间、地点的一致》里,他集中论述了如何扩展“行动、时间、地点的一致”的问题,对“三一律”的局限作了调节:
我认为,行动的一致,对喜剧说来,就是倾轧的一致……对悲剧说来,则是危局的一致……
我并不因此而否认把几种危局同时写入悲剧,或把几个倾轧或阻碍同时写入喜剧的可能性,只要其中的一种危局或倾轧必然能够引起另一种危局或倾轧就行……
从另一方面说,“行动一致”的说法不应被理解为悲剧应当对观众表演一个孤立的行动……应当只有一个能够抚慰观众心灵的完整的行动;但是,观众总是乐于等待其他若干行动,来使戏剧情节继续发展,因此只有借助于这种等待心理的唤起,才可能使剧中行动成为完整的。[④]
这一观点较之卡斯特尔维屈罗的主张——“悲剧应当以这样的事件为主题:它是在一个极其有限的地点范围之内和极其有限的时间范围之内发生的”[⑤],在情节的包容量上有一定的扩充余地,也比布瓦洛倡导的“只有一件事在一地一日里完成”[⑥]要开放得多。这种有机连接的行动连续,表明了高乃依对“开放性”戏剧结构的某种认同倾向。
在谈到“时间的一致”时,高乃依从艺术规律出发,认为“是否应该以24小时或12小时为根据,……我发现有些题材很难容纳在如此短促的时间片断中”[⑦]。为此他十分强调题材的决定意义:“如果题材并不要求规定行动所占用的时间,特别是规定了时间之后就会使事件显得有些牵强的时候,我宁愿让观众去想象行动的延续时间,绝不去规定事件所占用的时间。”[⑧]这里,高乃依强调题材的决定意义比卡斯特尔维屈罗的“事件的时间应当不超过12小时”[⑨]的僵死规定要合理得多,活泼得多。
“关于地点的一致,我从亚里斯多德和贺拉斯的言论中没有发现任何指示。……让观众在不必换景的一场戏中看见的行动,能够集中在一个房间或一个大厅内,这要根据选择而定;不过这样做也常常是不方便的。时间一致的必要性迫使我们寻找方法扩大地点的广度,正如延长时间的长度一样,这不能说是不可能的。”[⑩]这是高乃依对“地点一致”的异议、驳难以及扩展。
他进一步指出:“为了略微调整这种难以避免的地点的二重性,便应当遵守两件事:第一,在同一幕中绝不变换事件的地点,只是在不同的幕中加以变换……;第二,两个不同地点有必要换景,并且两个地点都不必标出名称,只要标出包括两个地点的那一个地名就行了。”[(11)]这里,他提出以幕的更迭变换和地点的提示来安排地点的转换,这一可行性的设计,实际上也体现了调动观众想象衔接剧情、地点的思想。
高乃依在对“三一律”的局限进行矫枉、扩展的过程中,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提出了一些原则和方法,其目的之一,就是“让观众去想象”剧情的发展,这在西方戏剧美学由被动地接受舞台摹仿变为主动地欣赏舞台表现的流变中,显示出戏剧表现派美学思想的萌动。这是向写意派戏剧美学方向的一个重要调节,这个理论调节,可以说是布莱希特戏剧美学的先声。
当然,高乃依的戏剧美学思想总体上仍然是写实的。他的剧作《熙德》虽然突破了“三一律”的束缚,也仍然是写实的。但是,我们要看到,除却个别的思想火花外,人类任何有价值的探索都是渐进的,所以,高乃依立足于写实美学向写意美学方向的调节,就当时来说,也许更接近戏剧艺术的内在规律,而且在理论建树上,他的成绩超过了同代人。西班牙剧作家维加(1562—1635)在创作上对剧情的时间、地点任意支配,理论上也反对“三一律”,但他的阐述没有高乃依系统化、理论化。所以,高乃依对“三一律”的调节成为莱辛以至后来的浪漫主义打破“三一律”的先声。正如张翼先生所言,布莱希特的接力棒,即使是从浪漫主义美学思想家手中接过去的,那上面也沾有高乃依努力的血汗。因为表现派戏剧美学必须首先打破、摆脱“三一律”的清规戒律。
“结构第一”的标举:中国戏剧“抒情中心”向“叙事中心”的历
史性转移
中国的叙事文学成熟较晚,所以戏剧的成熟也较晚。经过唐宋传奇小说的催化,萌发于秦汉的戏剧因素终于在元代蔚为大观。但中国文艺的写意高潮——诗词的言志说,歌、舞、白三合一的表现性形式,传奇小说的写意倾向,使中国戏剧从成熟的那一天起,就走上了写意戏剧的美学之道。当然,这条道路也是在探索戏剧形式的规律中曲线延伸的。在元曲不可挽救地衰落下去后,明清戏剧的实践就以传奇故事的新奇对抗“填词”的案头欣赏性,于是历史在呼唤一个理论性的转换、调节。所以,李渔的“非奇不传”、“非新不传”的戏剧观出现了。其具体表现为对“叙事趣味”的重视和追求,围绕这一点,李渔提倡“结构第一”,这是戏剧发展史上的一个必然现象。关于戏剧结构的理论是李渔戏剧理论中最有价值、最引人注目的部分。在李渔之前,戏剧文化的积累不可谓不深厚,曲家人才辈出,戏曲作品难以计数,戏曲理论著作也不少,何以竟无一人、竟无一部著述确定“结构第一”的思想?相当一部分曲论家涉及到结构问题,但遗憾的是,与“结构第一”的命题失之交臂。导致这种理论上短视的原因有三[(12)]:
第一,对抒情趣味的着意追求。中国戏曲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与诗歌结下了不解之缘。对诗歌抒情趣味的追求在戏曲中演变为对曲词抒情趣味的追求,曲词在戏曲诸要素中取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维系着一部戏曲作品的生命。对“曲”的过分看重则意味着对“戏”的相对轻视,故将本应优先考虑的结构问题放到了次要位置上。
第二,对戏曲舞台生命的忽视。鲁迅先生说过:“剧本虽有放在书桌上的和演在舞台上的两种,但究以后一种好。”[(13)]然而,戏曲史上相当一部分曲家并不重视戏曲的舞台生命,由此产生了不少难以搬上舞台供观众欣赏的案头剧。案头剧既然无须面对广大观众,其结构严谨抑或松散就不是作者考虑的主要问题。
第三,对现成题材的依赖。这一点应归咎于历代统治阶级对进步戏曲的迫害与摧残。元代《刑法志》明文规定:“诸妄撰词曲,诬人以犯上恶言者处死。”明代在明律上写着:“凡乐人搬做杂剧戏文,不许装扮历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神像,违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令装扮者同罪。”从这些禁戏律令中,我们可以理解剧作家们不敢直接反映现实、而要从古代的书本中去寻找现成材料的原因所在。与此同时,剧作家也套用了现成的结构,即使有所创新,总体框架也基本不变,这也使戏曲家们无意中忽视戏剧结构的重要性。
上述三个原因,或各自起作用,或合并起作用,使得“结构第一”的思想在李渔之前的古代戏曲理论中始终未能脱颖而出。一些涉及戏曲结构的零星见解不得不淹没在大量关于词采和音律的论述中。
李渔则不同,在“戏”与“曲”之间,他更重“戏”,他认为戏剧情节是戏剧产生娱乐作用的关键因素。因此叙事性在李渔的戏剧理论和创作中,取得了在传统的戏曲理论和创作中从未有过的地位。这使得李渔的戏剧理论和创作呈现出极为独特的风貌,标志着李渔试图实现从戏曲的曲词地位至高无上的“抒情中心”向戏剧的情节地位至高无上的“叙事中心”的转移,在这种微秒的转移中,可以寻觅到后代话剧的一丝萌芽。强调戏剧的“叙事趣味”,重视舞台演出,提倡新编独创,这三者构成了李渔标举“结构第一”的必然性。
李渔的《闲情偶寄·词曲部》从总体上建构了他的理论框架:结构第一,词采第二,音律第三。至此,三者列出了一个相对科学的顺序。它既抓住了民族传统戏剧的表现要素,又强调了戏剧表现形式的本质规律,对时人重词采、音律的偏颇做了理论上的重要调节。
李渔“结构第一”的主张,具体表现为七条原则,即“立主脑”、“密针线”、“减头绪”、“戒讽刺”、“脱窠臼”、“戒荒唐”、“审虚实”。这七条原则呈现出鲜明的理论指向:构思和组织观众乐于欣赏新奇的故事情节。中国戏曲舞台不重时间、空间的写实精确,主要体现为一种表意的程式科范,不仅虚拟时间、地点的转换,而且虚拟人物的行动,因而中国戏曲的结构主要是表意性诗化的情节结构。“立主脑”固然称关键的“一人一事,即作传奇之主脑也”,但李渔着力突出的是“一事”,用今天的话说,即全剧的戏眼,以后全部情节的派生点。他反对不顾舞台表现条件,情节涣散的弊端,他说,“后人作传奇,但知为一人而作,不知为一事而作,尽此一人所行之事,逐节铺陈,有如散金碎玉”[(14)],如此构成全剧,“则为断线之珠,无梁之屋,作者茫然无绪,观者寂然无声[(15)]。”缺少主脑,观众就缺少一个把握剧情的制高点。亚里斯多德说:“有人认为主人公是一个,情节就有整一性,其实不然;因为有许多事件——数不清的事件发生在一个人身上,其中一些是不能并成一桩事件的。”[(16)]也就是李渔所言的“立主脑”。高乃依扩展“三一律”的“情节一致”,强调“并成一桩事件”的主要事件,而且认为它应该由一系列非孤立的、有机的、能引起期待的行动所构成。可见,上述三家,从接受美学看,都表达了一个重要的审美欣赏的心理需要,即“戏剧的中心事件的同一性”。
突出“主脑”,就需要“密针线”、“减头绪”。“密针线”简言之是将剧情组织得天衣无缝,使观众挑不出任何破绽。“每编一折,必须前顾数折,后顾数折。顾前者欲其映照;顾后者便于埋伏。照映埋伏,不止照映一人,凡是此剧中有名之人,关涉之事,与前此后所说之话,节节俱要想到。”[(17)]李渔的“针与线”的映照作用,与上述亚里斯多德、高乃依的“并成一桩事情”的“并”字,意义完全相同,即主张在短暂而有限的舞台表现中,注意戏剧情节的映照埋伏,苦心经营,使之成为富于美学意味的无破绽的有机整体。“减头绪”将“无用”的人、事、言词剔除,使情节、行动更加紧密,以利于舞台演出。“头绪繁多,传奇之大病也。……事多则关目亦多,令观场者如入山阴道中,人人应接不暇。”他认为“做传奇者能以‘头绪忌繁’四字刻刻关心,则思路不分,文情专一”[(18)]。
“立主脑”、“密针线”、“减头绪”构成了李渔“结构第一”的编剧理论大厦的三块基石,以整一的情节作为人物写意的理论基础,而且也从宏观上把握了戏剧表演对时空的特殊要求。强调照应伏笔,就是有效地调动了分散的时空场景,从而使结构富于灵性与动态美的形式。强调“减头绪”就是限制了不必要的枝叶,为突出中心主题服务,这样就使舞台演出不至于过多地更换时空,以保证主要情节,主要人物的抒情、写意场面的“文情专一”。减少戏剧舞台时空的变化,突出主要人物、事件、李渔的这些主张容易集中观众的审美注意,产生相应完整的审美感知与判断。
李渔还主张“戒荒唐”、“审虚实”、写常人常事,他说“说何人,肖何人”;“妆龙像龙,妆虎像虎”。[(19)]高乃依在《论三一律,即行动、时间、地点的一致》中也提出了类似的关于艺术真实的审美理想:“戏剧作品是一种摹拟,说得确切些,它是人类行为的肖像;肖像越与原形相象,它便越完美,这是不容置疑的。”这实质上是一种写实主义的表演艺术论。可见李渔在中国戏剧史上,已经完成了一次由写意派戏剧美学向写实派戏剧美学方向的重要调节与转移。关于非僵化的情节整一,高乃依与李渔不约而同地取向了对立的艺术原则。由于情节整一便于生活横断面与相应时空结合的真实性再现,避免线性结构可能出现的单薄,所以这里一定程度上触及到“闭锁结构”的合理基础,具有一定的方向性意义。
当然,李渔戏剧理论的写实倾向,是立足于写意戏剧美学的。“说何人,肖何人”为的是“情乃一人之情”。“密针线”、“减头绪”客观上减少了时空转换的繁乱,有助于行动真实的扩展,保证主要情节和人物抒情、写意的集中,目的不在于保证时空与行动结合的确定。但是,就是在这一点上,李渔远远地超过了他的前人和同代人。为写意而写意缺少坚实的基础,为写意而写实,使虚拟以摹拟为基础,在真实感人的基础上,“意”得以升华,就能充分发挥舞台艺术的魅力,使戏剧得以健康发展。历史呼唤中国戏剧由写意向写实方向进行调节,李渔的戏剧主张完成了这个调节,所以他成为中国戏剧史上,乃至世界戏剧史上的杰出人物。
虚实相生:双向调节的文化意义与美学价值
美国文化生态学派学者斯图尔特(1902—1972)认为,文化的进化过程是“多线进化”,他认为每一类文化均因其生态环境不同而有不同的演进路线。我国学者庞朴也这样阐释文化的趋同论:“文化的源头是不同的,发展起来就趋于相同,为什么趋同?不是万有引力,而是文化要受到人本身生存发展与环境的限制。”[(20)]作为文化深层次现象之一的戏剧艺术,也是在不断探讨戏剧艺术的规律中由单一趋于多维、多线进化而趋同的。我们说中西戏剧艺术的发展规律,都必须不断突破某些过时的原则或规律。西方戏剧在17世纪后受浪漫主义诗歌、小说的影响,终于在20世纪初形成以布莱希特为代表的表现派戏剧美学潮流,与梅兰芳为代表的写意戏剧美学相贴近,并领悟中国戏曲表现意念中的“第四堵墙”的存在,从而丰富了表现派戏剧的美学思想;中国戏剧在17世纪后继续受到现实主义小说因素的潜移默化影响,并于20世纪初受西方戏剧的影响出现所谓“文明戏”的话剧形式,再加上稍后逐渐加强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写实戏剧美学体系的影响,中国戏剧的写意美学潮流,渗进了越来越多的写实成分。中西戏剧美学的发展走向,在文化传播的开放环境中相互渗透、影响,在曲折的发展中,进一步趋同,在走向世界文学的道路上,在获得新质的嬗变中,以新的面貌去建构更加丰富多彩的多元化格局。
当我们比较清晰地看到这种趋同现象时,回顾剧作家、剧作理论家在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大背景上对戏剧艺术的思考、探讨轨迹,那些对戏剧本体、形态、功能等方面做出量变努力的探索是多么难能可贵。高乃依和李渔在戏剧艺术面临由古代形式向现代形式的转化中,遵循戏剧艺术的内在规律,不约而同地对各自体系的某些偏颇做了重要的调节,这种打破传统观念,向对方方向所做的重要调节,在中西戏剧学趋同发展的历史嬗变之中,是一次可贵的量变贴近。正是这种量变的积累,才形成某种程度的突破,加速了中西戏剧结构美学的趋同进程。
文艺史的发展呼唤着高乃依与李渔做一次必要的双向调节,高乃依和李渔的双向调节实现了他们那个阶段的历史必然。这一双向调节应该予以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
注释:
① 刘若愚《中国的文学理论》,转引自牟世金《中西戏剧艺术共同规律初探》,载《文史哲》1981年第3期,第62页。
② (16) 亚理斯多德《诗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23、27页。
③ 布莱希特《戏剧小工具》,转引自杜书瀛《论李渔的戏剧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91页。
④⑦⑧ ⑩ (11) 高乃依《论三一律,即行动、时间、地点的一致》,见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上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第262、263、264,264—265、265页。
⑤⑨ 卡斯特尔维屈罗《亚里斯多德〈诗学〉的诠释》,见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194、195页。
⑥ 布瓦洛《论诗艺》,转引自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第193页。
(12) 黄强《李渔的戏剧理论体系》,载《扬州师院学报》1994年第1期,第13页。
(13) 《致窦隐夫》,见《鲁迅书信集》下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655页。
(14) (15) (17) (18) (19) 《李笠翁曲话》,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0、26、26、29—30、44页。
(20) 《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年,第47页。
标签:戏剧论文; 高乃依论文; 李渔论文; 三一律论文; 布莱希特论文; 戏剧影视文学论文; 美学论文; 艺术论文; 西方美学论文; 文化论文; 中国戏剧论文; 诗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