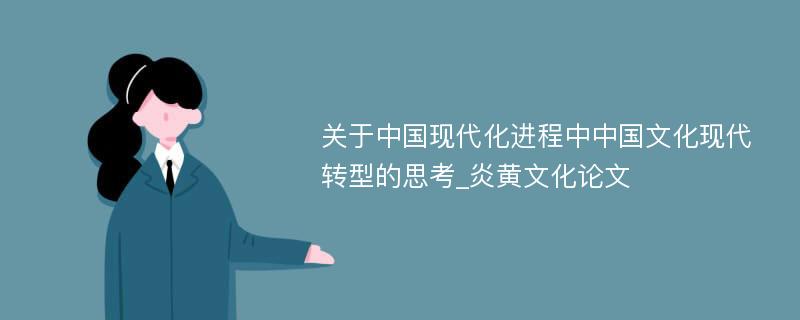
中国现代化进程研究 中国文化现代转型随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文化论文,中国论文,随想论文,现代化进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今日我们所面临的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问题,是一个古老而又常青的题目,它既与运作已久的“古今之辨”一脉相承,同时又包蕴着丰富的新内涵。简言之,所谓“文化转型”,是指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整体性变革。如果说,历史的多数时期都发生着文化的局部性量变,那么,“文化转型期”则指文化发生全局性质变的阶段。今天我们所讨论的“现代转型”,是指从自然经济为主导的农业社会向商品经济占主导的工业社会演化的过程,其显著标志是,有生命动力系统(人力、畜力)为无生命动力系统(矿物燃料、水力、核能)所接替,机器生产取代手工劳作,人类获得财富的手段由驯化利用天然原料为主变为加工改造天然原料为主,“征服自然”所需要的“高效率”和“标准化”成为经济生活的准则。与物质文化层面的变迁相表里,在制度文化层面,彼此隔绝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静态乡村式社会,转化为开放的、被种种资讯手段紧密联系起来的动态城市式社会,同质的单一性社会变为异质的多样性社会,礼俗社会变为法理社会,人际关系由身份演为契约,宗法—专制政体为民主—法制政体所取代。作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转型的精神先导和思想反映的观念文化,也在这一过程发生深刻的变异,诸如神本转向人本,信仰转向理性,宗教转向科学,教育从少数特权阶层的专利变为大众所享有。传统的农业文明和现代的工业文明转型过程所必须完成的社会重建和文化重建任务,分别由中产阶级的形成与壮大、知识分子的形成与壮大而逐步得以实现。
一种文化现代转型的关键是赢得“现代性”。而围绕“现代性”的把握,曾流行过两种极端之论:其一为“经济单一论”,即把现代性仅仅归结为生产方式的变革,只强调器用层面现代转换的基础功能,而忽视制度层面和观念层面现代转换的能动作用,尤其忽视文化的主体——人的现代化在转型中的枢纽地位。因此难以实现现代转型的健全发展。19世纪下半叶曾经颇有声势的洋务运动,其器用文化的进步由于得不到制度层面和观念层面进步的支撑,终于遭到严重顿挫便是一个例证,亚非拉一些国家19至20世纪现代化一再走弯路,也往往与此相关;而与中国的洋务运动大体同步的日本明治维新能取得成功,其重要原因之一是,相对完整地实现诸文化层面的协同进步,明治时代思想家福泽谕吉的《文明论概略》强调“不应单纯仿效文明的外形而必须首先具有文明的精神,以与外形相适应”,便显示了这一认识的高度。亟欲求得现代化的当下中国人,应当从历史的昭示中获得教益。其二为“观念决定论”,即把现代性归结为某种精神的勃兴。如前有德国人马克斯·韦伯,后有美国人列文森将资本主义在欧洲诞生的动力归结为新教伦理和复兴了的希腊理性[1],又进而将中国停滞于中古,无法实现现代转型的因由推原到儒道两家的滞后作用[2];而今天活动于海外的现代新儒家则反其意而论之,认为儒家学说包蕴着推动现代化的潜能,并举出日本和东亚四小龙现代化成功的实例为证[3]。这一论战的双方,都有许多精辟的、足以开启神智的见地,他们各自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欧洲及中国古典精神均有可供现代转型借重的宝贵资源。但是,论战双方的一个共同点是:仅仅在精神层面探求现代性的动力源,这就难以获得真解,例如无法说明洋溢着理性精神的古希腊何以未能在近代以前孕育出资本主义,中国先秦以降的儒家学说何以不能原发性地在中国启迪现代性文化,反倒一再成为宗法—专制政体的御用工具。总之,无论是“经济单一论”还是“观念决定论”都不能全面揭示“现代性”的内蕴,也无法对欧洲及东方的现代转型的种种路径作出深刻阐发。而只有从广义文化所涉及的诸层面——器物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观念文化——进行综合性考察,并辩证地探讨诸层面间的互动关系,方有可能寻觅出对“现代性”及“现代化动力”解释的正途。
二
从全球范围观之,传统社会及文化的现代转型是以15、16世纪南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和世界性远航开其端绪的,此间勃生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和兴起于中欧的宗教改革是其文化标志;这一转型的大规模展开则是18世纪英国的工业革命和继起的法国政治大革命,其文化标志是启蒙运动。成长于西欧的工业文明伴随殖民扩张又延至北美,进而播及全球,德意志、俄罗斯、日本是效仿英、法实现文化转型的“优等生”,其他国度也不同程度地沿着现代转型的道路迈进。世界历史以统一市场和“世界文化”的形成为契机,从分散走向整体,五湖四海的人类渐次汇入波澜壮阔的现代化大潮之中。
对于西欧而言,发端于15世纪的现代转型是从中世纪母胎内自然孕育而成的,可以称之为“内发自生型”;对于所有其他地区(包括易北河以东的欧洲诸国)而言,现代化过程则是在世界历史已经走向整体化之际逐步实现的,也即在西欧现代文明强有力的影响下发生的,因而其现代化呈“外发次生型”。
欧洲以外地区(严格意义上应是西欧以外地区)的“外发次生型”现代化过程,又大略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欧洲殖民者入侵之际,土著人十分落后,如北美洲和澳洲,当欧洲文明进入前夕,当地尚处在新石器时代,欧洲近世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连同人口,较为便利地全盘迁徙而来,因此,北美洲(美国与加拿大)和澳洲(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的现代化基本上是西欧模式的整体移植,也可以说是“全盘欧化”。另一种类型是,当地早已形成悠久深厚的历史传统,如阿拉伯、波斯、印度、中国、越南、朝鲜、日本、印加、玛雅、阿兹台克,都有着数千年的文明史,欧洲人入侵之际,这些国度虽然尚滞留在“前现代阶段”,却不同程度地拥有与外来文明相抗衡的物质资源及精神资源。因而,这些国度的现代化,并非欧洲文明的简单位移,而呈现欧洲文明的强劲影响与本土文明对此既排拒又吸纳所构成的错综图景。这类地区的现代化进程,不仅要完成文化的时代性转换,还要面对文化的民族性传承问题。这两者间虽不乏统一性,却往往在相当长的时段内相互矛盾,彼此牴牾。对于此类“外发次生型”现代化进程的复杂性不可失察。曾经颇有影响的“民族文化本位论”和“全盘西化论”,或固守内因一隅,或偏执外因一端,都不能全面、深刻地诠释这一复杂的历史过程。
三
关于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外力影响和内在动力的相互关系问题,一直聚讼未决,由此引申出来的一个假设性问题是——如果没有西方侵入,中国文化自身能否实现现代转型?持否定论的如梁漱溟,他在《中国文化要义》中认为中国、印度、西方分别走着不同的路向,中国文化无论怎样发展,也不可能走到西方文化所达到的目标。而这个目标,正是我们所讨论的由西方人率先实现的、以工业化为显在标志的“现代化”。与此形成相反之论的,是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指出的,如果没有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社会也会缓慢地向资本主义过渡。基于我们对中国历史(尤其是明清史)的认识,大体可以接受后一种判断,但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中国自身固然有着现代转型的潜势,但压抑这种潜势的惰力十分强劲,如果没有世界性现代化浪潮的猛烈冲击,中国“走出中世纪”是极其困难的。
中国社会及文化的现代转型,人们一般以19世纪中叶爆发的鸦片战争,也即西方资本主义打破中华帝国闭锁的国门为其端绪。但如果从中国历史的纵深度加以考察,便会发现,自明代中叶(16世纪)开始,中国社会及文化已隐然呈现走出中世纪的某些征兆。在长江中下游及东南沿海(还包括晋东南等少数北方地区),工场手工业和商品经济渐成规模,出现某种从“农本”向“重商”转化的苗头。与之相随,在观念领域也初露“破块启蒙”的动向。诸如明清之际的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对专制君主的总体性抨击(已不是像孟子那样只限于对于殷纣王等“暴君”的批判),对君臣之间从主奴依附向平等同事关系转化的期望,对学校议政、“工商皆本”的热烈倡导,都暗示着一种新的文化精神的迫近。此外,方鹏、归有光、毛奇龄、俞正燮等人对戕害女性的“节烈观”的批判[4],戴震对“以理杀人”的深沉谴责[5],也有类似意味。即使是清学的主潮——乾嘉考据学,虽然弥漫着古典气息,但其间洋溢着理性—实证精神,将“神圣”的经书还原为历史典籍的努力,其对经学传统的解构作用也为观念文化的转换准备着条件。
中国从明中叶到清中叶固然出现了某些时隐时显的新文化因子,但其文化的整体结构却具有抗御现代转型的顽强功能。在经济层面,农业—家庭手工业稳固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体系难以打破;在政治层面,君主专制政体得到科举制、郡县制的有力支撑,还在不断强化,直至明清尚不见解体征兆,而且,这种专制君主政体与地主—自耕农经济彼此契合,对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民的成长推行压制政策,明代后期“矿监”、“税监”的倒行逆施便是典型例证,其对转型的阻滞作用与西欧中世纪晚期王权与市民结盟,推动商品经济发展和统一市场建立的情形恰成反照;在社会结构层面,中央集权的垂直式官僚机器与基层的家族—宗法组织纵横交织,使独立的、自治的市民社会全无生存空间,而这种市民社会的孕育和拓展正是文化近代转换的必要土壤;在观念层面,外儒内法、儒道互补的格局又与上述经济、政治、社会状况彼此适应,达到一种自足状态,即使明清鼎革带来的震荡已焕发出文化上的“破块启蒙”动向,但由于整个社会尚未达到转型阶段,缺乏强劲的经济—政治助力,少数先觉者的呐喊,其规模和力度都远不足以掀起大波。就整体而言,当时的社会及文化仍然徘徊在中古故道,中国尚自外于15、16世纪以来已经开始的世界性现代化过程。1793年(约与法国资产阶级政治大革命同时)乾隆皇帝接见英国使臣马戛尔尼勋爵所显示的“集体孤独症”,尤其是乾隆致英国乔治三世的复信所宣称的“天朝德威远彼”、“无所不有”,生动地表明,已经落后了的中国人当时还自认为是“世界上唯一的文明”[6]。这种情形迁延至19世纪中叶,西方殖民者用炮舰、鸦片和商品打开了清王朝封闭的国门,以自然经济和专制政体为基石的中国社会逐步被纳入世界统一市场,源远流长、自成体系的中华文化开始与西方近代文化相交汇。这样,中华传统文化尚未达到自我扬弃以实现时代转换的时刻,便因遭遇到外来的近代文化的撞击而进入剧烈的转型期。陈寅恪称其为“赤县神州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此语表达了19世纪中叶以降的中华文化现代转型的空前激变性和复杂性。
四
中华文化现代转型的激变性和复杂性,首先表现在这种转型是在西方文化强行侵入,打断中华文化自身进程的情形下发生的。正如人体器官移植必将引起排异反应一样,西方现代文化的楔入,给中国传统文化造成激荡之深切是空前的。中国的现代转型,不仅要完成文化的时代性跃进,还要处理文化的民族性保持与变异这一对矛盾。中国学界、政坛自19世纪末叶开始,直至20世纪80、90年代仍然聚讼纷纭的“体用之辨”,正是中华民族现代转型过程中时代性转换与民族性维系之间复杂关系的形而上反映。
中华文化现代转型的激变性和复杂性,还表现在任务的交叉与多重上。其原因是中国人经历的这一转型过程,较之西方人,存在一个“时间差”,以至西方人用数百年时间解决的问题,一起积压到一个世纪间,要求中国人一并解决:一方面,今之中国人要完成西方人在18、19世纪完成的以工业化为核心内容的现代化过程,实现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换,这种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基本内容;另一方面,本世纪以降,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电气化和电子技术导致的新科技革命的纵深发展,西方诸国已步入后工业时代(或称“后现代”),随之出现以信息化为标志的新现代化浪潮对整个“地球村”的冲击,工业化任务尚未完成的中国人当然不能自外其身,置此之际的中国人可谓利弊双收——既可以从后工业文明借鉴最新成就,不必亦步亦趋地走西方人曾经走过的工业化老路,从而获得“超前效应”;同时,还不“发达”的中国人也难以避免发达国家的种种“现代病”,诸如环境污染、能源危机、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分离导致的道德危机、信念失落等等,而不得不寻觅救治之策,这又增添了现代转型的普世性内容;此外,由于新中国前几十年的经济—政治—社会体制是按照第三国际和苏俄体制建立起来的,今日为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还面临一个从中央指令型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课题,这又为中国现代转型增加了复杂性,是现代转型的“中国特色”所在。总之,今之中国现代转型所面临的问题是一种“中西古今”的层累式积淀,呈现“多重”状态,使中国人不易从容应对,同时也为中国社会现代转型提供了视野广阔的机遇。
早在1919年,鲁迅便描述过现代中国的“多重”性状,今日读来仍有切肤之感:“中国社会上的状态,简直是将几十世纪缩在一时:自油松片以至电灯,自独轮车以至飞机,自镖枪以至机关炮,自不许‘妄谈法理’以至护法,自‘食肉寝皮’的吃人思想以至人道主义,自迎尸拜蛇以至美育代宗教,都摩肩挨背的存在。”[7]有着宏阔世界眼光的孙中山,也对近世中国的“多重”任务深有体悟。他作为中国现代化的热烈倡导者,同时又深悉西方资本主义的弊端,故力求中国在资本主义“祸害”“未萌之际”便加以防范。他在1905年撰写的《〈民报〉发刊词》中提出“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设想,就是试图对现代中国面临的“多重”问题作一总体式解决。这一构思当然包含着主观空想成分,缺乏可操作性,却又蕴蓄远见,富于创识和预想,对面临类似问题的今之国人,仍颇具有启迪意味,并提供了宝贵的思维教训。
五
中国社会及文化的转型,是亿万中国民众在长达三个世纪间经历着的伟大社会实践。纵观这一起伏跌宕的过程,仅就观念文化的转变而言,有几个阶段尤其值得注意。一为明清之际(17世纪),早期启蒙思潮兴起,继之隐遁,如地火潜行;二为清道光、咸丰年间(19世纪30至60年代),外患内忧的刺激,使得经世实学和今文经学勃发,构成传统文化走向近代新学的桥梁;三为清同治及光绪前中期(19世纪60至90年代),随着“洋务新政”的拓展,西学输入渐成规模,新教育雏形初现,早期改良思潮由孕育而兴盛;四为清末至“五四”时期,发端于甲午战败激起的国人觉醒,又历经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近世新学形成、发展,并渐成主潮,新知识分子取代士大夫走上历史舞台;五为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改革开放大潮使现代化进程赢得加速度,并与世界接轨,观念文化逐步寻觅到时代性进步和民族性发扬相统一的路径,中国现代化呈现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同时又面临着诸多挑战。
注释:
[1] 见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2] 见列文森《儒家中国及其现代命运》。
[3] 见杜维明《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
[4] 见方鹏《矫亭存稿·风俗》、归有光《贞女说》、毛奇龄《禁室女守志殉死文》、俞正燮《贞女说》。
[5] 见戴震《孟子字义疏证》。
[6] 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326—330页。
[7] 鲁迅:《热风·五十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