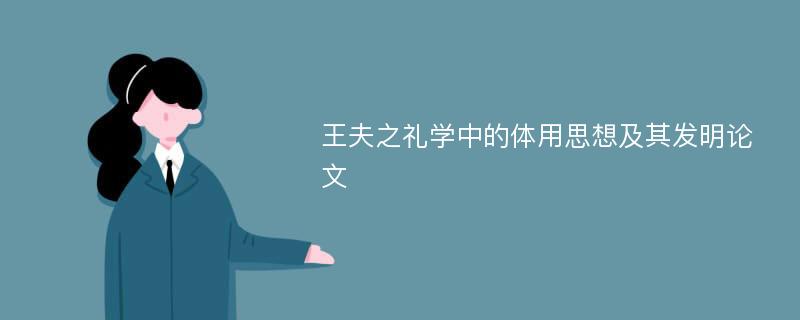
王夫之礼学中的体用思想及其发明
路鹏飞
摘要: 《汉书·艺文志》言“礼以明体”,《庄子·天下篇》言“礼以道行”,可以说礼学体用并重,然而却少有人论述礼学之体。王夫之重点阐述了礼学中的体用观,以及礼治义理思想,以反心学玄想空虚之弊,以严夷夏、人禽、君子小人之别。王夫之不仅借体用思想论证客观世界,阐明主客、理气、道器、知行关系,反对佛老申韩之辩,而且他还以体用观点对礼学思想进行阐述,强调了明体达用、重实黜虚的观点,反映了明清之际注重实践的研究趋势。不同于此后清代的许、郑后学,且郑玄学问以礼为本,王夫之以礼解易,虽然同是对经典的注解,但是二者思路并不相同。
关键词: 王夫之;礼学;体用;易学
王夫之作为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家,其礼学思想宏富。《汉书·艺文志》提出:“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1〕文中强调了礼学明体著见的特点,以及作为五常之道之一的地位,指出了礼学对于明体的重要性。《庄子·天下篇》言“礼以道行”,强调了礼学的实践方面。王夫之在学术上提出“六经责我开生面”的观点。《清儒学案》评价王夫之“以汉儒为门户,以宋五子为堂奥……以羽翼朱子,而渊源尤在《正蒙》一书”。〔2〕他在礼学上体用并重,强调明体达用的观点。
一、王夫之礼学思想的渊源及其研究特点
王夫之礼学思想主要在他的《礼记章句》中,同时散见于其他著作。《礼记章句》是王夫之在五十九岁时完成的一部礼学著作。耗时四年,始于1673年,完成于1677年。对于礼,老子曾经提出:“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王夫之反对这种看法,他认为礼是性之四德——仁义礼智之一。对于礼,他赞成“天理之节文”的解释,并以此礼来“妙众理”,即他所说:“节文著而礼乐行,礼乐行而中和之极建。”〔3〕王夫之还就礼和仁、礼和文之间的关系来理解礼,就礼和仁之间的关系来说:“礼者,仁之实也,而成乎虚。无欲也,故用天下之物而不以为泰;无私也,故建独制之极而不以为专。其静也正,则其动也成章而不杂。”〔4〕就礼与文的关系来说,王夫之认为礼是合乎情理之文,而非不合情理强致之饰,“是故礼者文也,著理之常,人治之大者也,而非天子则不议,庶人则不下”。〔5〕对于礼,王夫之认为文称其质,物称其情。
1.4 GBS的分离培养、鉴定和药物敏感试验 将标本接种于5%羊血琼脂平板,35℃,5%CO2培养18~20 h,通过菌落形态、涂片镜检、CAMP试验进行初筛,使用VITEK 2 COMPACT全自动细菌鉴定及药敏分析系统进行GBS鉴定和药物敏感试验。CLSI指南2016版M100-S26作为药物敏感性试验判读标准。肺炎链球菌ATCC49619作为质控菌株,所有质控在控。所有操作严格按照《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第四版)执行。
“三师”工作由学校马克思主义学院负责组织实施,为马克思主义学院的“一号工程”“一把手工程”。实施之前必先制定具体工作方案,经全体教师讨论,通过后再实施。每个月收集一次“三师”工作材料并及时通报,以督促进度,强化过程管理,防止弄虚作假。“三师”工作自2017年秋季展开后,经过一个学期的实践,发现存在以下问题:
③专用振动器振动不应在同一位置持续振动,振动时间不能过长,防止过于密实,出现离析现象。因透水混凝土其孔隙率大,水份散失快,当天气温高于35℃时,施工时间应宜避开中午,适合在早晚进行施工。
王夫之提出“运”即“载而行之”,《礼运》篇主要表明礼如何能周流天下而使万事各得其宜。王夫之认为,原因主要在于:“为二气五行三才之德所发挥以见诸事业,故洋溢周流于人情事理之间而莫不顺也。”〔31〕王夫之引用张载的观点再次强调了体用之辨:“礼运云者,语其达也,礼器云者,语其成也。达与成,体与用。合体与用,大人之事备矣。”〔32〕《礼器》篇与《礼运》篇相互映照,礼器篇主要叙述了礼制的品节内容。王夫之认为,礼运为“体”,礼器为“用”。王夫之推崇张载的“礼器者藏诸身,用无不利,修性而非小成者与”,〔33〕认为“运之者体也,而用行焉;成乎器者用也,而要以用其体”。〔34〕
2005年,“北京DRC工业设计创意产业基地”规划投建,为中国工业设计带来全新的元素与升级。基地中搭建起“逆向工程实验室”“3D打印体验馆”“设计博物馆”等一系列创意空间;同年,“光华龙腾奖.中国设计十大杰出青年”评选启动,为中国设计行业发掘中国力量;2006年,“中国设计红星奖”设立,助力中国设计走出国门,在国际化征途中完成设计服务业和制造业的融合与蜕变;2008年,以北京奥运为契机,“奥运设计”的理念走进社区,走进人们生活,这一年,深圳成为全球第六个世界“设计之都”。
就仁和礼的关系来说,王夫之把礼,即仁的显现作为人与禽兽、中国和夷狄、君子和小人的区别,因为仁的显现要借助于礼——复礼为仁。这也是生活在明清之际的王夫之研究礼的主要目的:传续华夏文明,严夷夏之防。王夫之认为,中国、君子、人皆具备仁的德性,并能够行礼,而夷狄、小人、禽兽不具备仁的德性,不能行礼。王夫之把“礼”作为一种标准的划分,对于《礼记》的章节篇章和内容,王夫之认为虽然各篇章内容存在一定同异,但是仍可从中体会先圣复性立人极的意蕴。王夫之在开篇的《礼记章句·序言》中,第一句话便引用《周易》中的“显诸仁,藏诸用”的观点,强调了礼“用”的重要性。此后王夫之在《礼运》篇用《周易》中的“天尊地卑”来类比礼的上下等级之分,认为这是禀于自然秩序。他主张仁礼互释,进而提出了礼学意蕴的两个路向:缘仁制礼则仁体礼用,仁以行礼则礼体仁用。王夫之的礼学中贯穿着体用思想,同时体现了他对“用”的强调。
二、王夫之礼学中的体用思想
王夫之还借体用思想来反对佛老、申韩:“盖尝论之,古今之大害有三:老庄也,浮屠也,申韩也。三者之致祸异,而相沿以生者,其归必合于一。不相济则祸犹浅,而相沿则祸必烈。”〔21〕他站在儒家伦理纲常的角度,批判佛老没有君父、廉耻等观念,造成明朝后期人伦不存,天理不在的局面。在反对佛老的问题上,王夫之主张体用合一,有体自然要有用。例如在《思问录》中,王夫之指出佛老有体而没有用。用既然不存在,那么体也便没有了实际的内涵,“佛、老之初,皆立体而废用。用既废,则体亦无实”。〔22〕在气本论的基础上,他认为世界是往来屈伸变化的,而不是像佛教所说的生灭。“故曰往来,曰屈伸,曰聚散,曰幽明,而不曰生灭。生灭者,释氏之陋说也。”〔23〕在有和无的关系上,王夫之认为物体生于有,而不是生于无,“物生于有,不生于无”。〔24〕王夫之还提出世界是不断运动变化的,没有绝对的静止,“太极动而生阳,动之动也;静而生阴,动之静也”。〔25〕
就本末、体用的角度来说,王夫之认为礼之本在爱与敬,“礼之本无他,爱与敬而已矣”。〔17〕礼为天之秩,“夫礼,立本以亲始,率先以崇孝,统同以益爱,纪分以辨微,尚贤以昭德,旌贵以起功,立训以着义,广类以奖仁,顺古以作则,俟后以行远,十义赅焉。故曰天秩之也”。〔18〕就体用来说,礼为性之四德,因此,仁义礼智皆以性为体,“仁义礼智之体具于性,而其为用必资于才以为小大偏全。唯存神尽性以至于命,则命自我立,才可扩充以副其性,天之降才不足以限之”。〔19〕王夫之还以节用为礼之本,爱人为乐之本。就礼之用来说,王夫之认为知礼成性是变换气质之道。王夫之的体用思想还表现在他所说的“用者必有体而后有用”、“用即体之用”等观点中,即体用不二。丁祯彦认为,王夫之这种体用不二的观点主要包含两种意思:一是具体事务及其作用、功用、用处的意思;二是物质实体和属性间的意思。〔20〕王夫之同样用此观点对礼学进行解读。
对于礼学渊源,王夫之认为从天道秩序上来说,礼是天道之秩序体现,是天理自然之则,秩序明则礼乐兴。如王夫之曾经提到:“夫礼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礼者,天之秩也。其在诗曰:‘有秩斯祜。’天之所秩,而天祜之。祜者,以祜其秩也。”〔6〕在对张载的注释中王夫之也强调礼为天之秩序的说法,“此篇略释三礼之义,皆礼之大者,先王所以顺天之秩叙而精其义者也”。〔7〕有秩序方有礼,王夫之还曾提到:“知秩然后礼行。尊尊、贤贤之等杀,皆天理自然,达之而礼无不中矣。秩序人所必由,而推之使通,辨之使精,则存乎学问,故博文约礼为希天之始教。”〔8〕从礼出现的时间上来说,王夫之认为礼在伏羲、燧人氏之前,“礼乐之始,先于羲、燧。羲、燧导礼乐之精,扬诩于万物”。〔9〕从神道设教的渊源来看,礼是神道之所设,是阴阳、刚柔、仁义自然的秩序体现,如王夫之提出:“盖文与礼,一皆神化所显著之迹,阴阳、刚柔、仁义自然之秩叙,不倚于一事一物而各正其性命者也。”〔10〕他多次强调礼为神化之理的体现,是圣人神道设教的体现,“神化之理,散为万殊而为文,丽于事物而为礼,故圣人教人,使之熟习之而知其所由生;乃所以成乎文与礼者,人心不自已之几,神之所流行也”。〔11〕“天以神为道,性者神之撰,性与天道,神而已也。礼乐所自生,一顺乎阴阳不容已之序而导其和,得其精意于进反屈伸之间,而显著无声无臭之中,和于形声,乃以立万事之节而动人心之豫。”〔12〕从礼和心的关系来说,礼为心之所发,心与礼一以贯之,礼为心所安者。“心所不容已而礼不容已矣,故复礼斯为仁矣。礼者,复吾心之动而求安,以与事物相顺者也。”〔13〕王夫之还认为,心生事,事立礼,礼行而有名,“心生而后有事,事立而后有礼,礼行而后有名。名者,三累之下。天下为之名,而忠孝者不欲自居”。〔14〕此外,对于礼学渊源,还有学者指出了以下几个方面:梅珍生追溯了王夫之“因易以生礼”的源流论。〔15〕即王夫之所提出的:“《易》与礼相得益彰,而因《易》以生礼。故周以礼立国,而道肇于《易》。”陈力祥则指出了王夫之的三个礼学源流:第一是人性趋善角度的“仁以生礼”,即“礼本心生”说;第二是因为礼之基本原则尽在易中,因此,有“易以生礼”说;第三是圣王“继天而立人级”的源流。〔16〕
三、缘仁制礼和仁以行礼的体用关系
王夫之以体用之辨来强调《礼记》和《周礼》、《仪礼》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就最初创立的制度来说,《礼记》为体,《周礼》、《仪礼》为用;就个体修行来说,《周礼》、《仪礼》为体,《礼记》为用。三礼共同构成仁的体现,是人之所以为人,中国之所以是中国,君子之所以是君子的根本。王夫之认为,礼是立人之本、修己治人之道、躬行之密用,他作《礼记章句》的目的在于“存先王之精意,徵诸实用,以俟后哲”,〔26〕其中强调了他注重现实,提倡实践的观点。对于庄子所论述的坐忘顺序,忘仁义而后忘礼乐而后坐忘,王夫之认为与仁义相比,仁义更侧重于心性之体,礼乐更侧重于心性之用,如王夫之提出:“先言仁义,后言礼乐者,礼乐用也,犹可寓之庸也,仁义则成乎心而有是非,过而悔,当而自得,人之所自以为君子而成其小者也。”〔27〕
在对礼学的注解中,王夫之也贯穿着“体用不二”的思想。而且常常“本”、“体”互释。即本和体是同一物体,同时书中还贯穿着经与权、达与成、道与器等互为表里的概念。以下为简要分析。
《曲礼》篇内容详尽,无微不谨,此篇是下学先务,是君子反躬自省之辞。在这里他提出礼之“本”以正心修身、节情去私为要,主张存理遏欲。礼之“用”在于定亲疏、别同异、决嫌疑、明是非,他强调礼的大旨便在于本立而用行。王夫之提出“仁者,爱之体,义者心之制,礼以显其用,而道德仁义乃成乎事”。〔28〕即王夫之提到的第一条阐释礼学的路向——缘仁制礼则仁体礼用。第二个路向主要体现在《四书训义》中:“夫真爱真敬者,人心恻怛自动之生理,则仁是矣。故礼乐皆仁之所生,而以昭著其中心之仁者也。仁以行礼,则礼以应其厚薄等差之情,而币玉衣裳皆效节于动止之际。”〔29〕《檀弓》篇主要是记录孔子以后行礼的异同,王夫之主要研究其中所蕴含的“不易之理”和“精义之用”。对于礼的内容,王夫之指出,礼学是孔子折衷裁定周礼而定,杂含殷、周之礼。礼学有“经”、“权”的分辨,王夫之提出“唯圣人而后可兴权,则下此者不可兴也”。〔30〕
此外,王夫之还从个体、政教以及形而上的角度来理解和阐释礼的含义。从个体修养角度来说,礼为修己治人之大纲、治乱之准,从政教的角度来看,礼为齐民之要道。从形而上学的角度来说,王夫之认为礼为天理之经。熊考核曾经把王夫之的礼学思想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仁礼互为体用,礼为立人之本、立国之本等几个方面。
《大传》篇主要叙述了禘祀之礼、宗子之礼和其中的大义。王夫之认为:“禘以上治以统宗,宗以下治而统族,二者相为表里。”〔37〕王夫之提出族谱和祠堂可作为礼制复兴的根本。《少仪》篇记述了少长、贵贱之礼,是小学的补充,与曲礼、内则互为补充。《学记》篇则是叙述亲师等礼学之教,虽然“故或以为末而未及其本”,〔38〕然而所讲的依然是:“一皆格物致知之实功,为大学始教之切务”,〔39〕与《大学》篇相为表里。因为先王以礼齐民,首重便是礼教。王夫之反对忽略此项内容直接妄谈性命之学。《乐记》篇是戴氏记载先儒的乐教,王夫之认为乐教在古代十三岁以上是必须学习的,是移易性情、鼓舞迁善的有效捷径。然而传说驳杂,而且很多落于性情之论,这是王夫之所不喜的。《丧大祭》篇只是简单论述了“大”为“备”之意。
对于《孔子闲居》与《仲尼燕居》两篇,王夫之认为二者互为表里,《仲尼燕居》篇论“用”之大,《孔子闲居》篇言“体”之微。继续论述体用之辨。《坊记》篇与《表记》篇相为表里,坊为末表为本。“坊者,治人之道。表者,修己之道。修己治人之实,礼而已矣。”〔35〕他借此分析了性之所失,情欲之所发,而且还以《周易》里“遏恶扬善,顺天休民”来进行互释,同时与荀子的理论进行比较。提出《表记》:“以敬为本,以仁义为纲,修身以立民极之道尽矣。”〔36〕《缁衣》篇被认为是《表记》的下篇,记录好恶言行的旨趣,其中好恶为仁之表现,“言行为义之实”。王夫之认为,《坊记》与此三篇,本末相资,脉络相因。
王夫之在《礼运》篇就孔子“叹鲁”提出,其原因在于当时鲁国徒有礼的文饰而失去了礼的实质。对于礼的简繁变化,王夫之认为应该根据时俗而进行变化,三代以上民风淳朴,在上者可以无为而治,百姓礼节可以从简。三代以下淳朴民风不在,因此,先王制礼作乐,使民复合于道。王夫之主张礼治与时偕行,质文迁变,相因而立。对于其中提到的理想社会大同和小康,王夫之认为“大同”是同于礼,“小康”是作小安讲。王夫之在这篇中借夫子之言而阐述礼不可僭之意,主张礼的文质如一。王夫之认为,君王以礼自正,同时也以礼正人,这样诸侯、大夫才能各得其正,不至于僭越失礼,最终达到政治而君安。王夫之因此得出政即是礼的结论:“礼所以治政;而有礼之政,政即礼也。故或言政,或言礼,其实一也。礼以自正而正人,则政治而君安,不待刑而自安。”〔43〕百姓明白礼的法则能够自治,奉养服事无所不合于礼,这样便做到了“礼达分定”,礼才能够成为君王的“大柄”,即“秉礼以治人”、“以礼治人情”,这样即便是派遣臣民去做危亡之事,他们也不会有畏惧之心。王夫之主张做到齐于礼,而不必齐于刑。王夫之再次以体用本末相统一进行了总括:“天道人情虽无异致,而于天道之承徵礼之体,人情之治著礼之用,则本末功效之间亦已别矣。”〔44〕
在《礼记章句》中王夫之特别强调了“用”的重要性,即他的崇实黜虚思想。王夫之的崇实黜虚,一方面是树立实的内涵,一方面是反对王学的空虚,反对玄想,反对释老的邪说淫词。如王夫之多次借《礼记》反对王学之说,他在《大学》篇提出:“自姚江王氏者出而大学复乱,盖其学从入,以释氏不立文字之宗为虚妄悟入之本,故以章句八条目归重格物为非,而不知以格物为本者经也,非独传也,尤非独朱子之意也。”〔40〕王夫之认为,王阳明之说与郑玄之说不合,百年来学术道丧、世事纷乱都是宗王所致。王夫之批评王阳明把“亲民”解释为“如字”是释氏和墨学的余波,把“格”训“式”则是张九成和宗杲的邪说,此后有罗汝芳以“自谦”为“逊让”更是文义不通。王夫之提出:“夫道之必有序,学之必有渐,古今之不能违也。”〔41〕对于王阳明的良知之学则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若废实学,崇空疏,蔑规矩,恣狂荡,以无善无恶尽心意知之用,而趋入于无忌惮之域,则释氏之诞者固优为之,奚必假圣贤之经传以为盗竽乎?”〔42〕
《内则》篇是门内之教,主要叙述德行,内容包括孝德、孝行、友行、顺行。王夫之认为,这种孝友之德生于内心,能够不虑而知、不学而能。然而即便内心具备,如果不能施行于现实,也不能立道,内心最终也会逐步走向衰竭。倘若能够研习行礼,那么便能够在实施的过程中自然使内心充满。王夫之还借此反对良知的淫邪之说,要求学者能够慎思明辨笃行,这样才是经说的正义。《玉藻》篇主要记载冠服、容貌称名之仪。王夫之认为,“王者修明章服以为典礼之本”,〔45〕可以从此篇中考辨而得知,对于继承三代礼法来说具有重大的补益。而且章服之礼也是人禽之别、上下之等、君臣之分、男女之嫌、君子野人之辩的关键,因为衣裳体现了乾坤的法像、人道的纪纲。王夫之生活的时代世降礼坏,他以此反对当时夷狄的寒毛暑裸的“便安”做法。对于《中庸》篇,王夫之认为非躬行心得不能获其指归,他反对明末后期的空谈心性、反于自得、淫于佛老之说。王夫之提出“诚明相资以为体,知行相资以为用,唯其各有致功,而亦各有其效,故相资以互用,则于其相互,益知其必分矣。同者不相为用,资于异者,乃和同而起功,此定理也”,〔46〕在《经解》篇,王夫之认为五经之教化民成俗,所归于礼。五经微言见之于理,礼则实行于事。所以他提出:“五经者礼之精意,而礼者五经之法象也。”〔47〕如果不通五经的微言大义,不懂礼的实施,那么性情治乱之说很可能落为玄虚功利之学。
可一旦要将“道”落实到散文创作之中,就要到涉及到“文”与“道”的关系问题。欧阳修注意到文学创作的文道区别,肯定“文”的独立价值,认为道与文二者缺一不可,《代人上王枢密求集序书》中阐述“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后世”,文章需具有实际内容,同时追求文采。这种既重视文章的实际内涵,又注重文采的观念,将“文”与“道”提升到了同等重要的位置之上,即文道并重。
四、结语
王夫之处于明清之际,其学与此后的乾嘉多有迥异。其家学为春秋之学,然而他遍读群经,对于多部经典都有研究,平生著作多达一百多种、四百多卷。王夫之的《礼记章句》亦多有发明。清代经学昌明,学者对于五经多有研究,礼学著作也有很多。尤其自乾嘉之后,“家家许郑,人人贾马”,当时礼学研究往往通过郑注孔疏,由小学入手。然而,王夫之的《礼记章句》却不引郑注孔疏,只有《大学》、《中庸》篇保留了朱熹章句并为之作衍。而且郑玄注经是以礼学为本,王夫之曾以《礼》注《易》,强调易学的社会伦理思想;以《礼》解《诗》,注重礼制,同样宣扬伦理思想。然而,王夫之的《礼记章句》却是以《易》解《礼》,书中多次借易来阐发礼学意蕴。这是与清代注经思想的不同之处。在内容上,王夫之以“六经责我开生面”来律己,多有创新和发现,除上文外,还有如下几例:
“实践是认识的源泉”,造就人类物质生产的生活状态。“知识改变命运”,让人类意识到认识世界的重要性。人类在实践与思考的不断交替中,创造出专属于人类的意识形态与科学知识,科学技术的创造为人类提供了强大的力量,也为人类对自然的掌控带来了极大的信心。科学技术来源于人的认识与实践,同时也是帮助人类深入认识与实践的工具。主体的能动性实践行为与主观性思维探索所创造出来的精神财富,在一定程度上将会成为人类毁灭自我的无形力量。肉体的自然属性是见证人类是否走向自我毁灭的最好依据,而肉体的自然状态在体育中可以得到直接的检验,并以身体指标来考察主体的危机。
如《王制》篇,王夫之认为其成书于汉文帝,是文帝请当时博士诸生回忆虞、夏、商、周古王制而作,大体义具。内容上参差不齐、有所出入在所难免;在文献不足的情况下,参考四代的礼法来传先圣的思想同样厥功至伟。王夫之同样也是以体用来分析,认为只有把“体”树立起来,才能用之于行,“用”行之后才能表明体不是虚假树立的。在此,王夫之认为制度为体,“王者驭诸侯、齐万民”为用,认为这是长治久安的根本。
王夫之在《郊特性》篇主要就五礼的大端而阐发其中包含的义理,即礼器所阐发的五义:时、顺、体、宜、称。王夫之认为,此篇或为《礼器》篇的下篇,与《礼器》篇相互映照,互为发明。对于出自《吕氏春秋》的《月令》篇,王夫之认为它主要强调“奉天出治”、“敬授民时”。王夫之反对汉代以来附会谶纬之说,反对以灾祥来解经,认为这与五经不合,是惑世诬民之举。王夫之认为,《曾子问》篇是后儒补注,是礼经上所未曾记录的,然而文义精湛,可与礼经互为发明。在《文王世子》篇,王夫之论述了从唐虞的禅让制到商周王位世袭制的变化。王夫之认为,这种变化是为了避免“大奸饰德”,使得天下落在恶人手里。而这篇内容就是为了教育王位继承人,“以孝友中和之道”,〔48〕以培养他的德性。王夫之认为,这篇主旨是以孝悌为教育的根本,礼乐是成德的路径。
在《明堂位》篇王夫之还纠正了几个重要的观念,其一,《明堂位》篇是鲁国后儒记载的侈大之辞,是僭越天子之非礼之事。其二,明堂是天子之宫室,“天子朝诸侯于大庙、户牖之间,其庙之堂坫即所谓明堂也”,〔49〕而不是吕不韦所说的“天子于国之南立一十二月颁政之宫”,〔50〕更不是公玉带、蔡邕之所说。王夫之在《丧服小记》篇指出“小”是“详细”之指,提出礼不遗小,小者必察。对于礼和义之间的关系,王夫之认为“礼由义立而义于礼成”。在《礼运》篇,王夫之也提到,义为礼之质,礼为义之实。关于礼的来源,他认为“礼非由天降,非由地出,而生于人心,尽其心以几于复礼,则天则无不可见矣”。〔51〕
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5:20.
[2][22]徐世昌等.清儒学案 [M].北京:中华书局,2008:370、414.
[3][4][5]王夫之著.周易外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7:10、51、52.
[6][17][18]王夫之著.王船山诗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62:46、51、47.
[7][8][10][11][12][13][19]王夫之著.张子正蒙注[M].北京:中华书局,1975:297、86、136、136、77、50、199.
[9]王夫之著.庄子通[M].北京:中华书局,2009:60.
[14]王夫之撰.读通鉴论[M].北京:中华书局,1975:11.
[15]梅珍生.王夫之《因易以生礼》的源流论[J].船山学刊,2004(2):13.
[16]陈力祥著.王船山礼学思想研究[M].成都:巴蜀书社,2008:109.
[20]丁祯彦.王夫之“体用不二”的方法论意义[J].船山学刊.1993(1):97.
[21][29]王夫之.船山遗书(3)[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3093、1701.
[23][25]王夫之.船山全书(12)[M].长沙:岳麓出版社,1992:22、402.
[24]王夫之.尚书引义[M].北京:中华书局,1976:87.
[26][28][30][31][32][33][34][35][36][37][38][39][40][41][42][43][44][45][46][47][48][49][50][51]王夫之.船山全书(4)[M].长沙:岳麓书社,1988:10、16、131、535、535、579、579、1213、1359、825、869、869、1468、1468、1468、553、558、724、2256、1171、503、773、773、1547.
[27]王夫之.庄子解[M].北京:中华书局,2009:143.
The Physiological Thought and Its Invention in Wang Fu-zhi's Etiquette
Lu Pengfei
Abstract: Yiwenzhi says “courtesy should be in clear style” and Tiantianpian says “courtesy should be in line with morality” .It can be said that both etiquette and style should be emphasized, but few people discuss the style of etiquette.Wang Fu -zhi mainly elaborated the concept of body function and the thought of righteousness and principle of rule of rites in order to oppose the shortcomings of emptiness and to distinguish Yanyixia, human and fowl,gentleman and villain.He not only demonstrates the objective world by means of body and thought, clarif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bject and object, Qi, Taoist instrument and knowledge and action,but also opposes the debate between Buddha and Lao Shenhan.Moreover,he elaborated the thought of ritua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ody and function,emphasizing the viewpoint of using body and substance and removing emptiness,reflecting the research trend of emphasizing practice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Unlike Xu and Zheng Hou -xue in the Qing Dynasty, Zheng Xuan’ s learning was based on etiquette.He interpreted Yi with etiquette.Although they were the same annotations to classics,they had different ideas.
Key words: Wang Fuzhi,etiquette,practical use,easy learning
中图分类号 B234.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547(2019)10-0030-07
[作者简介] 路鹏飞,同济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阿 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