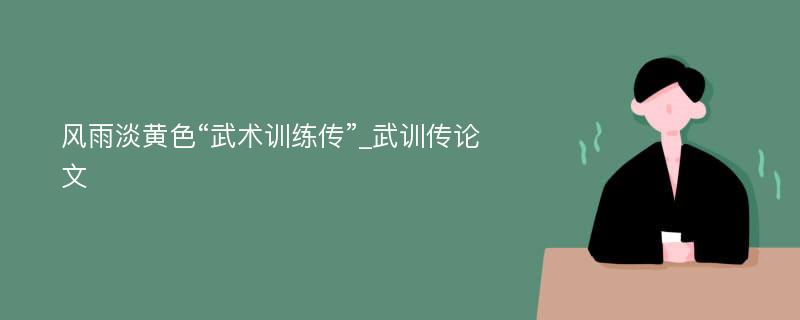
风雨苍黄《武训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苍黄论文,风雨论文,武训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武训传》批判是建国后发动的第一场全国规模的政治运动,它从电影发端,横扫整个思想文化界。运动深入到所有的文化部门,持续了将近一年。对电影事业而言,这场运动造成的后果是极其惨重的。首先,私营电影公司出品的影片受到批判,私营影业随即消亡。其次,电影审查愈发严苛,电影指导委员会更加谨小慎微,以致在一年半内没有一个剧本通过。国营电影厂被迫停产。再次是“对电影人的思想和精神心理的影响。新中国电影界普遍流行达几十年之久的‘不求艺术有功,但求政治无过’的心理病,由此开始。”[1]公式主义、概念化从此盛行。[2]尽管1985年胡乔木代表中共中央对这场运动做了“基本错误的”结论,但这场运动留下的阴影至今没有完全散去。《武训传》不能公映,不能出音像制品,绝大部分文学史和电影史著作仍旧按照主流话语来解释这场运动,把问题局限在所采取的方式态度上。
一、武训其人
武训(山东堂邑人,1838—1896)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平民教育家,他以乞丐之身而行兴学之事,艰苦备尝,终身不渝。为表彰他的义学善举,清政府赐其“义学正”之名号,“乐善好施”的匾额和象征最高荣誉的“黄马褂”。清国史馆将其事迹列入清史列传孝行节内。建国前,各界要人和社会名流对他都备极推崇。蔡元培、黄炎培、邓初民、李公朴、陶行知等民主人士,蒋介石、汪精卫、戴季陶、何思源等政界人物,冯玉祥、张学良、杨虎城、段绳武、张自忠等军界要人,郭沫若、郁达夫、臧克家等文化名流,或为他题辞著文,或为他的义学捐款。近代教育家陶行知更是以他为榜样,创办育才中学,提倡“武训精神”,抵抗国民党当局的压力,反对当时的教育体制。1945年,中共主办的《新华日报》曾发表过称赞他的文章,[3]1943年至1949年间,中共冀南行署还设立过武训县,成立了武训县抗日民主政府。总之,武训是一位有着巨大影响的历史人物,山东民众称其为“武圣人”,知识界视其为平民教育的先驱楷模,国外教育界称其为“无声教育家”。[4]在遭到批判以前,他在历届政权和不同的社会中都是正面的、被褒扬的、受崇敬的形象。
1944年,孙瑜受陶行知先生之托,决心把武训的事迹搬上银幕。1948年7月中国电影制片厂(“中制”)投拍此片。11月初,在影片拍摄三分之一的时候,“中制”因政治形势和经济困难停拍。1949年2月,昆仑影业公司以低价购得此片的拍摄权和底片、拷贝。孙瑜加入昆仑公司接拍此片。在1951年2月拍成前,这个剧本经过三次修改。
二、孙瑜三改《武训传》
第一次修改是在1949年底,在参加了新中国的第一次文代会,征询过周恩来对武训的看法之后,孙瑜采纳“昆仑”编委会陈白尘、蔡楚生、郑君里、陈鲤庭、沈浮、赵丹、蓝马等人的意见,对剧本做了第一次修改。这是一次根本性的修改。37年后,孙瑜撰文谈到主要修改的内容:“剧本的主题思想和情节虽然作了重大修改——改‘正剧’为‘悲剧’——武训为穷孩子们终身艰苦兴学虽‘劳而无功’,但是他的那种舍己为人的、艰苦奋斗到底的精神,仍然应在电影的主题思想里予以肯定和衷心歌颂。”[5]
1950年初,“上海电影事业管理处”的领导之一陆万美在听取了剧本的主题思想和剧情后,提出建议:“我感到影片提出的问题,和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已隔离得太远。老区农民翻身后自觉学习文化非常热烈,民办公助的‘庄户学’,新型的人民大众学校已成千上万地建立。武训当时的悲剧和问题,实际早已解决。但武训艰苦兴学,热忱劝学的精神,对于迎接明天的文化热潮,还可能有些鼓励作用。因此建议,在头尾加一小学校纪念的场面,找一新的小学教师出来说话,以结合现实,又用今天的观点对武训加以批判。”[6]孙瑜按照陆的意见,对剧本做了第二次修改。
从艺术形式上讲,这次修改主要在开头和结尾。剧本原来的开头是由一个“老布贩”在武训出殡时对他孙儿讲武训兴学的故事,结尾也是由这个旧时代的老人勉励孙辈们好好念书。孙瑜将时间、背景和人物做了修改。时间由清末(1896年)改成了解放后(1949年),背景由武训出殡改成了武训诞辰111周年纪念会,讲故事的人由“老布贩”改成了“人民女教师”,听众则由老人的孙子改成了新中国的小学生。为了达到“用今天的观点对武训加以批判”的目的,女教师在影片的结尾说了一番总结性的话:“武训老先生为了穷孩子们争取受教育的机会,和封建势力不屈服地、坚韧地斗争了一辈子。可是他这种个人的反抗是不够的。他亲手办了三个‘义学’,后来都给地主们抢去了。所以,单纯念书,也是解放不了穷人。还有周大呢——单凭农民的报复心理去除霸报仇,也没有把广大群众给组织起来。中国的劳苦大众经过了几千年的苦难和流血的斗争,才在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组织之下,在无产阶级的政党的正确领导下,打倒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权,得到了解放!我们纪念武训,要加紧学习文化,来迎接文化建设高潮。我们要学习他的刻苦耐劳的作风,学习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让我们拿武训为榜样,心甘情愿地为全世界的劳苦大众做一条牛吧!”[7]这段盖棺论定的话“是1950年底,《武训传》全片摄完时,经过党领导作过修改后审定的。基本上概括了《武训传》的主题思想(或称‘倾向’)和剧情发展——评述和刻画武训幻想‘念书能救穷人’并为之奋斗一生的‘悲剧’,歌颂他坚持到底的精神,描写武训发现他兴学失败的悲痛,把希望寄托在周大武装斗争的胜利上。这也是1950年初《武训传》剧本之所以得到通过并进行拍摄的主要原因之一”。[8]
第三次修改与前两次不同,前两次源于政治,第三次则是由于经济——昆仑公司发不出工资,要求孙瑜将此片拍成上下两集。在紧密结合主题思想的基础上,孙瑜添加一些情节:一,武训昏睡中幻入地狱、天堂的梦境。二,李四和王牢头协助周大越狱,周大逼上梁山。三,封建官吏为了收揽人心,利用武训,奏请朝廷嘉奖武训。这次修改虽然不如前两次重要,但是它加强了一文一武这正副两条线索,丰富了人物形象,凸显了主题思想。
1950年底,《武训传》公映,“观众反应极为强烈,可算是好评如潮,‘口碑载道’”
。[9]1951年2月,孙瑜带着拷贝到北京请周恩来等领导审看。2月21日晚7时,周恩来、
胡乔木、朱德等百余位中央首长在中南海某大厅观看了此片,“大厅里反应良好,映完
获得不少的掌声。”[10]朱德与孙瑜握手,称赞道“很有教育意义”[11],周恩来、胡
乔木没提多少意见,周恩来只是希望将狗腿子毒打武训的镜头剪短。[12]孙瑜马上照办
三、五十年评价:正—反—合
关于《武训传》的评价,五十年来经历了一个正—反—合的过程。从1950年12月公映到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前,人们对《武训传》的评价基本是正面的——国内各大报纷纷发表影评和介绍性文字:孙瑜介绍编导此片的艰辛过程,赵丹讲述了演武训时受到的教育,端木蕻良赞扬武训的奉献精神,育才学校的校长表示要进一步发挥“武训精神”……据统计,在这几个月中,各地报刊发表的有关文章共计55篇。[13]在这55篇之中,只有贾霁、杨耳、邓友梅等少数人对武训和影片持批评态度。在十七年的电影史上,“百家争鸣”的局面只有两次,这是第一次。
在反对意见中,贾霁的文章《不足为训的武训》值得一提,此文的观点不但颇有代表性,而且还有相当的“理论”色彩。贾文认为,影片是失败的。就人物的思想而言,武训没有透过现象看本质,不是把阶级压迫而是把不识字当做穷人受苦的根本原因。他生活的时代正是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兴起的时代,他身边还有一个参加过太平军的周大,“为什么这个时代这个影响没有在武训的头脑里起着积极作用呢?”因此,武训对生活的认识“是从个人出发的,主观唯心的,形式主义的”,“这种认识,违反历史现实的真理,它的出发点是错误的,它的结果是危险的”,就人物采取的方法而言,武训的行乞兴学,脱离劳动,脱离群众,脱离伟大的时代运动。办义学“不走群众路线”,“不依靠群众来实现计划”,而是依靠地主阶级。这说明武训“没有站稳了阶级的立场,是向统治者做了半生半世的妥协和变节”。因此,武训走的“是阶级调和的路线”,其方法是“近似于改良主义的方法”。就题材而言,武训这个题材根本不值得表现,“它与我们伟大祖国的历史不相称,与我们伟大的现实运动不相容,它对于历史和今天,都是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的”。而编导在表现这一题材上也犯了“严重的”、“根本性”的错误:“武训既然是一个善良的劳动人民,按照他小时候的‘聪明灵巧’善于学习的特征,对于私塾先生和掌柜这类人物的仇恨,到了后来为什么都丧失殆尽了呢?”“武训的幼年分明已经有着对于识字的渴望,为什么一定还要到地狱里去幻游一下才有所谓的觉悟呢?那一种变态的心理分析所表现的一种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疯癫痴迷患得患失的没落情调,难道是一个老老实实的劳动农民所能有的情绪吗?”一个更严重的错误是,影片宣传说,“文字无论掌握在谁手里也都是对任何人服务的,……这就是影片所编造的关于立据偷字据的等等戏剧性,突出地肯定地宣传了字据在当时社会的超阶级的社会效能”。字据是法律凭证,而法律是有阶级性的,封建社会的法律是为地主阶级服务的,所以他们根本不怕字据,武训并不会因为有了一纸字据,就能从地保那里要回他存的钱。地保也犯不着为了赖账而派人去偷与武训立下的字据。结论是:“作者在这里尽其能事地做到了一种模糊阶级斗争意识的一种无原则立场的宣传。”[14]
贾霁的观点是基本错误的。第一,他对武训“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要求背离了历史的规定性,把阶级斗争的观点强加给历史人物。第二,他对武训的责难——不走群众路线,投靠地主阶级办义学,对地主阶级的仇恨丧失殆尽等说法违背了基本的历史常识。第三,阶级斗争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唯一动力,阶级合作、改良主义同样是推动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力量。[15]第四,因此,同近代史上出现的工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等进步的、改良的思潮一样,武训“办个义学为贫寒”的人道主义思想和努力不但在历史上有意义,在现实中亦有价值。第五,影片表现武训觉悟的艺术手法——梦游地狱天堂,是否允当可以讨论。但将其说成“变态的心理分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疯癫痴迷患得患失的没落情调”则完全是以政治话语取代艺术分析,以打棍子扣帽子代替正常的学术探讨。
在中国电影史上,贾霁的这篇文章意义重大,它不但为反历史,反马克思主义,反现实主义的“政治索隐式影评”开了先河,[16]而且也为强辞夺理、上纲上线、“五子登科”的党棍学阀的恶劣作风开辟了道路。此文最初发表在《文艺报》上,在毛泽东发动《武训传》批判的前五天,被《人民日报》转载,成为发动这次政治运动的前驱先导。两年后又成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武训和<武训传>批判》一书的首篇,此文在权力话语中的意义和分量可见一斑。
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亲自撰写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这篇社论是毛泽东文艺思想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文献,它是对《讲话》中提出的“歌颂与暴露”观点的补充和发挥。《讲话》中,政治是区分歌颂与暴露的标准。社论则将这一标准深入到文化之中。这篇社论也是对关于京剧《逼上梁山》的通信中提出的历史观的丰富和发展。在通信中,毛泽东要求的只是“恢复了历史的面目”,而在社论中,则进一步提出了如何看待中国历史,如何看待农民革命的问题。并为《武训传》下了这样的结论:它是“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这篇社论开创了以政治手段解决文艺问题的先河,“强化了文学主题的单一性”,“使文艺隶属于政治的关系更加凝固化。”“《讲话》为中国当代文学思潮所奠定的这一基石,在这次批判运动中被夯实加固。”[17]
在社论发表的当天,《人民日报》在“党员生活”栏中,发表短评《共产党员应该参加关于<武训传>的批判》,《人民教育》发表社论《展开<武训传>的讨论,打倒武训精神》,文化、教育、历史研究等部门迅速地行动起来,召开各种批判会,各界名人被组织起来,纷纷发表表态性文章,徐特立、何其芳、夏衍、艾青、袁水拍、胡绳、王朝闻、钱俊瑞、华君武、陈波儿等踊跃参加。孙瑜、赵丹登报检讨。马叙伦、李士钊(《武训传》的作者)、端木蕻良等为武训说过好话的人们纷纷进行自我批判。《大众电影》等刊物纷纷刊出编辑部的检讨文章。不久,中央教育部发布了“各地以武训命名的学校应即更改校名”的通知。从社论发表到5月底的11天中,仅报上发表的批判和检讨文章即达108篇,6月份报上批判文章的数量则翻了四番,不算各报编发的文章,仅以个人署名的文章即达410多篇,至1951年8月底,这类文章已达到850多篇。[18]
此后为了彻底澄清文化界和教育界在武训问题上的混乱思想,人民日报社和中央文化部组织了一个武训历史调查组。调查组由周扬负责,由《人民日报》的袁水拍、中央文化部的钟惦棐和江青(化名李进),山东宣传部的冯毅之,聊城地委宣传部的司洛路,临清镇委宣传部的赵国璧等13人组成。在堂邑、临清、馆陶等县、镇、区、村干部的协助下,访问了当地各阶层的人160余位,进行了两个多月的调查。《武训历史调查记》由袁水拍、钟惦棐、江青三人执笔。7月23—31日,《人民日报》连载《武训历史调查记》。
《武训历史调查记》分五部分,一、和武训同时的当地农民革命领袖宋景诗;二、武训的为人;三、武训学校的性质;四、武训的高利贷剥削;五,武训的土地剥削。《武训历史调查记》的结论是:“武训是一个以‘兴学’为手段,被当时反动政府赋予特权而为整个地主阶级和反动政府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武训历史调查记》将这一全国性的政治运动推向高潮,各单位组织人马学习《武训历史调查记》,各种学习心得占满了大小报刊的版面。郭沫若、翦伯赞、管桦、李尔重等名人学者纷纷撰文,谈《武训历史调查记》给他们的教育启发。8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周扬的文章《反人民、反历史的思想和反现实主义的艺术》,这一长文为《武训传》批判做了理论性的总结:政治上反人民,思想上反历史,文学上反现实主义。周扬的逻辑前提是:“因为新中国是革命是武装斗争的成果,如果强调改良主义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当然,就等于质疑了革命的合理性和正当性。”“这个前提,一是否认对历史的不同阐释的合法性,另一个是否认文学写作的修辞性质,和作家的虚构的权利。”[19]根据这个前提,周恩来在中央做了检查,夏衍等电影方面的领导在报上公开检讨,李士钊六年后被打成右派,武训成为死有余辜的历史罪人,《武训传》被禁映。《武训传》的评价由正面走向了反面。
16年后的“文革”期间,对《武训传》的批判被人们以更狂热的姿态书写,1967年5月26日,《人民日报》重新发表毛泽东为《武训传》撰写的社论。5月27日,《人民日报》在报道全国亿万军民欢呼《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重新发表的同时,宣布“把《武训传》和《修养》一起抛进垃圾堆”。刘少奇的“修正主义”与武训的“奴才主义”挂上了钩。在挥舞批判的武器的同时,武器的批判也派上了用场——武训的坟墓被掘,尸骨被抛,塑像、匾额、祠堂被毁。《武训传》更成了过街老鼠。
这一局面直到29年后才被打破。1980年8月,江苏无锡公安分局张经济投书《齐鲁学刊》,希望为武训平反。作者根据亲身了解的事实指出:一,武训始终是一个靠行乞过日子的穷人,虽然后来有了田产,但都是为了办义学,他本人却不敢有所私。二,统治阶级确实嘉奖过他,但他没有接受那件黄马褂,没有以此欺压乡里,穷孩子读书仍然可以不缴学费。三,他本人没有反对过农民起义。四,他办义学确有一定成绩。至于义学失败,是社会造成的,绝不能由武训来挨棍子。在文章的结尾处,作者写了这样一段话:“从批判《武训传》、《清宫秘史》到文化大革命,我国开展了众多的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大革命,我们失去了什么,得到了什么,真该认真总结一下深刻的教训啊!”[20]从张文发轫,至1981年上半年,《齐鲁学刊》连续四期发表李士钊、范际燕、范守信等人重评武训和《武训传》的文章。但此后四年中,“由于极左思想的干扰,《齐鲁学刊》再未敢发表有关这方面的文章。”[21]直至1985年9月6日,胡乔木代表中共中央发表公开讲话。
胡乔木说:“我们现在不对武训本人和这个电影进行全面的评价,但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明,当时这种批判是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的,因此,这个批判不但不能认为完全正确,甚至也不能说它基本正确。”[22]这一表态为我们提供了两个信息:第一,中共中央承认当年的批判是错误的,错误在于思想和方法。思想上“非常片面、极端”,方法上非常“粗暴”。显然,这是一种非常简单、含糊的表态。它既没有说明这种思想的性质,也没有解释这种思想为什么会在党内畅通无阻。第二,尽管这种表态表明了新时期的执政党面对事实和重估历史的勇气,但是,表态的内容却说明,在武训和《武训传》这类涉及到重大理论问题的历史人物和事件面前,国家意识形态所提供的理论是贫乏无力的,它无法对武训和《武训传》做出全面的评价。
民间话语弥补了权力话语的缺席。在1991年和1995年召开的两次全国武训研讨会和此前发表的文章中,学界对武训和《武训传》做出了新的评价:一,武训走的是教育救国的路。其兴学活动反映了下层农民朴素的改良主义意愿。武训是改良主义中的平民改革派。二,武训继承发扬了“仁者爱人”的思想,对社会下层表现出强烈的同情心和博爱精神。三,毛泽东曲解了《武训传》。他指责《武训传》“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武训的行乞兴学。事实上,影片始终“没有在画面上反映出周大率领的农民起义军‘失败’,相反,影片倒用了不少镜头来描绘农民起义军给地主阶级的沉重打击”。“随着《人民日报》那篇社论的发表,电影《武训传》便给拍板定了案,从此打入冷宫,而且时隔四十多年,至今尚未翻身。在人民民主专政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封建式的长官意志竟然还有如此巨大的威势,这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震惊的憾事。”[23]四,《武训历史调查记》先下结论后找证据,歪曲、捏造事实。“脱离事实联系的所谓历史调查,可以说是开了唯心主义的反历史的先河,以这份调查记,和污蔑诬陷刘少奇同志的所谓调查相对照,我们就会发现其唯心主义的反历史的血缘关系。”[24]
历史在轮回,胡乔木讲话之后,关于武训的活动再次活跃起来。百余年来纪念武训的历程浓缩在十几年中重新上演——各种纪念活动接踵挨肩,戈宝权、臧克家、胡絜青、张劲夫、胡绳等社会名流为武训题辞,赋诗;武训纪念堂、纪念馆落成,武训展览馆、研讨会开幕。被列为山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七五”规划重点项目的《武训研究资料大全》出版,历史在自我嘲弄中走完了正—反—合的全过程。
四、思考尚未穷尽
与其说《武训传》批判引起的问题至此结束,毋宁说真正的思考才刚刚开始——几乎所有的论者都在努力地将武训和《武训传》与改良主义区别开来。其实,这种努力是徒荣的。在这一点上,毛泽东和周扬们是对的。问题并不在于武训和《武训传》是否与改良主义沾边,而在于我们如何看待改良主义在历史上的作用。进言之,在于我们如何评价剥削阶级、统治阶级的历史地位,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恶”对于历史的推动作用。凡是谈到武训与周大关系的论者都在为武训辩护,说他没有反对农民起义。其实,这种辩护没有多大意义。问题并不在于武训对农民革命的态度,而在于如何评价这种农民革命。进言之,在于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近代史的主流。如果我们将走向现代化作为近代史的主流的话,那么,真正的主流是给中国带来了资本主义的洋务运动和具有资产阶级改良性质的戊戌维新,而不是作为旧式农民战争尾声的太平天国和盲目排外、愚昧迷信的义和团运动。凡是论及《武训传》批判的教训的论者,都以国务委员张劲夫的说法为准,以为造成这场错误的批判的关键在于“未有将学术问题、艺术问题与政治问题区分开来”。[25]事实上,这种来自于权力话语的解释并没有说到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区别什么学术、艺术与政治,而在于当时的政治体制和这个体制所奉行的思想体系,在这种体制和体系之下,学术、艺术就是政治。正是这种体制和体系,为激进主义极左思潮的发展壮大,为毛泽东批判《武训传》提供了条件。毛泽东提供观点,贾霁等极左派提供方法,上下结合,配合默契,激进主义的政治——文艺运动从此大行其道。
标签:武训传论文; 武训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人民日报论文; 孙瑜论文; 胡乔木论文; 农民论文; 苍黄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