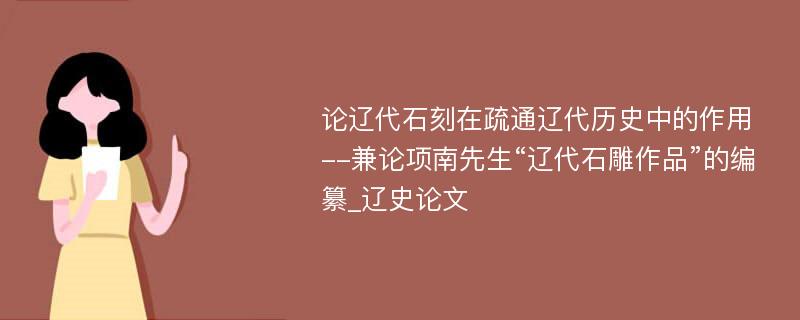
论辽代石刻在疏证《辽史》中的作用——兼评向南先生《辽代石刻文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辽代论文,石刻论文,向南论文,作用论文,辽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辽朝(公元907-1125年)是以契丹人为主体在中国北方建立的封建政权。而《辽史》则是于辽亡200余年后的元末至正三年(1343年),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异常尖锐,元政权已处于风雨飘摇中进行修撰的。由于当时国柄将移,人心惶惶,加之国家财政亦已极为困难,修史工作亦便匆匆行事,敷衍塞责。据载,史官廉惠山海牙、王沂等四人仅用了11个月时间(至正三年四月——四年三月),便将一部记述200余年历史的《辽史》仓促修成。由此,便注定了《辽史》从它脱胎之日起就存在着严重的先天不足——史事缺漏,舛讹百出。亦正如中华书局版《辽史》“出版说明”所云:元修《辽史》时,既没有认真搜集和考订史料,再加上纪、志、表、传之间相互检对也很不够,因此,前后重复,史实错误、缺漏和自相矛盾之处很多,甚至把一件事当成两件事,一个人当成两三个人,这种混乱现象在二十四史中是很突出的。
由于《辽史》存在着上述种种问题,便给历代学者研究辽代历史带来极大不便。有鉴于此,自明清以来,尤至近现代,不少史实便参阅其他历史文献,对《辽史》进行校勘疏证。但限于历史上传留下来的记述辽朝史事的文献资料奇少,便使得这项工作进展缓慢,成效甚微。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自80年代以来,史家为疏证《辽史》,在广泛勾沉文献史料之基础上,又把目光转向地下出土的、极富史料价值的辽代各种石刻(包括石经、庙碑、塔铭、经幢、造像、哀册、墓志、神道碑、石棺、枕石、井栏、题名等)。然而,由于辽代石刻出土(或被发现)的时间不一,出土及存放地点又极为分散,再加上大多数石刻文字缺损、剥蚀、泐漫不清及无标点断句等等,因而也给研究者带来了较多困难。值得庆贺的是,向南先生历10余年的艰辛搜集、拓抄、考证和整理,如今,一部收文300余篇的《辽代石刻文编》终于付梓,给辽史研究者带来了福音。
本文试就辽代石刻在疏证《辽史》中的补阙、订讹和释疑作用、略作论述:兼就向南先生《辽代石刻文编》一书的史料和学术价值,简加介评。
一、补阙——填补《辽史》记事之缺漏
后世史家编纂前代历史,主要依据是前朝遗留下来的文献资料。因而,所编成史书之内容是丰富还是寡略,记事是详实还是简缺,均取决于史官修史时所参阅的前朝文献的数量和质量。建立辽朝的主体民族契丹属北方游牧民族,原起松漠,崇武少文。建国后,在汉族文化的影响下,其文化虽有长足发展,但政府书禁甚严,不仅严禁文字出境,而且民间私刊书籍亦以死罪定论。因而,有辽一代文献流传极为有限。至辽末,女真、蒙古起于北方,五京兵燹,缣帛扫地,辽朝有限之典籍文献亦散佚殆尽。至元人修《辽史》时,几乎无直接文字可依,只能求助于宋、金人的间接记戴。故而,史事记述之缺漏,实在所难免。《辽史》记事之缺漏,出土之辽代石刻文字,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予以补之:
其一,补《辽史·百官志》中辽朝设官及机构设置之缺漏。契丹辽朝的官制及机构设置颇具民族特色。《辽史·百官志》载:“辽国官制,分北、南院。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因俗而治,得其宜矣”。但《辽史·百官志》对辽代的官制机构记载却缺漏很多,尤其是对一些低级职官和下层机构,漏载尤甚。如,《辽史·百官志》“北面宫官”条有“某宫提辖司”。但云“官制未详”。即,不知该机构内设有何种职官。查应历五年(955年)《刘存规墓志》,即有墓主人曾“拜积庆宫都提辖使”之记。又,统和二十年(1002年)《平州赵府君墓志》见“永阳宫平州提辖使”;天庆三年(1113年)《马直温妻张馆墓志》见“诸宫提辖制置使”;重熙十四年(1045年)《王泽妻李氏墓志》见“知延庆宫提辖”,等等。积庆宫,为辽世宗耶律阮的宫帐,契丹名“耶鲁盆斡鲁朵”(耶鲁盆,契丹语“兴盛”)。延庆宫,为辽兴宗耶律宗真的宫帐,契丹名“窝笃盆斡鲁朵”(窝笃盆,契丹语“孳息”)。《辽史·百官志》只记辽置“诸宫提辖司”机构,但缺漏该机构内的设官情况。然由上述诸墓志石刻文字,可知辽“诸宫提辖司”内设有“提辖使”、“提辖制置使”等官员。可补《辽史》之缺略。
其二,补《辽史》“列传”中辽代人物授职宫衔之缺略。《辽史》“列传”记载的均是有辽一代著名历史人物。这些人生前大多是辽代官贵名人,其中不少人官居要位,身兼数职。我们通过这些人物所任之官职爵衔,可以了解和研究辽代的职官制度及机构设置情况。但,元人撰《辽史》时,却将不少辽代人物的官职名衔给遗漏掉了。如,刘六符是兴宗、道宗朝著名汉官。《辽史·刘六符传》仅载其官至“三司使”。然乾统元年(1101年)《悟空大德发塔铭》有“兴宗道宗朝宰相、守太尉、兼侍中刘公,讳六符”。由此知刘六符曾在兴、道两朝任过宰相之职,《辽史》“本传”失载,应补之。
其三,补《辽史·地理志》中辽代州县机构设置之缺漏。辽代的地方行政区划,是以五京为中心,分全国为五道:上京道、中京道、东京道、南京道和西京道。其中州、县是辽朝地方的两级主要行政机构。据《辽史·地理志》“序”载:五道共辖“州、军、城百五十有五,县二百有九,部族五十有二,属国六十”。这是元代史家修撰《辽史》时统计的数字。但,查诸辽代石刻,辽代还有些州县,《地理志》漏记。如,金州,《辽史·地理志》即不见载记。但,乾亨三年(981年)《陈公之铭》中有墓主人陈公任“……金州诸军事、行金州刺使”之记。又,统和二十三年(1005年)《王悦墓志》中有:墓主人王悦之长女“适金州防御使国(管)内诸处置使张近武之次男日行为妻”。再,重熙八年(1039年)《张思忠墓志》中有:墓主人张思忠的一个儿媳为“金州防御使大守节女”。由上,知辽朝确置有金州。《辽史》漏载,石刻可补之。
其四,补《辽史》中人物名、字之缺漏。古人有名亦有字,辽代人亦不例外。同时,辽代契丹族人的名、字更复杂,他们既有契丹语名和字,又有汉名和汉字。然而,《辽史》中不少汉人及契丹人的名或字却被缺漏未载。如,耶律隆庆是辽景宗耶律贤的次子、辽圣宗耶律隆绪的弟弟。据《辽史·皇子表》:“隆庆,子五人,查葛、遂哥、谢家奴、驴粪、苏撒”。此五人之汉名,《辽史》均未载。据清宁八年(1062年)《耶律宗政墓志》:“王即孝贞皇太叔元子”。“王”,即墓主耶律宗政;“孝贞皇太叔”,指耶律隆庆。由此可知,耶律隆庆之长子契丹名为耶律查葛,汉名是为耶律宗政。查葛,圣、兴二宗“纪”又作查割、查哥、查割折,《契丹国志》作查个只,均为契丹语音译致岐。又,咸雍元年(1065年)《耶律宗允墓志》有:“王即孝贞皇太弟之第三子也”。“孝贞皇太弟”亦指耶律隆庆。由《皇子表》知隆庆第三子名谢家奴。这就是说,谢家奴是隆庆三子的契丹名,宗允是其汉名。该墓志还记:宗允“兄二人,长曰宗政,守太傅,兼中书令,魏国王;次曰宗德,大内惕隐,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湃王”。由此又知隆庆次子汉名宗德,即《皇子表》中的遂哥。《契丹国志》记宗教为圣宗之子。然《耶律宗教墓志》的出土,知驴粪(旅坟)即是宗教,且为隆庆庶子。以上均可补《辽史》之缺漏。
其五,补《辽史》中人物世系之缺漏。前已言之,凡于《辽史》入传者,均为对辽代历史在某些方面有过影响的重要人物。他们多出身宦家大族,或兄弟、或父子、或祖孙几代人均授官封爵,世袭显赫。因而,明晰《辽史》中人物之世系,有益于辽代社会政治及文化习俗的深入研究。但恰恰《辽史》中有不少重要人物之世系由于记载疏漏而模糊不清。如,王郁是辽初从中原投奔契丹辽地的汉官之一。《辽史·王郁传》未记其子孙,故其世系不详。据统和二十三年(1005年)《王悦墓志》,知王郁有子名王廷阮,曾任左千牛卫大将军、检校司空。墓主王悦是王廷阮之子、王郁之孙、官至宁远军节度副使、监察御史。又据乾亨三年(981年)《王裕墓志》,知王郁还有一子名王廷鹗,官至龙化州节度使。墓主王裕是王廷鹗之子、王郁之孙,官至崇义军节度使、御史大夫等职。此均可补《辽史》之缺漏。
其六,补《辽史》中辽代某些大事记述之缺漏。一部《辽史》,记录了有辽一代发生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及典章制度、礼仪风俗等等。但有些大事却漏载未记。如,辽与周邻国家均有互使来往,但有些互使活动却于《辽史》中缺漏未载;有些被记载者,亦缺漏使者姓名。如,辽圣宗太平五年(1025年),辽朝政府曾派韩橁出使高丽,然此次出使活动《辽史》却失载。据重熙六年(1037年)《韩橁墓志》:“乃命使高丽国,贺王询之诞辰也”。些即可补《辽史》之缺漏。韩橁此次出使高丽,《高丽传》亦有载:“显宗十六年秋七月辛已朔,契丹遣监门卫大将军韩橁来贺生辰”。可为佐证。又,《辽史·圣宗记》:开泰八年,“正月,封沙州节度使曹顺为敦煌郡王”。九年,“七月甲寅,遣使赐沙州回鹘敦煌郡王曹(恭)顺衣物”。《辽史》中这两次派员出使沙州事,均不记出使者姓名。而由《韩橁墓志》,知出使者正为韩橁。墓志云:“明年,奉使沙州,州主帅曹恭顺为敦煌王”。此亦可补《辽史》之缺漏。
二、订讹——纠正《辽史》史事之错误
《辽史》不仅记事简漏,而且因元末修《辽史》时距辽代时间已较久远,加之缺乏第一手资料,因而,所记之辽代史事,存在不少错误。此外,《辽史》修成后,在后世传抄、刊刻过程中,也难免有笔误出现。《辽史》存在记事之错误,对研究辽代历史亦极为不利,会以讹传讹,贻误后人。所幸,出土之辽代石刻文字可以订正《辽史》中的许多错误。
其一,对《辽史》中人名错误的订正。《辽史》中记载的辽代人物之名字,在传抄、刊刻过程中,不仅产生了大量缺漏,而还出现了种种错误。如,《辽史》“帝纪”、“皇子表”及“列传”中均记辽圣宗耶律隆绪的长子名耶律宗真(辽兴宗),次子名耶律重元。《辽史》记耶律重元在道宗朝曾与其子涅鲁古谋反,失败后自杀。据咸雍八年(1072年)《耶律仁先墓志》:“时帝(辽道宗)叔宗元与子涅里骨,恃宠跋扈”。由此墓志,知耶律重元应作耶律宗元,《辽史》误。因为,辽代契丹人受汉族文化影响,其同辈兄弟间的汉名有一字必是相同的,如辽圣宗耶律隆绪弟兄们的汉名中间字均为“隆”字,萧孝穆兄弟们汉名的中间字均为“孝”字,等等。那么,兴宗皇帝耶律宗真弟兄们的汉名中间字即应为“宗”字。宗、重音近,是为音译所致岐也。与之相类的例子还有《辽史·道宗纪》中的贾士勋,应据寿昌三年(1097年)《贾师训墓志》及《续资治通鉴》等改为贾师训。《辽史·兴宗纪》中的邓延贞,应据寿昌四年(1098年)《邓中举墓志》改为邓延正。
其二,对《辽史》中官称错误的订正。《辽史·百官志》中记述了有辽一代置设的各级诸类职官名称。但史官们在修史过程中,因避讳、笔误等原因,有意或无意地致使某些辽代职官名称出现了错误。如,《辽史·百官志》中记有“西头承奉”之官职。而乾亨三年(981年)《王裕墓志》中却作“西头供奉”。据考证,《辽史》作“承奉”,误。其致误原因应是金人修“辽史”时,为避金章宗父允恭名字讳,而改“供奉”为“承奉”。元人修《辽史》时又因袭沿用致讹。应改之。
其三,对《辽史》中地方机构名称错误的订正。《辽史》中地方机构名称指《地理志》及《百官志》中出现的辽代地方州(军)县机构之名称。这些地方州、县机构名称,亦常因字形、读音相近等原因,在史书刊刻传抄过程中被弄错。如,《辽史·百官志》记“西南边防官”中有“五州制置使司”。又云:“圣宗开泰九年见霸、建、宜、泉、锦五州制置使”。而《地理志》却载:“兴中府,本霸州彰武军,节度。统和中,制置建、霸、宜、锦、白川等五州”。上述五州,《百官志》与《地理志》中有四州名同,惟有一州名异,《百官志》记为泉州,《地理志》记为白川州,不知孰是孰非。开泰六年(1017年)《朝阳东塔经幢记》中有“建、霸、宜、白川、锦等州”之记,可证《百官志》“泉”乃“白川”之讹。与之相类的例子还有:《辽史·百官志》有勝州,而《地理志》则作媵州。太平九年(1029年)《萧仅墓志》中有“次迁勝节度使”。可证《地理志》“媵”误,应为“勝”。又,《辽史·地理志》显州附廓奉先县,县与军同名。而寿昌三年(1097年)《贾师训墓志》有“服阕,授奉玄县令”。知《地理志》作“奉先”误,应为“奉玄”。《金史·地理志》:“广宁府,旧有奉玄县,天会八年改为钟秀县”。“旧有”,指辽有也。此可为之佐证。
其四,对《辽史》中人物封号错误的订正。《辽史》中记载的亲王、公主、驸马、国舅以及其他官高位显的文臣武将等,大都有受皇帝分封的各种封号(爵号)。有些人不仅生前受封,死后还多次被追封,所以他们的封号多者可达几个至十几个。封号之多之滥,史官修史时就难免记错。如,辽景宗长女名观音女,为睿智皇后所生。观音女之封号,《辽史·公主表》记述缺略且有误:“封魏国公主,进封齐国。景福中,封燕国大长公主”。据重熙十五年(1046年)《秦晋国大长公主(观音女)墓志》,知其正确封号应为:齐国公主、楚国长公主、晋国长公主、吴越国长公主、赵魏国长公主、秦晋国大长公主。《公主表》中魏国公主、燕国大长公主封号均错,应改之。
其五,对《辽史》中各类记事“时间”错误的订正。史书对历史事件发生时间的记录准确与否,于历史研究至关重要。《辽史》记录的辽代各类历史事件,大都有其发生的具体时间,粗略者可为“××年间”或“×年”,详细者可至“×年×月××日”。但,有些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记载却是错误的。如,辽景宗第二子名耶律隆庆,封号为梁国王,曾官拜大元帅之职。《辽史·皇子表》记其拜大元帅时间在圣宗开泰年间:“初兼侍中,统和中拜南京留守。开泰初守太师,兼政事令,寻拜大元帅,赐铁券”。而统和二十三年(1005年)《盘山甘泉寺就创净光佛塔记》:“定州之战,隆庆封为梁王,加兵马大元帅”。按,“定州之战”发生在统和二十一年。此可作隆庆拜大元帅时间在统和年间的傍证。又如,耿延毅是圣宗朝著名之汉臣,官至户部使、御史大夫等职。据开泰九年(1020年)《耿延毅墓志》,知耿延毅死于开泰八年(1019年)冬十二月七日。而《辽史·圣宗纪》则记:太平二年(1022年)七月,“以耿延毅为昭德军节度使”。太平二年耿延毅已死三载,死人岂能再任节度之职?显系《辽史》纪年有误,应改之。再如,义州,《辽史·地理志》记其于兴宗重熙初年更名:“庆州富义县,本义州,太宗迁渤海义州民于此。重熙元年降为义丰县,后更名。录弘义宫”。又,永州义丰县,本铁利府义州。辽兵破之,迁其民于南楼之西北,仍名义州。重熙元年,废州,改今县。在州西北一百里。又尝改富义县属泰州(庆州)。始末不可具考,今两存之”。然据重熙八年(1039年)《张思忠墓志》及咸雍八年(1027年)《创建静安寺碑》,知重熙八年至咸雍八年间,义州尚存。《地理志》所记义州改名时间显系有误,应改之。
其六,对《辽史》中各类记事“史实”错误的订正。史籍中出现的史实错误,对历史研究之影响更为严重。《辽史》因编纂粗陋,所记辽代历史“史实”错误很多。如,《辽史·耶律仁先传》载:“仁先,字糺邻,小字查刺,孟父房之后”。而咸雍八年(1072年)《耶律仁先墓志》却记:仁先“远祖曰仲父述刺实鲁于越,即第二横帐,太祖皇帝之龙父也”。由此墓志知仁先应为仲父房之后,而非孟父房之后,《辽史》所记有误,应改之。另,《辽史·耶律仁先传》:仁先“父瑰引,南府宰相,封燕王”。而《耶律仁先墓志》却记:“王(仁先)父讳思忠,圣宗皇帝朝,为南宰相”。再查大安十年(1094年)《耶律庆嗣墓志》,知耶律思忠与耶律瑰引实为一人,前为汉名,后为契丹名。《辽史·皇族表》记瑰引为仁先之祖,显系错误,应改正之。又如,《辽史·地理志》:“武州,宣威军,下,刺史”。“武州统县一:神武县。初隶朔州,后置州,并宁远为一县来属”。大康五年(1079年)《武州经幢题记》有:“大辽武州宁远县”。由此“幢记”知武州统县应为宁远,而非神武,《地理志》所记有误。另,《金史·地理志》:“武州,县一:宁远,晋故县”。《山西通志》:“武州治宁远,在五寨县东北神武废县,又即宁远镇也”。可为傍证。再如,《辽史·道宗纪》:清宁元年(1055年),“是年,御清凉殿放进士张孝杰等四十四人”。而乾统三年(1103年)《师哲为父造幢记》却记:“重熙二十四年,一举明经擢第”。按,道宗清宁元年即兴宗重熙二十四年。兴宗皇帝死于是年八月,随之道宗耶律洪基称帝改元。由上幢文知此年御殿放进士者乃是兴宗皇帝耶律宗真,而非道宗。《辽史》将此事记在《道宗记》中显系错误,应改之。
三、释疑——开释《辽史》记事之疑团
《辽史》因记事简漏,因而,有不少史事真相或模糊不清,或似是而非,给研究《辽史》者带来不少困难。辽代各类石刻之出土,便使诸多《辽史》史事之疑团被开释、破解。
其一,释《辽史》人物世系之疑。前已提及,《辽史》存在着对所记述的辽代重要历史人物世系的严重缺漏。不仅如此,有些人物世系还迷雾重重,使人疑惑不解。如,《辽史·韩匡嗣传》记匡嗣有五子。然其是否有女儿?若有,有几个?女儿的夫家及子女如何?《辽史》中不见一字。据太平九年(1029年)《萧仅墓志》:墓主人萧仅之母为“今皇后之姨,故秦王之女。”“今皇后”,指圣宗仁德皇后萧氏;“故秦王”,即指韩匡嗣。又《耿延毅墓志》记:“燕京留守、尚父秦王季女,累赠陈国太夫人耶律氏,乃妣也。齐天章德皇后,乃姨兄妹也”。由上二墓志,知韩匡嗣有三女:一女嫁萧隗因,生女为圣宗仁德皇后菩萨哥;一女嫁左羽林统军秋绍纪,生子为耿延毅,官至户部史、武平军节度使等;一女嫁侍中萧罕,生子为萧仅,官至宁远军节度使。又如,韩匡美,《辽史》无传,其事仅见《辽史·景宗纪》:保宁三年(971年)正月辛酉:“南京统军使魏国公韩匡美封邺王”。韩知古,《辽史》有传,并记其有一子名韩匡嗣。那么,韩匡美与韩知古有何关系?匡美是否亦是知古之子?以前因材料不足,疑团无法开释。今据重熙六年(1037年)《韩橁墓志》,知墓主人韩橁曾祖父为中书令韩知古;祖父为燕京统军使、天雄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赠守太师、兼政事令、行魏州大都督府长史、上柱国、邺王韩匡美。由此即证实韩匡美也是韩知古之子。
其二,释《辽史》所记辽代州县置地之疑。由于《辽史》记述不清,再加上时间久远,历史地名多变,便使得《辽史》中所载之辽代设置的州、县具体地址多已不详。如,《辽史·地理志》:“利州,中,观察。本中京阜俗县。统和二十六年置刺史州,开泰元年升,属中京。统县一,阜俗县”。辽利州城置于何处,《辽史》无载。近世人发现在辽宁喀左县大城子镇东门,有一古城址,东西宽450米,南北长600米。钱大昕《潜研堂金石子字跋尾》及《热河志》、《塔子沟纪略》等均论定其为辽代利州城故址。但又均缺乏足够之证据。1958年,考古工作者在喀左坤都营子乡钱杖子村西北双尖山上出土了辽代《王悦墓志》。该墓志出土地正位于大城子古城西30里处。而志文恰云:“葬于利州西三十里”。由此墓志便可足证大城子古城址即为辽利州置地无疑。又如,《辽史·地理志》:“安德州,化平军,下,刺史。以霸州安德县置,来属。统县一:安德县”。“安德县,统和八年,析霸城东南龙山徒河境户置。初隶乾州,更属霸州,置州来属”。辽安德州置地,《辽史》亦不详,近世《热河志》、《蒙古游牧记》及《朝阳县志》等皆以为“在三座塔(朝阳市)东南柏山之上”。然却缺乏有力之证据。后来,人们在辽宁朝阳南70里五十家子柏山上发现了辽乾统八年(1108年)《兴中府安德州创建灵岩寺碑》,上有“灵岩寺者,北连龙岫,前俯郡城”之句。据此足证辽安德州应置于柏山之下。今朝阳城南70里五十家子村有一古城址,当是安德州故址,因其地恰在柏山脚下,北距灵岩寺遣址约5里,正与碑文所记相符。
四、拓新——《辽代石刻文编》的双重价值
向南先生以十数年之苦功,呕心沥血编就的大著《辽代石刻文编》,是近世以来研究古代石刻的拓新之作,其本身即具有史料及学术之双重价值。
说其具有史料价值,不仅仅限于如上所论之对《辽史》等文献的补阙、订讹和释疑,更重要的是,这些石刻所记述之文字,所涉及的内容相当丰富和广泛,它能为史学工作者研究辽代的政治经济、典章制度、人物事件、战争交聘、宗教文化、历史地理、城镇建设、民族关系、民风民俗、语言文字等提供丰富可靠的第一手资料,使辽史研究开拓新的领域,取得更大的研究成果。当然,出土之石刻资料亦并非百分之百的“信史”,尤其是一些“墓志铭”,同样存在着隐恶扬善、谀颂粉饰的毛病,在使用过程中,应当加以认真甄别。这些,笔者将另文介绍,此不赘述。
说其具有学术价值,是指该书并非仅仅限于汇集、整理石刻文字和断句标点,而是于书中还凝聚了编著者对每篇石刻文字的大量校订、考证及研究之心血,使该书不仅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而且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换言之,该书既是一部珍贵的辽史研究资料汇集,同时也是一部高质量的辽史研究学术著作。
其一,编著者对每篇石刻,都参照大量文献资料或其他石刻文字,进行了详细的注释,尤其是对石刻中出现的人名地名、人物世系、官职机构等等,均予详细注释,这样,便大大方便了读者,为他们省去了大量而繁杂的考证、索释之时间与精力。
其二,编著者对石刻文字中出现的某些疑难问题,进行了缜密的考证,使历史得以复原。如,编著者对辽代汉官王郁的历官职衔的考证,就是明显一例。王郁是辽代前期著名汉官,《辽史》有传,并且,王郁之后人还有墓志出土。但王郁在辽之官职,出土墓志与“本传”所记迥异。如《王裕墓志》记王郁职衔为“龙化州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中书令”。《王悦墓志》记王郁职衔为“明殿左相、义武军节度、易定祁等州观察处置等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守司空、同政事门下平章事、使持节定州诸军事、行定州刺使、太原郡开国公,食邑一千五百户”。而《辽史·王郁传》则只记他因随辽太祖阿保机征渤海有功,“加同政事门下平章事,改崇义军节度使”。太祖死后又“加政事令”。“墓志”与“本传”所记,除文散阶与加官相同外,其职事官则无一相符,究其原因乃王郁官职因时迁转变化所致也。于是,编著者经认真考证后认为,王郁在辽历官次第当是:初授义武军节度使,改授崇义军节度使,进授明殿左相,终任龙化州节度使,时间在天显三年(928年)正月。这样一来,王郁在辽历官便明了清晰矣。诸如此类之考证,在该书中俯拾即是,不胜枚举。
其三,编著者在该书中还对石刻文字中出现的辽代史事错误,进行了认真订正,显示出了编著者的认真、求实之学风。如,重熙二十三年(1054年)《张俭墓志》中有“诏充南朝皇帝生辰国信副使”之记。编著者认为此句有误。查《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大中祥符四年(辽统和二十九年)“十二月甲子,契丹遣使长宁军节度使耶律汉宁、副使太常少卿张俭来贺明年正旦”。编著者经考证后认为,墓志作“生辰”有误,应依《长编》作“正旦”为是,因为《长编》所据为宋人《实录》,不会有错。又如,大安八年(1092年)《韩瑞墓志》中有“秦王讳知古,即公之五世祖也”。编著者经认真参订《韩橁墓志》、《耿延毅妻耶律氏墓志》及《韩瑜墓志》后认为,韩知古从未被封为“秦王”,封“秦王”者乃其子韩匡嗣,是墓志撰者误把韩匡嗣之署衔爵位加在了乃父身上。此类之例证,在该书中还有很多。
*本文所举之事例,均参引自向南先生编著之《辽代石刻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