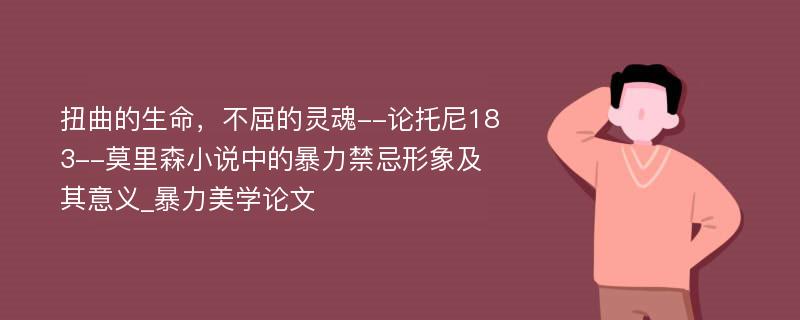
扭曲的生命,不屈的灵魂:论托妮#183;莫里森小说的暴力禁忌意象及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象论文,禁忌论文,暴力论文,灵魂论文,莫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539(2008)10-0017-06
暴力是人类基于原始冲动的一种行为。在人们彼此交往的社会活动中,通常都具有避免伤害他人的愿望,即“道德的关心”。这种关心的基础存在于与他人的联系中。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中,移情作用和认同与理解他人的能力为社会关系中的道德与和谐提供了基础。只有缺少移情作用与道德的关心时,残忍的反社会的暴行才会发生,并被称之为“非人性”①。禁忌的出现也同样与社会道德规范有关,破坏禁忌也就同样会受到非人性的责难。由于暴力和被禁忌行为的非人性,也因其凶狠残酷的摧毁手段总是具有悲剧性质,所以人类的文明总是在尽量消解着暴力。然而,暴力和破坏禁忌带来的悲剧却总是无法根除的,表现并反省暴力也就成了文学中的经典主题之一。从西方文学源头的圣经与希腊罗马神话到当代文学,无数著名的文学篇章因对暴力的描写与揭示而震撼人心:战争、暴行和酷刑的审视创造了《麦克白》、《战争与和平》、《丧钟为谁而鸣》等流芳百世的文学经典,使人们在惊悚中体验人性的悲哀,经历感情的升华。当代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美国作家托妮·莫里森则从一个新的角度向读者展示了属于少数族裔的非裔美国人的暴力世界。他们的世界曾经是无人关注的角落,但他们遭受创伤后却发出怒吼并在深重痛苦中自省。现实与历史的尖锐冲突通过莫里森笔下的暴力和破坏禁忌的意象尽情展示,接受着读者的审阅,也考验着读者的承受力。
一、暴力意象的文学原型基础
作为美国历史上曾经遭受制度之痛、人身权利之痛最为深重的非裔美国人,在承受了社会集体暴力和个人暴力之后,一直处于种族冲突的高峰,是美国暴力事件的主要承受者和发动人。“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美国城市的种族暴力冲突主要限于白人和黑人之间,大大小小的暴力冲突共有30多次,其中主要集中在两次高潮期。第一次是1915~1919年间,共达22起。规模较大的一起是1917年圣路易市的种族冲突,其间有312栋房屋被毁,48人被杀,100多人受伤;另一起是1919年芝加哥的冲突,造成38人死亡,537人受伤,财产损失200多万美元;同年,类似的暴力冲突在首都华盛顿、奥马哈和查尔斯顿等20多个城市爆发,达到第一次高潮期的顶峰。第二次高潮是1943年,主要冲突发生在纽约市和底特律。两次冲突共造成60人死亡,1000多人受伤,600多人被捕,财产损失达500多万美元”②。这些暴力事实是莫里森小说中暴力现象的来源和原型基础,是非裔美国人生活中无法回避的社会现实。
从非裔美国文学传统来看,它在某种程度上也包含着张扬暴力的因素。非裔美国文化中著名的传说“恶作剧的猴子”就有暴力的特征。恶作剧的猴子在民间故事中并不是以强者的身份出现的。它正像非裔美国人一样,在个人力量上处于弱势,但猴子有着暴力的报复目的,它所运用达到目的的手段也包含着暴力的因子(例如,有一次狐狸开罪于恶作剧的猴子,猴子就运用非裔美国人特有的喻指的语言③教唆大象攻击狐狸,把狐狸踏伤)。而猴子通过语言的暴力体现了强烈的情感,如同长期处于压抑状态下的黑人奴隶的情感,一旦爆发就有不可遏止的趋势。莫里森在斯德哥尔摩诺贝尔奖授奖典礼上的演讲中,在谈到语言和对语言的控制时指出,语言具有启示性功能,因此,压抑语言比采取行为上的暴力更为有效。这本身就是暴力。
因此,在莫里森的小说中存在大量对非裔美国人暴力的描述既符合种族生存的现状,也是文学史上对暴力美学的一次族裔文学实践。从她的第一部小说《最蓝的眼睛》到新近出版的《爱》,8部小说中都有关于乱伦、谋杀、强暴和家庭暴力等内容,对小说情节的发展、人物的塑造起着重要的作用。例如,在《乐园》中由于狭隘的信仰局限而在修道院发动大屠杀。出于母亲亲子之爱的杀子行为在《宠儿》和《秀拉》里均有所表现(《宠儿》中奴隶母亲赛丝用锯条割断了女儿的喉咙以使她逃脱奴隶命运。《秀拉》中不愿看着儿子颓废崩溃的母亲、秀拉的祖母伊娃将儿子淋上汽油烧死)。《最蓝的眼睛》中毕珂拉的父亲强暴了女儿。此外还有因爱而谋杀的例子,如《爵士乐》里名叫乔的中年黑人持枪袭击他的情人。莫里森描写的这些暴力禁忌事件由于已经触及了人类道德伦理的底线,因此,显得敏感而微妙,在读者和评论者中也是议论纷纷。而莫里森自己在《所罗门之歌》里对频繁出现的暴力意象做了一个意味深长的解释:“人们常会做一些古怪的事情。特别是我们(非裔美国人)。这副牌的安排顺序对我们就是不利的,而我们还是尽量去玩牌,保住命还要去玩牌,这就常使我们做出古怪的事情来——一些我们必须得去做的事情,一些使我们互相伤害的事情。我们甚至不知道为了什么。可是你看,不要把它变成心理负担,也别把它转给别人。尽量去理解它,如果做不到,就忘记它,使自己保持坚强。”④这段话对我们认识她的小说中如此频繁的暴力意象可作参考。
二、多维度的暴力禁忌意象
莫里森小说中的暴力和破坏禁忌的意象是多方面的,主要有如下几种形态:杀子、乱伦与谋杀。针对上述形态,莫里森进行了不同的阐释,从多方面、多角度展现了非裔美国人灾难深重的现实处境。
1.杀子——异化的母爱
在小说《秀拉》和《宠儿》中均出现了母亲亲手杀死自己子女的情节。在小说《秀拉》中,主人公秀拉的祖母伊娃有一个最心爱的儿子布朗。伊娃孤单一人,为了养活子女不惜在铁轨下自残身体以换取一点微薄的赔偿,含辛茹苦地终于将孩子们养育成人。伊娃在国家需要的时候将儿子送上战场,期望他以一名真正的男子汉的勇气报效祖国。然而战争的残酷击垮了布朗脆弱的神经,退伍以后他沉沦堕落,完全丧失了面对世界的能力,吸毒上瘾不能自拔。伊娃的百般开导也丝毫不能使布朗振作起来。于是最后伊娃在布朗醉酒后将其淋上汽油,锁在房间里烧死了。
《宠儿》中杀子的情节比《秀拉》中的情节分量和意义都重,是小说故事发生的契机。小说主人公赛丝一直有心事:她曾经是奴隶制下的黑人女奴,因为不堪忍受奴隶主的虐待,怀着身孕带着孩子一起出逃。由于途中产子行动不便,又遭到奴隶主的追捕,赛丝用手锯割断大女儿的喉咙,还准备杀掉小女婴但未能成功。事隔多年,赛丝仍然常常想起被自己杀死的大女儿,而女儿的怨灵也经常回来骚扰她。
母爱在文学作品中是经常被讴歌的对象,母爱的无私、宽容与自我牺牲精神使母亲这一身份往往被冠以“慈爱”的标签,在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中莫不如是。然而莫里森笔下的母亲与传统母亲形象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与对比。她们刚毅、果断、性格强悍,对亲生子女也能痛下杀手。自然界的雌性动物都会竭力保存自己的后代,但莫里森小说中的母亲则令人望而生畏,能让人想起莎士比亚名剧《麦克白》中著名的恶女人原型麦克白夫人,她宣称能够将上一分钟还在她胸前吃奶、微笑的婴儿毫不留情地从奶头上摘下来摔得脑浆涂地。然而莫里森小说中的这些母亲却又不是以恶魔般的形象定位的,读者在震惊的同时,很明显可以从行文中感受到主人公给家庭的保护和安全感。那么,应当如何看待这种悖论,作者这样描写的真实意图又在哪里呢?
莫里森没有以作者的权威为她们百般辩护,但是在小说中有这样一些文字的痕迹,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找到真实的答案。面对已然知悉自己曾经杀子的孙女,伊娃说道:“我没有办法。他想爬回我的子宫,但他已经太大了,我再也装不下。”⑤伊娃可以用家里仅有的一点猪油整夜不合眼地救治婴儿时期差点因便秘死去的布朗,可以拖着一条腿的残躯从三层楼上往下跳,奋不顾身地搭救身上着火的女儿汉娜,她对孩子不但不是没有母爱,而是母爱相当深厚的。秀拉的祖母伊娃宁可让儿子布朗怀着尊严去死,也不愿他浑浑噩噩地倒退到如婴儿般活着。
《宠儿》中,深爱赛丝的保罗·D,理解她在特殊处境下的特殊选择是因为“她的爱太浓了……这是一把手锯带来的安全”⑥。赛丝宁愿让幼女死在自己的怀中也不要她重蹈母亲的覆辙,沦为牛马不如的女奴。这种将生命的尊严看得比生命本身还要高贵的情感,在被逼上绝路的时候就变成了暴力。武断的暴力,替别人决断生死的暴力,即使是因为爱,即使是因为出自于母亲,也在血腥中令人掩卷。这是异化的母爱,无奈的母爱——因为将生而为人的尊严看得高于一切——所以替最心爱的人做出了毋宁死的选择。这种生怕子女受辱的疼惜之情演变为一种攻击力,为子女做出了反对他人的伤害而不是逆来顺受的决定,在缺失了与环境对话的声音时,以行动代替了声音倾诉她所被禁止、不能诉说的内容。
莫里森在这里以浓重的笔墨、强烈的情感与冷静的理性评判了母亲/女性的暴力攻击力。整个杀子事件因为是由母亲来完成的而更显得不能见容于社会。事实也正是如此,伊娃和赛丝的家庭都被她们所在的社区回避着、隔离着,取消了平等的交流权。在通常父权社会意识形态的深处,女性的完美表现是服从和逆来顺受的,母亲更是被定位为温柔慈爱甚至溺爱子女阴柔情感的代表。非裔美国妇女则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她们甚至不如非裔美国人中的男性。具有反叛性的女性攻击力之所以受到社会排斥,是因为社会对她们的期待值正好相反。反叛性的非裔美国妇女的行为受到的限制更多,得到的指责与惩罚也更强烈。但那些合乎社会承认和许可的行为仅仅具有的生存价值,可以使她们在这样的社会活下去,却不是她们与生俱来的性格特点和心灵的渴望。因此,当她们无法获得相应举止的生存价值时,生存下去只能使用攻击的方式。暴力,看起来仿佛是一种无法控制的情感,带走了她的呼吸。她使用身体语言去表达她的痛苦,与此同时,也更为直接地表达了她的愤怒和孤独。孩子的死亡不仅是个人的悲剧,也是母亲的悲剧,更是整个家庭的悲剧。而赛丝一度被剥夺的母性发出的强烈的母爱使她在悲剧发生后的几十年间一直受到内心痛苦的煎熬。宠儿的鬼魂与其说是超现实的影像,不如说是一个母亲的良心一直耿耿于怀、耽于自责,因而对自己进行审判的一个幻影。
莫里森笔下的女性都不愿让自己向歧视性的关系或环境妥协。她们不能放弃自我,听凭自我消失在别人的意志中,哪怕这种外在的力量比她们自身强大上千倍。她们肯定自己的价值,为维护自我不再逃避或者退缩。在充满暴力的家庭中,在充满敌意的社会上,她们选择“用攻击性的武器保护自己。她们站在自己的根据地上,把身体、情感与精神方面的体验结合在一起”⑦。心理上的恐惧会蒙蔽一个人的感知力,让人无法思考。而被迫采取的新的行动使自己对自身的力量有了新的感知⑧。这是最后的抉择,是深切的无奈下绝望的反抗。
2.乱伦——无所适从的安慰
在《最蓝的眼睛》里,莫里森描写了父亲对女儿的强暴。主人公佩可拉的父亲乔利在看到瘦弱的女儿独自做家务时,想起妻子对女儿的冷漠,试图安抚女儿。然而醉酒的他不由自主地对女儿性侵犯,导致佩可拉怀孕,最后疯狂。这段场景令人联想到拉尔夫·艾里森的《看不见的人》里也有一段类似的情节:“看不见的人”在上大学期间,曾经领着学校的捐款人视察黑人民宅。他们无意中了解到,这家的家长,身为父亲的黑人贫民因为窘迫的居住环境与女儿同居一室,最后发生乱伦。具有嘲讽意味的是,这家人苦苦挣扎时无人理会,但悲剧俟一发生,众人却争相救援,致使这位父亲无所适从,不知是悲是喜。
佩可拉的父亲乔利是一个毫无成就的底层黑人。缺乏教育和缺乏经济基础的他对子女的爱无从体现。他既没有能力给予她足够的物质生活条件,也不善于将自己对家庭成员的精神关爱表现出来。这可从小说第30节在性攻击发生前对乔利的心理描述中得到印证:
当他喝醉酒后回到家里,这时佩可拉正在厨房里做家务。面对女儿辛勤劳动的背影“瘦窄的脊背弯曲着”,乔利心情复杂。“乔利迷迷糊糊地瞧见了她,但说不清他看见了什么,感觉到什么。然后他感到不自在,接着,不自在的感觉又被喜悦代替。他感情发展的顺序是嫌弃、内疚、怜悯,然后是爱怜。”这种复杂的心情来自他潦倒的人生。因为自己受到挫败,所以不愿看到自己的女儿也是生活的失败者:“(乔利的)嫌弃之心是对她年轻无助、毫无希望的生存的一种反应。她的腰弯着,头歪向一边,好像总是在躲闪还未出击的一拳。她为什么看上去那么胆怯?”(Morrison,1994:161)作为还未成年的孩子,女儿理应在父母膝下承欢,无忧无虑地享受童年,而他的女儿却因为父母的无能和冷漠,必须在小小年纪就分担家庭的生活重担和忧虑。这个家庭给她的欢乐和自信都太少了。
可是作为一个收入和地位都十分窘迫的黑人男人,他又拿什么给女儿,让她快乐呢?乔利对女儿充满怜爱,却又恼恨自己无法给她实质性的帮助:“她还是个孩子,没有负担,可为什么她并不快乐?她所表现的苦难是一种职责。他想扭断她的脖子,但要轻轻地。自责与无能汇成一曲狂暴的二重奏。他能替她做些什么呢?能给予她什么?能对她说什么?一个贫困潦倒的黑人能对他弯曲着腰背的十一岁的女儿说些什么呢?”
失败的个人经历使他感到极度困扰,损伤了为人父的自尊,甚至使他有了挫败感,以及对引起挫败感的女儿的羞恼之情:“如果他正视她的脸,他能看见那惊恐却又充满爱意的双眼,前者使他烦躁,后者使他暴怒。她竟敢对他表示爱意。难道她丧失理智了吗?他该怎么处理此事?回报吗?怎么回报?他长满老茧的双手怎样才能让她露出微笑?他的哪些人生哲理会对她有用?他凭借自己粗壮有力的胳膊以及喝得烂醉的脑袋做出什么成功之举才能获得自尊,并使他能接受女儿的爱戴呢?他对她的忌恨进入了肠胃,令他作呕。”
小说在这里急转直下,醉酒的父亲在一阵复杂的思想活动后,选择了逃避。他的意识突然模糊了,他从女儿与妻子相似的体态与相似的家务工作中回想到他的黄金年代,那时和妻子相亲相爱,于是心里充满柔情蜜意,那是“一种温情,一种护卫之情”。朦胧中他已经分不清妻子和女儿,混乱的理智和混乱的爱使他突破了道德防线,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恶。
这场性攻击的悲剧性在于乔利原始本能的感情——要求被承认,并付出感情找错了对象。施与感情的主体身份完全不切合承受者的客观需要。父爱与性爱相互掺杂,对人类文明的伦理基础公然挑战,结果当然是一场灾难。佩可拉的怀孕与崩溃再次提醒了乔利,他的自责是多么可怕的正确——他不仅不能为女儿做些什么,反而因为自己的昏聩毁了她的一生。
莫里森在谈到佩可拉父亲性暴力情节的处理和构思时也说:“这无疑是最骇人的一幕。但是当你读到此处,你会忽略这种暴行。因为我想向人们展示的是他对女儿的爱和他面对女儿所受的伤害的无力感。在那样特定的时刻,他的拥抱和性暴力是他所能够给予的全部的馈赠。”⑨事实上,美国黑人奴隶在获得解放后,男性较女性而言,在突然敞开的白人父权社会里处境更为艰巨,承受着更为深重的精神压力。他们在获取自由后必须调整身份,重新适应社会规则,并同仍然存在的歧视抗衡。他们必须为生存奋斗,然而竞争的起跑线已经不平等。在奴隶制下被剥夺拥有家庭的权力是他们没有对家庭的责任感的根源,这使他们的家庭生活面临危机。乱伦的禁忌因此被打破了,精神上的爱护和肉体上背道而驰的暴力行为构成了人伦的悲剧。这不仅是佩可拉和她父亲的悲剧,而且是处在丧失了平等竞争和生活权利之下的非裔美国人最深沉的悲哀。
3.谋杀——压力之下的崩溃
对于非裔美国人的暴力行为莫里森特并不是一味同情,全力支持的。在她笔下也有对消极的、失去自我控制的非裔美国人暴力的暴露与批评,充分体现了客观公允的审视态度。例如,在《爵士乐》和《乐园》中,莫里森写到了谋杀——因爱生恨和移情泄愤的复仇。如果说,对杀子和乱伦两种暴力行为莫里森还存有基于历史的同情和感慨,那么谋杀则更多地体现了作者对奴隶解放以来非裔美国人发展进程中滥用暴力的思维模式的警示与反思。
《爵士乐》中的男主人公乔和妻子从南方来到北方建立家庭。他人到中年以后和少女多卡丝发生了婚外情,多卡丝背叛了他之后,乔在失望之余来到多卡斯狂欢的舞会上,拔枪射杀了她。乔既毁了多卡丝,又毁了他和患难与共的妻子建立的家庭。《乐园》中则是讲述奴隶制废除以后,四大家族带领百多名黑人北上寻找新生活,几经沿途城市拒绝之后,他们建立了属于自己的纯血统小城。可是,这个理想主义的小城爆发了精神危机,瘟疫的流行加深了人们的惶恐,他们陆续迁走。留下的人和小镇的领袖们怪罪于城外的一个救助女性的女子修道院,最终带人闯入并进行大肆屠杀。天堂流血了,人们在为婴儿下葬时心灵在颤抖。
对这类的暴力复仇事件,莫里森的笔触是贬抑的。或许非裔美国人曾经承受了来自国家与社会历史太多的暴力,而美国传统中暴力的一面——从殖民时期开始,许多边疆居民养成了依靠自己和社区的力量以法律和正义的名义来维持安全的传统,而非裔美国文化所交汇的南方文化更是热衷于以暴力维护自身荣誉的传统——也将滥用暴力和私刑的阴影投向了它的另一些居民:非裔美国人。小说中的非裔美国人既是暴力的历史受损者,又沿着施暴者提供的思维和行动方式对社会复仇。因此,莫里森在《爵士乐》中剖析使乔发生心理失衡的个人原因的同时,探讨了族裔文化本身的缺憾和误区在这场不幸中扮演的角色。在《乐园》中,这种思考进一步深化了。在建构族裔身份的努力中,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应该怎样填补;一个按照种族主义模子印制的黑皮肤居民的家园能否真正成为理想的安居之地?而《乐园》通过一个被血腥味玷污的乐园,诘问一个心胸狭隘的民族怀着不宽容、不谅解的心态又如何战胜生活的挫折,最终站立起来?理想早已在复仇泄愤的过程中背离了初衷,这不仅是非裔美国人纯血统小城鲁比的悲剧,更应当是引起所有种族所有人类共同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宽容谅解与自强不息应当如何相辅相成才可以创建充满希望的未来。
三、再谈暴力与禁忌意象的意义
历史苦难与现实压力之间的矛盾、避免伤害他人的意志与受到他人伤害的事实之间的矛盾始终存在于非裔美国人的生命中。这是所有悲剧的本质:一方面,人对尊严和理想的要求不可遏止;另一方面,人在现实中受到限制,人性的脆弱和生命的短促使得预期目标无从达到。在研究非裔美国人的暴力禁忌行为时,不承认这样的矛盾,对其心理的解释就会导致误读。丧失了正常宣泄途径的父母之爱、子女之爱和情侣之爱与暴力之间的关系仍然是种族歧视文化下的一个阴影。而沉默和噤声也有可能并非是由于爱的缺乏,而是因为无法表达。而“当个人受虐史与社会现实交织在一起时,往往导致绝望与恐惧”⑩。暴力因此产生了。它是情感的宣泄,在无从发出自我之声的时候,以行动诉说无法言传的心声,于是暴力取代了表述。
莫里森小说中由暴力引起的悲剧效果与欧洲经典文学对悲剧性的阐释是非常不同的。亚里士多德曾经将文学作品反映的悲剧性解释为:悲剧总是来自高贵的主人公由于过失遭受巨大灾难,在大场面、强纵深的悲剧情节引导下,读者/观众产生由灾难引发的普遍恐惧或者震惊,并由此得到心灵的荡涤与升华。暴力在此与人类对真善美的向往产生富有力度的张力,给人穿过历史探索生命本源的动力。
而莫里森以反讽的方式将文学经典中的暴力和暴力引发的悲剧放置到非裔美国文学里来,引发悲剧的暴力实施者不再是高贵而理想化、典型化的主人公,而是卑微的普通非裔美国人。他们在危机时分被命运胁迫而奋起最后绝望的抗争,以自我的牺牲、尊严的牺牲和人性的牺牲为代价谱写了一曲悲怆交响乐。甚至暴力的主角施与者亦被颠覆,被更多地分配给处于社会最底层、“骡马似的”黑人妇女。虽然她们单薄的力量不足以对抗整个社会的主力意识形态话语,但她们刚烈的性格促使了生命绝境下泣血的反击。面对这样的悲剧,这样总是以丑陋的形式咄咄逼人地出现的人性灾难,读者感受到的已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恐惧或者震惊,而是应当重新认识社会历史对弱势群体深重的负债,以及如何寻找解决之道的思考。
当然,非裔美国人也应当为他们的暴力担负一定的责任,莫里森在小说中的反思已经说明了这一点。但是如果社会能够对以前犯下的罪恶及逆行进行忏悔和有效弥补,那就将更有效地促进非裔美国人选择从暴力走向温和。人之向善往往是因为有一个使人向善的环境,只有这样,社会才能和谐进步。莫里森通过展现非裔美国人的暴力根源和人性的冲突,来为非裔美国人寻找身份和政治权力的努力伸张正义,她的小说的暴力美学原则因此构成了对欧洲经典悲剧原理的反讽,是少数族裔文学解构经典话语的又一次胜利。
收稿日期:2008-8-31
注释:
①黛娜·克劳雷·杰克.刘盛林译.面具后的女人[M].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00:124页.
②Hughs D.Graham and Ted R.Gurr,Violence in America,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A Report to the National Commission on the Causes and Prevention of Violence (Washington 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69),vol.1p.41.Dary1 B.Harris,The Logic of Black Rebellions.
③喻指的语言是黑人英语的特征之一,通常通过“言此意彼”的手段表述字面含义所不能及的内容,详见拙作“视角的重构:论盖茨的喻指理论”[J].外国文学研究,2004(4)。
④Toni Morrison.Song of Solomon[M].NY:Penguin Books,1977:101.
⑤Toni Morrison.Sula[M].NY:Knorf,1974:32.
⑥Toni Morrison.Beloved[M].NY:Knorf,1987:196
⑦黛娜·克劳雷·杰克.刘盛林译.面具后的女人[M].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00:292。
⑧同上,300。
⑨ed.Danille Taylor-Guthrie.Conversations with Toni Morrison[M].US:University Press of Mossissippi,1994:164.
⑩黛娜·克劳雷·杰克.刘盛林译.面具后的女人[M].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00: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