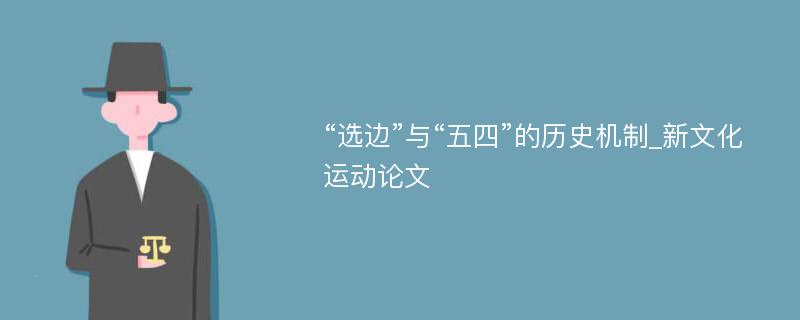
“选边站”与“五四”的历史机制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机制论文,历史论文,选边站论文,五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五四”作为“运动”的身影早已远去,但历史却没有因此而平静下来,它留下的诸多话题,如民主、科学、自由、启蒙等,在今天依然莫衷一是,其分歧并不亚于“五四”当年。甚至,连“五四”本身的意义和基本形象都还存在着莫大的争议。直到今天,围绕“五四”,我们似乎还在进行着一场没有硝烟的文化激战,或者说,是剑拔弩张、非此即彼的“选边站”。问题是,今天的争论甚至激战究竟在多大的意义上立足于对历史事实的把握,论战双方又是否具有文化研讨所必需的思想认同平台?本文试图重返“五四”思想论争的现场,再现这些思想分歧和论争发生时的历史情景,剖析“五四”的思想分歧与今日人们的“选边站”是否出自同一种逻辑,思考“选边站”的我们是否与“五四”时期的思想论争处在同样的历史机制中。 围绕“五四”的文化激战之所以能够在今天持续展开,乃是因为“五四”一直是各种思想流派(乃至各种党派、政治力量)谈论中国现代文化的起点,对所谓“五四”的理解和认识更是学界分析、评价和判断中国现当代社会文化问题——包括成就和局限——的主要“根据”。左翼政治家已经得出“五四”运动是新民主主义开端的结论,而如蒋介石这样的专制独裁者则批评“自由主义”的“五四”背弃了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到了新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将思想文化“启蒙”的想象尽情交付给那个时代。当然,随即引入的西方汉学(尤其美国中国学)又提醒人们反思其“激进”与“偏激”……历年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纪念一点都没减少当下围绕它的种种争论。问题是:“五四”究竟是什么?它是怎样“构成”的?研究者在今天是否能够按照历史本身的理路来读解“五四”?“五四”当时的分歧与今日之评判是一回事吗?众说纷纭的“五四”还有哪些因素被我们忽视了?而这些因素是否可以为我们今天的历史认知与文化建设提供有益的启发? 在今天,质疑、批判“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理由至少包括以下七点:(一)少数知识分子的偏激导致了全民族文化的悲剧。(二)彻底反传统、割裂民族文化传统。(三)唯我独尊,充满了话语“霸权”。(四)引入线性历史发展观、激进主义的文化态度,导致现代中国一系列文化观念上的弊病甚至迷失。(五)客观上应和了西方的文化殖民策略。(六)开启现代专制主义,特别是“文革”思维的源头。(七)白话取代文言,破坏了中华民族的书写传统。以上可谓“五四”的“七宗罪”。然而,由论争中的激烈言辞所概括出来的“罪行”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历史真实?“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立场与思想内涵是否就由这些情绪性的言辞所体现?进一步说,我们今天反省和批判“五四”的根据是否充足?促使我们反省和批判的动力究竟是“五四”的偏激还是我们自身立场的需要?在我看来,恰恰在这些根本性问题上,呈现出了从历史知识到思维理路等多方面的缠绕和混沌。今天的研究者很容易假设:“五四”的历史早应成为稳定的“故纸堆”中的材料,只等待我们的重读和阐释。然而问题却远没有这样简单,分析近年来那些对“五四”的讨论,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多少让人有些惊讶的事实:一系列基本史实其实都还笼罩在迷雾中,学界的不少批评性判断竟然建立在许多虚幻不实的“传说”的基础上。我以为,以“传说”而不是事实为基础,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被任意涂抹的主要原因。 “五四”的历史或许本身就是迷离混沌的,而今人的立场竟又是如此的非黑即白、阵线分明。关于“五四”思想论争的历史叙述,总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新文化在“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发展,要么是如昨所述,新文化经过一番鏖战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要么就是如今的观点,新文化“摧毁”了“优秀的传统”①。无论是前者的胜利者姿态还是后者的痛心疾首,其实思维方式都是一致的:将“五四”的思想分歧认定为非此即彼的尖锐的“路线斗争”,只不过有时我们认同前者,有时又选择了相反的立场而已。于是,由“五四”思想争论所引发的历史评价问题首先就成了我们自己的“选边站”问题。在这样的叙述中,最重要的是我们究竟属于“哪一边”,是肯定“五四”的“反传统”,还是肯定被“五四”“反”过的传统,这里并不存在一种超越两“边”的新的思想方式的可能性。这样的“讲述”显然是以最大的省略、最大的一厢情愿来使用历史材料。 如此非此即彼的立场当然不是对历史的尊重而是对历史本身的切割。在20世纪下半叶,我们完全按照政治斗争、阶级斗争的模式来解释一切文化发展与文学活动,严格按照“政治正确”的标准来选择和剔除历史事实。在权威的文学史著作中,我们读到的往往是如下判断: 从“五四”文学革命开始,作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条重要战线,现代文学就是随着时代的前进和革命的深入而得到发展的……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区分敌我,是对革命的对象和动力采取截然不同的立场和态度。② 文艺斗争是从属于政治斗争的。政治的分野决定着文艺的分野……“五四”新文学在思想上不但和封建文学形成尖锐的对立,同时也远远高出于封建时代具有民主倾向的文学以及近代一般的资产阶级文学。③ 20世纪90年代以降,随着“国学”逐渐升温,“复兴传统文化”之声日渐高涨,上述“斗争”模式被倒置过来。这一回,代表“政治正确”的又成了“传统文化”,而受到抨击的则是“五四”新文化。虽然结论不同,但非此即彼的斗争方式却没有改变,历史本身的复杂性同样没有得到必要的尊重。 实际上,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五四”思想论争的频繁与激烈在那个时代并没有造成中国知识界的撕裂,论争的双方——无论是激进的陈独秀、胡适,还是保守的学衡派、甲寅派——都继续在各自的领域里参与现代文化的建设,“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创的现代文化为观念不同的思想派别所“共享”,这是二元对立式的阶级斗争思维难以想象的。不仅如此,虽然“五四”新文化健将有不少激烈的反传统主张,但他们的文学实践与文化实践却坚实而理性。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人们时常提到五四新文学运动发难者对传统文化的激烈的甚至偏激的态度……然而,在发难者启导下站到新文学营垒里来的年轻的五四文学作者们,却并没有以那样强硬的、决绝的态度去批判传统文化……近些年来研究者很注意探讨五四新文学与传统的‘断裂’。应该说,与年轻一些的创作者相比,发难者们与传统文化的精神联系更为紧密。然而,‘断裂’的愿望却更多地表现在发难者的宣言里,而在年轻的创作者们的创作追求中,我们既能够看到告别传统的努力,却也容易感受到现代意识与古代意识的糅合。”④ 我认为,今天对“五四”思想论争的解读应该注意现代知识分子群体在那个特殊历史时期的生存状态,他们各自的姿态及相互之间的联系。在那些关于“五四”的种种简明的定性之外,只有努力还原当时的历史情境,理解和体会“你死我活”的斗争之外的生存法则,才有可能触摸到“五四”的脉搏。还原“五四”的历史,最需要我们理解的就是当时能够造就文化丰富性与多样性的历史机制是什么,它究竟是如何运行的。 要理解这个历史机制,最重要的就是将它置于特定的历史时空之中,而不是根据我们后来的思维方式,用我们今天的生存经验与文化逻辑来解释先前的历史。不同历史时空具有不同的经验和生存方式,后来的逻辑在很大的程度上会改变和扭曲那些基本的历史事实。 回到“五四”的历史,这个值得我们注意的历史机制就是我常说的“民国机制”。对此,可能有学者不无疑惑:民国,包括北洋军阀统治下的“五四”时期,各种现代法律、规则都不健全,是否存在一种统一的机制呢?其实,所谓机制既指政治、经济、法律等国家制度,也指社会发展(包括社会生活)过程中形成的对行为方式的规约,后者不一定属于某种强制性的制度规定,但是作为文化心态的自然表现却依然对一个时代产生着重要的作用。在王纲解纽、法纪松弛的“乱世”,在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圈内,首先应该重视的就是社会文化的氛围与知识者的行为准则。当然,由此进一步追问,我们会发现可能就是“乱世”中国家制度的松散性,参与了某种文化氛围的营造,这就是特定历史机制的意义。 对于“五四”思想论争的认识,我觉得历史机制有以下几种特征值得注意,它们都来源于传统的帝国控制形式的松动或者改变,为适应新兴的社会生活而逐步形成。 (一)作为论争承载者的报刊具有民间性质。介入“五四”思想论争的杂志或是以民营资本兴办,如《东方杂志》、《晨报副刊》、《京报副刊》、《中华新报》、《小说月报》、《新申报》等;或是部分由民营资本支持的同人杂志,如《学衡》(获得中华书局的支持);或是先由民营资本支持后转为同人杂志,如群益书社一度支持的《新青年》;或是单纯的同人刊物,如《新潮》、《少年中国》、《每周评论》、《国故》等;或主办人虽具有官方身份,但刊物本身并无官方名目,如《甲寅》周刊。总之,民间性质是这些刊物的共同特点。 众所周知,中国近现代意义上的出版业始于传教士,后来又出现洋务运动时期的官办出版,但进入20世纪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出版印刷技术的改进、国家的教育文化政策以及社会文化氛围的更新都有利于私营性质的出版传播机构的壮大。清末新政,民营经济始受鼓励,数量和投资额度都成倍增长,辛亥革命进一步打破了传统的经济环境,《临时约法》中明文规定“人民有财产及营业之自由”⑤,北洋政府的经济政策也基本上沿袭孙中山的构想。以“照相石印”为代表的新式出版技术在私人书局中获得运用,近代民营出版业迅速崛起。从晚清到20世纪20、30年代,在政府主导的四次重大学制改革中,民营出版社都积极介入,通过各种教科书的编订出版为自己赚取未来发展的“第一桶金”,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这几大出版重镇都借助于近现代教育的出现而实现了快速发展。新的教育文化的发展又反过来造就大批读者,甚至介入出版业,促进出版观念和文化理想的更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和各种新式出版传播机构实现良性互动,新文化生长传播的过程也就是现代出版传媒发展更新的过程。因此,孙中山当时就表示:“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推原其始,不过由于出版界之一二觉悟者从事提倡,遂至舆论放大异彩,学潮弥漫全国,人皆激发天良,誓死为爱国之运动。”⑥ 由现代市场经济催生的民营出版机构提供了言论自由的公共空间,开创了从政治到思想的多元格局,这在本质上与帝制时代的官方《邸报》大相径庭。刊发于这些民间期刊的思想论争再激烈,在本质上都不过是民间思想者的“一家之言”,不可能形成对不同意见者的实际威胁,因而对公共舆论空间的整体稳定和发展并无负面影响。知识分子个人的思想主张当然可以借助民间期刊自由抒发,但期刊本身却无权压制不同意见。这些民间期刊背后的民营资本也往往不是思想意见的直接参与者,更不是最后的裁判员。市场与读者是他们的衣食父母,即使经营者的个人趣味有悖于市场与读者,也只能顺应主流趋势,最终扩大了现代文化的发展空间。典型的例子是商务印书馆,它创办的《东方杂志》以保守的立场与《新青年》发生“东西方文化论战”,让它失去了“激进”的新文化知识分子的支持。作为商务印书馆的经营者,张元济等人虽不认同“激进”思想,但面对杂志销路减少的现状,也不能不高度重视新文化知识分子的巨大影响力。因此,他们加强与新潮人物的沟通与协调,向陈独秀、胡适伸出合作之手。不过,他们也依然保留了其他的思想文化倾向——那里也存在着另一种市场和读者。对于这些民间资本的经营者而言,多种文化倾向的存在就意味着多种市场的占有,这是必须接受的原则。对此,王中忱曾经有过生动的描述: 这种经营者的角色意识,决定他们在调整出版方针的时候,既考虑努力适应新兴的文化思潮,又始终注意和新思潮保持距离。这在他们处理该馆编辑出版的杂志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商务的领导人调整杂志主编人选,当然是希望藉此吸纳新资源,开拓新市场,但同时又不希望丢掉旧有的读者。因此,改革《东方杂志》,他们只是撤换了成为《新青年》批判目标的主编杜亚泉,阻止该刊与《新青年》的论战,此外内容并无太多刷新。至于《小说月报》,虽然交给年轻编辑沈雁冰联合文学研究会的新文学作家去改革,但后来很快又专门出版《小说世界》,给那些被冷落的旧派小说家(所谓鸳鸯蝴蝶派、礼拜六派)留一块园地。努力把多方面的资源吸纳到自己的经营轨道,这是商务领导人一以贯之的思路。⑦ 民间资本的“经营者的角色意识”在客观上支撑着思想文化的多元格局,而且,这种“角色意识”还超越了一般的文化商人,成为“五四”时期的普遍生存法则:在锋芒毕露的个性化言论之外,还存在更大的公共舆论空间,它的相对稳定是彼此沟通对话的基础。1925年,北洋政府的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章士钊复刊《甲寅》,这份刊物曾因批判新文化运动被研究者称为反动的保守势力,然而《甲寅》却不能标榜自己是教育部或司法部的“部刊”,代表居高临下的国家意志,它只能是甲寅周刊社的普通出版物,与《新青年》、《新潮》、《学衡》等同人刊物并无二致。 (二)论争各方相对单纯的知识分子身份。在历史发展的“代际”交替中,“五四”是一个承上启下的特殊时刻。往前,距晚清的维新变法也就是二三十年,那些推动中国现代变革的人虽年届老境,但依然有着极佳的思考能力,如康有为、梁启超等;距离清末的排满革命二十来年,一批资深的革命人士或已经转入学界,或继续辗转于政界,但也自诩对中国问题颇多关怀和见识,如蔡元培、章士钊、刘师培、黄侃等;20世纪初留学西洋的大批精英已经归来或即将归来,他们有着令人羡慕的社会地位,不轻易苟同他人的思想观点,如辜鸿铭、学衡派同人等;也有还在国外求学、于国内生存无甚根基因而对未来发展充满期待却不无焦虑的年轻一代,如郭沫若和创造社同人;有国内高等学府的在读学生,深受激进师长的教育和鼓励,迫切希望加入时代潮流的青年,如傅斯年、罗家伦等;当然,更有历经种种求学和社会经验,对中国现实感受深切而试图有所作为的人,如陈独秀、胡适、李大钊、周氏兄弟等。“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一个牵动了各方关注的社会文化事件,发表不同意见的人囊括了社会各方面的代表。“学历”上的前清进士、举人、秀才,留洋博士、在读大学生;职业上的作家、翻译家、学者、大学教授、中学教师、出版人、政府高官;专业上既有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又有自然科学家,大家纷纷汇入,一时间众声喧哗。但是,无论这些介入者有着怎样复杂的身份,他们都是以学者或教师作为自己社会交往的基础。蔡元培既是前清进士,又是留学多国的现代学人,更身居要职,但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推动者,他既没有仰仗前朝精英的资历,也没有炫耀当下的权柄,成就与官位并没有成为他压制不同意见的理由。新文化运动遭到质疑时,他只能以学者的身份勉力解释,以理服人。梁启超是近代政坛的风云人物,一度担任北洋政府要职,但能够与其论战者并不会顾忌这位资深政治家的“官威”,而梁启超本人也更愿意以学者、导师的姿态出现在思想界。曾经的革命者,如刘师培、黄侃,包括对“五四”作“壁上观”的章太炎,无论观点如何,他们倨傲的并不是“革命前辈”的资历,而是对自身“学问”的自信。有趣的是,某些与时代潮流不甚合拍的人往往以性格举止的独异甚至怪诞而闻名,独异和怪诞都说明他们其实生活在世俗的礼仪秩序之外,时常沉浸在个人精神的世界之中;长期活跃于出版业的杜亚泉也没有“媒介批评”的讨巧和功利,所讨论的问题都是其学术思考的一部分;章士钊在当时的政治身份和政治态度颇为敏感,也招致很多批评,但仅就他对“五四”新文化的批评而言,似乎与他的官方身份关系不大。正如朱寿桐所指出的:“甲寅派虽然有掌握大权的章士钊挂帅,但它确实没有运用权力贯彻自己的保守主义文化策略,正相反,它倒是自处于时代潮流的边缘,以一种抗争的姿态向新文化和新文学提出了自己的制衡要求。章士钊虽然手握大权,但在那个比较开放的时代,依然遭到胡适、吴稚晖、高一涵、成仿吾的猛烈批判,其中包括相当辛辣的嬉笑怒骂,甚至还有身为其下属的鲁迅的冷嘲热讽。这些人如此放肆地批判和冒犯‘老章’,与章士钊并未滥用自己的权力进行文化论争有关。”⑧ 这种对知识的看重甚至敬畏与科举结束后中国读书人逐渐形成的新的精神传统有关,但也得力于民国教育制度与教育文化所形成的新的文化氛围。作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蔡元培从根本上抛弃了帝制时代的教育原则,认为“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教育家得立于人民之地位以定标准,乃得有超轶政治之教育”⑨。他主持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临时会议,后来又着力对北京大学进行现代改造,其基本思路是将大学从官僚养成所转变为独立的“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⑩。这些努力可以说造就了一个时代,促进了与帝制时代不同的新的历史机制的形成,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知识人的自我定位与自我目标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言辞激烈的论争与论争参与者生活的安稳并行不悖。“超轶政治”是蔡元培教育独立的重要目标,这一目标不仅让敬畏知识成为多个社会阶层的共识,更避免了国家权力对知识人生存基础的威胁。在帝制时代的中国,政权对人的控制已经渗透到生存的各个方面,学术和思想不再具有独立价值,学术的分歧、思想的差异直接与根本性的国家政治问题捆绑在一起,成为政治态度的重要表现。只有蔡元培理想中的“超轶政治”的实现,才会带来真正与生存威胁无关的纯粹的学术争论与思想探讨。在“五四”思想论争时期,因为军阀混战,中央政府的权威相对弱小,“超轶政治”的愿望在客观上有了部分落实的可能。因此,所有的思想交锋都止于语言和舆论场域的内部,几乎没有对参与双方的现实生活构成太深的负面影响。这些学者、教授、作家的就职单位并没有因为他们各自的思想倾向与言论方式而采取惩罚性措施。蔡元培是北京大学新文化运动的策动者,但他亲自聘用了许多反对这一思潮的人;新文化派与以杜亚泉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论战,但杜亚泉本人却是蔡元培的至交好友;因为新文化派影响日盛,为了适应形势,商务印书馆高层撤了杜亚泉的《东方杂志》主编之职,但并不影响他担任理化部主任,为出版事业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反对新文化运动的章士钊在1927年为营救李大钊而奔走,在1933年为狱中的陈独秀激情辩护,李、陈二人恰恰是章士钊不能认同的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在这里,学术与政治被清晰地切割开来。 凡此种种,在一定的程度上将论争限制在了特定的范围——不是作为国家政治的一部分,也不是官方态度的晴雨表,甚至也不会对参与者个人生存形成威胁。这样的限制在相当的程度上避免了文化论争、思想分歧对个人生活与国家政治的直接冲击。于是,文化论争归根结底就是知识圈内部的思想讨论,它对于国家政治的影响不是颠覆性的而是浸润性的,不是强制性的而是说服性的,不是独占式的而是参与式的。而且,由于并不涉及论争者本人的现实生存,私人空间承受挤压的程度有限,“公义”的讨论不会全部转化为私人恩怨,知识分子圈不是在论争中撕裂而是彼此共生,甚至在思想上相互影响。 前述三种历史机制的特征都主要与各种社会制度或社会环境有关,但也源于人们的思想状况。就如同韦伯、齐美尔以及马克思对社会的观察和分析都注意到其中“冲突”的不可避免一样,对思想文化史的描述也理所当然地包括对那些从未停止过的思想分歧与思想论争的描述。思想的历史之所以能够不断贡献出有价值的成果,就在于这些分歧和论争不是让人类社会变得四分五裂而是促进彼此的思想分享,在不断的交流、沟通与砥砺中声张各自的发现。而差异性的思想表达不仅释放了各自的焦虑,还形成一个富有弹性的思想场域,并最终营造了思想界在整体上的共生关系。与20世纪下半叶所追求的思想高度统一不同,各种各样的战乱、矛盾造就了“破碎”的民国。从民国初年开始,其内部的思想分歧就从来没有统一过,但问题却在于,就是这样破碎不堪的时代却一度形成了思想界的繁荣。从“五四”到抗战,民国时代的思想文化在分歧、论争中发展,成为现代中国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产,从历史机制的弹性空间而不是阶级斗争的生死搏杀中来理解问题,是我们正确解读“五四”思想分歧的关键。 “五四”知识分子显而易见的思想分歧来自他们对当时社会的不同体验,沿着各自的现实体验,他们提出了不同的文化发展意见。胡适、陈独秀等《新青年》同人对清末民初的生存现实有着痛彻的经验,也有着留学域外的新异感受,更多断指求生般的决绝,愿意将他国的文化当作自我参照的基础,谋求中国文化的新生。痛彻的经验强化了他们面对现实的忧患与愤懑,清醒的问题意识造就了他们言辞的犀利和尖锐。他们的锐利批判从根本上打破了沉闷的文化生态,推动了历史的有效行进。不过,这些相对激进的知识分子也存在姿态与感受的差异,因而具体的文化观念也并不相同,不仅有具体问题的认知差异,也有中心与边缘之别。例如,胡适居于新兴学院派文化的高地,陈独秀把握了引领风骚的现代媒体,学院与传媒都属于新兴文化的中心,他们满怀着开创新文化的豪迈与自信。作为这些前辈的弟子,《新潮》同人更多一份年轻人的激情与梦想。游走于官僚体制、现代传媒与学院交界地带的鲁迅则一直自居边缘,对新文化的主张既理解、同情、支持又保持适当的距离,甚至早早就将关于“铁屋子”的疑问沉重地放置在世人的面前。 就“五四”文学革命而言,也有首开风气的《新青年》同人与迟到归国的创造社同人的区隔。郭沫若在回顾文学革命时,刻意表达了对前期“五四”新文学成果的质疑,同时提出文学革命“第二个阶段”(11)的设想。所谓的“第二个阶段”,不仅意味着超越那些文学成就贫乏的前辈,更意味着另辟蹊径,重新论述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例如,在郭沫若那里,狂飙突进的气质与他对上古文化传统的赞美共存。胡适虽有“中国文艺复兴之父”的美誉,但其“复兴”主要还是指外来文化对中国文化的“激发”,郭沫若才可谓是文化传统“复兴”的最诚挚的阐述者。他不仅执著地探索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而且这种探索更直达了古代文化的最前端——三代以前,与许多新文化倡导者判然有别。 保守的知识分子群体在相对稳定的人生际遇下,对现实的灾难性感受不及新文化派那么强烈,希望通过平和的方式推进现代文化的建设,一方面引进西方的优秀文化资源,另一方面继续承继中国的传统文化。学衡派、东方文化派长于对中外文化的知识性论述,弱于对当时中国切肤之痛的深入体察。当然,所谓的保守也只是相对于新文化派那样的峻急态度而言,不同的知识分子所要“保守”的内容与方式也并不相同,很难被简洁明了地概括为二元对立。以现代中西教育为基础的学衡派、东方文化派和传统教育加域外游学的梁启超、章太炎自有差别,胸怀现实政治梦想的梁启超也与作为学者的章太炎大相径庭。 知识结构有异,人生体验有别,角色身份不同,“五四”汇集了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思想的冲突、观念的论辩在所难免,或者说,正因为有了论争,才能让他们各自体验的差异性、思想考量的独特性完整地呈现出来。无论当时论争双方在多大的程度上批判对方的立场和思想,它们都已经构成了“五四”文化的组成部分,并对中国未来的现代化格局产生各种形式的影响。那么,就思想本身来说,这种冲突中的容忍与结合究竟是如何实现的? 我曾经提出,“五四”知识分子并不是过去的文学史描述的那样,只包括《新青年》同人,前述种种思想倾向的人都可以被称作“五四知识分子”。“五四”其实存在着更大的认知共容圈(12)。在这个文化圈的内部,存在着一定的思想认同基础,也维系着某种社会关系的底线。一句话,彼此有着基本的共识。 其共识之一是对外来文化的基本接纳的态度。在当时,无论具体的主张如何,大概都不会反对引进外来文化的优秀资源,这是他们能够在某种国际视野中保持沟通和对话的前提。 其共识之二是对发展现代文化这一基本方向的共识。无论他们具体的知识结构与现实判断有多大的差异,几乎都赞同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方向,没有人试图通过论争返回帝制时代。即便是所谓“保守”派,他们也都是作为现代知识分子关注着民族文化的现代命运,都在现代世界的背景上思考中国问题。这就从根本意义上将他们与前朝旧臣、乡村遗老区别开来,其观点的差异并不妨碍他们一同站在“五四”历史的起跑线上,绘制现代文化的斑斓色彩。 从某种意义上讲,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原则致力于教育部与北京大学管理的蔡元培就是“五四”文化能够如此粘合的象征性符号,他作为一个时代的思想代表也是“五四”时代的历史机制能够良性运行的助推器。蔡元培本人没有轻易成为哪一种时代思潮的服膺者,而是尽力保持包容的文化姿态,成为中外古今各种思想资源的迎纳人与守护人。蔡元培不仅从制度设计、人事管理、社会交往等实际活动中兼顾新旧、并容中西,更将这样的理念上升为一种深远的文化思想和学术观念,这就是自由、中和与择善而从:“中国民族,富有中和性……中和的意义,是‘执其两端,用其中’。就是不走任何一极端,而选取两端的长处,使互相调和。”(13) 这里所谓的“调和”不是无原则的“和稀泥”,不是通过回避矛盾来达成表面的“和谐”,在一些重大的原则问题上,蔡元培固守着自己的立场。他认定思想自由、学术自由的对立面并不是哪一种貌似偏激的理论本身,而是国家体制的压迫和封杀,专制才是思想自由、文化发展的大敌,这就是他所说的“中国素无思想自由之习惯”(14),“李斯之制,焚诗书百家语,欲习法令者,以吏为师。是个人职业教育之自由犹被限制也”(15)。将思想学术的发展从权力的控制中解放出来,在与国家权力对抗中坚守立场才是推动现代文化发展的主要方向和根本目标。这种有原则的思想宽容,是蔡元培洞悉历史大势后的坚毅选择,它真正推动着现代思想文化的发展,尽可能凝聚起现代知识分子群体的共识,为不同思想的自由生长创造基本的生存环境。蔡元培以自己的力量搭建并推行着“五四”时期作为思想氛围的良性的历史机制,体现了民国时代的中国如何在社会层面而不是国家层面酝酿新的历史动力的可能。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时代,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在现实中分离了。“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一定的社会制度、一定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16)。从一般的社会制度到特定时代形成的思想场域,这种新机制的酝酿和运行都是现代历史的产物。在传统的君主专制时期,国家的运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王权的各种严密的制度设计,以及国家层面的制度执行。为了保证君主专制,国家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必然以压制和削弱各种民间力量为前提,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巩固臣民对于王权的依附,将社会生活中一切离心力消灭在萌芽状态。相反,在摧毁君主专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现代国家则以限制政府权力、扩大民间社会自身的机能为目标,试图建立起平等自由、充满社会自治机能的文明。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文明的机制从根本上区别于传统帝制文明的机制,它不再仅仅是国家的制度运行,而是充分发展社会本身的各种规约与原则,并酝酿形成了人的思想在差异中生长(而不再径直上升为生死对抗)的可能。以宪政民主、自由平等为目标的民国虽然在国家层面的制度上千疮百孔,离人们理想中的“新中国”相去甚远,却显然已经与任何一个君主专制国家有着根本的区别,新的历史机制已经开始运行。 对“五四”思想以及论争的深入理解,必当自充分认识这一历史机制开始。同样,对于“五四”的误读和扭曲,也往往源于我们对这一历史机制的忽视和遗忘。在“五四”思想论争早已远去的当代,我们在面对“五四”时过于匆忙地“选边站”,以二元对立式的思维方式想象历史,一会儿是彻底的反封建,一会儿是幡然悔悟式的回归传统,殊不知这些都不是完整的“五四”。“五四”的价值孕育于现代文化已经逐步成型的时代,在那时,历史的合力已经形成了不可改变的机制,它们共同推动着思想分歧的各方献身于新文明的建设,共同营造着现代中国的精神大厦。 ①此说自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一书在中国出版(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后开始流行,更随20世纪90年代“后学”与新儒家的兴起而影响日盛。 ②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5页。 ③唐弢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第1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5—55页。 ④刘纳:《嬗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08—310页。 ⑤“中华民国”参议院编《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商务印书馆1916年版,第2页。 ⑥孙中山:《民国九年与海外国民党同志书》,胡汉民编《总理全集》第3卷,上海民智书局1930年版,第34页。 ⑦王中忱:《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商务印书馆》,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年第3期。 ⑧朱寿桐:《中国现代社团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4—105页。 ⑨蔡元培:《对于新教育之意见》,《蔡元培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36页。 ⑩蔡元培:《北大一九一八年开学式演说词》,《蔡元培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91页。 (11)郭沫若:《文学革命之回顾》,《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98页。 (12)李怡:《“五四”与现代文学“民国机制”的形成》,载《郑州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 (13)蔡元培:《三民主义的中和性》,《蔡元培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82页。 (14)蔡元培:《传略》上,《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332页。 (15)蔡元培:《教育之对待的发展》,《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260页。 (16)马克思:《致巴维尔·瓦西里也维奇·安年柯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7页。标签:新文化运动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政治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知识分子论文; 蔡元培论文; 东方杂志论文; 章士钊论文; 新潮论文; 新青年论文; 新文化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