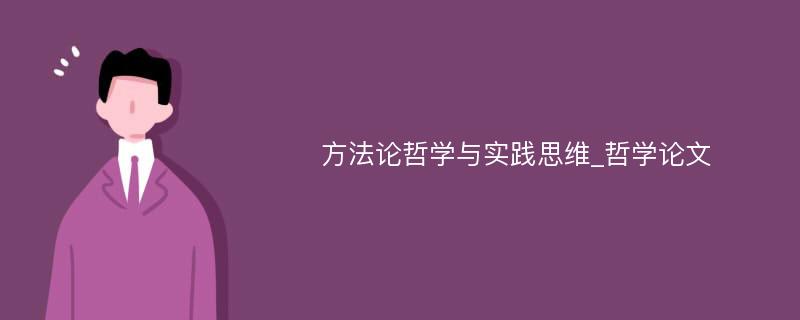
方法论哲学与实践思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思维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代哲学为什么是以方法论为主要形态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什么给人们提供的是“从实践观点出发的思维方式”即“实践思维”,这是本文要着重探讨的问题。
一
当代哲学之所以以方法论为主要形态,这首先是由哲学自身发展的状况造成的。在与宗教神话对立意义上萌发形成的古代哲学,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是以“知识总汇”的面目出现的。当时产生的各个学科、各类知识,只要是借助于观察和思考形成的,都属于“智慧”即哲学的范围。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研究自然现象的光学、声学、物学,还是研究社会现象的政治学、伦理学、法学,还是研究思维现象的逻辑学、修辞学,研究生理现象的医学等都在与藉幻想和猜测形成的、与神话对立的意义上届于哲学,各门具体科学研究范围的总和也就是哲学的研究范围,各门科学总和达到的知识水平也就是哲学达到的水平,二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因此,从理论性质上看哲学和部门科学之间不存在什么根本的区别,盖属于实证科学之列。
但是,在进一步的发展中,部门科学已不再满足于有些情况下因观察手段的不足而不得不借助于哲学思辨以弥补自身的状况。先是数学、自然科学,再是社会科学各部门逐渐由低级到高级、由粗略到精细日臻成熟,从哲学这一“母体”科学中纷纷独立出来,使得作为“知识总汇”的哲学日趋解体。但此时的哲学虽然不再是包罗万象的诸多科学之母,却依然是君临一切部门科学之上的“科学之王”。原因在于它的抽象层次最高,普遍性最广。可是好景不长,“科学之王”的宝座也摇摇欲坠,众多实证科学的长足发展不仅不再臣服于哲学,而且大有取而代之或“反叛”之意。康德在谈及这一点时曾形象地描述道:“有一个时期形而上学曾经号称一切科学的女王。如果我们拿愿望当作事实的话,形而上学的研究对象既然特别重要,这个光荣称号它也确实当之无愧。但是,时代变了,风尚变了,现在对它只有无情的轻蔑,这位年迈的贵夫人备受谴责,惨遭遗弃,只得象海姑巴一样自怨自艾地叹道:‘不久前,还是强中之强,有那么多儿女媳婿,威重四方——如今啊,被逐出乡邦,孤零零好不凄凉’。”[1] (P238)文中的形而上学即哲学,为什么它能由“科学之母”转而成为“科学女王”,原因在于“它是统究万类的普遍性学术”,而部门科学则是“各研究某些特殊事物”[2] (P120)。这表明正是由于作为“智慧”总和的哲学转而成为“最高智慧”的哲学,研究对象发生了变化,其理论性质也就随之发生了变化。即使如此,仍然不能适应学科分化的要求,这就发生了康德所说的,即使作为“科学女王”的地位也岌岌可危、朝不保夕,受到日渐增多的实证科学部门的蔑视了。从科学发展角度来看,这无疑是一种进步的表现,它说明人们不再满足于笼统、空泛、粗略地认识周围世界,而是要求精深、准确地认识世界了。具体科学部门之所以能迅速发展,原因正是为了满足人们实践日渐拓展、深化的要求。恩格斯在谈到这一点时曾明确指出:“现在无论在哪一方面,都不再是要从头脑中想出联系,而是要从事实中发现这种联系了。这样,对于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来说,要是还留下什么的话,那就只留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3] (P48)
为什么哲学越来越受到“轻蔑”,甚或“惨遭遗弃”呢?这是因为如果说作为“知识总汇”的哲学能够在科学没有分化之前,在与神话幻想对立的意义上为人们提供一幅比较合于理性、合于人们直观经验的“关于世界的总图景”的话,作为“科学女王”的哲学能够在科学虽已分化,但分化尚不充分,尚不深入之前常常借助思辨和猜测以弥补具体科学由于分散、孤立观察之不足因而具有一定价值和理由的话,那么,经过中世纪,特别是15—17世纪的长足发展,各种科学部门逐渐成熟,哲学再越俎代庖地企求解决实证科学所要解决的问题显然是力不从心、捉襟见肘了。此时此地,它所力求解决的每一个实证性问题都不可能像部门科学解决得那么完美和精确。因为后者是直接建立在观察和实验的基础上,并各具独特工具和手段,而前者除了跟在实证科学后面,借用实证科学的既有成果,并没有自己独特的、远远优于实证科学的观察、实验工具或手段。时过境迁,显然哲学此时再想作为“科学母亲”或“科学女王”实在是太不切合实际了。这也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由于自然科学的巨大进步,“我们现在不仅能够指出自然界中各个领域内的过程之间的联系,而且总的说来,也能指出各个领域之间的联系了,这样我们就能够依靠经验自然科学本身所提供的事实,以近乎系统的形式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联系的清晰图画。”描绘这样一幅总的图画在以前是所谓自然哲学的任务。而自然哲学只能这样来描绘:“用理想的、幻想的联系来代替尚未知道的现实的联系,用臆想来补充缺少的事实,用纯粹的想象来填补现实的空白。它在这样做的时候提出了一些天才的思想,预测到一些后来的发现,但是也说出了十分荒唐的见解,这在当时是不可能不这样的。今天,当人们对自然研究的结果只是辩证地即从它们自身的联系进行考察,就可以制成一个在我们这个时代是令人满意的‘自然体系’的时候,当这种联系的辩证性质,甚至迫使自然哲学家的受过形而上学训练的头脑违背他们的意志而不得不接受的时候,自然哲学就最终被清除了。任何使它复活的企图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一种退步。”[3] (P36—37)
古代哲学以总体世界为对象,目的是探求总体世界存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换言之,为人们提供关于世界的总图景,因而突出的是世界观侧面。尽管它为人们提供的这幅总图景是如此的粗糙,但由于它把当时萌发产生的所有学科统统包容在内,具有包罗万象的性质,因而在一定意义上,它是可以担当这个任务的。但是后来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既然各门实证科学纷纷脱离它而独立出来,再要求它像以往一样提供关于世界的总图景显然是不可能的了。揭示总体世界存在、发展的普遍规律的重任仅靠哲学已不能完成,总体世界的问题必须由包括哲学在内的所有科学部门的共同努力来解决。
面对这种情况,现实生活究竟给哲学提出的迫切问题是什么呢?在笔者看来,就是探讨为人的实践活动所分化了的主体如何、怎样才能正确地把握客体,在新的基础上达到主客体统一的问题。说得详细一点,各种部门科学像以往一样,直接面对的都是总体世界的某一部分或某一个侧面,所探求的都是对这个特定部分、特定侧面存在和发展的规律性认识。它们在各自的探索中都不可避免地有一些成功的经验要总结,有一些失败的教训要吸取。如何使已有的经验系统化、理论化,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现有各种具体科学部门中没有一门是执行此项任务的。而在当代科学体系的分化中,哲学恰恰应当担当起此项重任。提高一步来说,现实当中,无论是从事哪项研究的,认识、实践的执行者都是认识主体、实践主体,而被认识、实践的对象又都是客体。所谓经验和教训正是在主体把握客体的过程中产生的。当哲学把先前实践活动中产生的这些经验、教训系统化、理论化之后,自然会给后来的实践提供重要的指导作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代哲学既是近代哲学即以认识论为中心内容的哲学的延伸,又具有新时代的特点。而主要解决主体如何、怎样才能把握客体的问题,显然是方法论的问题。
二
这样说,是不是讲当代哲学仅具有方法论意义,而不具有世界观方面的意义了呢?不是。因为如上所述,各种实证科学虽然已从哲学母体中独立出来,且日益成熟,能够比原先涵盖于哲学之内更精深更准确地把握对象,但每门科学又毕竟对应的是世界的某一侧面。世界总体又不是各个侧面的简单相加即可构成的。总体世界存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又必须在具体实证科学分别探索特殊规律的基础上加以综合、分析、抽象、提高、升华的,这就少不了哲学,而且主要应由哲学来承担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哲学仍就具有世界观意义,只是和古代哲学相比,虽然同具世界观意义,但内涵又有区别罢了。但是无论如何,此种意义上的世界观内涵和此时哲学所具有的方法论内涵相比已不占主要地位了。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现实生活中的绝大多数人可以说都是以承认物质世界的先在性为前提的。换句话说,世界观方面的问题已不再如同古代哲学产生的时期那样是个必须经过热烈讨论才能解决的问题,而是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基本上已经解决了的问题。
再则,哲学虽然是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三者有机统一的学问,但从对人的实践活动所具有的意义、价值、功能来看,最直接的应首推方法论。世界观虽然关系到人籍以安身立命的终极关怀,认识论虽然给人的实践活动揭示了正确的认识原则,但从归根结底的意义上讲,最后都要落实到方法论上。因为人们对于周围事物不是为了认识而认识,不是为了理解而理解。认识、理解的目的全在于利用、改造周围事物,使其为人自身的利益服务,使主客体无论在观念形态上还是在实在形态上都达到完满统一。从这一点出发,弄清世界是什么样的和正确了解人的认识状况,最终都要转化为正确地指导人们进行新的实践的方法论原则。明白了这一点,也就比较容易回答学习、研究哲学究竟有没有用,究竟是大用还是小用的问题。
常常听到这样一种议论:舟车可以代步,稼穑使人足食,纺织于人着衣,物理学、化学分别可以揭示物理、化学现象发展变化的普遍规律,那么学习、研究哲学到底有什么用,即使有用,是大用还是小用呢?弄清以上所讲的道理,就可以毫不犹豫地回答:古代学习哲学能使人们对总体世界有一个远远高于神话传说的正确认识;近代学习哲学在使人们对总体世界有正确认识的同时,更使人们对于如何保证自己的认识符合世界本身的面目有了充分的、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信念;当代学习、研究哲学则不仅具有上述功能,特别突出的是给人们以如何正确地把握客体的方法论方面的指导。这样,不管你是从事什么工作的,都有一个如何面对研究对象、如何使对象客体为我所把握、所利用、以至于最后“转化为我的无机的身体”的问题。因此,它和研究某一部门科学或某一项专门技术相比,就其不能直接解决某一具体问题而论,似乎显得“无用”,但就其能够指导从事某项具体研究的人可以尽快达到预期目的、尽量少走弯路而又可能显得非常“有用”。而且,也正因为它不囿于某一个别领域的有用,才能普遍适应于每一个研究领域,因而才真正具有“大用”。这表明,哲学的“无用”和“有用”、“小用”和“大用”恰如对立的两极:互相否定的同时又互相规定,互相排斥的同时又互相依存。而且,哲学的“有用”又恰恰是通过解决具体问题的“无用”、哲学的“大用”是通过不局限于一时一地的“小用”而具体表现出来的,因而又互相渗透。更重要的是,因为它虽不能直接解决某种特殊问题而显得“无用”,但它却能解决普遍性的问题而显得“有用”;同理也正因为它所解决问题的范围不局限在某一特殊领域因而显得用处不大,但它却能解决所有领域中的同类问题,因而才有“大用”。这样说,颇有些类似于老子的“道”,“无为”而“无不为”。而哲学的这种“有用”、“大用”从现在的观点看来正是突出地表现在它所具有的方法论功能上。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优秀哲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它不仅帮助人们树立起实践唯物主义的世界观,遵循一条正确的实践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更重要的是给人们提供了严格、系统的实践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原则。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说唯物史观是“唯一的唯物主义的方法,因而也是唯一科学的方法。”恩格斯也曾多次明确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无疑是当代哲学的主流。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论述明确无误地阐明了当代哲学所应特别突出的是其方法论侧面。
三
哲学的方法论功能,集中表现在它主要是为人们提供思维方式的科学。哲学研究虽然曾经给人们提供过关于对象的事实性认识,但是只要回顾一下哲学发展的实际情形就不难发现,无论是古代、近代、还是当代,它所提供的有关对象的事实性认识,不管是广度、深度,还是精确性方面都没有、也不可能超过具体实证科学。如果说作为“知识总汇”的古代哲学关于世界总体的认识达到的水平和各门具体科学总和达到的水平大体相当的话,那么近代、现代则远远不及后者。“密纳法的猫头鹰”之所以“到黄昏才起飞”则是因为只有借助于实证科学的成果,它自己才能有所作为。然而哲学并未因此而消亡,一个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从哲学本性来看,它并不担负和具体科学同样性质的任务,即把握对象存在和发展的具体性、实证性规律,而是教给人们如何正确地进行思维。由此看来,哲学发展到今天,其理论性质成了主要是向人们提供思维方式的科学。
什么是思维方式,其基本内涵、结构如何,它是如何发生的,又是如何演进的?对于这些问题,学术界认识至今未能统一。在笔者看来,思维方式是人们认知、理解、把握、评价客体的程式和方法。既然是“程式”就不是没有相对稳定的、零散多变思维方法的随意组合。它由思维元素、致思趋向、运思途径、思维时空等方面有机结构而成,并具有历史性、层次性、多样性的特点。一方面,它是人类先前实践活动以观念形态在主体意识中内化、积淀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人们在新的实践活动中认知、把握对象的重要工具。事实表明,一旦思维方式发生某种转变,那么基于其它而形成的对客体的认识、理解、评价必然会随着发生变化。这不仅是逻辑上的分析,而且为思维方式嬗演的具体情形所佐证。
以方法论为主要形态的当代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具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呢?在笔者看来,那就是从实践观点出发的“实践思维”。这既是人类思维发展到今天的必然结果,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人类思维作出的重大贡献。简而言之,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成为哲学,正在于它具有一般哲学的共性。而它之所以被称为一种新哲学,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除了因为它是由马克思创立的以外,更主要的是因为它具有其他哲学所不具有的特殊性,在于它为人们提供的是一种具有崭新特质的思维方式,即从实践观点出发的整合辩证思维,或可简称为“实践思维”。这种思维方式既突破了以往思维方式的局限性,又吸收了已有思维方式的合理性,使人类思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