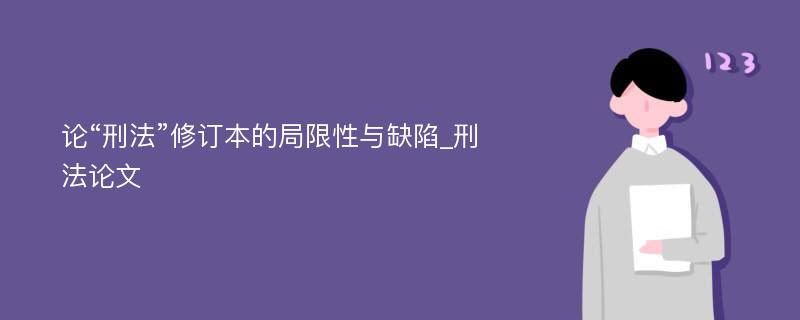
刑法典应力求垂范久远——论修订后的《刑法》的局限与缺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刑法典论文,刑法论文,久远论文,缺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第二部分之自首、正当防卫之论析,曾请黄祥青博土撰写初稿。其它个别地方亦曾与他进行讨论,有所启发;还曾获得他的资料帮助,在此谨致谢忱。但文章的观点及内容的全部问题,概由我负责。此外,郝铁川同志亦就拙作提出不少建议,在此一并致谢。
本文之旨,在于系统全面(但粗浅)地考察修订后刑法典的局限与缺陷。文章将分为上下两部:上部从宏观角度考察,下部从微观角度考察。文中所论,可能略嫌苛责,但我相信,这将有利于我国今后刑事立法的进一步科学完善。爱之切,故言之也苛。这就是我们讨论修订后刑法时的心境。
我认为,从宏观角度看,修订后刑法典的局限或缺陷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刑事立法指导思想上之缺陷
(一)“宜粗不宜细”导致“粗”、“细”两失
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类推制度的取消,追求具体而细当然是刑法不可避免的趋势。但“细”不等于繁琐杂乱,而是尽可能以科学完善的概念概括一切可能出现的犯罪。修订后刑法典共451条,长达七万言,当然不能算“粗略”、“简约”。刑法典的文字追求简洁或简约是应当的,但修订后刑法的许多条文不必要地重复,有些条文并无实际内容,仅象司法解释或关于操作技巧的提示。这当然是追求简洁的刑法典所不应有的。(这在后文将要论述)。这就是说,即使不从条文数量而仅从内容看,现刑法典也没有“粗”好。既然不“粗”,那么它“细”了没有呢?没有。从条文看,并没有真正增加多少。原刑法典共192条,原军职罪条例共26条,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发布的22个刑事补充规定或决定共计186条左右,还有其他散订于经济、行政等非刑事法律中的刑事条款数十条,合计早已超过451条之数。即使考虑到全国人大常委会22个刑事决定中的“条”常常内容庞大不可与刑法典之“条”相提并论,还考虑到许多单行刑事法规和非刑法中的刑事条款在法典编纂时因内容重叠而合并,我们还不能不看到,修订后刑法典条文并未增加多少。据估计,可能仅仅40条左右确实属于新内容的条文,这主要体现在危害公共卫生罪、扰乱市场秩序罪、股票证券及计算机犯罪、危害国防利益的犯罪等四大类罪名上,其余均是从前单行刑事法规范所已规定者。四大方面的犯罪,千头万绪,日新月异,仅仅共以40余条规定之,这当然不能算“细”。当然,条文多并不一定就是“细”,并不一定科学、完备、周密,关键是要能尽可能包罗一切可能出现的严重危害社会的恶行,具有相当的可操作性。
(二)“破坏市场经济秩序”何必辨姓“社”、姓“资”
修订后刑法典第三章标题比原刑法同一章标题多“市场”二字,但把“社会主义”四字与“市场”仍放在一起,使人生疑。小平先生曾言:“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此语昭示,立法者只应于此注意的是市场经济秩序,而不是姓“社”还是姓“资”。
(三)保护人身权放在什么位置
刑法分则关于侵害人身权之犯罪列于什么位置,反映出一国立法对人身权保护之重视程度。近代各国刑法大多列于国事罪、公共危险罪、渎职罪之后,置于第三或第四位。但现代各国刑法大多已经改变,将侵害人身权之罪列于分则首章,以显首重人身权保护之意。我国1979年刑法典将其置于第四章,修订后刑法典仍旧置于第四章,即置于“危害国家安全”、“危害公共安全”、“破坏经济秩序”三章之后,显然与上述国际趋势不洽。我国宪法将“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列于总纲以下首章,相应地,刑法典也应置“侵犯公民人身权”之犯罪于分则首章,以显示我国刑法在新时代的价值选择。
(四)过分强调“具体经验”和“实际情况”,相对牺牲了科学性、长远性追求。
修订后刑法典第1条即申明立法指导思想是:“结合我国同犯罪作斗争的具体经验及实际情况,制定本法。”任何国家立法都应从“具体经验”和“实际情况”出发,这样表述当然可以。问题是,如何认识或评价“具体经验”和“实际情况”,强调它们该到什么程度为妥。修订后刑法典的确体现了这一指导思想,但似乎强调太过,相对牺牲了科学性、长远性追求。这一问题可从多方面去看。
首先,对一特定现象,如认为现实生活中严重存在,不惜多头或多方面规定,不免重复。如关于拐卖妇女儿童,即有第240、241、242、416条多方规定,共达四条之多,文字繁琐。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因系单行法规,文字稍繁可以理解,但是一旦进入刑法典,与其他条文成为一个有机体系时,再将这些条文及文字如数搬列,就有些重复啰嗦了。比如在第240条、241条分别规定了拐卖者、收买者的罪刑以后,第242条关于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解救的规定就不必要,因为其既无独立罪名,又无独立适用刑罚,通过司法解释适用第277条妨害公务之规定便可以了。第416条关于国家工作人员渎职不解救的规定也不必要,通过司法解释适用第397条就够了。
其次,把许多办案经验、适用法律指南或司法解释性的东西塞入刑法典,列为正条,损害了刑法典应有的简洁、逻辑性,也使内容显得重复。这一方面最为典型的三种情形:一是许多条文仅属引伸性解释,没有刑罚规定。如第155条关于走私的外围行为(即准走私行为)视同走私罪处罚的解释;第242条关于阻碍解救被拐卖者这种特定的阻碍公务视同妨害公务罪处理的解释;第269条关于盗、骗、夺等犯人暴力拒捕视同抢劫罪处理的解释;第265条关于盗接通信线路复制电话号码等视同盗窃罪处理的解释。这类规定甚多,另如第156条、第247条、第289条、第388条、第394条等等。其实均可于相应走私、妨害公务、抢劫、盗窃等正条中以适当文字概括进去,或以司法解释处理,没有必要另立正条。二是纯粹定义性条款太多。如第382条关于贪污的定义,第357条关于毒品的定义,第367条关于淫秽物品的定义,第389条关于行贿的定义,第385条关于受贿的定义等等。这些规定并非不能有,但应置于各类罪名之一般情形处罚条款中,以免累赘。三是纯粹将某犯罪的一种情节单列条款。如第102条第2款关于与境外勾结犯背叛国家罪的规定,所指仅是前款背叛国家罪的一个最普通常见的情节,且无加重或从重处罚规定,显然没必要重复。又如第106条关于与境外勾结犯分裂国家、叛乱暴乱、颠覆国家等罪从重处罚之规定,也仅是一个常见情节,应于各正条中解决,或通过司法解释解决。再如第157条关于武装掩护走私、暴力抗拒缉私的规定,第247、248条关于司法人员刑讯逼供逼证或体罚致人伤亡的规定,均是“严重情节”或“特别严重情节”,单独规定条文且规定按别的条款之罪名刑等处罚,均显有不妥。如在原罪正条或准用罪名正条中解决不是更简洁吗?此外,有些条款纯系指示法官数罪并罚。如第241条第2、3、4、5款,均系关于收买妇女儿童者又同时犯强奸、拘禁、伤害、侮辱、出卖等罪行时数罪并罚的规定;第318条后款关于组织偷越国(边)境者同时犯杀害、伤害、强奸、拐卖等罪时的数罪并罚规定,等等。
第三,只考虑到现在严重存在的行为,不关心现已出现的但不严重或将要出现的行为,显然有“今天只管今天”之指导思想,不注重罪名概括面或周密性。如第147条仅仅列举假劣农药、兽药、种子、化肥,就不曾想到还有假劣农机具、塑料薄膜、蚕种及其他养殖物种植物(且不够第149条所定5万元之标准)种苗仔之情形,为何不于该条后加上“以及其他农用物资”一语概括一切可能情形呢?再加第382条、第385条第389条关于贪污、受贿、行贿三罪的规定,其犯罪赃物仅仅规定为“财物”,显然落后于时代。
第四,某些过去的“经验”或体验仍萦绕于刑法中,有过时感。比如第289条的聚众“打砸抢”,显然是原刑法中第137条的翻版。
综上四种情况可知,修订后刑法典在某种意义或程度上有过于重经验、重眼前现实的“短期行为”之弊。
二、刑事制度上之缺陷
(一)追诉时效制度几乎取消
原刑法第77条规定曾被公检法三机关之一采取强制措施(包括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逮捕、拘留)以后逃避侦查审判的不受追诉时效期限之限制。修订后刑法则不然,改为凡被公安、安全、检察、法院四机关立案或虽未立案但已被控告而应立案者,不再受追诉时效之限制。这样一来,实际上几乎取消了追诉时效制度。这显然违背了近代刑法追诉时效制度创设之初衷。由于国家司法权力的行使有着一些不可克服的客观限制,不可能如愿地及于一切犯罪。因此,对国家权力客观上不能及的犯罪而言,时效制度就是一种较好的替代办法——与其让逃亡罪犯在随时都有被抓获之危险且终身难免刑罚责任的威胁下“破罐了破摔”,不如定下一个免责期限让其有所期待而后畏法隐匿、夹紧尾巴做人,在一种“守法”的外表下度过一个相当长时期。只要畏法隐匿如此一个时期,国家司法权力虽尚未直接及于他,但刑法震慑犯罪的目的已部分达到。这就是设立追诉时效制度之初衷或本意。此外,追诉时效还有限制国家和受害人追诉权无限期使用之意,给权力(利)定下时效同时也是为了促使权力(利)尽早行使。若以修订后刑法典第87条的方式,实际上取消了追诉时效制度,其结果会促使在逃罪犯“一不做二不休”,会使得受害人及公安检察等机关没有行使权利(力)之紧迫感。
(二)自首制度不完善
第一,自首后重大立功者必减免刑罚之规定不妥。修订后刑法第75条作出刑责必减主义规定,主要注重的是鼓励自首、鼓励检举犯罪的功利目的,却可能违背罪刑相当及刑罚公正性原则。从罪刑相当原则出发,犯罪达到了相当严重程度时,就应处以相当严厉之刑。如各国刑法对谋杀罪一般均处死刑或终身监禁。对那些最严重的杀人和故意伤害(如一次谋杀多人或重伤多人)而言,由于刑罚的“有限性”与犯罪危害的“无限性”之间的天然矛盾,即使处以极刑,也仍不能与其犯罪严重程度相当。此时,犯罪人在犯罪后虽既自首又重大立功,但均不能将其危害降低,也不能将其罪责降到当处次极刑程度上。若于此时采必减主义,对最严重犯罪处次严厉之刑,甚至可以是处最轻之刑,无异于破坏了刑法的罪刑相当原则,无异于鼓励某些犯罪人:只要掌握了他人重大犯罪线索,作好自首准备,那么犯再严重的罪也不会受最严厉的处罚。以牺牲刑法公正价值的代价换取破案率提高,值吗?
第二,缺乏于受害人或有诉权人处首露也视为自首的规定。犯罪人在犯罪后于受害人或其他有诉权人处首露,坦承犯罪、退还赃物、赔偿损失之类,在各国刑法中均视为自首的一种形式,如《日本刑法典》和《韩国刑法典》均规定告诉才处理的犯罪,向被害人自白者,准用自首规定。[1]我国民国时代历次刑法典也有此规定。中国古代刑律在此方面规定更详。如《唐律》规定:“诸盗、诈取人财物而于财主(处)首露者,与经官司自首同。”[2]这种情形,只要犯罪人未与受害人订立“不告发”协议,即与自首效果一样。即使后来受害人告诉到法院,应视同自首,减免其刑责。当然,对自诉罪案而言,受害人接受这种自首而不告诉是合法的。司法实践中,我们也常将此种情形视为从轻或减免处罚情节,但毕竟不如定为法典中的经常制度,更有利于鼓励犯罪人主动承担责任,同时也提高了破案率。
(三)保安处分制度未能正式确立
“保安处分”概念,由于曾为法西斯刑法使用过,新中国刑法一直避免使用。用不用这一概念不要紧,问题是我们在刑法典中一定要建立一个完备的“次刑罚”或“辅刑罚”体系使之与刑罚互补配套。当今许多国家刑法典中均有“保安处分”专章或专节,将感化教育或训诫、监护、强制禁戒、强制工作、强制治疗、禁止在一定范围内居住,禁止进入特定场所,驱逐出境(对外国人)等等合为一个有机体系,以管教少年犯罪人、精神病犯罪人、酗酒犯罪人、有传染病之犯罪人、吸毒犯罪人等等。我国刑法虽不用“保安处分”概念,但实际上有保安处分,只是极不完善。如原刑法第14条即有对少年犯“收容教养”之规定;修订后刑法在“收容教养”之外,又增加了对精神病犯人“强制医疗。”此外,有责令家长及家属或监护人对少年犯和精神病犯人“加以管教”或“严加看管和医疗”的规定,但不是正式保安处分。[3]我们缺少一个类似于“保安处分”的制度概念来统率这些处分,且缺乏这一制度体系中一些应有的部分:如对精神病犯人的强制监护处分,对酗酒者的强制禁戒处分,对以犯罪为常业或懒惰成习的犯罪人强制工作处分,对某些犯罪人于一定范围内一定种类场所禁居禁入处分等等。实践中,虽或偶尔如此做(特别是强制戒毒),但毕竟不如上升为庄严的刑法制度更有利。这是刑法制度体系科学完善之任务的一部分,这一任务大概只有通过刑法中的专章节及一个附属的《保安处分实施条例》才能完成。
(四)“无限防卫权”制度隐然建立
修订后刑法典第27条规定:“对于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这一规定,实际上抵销了前款关于“防卫过当”的规定,创设了“无限防卫权”制度,损害了刑法的公正价值。
一般说来,正当防卫或防卫过当主要发生在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场合,这些场合,不外“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及其他类似暴力犯罪。除这些场合之外,理论上讲虽然还有些场合(如侵犯财产权、名誉权、婚姻中的权利等犯罪)也可有正当防卫,但实践中人们一般不这么看,司法上也不视为正当防卫。如将正在诽谤自己、偷自己的财物、与自己老婆通奸的人打伤,就几乎没有人朝正当防卫上去想。所以,一旦在严重伤害人身场合取消了“防卫过当”之限制,实际上就几乎赋予了人们“无限防卫权”。把“足以制止不法侵害为限度”之限制一取消,等于告诉所有防卫人:只要认为对方是严重危害自己或他人的人身安全,就可以毫无顾忌地反击,哪怕手段已经超过足以制止不法侵害的限度或犯罪人已无力再实施侵害,还可以继续“防卫”直至其“伤亡”。一旦如此,何等危险。这无疑是从另一个角度助长公民滥行暴力滥施私刑,助长私力报复。况且,即便是这五类危害人身安全的犯罪中,也有情节轻重之分。轻者甚至可能只应判处3、5年有期徒刑。若对这样的轻情节侵害人身犯罪也纵容无限防卫,纵容用剥夺生命的手段方式防卫,这岂是刑法公正价值所应容许的?刑法此条设计初衷是鼓励公民勇敢地同犯罪作斗争,但是也造成了一种新的危险。这种危险还应包括可能使不轨之徒易于歪曲利用无限防卫权以遂其杀人目的。这种危险,比起在“防卫过当”限制下可能会使一些公民在防卫时缩手缩脚纵容或鼓励犯罪的危险而言,真不知孰大孰小!
(五)“剥夺政治权利”对有关权利剥夺不当
修订后刑法典与原刑法典一样,坚持将宪法第35条规定的公民的最基本权利——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等6项列入可以剥夺的政治权利之中,显有不妥。宪法第二章规定公民基本权利主要有10项(从第34条到第43条),其中能依法剥夺或限制的权利都特别注明,即第34条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和第37条的人身自由权和第40条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权。此外一切权利,都未注明可以剥夺或限制,均应视为不可剥夺和限制的权利。也就是说,宪法第35条规定的六项权利,与第37条的信仰宗教自由权、第38条的人格尊严权、第39条的住宅权、第41条的批评建议控告权、第42条的劳动权、第43条的休息权一样,均不可剥夺。[1]
综观各国刑法典,其所列举的剥夺公权内容不外以下几项:(1)选举公职或被选为公职之权利;(2)担任非经选举产生国家公职之权利;(3)出任需要相当荣誉或信誉为条件之公共职务(如陪审员、证人、公证人、鉴定人、指定监护人和辅佐人)之权利;(4)拥有和获得国家荣誉名号(勋章、称号、奖章、军衔、荣衔、学位)及与此相关的利益之权利。也许,国外(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的立法者们早已共同认识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6权是基本的人权,不可剥夺。也许有人说,修订后刑法第54条第2项仅仅剥夺这六项“自由的权利”,与原刑法第50条第2项直称“宪法第45条(应为第35条)规定的各种权利”不一样,这也许表明经申请批准后,被剥夺政治权利人还可以部分行使这6项权利。这是误解,只有“自由”时才能叫“权利”,若“他由”,就谈不上权利。况且无罪公民行使此6权,特别是后5权,也要经批准。
(六)一些重要刑事制度仍付阙如
许多为各国刑法共有而为我国司法迫切需要的刑事制度仍被排除在修订后刑法典之外,令人遗憾。主要有以下三者:
1.剥夺民事权、亲权制度
各国刑法,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刑法,大多有剥夺民事权、亲权之制度。如《法国刑法典》有剥夺民事权与亲权规定,具体指剥夺民事代理权、出任子女以外的未成年人无行为能力人之监护人和财产管理人之权,和限制为子女监护人及财产管理人之权利。[2]法国、波兰、蒙古、罗马尼亚等国刑法还将剥夺民事权扩至禁止从事某种职业、职务或社会活动特别是禁止犯罪人从事或担任与犯罪有关或曾籍以犯罪的职业、职务或因犯罪人的恶名不宜担任的职务。罗马尼亚刑法还包括剥夺充当被信托人之权。意大利刑法除剥夺父权、夫权之外,还包括遗嘱权,他们总称为依法宣告禁治产(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西班牙刑法只剥夺对家之财产管理权与处置权。阿根廷刑法还包括丧失获得养老金和社会救济金之资格。[3]这些规定,对于那些滥用职务权、职业权、营业权、亲权、夫权、父权、代理权而犯罪的人来说,是应有的处罚方式,是十分必要的。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也经常发生被判刑人服刑期间所为民事行为的效力、处理家庭(夫妻)共有财产的效力、处理子女特有财产的效力等等一系列问题,但因为没有统一的关于剥夺民事权、亲权的法定制度,所以处理起来十分混乱。民法通则和民诉法虽然有认定公民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的规定,但未规定因犯罪而宣告禁治产或剥夺部分民事权、亲权之情形。[1]这种情形,是远远不适应司法之需要及保护人民权益之需要的。
2.刑罚易科制度
许多国家刑法还有刑罚易科制度。修订后刑法第53条规定:“对于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如果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缴纳确实有困难的,可以酌情减少或者免除。”实践中,如果没有不可抗力的灾祸,仅因为被罚金人不会生计长期贫困无力交纳,这罚金刑又如何执行?如减少或免除,岂不是说犯罪后贫困也是实现刑事责任的一种方式吗?所以,这种因窘只有通过刑罚易科制度才能够解决。
3.行刑时效制度
各国刑法均在设立追诉时效制度同时设有行刑时效制度,我国刑法不能容许行刑时效制度,大概与实际上取消追诉时效制度之心态有关。
三、多类多种犯罪未有规定
修订后刑法分则虽然规定了409个罪名,但仍有许多国外刑法共有的罪名并未规定。按罪名的性质来划分,我认为至少主要有以下四类犯罪[2]应当规定而未规定(其他缺乏者暂且不提)。
(一)关于严重违反社会公德和国民责任之犯罪。
我们常讲要以法制推动精神文明建设,这当然包括以刑法强化国民道德。但是,对许多严重违反国民责任和社会公德的行为,国外刑法早就定为犯罪加以处罚,我国刑法一直视而不见,听之任之。这类行为有四种,第一是见他人有危险、灾难不予救助或不报告当局,即是犯罪。如《德国刑法》第330条:“意外事故或公共危险或急难时,有救助之必要,依当时情况又有可能,尤其对自己并无显著危险且不违反其他重要义务,而不为求助者,处1年以下自由刑或并科罚金。”《奥地利刑法》第95条、《法国刑法典》第223-6条第2款、《意大利刑法》第593条等均有此类规定。[3]这种罪名只能叫“见危不救罪”(在我国仍仅被视为道德不好的行为),《法国刑法典》甚至以高达5年监禁并科30万法郎罚金处罚之。第二是阻止他人救助别人灾危,构成犯罪。如《法国刑法典》第223-5条规定:故意阻挠旨在使面临危险或灾难的人脱离危险的救援行动者,处7年监禁并科70万法郎罚金。[4]这类规定其他国家也有。第三是遗弃原无法定养护义务且无自救力之人,构成犯罪。如《法国刑法典》第223-3条规定:“抛弃因年龄或身体状况或精神状况而不能自我保护之人于任何场所的,处5年监禁并科50万法郎罚金”[5]《德国刑法典》221条第1款,《奥地利刑法》第82条等均有此意。特别是,将这种遗弃与父母监护人、监管人、教师等遗弃无自救力之人并列,说明其刑法已将本无法定义务抚养保护之但因特别危困情势而有道义义务救助的无自救力之人的遗弃定为犯罪。[6]第四是见犯罪不斗争、不报告也构成犯罪。《法国刑法典》第223-6条第1款规定:“任何人能立即采取行动阻止侵犯他人人身之重罪或轻罪发生,这样做对其本人或第三人并无危险,而故意放弃采取此种行动的,处5年监禁并科50万法郎罚金。[7]《德国刑法》第138条有“怠于告发犯罪”,《奥地利刑法》第286条有“怠于阻止犯罪行为罪”,《意大利刑法》第364条、第366条有“国民怠忽告发犯罪罪”和“国民拒绝协助正在缉捕罪犯之司法官员罪”都有类似的规定。还有国家(如波兰、希腊)甚至以明知他人有无罪证据而不报告司法当局坐视他人冤狱者也构成犯罪。上述五类恶行,在我国并不少见,报刊上也经常有人讨论应否将其定为犯罪,讨论了多年也没有结果。在通常被认为精神文明最不好的资本主义国家却早已规定进了刑法。当然,也许是因为人家精神文明太差才需要强制,但我们没有刑法强化精神文明也肯定不行。修订后刑法典产生于高扬精神文明大旗之际,不将这些国际通行规定纳入以督促国人走向文明,是大不应该的。
(二)关于严重的“国际犯罪”
对于许多人神共愤、全球共诛的国际犯罪修订后刑法典未设单章、单节或专条,未有加重处罚之规定,显得与国际刑事立法潮流有差距。现今各国刑法对于侵略罪、战争罪、对外私用武力罪、非法试验药物武器罪、灭种罪、反人道罪、种族歧视罪、奴役罪、酷刑罪、海盗罪、扣留人质罪、毒品罪、恐怖活动罪等等有“国际公罪”性质的严重犯罪,多有专章专节或专条规定,以昭格外重视和严厉打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刑法和韩国刑法的“与外国私战罪”,[1]犯罪地点主要可能在境外。我国刑法对于发生在我国境内的上述犯罪行为,大多可以当然视为杀人、放火、决水、贩毒、爆炸、伤害、抢劫、劫机、绑架等罪,适用我国刑法追究。但也有些无法归入这些犯罪中,成为“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形,如民族或种族驱逐流放,民族(种族)奴役、对外国私用武力、非法进行有害人类的人体试验或生物试验、非法进行有害的药物和武器试验、奴役或奴隶贩卖等等,因法无专条,将可能不得不放纵之。或者即使勉强归入现有罪名中处罚(如将奴役罪纳入“非法拘禁”罪中处罚),又显然太轻,与这些犯罪之严重性远不相称。特别是当这类国际犯罪为我国公民在境外所犯,而犯罪人又逃回国内时,假如我国刑法无专条规定,又据“本国人不引渡”原则拒绝将罪犯引渡给外国审判,则我国将如何处理此种案件?所以,刑法中的这类规定是否突出,是否有专条专节,是一国刑法是否具有国际性、现代性的重要标志。[2]我们不是常讲法律要“与国际接轨”吗?
(三)关于强奸以外的性犯罪
关于性侵害犯罪,修订后刑法典于强奸之外,比原刑法增加了一个强制猥亵侮辱罪(第237条)。但是,严格地以发生性关系为侵害目的的犯罪,仍只列强奸一种。对于外国许多刑法典中列为犯罪的诱奸未成年妇女、诱致猥亵未成年男女,利用特定身份关系、权威(如监护、教育、管理、传教、隶属、雇佣等)奸淫妇女等性侵害以及通奸、亲属相奸等两种性犯罪,修订后刑法典均无规定,这些规定的缺乏,也许是有意“反封建”的结果。因为通奸、亲属相奸、无夫奸均被视为典型的“封建主义”罪名。但事实并非如此。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刑法典中,这些罪名规定之详,超出我们相象。以“资产阶级自由化”最严重的美国而论,据1983年统计,美国仍有27个州有通奸罪,有20余州有私奸罪(未婚性交)或非法同居罪(非婚性交)。许多州都有乱伦罪(其中俄克拉何马州七八亲等以内血亲姻亲结婚或非婚性交都构成乱伦罪),许多州有诱奸未婚女子罪,还有反自然的性交罪(如鸡奸、奸尸、兽奸),等等。[4]这些犯罪,在我国均“法无明文规定”。特别是利用特定身份关系和职权奸淫妇女,特别是少女,在西方国家大多视为仅次于强奸、奸淫幼女两罪的严重性侵害,但我国竟一直不规定。如《西班牙刑法》第434条规定的治安官员、神父、佣仆、监护人、教师、看护人奸淫12岁以上21岁以下少女之罪,《意大利刑法》第520条公务员利用官署权威奸淫妇女之罪;《奥地利刑法》第206条、第212条权力关系滥用奸淫猥亵未成年人之罪;《瑞士刑法》第192条奸淫16岁以上未成年人、养继子女、被抚养人、被监护人、学生、艺徒、学徒、仆役之罪、其第193条官员或医护人员奸淫被收容、监禁、救治、受刑、济养、被告之人之犯罪……,等等,在我国刑法中都视为无罪。这种情形,对保护妇女儿童,对防止权力关系滥用或约束有特定身份权之人的目标而言,都是重大缺漏。这类强奸以外的性侵害或性犯罪,在我国经常发生,但因为不视为犯罪,所以受害人只剩下两条选择:要么忍气吞声自认吃亏不敢声张,让犯罪人扬长而去或让其继续大胆侵害自己;要么伪造证据或现场,把案件“提升”为“强奸”,以达到使罪犯受惩之目的。这两者都不是国家立法的本意。此种性侵害,视为无罪,太轻,不利保护妇女和未成年人权益;视为强奸,太重,又使罪刑不相称。如果刑法上也纳入欧美刑法类似的过渡罪名,问题不是就解决了吗?
(四)关于侵害精神、尊严、人格、隐私之类犯罪
国外刑法特别重视侵害人之精神、尊严、人格、隐私之犯罪,规定甚详。这是刑法现代性的重要标志之一。修订后刑法典对此规定相当薄弱。主要以打击侵犯人之精神、尊严、人格、隐私为目的的罪名,实际上仅有第243条诬告罪、第246条侮辱诽谤罪、第252条侵犯通信自由罪、第245条非法搜查及侵入住宅罪4条。其他罪名虽间接有此意,但主要或直接目的是保护公民人身完整、安全及自由之权。因此,国外刑法典中许多常见的罪名我们没有。比如《法国刑法典》中的“威胁罪”(以实施重罪或轻罪相威胁使人产生恐怖)、“性骚扰罪”、“歧视罪”、“违反人之尊严与劳动住缩条件罪”、“侵犯私生活罪”、“侵犯人之风度形象罪”、“侵犯职业秘密罪”,等等,我们都可能视为“资产阶级刑法的虚伪”。又如《德国刑法典》第15章之“言论隐私权之侵害”、“私人秘密权之侵害”、“他人秘密之利用”等罪,[2]《奥地利刑法》第5章之“私人秘密及职业秘密之侵害”罪,[3]《瑞士刑法》第3章妨害名誉及秘密罪中之“无权录取他人谈话”、“窃听或盗录他人谈话”、“以录音方式或摄影妨害秘密或隐私”罪,[4]等等何等周密,我们可以振振有词地说这类规定“不合我国国情”,所以要排除于刑法分则之外。但是时代变了,国情也在变,难道我们的“国情”永远是“斗私批修”斗到夫妻的枕头上吗?从前被视为荒诞的“隐私权”概念现在日渐为全社会普遍接受,这才是我们新时代的真正国情。刑法必须迎合这一国情!
从微观角度看,修订后刑法典的局限与缺陷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一些条文内容逻辑不严密
修订后刑法典条文内容及逻辑不完善、不严密之处也很多,这里仅拣择一些略加分析。我们按条文先后之顺序分析。
1.第6条第2款“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或航空器内犯罪的,也适用本法。”依此逻辑,特别行政区的船舶飞机内都应适用本刑法典,因为它们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船舶飞机。但这显违“一国两制”,也不合基本法及附件三之规定。应为“……也适用我国的刑法”。因为我国的刑法可以包括中央刑法和特区的刑法。
2.第12条第2款“过失犯罪,法律有规定的才负刑事责任”,此语逻辑有误。过失造成损害者,刑法有规定的才视为犯罪,未规定者只能叫过失致人损害之行为。此语给人的印象是,过失犯罪有两种:一是法律有规定应负刑责者,一是法律无规定不应负刑责者。其实大误。法律无规定且不应负刑责者岂能叫犯罪?此句应为:“过失行为,法律有规定者才负刑事责任”
3.第20条第2款:“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此语亦不严谨。此处规定的是“防卫过当”。既为“过当”,就不能叫“正当”。也许有人说,修订后刑法与原刑法比,“正当防卫”的概念已经变了,“正当防卫”的四个条件中,“防卫手段和程度必须以足以制止不法侵害为限度”的条件取消了,所以可以在防卫过当表述中曰:“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这是误解。修订后刑法与原刑法条文文字中都没有明确表述“防卫手段相当”或“足以制止侵害为限度”之意,这一意思都是从后项“防卫过当”的规定中推论出来的。防卫过当的规定,就是“正当防卫”之正当性的重要条件之一。修订后刑法还有防卫过当规定,就不能有“正当防卫过当”之表述。只应有“防卫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之表述。
4.第20条第3款“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采取防卫行为”,此语亦谬。其一,从文法上讲,“行凶”就是“进行(实行)凶害行为”,“进行行凶”,就是“进行进行凶害行为”,说不通。其二,什么是“行凶”?所有实施凶害行为者都是“行凶”。因后文有“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所以,“行凶”实际只能指“伤害”,或者仅指“重伤害”。但是,“行凶”不是一个严格的法律概念,易生歧义。它是日常生活用语,“轻伤害”行为在日常生活中也常被叫作“行凶”,如拿小裁纸刀挥舞威胁人,以小棍棒威胁人,或强而有力者以拳头挥舞威胁人,都常被叫作“行凶”。如果对这种一般只能造成轻伤害的“行凶”也公然于刑法上鼓励人们去用“造成不法伤害人伤亡”的方式“防卫”,岂非鼓励私杀?为何不使用“重伤害”这样的法定概念?也许有人说,正是因为考虑到受害人在他人行凶之威胁紧迫形势下无法判断是重伤害故意还是轻伤害故意,所以干脆模糊地规定一个“行凶”。这种解释站不住脚。判断不清加害人的故意,难道就该不分轻重地把轻伤害也当成重伤害反击吗?通过其加害手段、方式难道不能判断(一般情形下)造成伤害的大致严重程度吗?照这样说,是否杀人(杀人和伤害在结果未出现时无法区分),是否强奸(强奸和强制猥亵在犯行结束前无法区分)不是也不必区分了吗?
5.第50条“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没有故意犯罪,二年期满以后,减为无期徒刑。”这一条内容也值得商榷。将原刑法的“如果确有悔改”改为“如果没有故意犯罪”,当然更便于理解、操作。但是,故意犯罪难道一定重于过失犯罪?最轻的故意犯罪(如诽谤、侵犯通信自由、非法拘禁或非法搜查他人身体等罪,在服刑犯人中间经常发生),其犯罪主观恶性难道一定比因疏忽失职造成机器爆炸,厂房倒塌,仓库失火,多人伤亡之类的过失更重?其犯罪后果(危害性)难道一定比过失犯罪重?况且,即使仅就故意犯罪而言,也有轻重之分,也有犯罪动机是否恶劣之分,如非法拘禁、非法搜查等罪只要一有此种行为即构成犯罪,不论情节严重。一有此种轻故意罪即置“死缓犯”于死地,而造成重大人身财产伤亡事故的过失犯则仍宽谅如期减刑,这是否公平?假如这非法拘禁和非法搜查身体是出于一种可以悯恕的动机(如寻找被盗物,情急之中),或有受刑人在故作圈套引死缓犯上钩,使其符合执行死刑条件,那又能算公平吗?
6.第53条罚金“如果由于遭遇不可抗拒的灾祸缴纳确实有困难的,可以酌情减少或者免除。”此规定也不严密。如果不是由于不可抗力的灾祸,而只是由于受罚人不善经营生计而长期贫困,或故意长期拖欠不缴,又怎么办?过了10年20年去追缴一个轻罪的罚金,恐与刑法设追诉时效制度本意相违。[1]
7.第89条“追诉期限从犯罪之日起计算;犯罪行为有连续或继续状态的,从犯罪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此规定也有疏漏。设若有犯罪行为终了或结束而犯罪之结果必待(或偶然拖到)追诉时效期限届满以后再发生,此种犯罪岂不是就不当追究?在投毒伤害或杀人案中即有此种可能性,而在犯罪结果出现之前又不可能被控告或立案。其他轻罪案件也许还有此可能,如故意设计计算机“定时炸弹”,于5年以后炸毁国家重要信息库,造成重大损失,依现行追诉时效制度,即不能适用刑法第286条追诉了。所以,国外现多采“自犯罪成立之日起算”,这就包括了犯罪行为终了而犯罪结果久后发生的情形。我国民国时的刑法也采“自犯罪成立之日起算”之制。这都值得借鉴。
8.第98条“被害人的近亲属也可以告诉”,这里的“近亲属”何所指?国外刑法典于此处均会规定近亲属具体范围(几亲等以内),我们为何不规定?若直接规定亲等或指明以继承法之继承人范围为近亲属,都无不可。现没有明确限定,就必然发生有些亲属的告诉是否有效的问题。此外依刑法此条本意,近亲属的告诉权象是独立告诉权,因无要被告人本人同意之规定,又象是非独立告诉权,因只有被害人无法告诉(想告诉而客观上不能)时近亲属才能告诉。那么,被害人本人不要告诉而近亲属执意要告诉并告诉到法院,是否为有效告诉?法律也不清楚。
9.第133条交通肇事后逃逸致人死亡,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此规定不妥。若开车人将人撞成重伤,生命垂危,而故意弃之效外不顾,明知不抢救即有死亡危险而任逃逸,放任此结果发生,完全符合刑法第14条故意犯罪之一(间接故意)的标准。应视为间接故意杀人。其肇事撞伤当然不是故意,但放任受伤人死亡危险发生则是故意。相形之下,仅处有期徒刑恐太轻。如果是重伤多人后逃逸致多人死亡呢?罪刑相当吗?我们比较第141条生产销售假药罪中,若生产销售者明知可能致人重伤或死亡而仍销售,则应视为间接故意杀人。是以该条规定了死刑、无期徒刑。相比之下,肇事重伤逃逸致人死亡是否处罚太轻?
10.第240条拐卖妇女儿童罪,不如拐卖人口罪全面。若发生拐卖老人、精神病人以供非法试验之用又该如何处理?若发生拐卖成年男人或未成年(18岁以下,14岁以上)人又如何处理?
11.第241条收买被卖妇女罪,若被买妇女本人愿意与收买者结婚,不愿被“解救”,其父或前夫又强烈要求“解救”,又怎么办?特别是当未有前婚时,“收买婚”若一概不承认,一概将与被卖人感情尚可的收买人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是否恰当?
12.第289条聚众“打砸抢”规定易生歧义。其一,致人伤残死亡视同伤害杀人处理,但倒底是处罚“聚众”之人(组织者)还是下手之人,或二者同处,若在下手人不明时仅对“聚众”之人处以伤害、杀人之罪刑?法条不明。其二,毁坏或者抢走公私财物的,“除判令退赔外,首要分子依抢劫论处”。这是不是说首要分子以外参与打砸抢者(只要未打伤或打死人)都无罪?既打又砸又抢,岂能无罪视之(仅退赔了事)?其三,仅打砸而未抢时,难道不可依第275条故意毁坏公私财物罪处理?打砸为辅、哄抢为主时难道不可依第268条聚众哄抢公私财物罪处理?法条为何不注明?这一条有否鼓励追随打砸抢之嫌?
13.第295条传授犯罪方法最高可处死刑,显然太重。既不视为教唆犯,而独立罪名,则一般不视为共犯。即使是杀人罪的教唆犯,只要不是教唆未满18周岁人犯罪,恐情节再重也不会按主犯处理。传授犯罪方法罪应轻于教唆,因无促使他人完成特定犯罪之故意。最高处死刑是太重了。由此联想到共同犯罪中的一种新形式——雇佣犯罪,刑法总则未有明确规定,也是缺陷。将出钱雇人者视为教唆犯显然不当,因非传统意义上的教唆;视为从犯也显然不当,因为他确实是“造意者”,共犯应以造意者为首。所以,此种雇佣犯罪情形下,二者(雇者,受雇者)均应视为主犯,同等处理。
14.第300条利用迷信致人死亡仅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太轻。若犯罪人对于明显身患重病的人用明显危及生命的迷信方式(如棒击驱鬼,于面部贴湿布阻止呼吸以驱邪或其他依一般人常识都可知明显威胁生命的方式)或迫使人们去冒明显的生命危害而致人死亡,为其“治病”致其死亡应视为间接故意杀人。仅处有期徒刑,不足以打击危害甚大的巫婆、神汉、邪教教主之类。
15.第360条第2款嫖宿14周岁以下幼女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显然与第236条奸淫幼女罪相矛看。既然符合奸淫幼女(强奸)的一切条件,为何不视同强奸?也许有人说,幼女在卖淫中,是同意奸淫,故嫖者罪轻。这不对。奸淫幼女本不问幼女本人心态如何。若说奸风尘幼女应处罚轻一些,则违背人权同等保护原则;即使幼女主动路到风尘之所去卖身挣钱,她仍是“奸淫幼女(强奸)”的受害者。还有,嫖幼女与奸淫幼女如何区分?以是否在风尘场所来分?以是否处女来分?以是否给报酬来分?实践中都无法区分。况且若有风尘幼女离开风尘场所后仍被人以钱财诱奸,而后又告发,是强奸乎?嫖幼女乎?或幼女被卖入妓所初夜被奸(或难免有不愿或反抗),作嫖幼女处罚乎?依强奸处罚乎?
16.第八章之贪污、受贿、行贿三罪仍仅以“财物”为赃物,显然不够,不能概括许多新起的贪污贿赂罪之赃物情形。
17.第八章贪污受贿罪以“国家工作人员”为限。这包不包括已经离退休但实际仍有相当权力且又积极发挥此种“余热”的人贪污受贿之情形?对这种人仅以“介绍贿赂罪”处罚显然不够(因有时他介绍的对象并未受贿)。实践中的情况比我们想象的复杂。
这样的问题很多,这里仅随便捡出十几项加以说明就可以看出问题的严重。若对每一个再加细研,会发现更多。这因篇幅之限只能留待将来另撰专文了。
二、一些文字表述有语法问题
修订后刑法的文字表述中语法问题也有一些。这里仅拣择一些较明显的加以分析。
1.第六章第六节标题“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表述不明。从其规定的9个罪名看,其犯罪行为都是在破坏环境和资源,并不只是破坏对环境和资源的保护措施办法。若说违反有关保护规定而构成的犯罪就应叫做“破坏××保护罪”,那么几乎所有的犯罪都可以叫做“破坏……保护罪”,危害人身权、财产权、民主权等等犯罪,违反公共安全、公共卫生保护之法规的犯罪不都如此吗?况且这类犯罪的目的和后果都是在破坏环境和资源本身,而不是破坏对它们的保护。这一表述文字上欠严格。
2.第4条“对任何人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表述不准。“对……犯罪”,通常理解为“对某某对象而为犯罪行为”。若说本句原意就是“对任何对象而为的犯罪行为,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显然偏离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本意。因此,这句应表述为“对任何犯罪的人,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这句强调的是不同犯罪主体定罪处刑的平等。
3.第5条“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有适应”,语法有问题。“承担的刑事责任”似言责任承担了之后,而承担后的责任就主要是刑罚。因此,这就等于说:“刑罚的轻重应与刑罚相适应”。因此,在“承担的刑事责任”之前加一个字,改为“应承担的刑事责任”,问题就解决了。事实上,刑罚尚未决定时,只能有依法应承担的刑责问题,尚不存在“承担的刑责”。
4.第22条“为了犯罪,准备工具、制造条件的,是犯罪预备”,这种表达远不如“为犯罪准备工具、制造条件”更准确、干脆。
5.第24条“对于中止犯,没有造成损害的,应当免除处罚”,此表述显有语法问题。到底谁应当免除处罚?是中止犯(犯罪人),还是“没有对中止犯(犯罪分子)造成损害的人?”依立法本意显然是前者,但依文字表述又应是后者。为何不改为“中止犯,没造成损害的,应当免除处罚”?
6.第39条第1款第2项和第54条第2项关于“不得行使”或“剥夺”言论、出版、集会等“自由的权利”,表述不合语法。“自由”,就是自己完全自主决定自己言论的行为,任何权利只要真是权利,它必须同时也可以称为自由,如言论权可称言论自由,出版权亦即出版自由。所以,权利和自由实质上几乎是同义词,不过二者使用角度不同:权利与义务对应,自由与管制对应。说“自由的权利”,犹如说“权利的权利”或“自由的自由”。也许有人说,法律之所以选择“自由的权利”一语,可能是为了表示仅限制剥夺受刑人“自由自主决定行使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权利的权利”,即可能表示经有关机关批准还可以行使此6种自由或权利(即仍在此6种方面有“他由的权利”),这是诡辩。既要经事先申请他人批准同意后才能行使,那就不叫“自由”,也不能叫权利。自由或权利的定义是,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完全自主决定。既要事先申请批准同意后才行使,那不就是剥夺了或限制了言论权、出版权、集会结社等权利本身吗?岂止仅是限制或剥夺“行使……自由的权利”呢?“行使××自由的权利”并不单独存在,若有,那就是“××权”本身。[1]
7.第59条“没收全部财产的,应当对犯罪分子个人及其扶养的家属保留必需的生活费用”,此语也不通。通常,我们说“对……保留……”是对一个特定对象有所保留,不全部让其知道什么,不充分亲近他,不给他什么……等等。此句按文法逻辑,是对犯罪分子及其家属保留生活费用,即保留一些生活费(给谁?),不让他们知道或不给他们。保留下来给谁作生活费用?没有逻辑主语。如果将“对”字改为“为”字,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8.第64条“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这个“对”字又多余。“被害人的合法财产”是宾语,加一个“对”字,就没有宾语了。因为“对……”是状语结构。
9.第64条“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又不通。“供犯罪所用”不通,应为“供犯罪使用”或“为犯罪所用”。同时,“本人财物”本人是谁?不明,应为“犯罪分子本人”。其实,“本人”一词除了写信人或讲话人第一人称自称外,其他场合应称“××××本人”,不能独用。法律条文尤应严谨。
10.第68条“犯罪分子有揭发他人犯罪行为,……从而得以侦破其他案件等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此语文法不通更明显。这一句的主语是“犯罪分子”,谓“可以(被)从轻或减轻处罚”,是被动语态。“有揭发他人……等主动表现的”是假设条件状语,本意是“如果有……表现的”。问题是,在这个条件状语从句中,逻辑主语仍是“犯罪分子”,说“犯罪分子”从而得到侦破其他案件,真是莫名其妙。如改为“从而使侦查机关得以侦破其他案件”或“从而帮助(或有助)侦破其他案件”,那就通顺了。
11.第63条减轻处罚是“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之说不确。“法定刑”概念未加限制不行,减轻处罚后所处之法定刑仍是法定刑之一类。因此,此处表述或许应改为“在其所触犯的罪名正条规定的最低刑以下判处刑罚”。不过,即使这样改,恐也不是“减轻处罚”制度之本意。如杀人罪、重伤罪、强奸罪、抢劫罪等最重罪,其法定最低刑都是3年有期徒刑,难道仅因为未满18周岁、间歇性精神病、聋哑盲、从犯、自首或立功等原因就可以合法将其刑罚减到3年以下刑、拘役、管制?[2]因为法定量刑幅度太大了,若减轻处罚是在“法定刑”以下,则显然罪刑不相适应。其实,主法本意中的减轻处罚应是在若无这些减轻情节时当初的最低刑以下判处刑罚,此时有可能低于分则正条中的法定最低刑,那只是一部分情况,大部分仍在法定刑幅度内。不能以偏概全,一律规定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那样有鼓励重罪之危。
12.第72条“对于被判处拘役……的犯罪分子,根据……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宣告缓刑”。此条文法有误。本句的主语省略,应是“人民法院”。“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不是一个已经发生的事实,而是人民法院的判断。所以,应在“适用缓刑”之前加上“(人民法院)认为”二字,话就通顺了。否则,“对于……犯罪分子,根据……适用缓刑”好象在陈述一个已完成的行动或事实一样,与下文“可以宣告缓刑”语气时态不符。
13.第70条、第71条、第77条“数罪并罚”表现有语病。这三条均有“把前后两个判决所判处的刑罚”、“把前罪没有执行的刑罚和后罪所判处的刑罚”、“把前罪和后罪所判处的刑罚”,“依照本法第69条的规定,决定执行的刑罚”之表述,但这些表述均不通。“把……,决定……”,这种句型没见过。“依照……,决定……”这种句型是可以的,但又把“把……”挂在前面,显得不通。日常生活中,“把……”句型是一个倒装句型,宾语前置:“把车开走,“把他逮捕起来”、“把他释放了”、“把人们合并在一起”,实际上是主语省略后的“开走车”、“逮捕他”、“释放他”“合并他们在一起”,从来未见单独有一个“把”字把宾语提搂在一起,却反而没了谓语,这就象说“把车”、“把他”、“把他们”一样,不是一个完整从句,“把”他们怎么?显然是半截子话。此句若改为“把前罪和后罪所判处的刑罚合并考虑,依据本法第69的规定,决定应执行的刑罚”,就通顺而清楚了。或者干脆将“把……”这个残疾分句或从句取消,在下句“依照”前加上“然后”二字,文法和内容都清楚。因为“依照本法第69条的规定”已经包含了“把前后两罪合并考虑”之意,不必啰嗦。还应注意,“决定执行的刑罚”之表述也不通,“执行的”一般指已经执行的,本处显然是“决定应执行的刑罚”,这个“应”字不能少。
14.许多条文中的“对……”句(宾语前置句)不通。如第103条,“组织、策划、实施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的,对首要分子……处无期徒刑……”;第104条,“组织……武装叛乱……,对首要分子,处无期徒刑……”,这类“对”字在分则中不胜枚举,其实均不通。若说“对”字在此有利于指明处罚对象,则刑法分则每条都有处罚对象,处处均应用“对”字。在刑法典中,指明处罚对象的“对”字一般均省略,以免累赘。这里多了一个“对”字,使整个句型似乎是表示“破坏国家统一的”(人)“对首要分子”如何如何,似乎“破坏统一”或“武装叛乱”的人是主语“对……处刑”是谓语,“首要分子”是宾语(通过“对”字结构前置)。这显然不通。类似的问题在第105条、第137条、第138条、第139条、第250条、第273条、第289条、第290条、第291条、第292条……等等都有类似的语病。其实,这些“对”字改为“其”字,或干脆取消,意思及语气都更清楚。这是不是说刑法分则条文表述就一律不该用“对”字呢?不是的。“对”字只是不能用来指明刑法的处罚对象,但可以用来指明犯罪行为的侵害对象,如刑法第123条“对飞行中的航空器上的人员使用暴力”,第142条“生产劣药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第247条“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刑讯逼供”等等,都是用得恰当的“对”。当“对”而不“对”,不当“对”而“对”,那岂能算对!
15.第110条间谍罪第1项“参加间谍组织或者接受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的任务的”一语表达不通。“接受……任务”这句型当然可以,但接受“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的任务”说不通,“任务”是组织或个人所“任”之“务”(担任的事务),间谍组织或其代理人的任务,那是他们所“任”之“务”,那就不存在直接接受过来的问题,只有“转交”、“委托”、“指派”。所以此处应改为“接受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指派的任务”。
16.第112条“战时供给敌人武器装备、军用物资资敌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此语也不通。“供给敌人”就是“资敌”之意,这句话无异于说“战时以资敌资敌的”,显然不通。如果改为“战时以供给敌人武器装备、军用物资的方式资敌的”就通顺了,因为资敌方式可能不止此二者。或者干脆改为“战时以武器装备、军用物资资敌的”更好。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1]《各国刑法汇编》上册,第334页。《韩国刑法典》,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页。
[2]《唐律疏议·名例五》。
[3]刑法第35条“驱逐出境”应视为一种保安处分。刑法第37条“训诫”、“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也可视为“准保安处分”。
[1]因此,刑法剥夺政治权利之制所能夺及的权利,应仅指宪法第34条之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因宪法未明文规定任何公民有:“应考试服公职之权”(民国时代宪法有此规定),故第34条被选举权应作广义理解,即包括出任非经票选的公职之权利。
[2]《法国刑法典》(1994),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9页。
[3]参见方蕾等编:《外国刑法分解汇编》(总则部分),第259~280页。
[1]我国刑事诉讼中,如无附带民事诉讼,就不会有附加的民事判决。其实,剥夺亲权、民事权,可以视为准刑事判决,可以视为附加民事判决。
[2]这里的“类”是我的方便分类,不是刑法分则上由“种类客体”所确定的犯罪之“类”。这里的“类”没有分则章节标题之涵义,而可能是跨章节的,或仅是一章节中的一部分。
[3]《各国刑法汇编》,上册第853页、919页,下册第1633页。
[4][5]《法国刑法典》,(1994)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3页、70页。
[6]如两人同行旅游至僻远处,一人生病,另一人即有救助义务,否则即犯罪。
[7]《法国刑法典》(1994),第73页。
[1]《各国刑法汇编》,上册,第343页。《韩国刑法典》,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9页。
[2]也许有人说,“国际犯罪”是国际公约规定的内容。事实不尽然。国际公约中的刑事条款一般均应有国内刑法的具体规定去实施、执行。我国参加这样的公约甚少,更应在国内刑法中有所规定。
[3]储槐植:《美国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52页,第254~256页。我国刑法有“侮辱尸体罪”,但无“奸尸”罪。
[4]《各国刑法汇编》下册,第1806页,1610页;上册,第962~963页;第1088-1089页。
[1]《法国刑法典》第65页,第67页,第80页,第84页,第88页,第89页,第91页。
[2]《各国刑法汇编》上册,第796-797页。
[3]同上,第928-929页。
[4]同上,第1082-1083页。
[1]对此,前文我曾提出借鉴刑罚易科制度解决。
[1]当然,无罪公民出版、结社也要审批,但这种审批与管制、剥夺政治权利情形下可能有的因言论、出版报审批,含义大不一样。前者只要合法就一定要批准,后者只要不合监管之需要一律可以不批准。对后者而言,此种情形还能说明并没有完全剥夺或限制6项权利或自由本身吗?
[2]当然,这里还有依情节轻重的分档问题。如杀人罪法定刑为3年以上10年以下、10年以上至死刑两档;重伤、强奸、抢劫罪亦是此二档。但对最严重的杀人、强奸、抢劫等罪,若仅因其自首后立功而必减至10年以下(不含10年)有期徒刑,这公平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