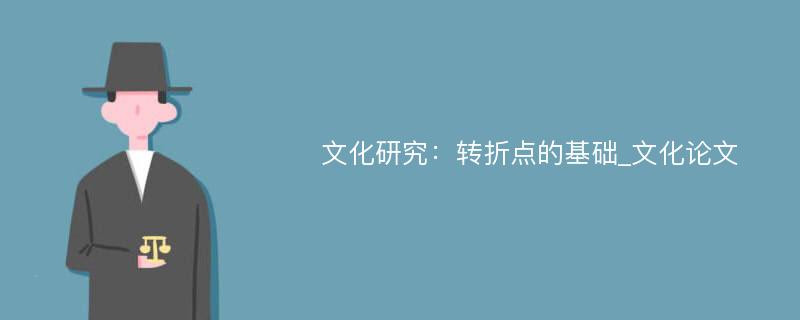
文化研究:转折的依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今,文学批评的现状赢得了两种相互矛盾的评价:批评的缺席与批评的泛滥。许多人听到一种抱怨:批评撤出了文学的前沿,不再承担阐释和评判的责任,文学舞台上仅仅剩下了作家的独白,批评家躲到学院体制的树荫下乘凉去了。另外,人们又会惊讶地从学术杂志上发现,抛下了文学的批评莽撞地空降到另一些疆域,批评家开始对广告、流行歌曲、商品包装指手画脚,侃侃而谈。他们似乎无视学科知识的限制。这些越界行动遭到了不少异议:批评家的手是不是伸得太长了?他们无所不在,任何问题都要插嘴过问——这是谁赋予的权力?
就在此时,人们听到了一个概念:文化研究。文化研究仿佛是一场新型的学术革命。批评家可能染指“文化”所包含的一切,尤其是当文化被解释为传统的经典,被解释为当下的日常行为及社会制度之际。这时,传统的学科地图被抛弃了:批评家遭遇的现实经验如此复杂,问题的根系可能横跨几个学科,他们没有理由因为学科的既存边界而削足适履。为什么学科地图不容修改?学科知识如何划定疆域?这本身就是文化研究必须追溯的问题。既存的学科体系诞生于特定的历史时期,知识分类的依据涉及科学史的沿袭、教育理念、学院机构的设置、现实的强大需求等。然而,形式自律一旦转化为刻板的教条,保守势力随即形成。许多时候,知识分类形成的学术体制可能将某种权力授予学科规范,这种权力时常成为阻挡现实经验的盾牌。文化研究的出现的确源于一种洞察:某些学科的分割人为地约束了思想,现在已经到了破门而出的时候。正如弗·詹姆逊所言,文化研究的“崛起是出于对其他学科的不满,针对的不仅是这些学科的内容,也是这些学科的局限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化研究成了后科学。”(注:弗·詹姆逊:《论“文化研究”》,《文化研究和政治意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3页。)
不错,“文化研究”这个称谓来自西方。多年以来,人们对于类似的理论旅行十分熟悉。但是,文化研究并没有得到一个标准的模式作为仿造的范本。文化研究的主题和方法五花八门,人们的兴趣毋宁说是一个基本理念:援引学院的知识处理复杂的日常社会,处理人们置身其间的现实经验。可以说,文化研究的兴盛与某些前所未有的现实经验密切相关。甚至可以推测,现实经验正在赋予文学批评某种前所未有的功能。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文类,文学批评令人惊奇地出现了一个意味深长的转折。很久以来,文学批评的主要功能是解读、分析、阐释、评判文本或者作家。文化研究的重要动向是,批评跨出了文学,投入一个更大的世界——批评家兴致勃勃地将现实视为一个可供分析的大型文本。他们的心中,某些现实经验产生的冲击和震惊决不亚于文学。批评家意识到,现实正在进入另一阶段。文化研究的扩张是现实的产物。
现实发生了什么?如同许多人发现的那样,符号生产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信息时代”成了一个时髦的命名。工业时代的特征是巨型的物质景观,例如摩天大楼或者远洋巨轮;信息时代的标志是符号的大量繁殖。这显然是大众传媒急剧崛起的后果。从书籍、报纸、卫星电视到互联网,交叉的大众传媒网络愈来愈密集地覆盖了全球。尖端的摄像设备和电子技术不仅制造出影像、音响等多种新型符号体系,同时,大众传媒的符号生产通常拥有巨额的资金和全球性销售网点。“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口口相传是前现代社会典型的传播方式。现在,大众传媒可以轻易地让形形色色的符号体系占据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护照、电话号码、官衔或者职务、服装款式,各种符号体系愈来愈多地成为现实的代表——例如证明一个人的身份,或者象征一个机构的权威。有时,符号即是现实本身。电视主持人播报的滚动新闻或者触目可见的广告不是现实又是什么?如果现实开始按照某种符号体系生产自己,如果符号的结构深刻地影响了现实的结构,那么,符号不再是外在于现实的象征物;相反,符号就是现实的构成。
相对于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政治体制,大众传媒、符号与历史特征之间的互动关系并未得到足够的关注。符号生产与权力或者经济之间可能产生种种新型的联结与合作,这将深刻地影响历史。根据本尼迪克·安德森的观点,印刷术对于民族或者民族主义的形成——安德森称之为“想象的共同体”——产生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注:本尼迪克·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吴睿人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年,第46-55页。);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说来,《新青年》杂志显然功不可没;广播、电视和互联网不仅是大众传媒的电子形式,它们同时缔造了另一种文化和政治民主形式。现今,人们已经有充分的理由意识到,世界正在愈来愈“文本化”。符号不仅是能指,而且成为所指。一些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家看来,符号与真实的界限已经相当模糊。这并没有推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命题,但是,情况正在变得日益复杂。不断扩大的符号生产增强了文化的相对独立性,物质生产与文化之间的“不平衡关系”——马克思的深刻发现——愈来愈常见。另一个意味深长的动向是,经济与文化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大众传媒、广告与观众数量之间的循环表明,许多文化产品与文化商品之间的距离正在消失。如今,人们完全有理由用经济学术语将看电视或者参加一场歌舞晚会称之为符号“消费”。在相同的意义上,“文化产业”这个概念的盛行可能象征了一个历史性的转折。
对于如此重大的历史变化,文学能够说些什么?显然,传统的文类无能为力。王国维对于戏曲与祭祀关系的考证显明,戏曲部分脱胎于远古的宗教文化,戏曲的歌舞回应的是“巫之事神”的时代;钟嵘以“气之动物,物之感人”的天人关系解释了诗歌的缘起。从青峰斜阳、孤舟细雨到清风明月、落花流水,围绕人与自然的核心主题表明,古典诗词是农业时代的经典文本。相形之下,现实主义小说是市民社会的产物。小说的庞大篇幅擅长处理众多人物性格及其复杂的社会关系。可以看出,诸种文类分别拥有独特的现实区域。它们嵌于某种文化结构之中,呼应和表现特殊的现实演变。现今,符号与现实的关系正在颠覆一系列传统观念,深刻的历史后果呼之欲出。哪一种文类有可能充分地给予说明?文化研究的越界、扩张无不表明,某种新型的文化结构力图铸造独特的文类——传统的文学批评有幸成为回炉的素材。
托尔斯泰在《艺术论》之中曾提出挑战性的观点:如果一部作品完整地将作家的体验转述给读者,二者之间的文学批评无异于多余的蛇足。至少在当时,托尔斯泰没有意识到批评的一个重要功能:解读。解读并非一种单纯的复述,解读包含了文本潜在规则的解析,从而说明一个文本何以如此组织。这可能涉及某种形式史,也可能涉及某种意识形态的巧妙运作。另一方面,解读还包含了识别种种隐蔽的意义,发现一些晦涩的象征或者习焉不察的歧视,某些意义甚至只能在特殊的理论溶剂之中显影——例如精神分析学派理论之于《哈姆雷特》的恋母情结。如果说,文本已经包括了一个故事,一组意象,那么,后续的批评将是一种意义再生产。意义的持续增添意味了生活内容的扩展。杰作的标志之一即是丰富的意义矿藏。说不尽的莎士比亚——这句名言证明,这个伟大的剧作家仍然源源不断地为人们的生活提供新的意义。
文化研究的重要动向是,文本解读的技术转移到现实的解读。即使物质生活并没有明显的改变,符号的大量增殖仍然可能制造一个迥异的空间。关闭电视机的时候,屏幕上的影像完全消失了。但是,谁能够说,这些从未体现为物质的影像符号对于人们的生活毫无影响?从学院门口的海报、城市广场的抽象派雕塑到麦当劳餐厅门口的小丑、咖啡厅里低回的音乐,这些符号使生活充满了意义。人们存活在各种意义之中,想象何谓幸福,何谓正义,何谓快乐,何谓悲惨。许多时候,人们的某些身体快感也开始纳入特定的意义系统。万宝路香烟或者XO酒调教出来的口味可能包含了隐秘的文化密码。所以,解读这些符号的意义即是解读人们的生活。为什么必须是乔丹而不是其他什么人的耐克鞋?为什么必须是圣斗士的天马流星拳而不是关云长的青龙偃月刀或者张飞的丈八蛇矛?政治家在竞选相片之中摆出的身体姿态暗示了什么?摇滚乐震耳欲聋的音响又在夸张什么?西装革履与长袍马褂会在哪一个场合形成冲突?如果对于种种符号的意义茫然无知,人们只能徘徊在现今的文化生活之外。当然,文化研究不是提供一份节目单或者说明书,文化研究分析的是隐藏在这些符号背后的文化脉络,分析这些符号如何教导人们想象生活,想象自己占有的社会位置。作为文化研究的一个经典范本,罗兰·巴特的《神话集》富有启示性。这部著作犀利地揭示了一系列符号制造的现实,并且解剖了符号制造者的意图以及伪饰手段。显然,种类繁多的符号体系拥有不同的文化后援,相异的价值观念体现为符号之间的激烈冲突。文化研究不可避免地卷入这些冲突,认同什么或者批判什么,批评家甚至不惜放弃价值中立的名义。的确,就是在符号解读之中,文化研究可能触及乃至进入一系列重大的社会问题,各种政治学、社会学或者历史学的概念将在这个时刻活跃起来,介入分析和批判。种族、性别与阶级、阶层等一系列有关身份的概念同时启动表明,压迫与解放仍然是文化研究持续关注的主题。当然,阶级不再是主要乃至惟一的分析概念,民族、性别、阶层等各种概念的交织说明了问题的复杂程度。这时,一个文本、一份广告、一个博物馆的陈列或者一本时尚杂志的解读能够走多远,这常常是多门学科知识共同运作的后果。
对于文化研究说来,破译种种符号的隐蔽意义决不亚于文本解读。每一种符号体系都拥有特殊的表意方式以及文化根源。但是,这仅仅是解读的开始。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意图在于,识破隐藏在符号背后的秘密信息。擅长文本分析的批评家熟知,文学时常在巧妙繁杂的修辞之中藏匿种种意识形态。利用一个快意恩仇的武侠故事维护男性中心主义,利用巧妙的人物关系设置贩卖种族歧视观念,这是批评家屡屡发现的把戏。事实上,这种把戏不断地在一个更大的范围重演。制造种种堂皇的口号或者宏大叙事夹带某种意识形态,有意将局部的成功夸大为普适性的命题,这些手段均属“文本化”世界的基本修辞。“全球化”不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口号吗?的确,跨国公司开拓了全球市场,卫星电视与互联网成为多民族文化相互对话的平台,越洋电话与大型喷汽式客机已经如此普遍——不同肤色的人种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握手言欢的机会。然而,尽管大量的理论描述、电视肥皂剧和商品广告都在许诺各种美妙的历史景象,文化研究仍然可以发现,这个激动人心的口号可能遮蔽另一些严重的问题:例如各个国家在全球市场之中极为悬殊的份额,又如强势文化对于本土文化的吞噬,再如英语崇拜对于民族对话的制约,如此等等。当然,这些问题不可能只有一个维面。从有意的误读、强势文化的“杂质化”到嬉皮士式的激进叛逆,文化研究还可以察觉某种挑战文化霸权的潜在能量。这时,解读意味了发现症候,祛除遮蔽,尤其是善于从症候之中发现有意的隐瞒、伪饰、歪曲以及象征性转移。这显然是文化研究垂青精神分析学派的原因。从欲望、超我、压抑到无意识和力比多,弗洛伊德与拉康的基本观念得到了相当普遍的认可。对于许多批评家说来,精神分析学派的重心并非泛性欲主义——精神分析学派的真正启示在于对一整套表象与无意识关系的深刻解读。
现在,批评是不是离文学愈来愈远了?“新批评”以来的传统是,文学就是文学,文学批评必须坚定地驻守在文学内部,“封闭式阅读”是“新批评”的不二法门。“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成为一个著名的区分——批评必须从“外部”转向“内部”,转向韵律、节奏、象征、神话、叙事等语言分析。那么,“文化研究是不是重返‘外部研究’?”我曾经在另一个场合涉及这个问题:“回答既否定又肯定。在我看来,文化研究没有理由省略文学的语言层面,单纯地将文学想象为再现现实的一面客观而公允的镜子。事实上,种种文学问题的提出必须包含了文学语言的考察,或者说,文学语言的考察表明了这些问题的确是‘文学问题’;但是,这并不是说,种种文学问题的解决仅仅回旋于文学语言内部。人们没有理由狭隘地将文学语言的考察想象为挤柠檬式的字、词、句辨析。许多时候,文学语言的隐喻、反讽、叙事特征、文类的演变与历史语境息息相关;另一方面,文学语言的美学意义只能书写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之内——文学的先锋意义或者文学的美学反抗无一不是以某种历史文化的概况作为衡量的基准。这个意义上,巴赫金的观点富于启示。巴赫金承认语言相对自主的内部逻辑,但是,语言同时还卷入社会关系,卷入政治系统、意识形态系统和经济系统。”文化研究并没有放弃文学,但文化研究重新将文学置于众多符号体系形成的文化网络之中。这至少表明,文本、作家、读者——构成文学的基本要素——无不存在于这种网络内部,并且与网络所拥有的种种因素形成互动。这时,作家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生产者。作家首先是一个特定的社会成员,著作权法、稿酬、言论开放的程度、作家的组织形式、文学氛围乃至作家的性别都有可能影响文学写作;读者也是如此——历史时期、阶层、文化教育的程度无不意味了相异的阅读效果。的确,文化研究没有理由绕开细致的文本内部考察,但是,所有的考察结论——即使是文学语言的独特性——都不得不进入文化网络给予衡量。如果没有提到中国古典文学和西方现代文学,没有提到左翼作家以及鸳鸯蝴蝶派,人们又怎么认定鲁迅《狂人日记》是一个开创性的文本呢?
当然,对于“外部研究”的疑虑决不是空穴来风。相当长一段时间,文学批评曾经用国家、民族、阶级、人民性等几个有限的大概念配成诊断一切文本的不变处方。批评家体会不到一个微妙的眼神、一丝隐秘的心理波纹或者一串精彩的比喻。总之,大概念降临的地方,文学消失了。但是,文化研究认为,恢复文学的地位并不是割断种种联系,制造一个“纯文学”的孤岛。相反,文化研究力图考察历史之中的文学,进而解释文学之中的历史。
没有必要想象文学批评的某种正宗或者“本质”——批评的面目并不确定。查阅文学批评史可以看到,批评家曾经专注于韵味和意境,专注于炼字炼句;也曾经考察某种典型人物,或者考察某故事背后的神话原型。从中国古代的诗话词话到罗兰·巴特的《S/Z》,从柏拉图的《文艺对话集》到刘勰的《文心雕龙》,文学批评显示为极富潜能的文类。很难说文化研究能走多远——新型的解读模式?学院知识的活力?形而上学的终结者,或者意识形态的挑战者?无论如何,文化研究至少表明:这个时代开始大规模地生产符号的时候,理论阐释及时地跟上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