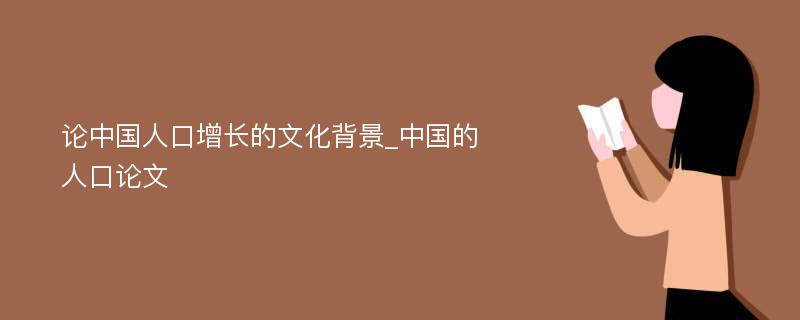
试论中国人口增长的文化背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试论论文,文化背景论文,人口增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是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国之一,从古至今,她始终雄踞于世界人口之巅。今天,华夏大地已拥有十二亿“龙的传人”,不断膨胀的人口导致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的进一步失调,并形成多重矛盾和危机,共和国许多被人们引以自豪的伟大成就,在人口问题面前也变得黯然失色。中国人口增长的动因和机制是什么?民众的生育欲望为何仍然强烈?以上问题在计划生育已列为“国策”的今天,更加令人困惑。
现实社会是历史的沉积。马克思说:“事实上,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的、历史地起作用的人口规律。”〔1 〕中国有几千年悠久的文明历史,其人口历史演变的动因和机制既有社会生产方式的决定性影响,也不乏社会上层建筑的干预和渗透,中国人口的发展与社会文化的发展有着相互影响、制约的内在联系。当十二亿人口使共和国在攀登世纪峰巅的山道上步履维艰,当我们更为九亿农民的生育控制问题窘迫不安的时候,本文试从文化背景入手,步入时光的长河溯流而上,对中国人口增长的动因和机制,以及民众生育意愿的生成基础进行多角度的考察,藉此企望理性的思索能引领我们驶出困惑的港湾。
一、农耕文化——人口增长的经济背景
中国古代有神农氏的传说,他是第一个教给人们用耒耜进行农业生产的人。远古的先民追随这位农神植五谷,务稼穑,耕而食,织而衣,代代生息,孕育出古老的华夏文明。
二千多年前,孟子就描绘过这样一幅极富东方情韵的图景:“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2〕以男耕女织、 一夫一妻的个体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小农经济,在春秋战国前即开始出现在华夏大地。公元前645年, 晋国的土地制度改革最早用行政力量推行这种小农自然经济〔3〕, 以后千百年,小农自然经济一直是中国传统经济的主要形式,而这种农业模式,从各个角度影响、推动了中国人口增长。
马尔萨斯在论述中国人口问题时曾说:“自开国以来,对农业一直给予巨大的鼓励,这导致人民的劳动尽量去生产人类生活所需的生活资料。”〔4 〕历代封建君主认识到发展农业是增强“国力”的主要途径,始终以农业为“立国之本”;由于封建社会早期地广人稀、战乱频繁和农业生产力的低下,又以繁衍生息为发展农业的动力,从而刺激人口不断增长。这不能不是中国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一个重要原因。
春秋末期的越王勾践,战败后为报仇雪耻,提出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计划,他“帅二三子夫妇以蕃”,施行了一系列奖励生育的政策,努力发展农业生产,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终于使越国强盛,一举灭掉了吴国〔5〕。
战国时的商鞅,在秦国奖励耕织、重农抑商、编制民户以促进农业人口增加,“以农养战”,为封建制在秦确立、秦始皇统一天下奠定了基础〔6〕。
魏国梁惠王治国,自谓“尽心焉耳”,但仍困惑于“民不加多”而求教于孟子,孟子主张给民“百亩之田”的恒产,劳役要不误农时,才能使“黎民不饥不寒”、“死徙无出乡”,紧紧依附于土地,以耕织结合的小农经济来促进封建国家的强大〔7〕。
西汉的贾谊和晁错也曾以《论积贮疏》和《守边劝农疏》、《论贵粟疏》阐述“农本”、“重农”思想。汉初统治者更是采取宽舒政策,创造安定环境,使老百姓休养生息,实行“民产子,免除徭役二年”,“女子十五岁以上不嫁”罚交五倍的“人头税”等奖励生育、提倡早婚的措施,并大力发展农业生产〔8〕。到武帝时粮丰仓满, 人口也由汉初的一千五百万陡增到六千万,登上了中国人口发展史“三大台阶”中的第一大台阶〔9〕。
封建统治者以农业为“立国之本”的政治主张,需要不断膨胀的人口来加以支撑,而一系列以“丁、口”为基础的发展农业的经济政策,也刺激着平民百姓以“添丁加口”来谋取更大的经济利益。
早在周代实行的“井田制”,就遵循着按人分配耕地的原则,以一百亩为“一夫之田”。以后王莽新朝的“王田制”、西晋的“占田、课田制”和自北魏始、又相继推行于北齐、北周、隋、唐的“均田制”,都是由封建国家按照农户人丁的数量,“计口授田”,以收取租调。无论每一丁男是授田百亩还是八十亩、三十亩,所授之田称为“露田”、“桑田”还是“永业田”,也无论是否存在受田不足的情况,流民和农民都是以丁数来决定所受田地的多少。只要多添丁,就能多得田,也就能多产粮帛,以求温饱。这样的土地制度大大刺激了农业人口的增长。以唐代为例,实行“均田制”仅百年,人口由二千五百万猛增到八千万,超过了西汉人口〔10〕,出现了杜甫《忆昔》诗中“忆昔开元全盛时,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的盛唐气象。
按人数收取赋税是中国封建国家自秦汉以来延续了二千多年的赋税制度。到了“户口日繁、地亩并未加广”的清代,“人丁税”越来越成为束缚人口增殖的桎梏。康熙五十一年实行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和雍正年间推行全国的“摊丁入亩”重大赋税制改革,又一次促进了中国人口加速膨胀,由总人口不足一亿,骤然猛增到鸦片战争前的四亿,跃上了中国人口发展史上的第二大台阶〔11〕。
千百年浓郁的农耕文化和统治者政治、经济政策的鼓励,使开端于战国时期的传统农业不断发展,到西汉时期,随着第一次中国人口倍增台阶的出现,农耕区迅速扩展。至隋唐时期,农业中心区已经逐步从北方转移到南方。唐人元吉说:“开元、天宝之中,耕者益力,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耜亦满。”可见全国农耕区范围之广。随着第二次中国人口倍增台阶的出现,清代的农耕区大大推向边疆:由辽松流域伸展到乌苏里江流域,接着发展到青藏高原、天山南北直至台湾〔12〕。到了近代,已到了“驱人归农,无田可耕”〔13〕,人多地少,人满为患的地步。正如汪士铎所哀叹的:“山顶已植黍稷,江中已有洲田,川中已辟老林,苗洞已开深箐,犹不足养,天地之力穷矣。”〔14〕
“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农耕文化与传统的小农经济方式产生其独特的人口再生产规律:长期延续的垦殖型农业在低下的技术条件下,其产量的增加有赖于劳动的不断追加投入,由此必须最大限度地压缩劳动力自身再生产周期,促成早婚、早育、密育、多育的风尚;而人口增加要求相应增加维持生命的基本消费品——粮食;多产粮食又要求投入更多的劳动力,以扩大垦殖面积或提高单位产量……如此,形成了“人口—粮食—耕地”的互动增长循环,“雪球”效应的结果是,神农氏的后代布满了黄河两岸、长江之滨,遍及神州。
建国后,“人口——粮食——耕地”的互动增长循环链仍然没有被切断,继续保持着其强大的惯性。人民公社化后,日趋尖锐的人地矛盾更被掩盖了。手工密集型生产方式只追求劳动力的数量,不重视劳动力的质量,以致于劳动力的教育成本不高;贫困的生活水平又使得劳动力的抚养成本极低,增加一个孩子无非是“锅里多放一瓢水,桌上多摆一双筷”而已。农村传统的“自然就业”方式又使得孩子一成年即可为家庭增加收入。这些因素都刺激农村家庭多生孩子。因此,无论是建国前后,中国浓重的农耕文化氛围客观上对人口增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了刺激人口不断增长的经济背景。
二、宗族文化——人口增长的社会背景
人类自身的再生产是以血脉承传不断的方式表现出来的,血脉,既是物质生产的基础,又是物质生产的目的,因此,血脉崇拜在中国文化里占有极突出的位置。周代以来,中国在改组氏族单位的基础上建立起了自己的文明,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关系与贵族政治相结合,形成了完整的宗法制度,并酿造出对后世有深远影响的宗族文化。
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国”和“家”相连,“君权”与“父权”互用,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权形式,不过是宗族权的扩大,众多的封建思想家都极为重视宗法制社会组织对巩固封建统治的作用。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族的不稳定必然导致社会的动荡,北宋理学家张载便主张“立宗子法……以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15〕达到“本固邦宁”的目的。
历代统治者把宗法制家族视为治国平天下的命脉,加以维护并鼓励其扩大,同时也大力倡导和推行宗族文化:从殷墟宗庙遗址、山东孔庙、北京太庙到大大小小的民祠家庙,历代广建血脉崇拜的圣殿;从“三牲三献”、“鼎彝铭文”的周朝到墓祭流行、家谱泛滥的明清以降,大兴祭祖、修谱之风气;从远古“践履”〔16〕、“祓禊求子”〔17〕、生殖崇拜祈望血脉的延续到溺弃“私生子”以维护血脉的纯正……宗族文化的种种表现不一而足,其核心内容都与生育文化有关,但却不是从整体的角度关心人类本身的再生产,而仅仅从宗族角度关心祖先血脉的传递、繁衍,以确保宗族的永远昌盛。
传统中国人在获得家族的持续生存后,还要谋求家族的不断发展:“丰衣足食以立身;达官显贵以立功;书香门第以立言;帝王世家以立天下。”在封建社会众多家族的对峙和斗争中,家族也形成了一种无限扩大人口规模的内在机制。这是因为:家族人口数量的多少与家族力量大小之间呈正相关关系。人口稀少的家族势单力薄,在对峙中处于劣势,难以在政治、经济诸方面发展,往往受尽大族的欺凌,只能用叙宗合谱、结婚联姻的办法以自固,并扩大家族势力;而人丁兴旺的家族势强力大,在对峙中处于优势地位,在斗争中能稳操胜券,政治势力也易于膨胀。比如南朝的“王”、“谢”二姓和北朝的“崔”、“卢”、“李”、“郑”等姓,在社会上的势力与地位,连皇族也不能与之抗衡〔18〕。又据《清高宗实录》,清代血族复仇械斗成风,“泉、漳等处,大姓聚族而居,多至数千余丁”〔19〕、“偶因小故,动辄纠党械斗,酿成大案。及至官司捕治,又曾逃匿抗拒,目无国宪”〔20〕,已成了中央王朝的心病。雍正朝中期,泉州同安县就发生大姓李、陈、苏、庄、柯合为“包姓”,小姓合为“齐姓”的械斗大案〔21〕。械斗往往是族大丁繁者欺压单寒弱小之族,人丁稀少的单寒之族在这种斗争中的劣势是显而易见的,不断扩大宗族人口规模也就成了宗族兴旺发达的基本要求。
在封建社会,宗族无限扩大人口的利益要求,是凭借森严的等级制度和社会群体意识的强大影响力,转化为宗族成员的生育行为的。宗族制度强调“夫为妻纲、“父为子纲”、“家事统一于一尊”,家长有权支配家产、处罚不肖子孙、干涉子女婚姻。宗族社会群体意识的核心则是“宗族至上主义”,人生的价值首先在于使以宗族为单位的社群繁衍和荣耀,宗族成员的婚配嫁聚、生儿育女只能听命于家长的意志和宗族的利益。作为婚育主体的妇女不能主宰自己的婚育行为,不过成了听凭宗族和丈夫摆布的生育机器。从血缘角度来看,家族无后代,就意味着祖先留下的血脉就此中断,这在宗法社会当然是天大的祸事。因此,妇女嫁夫后若无子,便属“七出”之列,难逃被“休”命运。唐代有一首《感夫诗》,就是一位叫慎氏的女子,抒写她因无子被“休”,赶出夫家的激愤之诗〔22〕。有人考证后认为,传诵百世的《孔雀东南飞》诗中的兰芝,也是因为不育而被婆婆寻衅“休”掉的。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有钱的男子为“求嗣”,便可以堂而皇之地纳妾聚小,甚至可以租用他人之妻以作生儿子的工具。贫苦农民为生活所逼,被迫出卖或典押妻子的事,也时有发生。清代才子郑板桥曾写过一首《还家行》的诗,描述了一位农民逃荒前典妻,归来后赎妻的事〔23〕。诗中的农妇在丈夫来赎她之时,已为后夫生有一子,她在故夫和后夫与乳儿之间,去留两难,其状木石动情。无独有偶,现代文学家柔石也曾用小说《为奴隶的母亲》表现了同样的故事〔24〕。从《孔雀东南飞》到《为奴隶的母亲》,几千年来,中国大地上敷演过多少出这样凄婉缠绵的人间悲剧,其根源都是罪恶的宗族制度。宗族文化所支持的宗族无限扩大人口的内在机制,也就成了促进中国封建社会人口不断增长的直接动力。
新中国的建立铲除了封建宗族制度赖以生存的政治、经济基础。但是,根深蒂固的宗族文化积淀,并未从人的观念中完全铲除,女子名字中“招娣”、“带娣”、“来娣”、“莲娣”等一系列祈盼子嗣意味的名字频繁出现,就是一个有力的佐证。特别是近几年一些地方宗族势力又重新抬头,乱起了按“丁”收钱续家谱、建宗祠、定族规、选族长,岐视和排挤无男和少男的农户的歪风,一些祭祖和封建迷信活动也死灰复燃,这使得封建宗族文化重新泛滥,并激发了部分农民生男和多生的愿望。可见,千百年来制约人们生育行为的宗族文化仍发挥着作用,还需要进一步肃清其影响。
三、儒家文化——人口增长的思想背景
在古老的中国,小农经济与宗族制度联姻,孕育出传统的中国文化——儒家文化。儒家文化是一个庞大的体系,生育文化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家天下”的社会,皇权依赖于族权,国法得益于家法,统治者奉为“独尊”的儒学,在“治国”与“齐家”两方面都与生育文化密切相关。
从“治国”之纲探究,历代统治者为了开辟更多的兵源、税源,总是鼓励人口增殖,儒学思想家也总是宣扬人口“多多益善”。孔子的治国纲领“庶、富、教”三字中, “庶”即人口众多是放在第一位的〔25〕,《礼记》解释说:“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26〕管仲的话更明确:“地大国富,人众兵强,此霸业之本也。”〔27〕孟子则说:“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28〕唐代刘晏和南宋叶适的话更为露骨,一个说:“户口滋多,则赋税自广”〔29〕,另一个说:“为国之要,在于得民,民多则田垦而税增,役多而兵强”〔30〕,真可谓一语道破天机。上述这些代表统治者的人口观促使他们推行一系列鼓励生育的政治、经济政策,诸如生子可免除徭役,减免赋税,分得更多的田地,晚婚则加倍征收赋税、罪及父母等等。这使得平民百姓也以“早生贵子”、“多子多孙”为福,上下几千年,“多福多寿多男子”、“三代同堂”、“五世其昌”一直是国民所羡求的目标。“多子多福”即是儒家生育观的一个重要内容。
从“齐家”角度考察,“传宗接代”是儒家生育观另一突出的内容。孔子承袭了殷商以来“奉先思孝”的思想,提出了“孝”这一儒家伦理思想的重要范畴,传于后世就有“生民之德莫大于孝”〔31〕、“孝为百行之首”〔32〕之说,而“五刑所属三千,罪莫大于不孝”〔33〕,“不孝”、“恶逆”、“不睦”俱属“十恶不赦”之列〔34〕。那么,什么是“孝”?许慎《说文解字》注:“孝,从老从子,善事父母者。”无子,焉能事父?所以孔子曰:“父母生之,续莫大焉。”〔35〕孟子也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孝”本质上就是嗣,就是传宗接代,不绝祖祀。这使得传宗接代的生育观已上升为人们必须遵循的道德规范,否则就要愧对列祖列宗,有“大不孝”之罪名。马尔萨斯说:“中国人认为结婚有两个目的:第一,永远延续宗祠中的香火;其次,嗣衍种族。”〔36〕可谓把握了儒家婚育观的精髓。
传宗接代、无子不孝的伦理道德,千百年来形成了人们生育观念的思维定势,已不再是迫于社会群体规范而成为了个体的自觉要求。远古即已萌生的求子习俗,在儒家文化的薰陶下成为民间信仰,推演出种种神秘复杂的形式,渗透、表现在岁时风俗、人生礼仪、交际游乐、器物佩饰以及衣食住行各个方面,成为中国民俗活动中的一个突出事象。女娲、子孙娘娘、土地老爷、观音菩萨、释迦牟尼皆成为民众敬奉的“求嗣之神”,抱泥孩、讨红蛋、偷生菜、送麒麟灯、摸秋送瓜……因地而异成为各地恪守的求子民俗。由于无子中断了祖先传下的血脉,不育便成了妇女的罪过,苏、浙、闽、粤还流行“打生”的风俗。江苏《西石城风俗志》载:“新妇逾年尚未生子,村中恶少或于新年,出其不意,曳之于土地庙,扑打为戏,谓之‘打喜’”〔37〕。浙江石方洛的《且瓯歌·打生》诗云:“打生,打生,打尔何不把孩生。跪神前,请薄惩,袒而鞭之呼声声。”〔38〕台州有《打生歌》:“结桔树下夜三更,女伴相约去打声。不管旁人来偷听,‘会生’自己叫连声。”〔39〕妇女不育既为过,一旦生子便母以子贵。如《红楼梦》第二回中甄家丫环娇杏,只因被贾雨村讨来做妾后生有一子,便被扶作正室夫人,安享荣华〔40〕。求子,即是求嗣,有子也就是有了“后”,这些都是“传宗接代”观念的反映。
在封建社会,世系按男性计算,姓氏由男性延续,家庭以男性为中心,财产由男性子孙承继,传宗接代、绵续香火的更只能是男性。因此,儒家生育文化又派生出“男尊女卑”、“重男轻女”的观念。《诗经·小雅·斯干篇》:“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褐,载弄之瓦”,婴儿一降生,由于性别差异,就受到如此不同的待遇。而西晋傅玄《豫章行苦相篇》诗中同样反映了封建社会“男儿当门户,堕地自生神”、“女育无欣爱,不为家所珍”的男女不平等观念,是广大妇女“苦相身为女,卑陋难再陈。”的血泪控诉〔41〕。由于“重男轻女”,旧中国还出现了“产男则相贺,产女则采之”的溺杀女婴的恶行。明代冯梦龙在担任寿宁县知县时,就曾出过《禁溺女告示》〔42〕。近代郑观应也曾专门写过《劝戒溺女》〔43〕文章,为女婴的生存权利发出强烈呼吁。至于古诗中曾出现过类似陈琳《饮马长城窟行》中“生男慎莫举,生女哺用脯”、杜甫《兵车行》中“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白居易《长恨歌》中“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这样的诗句,粗看似乎是“重女轻男”,其实是对“重男轻女”传统观念的表象的反逆。其缘由诗中已有答案:“君独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拄”、“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而杨贵妃一朝得宠便“姐妹兄弟皆列土”、“光彩生门户”,因此,诗人们对封建统治者的残暴、荒淫和穷兵黩武才使用了激愤、讽谕的反语。这也反证出“重男轻女”观念的根深蒂固。
孕育于小农经济和封建宗族制深厚土壤上的儒家文化,由于适应统治者的需要、受到统治者的推崇而处于“独尊”的地位,它不但为统治者的鼓励生育政策提供了决策指导,而且通过广泛久远的宣扬传播,沉淀在民族心理的深层结构中,成为制约人们生育行为的重要因素,成为深刻影响中国人口增长的思想背景和根本源泉。
新中国建立后,随着社会制度的变更和两个文明建设的发展,儒家生育观有所触动,但远未消失,特别是在农村。多生多育、重男轻女和儿女双全仍构成中国家庭生育决策的基本内核,“生男孩”更是超生最直接、最强烈的动因。这种强烈的超生愿望难以在短期内被消弭,一旦条件稍稍具备,就会迅速地转化为现实的超生行为。于是“国策”与“民意”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当今中国,计划生育也就成了“天下第一难事”。
人类学家克莱德·克拉考思曾指出:“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每个人从生到死每时每刻都受到文化的控制,文化不断迫使我们服从一定的行为模式。”〔44〕
历史象流水般地逝去。现在,面对“国策”与“民意”的强烈反差,面对“社会”与“家庭”在生育价值取向上的严重错位,我们需要反思,反思的不是我们的“国策”,而是实现“国策”所拥有的手段;我们需要探求,不仅是探求如何禁绝与“国策”相悖的生育行为,重要的是对中国人口增长的文化背景进行了深入考察和深刻思考后,探求如何对民众的生育意愿及生育行为加以有效的引导。
英格尔斯在《走向现代化》一书中说:“只有当国民从心理上自愿地接受了新的家庭观念、新的人口道德,这个国家的人口数量才能稳定地下降或趋于缓慢的增长,以同经济和文化进步的速度相协调。”〔45〕正确的引导必将促成“国策”与“民意”的统一,使实行计划生育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人们只有在全社会范围内能够有效地计划自己的生育时,才会真正成为生育的主人,人类才会以高度文明的方式繁衍生息。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92页。
〔2〕《孟子·梁惠王上》
〔3〕白寿彝《中国通史纲要》第97页。
〔4〕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第120页。
〔5〕《国语·越语》。
〔6〕白寿彝《中国通史纲要》第90页。
〔7〕《孟子·梁惠王上》
〔8〕刘淑英《中国人口史话》第27页。
〔9〕〔10〕〔11〕〔12〕〔45〕邹平、 胡鞍钢《人类·发展·前景·抉择》第91页。第95页、第134页。
〔13〕〔14〕汪士铎《乙丙日记》。
〔15〕《张子全书》第四卷,《宗法篇》
〔16〕参见《诗经·大雅·生民》
〔17〕、〔37〕、〔38〕、〔39〕刘黎明《祠堂·灵牌·家谱》第86页,第85—108页。
〔18〕汪泽树《姓氏·名号·别称》第33页。
〔19〕《清高宗实录》第49卷。
〔20〕《清世宗圣训》第26卷。
〔21〕刘黎明《祠堂·灵牌·家谱》第126页。
〔22〕〔23〕〔41〕佟道庆《人口诗话》第82页、第132页、第7页。
〔24〕《现代文学作品选》上集(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第398页。
〔25〕《论语·子路章》。
〔26〕《礼记·大学》。
〔27〕《管子·重令篇》。
〔28〕《孟子·尽心上》。
〔29〕《资治通鉴》第266卷。
〔30〕叶适《水心别集·民事中》。
〔31〕〔32〕朱熹《家礼》。
〔33〕《孝经·五刑章》。
〔34〕《唐律》。
〔35〕《孝经·圣治》。
〔36〕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第210页。
〔40〕曹雪芹《红楼梦》第2回。
〔42〕〔43〕丁振东《人口轶闻录》第256页。
〔44〕尹恩·罗伯逊《现代西方社会学》第9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