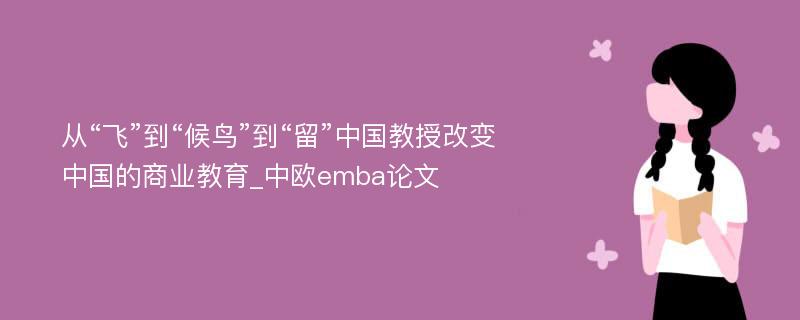
从“飞行”到“候鸟”到“留驻”华裔教授改变中国商业教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候鸟论文,华裔论文,中国论文,教授论文,商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鸟儿在漫步觅食,随后腾空而起,飞离大地,一路越过冰川大海、高山草原、城市社区,到达它迁徙的目的地。
天才的法国导演雅克·贝汉历时三年,于2001年完成了纪录片《迁徙的乌》。
“鸟的迁徙是一个关于承诺的故事。”这部惜言如金的影片的一开头,使用了这样饱含深意的句子。
恰恰是雅克·贝汉开始制作这部纪录片的前后,另一群“迁徙者”开始了他们的飞行之旅。
这是一群华裔商学院教授。他们先是集中在一年中的某几天,“飞”到中国的商学院“传道授业解惑”;后来,有人选择了“候鸟”的方式,两地停留;再后来,一些教授举家迁往中国,把自己的教学和研究重点放在了这个正在蓬勃发展的地方。
“教授的迁徙是一个关于承诺的故事。”借用上述影片的开头,或许可以这样说。
这个承诺,是关于个人职业发展、中国商业教育的承诺。
“飞行教授”
2001年,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凯瑞商学院会计与信息管理系教授黄钰昌第一次来到中国北京。中国台湾出生,美国求学、做教授,黄钰昌的经历如是。他并没有预料到,这次“飞行教授”的经历竟然促成了后来自己与中国大陆商学院的缘分。
那一次的课程,黄钰昌面对摩托罗拉的高级经理们,开始讲述自己在美国的研究案例。台上他讲得过瘾,台下“学生们”听得过瘾。中国职业经理人如饥似渴的求学态度,让他记忆深刻。
一年后,黄钰昌受聘于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凯瑞商学院与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合办的EMBA项目,开始了每年一次的“飞行教授”生活。
他给学生开的是“绩效优化、激励设计与管理会计”的课程,在凯瑞,加上考试时间,这门课要上10个礼拜,每个礼拜4个学时。
不过由于EMBA项目课程设置的缘故,在上海国家会计学院这门课被因地制宜地集中在了4天完成,两个周末,算下来,黄钰昌教授每年要在国内待上10天。
来自麻省理工学院(MIT)的王江教授每年也会因为这个项目到上海一段时间,与黄钰昌相比,王江的背景更为“本土化”。他上个世纪80年代初毕业于南京大学,后在美国学习和任教。
这个在美国顶尖商学院中屈指可数的华裔金融学教授、金融市场微结构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与国内商学院的缘分其实可以追溯得更为久远。事实上,早在11年前,其所在的MIT就已经与复旦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等国内知名的大学合办了IMBA(国际MBA)项目。1998年,王江以MIT斯隆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的身份首次回国讲学。那次讲课是在复旦大学和清华大学两个学校进行的,共3天时间。
同一年,受聘于香港城市大学商学院的周东生教授,第一次来到当时还位于上海闵行区的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他的目的很明确,为了一项研究对在校的企业家学员作调研。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凯瑞商学院林肯讲席教授周林参与了不少国内的商学院教学。清华大学、同济大学、长江商学院,以及上海国家会计学院的EMBA项目,都是他“飞行”的目标。
那几年,随着中国商学院与欧美商学院、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商学院的合作、交流的日益频繁,不少教授特别是华裔教授有了更多地了解中国商学院的机会,而商学院也认识到他们的价值,他们成为这些商学院力邀的主流授课教授。
“让教授以飞行授课的方式来国内,我们可以接触到的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师资,获得新的管理理念,将不同领域的经验打通。”SPX公司采购经理周华今年开始了他的EMBA课程,他喜欢这种授课的方式。
“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后,需要有更好的商学院教育。”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扣庆教授分析,而供需往往还达不到平衡,通过与项尖的商学院合办项目,能够搭建一个好的平台,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供需的平衡。
在他看来,华裔背景的“飞行教授”,能够带来的价值在于,他们了解最前沿的理论和实践,并且在实践的基础上进行理论的阐述,使学生能够很快更新自己的理念、方法:他们能够带来新的教学方法,这些教学方法能够帮助学校推进教学上的改革;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中国文化背景使得他们更为了解中国的经济文化,能够架起国外理论与中国经济发展之间的桥梁。
“候鸟教授”
不过,“飞行教授”对于教授、商学院、学生而言似乎不够“解渴”。2002年,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向前迈了一大步,聘请了28位华裔的讲席教授,他们分为7组,每组4人,每组每年完成一个全职教授的全年工作量。
王江教授是当时的金融组的牵头人。周林教授、来自耶鲁的陈志武教授、来自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卡尔森管理学院的张春教授等等,也都在28人名单中。
2003~2005年三年时间里,特聘教授们每年在清华大学授课、带本科生和研究生、组织和参与各种学术活动,无论从时间上和工作量上都超出了合约的约定。这段“候鸟教授”的经历,成了一个“桥梁”。
“交流不仅仅局限于师生之间。”王江说,一方面新的理念和技术被带到国内的教学中,另一方面,特聘教授们也有机会了解国内的金融市场的发展状况、和国内同行建立起合作关系。
不过,王江教授现在在国内授课的时间仍然有限,主要是MIT与国内合作的IMBA项目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与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合办的EMBA项目。但他在研究方面,对中国金融市场的问题开始投入更多的精力,如国债市场的发展、股市投资者的交易行为和外汇储备的管理。
而陈志武教授则每年有三个月住在国内,他对国内的情况有了越来越深入的了解。在一次午餐时间,他跟媒体聊的就是围绕资本市场发展所需要的法律、新闻媒体等配套的支持架构,此外,他还关心金融史特别是中国过去几百年借贷市场及其他市场跟证券业的发展到底是什么关系等等。
周林教授的“战场”则清晰地拆分成了两个。去年他受聘于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管学院任经济学院院长,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凯瑞商学院的教授工作也仍在继续。
“我每年在国内的时间大约三个月。”在一封邮件中,周林告诉记者,这样的时间安排让他的工作也变得集中起来,一除了完成美国的教学任务和交大的行政、教研工作以外,他在国内保留的教学工作,只剩下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与上海国家会计学院的EMBA项目。
周林教授从资源配置的角度解释了自己的选择,“同美国相比,显然中国在经济与管理教学方面的人才更稀缺。”他希望包括自己在内的境外学者,可以在中国发挥更大的作用。
“留驻教授”
1997年,周东生博士毕业时,就已经给自己画了一张清晰的蓝图——回到亚洲去,或是新加坡,或是香港。
“美国学生有他们的‘孙悟空’和‘白骨精’,我们有我们的‘孙悟空’和‘白骨精’。”周东生在美国5年,深感成长环境的不同,若在美国教学则会有力无处使,他想着怎么能够把前面的人生经历盘活。
而与此同时,中国的商学院教育刚刚起步,跟国际还没接上轨,“我直接回到国内,也带不回来什么特别有价值的东西。”他于是决定,去那些文化上一脉相承的地方。
1997年香港回归之前,周东生受聘于香港城市大学,次年他第一次接触中欧。5年后,因为帮助中欧推荐教授,周东生自己也成了“被猎”的对象。他因此受聘于中欧,成为早期三个“留驻教授”之一。
他最早的EMBA学生包括青啤总裁金志国、光明乳业董事长王佳芬等等,这样的经历在香港是很难得的,那里商业教育已经日趋成熟,公司最高层管理者再去读MBA或是EMBA课程已经不多见。
周东生发现,学生渴求知识,并非单单是理论,他们更需要那些拿来就用的解决方案。他后来不时给学生一些方案,比如青啤,他就提了一个创新性的渠道互换的概念,尽管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这个方案并没有付诸实施,但是对于青啤和周东生本人而言,这个概念的价值都是不同寻常的。
“我看到的是,在市场营销领域,中国是有可能诞生新的理论的。”周东生感到很兴奋。
中欧另一栋灰色教学楼的三楼,张春教授的办公室。这里堆满了书,地上、书架上、桌子上,到处都是。这些书,见证了一场迁徙。此时张春已经受聘于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从美国陆续寄来的书籍、资料正承担着他教授生涯中“承前启后”的责任。
张春与国内商学院的缘分开始于2001年,那一年,他两次接触中国的商学院,一次是在中山大学,一次是在重庆大学。
第二年,张春成为清华特聘教授。夏天的时候,他又接受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邀请,为MBA学生开了一门课。
2003年的夏天,张春又一次走上中欧国际工商学院MBA课堂讲台。随后的两年,因为家庭的缘故,他开始请长假待在上海,与中欧的接触更深了。
一年前,张春决定离开明尼苏达大学卡尔森管理学院,那时他已经在那里任教17年,为金融学终身教授。
这个决定,在他的同事周东生教授看来是充满着勇气和冒险精神的,毕竟,机会成本太高。事实上,真正把“主战场”转移到国内的华裔金融学教授,也就只有张春一个。
不过张春似乎早已经想好并且适应了这种变化,他甚至迅速地卖掉美国的房子在上海浦东买了房子。安顿好家人之后,他自己的研究也在向中国有关的方向转,除了教学、研究以外,他也开始参与到学校的行政工作中去,做学科主任、筹建金融研究中心,这一年他的工作排得满满的。
位于上海浦东金桥一条寂静街道上的中欧,的确留住了不少“飞行教授”和“候鸟教授”。
除了张春,会计学副教授丁远也是个典型的案例,2003年他来中欧上了2个月的课,2004年上了4个月的课,2005年上了5个月的课,2006年干脆下了决心,留在了中欧。在来中欧之前,他也已经是终身教授(法国HEC管理学院会计与管理控制系)。
丁远讲课生动、幽默,总是三言两语将难懂的理论简化成耳熟能详的身边事物,以至于上过他课的学生,总是想给他出个“丁教授语录”。
他早早地感受到新的挑战,学生们的开放度、视野的广阔度、考虑问题的复杂度都已经不是当年,他说,教课就像看电视连续剧,上个世纪90年代,大家看《射雕英雄传》,总是能一集不落地看下去;上个世纪90年代,学生看到案例教学感到新鲜,上课还可课堂讨论,何等满足。
而现在,海外培训对于学生都不算是新鲜事了,更不用谈在学校里用些国外案例讲讲课,再加上点“道听途说”来的中国案例“糊弄”他们了。
“你要四季都在中国,对中国非常了解,这是‘飞行员’做不到的。”
丁远成了“教学标兵”,在学生中口碑好的教授总是“稀缺资源”,找他上课的项目也特别多。EMBA项目、MBA项目、EDP项目……丁远的时间有点安排不过来,研究的计划被打乱了。
他后来找到办法,课程还是有多少力量就使多少力量,一想到学生的求知欲他就没法儿拒绝。不过他计划着,每年要雷打不动,预留出一些时间作研究。
丁远倾向于参与到跨国家地区、跨学科的研究中去。“不能闭门造车,协同作用力量大。”比如他近期的研究中,就有跟香港城市大学,跟芬兰、加拿大,跟法国等等合作的新项目。
留还是不留?
“台湾的商学院,华裔教授回流的数量很少,再不正视这个问题,15~20年内,断层就会出现。”黄钰昌忧心忡忡。
对比起来,大陆商学院的华裔教授回流状况却呈现出令人欣喜的景象。尽管整体上而言数量不多,但“留驻”的趋势却已经慢慢出现。
而面对着学生越来越“挑剔”的“口味”,李扣庆发现,教授们以“飞行”或者“候鸟”的方式,始终能够在西方的环境中更新,将之用于中国经济、商业与企业的发展,即便他们还没有作出“留驻”的决定,对商学院也是带来了不小的价值。
周林正在考虑的是,在“留驻”尚不那么可行的情况下,怎么能让“飞行教授”和“候鸟教授”做更多的事情。“对每一个商学院来说,‘飞行教授’毕竟只是‘雇佣军’,而要自己办成世界一流水平的商学院,必须有自己的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建设自己的‘常备军’。”
在他看来,切实可行的操作方法是,引进一些每年在国内可以停留时间更长一些的专家学者,其主要任务不是授课,而是帮助中国商学院培养自己的师资队伍,并且在学院的建设和发展方面出主意以及参加管理。
“事实上,对于教授而言,他们也需要在教研的过程中有相对稳定的时间段落。”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管学院EMBA项目主任过聚荣分析,根据中国和欧美商学院的学期安排,教授们有条件可以做“候鸟教授”打时间差,两边教研都不误。
“候鸟”能不能留驻?“回来”或者“不回来”?在一些教授看来这是“理性选择”,而在另外一些教授看来则是一种“情结”。
私下里,有了解中国商学院薪酬体系的人士说,排在前面的问题是薪酬,中国的商学院大多薪酬无法与境外接轨,教授们的家庭问题也难以通过福利的方式得到妥善的解决。此外,城市的污染问题无法解决,安全问题没有保障;课程任务太重、研究时间排不出来、学院缺乏研究氛围等等,都成了障碍,因此,选择就真的变得“理性”起来。
而“情结”的问题,张春感受颇深:“中国经济的发展对于教授们是机遇,最终大家还是要回来,要为中国做点事。”
丁远记得一个对他触动极深的细节,哈佛大学的开普兰教授在演讲中这样对听众发问:“知道美国为什么有TOP10、TOP5的商学院吗?因为它们是依附在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上。”
“下一个世界级的商学院必然出在中国。”丁远坚定地相信,因为他看到,中国提供的平台是如此之大,无论从个人的职业发展,还是从工作的满足程度上来看,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的商学院能够超越中国。“你能看到,自己的教研对社会、对企业有更大的影响。”张春说。
中欧正在实践一个接近于“教授治校”的方案,张春、周东生等教授都担任着行政工作。“不少教授都很熟悉国外的‘教授治校’的做法,这一做法的特点是,学校的重大决策由教授决定,它保证了学术的纯洁度。”张春介绍。
标签:中欧emba论文; 复旦mba论文; 大学论文; 商业论文; 长江商学院论文; 张春论文; 上海国家会计学院论文; mba论文; 商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