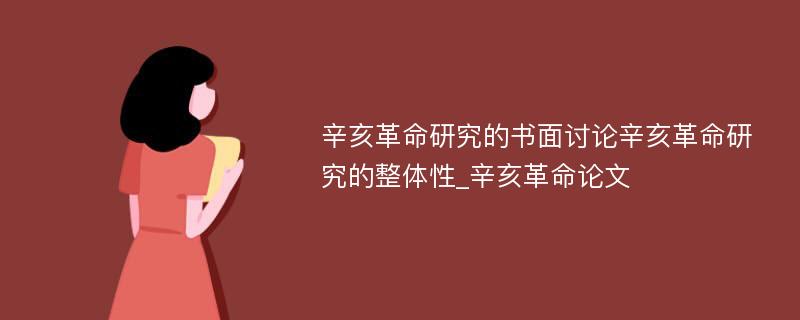
“辛亥革命研究”笔谈——1.辛亥革命研究的整体性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辛亥革命论文,笔谈论文,性问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主持人语:辛亥革命爆发迄今已整整百年。这场举世瞩目的革命虽然离我们已愈来愈遥远,但其重要意义与历史地位却并未因此而被忽略。百年以来,辛亥革命对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的重要意义,乃至在亚洲及世界范围内所产生的重大影响,一直受到广泛的关注。海内外学界对辛亥革命的研究也可谓硕果累累。在百年纪念到来之际,需要我们思考的是:辛亥革命史研究如何更加走向深入,怎样更进一步挖掘辛亥革命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为此,也需要学者们以“百年”之眼光对辛亥革命重新加以审视,从而实现辛亥革命史研究的“百年超越”。这一组笔谈,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如何扩展与深化辛亥革命史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认识与学术见解,多有启迪意义,对于促进辛亥革命史研究向纵深发展将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中图分类号:K2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1)02-0146-03
辛亥革命的研究在整个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较为成熟,表现之一,现在学人很少选取直接的题目。即使逢纪念周期的应景之作,也被质疑虽然扣题,却少新意。当然,并不是说辛亥革命的研究已经完善,只是难度较高,一般不敢轻易下手。换一角度,也可以说辛亥革命史的研究已经过了多以新材料发现新问题的初级阶段,走向摸高探深的成熟期。所面对的前贤遗留的各式难题,往往需要学人训练较好,超越前人的局限,才有可能别开生面,并达于高明的境界。不能一味钻空子找漏洞,而美其名曰填补空白;或是简单拼凑,而自诩为综合概括。
对于这样一些前人研究较为成熟的领域如何进一步深入扩展,20世纪以来不断有学人贡献真知灼见。只是倡导的结果,很难扭转热门变冷,显学退隐的趋势。后进学人,更喜欢选择由新材料新观念以发现新问题的捷径,而不愿尝试接着前贤未竟之业往下做的荆棘之路,于是将目光转向其他方面。其实,前人关注的往往是枢纽性的大问题,尽管近代学术史上不乏附庸蔚为大国的先例,时段与层面下移也呈现大势所趋,毕竟接着做更接近大道正途,更能体现学术研究的深度和高度。
中国近代史研究普遍存在的一大问题是,由于材料太多,不得不缩短战线,专题研究取代了学术准备,导致分化过细,以致不能贯通。时间上分段,空间上分区,问题上分类,专题研究的深入异化成学术视野的孔见,结果流于盲人摸象。贯通并非一般所谓扩展研究视野和领域,不是仅仅以辛亥革命为中心的延伸,而是将辛亥革命放到历史发展的时空整体联系的脉络之中,将辛亥革命作为历史的一部分,而不作为一种断代之断代史的划定;也就是说,这样的取径并非只是以辛亥革命的问题意识作范围的扩展,那样很可能结果只是辛亥革命的简单放大,而是将辛亥这一时期的历史整个放到近代中国、东亚乃至世界历史的整体中去,放到三千年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去,放到不作任何分门别类的细分化的历史本来状态中去,进行贯通式考察,用整体的历史眼光探究辛亥革命。类似辛亥这样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且对历史发展进程具有重大影响的历史时期,不仅整体意义必须古今中外地加以认识,就连具体问题要想认识得当,也非有贯通的眼光不能奏功。这样的取径做法,其实不过是前贤治史的基本,因而卑之无甚高论。只不过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现状,与之距离甚大,而其趋势,还可能渐行渐远,所以值得特别强调,以免流弊滋生,以至于不可收拾。
限于篇幅,无法展开详论,仅就若干方面,举例说明。
辛亥时期的整体性
辛亥革命研究存在一味注重革命党,忽视其他方面的偏向,早经中外学人明确指出,研究保皇党、立宪派,乃至清政府,都是补偏救弊之举。单纯从革命的角度立论,辛亥时期历史整体性的失位,不仅全局上往往漏洞百出,而且具体上容易捉襟见肘。辛亥时期革命当然处于无可争议的重要位置,但不是仅仅有革命的历史,整体把握不当,革命史的认识也难以适得其所。现行的历史分期,不免用后来的目的论取舍,而多少忽略了历史进程本来的意义。相关研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仅仅强调辛亥革命实现共和政体,而且还不过是一块招牌。这样的观念,与辛亥时期中国历史进程发生整体根本变动的实情相去甚远。清季十年也就是辛亥革命前十年间中国的全面变动,是因应千古未有之大变局的总结式变动,在整个中国历史进程中,只有周秦、唐宋的变化可与之相较,而且就变动的范围和程度而言,甚或还在前两期之上,使得中国的社会历史前后两分,承前启后。就此而论,无论革命派、保皇党、立宪派、社会人士,甚至清政府和统治集团的各派系,除少数人外,都在因势求变。只不过因为利害各异,变的取向和求的方式有所不同。各方面公开的争与暗中的合,看似相反,实则相成。而不同的利益诉求和势力争夺,使当事各方形成错综复杂的纠结关系,相互缠斗。在此观照下,各种政派、社团、群体、阶层以及人脉关系全面展现,才能前后左右贯通联系,避免以单一方面的取向为普遍准则,以就事论事为具体分析,以盲人摸象为管中窥豹。得其所哉地安放理解各方言行,不必牵强取舍、放大掩饰、以偏概全甚至故意曲解,辛亥历史时期之于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意义才有可能充分展现。
古今的连贯性
今日后学新进,常有一预设的误会,以为古文和外文都不行,反而可以治中国近代史。这样的退而求其次,便是将犯难误认为趋易,立意一偏,必然浅尝辄止,注定见识表面,学问难以达致高深程度。辛亥时期中国的知识与制度发生乾坤颠倒式的根本转折,中国人的思维与行为随之变化。而清代学问对历代进行过系统的梳理总结,清代制度又是集历代王朝体制之大成,要妥当理解把握辛亥时期,首先应该了解把握近代中国的整体,进而上出嘉道,理解把握整个清代,并且由清代而历代。所谓理解把握,不能简单地依据现成的教科书或各种通史专史,因为这些晚清尤其是辛亥时期以来源自域外的各种重新条理的系统,充其量只能说是后来的见识,而不等于所指的事实。民国以后思想学术所讲的历代,许多问题意识其实出自清代,与历代既有联系又有分别。而清季改制,并非单纯移植域外,也有自称参照唐宋的成分。诚然,清季的知识与制度转型,主要影响来自域外,可是承接知识与嫁接制度,所凭借依托的还是清朝固有。不能贯通古今,解读近人的言行,只好望文生义,格义附会,越有条理系统,去事实真相越远。凡事须知渊源流变的脉络,研究近代尤其是辛亥时期的思想学术文化以及制度问题,必须纵贯古今,才能把握得当。否则,不仅门外文谈,而且参野狐禅,而自以为见仁见智。以往研究中,诸如此类的横通之论不在少数。
内外的联系性
空间的整体性包括内外两面。前者自1970年代美国修正学派兴起,重审辛亥革命的历史进程,区域研究逐渐推广。开始主要是分省,其后逐渐下移,直到基层社会。其问题意识是中国幅员广大,各地千差万别,不可一概而论。加之在全国层面上研究问题,只能突出特定方面,而割裂史事的整体联系。所以其潜在取向为相反相成的两面,既缩小范围,又注重整体,或者说以缩小范围换取整体观照。不过,此类做法的生成,实由各国社会结构的差异,未能充分考虑中国的国情,忽略中国长期以来作为文化和社会政治集合体的整体性,一味强调区域差异,不能深究保持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各项因素(如作为文化集合体的时间长,移民文化,汉化与胡化)。如分省意识其实生成于清代,晚清以后才被强化。结果,区域研究的所谓特色大都自说自话,最终难免千篇一律,不仅不见特色,反而导致片面和放大的偏蔽,甚至出现割裂集合体各区域间基本联系的潜在危险。在整体之下研究具体,而不是简单比较各地异同,才能消除看朱成碧的成见,避免故意夸大特点,导致突出特性否定共性的误读错解。
至于对外的一面,更为重要。中国长期以天下的中心自认,近代以来开眼看世界之类的世界眼光,反而导致置自身于世界之外。辛亥时期的知识与制度全面转型,不仅形成中国历史社会文化古今的分界,而且制约着今日中国人思维行为的基本样式及取向。导致这一重大变化的,却是古往今来所有的西学、东学和中学。也就是说,中国是在逐渐成为世界一部分的过程中发生上述变化的,其密集变化的集中阶段,恰是辛亥时期。必须具有古今的纵贯和中外的横通,才能清楚准确地认识知识与制度转型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如中国进入世界,与近代东亚精神世界的共同性关系紧密。早在甲午战前20年,西周等人以朱子学应对西学,建构起东亚的新话语系统,已经决定了整个东亚近代的走向。辛亥时期大规模逆输入汉语新词和取法日本,实行包括政体、教育、外交、警察、地方自治等各种制度在内的全面改造,中国人无论其政治属性如何,其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均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这些变化,包含中西新旧的复杂纠结,未必全是进化,造成现在,却不一定具有现代性。
收稿日期:2010-11-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