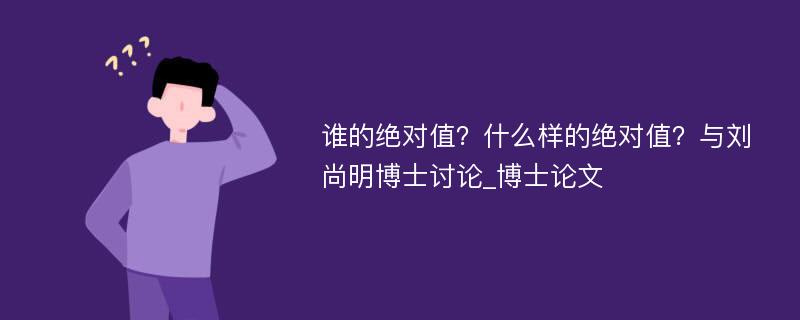
谁之绝对价值?何种绝对价值?——与刘尚明博士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价值论文,博士论文,刘尚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2)02-0159-05
当前,社会主流价值观边缘化危机已经成为我们社会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①。寻求绝对价值观念,为人们设定终极的价值目标,使不同价值观念在绝对价值观念的指引下走向统一与和谐,确实是当下人们善良的愿望。刘尚明博士和李玲的《论确立绝对价值观念——兼论对价值相对主义与价值虚无主义的批判》一文(以下简称为刘文),所表达的对绝对价值追寻的紧迫性,我们深有同感。但就刘博士对于绝对价值的意义的表征和追寻绝对价值的方式,我们想进行几点商榷:第一,“绝对价值”的主体是谁?是否存在超越于价值主体之上的“绝对价值”?第二,“绝对价值”是否存在于人的现实生活世界之外?对人的现实生活提供范导的究竟是何种价值?第三,导致价值虚无主义的究竟是价值相对主义,还是陷入“空洞的抽象”的无主体的“绝对价值”?
一、绝对价值置身于何种价值关系之中?
在对绝对价值展开讨论之前,我们有必要澄清几个基本的概念。
首先,就“价值”这个概念,我们想澄清以下认识:第一,价值是一种关系范畴。“价值这个经济学概念在古代人那里没有出现过。价值只是在揭露欺诈行为等等时才在法律上区别于价格。价值概念完全属于现代经济学,因为它是资本本身的和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最抽象的表现。价值概念泄露了资本的秘密”[1]。“这个所谓的‘秘密’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2]。马克思通过商品的二重性揭示了价值概念所反映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丰富内涵,对于我们理解哲学上的价值概念有着深刻的启示意义,即只有在关系范畴中,才能真正理解价值的含义。第二,既然价值是关系范畴,那么总离不开互相关系着的两极。石里克说:“在我们看来,价值的本质完全就在于快乐的感情”[3]。“[价值的]标准最终在于意识材料,亦即‘主观的东西’的领域,这一点本身是没有问题的”[3](P98)。他仅把价值当做主体自身的主观感受,而没有把价值的本质作为关系范畴去理解,当然不能把握价值的本质。价值作为关系范畴,其两极就是价值主体和价值客体。第三,价值是客体属性满足主体需要的现实效应。也就是说,同价值客体相对应的并不是主体本身,而是主体的需要。第四,对价值关系的深刻理解离不开评价,这种评价是价值主体对主客体之间价值关系的认识活动。通过评价活动形成了价值意识,“价值意识在主体意识中不断地反复,就会积淀为价值观念”[4]。
刘博士说:“绝对价值表述着这样一种观念:存在着一个与人相关但并不依赖于人而存在的价值世界,它强调存有和应有一些确定性的真、善、美等具有价值性质的终极原则,它们具有客观性、普遍性、一致性、确定性和非个人性”[5]。这不仅把绝对价值理解为了一种观念,而且也把绝对价值理解为“不依赖于人而存在的价值世界”。如前所述,价值是关系范畴,离开了价值关系两极中的任何一极,也就无所谓价值。价值在任何时候都不能离开主体的需要而存在,也就是说,价值在任何时候都是依赖于人的,根本不存在超越于人以上的价值世界。因此,刘文所说的“不依赖于人而存在的价值世界”只能是一种虚幻。绝对价值的“绝对”是相对于价值主体而言的,也就是与主体的绝对需要相对应。客体属性满足了主体的绝对需要,则具有绝对价值。因此,判断是否绝对价值的依据,不能到超越主体以外的世界中去寻找,而只能以主体绝对需要的满足为根据。
价值主体对于客体属性与自身绝对需要之间的价值关系的反映形成绝对价值意识。这种价值意识在主体意识中的不断反复,就逐渐积淀为绝对价值观念。
因此,要谈绝对价值观念,就要理解绝对价值关系,而厘清主体的绝对需要是我们追寻绝对价值的前提。所谓绝对,指的是不受限制的、无条件的意思。王玉樑教授在谈到价值的绝对性时说:“价值的绝对性就是价值作为客体对主体的效应存在着普遍性、无条件性、恒常性、客观性”[6]。王教授谈到的是价值的绝对性,我们不妨用这几个关于价值绝对性的规定来看主体需要的绝对性。
首先,主体需要的普遍性。也就是任何主体要存在于世都绕不开的需要,我们发现,在主体的诸多需要中,最具普遍性的就是维持生命的需要,离开维持生命的需要,也就不能作为主体而存在。其次,主体需要的无条件性。任何人只要生下来,他就有了维持生命的需要,无论主体出生的时间、地点、家庭背景如何,他都有维持生命的需要。尽管有着生存条件的不平等,但人维持自己生命的需要却具有无条件的平等性。第三,主体需要的恒常性。任何人从出生到死亡的整个过程中,始终有维持生命的需要,维持生命的需要伴随着任何人的一生。而人类社会绵延不断地发展,维持生命的需要也从来没有间断,也不能间断。第四,主体需要的客观性。主体只要存在,他就具有了维持生命的需要,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任何人无法在选择存在的同时却放弃了维持生命的需要,存在于世本身就意味着有维持生命的需要。由此可见,人的生命需要就是人的绝对需要。表征人的生命需要与客体属性之间价值关系的就是人的绝对价值;对这种绝对价值的反映形成相应的价值意识,并逐渐积淀为主体的绝对价值观念。
但我们在这里可能受到的质疑是:一旦我们把人的绝对价值理解为人维持生命的价值,那么人如何与其他生物区分开来呢?对此,我们需要对“人”的价值和“人生”的价值作些分析。
人生价值适用于价值的一般规定,但人的价值不能简单地套用价值的一般规定,因为人的生命存在本身就是价值。“人的价值是指人类在自然界中的地位和作用”[7]。尽管我们今天在大力地提倡“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但“和谐”并非地位的平等。重视自然,并不等于就把自然置于与人相等的地位,从根本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最终价值目标依然是为了人。“天地万物人为贵”,与宇宙中的万事万物相比,人的存在本身就是“贵”,就是价值。“人类的价值并非只在于存在而已。人类拥有智慧、理性和心智,正因为拥有这些特质,所以人类被称为‘万物之灵’,被视为地球上进化程度最高的生物。因此,人类内在拥有的是远比‘存在’更伟大的价值”[8]。我们在应对禽流感疫情的时候,并没有把方圆一公里范围内的鸡进行全面“体检”以区别对待,而是为了人的安全而采取了一律捕杀填埋的办法。对动物疫情采取的这种做法,在全世界是得到认可的。这本身就说明了人的生命高于任何动物的生命已经得到了全世界的认可,我们不需要再花费太多的笔墨来进行论证。由此可见,不能以动物也有维持生命的需要而否认人的生命价值的绝对性。
刘文在批判价值相对主义时引用了邸利平、袁祖社两位学者的话:“价值相对主义并不是不承认多元的‘价值’,而是不承认在众多的价值之上还有某种具有优先性和普遍性的‘绝对价值’”[5],但两位学者接着说到:“‘绝对价值’不能等同于‘最高价值’。‘最高价值’首先肯定了它自身是一种价值,它是在与其他的价值对比和角逐中确立自身的;但‘绝对价值’却可以是非价值,它并非可以仅仅以价值来涵括和替代”[9]。虽然我们不能理解两位作者是在何种意义上讲“‘绝对价值’可以是非价值”,但我们完全赞同他们关于绝对价值和最高价值的区分,因为这两种价值实际上是处于不同的论域中的。对基于生命价值的绝对价值的质疑,实际上是混淆了绝对价值与最高价值的区分。
二、作为人们生活范导的价值是什么?
“我们迫切需要唤醒关于绝对价值的自觉意识,来统一和协调各种价值观念之间的对立和冲突”,“绝对价值既是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又是人类生活的范导”[5]。刘文在这里谈到的绝对价值应该是我们理解的最高价值。最高价值是表征客体属性与人的最高需要之间的价值关系,要理解人的最高价值和最高价值观念,我们就需要理解人的最高需要。
恩格斯在《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单行本导言中写到:“通过有计划地利用和进一步发展一切社会成员的现有的巨大生产力,在人人都必须劳动的条件下,人人也都将同等地、愈益丰富地得到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发展和表现一切体力和智力所需的资料”[10]。在这里,我们可以说,人的最高需要是“发展和表现一切体力和智力”的需要。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影响甚广,马斯洛认为人的最高需要是自我实现的需要,“只有一个人类的终极价值,一个所有人都追求的遥远目标。这个目标就是被不同的著作家分别称之为自我实现、自我现实化、整合、心理健康、个别化、自主性、创造力、生产力的东西。但是,所有这些著作家都一致认为,这个目标就是使人的潜能现实化。也就是说,使这个人成为有完美人性的,成为这个人能够成为的状态”[11]。马斯洛所说的“使人的潜能现实化”与恩格斯所说的“发展和表现一切体力和智力”有异曲同工之妙。因此,我们可以把人的最高需要理解为自我实现的需要。相应地,最高价值也就是表征客体属性与人的自我实现需要之间的价值关系。追求自我实现需要的满足,也就是在寻求最高价值。
刘文说:“绝对价值不仅是人类生活追求的终极目标,而且也对人类追求价值的活动起着指引规范导向作用。我们受到我们行为与之保持紧密关系的那种价值的引导”[5]。我们承认我们的行为受与我们保持紧密关系的那种价值的引导,但我们并不认为这种价值是绝对价值。真正引导我们的是在绝对价值基础之上的最高价值。
“自我实现需要的明显的出现,通常依赖于生理、安全、爱和自尊需要的满足”[12]。就像最高需要不能凭空产生一样,最高价值也不能离开人的生活世界。黑格尔在谈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关系时说:“所以谁使用耕地,谁就是整块地的所有人。如果就对象本身承认另一个所有权,这是空洞的抽象”[13]。我们也可以说,离开对主体绝对需要和在此基础上的最高需要的满足而谈最高价值的范导,也必然导致“空洞的抽象”。今天,我们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我们正在遭遇着信仰的危机。重建信仰当然离不开一种终极价值目标的确立,但有感于历史的教训,我们确立的终极价值目标不能脱离人们现实的生活世界,而必须把最高价值目标从“天上”拉回“人间”。
刘文说:“越是普遍性、持久性的价值,越是代表了人的根本利益,对于互相对立和冲突的价值具有统一和调节作用”[5]。事实上,越是脱离人的具体需要的普遍价值,越是没有吸引力,从而难以起到对相互冲突的价值的统一和调节作用。因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14]。而以人的自我实现为实质内容的最高价值,是立足于人的多种需要满足的基础上的,是扎根于人自己的情感体验过程中的,因此能够确立起合理的信仰,“合理的信仰是扎根于自己思想或感情体验的一种坚定的信念。合理的信仰首先不是信仰什么东西,而是一种确认,这种确认是符合建筑在自己真实经历上的坚定的信念的”[15]。
与现实的人的诸多需要相对应的多元价值,势必发生冲突与对立,但以普遍的一元将诸多的多元收归囊中,也只能是一种幻想,正如黑格尔所说:“有人认为如果普遍性把特殊性的力量都吸收过来,诚如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中所阐述的那样,看来普遍性的景况会好些。但这也只是一种幻想,因为普遍性和特殊性两者都只是相互倚赖、各为他方面存在的,并且又是相互转化的。我在促进我的目的的同时,也促进了普遍物,而普遍物反过来又促进了我的目的”[13](P199)。黑格尔的论述对于我们对终极价值目标的寻求有着深刻的启示意义。终极价值目标应该是普遍的,但这种普遍性不能涵盖特殊性,更不能压制特殊性,而只能处于与特殊性相互依赖的矛盾运动中。“在市民社会中,每个人都以自身为目的,其他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虚无。但是,如果他不同别人发生关系,他就不能达到他的全部目的,因此,其他人便成为特殊的人达到目的的手段。但是特殊目的通过同他人的关系就取得了普遍性的形式,并且在满足他人福利的同时,满足了自己”[13](P197)。每一个现实的个人从自身利益出发,“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6]。而为了满足自己真正的利益,就需要满足他人的利益,黑格尔认为特殊性的个人的需要通过劳动得到满足。马克思主义也认为,在劳动作为人的第一需要的社会阶段到来之前,劳动依然是谋生的手段,也就是满足需要的手段。而劳动的过程也就是主体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过程,就是“发展和表现一切体力和智力”的过程,当然,这个过程也是通向自我实现的过程。“自我实现……可以归入人对于自我发挥和完成的欲望,是一种使它的潜力得以实现的倾向。这种倾向可以说是一个人越来越成为独特的个人,成为他所能够成为的一切”[12](P29),而同时,通过主体的劳动,满足他人和社会的需要,使得主体需要的特殊性通过自我实现需要的满足而上升到普遍性,“需要的目的是满足主观特殊性,但普遍性就在这种满足跟别人的需要和自由任性的关系中,肯定了自己”[13](P204)。
由此可见,可以作为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和提供生活范导的价值不是绝对价值,而是最高价值。由于最高价值所满足的是在绝对需要基础上逐渐激发出来的最高需要,因此也就立足了根基、脚踏了实地。这样的最高价值由于与主体的利益密切相关,因而能够让主体经由可信、确信而达到信仰的高度。
三、何种价值将导致价值虚无主义?
刘文批判的相对价值是什么呢?“相对价值是人类的一种现实生存状况的写照。诸如事物之‘用’、道德之‘善’、艺术之‘美’、科学之‘真’、人格之‘尊’以及社会的‘自由’、‘平等’、‘正义’等等都是价值的种类”[5]。如果连真、善、美、自由、平等、正义都要作为相对价值的种类进行批判,那么在此基础上追寻的绝对价值究竟是什么呢?如果说这些价值因具有不同主体的相对性而应该被超越,那么凌驾于不同主体之上的普遍的价值能是什么呢?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共产主义者并不像圣麦克斯所想像的……那样,是要为了‘普遍的’、肯牺牲自己的人而扬弃‘私人’,——这是纯粹荒诞的想法……‘共同利益’在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是由作为‘私人’的个人造成的”[17]。离开了“私人”利益的普遍价值,也就是说不以现实的个人的利益为根据的普遍价值,只能是一种虚幻。马克思在描述未来的理想社会时写到:“代替着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0](P294)。显然,在马克思所描绘的理想社会中,自由发展的是“每个人”,而非离开现实的个人的所谓“普遍整体”。以凌驾于“每个人”之上的“整体主义”作为终极目标的绝对价值观念,是一种脱离了现实的个人需要的“空洞的抽象”,由于不能在价值主体内心产生共鸣、获得共识,从而最终将走向价值虚无主义。“对于价值的相对主义而言,它不是把各种具体的、相对的价值放在与绝对价值的关系方面去说明它的合理性,而是以此掩盖、否定绝对价值,实际上否定了价值本身,导致了价值‘虚无主义的幽谷’、‘崇高的消解’和‘生存意义的丧失’,放弃了人本来可以自由地去创造的理想境界,使现代人失去了最基本的价值判断和生存方向”[5]。其实真正走向虚无的不是在刘文中被批判的相对价值,而恰恰是在刘文中被作为批判的武器的“不依赖于人而存在的”、说不清楚是一种什么价值而呈现为“镜中花、水中月”的“绝对价值”。刘文引用尼采的话说:“虚无主义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最高价值自行贬值。没有目的。没有目的的回答”[5]。尼采所说的最高价值就是人们心中的“上帝”。自启蒙以降,随着理性的崛起,人们逐渐意识到上帝只不过是“空洞的抽象”,人们心中的上帝逐渐“死”了。上帝“死”后的价值虚无主义不是价值相对主义导致的,而恰恰是长期以来用虚幻的普遍性对价值相对主义的否定而导致的。
我们同时应该重视刘文中所说的“‘崇高的消解’和‘生存意义的丧失’”,但引导人们寻找崇高的生活意义的出发点正是人们的多元价值观念。“价值相对主义困境的解决和绝对价值的寻求,最终落在现实的‘生存个体’身上”[9]。多元价值观念的价值主体能够在最高价值观念的引导和激发下寻找到崇高的生活意义,而不会导致价值虚无主义。“价值的多元化是在人类内部存在着多样化生存条件、多样化利益差别和多样化角色分工的情况下,一种不可避免的基本现象”[18]。而且在“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理想社会到来之前,这种价值的多元化都将一直存在,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实。“只承认价值的绝对性而否认相对性,就会抛弃了辩证法而陷入形而上学,就无法解释价值世界多姿多彩繁花似锦的景象”[6](P206)。
“利益总是主体活动的直接的、自觉的目的性基础。不管主体是否意识到,他总是把利益作为衡量自己与事物或他人关系的一个尺度”[18](P99)。我们把绝对价值表征为人的生命价值,那么这就与每一个现实的个人息息相关,能够在每一位价值主体内心产生共鸣,在此基础上激发出主体的高层次需要,直到最终激发出主体自我实现的需要。当自我实现的需要产生后,价值主体就会摒弃此前对低级需要的过分关注,开始以这种高级需要作为价值评价的标准,“虽然我们要在低级需要得到满足后才转而对高级需要感兴趣,但人们在满足了高级需要,并获得了价值和体验之后,高级需要会变得具有自治能力,不再依赖低级需要的满足。人们甚至会蔑视与摒弃使他们得以过上‘高级生活’的低级需要的满足”[12](P42)。而在这个过程中,主体不断对与自己不同层次需要相对应的价值关系进行评价,在绝对价值观念的基础上逐渐上升到最高价值观念。由于这整个过程都伴随着主体自身的情感体验,因此能够形成弗洛姆所说的“合理的信仰”。在主体自身中产生的这种以自我实现为内核的“合理的信仰”,能够统摄主体的各种价值观念,包括绝对价值观念。
我们需要说明的是,在不同的价值体系中,自我实现有着不同的意蕴。在以“三纲”为核心的价值体系中,个体的绝对需要就要从属于“君、父、夫”的需要,“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理念实际上在漠视着个体的绝对价值。在这样的价值体系中,价值主体的自我实现就是为“君、父、夫”的需要而献身,“君”的需要是最高需要,满足这种最高需要也就是价值主体的最高价值。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传统社会的价值体系中,人的绝对价值和最高价值是对立的。而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绝对价值和最高价值能够走向统一。因为在应然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价值主体是人民,这样的价值体系以人民的需要和利益作为出发点和旨归,使人民能够在“高天、阔海”中满足自我实现的最高需要。
哲学研究应该为人们的生活意义提供指导,否则就真成了“密纳发的猫头鹰,要等黄昏到来,才会起飞”[19]。当前,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已经为我们所共识,但核心价值观的表述还需进一步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所以不能以达成共识的方式表述出来,一定意义上正是由于我们当前社会的核心价值还不明朗,对核心价值进行反映的价值意识尚需进一步自觉。因此,我们当前追寻最高价值观念的紧迫任务就具体化为,首先以精练的语言概括出社会核心价值观,为人们处理各种价值观念的冲突提供范导,引导每一个现实的个人在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下满足自我实现的需要。
自我实现作为每一位价值主体的最高需要,是分层次的。生活于每一层境界中的人,其自我实现都有其特定的高度。比如植物人,就生活于冯友兰先生的“四个境界”中的自然境界,我们无法用在功利境界之上的其他境界中自我实现的应然要求来苛求于他,超越了他所生活的境界,对他提出的理想目标也就只能是“空洞的抽象”。
我们立足于现实的人的绝对需要和最高需要,区分了绝对价值和最高价值。绝对价值是每一个现实存在的人本身具有的价值。但最高价值却像是地平线,永无止境,永远激励着价值主体不断地奋斗、不断地超越,不停地从实然走向应然。
注释:
①《人民论坛》2009年12月发表的千人问卷调查报告未来10年10大挑战的第十项为“主流价值观边缘化危机”,36.3%的受访者选择了此项。高源、马静,《“未来10年10大挑战”调查报告》,人民论坛,2009年第12期下:14-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