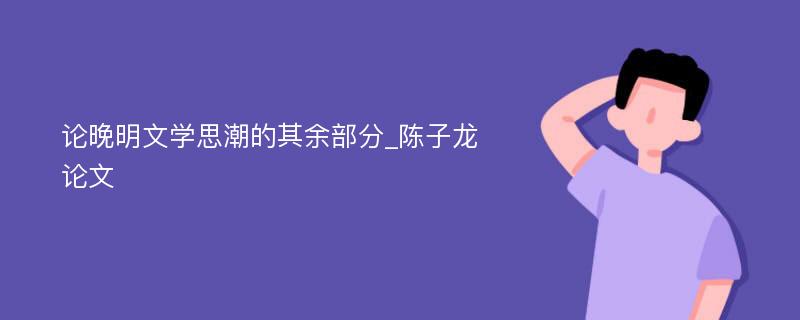
论晚明文学思潮的消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明文论文,思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所谓晚明文学思潮,指的是明代万历前后在阳明心学及泰州学派影响下所形成的一股弘扬主体、张扬个性、正视人欲为其主要精神的文学思潮。明代万历时期,以李卓吾、公安派、《金瓶梅》、《牡丹亭》、《三言》的出现为标志,把这股声势浩大的文学思潮推向高峰。而当历史步入了天启、崇祯年间,这股声势浩大的文学思潮已趋于消歇。据《明史·文苑传序》:“……汤显祖、袁宏道、钟惺之属,亦各争鸣一时,于是宗李、何、王、李者稍衰。至启、祯时,钱谦益、艾南英准北宋之矩蠖,张溥、陈子龙撷东汉之芳华,又一变矣。”那么,晚明时期那股声势浩大的文学思潮为何骤尔消歇?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一
晚明文学思潮消歇的原因,首先导源于东林学派对阳明心学的反拨。嵇文甫先生在《晚明思想史论》中指出:“明代思想解放的潮流,从白沙发端,及阳明而大盛,到狂禅派而发展到极端。于是乎引起各方面的反对,有的专攻击狂禅或王学左派,有的竟直接牵涉到阳明,这里面最有力量能形成一个广大潮流的,要首推东林派。……其代表人物为顾泾阳与高景逸。”
晚明文学思潮的兴起,导源于阳明心学及在阳明心学影响下所形成的泰州学派。这主要是因为阳明心学及泰州学派为晚明文学思潮提供了哲学基础。而东林学派对阳明心学及泰州学派的批判,形成了对晚明文学思潮的釜底抽薪之势,从而导致了这股文学思潮的消歇。
阳明心学以“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注:王守仁《答顾东桥书》,《王阳明全集》卷二,上 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用“良知”取代了“天理”的地位,在弘扬了主体意识的同时,又导致了对程朱理学的反拨,从而使阳明心学成为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哲学思潮。这一点《明史》卷二百八十二之《儒林》说得很清楚:“宗守仁曰姚江之学,别立宗旨,显与朱子背驰,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而东林学派对阳明心学的批判,则是以力避“良知”之说,复兴程朱理学为宗旨的。
据《明史·顾宪成传》云:“宪成姿性绝人,幼即有志圣学。暨削籍里居,益覃精研究,力辟王守仁无善无恶心之体之说。”黄宗羲《明儒学案·端文顾泾阳先生宪成》叙其论学主旨曰:“先生深虑近世学者,乐趋便易,冒认自然,故于不思不勉,当下即是,皆令究其源头,果是性命上透得来否?而于阳明无善无恶一语,辩难不遗馀力,以为坏天下教法,自斯言始。”如顾宪成在《证性篇·罪言上》中说:
以为心之本体原来是无善无恶也,合下便成一个空。……空则一切解脱,无复挂碍。高明者入而悦之,且从而为之辞曰:理障之害甚于欲障。于是乎委有如所云:以仁义为桎梏,以礼法为土苴,以日用为尘缘,以操持为把捉,以随事省察为逐境,以讼悔迁改为轮回,以下学上达为落阶级,以砥节砺行、独立不惧为意气用事者矣。
而对于朱熹,顾宪成则予以极高的评价,在《小心斋札记》中,顾宪成高度肯定了朱熹在儒学史上的地位:“孔子表章六经,以推明羲、尧、诸大儒之道,而万世莫能易也。朱子表章《太极图》等书,以推明周、程诸大儒之道,而万世莫能易也。此之谓命世。”
又据《明史·高攀龙传》:高攀龙“有志程朱之学”,黄宗羲《明儒学案·忠宪高景逸先生攀龙》也说:“先生之学,一本程、朱,故以格物为要。”如《高子遗书》卷一之《语》曰:“朱子曰:‘致知格物,只是一事。格物以理言也,致知以心言也。’由此观之,可见物之格即知之至,而心与理一矣。今人说著物,便以为外物,不知不穷之其理,物是外物,物穷其理,理即是心。故魏庄渠曰:‘物格则无物矣。’”正是出自对程、朱的推崇,高攀龙辑有《朱子节要》一书,在《朱子节要序》中高度评价了朱熹在儒学史上的地位,认为“朱子功不在孟子之下”:
圣人之道,自朱子出而六籍之言乃始幽显毕彻,吾道如日月之经天,江河之流地。非独研穷之勤,昭析之密,盖其精神气力真足以柱石两间,掩映千古,所谓豪杰而圣贤也。(注:高攀龙《朱子节要序》,《高子遗书》卷九,文渊 阁本《四库全书》。)
并在《崇文会语序》中说:“崇文者何?崇文公朱子也。”正是出于对朱熹的推崇,高攀龙对阳明心学的流弊进行了批判:
姚江之弊,始也扫闻见以明心耳,究且任心而废学,于是乎诗书礼乐轻而士鲜实悟;始也扫善恶以空念耳,究且任空而废行,于是乎名节忠义轻而士鲜实修。(注:高攀龙《崇文会语序》,《高子遗书》卷九,文渊 阁本《四库全书》。)
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顾宪成、高攀龙、顾允成、钱一本等,重建东林书院,从事讲学活动。在讲学过程中,以复兴程朱理学,矫正王学流弊为己任,对阳明心学及后学,尤其是泰州学派的学术思想进行了批判。在顾宪成和高攀龙的文集中,对王畿、罗汝芳、颜山农、李贽、何心隐、周汝登、陶望龄、管志道等人的学术观点进行了不同方式,不同程度的反驳,直接导致了明代心学思潮的消歇。同时,东林学派又是一个关注现实政治的学派,东林书院的那幅著名的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就是东林学派学术精神的典型写照。由于他们在讲学之余议论朝政,裁量人物,并与在朝正直官员赵南星、邹元标、李三才等互通声气,这样就使这一学派具有极浓的政治色彩,而被称之为“东林党”。在天启年间对阉党的斗争中,东林党人以名节相砥砺,追求高洁的人格。天启六年(1626年),阉党魏忠贤下令逮捕高攀龙、周顺昌、缪昌期、李应升、周宗建、黄尊素、周起元等七人。缇骑将至,高攀龙“夜半书遗疏,自沉止水”,疏云:“臣虽削夺,旧系大臣,大臣受辱,则辱国。故北向叩头,从屈平之遗则。”(注:黄宗羲《忠宪高景逸先生攀龙》,《明儒学案》卷五十八,中华书局1985年版。)“一堂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忠义之盛,度越前代,犹是东林之流风余韵也。”(注:黄宗羲《东林学案一》,《明儒学案》卷五十八,中华书局1985年版。)东林党人在与阉党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忠肝义胆和高风亮节,对当时的社会风气也产生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影响。
据黄宗羲《明儒学案·端文顾泾阳先生宪成》“甲辰(1604年),东林书院成,大会四方之士,一依《白鹿洞规》。其他闻风而起者,毗陵有经正堂,金沙有志矩堂,荆溪有明道书院,虞山有文学书院,皆捧珠盘,请先生蒞焉。先生论学,与世为体。尝言官辇毂,念头不在君父上;官封疆,念头不在百姓上;至于水间林下,三三两两,相与讲求性命,切磨德义,念头不在世道上,即有他美,君子不齿也。故会中亦多裁量人物,訾议国政,亦冀执政者闻而药之也,天下君子以清议归于东林。”高攀龙门人周彦在《论学语序》中也说:“自顿悟之教炽,而实修之学衰。嘉隆以来,学者信虚悟而卑实践,……视居敬为拘囚,目穷理为学究;恶言工夫,托之本体,更不知操存为何物矣!斯文未丧,东林代兴。高景逸先生心程、朱而脉孔、孟,拜官之日,首辟世则张子之邪说,使程、朱之学而复明。未几罢官,归里三十年,与泾阳顾先生辈力扶正学、专事实修。”东林学派的崛起,在各地迅速引起反响,程朱传统因之得以恢复,并取代了阳明心学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主导地位。据清人胡慎《东林书院志序》:
姚江之学大行,而伊洛之传几晦,东林亦废为丘墟。至万历之季,始有端文顾公、忠宪高子振兴东林,修复道南之祀,仿白鹿洞规为讲学会,力阐性善之旨,以辟无善无恶之说,海内翕然宗之,伊洛之统复昌明于世。
叶裕仁在《高子遗书跋》中也说:
明正、嘉之际,王学炽行,洎于隆、万倡为三教合一之说,猖狂恣肆,无所忌惮,学术之裂极矣。公(指高攀龙)与顾端文公起而拯之,辟阳儒阴释之害,辩姚江格物致知之谈,其深切明著,由是绝学复明。
由上述记载可以看出,东林学派对阳明心学的批判和程朱传统恢复,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从而使明代心学思潮迅速走向低谷,这无疑是导致晚明文学思潮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
随着东林学派的崛起和阳明心学的消歇,在文学上也出现了复古思潮的复兴。而明末复古思潮的复兴,则是导致晚明文学思潮的消歇的另一个原因。
晚明文学思潮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对明代中叶所出现的以“前、后七子”为代表的复古主义文学思潮的批判。从“童心说”出发,李贽指出:“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者焉也。苟童心常存,则道理不行,闻见不立,无时不文,无人不文,无一样创制体格文字而非文者。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注:李贽《童心说》,《焚书》第99页,中华书局1975年版。)。以文学创作中“童心”的强调,批判了“前后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主义主张。袁宏道则在《叙小修诗》中明确地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以对“性灵说”的倡导,对当时文坛上的剿袭模拟之风进行的尖锐的批判:“盖诗文至近代而卑极矣,文则必欲准于秦、汉,诗则必欲准于盛唐,剿袭模拟,影响步趋,见人有一语不相肖者,则共指以为野狐外道。曾不知文准秦、汉矣,秦、汉人曷尝字字学《六经》欤?诗准盛唐矣,盛唐人曷尝字字学汉、魏欤?秦、汉而学《六经》,岂复有秦、汉之文?盛唐而学汉、魏,岂复有盛唐之诗?唯夫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所以可贵,原不可以优劣论也”(注:袁宏道《叙小修诗》,《袁宏道集笺校》第18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李贽的“童心说”、袁宏道的“性灵说”,以文学创作中的主体意识和个性精神的倡导,扭转了当时文学创作中的复古模拟风习,从而形成了晚明诗文“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创作格局。这一点,诚如钱谦益所云:“万历中年,王、李之学盛行,黄茅白苇,弥望皆是。文氏、义仍,崭然有异,……中郎之论出,王、李之云雾一扫,天下文人始知疏瀹心灵,搜剔慧性,以荡涤模拟涂泽之病,其功伟矣。”(注: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第56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59年版。)袁中道在《中郎先生全集序》中也肯定了乃兄对当时创作风气的转变:“一洗应酬格套之习,而诗文之精光始出,……至于今天下之才士,始知心灵无涯,搜之愈出,相与各呈其异,而互穷其变,然后人人有一段真面目溢于楮墨之间。”而到了明代末年,随着一批以复古为职志的文社的出现,形成了明代文学复古思潮的复兴。“明之末年,中原云扰。而江以南文社乃极盛。其最著者,……陈子龙倡几社,承王世贞等之说而涤其滥。溥与张采倡复社,声气蔓衍,几偏天下”(注: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九,中华书局1959年版。)。这股复古思潮的复兴,则是导致晚明文学思潮消歇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据《明史·夏允彝传》:“时东林讲席盛,苏州高才生、张溥、杨廷枢等慕之,结文会名复社,允彝与同邑陈子龙、徐孚远、王光承等亦结几社相应和。”作为东林学派影响文学创作的产物,明末文社的大量出现,推动了当时复古思潮的复兴。而在这些文社中,影响较大的有以张溥为代表的复社和以陈子龙为代表的几社。
张溥于崇祯初年创建复社,复社其命名的由来,即在于复兴古学。据杜登春《社事始末》:“复者,兴复绝学之义也。”其实,在创建复社之前,张溥还组织了应社。据张溥《五经徵文序》:“应社之始立也,所以志于尊经,复古者盖其志也。”可知“尊经复古”就是张溥创建文社的主要宗旨,张溥在《程墨表经序》阐发了这一思想:
夫好奇则必知古,知古则必知经,知经则必知所以为人。至于知所为人,而文已毕精矣。故驳而不纯之文,予所甚恶也;才而不德之士,亦予所甚恶也。
与张溥创立复社的同时,陈子龙创立了几社。几社命名的由来,据杜登春《社事始末》,“几者,绝学有再兴之机,而得知其神之义也。”姚希孟《壬申文选序》亦云:“近有云间六、七君子,心古人之心,学古人之学,纠集同好,约法三章。”可见几社的建立,也旨在“心古人之心,学古人之学”。这一主张在陈子龙的《壬申文选凡例》得到集中的体现:
文当规摹两汉,诗必宗趣开元。吾辈所怀,以兹为正。至于齐梁之瞻篇,中晚之新构,偶有间出,无妨斐然。若晚宋之庸沓,近日之俚秽,大雅不道,吾知免矣。
杜登春《社事始末》云:“两社(复社、几社)对峙,皆起于己巳岁。”可知复社与几社的活动,始之于己巳岁,即崇祯二年(1629年)。两社的文学主张虽然不尽相同,但复兴古学,则是他们的共同宗旨。基于这一宗旨,他们肯定了“前、后七子”的复古主义创作。如陈子龙在《六子诗序》中说:“献吉、仲默、于鳞、元美,才气要亦大过人,规摹昔制,不遗余力,苦加推驳,可议甚多。今人之才又不如诸子,而放乎规矩,猥云超乘,后世可尽欺耶!”而对公安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创作倾向则进行了较为尖锐的批判:
夫诗衰于宋,而明兴尚沿余习,北地、信阳力返风雅;历下、瑯琊,复长坛坫,其功不可掩,其宗尚不可非也。……后人自矜其能,欲矫斯弊者,惟宜盛其才情,不必废此简格,发其眑渺,岂得荡然律吕。不意一时师心诡貌,惟求自别于前人,不顾见笑于来祀。此万历以还数十年间,文苑有罔两之状,诗人多侏俪之音也。(注:陈子龙《仿佛楼诗稿序》,《陈忠裕公全集》卷二十五,嘉庆八年刊本。)
一方面,陈子龙肯定了李梦阳、何景明、李攀龙、王世贞“复长坛坫,其功不可掩”;同时又批判了公安派“废此简格”,“荡然律吕”,“一时师心诡貌,惟求自别于前人,不顾见笑于来祀”。在《答胡学博》中,陈子龙还要求诗歌创作效法“古人所为”,并从这一角度出发,对万历末年“祖述长庆”,“学步香奁”的诗风进行了反拨:“万历之季,士大夫偷安逸乐,百事堕坏,而文人墨客所为诗,非祖述长庆,以绳枢瓮牖之谈为清正,则学步香奁,以残膏剩粉之资为芳泽,是举天下之人,非迂若老儒,则柔媚若妇人也。……然古人所为温厚之旨,高亮之格,虚响沈实之工,珠联璧合之体,感时托风之心,援古证今之法,皆弃不道”。明末复古文社对公安派的批判引起了当时诗文创作风气的变化,今卧子出,而言诗之家又为一变。纵横浩达,于学无所不窥。雄深凄惋,尤极于古。……及为歌诗,本于性情,该以学问,其言无不似古人,而又无古人得似之”(注:周立勋《岳起堂诗稿序》,《陈忠裕公全集》卷首,嘉庆八年刊本。)。明末复古思潮的复兴,无疑也意味着晚明时期弘扬主体、张扬个性、正视人欲的文学思潮的消歇。
三
如果说,东林学派的崛起和复古思潮的复兴构成的晚明文学思潮消歇的外因,那么,晚明文学思潮的消歇还有其深刻的内在原因,那就是晚明文学思潮自身所面临的矛盾与困惑。黄宗羲在《明儒学案·泰州学案一》中分析明代心学思潮盛行和消歇的原因时说:
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亦因泰州、龙溪而渐失其传。泰州、龙溪时时不满其师说,益启瞿昙之秘而归之师,盖跻阳明而为禅矣。然龙溪之后,力量无过龙溪者,又得江右为之救正,故不至十分决裂。泰州之后,其人多以赤手搏龙蛇,传至颜山农、何心隐一派,遂复非名教所能羁络矣。顾端文曰:“心隐辈坐在利欲胶漆盆中,所以能鼓动得人,只缘他一种聪明,亦自有不可到处。”羲以为非其聪明,正其学术也。所谓祖师禅者,以作用见性。诸公掀翻天地,前不见古人,后又不见有来者。释氏一棒一喝,当机横行,放下拄杖,便如愚人一般。诸公赤身担当,无有放下时节,故其害如是。
阳明心学之所以“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乃至于“诸公掀翻天地,前不见古人,后又不见有来者”,主要是由于王艮、王畿一派主张张扬个性,正视人欲;而阳明心学之所以“因泰州、龙溪而渐失其传,”乃至于“一棒一喝,当机横行,放下拄杖,便如愚人一般”,主要是由于个性与人欲一旦到达“非名教所能羁络”的地步,而“无有放下时节,故其害如是”。个体意识的张扬无疑引起了对束缚人性的传统礼法的冲击,但个体意识一旦脱离道德的轨道而任其放纵,必将导致社会关系的失调和人际关系的混乱。对人的合理欲望的正视无疑引起对程朱理学禁欲主义的批判,但人的欲望一旦失去应有的规范而发展为人欲横流,必将形成对群体利益的损害而阻碍社会的进步和人类的完善。个体意识的张扬和合理人欲的正视引起了对传统价值体系的冲击,而在传统价值体系开始解体,新的价值体系尚未建立的时代,矛盾与困惑就成为这样一个新旧交替时代的历史必然。如泰州学派中较为激进的人物颜山农,一方面主张“性如明珠,原无尘染,有何睹闻?著何戒惧?平时只是率性所行,纯任自然,便谓之道”,同时又要求“及时有放逸,然后戒慎恐惧以修之”(注:黄宗羲《泰州学案一》,《明儒学案》卷三十二,中华书局1985年版。)。因而,晚明文学思潮一方面表现出对个体意识的张扬和合理人欲的正视,同时又对那个时代由于个体意识的张扬和合理人欲的正视所引起的私欲放纵与人欲横流的社会现象表现出深沉的忧虑。怎样匡正由于个体意识的张扬和合理人欲的正视所引起的私欲放纵与人欲横流,使个体意识和合理人欲朝着有利于社会进步和人类完善的方向发展,是当时每一个有良知的作家都必须面临的问题。而在那个新的价值体系尚未建立的时代,从传统的价值系统中寻找参照系以匡正那个放纵私欲、人欲横流的社会,就成为当时的人们别无选择的选择。
因而,晚明文学思潮一方面以个体意识的张扬和合理人欲的正视表现出对传统价值体系的反叛,同时又不得不用传统的价值体系来匡正由于个体意识的张扬和合理人欲的正视所引起的私欲放纵与人欲横流的社会。李贽大胆地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但却难以提出评判是非的价值准则。“人之是非初无定质,人之是非也无定论。无定质,则此是彼非,并育而不相害;无定论,则是此非彼,亦并行而不相悖矣”(注:李贽《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前论》,《藏书》第7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而在评价《昆仑奴》时,他仍然用传统纲常评价人物:“自古忠臣孝子,义夫节妇,同一侠耳”(注:李贽《昆仑奴》,《焚书》第194页,中华书局1975年版。)。汤显祖在《牡丹亭》中以对杜丽娘和柳梦梅之间“理之所必无,情之所必有”的真挚爱情的歌颂,表现出对传统道德和对程朱理学的尖锐批判。但在《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中却极力强调戏曲的伦理功能和名教作用:“可以合君臣之节,可以浃父子之恩,可以增长幼之睦,可以动夫妇之欢,……为名教之至乐哉”。在《董官贞赞并传》中,汤显祖描写了一个夫死守节,最后自经而死的列女董官贞的形象,且赞之曰:“董得嘉名,名曰官贞。岂缘渭浊,故作冰清。凡今之人,尽谓老成。谁言季女,一誓无倾。”并在《南昌学田记》主张以“礼义”治天下:“是故圣王治天下之情以为田,礼为之耜,而义为之种。然非讲学,亦无以耨也。于是乎获而合之仁,安之乐,至于食之肥,而天下大顺。嗟夫,天下之于一邑也,一而已矣。”《金瓶梅》的作者在第一回就开宗明义地指出:“情色二字,乃一体一用。故色绚于目,情感于心,情色相生,心目相视。亘古及今,仁人君子,弗合忘之。晋人云:‘情之所钟,正在我辈。’如石吸铁,隔碍潜通。无情之物尚尔,何况为人终日在情色中做活计?”并以真实的描写,展示了人情物欲对“天理”、“纲常”的冲决,表现出对人情物欲的大胆认识和勇敢正视;同时,作者又喋喋不休地劝告人们:“酒色多能误邦国,由来美色丧忠良”,“贪财不顾纲常坏,好色全忘义理亏”,希望以“天理”、“纲常”来拯救那个人欲横流的社会。冯梦龙在《叙山歌》中提出“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要求通过男女之间真情实感的表现,以揭示封建伦理纲常的虚伪,并在《三言》中以对真挚爱情的歌颂和合理人欲的肯定,显示出对传统伦理的悖戾。但在《古今小说序》中却强调小说的伦理教化功能,“试令说话人当场描写,可喜可愕,可悲可涕,可歌可舞;再欲捉刀,再欲下拜,再欲决脰,再欲捐金。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虽小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并在《警世通言序》提出:“六经、《论语》、《孟子》,谭者纷如,归于令人为忠臣,为孝子,为贤牧,为良友,为义夫,为节妇,为树德之士,为积善之家,如是而已。经书著其理,史传述其事,其揆一也。……而通俗演义一种,遂足以佐经书史传之穷。……说孝而孝,说忠而忠,说节义而节义”。通过小说创作教忠教孝,以匡正世风。袁宏道继承了李贽的“童心说”而提出了“性灵说”,在生活中和创作上表现出对个性的张扬,但据袁中道《吏部验封司郎中中郎先生行状》,戊戌(1598年)之后,“先生(指袁宏道)之学复稍变,觉龙湖等所见,尚欠稳实。以为悟修犹两毂也,向者所见,偏重悟理,而尽废修持,遣弃伦物,偭背绳墨,纵放习气,亦是膏肓之病。夫智尊则法天,礼卑而象地,有足无眼,与有眼无足者等。遂一矫而主修,自律甚严,自检甚密,以淡守之,以静凝之”。对以往“遣弃伦物”,“纵放习气”表示忏悔,于是“一矫而主修,自律甚严”。一方面,这些思想的先行者们对传统的“名教”、“天理”进行猛烈的抨击,但当社会一旦冲破传统的道德规范而走向倾斜和失调的时候,寻找一种新的行为规范维系世风必然成为人们的价值渴望,而残存于人们记忆中的传统的价值体系便提供了最方便、最现成的参照系统,矛盾与困惑于是成为新旧嬗变之际的历史必然。也正是这种矛盾与困惑,才最终导致了晚明文学思潮的消歇。
那么,个体意识得以张扬和合理人欲得以正视之后,人们应该以怎样的方式避免私欲的放纵与人欲的横流,以保障人类自身的完善和社会的进步发展?也许,晚明文学思潮的消歇留给我们的,是一个更应该引起注意,并值得去深入研究的课题。
标签:陈子龙论文; 儒家论文; 文学论文; 读书论文; 文化论文; 心学论文; 明儒学案论文; 国学论文; 高攀龙论文; 袁宏道论文; 东林党论文; 复古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