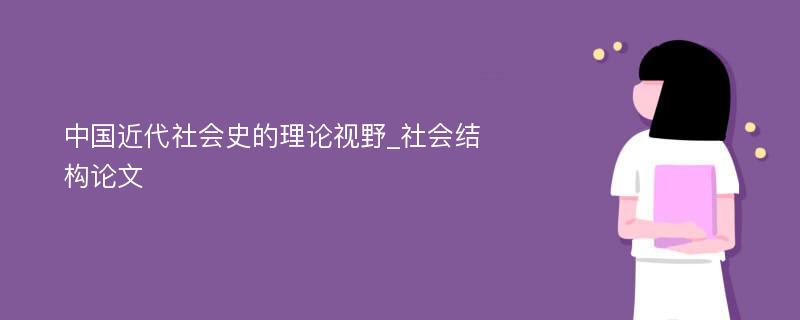
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理论视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野论文,中国近代论文,理论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若干理论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或构想,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教正。
一、社会史、中国近代社会史及其他
社会史作为一门学科,它的历史并不算长,如从1929年法国历史学家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创办《经济社会史年鉴》杂志算起,迄今还不到70年。至于与社会史相关的内容的研究,当然要早得多。
那么,什么是“社会史”?这个问题至今未达成共识。在西方,社会史这一术语一直难以界定,直到1985年英国《今日历史》杂志还专门组织文章加以讨论,异见纷呈。因此,社会史是以“灰姑娘”的面貌出现在人们的面前。
社会史概念,在西方,过去至少在三种意义上重叠使用。第一,社会史是关于穷人或下层阶级的历史,特别是关于穷人运动(“社会运动”)的历史;第二,比较普遍的,常常把“社会”与“经济史”合用,必须承认,这种结合中经济所占篇幅大大超过一半;第三,G·M·屈维廉在他的《英国社会史》一书中提出的社会史是“除去政治的人民史。”(注:〈英〉E·J ·霍布斯鲍姆:《从社会史到社会的历史》载蔡少卿主编:《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这个定义实际上包含了两重意义:一是政治史以外的历史都是社会史研究的范畴,二是“人民史”是社会史的核心。
在中国,南开大学冯尔康教授、山西大学乔志强教授都曾给社会史作过界定。冯尔康先生认为:社会史是研究历史上人们社会生活的运动体系。具体地说则是:社会史是以人们的群体生活与生活方式为研究对象,以社会结构、社会组织、人口、社区、物质与精神生活习俗为研究范畴,揭示它本身在历史上的发展变化及其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和地位;它是历史学的一个专门史,以其开拓历史研究领域,促进历史学全面地系统地说明历史进程和发展规律;它与社会学、民俗学、民族学、人口学等学科有交叉的内容,具有边缘学科的性质。(注:冯尔康等:《中国社会史研究概述》天津教育出版社1988 年版,第2—3页。)冯先生的定义包含了社会史的研究对象、范畴、任务、功能及社会史与历史学其他专史、其他学科的关系等内容。
乔志强先生认为,社会史研究的对象是社会的历史,但不是包罗政治、经济、文化等在内的所有社会现象的历史,而是研究人类有史以来赖以生存并必然结成的社会本身的历史。有史以来,人们从来不能单个生活而是在人们结成的社会中生活,它本身有其发展变化的历史,这就是社会史,它由社会构成、社会生活、社会功能三个部分组成。(注:乔志强主编:《中国近代社会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第2—3页。)
上述可见,人们对社会史的理解是不尽相同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里也谈谈我对“社会史”的理解。
“社会史”,毫无疑问,是历史学的分支,我们可称之为“社会历史学”,它同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思想史、文化史等,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作为一门专史,它既有相对独立性,同时又是通史的组成部分,这是中外学者一致的看法。这是应该明确的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无论中国学者,还是西方学者,总是把“社会史”踢出社会学的门户之外。笔者则持不同看法。我认为,社会史是社会学的一门边缘学科,我们可称之为“历史社会学”,社会学研究的对象社会结构——个人、家庭、群体、组织、阶级阶层、民族、社区,和社会过程——社会互动、社会变迁,往往需要站在现实和历史的交汇点上,去再现过去,这就是社会史所要研究的主要内容。第三个方面,“社会”一词,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早有记载,从语言学的意义上,我们或能够引伸出社会史研究的某些方面。“社”是周秦时代的“土地神”。《神契》谓“社者土地之神,能生五谷”;《白虎通》说:“人非土不立,土地广博,不可遍敬也,故封土为社而祭之,示有土尊。”“社”即由此而来。“二十五家为社”应该是村落形成的原始意义。祭祀“社”神的活动也逐渐形成一种风习,这种风习世代相沿,成为中国农民日常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相传阴历二月二日为土地神生辰,这一天也就成为农民一岁中的重大节日之一。我们可以摭拾几段文字,以见其情形。
——“习俗相传,二月二日,为土地神之生辰,阜宁农人,以为土地是管理禾苗之人,我辈希望禾苗之盛旺,应该致敬,祈伊暗中默佐,免受风雹螟蝗之灾。阜宁人对于土地之供奉,颇为郑重,大村庄,均筹集公款,起造土地祠宇,小村庄无钱力起造祠宇者,则用粗瓦缸一只,将缸之近口处,敲成长方洞门,覆之于地,将土地版位,供之于内,权当土地之祠宇,而其所敲之缺处,则祠门也。谚云:土地老爷本姓张,有钱住瓦屋,没钱顶破缸,即此之谓也。”(注: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第3卷,《阜宁二月二日之三件事》。)
——“二月初二日,土地神诞辰,纸札铺剪纸为袍,而粉绘之。人家买以作供,大街小巷,供当方土地,张多灯于神前,人窃其灯以送妇人不育者,苟怀孕,则来年诞辰,一以奉十,而还灯于神前,悬署福祠旁,搭草台,演土地戏,是日家家接女,留之过宿,二月空房不忌矣。”(注:同上第3卷,《仪征岁时记》。)
——“二月二日为土地会,鼓乐喧天以迎土地,家家必礼之,宴会一堂,宴罢继之以博,尽欢而散,会费公派。”(注:同上第6卷,《武昌之岁时》。)
由此可见祭祀土地盛况之一斑。在汉族聚居的地方,几乎找不到没有土地庙的村落。祭祀土地,是一项集体活动,这就是“会”的本来意义:“集会”。总之,“社会”一词包含了神灵崇拜、民间信仰、乡土意识、风土民情,以及在这种社会活动中所形成的人际关系等,所有这些,都是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由此我们可以把“社会”引伸为“社会生活”的代名词。社会生活理所当然是社会史研究的主要对象。
根据上述,可以作这样的归纳:所谓社会史是研究社会的历史;它既是历史学的分支学科,也是社会学的边缘学科;社会结构、社会过程和社会生活是它研究的主要对象。社会史的定义明确了,那么,什么是中国近代社会史也就不言而喻了。中国近代社会史是中国社会史的断代史,它所研究的对象是近代历史条件下的社会结构、社会过程和社会生活。当然,这里所讲仍不全面。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尝试建构较为完整的社会史学科体系。
二、中国近代社会史的学科体系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的学科体系,中国近代社会史也不能例外。通过对学科体系的构建,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研究内容就会清晰可见。
有关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理论框架,乔志强先生和已故著名历史学家陈旭麓先生都作过有益的尝试。1986年乔先生在《光明日报》(8月 13日)发表《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对象和方法》一文,初步勾勒出他关于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理论模式,随后在他主编的1992年5 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社会史》一书中,基本完成了他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理论体系。”乔先生的理论体系,有三个有机组成部分:一、社会构成,包括人口、婚姻、家庭等最基本的社会元素和细胞;二、社会生活,包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以及错综复杂的社会诸关系,它们组成了社会的网络式的内容;三、社会职能,它包括教育、教养、社会控制等。陈旭麓先生的观点有所不同,1989年《华东师大学报》第5 期发表陈先生遗文《略论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提出了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理论模式。他认为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主要有三个方面:一、社会结构,如行会、家族、会党等,要研究社会结构在百年近代历史中的嬗递变迁;二、社会生活,除直接关系和影响着最大多数人民生活的清代“四大政”(赋税、漕粮、盐政、河工)外,更值得注意的是人们衣、食、住、行在一百一十年间的变化;三、社会意识,他认为不是从社会精英的意识,而是从民众的社会意识着手去研究近代社会历史。乔、陈两位先生的近代社会史理论构架虽有较多的歧异和各自的特征,但对笔者的认识均多有启发。
下面谈谈我个人的一点看法。
我们可以把近代中国社会视为一个整体,这个整体,我以为可由四大子系统构成,这四大子系统,除上文论及的社会过程、社会结构、社会生活外,还有一个社会问题及调节控制系统。社会问题是社会史研究的重要方面。如果对此不加重视,中国近代社会史就不能很好地发挥它的社会功能。在这四大子系统中,各个系统又有自己的组成要素,由此构成一个系统网络。
先看社会过程。社会过程,是研究社会的纵向关系,其中最主要的是社会变迁。近代社会是一个扭曲变形的特殊的社会,这种特殊性表现在社会性质上,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是近代社会的基本面貌,不了解这个扭曲过程,就无法把握近代社会跳动的脉搏,也不可能很好地重现近代社会生活。因此,可以把社会变迁(实即社会过程)视为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纵向线索。一般来说,社会变迁是由于生产方式的变革而引起的社会形态的变化,这种具有根本性的变化就是社会变迁。实际上,社会变迁的内容是多方面的,社会形态的变更是社会变迁,价值观念、社会结构、生活方式、行为规范等的变化也是社会变迁。为便于研究,可以把社会结构的变迁归入社会结构系统,把行为规范、生活方式的变迁归入社会生活系统。
社会变迁的形式表现在外力冲击与中国的回应上。外力冲击是指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中国回应是指中国为抵御外国侵略所采取的应变方式,直接抗击是一个方面,而与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关系最密切的是社会改良和社会革命。社会改良又称社会进化,是社会的自我调节形式;社会革命则是用极端手段对整个社会进行改铸的重大历史变革。这两种形式及其与近代社会演进的互动关系,应是近代社会变迁研究的基本内容。
再看社会结构。社会结构是指支撑或维系社会整体的各组成部分之间的比较稳定的构成方式,或者说是组成社会的基本要素,这些要素就象人体骨架支撑人体一样支撑着整个社会,由此构成社会结构系统。
社会结构有社会的实体结构和社会的文化结构之分。这里所讲的社会结构是指社会的实体结构。构成社会的基本元素有人口、家庭、宗族、社区、民族、阶级阶层。有了这六个方面,还不能说就是一个社会整体,因为社会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就象一台机器一样,有许多零部件组合而成。除了六大元素之外,我们还可以列举出诸如社会组织、社会群体以及次生社会集团等。但是,通过对六大元素的细化研究,我们可以了解近代中国社会的基本面貌。
如果我们把上述六大元素看作是社会结构的“部件”,那么,各“部件”还有许多“零件”(具体的研究内容),比如“人口”,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中国近代人口,主要研究人口素质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人口分布的态势、人口的自然构成、社会构成、职业构成、人口迁移流动等等。限于篇幅,此处不一一赘述。
再看社会生活系统。社会生活是在一定生产方式基础上人们结合起来的共同活动过程。社会生活主要分为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物质生活,侧重于衣、食、住、行的习惯和方式的研究;精神文化生活主要研究民间宗教信仰、岁时风俗、文化娱乐等。研究社会,离不开人的交往。因此,人际关系也是社会生活研究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人际关系是人和社会关系的核心,往往体现社会的风貌。人际关系按组成的纽带可以划分为血缘关系、地缘关系、业缘关系、趣缘关系、事缘关系等。这些方面,都是近代社会史所感兴趣的。
最后看社会问题及调节控制系统。每个时代都有它所关心的问题,也都有它所感到头痛的问题。正因为如此,社会问题的研究应该也必须成为社会史研究的重要方面。英国社会史学家哈罗德·珀金提议,“社会史学家可以从现代国家的五大问题着手——需求、疾病、愚昧、从事卑劣行当和游手好闲;但在许多时代的许多社会里,还有许多其他问题有待发现——卖淫和犯罪、偏狭、内乱、战争的蹂躏。医治这些社会弊病,使其义不容辞地涉及到政府政策、社会管理、警察、惩罚、个人的和组织的赈济、互助、和睦里邻等方面。”(注:〈英〉哈罗德·珀金:《社会史》载弗里茨·斯特恩编:《历史学万花筒》见蔡少卿主编:《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第136—137页。)可见西方社会史学界对社会问题的研究是比较重视的,而我国学术界相对来说重视不够。本文把社会问题纳入近代社会史的学科体系,就在于引起学术界对此问题的关注。中国近代社会是一个复杂多变的社会,社会问题显得特别突出。近代社会问题突出的有流民问题、娼妓问题、乞丐职业化问题、土匪问题、社会反抗现象、鸦片流毒、赌博、溺婴、械斗等等,这些问题曾严重困扰着近代中国社会。如何解决这些社会问题,就需要社会加以调节与控制。
以上四大子系统的有机组合,构成了中国近代社会史的学科体系。
三、社会史的邻里关系
为加深对社会史范畴的理解,有必要简单谈谈社会史与相邻学科之间的关系,这里着重考察社会史与社会学以及学界极少论及的与农民学、政治史、军事史、经济史的关系。
首先,看看社会史与社会学之间的关系。社会学是研究社会结构和社会过程中的社会关系、社会行为及其变化规律的科学。它的研究目标非常明确,那就是紧紧抓住现实问题,从现实出发,寻找它未来的规律。总之,它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综合性的学科。要认识现实,往往需要追溯过去,比如社会保障问题、工业化问题、城市化问题、生活方式的变迁、社会冲突与社会变迁、社会越轨与社会控制问题、社会现代化问题等等,都有其历史发展过程,社会学需要历史学的援助去对现实问题寻根探源,由此产生了它的边缘学科——历史社会学。历史社会学因现实需要引发对历史问题的探索,虽然与社会历史学即社会史从历史学的角度引发对现实问题的思考、其出发点不同,但其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不可分割,正因为如此,笔者视社会史为社会学的边缘学科。而且,社会学的许多理论,如分层理论、冲突理论、越轨与控制理论,等,对社会史的研究是有借鉴意义的。因此,我认为,社会史应该放开历史的视界,应该敞开胸怀,豁达地让社会学介入,而不是闭关自守,将其拒之门外。事实上,近年来欧美一些国家的学者在不断为社会学与社会史的交流和对话创造条件,而且着重于两者结合的努力“正在不断的扩展之中。”(注:《布劳岱与韦伯:历史对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的意义》载黄俊杰编:《史学方法论丛》台湾学习书局1984年版。)我们应该看到这一趋势。
其次,社会史与农民学。中国农民学是一门年幼的新兴学科。说它“年幼”,是因为它创建的时间很短。《江海学刊》1993年第1 期发表方之光、池子华合撰的论文《中国农民学:历史和现实的呼唤》,标志着这门新兴学科的诞生。中国农民学创建的时间虽短,但已在学术界产生广泛影响,成为社会学界和历史学界共同关注的焦点。不是别的,因为中国是农民大国,农民问题是中国最基本的国情。学术界有敦煌学、红学,还有研究《水经注》的郦学等,却没有农民学,这是与中国的社会现代化建设不相适应的。可以说,历史和现实的呼唤产生了中国农民学。农民,毫无疑问是农民学研究的对象,中国农民学就是以中国农民为其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它所研究的内容,从纵的方面说,由两大部分组成,即农民史的研究和当代农民研究,探讨农民的产生、发展及其演变的轨迹。按照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托达罗《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一书的观点,传统农村向现代农村的变迁经历了糊口农业、混合型和多种经营的农业、现代商品农业三个阶段。假如这种划分是科学的话,我们还可以全面考察不同阶段农民自身变化的情况。农民史和当代农民的研究是互相关联、不可分割的。中国农民学研究的内容,从横的方面说,就是农民多边关系的研究,农民与土地、农民与宗教、农民与城市化、农民意识、农民与农业现代化、农民与市场经济、农民的分化与流动、农村雇工问题、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农村政治民主化问题、农民的消费方式问题、农村发展中的“东中西”问题、农民家庭婚姻问题、农民的经营素质问题、农民自治组织的建立与发展问题、农村社会保障问题,等等,都是中国农民学研究的重要问题。根据上述,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农民学与社会史的研究内容是有重合的,这就是对农民史的研究,尽管中国农民学侧重于当代农民问题的研究,但社会史“社会结构”系统对农民问题的研究,必然有助于中国农民学体系的完善。中国农民学和中国社会史完全可以相互交流,相得益彰。
其三,社会史与政治史。政治史是研究历史上的政治现象及规律的学科,侧重于政治体制、政治制度、政治斗争、政治思想与行为、政权建设等方面的研究。社会史与政治史似乎距离最远,似乎互不相犯,至老死不相往来。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比如政治史要研究阶级、阶层、社会团体等,而社会史研究社会结构,当然也要研究这些内容;再如,太平天国革命是一场政治革命,政治史如果不追寻它的社会根源,那么就不可能作出客观评价,而社会史要研究这次革命的社会意义、社会影响,两者还是要碰面的;再比如政治行为对人们社会生活的影响,“苛政猛于虎”,历来是农民起义的主要原因,政治史和社会史,都不能漠然视之。可见,政治史与社会史的关系也是相当密切的。莫里斯·鲍威克认为“政治史和社会史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如果把这两者割裂开来,那么社会生活的乐趣将失去一半,政治运动的意义也将去其大半。”(注:《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第123、 127页。)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我认为, 社会史研究不应该除开政治,政治史也不应该除开社会,两者应该开放边界,双向交流。
其四,社会史与军事史。军事史是研究历史上的战争理论、战争行为以及战争规律的学科。军事与政治最为密切,战争历来被称为流血的政治、或以剑代笔的政治,而与社会史的关系显得不太直接。然而,事实上,要进行战争,就必须动员群众,军事史不可能不研究民众的参与;要进行战争,还需要民众运动相配合;战争的胜负往往取决于人心的向背。因此,军事对社会不能不有所关注。社会史当然要研究战争行为对人们社会生活的影响;近代中国土匪遍地,被称为“土匪世界”,不考虑战争的影响,就无法对这种现象作出解释;近代中国人口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的历史过程,要考虑战争因素;长江流域哥老会的崛起,要考虑湘军对太平天国战争;淮北以“尚武”闻名,这与江南“崇文”的社会风尚形成巨大反差,如果不从战争环境对人们身心的影响进行解剖,就不可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总之,我认为,军事史和社会史,尽管各有侧重,但也有交叉,其关系相当密切。
其五,社会史与经济史。经济史是研究一定历史时期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发展规律的学科。经济史与社会史的关系至为密切,往往结合使用,称为“社会经济史”。J·F·里斯说:“现在人们对经济史实际上有一种一致的看法,认为它研究农业、工业、商业和交通,以及阐释货币、信用和税收等技术问题”,而“这些科学的研究必然包括对社会条件的考察和阐述。事实上,经济史和社会史之间是难以严格地划分界限的。”(注:《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第123、 127页。)这样说,我觉得并不算过分。事实上,社会史研究中随处可以看到经济的影响力,如社会的变迁主要靠经济力所推动,帮会是经济互助组织,社会越轨犯罪也有经济的驱动因素,社会的变革总是紧跟经济发展之后的,如此等等。但经济史和社会史研究的侧重点是不同的,如物质方面,经济史留意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水平,而社会史所感兴趣的是衣食住行的习惯与方式;科技进步是经济史所关心的,而社会史则更关心科技应用对社会生活的影响等等。由此可见,社会史与经济史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谁也代替不了谁。
至于社会史与文化学、民俗学、民族学、人口学之间的关系,冯尔康先生、乔志强先生在有关论著中均有所探究。这些学科与社会史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既有平行的一面,也有交叉的一面。通过揭示社会史的邻里关系,可以了解社会史研究的若干内容,加深对社会史特别近代中国社会史范畴的理解。
四、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上
如何发挥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社会功能?如何研究中国近代社会史?回答是“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上。”就是说我们的学习研究应该着眼于历史和现实的结合。
先简单谈第一个问题:如何发挥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社会功能。
首先,众所周知,历史学有它的学科特点,就是研究过去,是一门“过去的科学”,因此之故,历史和现实之间总是保持相当的距离,但是,正如法国历史学家吕西安·费弗尔所说:“历史既是过去的科学,又是现时的科学。”就是说要发挥社会史服务现实的功能。要让中国近代社会史成为现时的科学,就必须深入到近代社会生活的深处。马克思曾经指出:“现代历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进步,都是当历史学家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时才取得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450页。)可是,以往的研究过分强调了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外交史的研究,而忽视了近代社会的研究。毫无疑问,研究中国近代社会史,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同地为社会史成为现时的科学创造条件。
其次,不了解中国的昨天,就无法理解今日中国。譬如人口问题,1989年4月中国度过“十一亿人口日”,1995年2月15日又度过了“十二亿人口日”,人口问题成了当代中国的沉重包袱。法国著名人口学家阿尔弗雷·索维在他的《人口通论》中说:“只有当我们感觉膝盖疼痛或膝关节动作不灵时,才会想到我们的膝盖。同样道理,只要国家还没有感受到人口过剩或经济不景气的疼痛,就不会引起人们注意。”(注:〈法〉阿·索维:《人口通论》上册,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3页。)我们意识到人口问题的严重性,可是已有“切肤般”的感觉。当代中国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就是“人口爆炸”的现实。今日中国的众多人口,是历史所形成的,不了解这个过程,就无法理解今日中国的人口国情。其他问题也是一样。难怪莫里斯·鲍威克说,“进行社会史研究是深入了解社会变动的基础。”(注:《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第123、 127页。)因此,开展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研究,就成为国情研究、国情教育所必需了。
其三,中国近代社会史对社会问题的研究对现实多有裨益。如1989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获得迅速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越来越多,加上沿海与内地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所以出现了居高不下的“流民潮”(即民工潮)。而流民问题正是近代中国的一大社会问题。如果能对近代中国产生流民的原因、流民的流向、流民对近代中国社会所产生的效应以及解决流民问题的途径及历史启示等进行多层次、多角度、多学科交叉研究,可以为现实问题的解决提供决策依据。其他相关的问题也是一样。
其四,研究中国近代社会史,应当紧密联系现实,不断开拓新的领域。现实社会里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积极探索,进行历史的省思。如随着市场经济的扩张,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下岗人员的日增日多,社会保障越来越显示出它的重要性,如何建立、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这是我们面临的严峻的现实问题,我们可以向西方学习,也可以向历史学习。现实社会出现的新问题,应引起学界关注,应当开辟这一新的研究领域。再如,在现实社会里,“三鸟”(鸦、雀、鸨,泛指鸦片等毒品、赌博、卖淫嫖娼)之害触目惊心,成为当今严重的社会问题,也应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研究中寻求治本之方。再如,现在有些经济并不算落后的地区忙着修祠堂、建庙宇、续家谱,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不时出现,这些现象,都应当引起我们的思索,都要求我们作出理性的回答。
总之,我认为社会史学者应该象关心历史那样关心现实,只有这样,才能勾通历史与现实的交流和对话,才能发挥社会历史的社会功能。
现在再来谈谈第二个问题:如何研究中国近代社会史。这里只简略谈点研究方法。
研究历史,最主要的方法是“文献法”,也就是利用历史文献来再现近代社会。但中国的历史文献浩如烟海,汗牛充栋,如果不懂得利用文献,可能会事倍功半。如,要研究近代会党史,魏建猷先生编的《中国会党史论著汇要》就不能不看;要研究城市化、工业化、城市社会生活,汪敬虞先生编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不能不看;要研究农村社会、农民生活,李文治、章有义先生编的《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非看不可,要研究民风民俗,就必须翻阅胡朴安的《中华全国风俗志》以及《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要研究社会救济,邓云特的《中国救荒史》也是必读之书。总之,只有懂得利用近代历史文献,才谈得上研究近代社会。
其次,正如前面所说,社会学与社会史的关系至为密切。但是不应当简单的把社会史看作社会学向过去的投影,就象不要把经济史看作是经济理论的还原一样。但社会史毕竟是社会学的一门边缘学科,因此,社会学方法对社会史的研究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比如社会学最常用的方法“社会调查法”,就可以为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所采用。社会史有许多方面的内容,如风土民情,岁时风俗等,都具有传承性,特别在一些交通不便的山区、边缘地区,至今还保有近代社会的风貌。因此,研究中国近代社会史,进行社会调查是很有必要的。
其三,目前学术界流行一种说法:“新的综合”,就是主张学科交叉、渗透,进行跨学科多学科综合研究,这种综合研究方法,很值得提倡。就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研究而言,我们不仅应当吸收社会学的研究方法,还应当吸收其他学科的方法,用“他山之石”,来攻“玉”,这是大势所趋,如社会病理学、社会病源学、社会医学对近代社会问题的研究很有帮助;研究中国近代人口问题,采用计量方法,可以增强描述的准确性,提高解释水平,等等。总之,中国近代社会史应是一门非常开放的学科,凡是对本学科有用的理论、方法,都应该引入。
当然,研究中国近代社会史,离不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这一点,必须明确。除此而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还写出了一批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社会史或与社会史内容相关的著作,如马克思的《资本论》、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都值得我们认真学习。
本文是笔者1994年动笔写作的《中国近代社会史讲演录》稿的“导论”,限于篇幅,这里未充分展开,所述管见,亦未必正确,企盼得到学界同仁的指教,以便将来本书出版时加以修正。
标签:社会结构论文; 社会学论文; 中国近代社会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社会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人口问题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社会变迁论文; 经济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