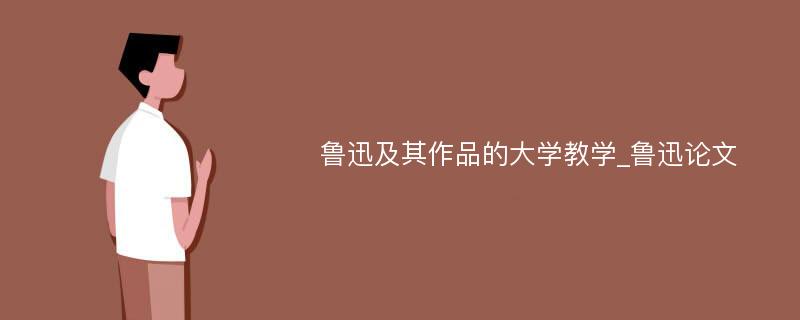
鲁迅及其作品的大学教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作品论文,大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3X(2009)01-0095-04
中学语文教学中鲁迅作品教学呈现一种并不理想甚至还比较尴尬的局面,这种局面到大学的文学教学中并没有得到多少改观。大学生对鲁迅的接受状况不容乐观。根据我们在全国中文系(或文学院、人文学院)展开的抽样问卷或实地调查,结果显示竟然有65%的大学生不喜欢鲁迅,只有35%的人才真正推崇鲁迅。而前一类即65%不喜欢鲁迅的大学生中,情况又很复杂,其中25%的人不喜欢乃至十分讨厌鲁迅;20%的人则既觉得鲁迅伟大,但又对鲁迅及其作品没有什么兴趣;10%的人对鲁迅表示不屑,认为鲁迅的文章一般化,甚至有的恃才傲物,根本不把鲁迅放在眼里。还有10%情形更为特殊,他们对鲁迅干脆就“没感觉”,相当淡漠。作为一个相当重要的经典作家,鲁迅在当今大学生中的接受状况如此不理想,这的确颇可深思并引人重视。鲁迅过时了吗?我们今天真的不需要鲁迅了吗?鲁迅作品的生命力已经丧失了吗?从总的接受状况,从多次中国作家排序鲁迅总是名列第一,从《呐喊》、《故事新编》等小说集、《朝花夕拾》、《野草》等散文集、《阿Q正传》、《孔乙己》等小说多次排到受喜爱的作品的前列等情况看,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上述问题显然是不成立的。那么是在哪里出了问题?是鲁迅和鲁迅作品的时代与当今的青年有点“隔”?是“贬鲁风潮”的影响?是曾经的政治化的、神化的鲁迅的余波?这些因素可能都有点。但在笔者看来,主要的问题怕是出在我们的教学上。中学的应试教育影响了中学生对鲁迅的把握,大学课堂有关鲁迅的“继续教育”从总体上讲看来也是不成功的,尽管有的高校、有的教师可能讲的效果很好,但对大学生的调查显示,总的情况不佳,鲁迅及其作品与思想作为十分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其承传与发扬在青年学子当中面临一种“断裂”的情势,对此一严峻的势态,大学课堂的鲁迅教学难逃其咎。
就教学目的而言,大学中文课设置日趋严重的应用性实用性取向,构成了对基础文学课的挤兑。应用性实用性固然要讲,但有时强调得过了头,大量应用性课程的蜂涌加入,导致文学课时的大幅度压缩。以中国现当代文学为例,以前既有“文学史”课,又有“作品选”课,后来将“作品选”课程取消,并进“文学史”的课里。以前既有中国现代文学课,又有中国当代文学课,现在不少高校已将这两史合并,这样课时势必减少。而且就普遍的情况看,无论现代文学课还是当代文学课,课时都压缩到每周2节或3节,使授课教师无法对作家作品作过多展开。加上学生因为过多的考级考证等等,对原著的阅读少,这样在课堂上对原著的介绍又占去一定的时间,就使对文本的深入更受到限制。尽管大部分现代文学的教师都把鲁迅作为重点,尽可能多地给予较为充足的课时,但毕竟整个教学任务要完成,整个现当代文学的内容要安排得较为匀称,因此也不可能给予鲁迅教学以太多时间。更为重要的是,市场经济的影响和现今的大学教学理念让大学生觉得学习鲁迅“没用”,对于找一个好的工作,对于今后生活得好一点“根本没用”。同时,过分追求“应用性”、“实用性”的另一极,大学的文学教学(又可具体到大学的鲁迅教学)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即过分讲究“研究性”、“学术性”,很多高校很多教授副教授博士都把培养新的博士、学者、教授当作教学的目的,明确培养的是“研究性人才”,普遍地看重评论、研究,而忽视创作、忽视“文学”的“感受”。这样的教学目的与理念,其实也不利于学生对作家作品的把握,尤其不利于学生走近鲁迅。把握鲁迅需要阅历,需要丰富深切的感受,在课堂上过分讲究对鲁迅进行“学术研究”,要让学生都能够“研究”鲁迅,这恰恰会适得其反,让学生“研究”得没有了兴趣,磨掉了学生对鲁迅作品的原初的、鲜活的感受。因此片面强调对“研究性人才”的培养,这样的教学定位是有偏差的。合理的可行的更有远见的做法也许应该是,将应用性、实用性与文学基础课的比例安排适当,既增进应用实用的课程与内容,又不让其占去过多的文学基础课空间。既强调学术性,注重研究性人才的培养,又让文学课回到“文学”,切合大学生实际,切合本科教学的特点,培养学生的文学感受,让学生对鲁迅作品有着充分感性把握的基础上再进行深入的研究。
就教学主体连带教学方法而言,作为“学”的主体的青年学生,与鲁迅及其作品很有点“隔”。这种“隔”是多种“合力”造成的。极左年代官方和知识阶层共同打造的那样一个过于政治化的、神话的鲁迅,其阴影依然存在,这使当今的大学生本能地反感;鲁迅所生活的时代与鲁迅作品所反映的时代与今天相“隔”,鲁迅独特的语体、文体也与今天相“隔”,学生不太容易贴近,而这又与老师的引导有关;中学里总体上不成功的鲁迅作品教学打下了一个不好的基础,对学生构成了一个负面的“形成性影响”;中学里大部分教师没有接受新的鲁迅研究成果,还是旧的一套观点传授给学生,这使学生对鲁迅的理解停留在过去的水平上,造成许多误读。而许多大学老师则反过来把诸多最新研究成果一古脑儿灌输给学生,让学生应接不暇,却不是让学生自己去得出结论,对于不是他们自己仔细阅读文本而琢磨出来的结论,学生显然觉得“隔”;再就是影像与网络的冲击,青年学生更多地喜欢读图、观影,把观影作为一种享受,而把读书当作一种苦差,从而不喜读书,更不喜欢读鲁迅一类的比较严肃沉重的文字;而在总的休闲语境之下,现今的大学生即使读书也偏重于喜欢读林语堂、梁实秋、周作人的休闲小品,或者带有浓厚小资情调的张爱玲的作品,或者时尚的、轻松的文字,而不大喜欢鲁迅的沉重、犀利、冷峻、深刻,在一定或者很大程度上,休闲的极致化对沉重严肃构成了遮蔽乃至压制;还有的大学生则因为鲁迅独特的语体文体,抱了和王朔一样的想法,认为鲁迅的文字疙疙瘩瘩,从而认为鲁迅的文学水平一般,甚至还不如他们自己……作为“教”的主体的大学现当代文学的老师,则往往有着过重的“研究性”、“学术性”取向,把鲁迅更多地作为一个学术研究对象在课堂上“研究”,而不是作为一个审美对象在审美、鉴赏。一个理念误区是,大部分教师可能认为“鉴赏”是浅层次的,而“研究”才是高层次的。片面追求讲课的“学术水平”、“深度”,从而多少离开了本科生的接受实际,将更多地适用于研究生教育的东西用到本科生身上。或者对学生进行大量的新术语新概念的轰炸,弄得大部分学生云里雾里,对鲁迅的印象更加模糊,如果说中学往往集中对鲁迅的某一两篇作品进行分析,缺乏对鲁迅的全局的把握、放在“文学史”里的把握,那么大学里则往往走到另一极端,过多地在“文学史”格局内、“全盘”地把握鲁迅,又因为课时的限制,因而往往缺乏对鲁迅单个文本的集中深入。或者有深入,却又“过度深入”、“过度阐释”,重阐释,轻鉴赏。中学课堂里有些好的方法,如对《记念刘和珍君》、《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等的讲授,许多中学教师会动情地、很到位地朗诵原文,或者叫学生朗诵,这样的确能收到以少(诵)胜多(讲)的效果,借助于到位的朗诵这些文章的思想与艺术都可以比较有效地把握到。但是大学教师往往认为朗诵显得“小儿科”,显得没有“学术水平”,因而课堂上往往缺乏师生对鲁迅作品的这种直观的、感性的、生动的把握。这样实际上是使学生与鲁迅的距离越拉越远。
面对不算理想的大学鲁迅教学,笔者不揣浅陋,提出几点浅见。一是强调对鲁迅原著的阅读。对鲁迅的把握显然必须建立在对鲁迅作品大量的、仔细的阅读基础上,这是共识。但因为如上种种原因,比如课时压缩,比如学生对鲁迅作品提不起兴趣等等,这一“共识”往往并不能变成现实。在此,笔者提一点方法论上的建议,即可以将中国传统的“批注”、“评点”与西方新批评的“细读”结合起来,引导学生深入鲁迅作品的文本内部。西方新批评的“细读”对于我们的文学教学的确颇多启示。20世纪英美新批评主张的“细读”,是指对作品进行仔细的阅读和评论,强调认真、审慎、反复、仔细地阅读原文,从词、词组、词义及其关系中把握和解释原文及其意义,反对以一种先验的意识和理论介入作品。这些主张的确有助于我们纠偏教师讲课当中离开具体文本的解读而大量堆积信息、堆积研究成果,学生听课当中跳过作品阅读直接记忆别人关于该作品的观点和结论的失误。由于新批评的“细读”侧重形式上的把握与研究,这自有其偏颇之处,因而有必要引入中国传统的“批注”、“评点”,以期更为完善地阅读原文,把握文本。“批注”或“评点”作为中国“古已有之”的阅读方式,也是强调对原文的阅读,在阅读过程中,在原文的上下左右空白处作眉批、旁批、尾注,即在这些空白处即兴地写下评点性的文字。这种方法可以追溯到唐代,那时即已有了诗的评点,宋代出现了文的评点,后来又有了小说评点,张竹坡、金圣叹、李卓吾(即李贽)、毛伦毛宗岗父子以及脂砚斋等人,在明清时代大规模地评点小说,以致创下了一门学派。但是后来过于借鉴西方论文形式,讲究宏篇大论,以致批注式阅读中断乃至绝迹。今天重提,既可以使民族评点精粹重新发扬光大,也利于对长期以来过分强化知识论、系统论,轻感悟、轻感知的偏颇作有效反拨。“很多人读书,急于做的事情是,当一本书读完的时候,要对他的感受进行概括、提炼、总结。我想说的是,要把后面做的这些事情放得慢一点,读完一本书的时候,尽可能把读书过程中的那些零星的,你说不清道不明的感受保持得长久一点……其实那些感性的东西是最珍贵的,你不有意去保护珍惜的话,它很快就没有了。”[1]将这种传统的“评点”演绎成今天的“批注式阅读”,即是指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阅读文本,深入文本内部,与文本对话,采用圈点批注的方式,利用眉批、旁批、夹批等形式把自己对原文的独特感受表达出来。用这些眉批、旁批、尾注等方式对鲁迅的文本进行细读,可以有助于学生走近鲁迅,深入鲁迅的作品内部,深入鲁迅的文学世界的内部,同时深入鲁迅的精神与思想的内部。开始运用这种方法时甚至可以强制或半强制地,以作业与练习的方式,要求学生细读鲁迅作品的原文,在阅读时在空白处随时写下批注。不必要求或强调“学术性”、“深度”,完全可以是即兴的、感悟式的文字,甚至可以是青年人的一些时尚用语如“晕”、“我倒”等,这至少表明学生仔细阅读了鲁迅的原文,进入了文本,与文本、与鲁迅构成了对话,哪怕这种“对话”是浅层次的,读多了,这种对话就会由浅变深,学生对鲁迅原文的阅读也会由强制性变成自愿,由被动变成主动。通过这种批注式的细读,这种随时批注、自由发挥的创造性阅读,学生对鲁迅作品的兴趣就会培养起来,那些对鲁迅作品的成见如“枯燥”、“沉闷”、“难读”等等都会得到消除。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学生会“批注”“上瘾”,会情不自禁地或说是习惯性地对作品进行眉批、旁批的细读,这样就不用担心学生不读原文了。有了丰富的阅读积累,有了对鲁迅作品的原初的真切的感受,再在此基础上往深处引导,对鲁迅作品的有效把握就变得容易了。因而在谈到鲁迅作品教学,钱理群教授认为,与鲁迅的生命相遇,可以是一种直感,也可以是理性分析。“我自己感觉到,这种直感恐怕是基础,首先你也要有一种朦胧的感觉,然后才有理性分析,有时候理性分析反而会将直感简化,因为直感它是更丰富的。理性分析要抽象出一些东西,我们现在搞文学研究的人喜欢理性分析,这是肯定需要的。但那种感悟,那种朦胧的把握可能是更重要的。”[2]
另外,抓住青年人喜欢“图像”,喜欢追新的心理,充分调动和利用影像、网络等现代媒介资源,把影像资料,把网络应用于教学。尤其是鲁迅及其作品的教学,因为时代相“隔”,学生不太容易走近鲁迅所反映的时代语境中,借用影像、图像等直观生动的资料复现鲁迅及其作品的时代,有利于学生进入特定的情境中,在栩栩如生的画面和场景中感同身受。因为课时限制不可能放映全片,可以用简单的电脑技术处理成小的片断,诸如电影《阿Q正传》中阿Q画圆圈和赴刑场的片断,电影《祝福》中祥林嫂唠叨“阿毛之死”的片断,电影《药》中看客看夏瑜被杀头的片断等等,这些影像观摩结合文本的分析,会传达给学生一个全息的鲁迅,对于理解鲁迅及其作品是十分有益的。当然,要处理好影像与文本的关系,图像为辅,文字为主,图像为文字服务;影像为辅,文本为主,影像为文本服务。先有对作品原文的细读,再参以影像片断乃至整部影片,不可本末倒置。强调在第一种方法——批注式阅读的基础上,对照观摩影像,要防止学生养成懒读原文而只看影像的“恶习”。事实上,如果没有对鲁迅作品的深入细读,没有真正进入鲁迅作品的内部,现今的青年学子即使是对于《祝福》、《药》等电影也是没有兴趣观赏的。与影像配套,可以充分利用网络资源来完善鲁迅及其作品的教学。大部分高校的图书馆和资料室关于鲁迅(也包括其他作家)的作品及资料都还是有限的,是无法同时满足哪怕一个班级的学生的阅读需求的。这样就要用到网络。事实是网络上关于鲁迅的作品及相关资料应有尽有,“一网打尽”。鲁迅作为一个相当重要的经典作家在互联网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随意登陆国内任一著名网站的搜索引擎,键入“鲁迅”或“鲁迅研究”两个关键词,就可搜索到大量关于鲁迅的网站、频道、论坛、主页。作为图书馆的必要补充,网络提供了有关鲁迅的丰富的资料和阅读鲁迅的便捷的方式,有关鲁迅作品的两个网站——一是“鲁迅文选”(网址:http://www.Eshu net.com/),二是“鲁迅文集”(网址:http://www.Zhongshan.gd.cn/kookroom/xiao_shuo/luxun),基本上提供了鲁迅的全部作品,如小说集《呐喊》、《彷徨》、《故事新编》、散文诗集《野草》、散文集《朝花夕拾》以及19本杂文集。打开网站就打开了一个鲁迅的文学世界。要根据大学生喜欢网络的心理因势利导,引导他们充分利用网络资源查阅鲁迅作品和鲁迅研究资料,并在BBS等上将自己对于鲁迅的独特感受发表出来,在网上获得及时的碰撞与交流。
当然,在笔者看来更其重要的是,要善于挖掘鲁迅作品的人性内涵、人文主义内涵,要把鲁迅作为一种精神资源,作为民族原创性的精神源泉,向学生传授,而不单是或不多是作为一种学术资源传授。要改变对鲁迅作品过多琐碎分析,而缺少真切体验,过多技术上的分析,而缺少精神上的把握的局面。要挖掘鲁迅及其作品在今天、在当下的意义,从人文、从人生的角度,而非单纯从学术、从知识的角度来把握鲁迅,启发大学生注意到鲁迅的作品、鲁迅的精神、鲁迅的思想与当今生活的密切关系,与当下人生的密切关系,注意到鲁迅的立人思想、批判性思维、人性内涵、韧的意志等等对于大学生自己的人生的启迪意义。大学里对于鲁迅的讲授,不应该成为知识的炫耀、学术的炫技,更不应该成为应试的工具。大学里关于鲁迅及其作品的教学,应该成为对民族原创性精神资源的不断开发——精神资源是一个能经得起开发的思想富藏,它既能在人们的观念接受和精神营养意义上被常说常新,又能在人们的抗拒情绪和反叛精神中屡遭酷评,无论从正面加以肯定还是从负面予以否定,它都是一个经典的言说对象,又总是一个新鲜的议论话题,一个传统化的表述的核心。[3]
收稿日期:2008-11-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