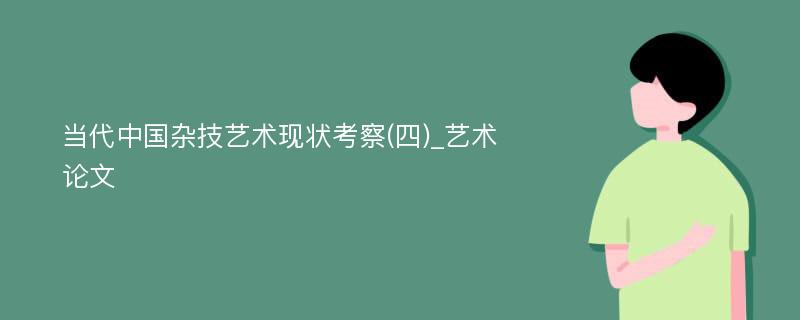
当代中国杂技艺术现状扫描——(4),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杂技论文,当代中国论文,现状论文,艺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四分天下之四——杂技剧
2005年3月25日,将成为中国杂技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日子。因为在这一天,中国的杂技节目标题中,第一次出现了“杂技剧”;也因为在这一天,战士杂技团在上海大剧院推出了中国杂技有史以来的第一出杂技剧《天鹅湖》。
杂技剧《天鹅湖》—经问世,便立即石破天惊:
上海大剧院是中国最高级别的演出场所之一,每场场租10万元,接待的都是著名院团,进驻上海大剧院演出的杂技团,至今只有战士杂技团一家。
在战士杂技团的《天鹅湖》进驻之前,国内各类院团和剧目在上海大剧院演出的场次最多不超过10场。
战士杂技团的《天鹅湖》2005年3月25日起在上海大剧院首轮公演就是20场,最高票价为680元,后应主办方要求加演1场,共计为21场;同年11月应邀在上海大剧院参加“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闭幕式演出,并进行第二轮公演,共演出1 1场,累计为32场。这个数字创造了国内各类艺术院团和剧目在上海大剧院演出的最高纪录。
2006年3月15日至26日,杂技剧《天鹅湖》赴俄罗斯莫斯科、圣彼得堡进行首次海外商演,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大剧院芭蕾舞团上演的《天鹅湖》最高票价6000卢布,而中国杂技版的《天鹅湖》最高票价为8000卢布(约折合人民币2500元)。杂技剧《天鹅湖》的演出在拥有5500个座位的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大剧院连续演出三场,场场座无虚席,最后一天的演出,不得不临时增加500个座位。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俄罗斯文化基金会为此授予主演吴正丹、魏葆华芭蕾舞艺术的最高奖——乌兰诺娃金质奖章。
2005—2006年度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大精品剧目冠名仪式上,杂技剧《天鹅湖》榜上有名。
“你们的节目改变了我五十年来对杂技的印象!”
国务委员吴仪的这句话也许更能代表中国普通观众的感受。
这就是战士杂技团的杂技剧《天鹅湖》。
在杂技剧《天鹅湖》出现之前,“剧”,这个概念对杂技这个艺术门类来说,是遥远的,是陌生的,在相当部分业内人士的观念里,甚至是不可及的。
因为杂技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艺术模式及其艺术观念,都是以对各种技的表演为本,由于历史制约、文化积累、艺术修养……等多种因素的制约,久远以来,在一般杂技从业人员的观念里,大概也没有对杂技能成为“剧”产生过奢望。
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从艺术形式方面来讲,杂技的主体是对各种技的表演,而单纯的技的表演过程一般来说并不具备叙事的功能,出于一种趋利避害的本能,杂技在其发展的过程中自然扬其技之所长,避其叙事之所短;另一个原因,则与主观意识有关。
历史上的杂技,由于其节目生产和表演方式的特殊性,在很长一段历史时间里是以家庭作坊的方式经过一代又一代而传承下来的,在这种长期的历史传承过程中,形成了杂技对技的坚守与张扬的观念,这种观念随着技的传承过程在主观意识上积淀为一道坚固的屏障,这个屏障在保护了技的纯正的同时,也在有意无意间阻碍了杂技与其他艺术门类的沟通与交流,延缓了杂技的前进步伐。
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随着社会与文化的进步,随着杂技人才结构与知识结构的深刻变化而带来的观念转变,杂技的眼光开阔了,杂技的胸怀敞开了,角色、情感、情节、情绪、意境、叙事、主题、综合艺术……这些艺术美学中的重要概念,开始进入杂技人的观念之中,多种艺术门类的专家在热情的邀请下开始涉足杂技,新的知识、新的形式、新的观念也随之而来与杂技发生交流、发生碰撞、发生融合,杂技因此进入一个艰难、痛苦、但也是充满自豪与辉煌的蜕变期。
战士杂技团杂技剧《天鹅湖》的创作经历可以视为中国杂技这种蜕变的一个缩影,一个典型。
变革,首先从观念开始,观念转变了,才能导致实践的转变。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杂技之所以长期“千团一面”,是因为观念的保守阻碍了杂技的进步,八十年代以后杂技的发展之所以日新月异,是因为观念的进步推动了杂技的变革。
“尽管中国杂技历史悠久,但发展缓慢。从地摊杂耍到登上舞台经历了漫长的过程,直至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才开始向姊妹艺术学习,注重综合艺术效应;九十年代又从国外学来包装术,知道剧情、服装、音乐、舞蹈、舞美等融为一体可以为杂技带来整体感染力。然而,十几年的实践表明,一台貌似完整的杂技节目其实并没有什么整体性,往往是外穿时装,内里依旧,杂技与故事相脱节,动作还是老一套。”
这是战士杂技团宁根福团长对杂技现状的评述,见解是尖锐的,认识是深刻的。
“杂技长期技字当头,重技轻艺、有技无艺,品位不高,天生不足,一直没有成为中国舞台的主流艺术。”
作为一个不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都有着相当影响的杂技界领军人物,能从这样的美学角度,这样的美学高度,这样清醒的看待自己从事了一辈子的杂技,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也因此,变革杂技,让杂技成为中国舞台的主流艺术,在宁根福心中逐渐形成了一个目标明确的情结:
“自古以来,杂技都是一个个几分钟的小节目,缺少整体性。我多年来的一个愿望,就是创作一台具有很高艺术水准的大型杂技剧目。提升杂技品位,让杂技成为像歌剧、舞剧、话剧、音乐剧那样的艺术,登上大雅之堂,不再是杂耍,也不再是内旧外新硬加点情节的那种所谓新杂技。”
“中国杂技要想突破传统,再上一个台阶,就要进行革新,提升杂技品位,中国杂技要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而不是进行局部修改或片面的拿来主义就行的,中国杂技必须走出一条真正属于自己的道路。”
正是宁根福的这种宝贵意识和观念,为杂技剧《天鹅湖》的产生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
正是有了这种求新、求变、求艺、求美、求品位的艺术观念,战士杂技团才一路领导着中国杂技变革的潮流,创作出一鸣惊人的《对手顶·东方的天鹅》,进而创作出震惊中国、震惊世界的杂技剧《天鹅湖》。
萌动创作杂技剧《天鹅湖》的念头不是一时心血来潮的突发奇想,杂技剧《天鹅湖》的问世也不是一蹴而就,杂技剧《天鹅湖》的成功是一个漫长的创新积累过程,她是战士杂技团求新、求变、求艺、求美、求品位的艺术观念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勇于探索,逐步积累,而后升华的结果。
回头进入历史,就能找到答案。
战士杂技团原本只有《对手顶》,而没有“东方的天鹅”。
1996年,辽宁体操队的国家级运动健将,获得过全国冠军、世界锦标赛第三名、世界青年锦标赛冠军的吴正丹和魏葆华,被战士杂技团看中,借调到团里进行了一年的艰苦训练,1997年,他们回到辽宁技巧队后退役,1998年,他们两人正式成为战士杂技团的演员。
当时,他们承担的节目是《对手顶·东方的天鹅》的原型——《对手顶·双人技巧》,节目中,吴正丹穿的是普通软底舞鞋,表演也以倒立、扳腿、抛接性空翻等技巧动作为主。
1998年战士杂技团访欧演出,丹麦皇家芭蕾舞团团长看完演出后激动地表示:“你们的节目把我们皇家芭蕾舞团的演员都比下去了!”丹麦皇家芭蕾舞团团长的这个评价,启发了节目的主创、副团长高俊生的创作灵感:“借鉴芭蕾舞的动作,把芭蕾舞跳到人身上去。”
之后,高俊生开始给吴正丹、魏葆华设计在身体上练芭蕾舞的动作,半年后,吴正丹终于成功地完成了从站背到站肩,再到站头这三个高难度技巧的跨越。1999年,为参加全军的文艺会演,他们请辽宁芭蕾舞团编导晋云江,把高俊生训练的芭蕾技巧和对手顶技巧编排为《对手顶·鸽子》,意为歌颂和平。紧接着,为了迎接2000年第五届全国杂技比赛,战士杂技团又请来了总政歌舞团编导张继刚,张继刚对节目的整体进行了新的构思,对技巧与舞蹈、音乐也进行了新的编排,尽管“当时团里有强烈的反对意见,认为这个节目太超前了,过于偏重舞蹈,不像传统杂技,而且技术含量有限、难度也不是最大……”(吴正丹语)但在具有强烈的创新意识和现代艺术观念的宁根福、高俊生的坚持下,“东方的天鹅”终于排除了阻力,走进了赛场并一鸣惊人:《对手顶·东方的天鹅》在第五届全国杂技比赛中荣登金狮奖榜首。
2001年在上海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十三届部长级会议的晚宴上,《对手顶·东方的天鹅》这个仅约7分钟的节目赢得了在座的各国首脑18次的掌声。上海APEC晚宴上的这18次掌声,证明了《对手顶·东方的天鹅》所拥有的艺术品位及其审美价值,对“东方的天鹅”日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在2002年第26届蒙特卡洛世界杂技大赛上,《对手顶·东方的天鹅》夺得了最高奖金小丑奖。
《对手顶·东方的天鹅》以其独具的美,独具的艺术魅力征服了业内同行,征服了专家,征服了观众,征服了世界。
《对手顶·东方的天鹅》的成功,为杂技剧《天鹅湖》的问世奠定了坚实的第一块基石。
原来杂技也可以演出这样的节目。
原来杂技也可以创作出这样的艺术精品。
第26届蒙特卡洛世界杂技大赛比赛结束后在德国的演出期间,宁根福、赵明和时任柏林国家剧院芭蕾舞团编剧的刘军、时任广州军区政治部文化处处长苏玉光在一起小聚,那次小聚,就是三年以后震惊中国、震惊世界的杂技剧《天鹅湖》的构思诞生的时刻。
之后,便是三年的艰苦创作与奋斗,但就在战杂人在创新道路上艰难跋涉的那些日时里,面对的却是来自杂技界、舞蹈界……的一片质疑声,各种各样的质疑从杂技剧《天鹅湖》投排一直延续到2004年参加第八届全军文艺汇演之前。
2004年10月25日,第八届全军文艺汇演在北京举行了隆重的颁奖典礼,杂技剧《天鹅湖》获得了剧目一等奖,赵明获导演一等奖,吴正丹、魏葆华、许玮妍、金唯一获表演一等奖,张继文、王德来获舞美设计一等奖,李锐丁获服装设计一等奖,翁纯璞、张继刚获灯光设计一等奖,王德来获道具设计一等奖等10个奖项。以此为转机,杂技剧《天鹅湖》的成功及其开拓精神开始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成为社会的一个热门话题,之前的各种置疑声组成的浪潮开始消退。
但传统杂技及其观念的根基实在是太深厚了,尽管杂技剧《天鹅湖》取得了如此的成绩,但置疑的意识并没有因此而销声匿迹,一个小插曲特别的令人回味:
2005年11月,也就是距杂技剧《天鹅湖》在上海大剧院首演21场的8个月后,在上海大剧院第二轮11场演出结束之际,在中国杂技金菊奖第五届理论奖颁奖仪式暨第十届全国杂技理论研讨会上,宣读了一篇题为《杂技剧:对后现代主义杂技的一种推想——兼论杂技本体与戏剧本体的碰撞》的获奖文章:“……笔者不是要否定杂技剧这种表现形式在杂技的艺术范畴里出现的可能性……就目前杂技舞台上的艺术表现来看,至今没有一出真正意义上的、用杂技的艺术表现手段来结构故事、铺陈情节、化解冲突、塑造人物形象的杂技剧出现……现实地看,杂技剧的出现恐怕不是简单的事情,也不是在一个短时期内能够见出成果的。”
文章应该是以《天鹅湖》为理论对象有感而发的。因为在2005年之前的中国杂技界,使用“杂技剧”这个概念并进行艺术实践的,只有战士杂技团一家,只有《天鹅湖》这一个剧目。
文章不论是标题还是文中的观点和意识,都流露着作者对杂技剧那深深的质疑。
当然,作为理论研究,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天下一统,允许各抒己见,可以自圆其说,提倡百家争鸣。
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篇文章宣读时,距离战士杂技团的杂技剧《天鹅湖》参加第八届全军文艺汇演并获奖及2004年10月27日《人民日报》文化版头条《“天鹅湖”引起杂技革命》的报道:“短短4个月,《天鹅湖》全剧就已成型,通篇流畅,绝技迭出,精彩纷呈,不但美妙,而且神奇。9月,全军文艺会演的评委观后惊叹不已,许多人连呼“没想到”!北京、辽宁、四川等地的演出公司和剧院的电话接二连三地打来;十几位日本、美国、欧洲的演出商在上海国际艺术节举办的国际演出招商会上为明年下订单……”已经一年有多,距离杂技剧《天鹅湖》在上海大剧院的首次公演也已经8个月。
时间在这里应该是有着特别的意义的。
这篇文章表达的虽然是作者个人的观点,但在某种意义上却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文章不是圈外观者的随意点评,而是出自长期从事杂技实践和理论工作的专业人士笔下并在中国杂技最高级别的理论研讨会上宣读的研究文章。文章在思维方法上,不是以客观存在的事实为研究的对象,而是以主观的“推想”代替客观现实并以此作为立论的理论依据。这种思维方式,偏离了理论研究最基本的方法和原则,而文章这种对理论研究基本原则的偏离的思维方法和所得出的“结论”,尽管笔者在会上提出了商榷与质疑,但却没有引起任何反响,一种被默认的客观效果似乎在提示我们:这种思维方式、研究方法及其研究结果的被默认,其深处或多或少的涵藏着那积淀了杂技久远历史惯性的传统意识和传统艺术观念,也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这种默认比文章本身流露的思维方式和艺术观念更让人咀嚼,更令人回味。
因为这种传统意识、传统艺术观念及思维方式对处于重要变革时期的现代杂技来说,是一道无形的屏障,它与宁根福、高俊生们……的艺术观念可以说处在近乎相反的两极,正因为如此,杂技剧《天鹅湖》才只能出现在战士杂技团而不可能出现在默认文章观念的其他环境中,也正因为如此,才会深深感悟到宁根福、高俊生、张继刚、赵明、刘军……们所具有的创新意识和现代艺术观念的宝贵。
从对历史的回溯中可以清晰的看到杂技剧《天鹅湖》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这样一个渐进的孕育诞生过程。
杂技剧《天鹅湖》之所以取得如此的成功,之所以对世界产生了如此的震动,从艺术的角度来说,最重要、也是最根本的一点,就是战士杂技团通过杂技剧《天鹅湖》的创作实践,让杂技这种从有史以来就一直以技为追求的终极目标的艺术门类终于成功的完成了杂技语言系统的创造,使中国杂技从此拥有了演绎剧的能力。
在艺术理论中,对“剧”这种艺术样式的界定是苛刻的:凡是剧,必须具备人物、情节、故事、主题这几大艺术要素,必须与音乐、舞台美术、人物造型等多种艺术手段相结合,必须以启(开端)、承(发展)、转(高潮)、合(结局)的戏剧结构方式演绎故事。
戏曲是这样,歌剧、舞剧是这样,话剧、音乐剧也是这样。在舞台表演艺术这个领域中的艺术门类,无一不是遵循着这个艺术规律而成为“剧”、而演绎“剧”的。
“剧”以其所具有的深刻的意义、完整的形式、丰富的内涵而被誉为艺术的最高形式。
演剧,就是通过对具有个性的典型人物的塑造,从而完成对情节、故事、主题的叙述。要塑造具有个性的典型人物,要完成对情节、主题、故事的叙述,就必须具有能叙述故事、能展现冲突、能塑造人物的“语言”。不同的艺术门类,如京剧、话剧、舞剧、歌剧……都以自己独有的、不同于其他姊妹艺术的艺术语言完成剧的演绎并把自己与其他姊妹艺术相区别开来。
在杂技剧《天鹅湖》出现之前,杂技是没有“剧”的。
杂技之所以没有剧的根本原因,是杂技对自己艺术门类语言系统的创造一直处于未完成状态。
尽管经过二十余年来的艰苦努力,杂技在标题节目和主题杂技晚会的创作实践中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初步完成了角色的塑造及对情节、情绪、情感、主题的表达,但在实践中可以看到,在标题杂技节目和主题杂技晚会的艺术实践中,不论是被叙述的对象,还是杂技自身所拥有的语言叙述能力,都还没有进入到“剧”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表现矛盾冲突、讲述故事的层面。从美学的角度看,标题杂技节目和主题杂技晚会在叙事能力上所呈现出的是一种朦胧的、诗意的美,较之于演“剧”所必须具备的条件而言,他们所拥有的语言表达能力和表达结果都还处在有待提升的初级阶段。因此,战士杂技团要搬演《天鹅湖》,人们最关心、也最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没有语言的、以对各种技巧的表演为门类艺术特征的杂技如何“演剧”,怎样“演剧”。
我们知道,在舞台艺术门类中,如京剧、话剧、歌剧、音乐剧……都是以口头语言为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艺术表现手段的,用生活中的大白话来说,就是这些艺术门类都可以“开口说话”,剧情主要通过唱、念传递给观众。而杂技则和舞蹈一样,是不用“开口说话”的艺术。在这个角度相对而言,杂技的语言系统属于非言语行为系统。
非言语行为是指人自身除了口头语言行为之外的用以传达信息的其他行为。非言语行为作为一个系统,在其中又可细分为身势语、体触语、手势语、目光语……等。
在有语言交流障碍的环境里,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交流时,非言语行为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它可以表达情感,可以传送信息,在一定的时候,可以代替言语行为的功能。
在另一个层面讲,非言语行为则是我们生活中的平常现象。在日常的生活经验中,特别是在人们的情绪处于高潮时,常常会以非言语行为来表达自己强烈的情感和情绪,如惊愕、瞪眼、吐舌、举拳、扭头、转身、握手、拥抱……在这个意义上,口头语言和非言语行为是相辅相成的,都是广义的语言的一部分。
而哑人之间使用的哑语、交警指挥交通时使用的手势、海军使用的旗语……则早已自成体系。
由于杂技在表演中不使用口头语言的特点,因此,非言语行为便成为杂技语言系统中极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艺术界,作为一种常用的术语,人们则习惯用“肢体语言”代替“非言语行为”作为表述方式。
从杂技剧《天鹅湖》的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杂技的语言系统是在向姊妹艺术学习、借鉴并融会贯通后,由多种艺术元素共同组成的视听兼备的、再现与表现相结合的综合语言系统:凡是能够表达思想、感情,并使接受者获得信息的一切手段、方式和方法,如技巧、表情、动作、造型、构图、色彩、光线、旋律、音响……都是构成杂技艺术语言的要素。
在杂技剧《天鹅湖》中,创作者运用这些“象征性符号”寻求观众对杂技剧的理解与认同,其表情达意功能的实现,是杂技语言系统各要素之间相互配置和综合的结果。
杂技剧《天鹅湖》语言系统的构成元素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所有舞台艺术表演门类都拥有的普遍的艺术元素,其中包括表情、动作、造型、构图、色彩、光线、旋律、音响……等多种艺术元素。对这些艺术元素的运用,虽然在标题杂技节目和主题杂技晚会的实践中已经有了成功的体现,但在杂技剧《天鹅湖》中,这些艺术元素因为进入“剧”的层面而与在标题杂技节目和主题杂技晚会中所具有的表达能力与表达深度上的不同而显得格外注目。
如造型语言
就广义而言,造型对杂技来说早已有之。不论是在类型杂技节目中,还是在标题杂技节目、主题杂技晚会里,造型都是杂技艺术的基本艺术元素之一。
需要指出的是,在杂技剧《天鹅湖》出现之前的传统类型杂技节目里,杂技的造型处于一般类型的化妆层面,基本没有个性可言;在之后的标题杂技节目和主题杂技晚会中,虽然开始出现少量的个别角色,但由于受节目本身构成元素的制约,造型的典型性在这类节目中还缺乏必须的、必要的展示空间。
而演剧则不同。
凡演剧,就是通过具有个别性的人物经历以演绎故事。在剧中,不论是主要人物,还是一般群众,他们都有着自己明确的角色身份。因此,演剧的第一直观层面,就是通过造型语言塑造具有个别性的典型人物形象。
杂技剧《天鹅湖》讲述了一个发生在欧罗巴的王子与中国的少女之间悱恻缠绵的爱情故事。剧中,有纯情的少女,有多情的王子,有凶险的老鹰,还有侍从、水手,以及美丽的白天鹅、可爱的青蛙、妖娆的黑天鹅……等众多人物。在杂技剧《天鹅湖》中,王子、少女、鹰王、黑天鹅、侍从、水手……每个人物都必须依靠造型语言把角色所独有的性格和特定的身份具体的形象化,这种造型语言用直观的形象在视觉的层面界定着人物的身份及其个别性,界定着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区别,造型,在这里越过了一般化妆的初级层面,从而成为观众理解剧中人物之间的关系,进而推动对剧情深入理解的重要的艺术语言。
再如形态表情语言
就广义而言,形态表情语言属于肢体语言范畴。
而肢体语言则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
如果以汉代毛诗序中“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为一种参照系,那么“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肢体语言就是指我们人自身用以表达情感、情绪、思想及内心活动的各种动作和面部表情。如果借助于中国的戏曲理论,肢体语言即是“舞”的另一种表述方式。
“戏曲者,谓以歌舞演故事也。”
这是中国近代戏曲理论大家王国威先生对中国戏曲所做的定义。
在现实中我们可以看到,戏曲所包含的艺术元素是极为丰富的,在音乐方面,有文场的各种吹、拉、弹乐器,有武场的各种打击乐,有各种声腔、曲调,在表演方面,有表情、身段、台步、圆场、把子、跟斗……但王国威先生在界定戏曲的基本特征时,只用“歌舞”两字,便把戏曲丰富庞杂的表演手段及艺术特征进行了简约的归纳。在王国威先生的这个定义里我们可以看到,“歌”,是对音乐、声腔的泛指,“舞”,则包括了表情在内的所有的肢体语言。王国威先生对中国戏曲定义的精到表述,至今仍被广泛引用且难以超越。
在杂技剧《天鹅湖》中,不论是王子、少女,还是老鹰、黑天鹅以及侍从、水手、……作为人物,他们是生活在(舞台虚拟的)现实之中的,他们的人生经历,他们的悲欢离合,他们的喜、怒、忧、思、悲、恐、惊,都是通过“舞”——肢体语言——形态表情给以表达,这如同戏曲除了唱以外,还有眼神、身段、台步、圆场、靶子、跟斗……一样。
2005年2月,在杂技剧《天鹅湖》上海大剧院首演的前夕,吴正丹、魏葆华作为中国杂技史上第一代在杂技剧中承担主演的杂技演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他们在得到要排演杂技剧《天鹅湖》并要他们在剧中担任主演的通知时说的一段话是比较朴实、也比较有代表性的:
吴正丹:“团里告诉我们时,我说,这怎么行啊?我能跳舞剧吗?”
魏葆华:“我们过去练技巧,只讲完成动作;现在演杂技,主要也是摆造型。舞剧是要表演的,我们没学过,所以心里根本没有底。”
作为采访的对话虽然简短,但却真实地表达了吴正丹、魏葆华以一个演员的亲身经历总结的关于技巧、杂技、舞剧三种艺术样式之间在表演美学上的差别,其中对杂技与舞剧之间差别的感悟,可以说是相当深刻的。
魏葆华所说的“表演”,可以理解为就是通过形态表情——肢体语言对人物情感、情绪及心理活动中各种喜、怒、忧、思、悲、恐、惊的表达。用舞蹈界的行话来说,就是每个演员的手和腿都要会说话,甚至全身的每块肌肉都要会表达感情。
因为在之前的现实中我们可以看到,就一般的杂技节目而言,由于受节目自身构成元素的制约,情感表达一般都比较单一,与剧的典型人物及其丰富内容相比较而言,对情感的表达还处于较简单的层面。
而剧则不然。
在杂技剧《天鹅湖》中,就人物身份而言,王子不同于侍从,侍从不同于水手,少女不同于白天鹅,白天鹅不同于黑天鹅……这些不同的角色所具有的不同的身份,需要有不同的眼神、动作、行为来体现;在故事中,少女、王子、老鹰、黑天鹅……不同的人物,有不同的欢乐,不同的忧伤,不同的痛苦……如少女失去人形后的痛苦,见到王子时的倾心;王子思念少女时的痴情,被老鹰蒙蔽后的惊愕;老鹰俘获少女时的阴险,看到王子中计后的狂傲;黑天鹅诱惑王子时的妖艳,被王子识破后的冷漠……剧中,每个人物的一举一动,一哭一笑,既要合乎人物的性格身份,又要合乎彼时彼地的规定情境,因此,对这些情感的表达便要具有鲜明且细腻的个别性;同时,当演员登上舞台进入剧中人物的整个过程中,形态表情——肢体语言必须保持连贯,不允许出现中断。杂技剧《天鹅湖》对杂技演员表演美学上的这种要求和高度,在杂技剧《天鹅湖》出现之前,在一般的杂技节目中是不曾有过的。
因为在一般杂技节目的表演中,由于节目没有剧所需要塑造的典型人物的悲欢离合,没有矛盾冲突引起的起伏跌宕,因此也就没有人物情感的复杂与多元,因此,在杂技一般节目的表演中,演员只需要把握住青春、阳光、微笑的神态与表情就基本可以满足节目的需要。
当我们把杂技剧《天鹅湖》对演员表演的要求与杂技一般节目对演员表演的要求相比较就可以看出二者之间在表演美学上的巨大差别,看出杂技剧《天鹅湖》在表演艺术上所具有的开创意义。
杂技剧《天鹅湖》的成功演出,标志着杂技艺术语言系统中形态表情语言这个极其重要组成部分的创造已经圆满完成。
与形态表情语言相关联但又相区别的是舞蹈语言
这里之所以把舞蹈语言单列叙述,是因为在一级概念里,舞蹈语言与形态表情语言同属于肢体语言的范畴,二者都是以人的身体作为表情达意的材料和手段;在二级概念里,形态表情与舞蹈之间虽然有关联,但二者之间也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区别。作为术语,舞蹈一般指的是经过编排的、有一定长度的、承担表达一定内容的连续性动作。在表演形式上,有单人的、双人的、三人的、集体的等多种表演形式;而形态表情语言一般则指随着剧情的发展需要而展开的具有随机性意义的情感表达方式。
在杂技剧《天鹅湖》中,舞蹈语言有着特别的意义和位置,在杂技剧《天鹅湖》的一种节目单上使用“大型杂技芭蕾舞剧《天鹅湖》”为标题便是一种证明。
在杂技剧《天鹅湖》中,对舞蹈语言的运用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把杂技技巧与舞蹈彻底的融为一体,以舞蹈的结构形式组织动作,在其中以杂技技巧为主要的艺术表达元素。如剧中王子与白天鹅的双人舞便是这种艺术形式的典型的例子。
在王子与白天鹅双人舞的段落中,所有动作的连接与贯穿,依靠的是舞蹈的结构方式和舞蹈身段,但其中的“单足肩上转体180度”、“单足头顶阿拉贝斯”、“单足头顶踹燕”等技巧,则属于杂技技巧范畴。
另一个层面则表现为:以舞蹈的结构、舞蹈的动作为基本艺术元素来组织、结构、编排具有表情达意的叙事段落,然后把这种舞蹈段落作为剧的有机部分参加对剧情的叙述并以推动剧情的发展。
这种结构的舞蹈段落如第一幕中的海浪舞——意在表现王子所乘坐的船已经开始了在海中的航行;灯笼舞——王子到达中国后所看到的中国的民风民俗;以及第三幕中的西班牙舞、匈牙利舞、俄罗斯舞等舞蹈段落——老鹰用来引诱王子的手段。
介于这两者之间的另一类舞段,是第二幕、第四幕中的白天鹅溜冰群舞。
之所以把白天鹅溜冰群舞单独举例,是因为这些舞段虽然也采用了杂技的溜冰技巧,但在舞段中,溜冰主要是取代了行走的功能,在整个的舞蹈中,并没有突出、展示溜冰技巧的意图,在演出的客观效果中可以看到,舞段的审美焦点和观众的视觉中心,主要都集中在肢体的舞蹈语汇所表达的情感和情绪上,而不在溜冰的技巧上。在第二幕和第四幕中,白天鹅溜冰群舞对整个剧情美感的营造和对剧情的推动作用是极其重要的,也是显而易见的。
通过杂技剧《天鹅湖》的艺术实践我们可以看到,不论从哪种角度讲,杂技要演剧,舞蹈语言都是其中必须的、极其重要的艺术元素,因为舞蹈语言是杂技技巧转换为叙事语言的艺术基点,技巧只有和舞蹈语言融合在一起,技巧的叙事功能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
杂技的表演主要靠技巧来体现,而舞则要靠细致入微的表情和精确的形体来展示,当二者因杂技剧《天鹅湖》而融为一体时,新的艺术环境要求所有的肢体语言不仅是技巧的,也是有意义的;不仅是表演的,也是表现的,同时也是体验的。演员在剧中对每一种技巧、每一种肢体语言的表演,需要有对文学内涵的理解,对节奏诗意的把握,以及对音乐灵魂的领悟。正是得益于这种高水平的要求,杂技剧《天鹅湖》才取得了如此的成功。
再次如音乐语言
应该说,在杂技剧《天鹅湖》诞生之前,音乐语言在标题杂技节目和主题杂技晚会那里已经基本成熟,对杂技剧《天鹅湖》来说,艰难的不是对音乐语言的创造,而是在杂技舞台上如何才能体现和保证柴可夫斯基这部举世闻名的经典作品的经典性。也就是说,柴可夫斯基的音乐,对于没有演剧历史和经验的杂技演员来说,在为他们提供了经典艺术样本的同时,也成为他们在表演上,在节奏的把握上,在情绪和情感的体现上一道严格、苛刻的艺术标准。
从技术的层面讲,由于柴可夫斯基的音乐先于杂技剧,先于技巧、动作、舞蹈的完成,因此,所有的技巧、动作、舞蹈的设计必须符合音乐的内涵、意义、节奏、情绪……的要求,也因此,柴可夫斯基的音乐也成为杂技剧《天鹅湖》创作过程中成败与否的严重考验。
为此,剧的创作者们在创作之初就音乐与其它艺术元素之间的关系在艺术观念上、在艺术创作指导思想上达成了高度的统一:
1、杂技艺术新的表现形式必须与经典音乐的艺术思想完美统一;
2、剧的故事、情节、矛盾冲突必须与音乐的听觉形象完美统一;
3、舞台的场景氛围的视觉形象必须与音乐的听觉形象完美统一;
4、杂技的本体技巧形象必须与音乐的听觉形象完美统一;
5、出现的角色形象必须与音乐的听觉形象完美统一;
6、演员的表演节奏必须与音乐的听觉形象完美统一。
这“六点统一”,体现着创作者们对经典音乐经典性的深度理解,体现着他们对经典音乐与表演及其他艺术元素之间关系的深刻认识,体现着他们把这种认识转换为艺术实践的正确方向和方法。正是依靠这“六点统一”的提出与实施,为杂技剧《天鹅湖》的音乐语言的完美表现提供了基础的保证。
而在这一点上,人们议论得最多,感触最深的大概要数时间仅1分37秒的四小青蛙倒立舞的设计与运用。通过演出的检验可以看到,四小青蛙倒立舞较之于原版芭蕾的四小天鹅舞,不论在艺术表现形式上,还是在艺术品格上,不论是对音乐内涵的体现上,还是在技巧的难度上,二者都充分地展示了各自艺术门类典型的艺术特征而无愧于经典。
表演中,四个演员完全处于倒立状态,随着音乐的旋律与节奏,四个人在不停的运动中不断地变换着队形和腿部动作,在必须保持四人动作整齐一致的前提下,还要用青蛙的神态和与观众进行交流,更重要的是,所有的这些技巧与动作的表演必须体现柴可夫斯基音乐的意义和内涵,以保持柴可夫斯基音乐的经典意义,而所有这些苛刻的要求,四小青蛙倒立舞都给予了圆满的体现,四小青蛙倒立舞所拥有的独特、高雅、机趣、高难等品格,是四小青蛙倒立舞成为经典的必然。
前面所举的造型语言、形态表情语言、舞蹈语言和音乐语言这些例子,对杂技来说其中的部分虽然具有首创的性质和意义,但就艺术而言,它们都属于所有舞台艺术表演门类都拥有的普遍的艺术元素层面,而非杂技所独有。杂技剧《天鹅湖》之所以一经问世就石破惊天,其关键的原因在于杂技剧《天鹅湖》极其出色的完成了杂技技巧语言的创造,并把这种杂技所独有的技巧语言与其他艺术语言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从而使杂技剧《天鹅湖》成为从业内专家到一般观众,从国内到国际得到一致赞誉的杂技剧的开山之作,经典之作。
就广义而言,杂技的技巧,也属于肢体语言的范畴。由于技巧语言对杂技剧《天鹅湖》的成功创作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此单独列章叙述。
技巧,是杂技之本。在一般的杂技节目中,一个节目展示的主体就是对一种技巧的完成过程,其展示的核心价值是体现演员完成这种技巧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杂技节目表演的技巧,在内涵上,一般并不具备更多的社会意义和文化意义,在功能上,也因此远离了一般艺术所擅长的通过叙事以进行教化的深度审美。技,既是杂技之所长,同时也是对杂技这种艺术形式的一种自我限制。如何发挥杂技的所长,超越由于历史形成的自我限制,把远离社会意义、文化意义的技巧转换为塑造人物、叙述情节、展现冲突的语言,这将是杂技剧《天鹅湖》能否成功的关键。
从杂技剧《天鹅湖》的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杂技技巧语言的创造,在相当的程度上并不仅仅局限在对技巧本身的整合,更重要的关节点是如何使用技巧,如何把技巧与情节、与舞以及其它艺术元素融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并使技巧成为其中的艺术支点,通过这个支点以彰显杂技的独特个性与魅力。
杂技技巧语言的这种特殊魅力,在杂技剧《天鹅湖》中随处可见。
在第一幕的欧罗巴皇宫场景里,主体技巧是球技,而球技作为技巧在这一场里之所以能成为叙事的主体,关键是剧的创作者为球技的展示提供了一个与剧的情节及其典型环境、与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相融合的艺术空间。
在这个场景中,从梦中惊醒的王子向侍从们讲述了梦的经过,他要知道那变成了天鹅的美丽少女所在的东方在哪里,为了指示东方在地球上的地理位置,侍从们推出了地球仪——剧的情节恰到好处的给球技的出现提供了必须而且是必然的空间,侍从们——西方典型小丑的人物造型为剧情的推进提供了准确的人物关系,也为喜剧氛围的创造提供了恰当的契机——侍从们在地球仪上向王子指示着遥远的中国位置,同时也在以滑稽消解着王子的忧愁——小丑与球技因此而在适当的时间、恰当的空间里得以尽情的展示,最后,王子下决心去东方追寻他的美丽梦想。
在这个场景里,也许最值得称道的是把展现球技技巧的大球转换为地球仪的这个精彩创意。这个创意,使一个本无意义的球形道具具有了文化意义,具有了情节意义并参与到对剧情的推进中来,从而使球技这种技巧成为推动剧情发展的技巧语言。
在第一幕的码头场景里,主体技巧是爬杆、扛杆、杆上顶技,剧的规定情景是停泊着王子即将远航乘坐的船只的码头。
在这个场景里,船员们正在忙忙碌碌的进行着出航前的各种准备——船只的桅杆当然是船员们进行工作的主要地方,必须的场景设置,使船只的桅杆顺理成章地成为爬杆、扛杆、杆上顶技等技巧展示的空间。杂技的爬杆、扛杆、杆上顶技在这个情节里的叙事作用,由于合理的环境设置而得以彰显。
在第一幕中以地图、舵盘为背景的这个场景,则非常明显的凸现出创作人员独出心裁的创意与设计所产生的艺术效果。
天幕上的地图和舵盘,象征着王子正在进行的长途旅行,中空透视圆洞中那移动的标志性景物,象征着王子行程的具体目的地,时间、空间的流动与转换在这个独到的舞美设计中成为观众一目了然的视觉艺术形象。
金字塔的出现,象征着王子到了埃及。在这个具象的环境里,一群阿拉伯人手中飞舞的短流星所蕴含着的欢快,似乎在诉说着这个民族对王子到来表示的欢迎;泰国的尖顶王宫出现了,几分妖娆的柔术,几多气势的滚环,随着王子在滚环车上的出现,彰显着泰国民风的一隅;中国天坛典型的大屋顶出现了,46名红衣女子在“一字接龙抡草帽”、“二节站肩对传”中欢快的舞动着草帽,男子热烈的高跷,以及随后惊险的高跷扔人,既凸显了华夏民族独有的风情,也预示着王子行程目的地的到达。
在这部分场景里,杂技的短流星、柔术、滚环、草帽、高跷以及高跷扔人等技巧,以其较密集的频率,叙说着王子一路的见闻与经历,剧情,在这些因典型环境的存在而具有了典型意义的技巧的展示中,得以逐步推进。
作为观众,从第一幕中可以清晰地看到王子从梦醒到跨海越洋经埃及、过泰国,最后到达中国的跋涉过程。观众的这种感知当然离不开舞台上多种艺术元素的综合效应,但不可否认的是,杂技的技巧,无疑处于对剧情进行叙述的中心位置,并成为观众视觉审美关注的焦点。
如果第一幕的基调是热烈,那么第二幕的基调则是优美;如果第一幕凸显的是杂技技巧与多种艺术元素的相融和而产生的审美效应,那么第二幕留给观众深刻印象的大概应是技巧与舞的融合与区别。
杂技要演剧,其叙事的主体手段当然是杂技的技巧,但在剧中对技巧的使用既要受到剧情的制约,同时也要受到技巧本身的制约。因为技巧毕竟不如戏剧的口头语言,也不如舞剧的形体语言那样的可以随心所欲的自由与灵活,要演剧,技巧虽然是核心的艺术元素,但技巧不可能从头至尾的贯穿始终,在对技巧进行创新的编排时,在对技巧使用的之前或之后,它需要与其它多种艺术表演手段如表情、身段、舞蹈……之间进行融合,才能充分发挥技巧语言的作用,才能构成剧的流畅与完整。
在第二幕中,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大都集中在王子与白天鹅的双人舞——肩上芭蕾和四小青蛙这个段落。
王子与白天鹅的双人舞——肩上芭蕾,源于战士杂技团在2000年第5届全国杂技比赛中获金狮奖的《对手顶·东方的天鹅》,在时下,人们已经习惯把这段表演表述为“王子与白天鹅的双人舞——肩上芭蕾”,如果我们仔细比较就可以发现,当年的“对手顶”在这里转换为了“双人舞”,“顶”与“舞”虽然只是一字之差,但其中所蕴含的意义不仅深刻,而且丰富,因为它既涉及到艺术观念,也涉及到艺术表现。
《对手顶·东方的天鹅》作为一个标题杂技节目,是通过对手顶这种技巧来塑造东方的天鹅这个艺术形象,而在杂技剧《天鹅湖》中,这段双人舞作为剧的一个重要情节,它表现的是王子对少女的长久思念和见到少女时的激动与倾心,肩上芭蕾,作为杂技特有的一种技巧,被融入到这段双人舞中,成为塑造王子和白天鹅这两个人物形象的核心艺术元素。在这段双人舞中,不仅有技巧,更重要的是还有王子与少女之间那纯真、美丽的情感,不仅有爱慕,有思念,还有热情、有向往……肩上芭蕾作为一种技巧在这里的运用,是为了用杂技独有的艺术手段以更好、更美、更精彩地表现王子与少女之间爱情的坚贞与不易。由于演绎了王子与少女的美丽爱情,中国杂技开天辟地的拥有了自己的剧,由于肩上芭蕾等技巧的运用,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的《天鹅湖》。
第二幕中另一个极其精彩的段落,就是四小青蛙倒立舞——一般人们在描述这个段落时,多用“四小青蛙”或“倒立四小青蛙”,这里之所以用了“四小青蛙倒立舞”的表述方式,是因为:四小青蛙,是角色的构成,倒立,是使用的技巧,而舞,则是这四小青蛙运用倒立技巧表演的艺术形式。在特定的剧情、特定的经典音乐的规定与配合下,这段倒立技巧的运用,从一开始就是作为一个独立的舞段来设计,来编排的。
四小青蛙倒立舞之所以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在于这个舞段全部是以手代替脚在表演跳舞,这前所未有的奇想所带来的表演难度和新颖程度便因此可想而知。
在这个段落中,创作者别出心裁的创意、倒立技巧的高难、机趣的编排,幽默的意境,使这个段落成为所有观众都有口皆碑的对象,同时也成为《天鹅湖》之所以成为杂技剧最形象、最具有说服力的典范之一。
杂技剧《天鹅湖》的创作之初,总编导赵明与宁根福就明确了三项创作原则:一、保持《天鹅湖》的典雅性,二、杂技动作必须与剧情晓畅地结合起来,三、绝不损伤音乐。
可以说,四小青蛙倒立舞是对这三项创作原则的完美体现者。
芭蕾舞剧《天鹅湖》中四小天鹅舞,演员以优美的芭蕾舞汇,给世界留下了永久的经典;而四小青蛙倒立舞,则创造了杂技技巧舞蹈化的典范;四小天鹅的舞标示了芭蕾舞的基本特征,而四小青蛙倒立舞中则明白无误地标明:这个版本,非杂技莫属。
第三幕,是浓墨重彩展示杂技技巧的篇章,其中主要技巧有蹦床,男女软功,倒立技巧,抖轿子,独轮车,对手顶,球技,三人技巧,魔术变人,王子、白天鹅双人舞——芭蕾足尖等。这众多的技巧之所以能在第三幕得到比较集中的展现,是因为剧的创作者为这些技巧的展现提供了符合剧情需要,并能推动剧情发展的空间,从而使这些技巧成为剧情重要的组成部分。
第三幕的场景被设计为鹰穴,几分阴森,几分幽暗的环境,提示着这里是一个没有阳光的角落。
王子来到了这里,为了引诱王子,众多折服于老鹰的动物们在肆意且卖弄地炫耀着各自的风情:有的在独轮车上嬉哈,有的借助(绷床)弹力在空中飞舞,一对妖艳男女在只有一平米见方的树桩上,配合着音乐的节奏,以“高圆宝脚上拉顶”、“双拐落平头上单手顶三起三落”等一系列高难度动作——软功——以展示自己妩媚的独特魅力,接着,是一对黑天鹅以高超的双人技巧显示着力量的强大和相互之间的缠绵……众多精彩的杂技技巧在这具有典型意义的情节设计中得到了尽情的发挥——就在这一切对王子都没有产生效用时,老鹰——创作者们——使出了高明一招——通过魔法——魔术变人——变出了黑天鹅,魔法——魔术在这里使剧情发生了突转;王子误以为黑天鹅就是自己心中的所爱,他与黑天鹅翩翩起舞并开始陷入了情网——三人技巧因此得以展现——王子的误判让老鹰为自己设计的引诱的成功而大笑,他再次使用魔法——魔术——变出被困的白天鹅——王子清醒了,他一定要救出自己的所爱。
在第三幕中,对魔术这种技巧的使用不仅高明,而且也是这一幕的亮点:在技术的层面,魔术的使用丰富了杂技剧《天鹅湖》的艺术表现手段;在塑造人物的层面,凸现了杂技特有的优势:通过魔术变人的运用,把芭蕾舞剧《天鹅湖》中老鹰拥有的魔法这个抽象概念变为了生动的、形象的艺术情节;在语言的功能层面,魔术成为穿插、连接及推动剧情发展的重要戏剧手段,成为第三幕推动剧情发展并发生突转的关节点。因此,杂技剧《天鹅湖》中对魔术的使用,不论是从理论上的总结,还是对艺术实践的启示,都应该得到格外关注。
“现在的杂技芭蕾舞剧《天鹅湖》就是沿着一条边缘艺术的道路,将艺术和技术结合在一起,两种艺术形式相互借鉴共同发展。这种特殊的艺术形式,戏剧化的表现方式能够让杂技演员的才能得到更全面的体现,拓展更宽广的舞台。”总编导赵明的这段话,是创作杂技剧《天鹅湖》的思想指导,也是对实践的深刻总结。
实践在证明,杂技剧《天鹅湖》是一次用中国民间杂技演绎西欧宫廷艺术的一次伟大创举,是一场文化与文化碰撞后进发出的永恒光芒。
在东方神韵与西方经典的完美结合中,技巧因舞蹈而优雅浪漫,舞蹈因技巧而惊险刺激,杂技剧《天鹅湖》既表现了对西方文化艺术的深刻认识又充满了对本民族主体文化的高度自信,并达到了高难技巧、新颖形式和深刻内涵的高度统一。
杂技剧《天鹅湖》的诞生过程告诉我们,杂技剧《天鹅湖》之所以能有今天,不是一蹴而就,不是异想天开,而是战士杂技团在宁根福一班人的带领下,在众多专家的帮助下,经过一步一个脚印的“八年磨一剑”,才有了杂技剧《天鹅湖》的问世。
“创作中国杂技剧《天鹅湖》是一次极具挑战性的全新尝试,我们渴望它能为杂技走进世界艺术主流殿堂贡献力量。”
走进世界艺术主流殿堂!
一个充满豪情壮志的理想!
一个值得为之奋斗的辉煌目标!
一个值得中国杂技人品味和思考的命题。
战士杂技团团长宁根福的这句话,可以视为当代中国杂技的艺术宣言。
杂技剧《天鹅湖》在上海大剧院和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大剧院以及在世界各地巡演的成功,标志着“走进世界艺术主流殿堂”这个辉煌目标在战杂人的汗水和智慧的浇灌下已经成为现实。
杂技剧《天鹅湖》的出现与成功,在中国的艺术史上为杂技谱写了光芒四射的一页华章。它标志着中国杂技艺术与歌剧、舞剧、话剧、音乐剧、戏曲等姊妹艺术一样,已经登上了自己艺术形式的最高一级台阶,齐头并肩的屹立在世界艺术之林。
结束语
从前面的叙述中可以看到,杂技节目标题的变化并不仅仅只是几个简单文字的重新组合,它的意义也不仅仅停留在给观众浏览的节目单上,杂技节目标题的变化对杂技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在杂技节目标题的后面,涵藏着的是杂技人的艺术观念与杂技人的艺术追求,而杂技人的艺术观念与艺术追求则关联着杂技的艺术生命形式,关联着杂技艺术的发展与未来。也正因为如此,当我们把近二十余年来变化了的杂技节目标题铺展开来时,我们便可以看到:“类型杂技节目”→“标题杂技节目”→“主题杂技晚会”→“杂技剧”这样一种图式,在纵向上,这四种不同的杂技节目标题呈现的是一种递进方式,它标示的是中国杂技艺术发展的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勾勒出的是杂技艺术的发展史;而在横向上,这四种不同的杂技节目标题则是当下杂技创作多样化丰硕成果的简约表述。
杂技取得的成就是辉煌的,但辉煌并不能代表一劳永逸。
杂技前面的路,依然是艰难而漫长的。
这不仅对杂技的技巧而言、对杂技的艺术而言,同时也是对杂技人而言,对杂技的艺术观念而言。
因为在攀登艺术高峰的道路上,耸立着这样一句警世名言:
“艺无止境”。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