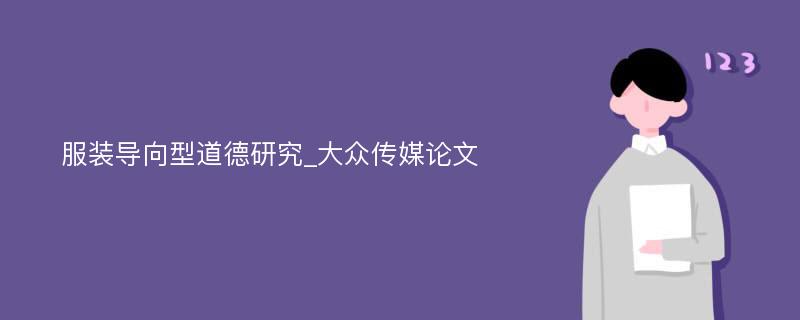
时尚导向的道德询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导向论文,道德论文,时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当代社会,时尚是极为常见的社会现象。从物质生活的浅层领域,到精神生活的深层领域,时尚以千姿百态的方式展现、流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其中许多积极健康的时尚开创了颇具时代气息的新风尚,开辟了文明生活的新天地,给我们的生活增添了丰富的色彩和情趣。然而,由于现代社会的市场化、商品化特征,决定了时尚与市场、商业的共生共谋关系,时尚便被打上了深深的商业化烙印,成为商家手中谋取利益的工具。这样,时尚在促进经济繁荣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负面影响。但我们却不能因噎废食,对时尚百般限制乃至禁止。因而,如何将时尚的负面效应降到最低,就成为亟待解决的课题。所以,在当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我们应对时尚的创始、传播、流行的整个过程进行道德的导向与监督,尽量遏制不道德时尚的产生、流行,促使时尚与精神文明的双向良性互动,以达到提升个体和社会整体道德水平的目的。
一、时尚主体谁主沉浮
时尚源自西方上流社会的奢侈行为,因而时尚的创始者、倡导者往往是地位显赫、颇具影响力的人物。他们往往是使一种新风气成为时尚的原始传播者和重要推动者。事实亦证明,时尚往往是由权势任先导,普通民众争相仿效而得以扩散、普及、流行的。H·布卢默在《社会科学百科全书》中为时尚一词概括了以下三个特点:对某种时髦形式及其正统性的统一认识;有规则的观察和标示社会生活变化的方式;通过对新风格的认可和对旧风格的抛弃而提炼出的普通感受性和趣味[1]。作为“有规则的观察和标示社会生活变化的方式”,时尚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社会成员的身份意识、文化认同和社会类型的标志,时尚象征着一个人的地位与个性,或者象征着一个人对某种生活方式投靠的倾向。因而,时尚与名人结下了不解之缘,可以说,时尚是由名人创造的,名人的一招一式、一颦一笑以及一举一动,都会激起芸芸众生的如痴如狂,从而引领着时尚的潮起潮落。如前两年歌坛天后王菲窜红之际,其标新立异的如蝴蝶般横亘鼻梁的“防晒妆竟也得到广大歌迷的备加欣赏”,效法者不乏其人;由于李雯的鼎力宣传,喝非常柠檬迅速风行于大江南北;孙雯那强劲的一脚,南孚电池也日渐畅销……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名人导向的时尚,往往能迅速地传播开来,得以广泛流行,个中原因,许多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已经中肯地指出,这是由于人们那种天然的对权威、名望、上流社会的崇拜与向往,渴望与他们平等的心理所致。这种名人时尚能使普通大众通过参与时尚从而在心理上觉得似乎拉近了与名人的距离而得到心理满足与平衡,当然有其积极意义。
然而,综观我们生活中流行的时尚,其发起者不外乎娱乐圈、演艺界、体育界的名人,而知名学者、专家、政界名流等却难以跻身时尚界。究其原因,是因为随着社会结构的转型,人们对长期以来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感到厌烦、恐惧和倦怠,对理想主义信仰消弱、启蒙主义热情消退和崇高感丧失。在道德上,许多人经历了集体主义向个人主义的转化,物质需求的欲望空前高涨,生活福利、娱乐消遣的欲望日益膨胀,于是符合大众物质和精神需要的大众文化迅速崛起,甚至毫不谦让地居于文化正堂。在这一将文化知识变为资本并与市场联系起来的过程中,传统知识分子固守其精神领域,矜高自守,怀着对文化与学问的神圣感、崇高感,埋首于专业领域,而与市场保持较大的距离,自然就难以与更具纯市场效应的影视明星、通俗歌星、体育明星们相匹敌。正如有学者分析的,当代中国受众之所以接纳明星,是由于明星的不同特点、类型和生动可感的方式满足了受众的想象和幻想。但这根本的原因则如陈刚在《大众文化与当代乌托邦》中所说的:“是大众在这些现象中发现了超越大众层次光芒四射的自由明星,在大众看来,这种光芒正是乌托邦中自由光辉折射的,它对大众是一种吸引和召唤。由于明星是由大众中创生的,所以这种呼唤不像神的声音那样遥远空洞,而是真实的可以把握的。”这或许就是当今的时尚为什么总是起源于那些从文化方面来说很难拥有厘定知识符号的权威资本的演艺、体育明星的原因。
既然,我们根本不可能无视作为当今文化重要组成部分以及人们日常生活挥之不去的时尚的影响,那么正视它并采取措施引导它步入正轨才是良策。首先,应完善文化管理制度,强化约束与激励机制,促进名人、明星们的道德自律,以形成积极良性的道德示范效应;同时,大众媒体也应发挥应有的道德监督、警戒的作用,利用舆论的力量对名人、权威们的公共行为进行监督,以形成一个清明的道德环境。其次,我们不妨因势利导,针对人们对明星崇拜心理,不失时机地创生一批适应于今天市场文化和现代高信息传媒的当代文化明星。如大陆曾兴起的“余秋雨热”就可以作为大众渴求的精神呵护加以引导。在当今市场文化时代,以文化明星作为创造、倡导时尚的主体,必然可以减少时尚中庸俗、非理性、非道德色彩,从而引领时尚朝着文明健康的方向发展,这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当然,一种时尚产生后能否流行,并不仅仅在于其领潮者身体力行,关键在于时尚赶潮者的积极参与。因而,欲摒弃不良时尚,抵制其消极影响,赶潮者就应具有良好的自我调控能力和独立的判断能力,要能够像点灯时控制火那样对感性冲动予以节制和引导,这样才不至于在时尚面前茫然不知所措而只会随波逐流,由此而丧失了个性和理性。然而,目前时尚参与的主体大多数是青少年,他们热情、开放、好奇,但往往缺乏冷静,易于冲动,好幻想,因此,他们在汹涌的时尚大潮之中难以把持个性、理性,缺乏冷静审慎的思考,往往跟风而动,一哄而起。他们这种盲目跟风的非理性行为,长此以往可能导致从众型、依附型人格,遇事易于感情用事,缺乏主见。因此,家庭、学校与媒体都应密切关注和重视青少年,培养其道德主体意识,提高其判断是非的能力,健全其和谐人格。
二 时尚传播谁是谁非
当今时代,社会高度信息化,大众传媒成了人们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因素,成了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而时尚更是依赖媒介的传播,媒介充当促进时尚形成、普及或妨碍其流行的主要条件与手段。大众传媒对社会时尚传播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提供流行信息,促进时尚产生
社会时尚产生之初,往往只是限于创始者、前卫派的小圈子里,它的普及流行以普通大众获知性方式的存在为前提之一。因此,它需要宣传、介绍,而大众传媒正是提供信息的重要渠道。对外部世界了解程度的深浅,对新奇事物的接触多少,都可以构成影响人们产生追求新奇愿望的因素。当某种新方式出现以后,以提供最新信息为天职的大众传媒就会大量、反复地将有关信息传递给不特定的多数人,使新方式的存在被人们共同认知,这样就形成人们对新方式作出判断、选择的信息基础。不仅如此,由于大众传媒反复信息轰炸,迫使人们从中选择适合自己的新方式。公众往往从媒介信息源中寻求关于最新时尚的信息。因而,现在意大利新设计的时装,巴黎刚生产的香水,由于发达的大众传媒的作用,几乎一日之内便风靡全世界。
(二)加速流行普及,扩大流行规模
大众传媒在为公众提供流行的最新信息的同时,“还报道流行采用的实际情况,告知采用新方式的方法,并评论、解说新方式,指导人们的行动”[3](第151页)。由于现代大众传媒具有快速与大规模传播的力量,因而,在新方式产生以后,通过大众传媒,公众能迅速获悉这种新时尚被采用的情况、社会的评价和流行程度。此时,大众传媒“不仅提供采用流行的判断标准,而且提示对流行做出反应的方法”[3]。这样就促使那些虽然关注新时尚但尚未参与的人们尽快行动起来追赶新潮流,从而时尚的流行规模得到扩大。有些时尚本来只在某一小范围内流行,若受到大众传媒的反复报道、渲染,范围很快就会扩大,甚至盛行于全社会。比如,送花、送贺卡原本只是在青年人、情侣中盛行,但现在社会上却渐渐流行开来,为老人祝寿、朋友新婚、乔迁之喜等都以鲜花、贺卡祝福为时尚,而且大有不减之势。这跟大众传媒的宣传介绍息息相关。
(三)影响流行期限,加速时尚变迁
作为提供最新流行信息的大众传媒永远都不会停滞不前,而是不断地发布信息,宣传最新方式。在这种不断传播信息的环境中,喜新厌旧的本性使得人们自然容易对获悉的最新方式产生兴趣,并热衷于最新时尚。这样就迫使已有的时尚让位于新出现的时尚;此外,大众传媒亦常常对正在流行的新方式加以评判,而人们一般信赖媒介机构在提供最新信息方面的社会权威,这种评判必然会影响人们对正在流行时尚的态度,引起人们对流行时尚的抑制,并相应地采取抛弃的行为,从而导致原本正在流行的时尚难以继续,不得不退出时尚舞台。大众传媒介绍新方式,批判旧方式的行为均会加速时尚现象的新陈代谢,因而缩短流行周期,促使时尚不断更新变化,异彩纷呈。比如,时装的色彩、款式等的频繁更替,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大众传媒提供的信息影响所致。
大众传媒对时尚的形成、普及与衰退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大众传媒所宣传的时尚,除了对受众的短期行为产生影响引发一次次时尚潮汐之外,还对受众的观念乃至社会习俗起潜移默化的影响。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在北京地区进行了一次有关“电视对小学生择业和偶像崇拜的影响”的抽样调查,研究结果表明:电视是影响小学生择业和偶像崇拜的重要因素。因此,大众传媒在享有自由权利的同时,必须克服目前存在的非道德主义的自由化倾向,恪守对社会对大众的义务和责任。大众传媒对社会对大众的义务和责任是什么呢?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应经常而深刻地影响舆论。按照普利策的理解,就应该是用高尚的理想、正确的知识、优秀的文化熏陶人、丰富人。具体而言,首先大众传媒就是充当社会雷达,发现值得向社会传播的最新时尚信息,迅速传递给社会公众,并进行宣传、解释、评论,促使这种时尚流行。同时监视社会环境,一发现那些不良时尚的苗头,就立即予以警示,鞭挞一切背离道德准则的时尚,并阻止其发展蔓延。其次,大众传媒负有提供健康有益的娱乐作品,倡导健康文明时尚的社会使命。一旦大众传媒忘却这一使命,其引导失误,就有可能产生消极的社会影响。今日弥漫在神州大地的“浮夸奢靡风”、“超前消费风”难道同传媒不负责任的误导无关?因此,大众传媒必须加强道德自律才不至于误入歧视,才不至于导致严重不良后果。同时,对大众传媒采取制度化的管理、监控,也是抵制传媒不良影响的必要手段。
大众传媒对时尚的普及、流行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对于追逐时尚个体而言,他们全都是在传媒的直接影响下参与时尚的,有的人是由于人际关系影响即亲戚、朋友、熟人的带动。对此,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拉扎斯菲尔德提出了著名的大众传播的“有限效果论”,他指出,在传媒宣传运动面前,个人并非都是以同样的方式做出反应的,而是被划分成两类:一类人积极接触并传播由媒介传递的信息,他们是“意见领袖”;另一类人则主要通过同他人接触作为自己的行为指导,他们属追随者,大众传媒是通过“意见领袖”这些中介人物产生影响的[3]。在时尚流行过程中,这类“意见领袖”属先锋派,他们率先采用新的时尚,对于其周围人而言这种真实可感的活生生的时尚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因而时尚往往是在此时以几何级数的速度流行开来。因此,在采用一种最新时尚时,人们应注意自己的行为不要给他人带来不良示范效应,自觉摒弃那些消极时尚,以尽到自己应有的道德责任。同时,每个人在诱人的新时尚面前都应予以理智的审慎的思考,不要被热情冲昏了头脑,不管适合不适合自己,不管有无益处,不问青红皂白地先尝试再说;每个人都应以自己的审美观、价值标准来加以评判,予以取舍,而不能以他人的喜好为喜好,以他人的标准为标准,这样自己就可能变成无个性无主见的随风飘转的浮萍,哪里还谈得上道德主体、独立人格?
三 时尚形式谁定美丑
时尚,作为在特定时期被普遍采用的新方式,作为一种广义的文化现象,其外延是相当丰富的。然而,如果从时尚表现侧重于形式或内容的不同来区分,则可将五花八门的时尚现象大致分实用的、观念的和审美的三种类型[4]。实用时尚(包括劳务与物质),诸如至今还盛行不衰的“考研热”、“计算机热”、“出国热”之类,他们的最大特点亦即共同点就是,人们往往确信追随着这类时尚能获得非常实际的好处,比如财富、地位等等;而曾经兴起的“金庸热”、“余秋雨热”,曾备受大学生推崇的尼采、萨特,以及当今学术界掀起的“大众文化”大讨论均属于观念时尚,他们往往能给参与者一种可能比较表面的理性认识上的满足;而一直人气很旺的时装、时髦发型、化妆品、畅销书、流行音乐、影视歌星等可以予以审美观照的时尚,则突出表现在它们的追随者常常获得情感上的愉悦,一种感性的精神满足。这类时尚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而时变时新,因而,它更具代表性,因其更时尚形式可以用美丑界定,故使其更为眩目、耀眼,应者云集。
毋庸讳言,有些审美时尚确实能给人以美感,如去年由于王家卫导演的电影《花样年华》的上演,饰演女主角的张曼玉演绎出了我们民族服装——旗袍的经典内涵,随之而掀起的旗袍热确实给花样迭出的时装界吹过一阵清新的古朴端庄之风,展示了东方女性端庄秀丽的迷人风采;又如从1995年以来流行的露脐装,穿在身材修长的妙龄少女身上,更能衬托其活泼清爽的青春风采;近年流行的“老板头”,给人以富于青春活力的美感。这些时尚洋溢着时代特色,给其追随者以精神上的愉悦、心理上的满足,因而其审美上的积极意义是不可否认的。
然而,正如美国经济学家托斯丹·本德·凡勃伦的断言:“我们对任何一个时期风行的式样所感到的美或‘可爱’,只是暂时的,假性的……我们对任何最新事物的一时爱慕,并不是从审美观念出发而是别有所依据的,一等到我们固有的审美感占了上风,我们对于这个新型设计就要感到难以接受,它的寿命就要在这个时候终止。”[5](第130页)并非所有的审美时尚都有审美价值,也并非参与审美时尚就能够给人带来审美乐趣。比如个子矮小、皮肤黝黑的女性穿上旗袍就只会显得滑稽可笑;没有良好身材的女性若穿上露脐装无疑是“家丑外扬”。这样的时尚无疑是难以用美来形容的,不过被美的意象和美感幻想弄得头晕眼花罢了……应该说,审美者实际并不钟情于美,有时因为时髦,他甚至拒斥美,会完全不把自己的美感冲动系于美。然而,对多数追随此类时尚的当事人来说,往往不会觉察到它们的不美,相反却觉得其十足的魅力而奋力追赶。当代俄国哲学家别尔嘉耶夫一语中的:“审美者并没有体验到由美所引发的美感,他常常漠视最真实的美,只是让虚幻的热衷于追赶时髦的人,正灾难参与某种审美时尚的人,往往缺乏稳定深刻的理性,他们往往屈服于暂时的感性的愉悦与满足,而放弃了理应具有的稳定的审美理想,有时甚至美丑不分,以丑为美。”[6]从人体美以及生理学的角度来说,女性拥有娇美丰满的身材才算得上健康美丽,然而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伦敦的模特莱司利·霍恩比就因体形苗条而成为当时最红的模特,她一反女性美的传统观念,促成了无性别特征的纤细体形的时尚。而此后几十年直到今天,从电影制片厂的摄影棚到情景喜剧的演出乡村现场,瘦得芦柴棒似的美女明星无处不见。在“清瘦苗条、不要脂肪、少些肌肉”的号令下,明星们的瘦身已走到了极端,甚至成了病态。
美是一种肯定性的价值,它使人感到振奋、愉悦、欢快。诚然,追随这种时尚能获得短暂的愉悦与乐趣,但欲从中获得真正的美的享受则绝非易事。因为,美可以是愉快的,愉快的却不一定是美的。而且,从美学意义上讲,由美所引发的审美快感的真正体验,取决于审美者丰富的知识积累、深厚的审美经验和健全的审美心理结构。追随常变常新的时尚虽然经历了许多体验,但正是由于其流转不定,变化起伏,因而很不利于审美经验的梳理、凝聚与升华。斯宾塞指出:“视为审美的东西……并非来去匆匆,转瞬即逝,而是存留在精神之中,发人深省。”泰戈尔亦形象地说:“颜色吸引眼睛,但要懂得和谐的美就需要用心,需要认真地观察……因此光通过肉眼,而不是通过心灵,就不能真正地看到美。”[8](第30页)一种时尚,总是刚刚普及开来就被汹涌而来的新潮流所淹没,因而时尚的追随者从中获得的有益的感性经验常常来不及梳理就被另一种经验所代替,由此紧跟时尚的人由于方向不定而常常迷失在审美的海洋里,那么需要心灵凝神观照才能烛照美丑,才能获得的审美快感当然就与之无缘了。因此,美丑不分,甚至以丑为美也不足为奇了。再者,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人的本质力量却离不开自由。因此,美的本质是自由,美是自由的形象。席勒认为:“在审美的国度里,人就只需以形象显现给别人,只作为自由游戏的对象而与人相处。通过自由去给予自由,这就是审美王国的基本法律。”[9](第145页)席勒所谓的“自由游戏”,就是人暂时处于卸下自己身上一切关系的枷锁,摆脱了一切强制的状态,在轻松愉快的精神自由情境中,倾心欣赏美。
然而,追随时尚,正如我们前面所分析的,很大程度上是由从众心理所致,因而审美时尚具有不以审美者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变化进程。因此,追随时尚的大众要达到无拘无束、凝神观照的自由心境便不可能,他们真正的美感体验也如镜花水月般不可企及。尽管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大量美丑不分的时尚,但是,审美时尚对人们的审美观念和审美标准的影响却是客观存在的,况且有些审美时尚确实能给我们带来美,让其追随者获得美的享受。所以,面对现实,我们只能正视它,并且努力提高自身的审美趣味和审美能力。因为,“在审美方面精细的心灵中,还有一种在内因道德的地方补充道德和在有道德的地方减轻道德的劳作的能力。这种能力就是审美趣味。审美趣味要求适度和得体,它不接受一切各部分不相称的、粗野的、强制的东西。在情欲的热潮中倾听理性的命令和约束本性的粗野发作,众所周知,这是好的风度对每一个文明人的要求。”[10](第256-257页)审美趣味的养成依赖于审美能力的提高,而审美能力作为人把握世界的一种特殊本领,是审美知觉力、感受力、记忆力、想象力、理解力、判断力、选择力和创造力等方面的统一,审美能力的提高得之于审美教育,即通过自然、社会与艺术的陶冶以及不断的审美实践,如对服饰、发型的选择,日常家居的布置等,着重使人们的审美感受能力得到训练,鉴赏水平得到提高,创造力得以培养,从而培养人们对美的热爱、独特的生活情趣和高尚的道德情操。这样,我们就能够以审察和反思的态度面对轰轰烈烈的审美时尚潮流,“择其善者而从之”,从而避免东施效颦的审丑效应。
标签:大众传媒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