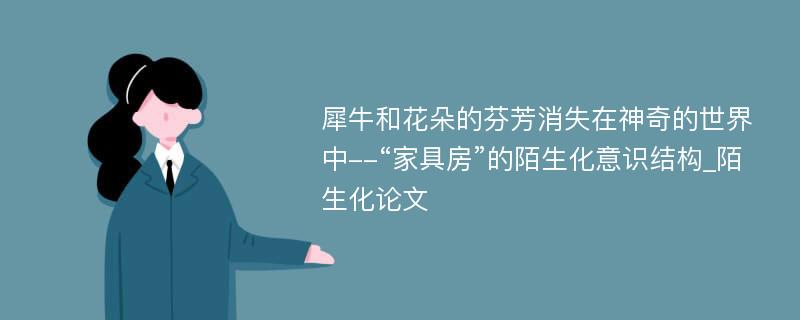
木犀花香,在魔幻世界消失——《供应家具的房间》的陌生化意识结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花香论文,房间论文,意识论文,家具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欧·亨利是天生令人发笑的幽默作家,即使是“笑中含泪”,其中也都含有逗乐的因素和带笑的成分,这就是所谓的欧·亨利风格。但欧·亨利又是一位永远使人感到新奇的作家,他经常变换手法,标新立异,因而他能在自己的创作中出奇制胜,令人惊喜,叫人倾倒。本刊探赏系列之三,我们已从《最后的常春藤叶》看出,欧·亨利固有的幽默、俏皮、风趣、诙谐和嘲讽全都不见了,严肃替代了逗乐,悲怆驱散了笑料,正表现了欧·亨利风格的变异。但这种变异,并不始于此,早此一两年,在欧·亨利创作高峰期和创作风格成熟期,就已经出现了,而且一开始变异就相当彻底——这就是发表于1904年8月14日的纽约《世界报》星期日版的另一小说名篇《供应家具的房间》,这虽是欧·亨利的一篇爱情小说,但它写的却是爱情的恶梦,美的毁灭,人生的悲剧,它更像一篇“死亡小说”。虽然《最后的常春藤叶》也写死亡,但那是一种救人活命的自我牺牲,是一种人性基督精神的升华,因而能让人从死亡中看到光明,从痛苦中获得力量,从悲剧中受到感奋。《供应家具的房间》则严肃而又严酷,悲怆而又悲惨,没有感奋,没有力量,没有光明,只有黑暗,只有绝望,只有死亡。在这里,更多的是揭露与控诉,叫人饱含眼泪而发笑不出来。但它却能以其“异化小说”的意识结构使人“陌生”而获得新奇的美感,成了欧·亨利变异风格的代表作而引人瞩目。
小说叙写一个不知姓名的年轻人来到纽约城,到处寻找离家出走的情人,一位左眉长有黑痣的秀丽的演唱女郎,但他费尽心机,都没有得到下落。当他拖着长期奔波而疲惫不堪的身体落宿于贫民区一家公寓的房间,忽然闻到一种熟悉的木犀花浓郁的芳香,而这种香味,是只有他所要寻找的女孩子身上才可能散发出来的,因而断定她曾住过这一房间。不料在打听中,女房东却再三推说房客中从来就没有住过这样一位姑娘,于是年轻人悄悄关严窗户,打开煤气躺在床上自杀了。读者最后才从女房东跟邻居的闲聊中得知,那左眉长了一颗黑痣的女孩子,一星期前就是在这个房间里开煤气自杀的。这里的故事情节非常简单,简单得几乎没有什么故事情节,因为构成故事情节的人物性格被淡化了,淡化到几乎看不出有什么人物性格。这是欧·亨利首次为我们推出的一种意识结构小说,只写一个“供应家具的房间”的场景画面,只写活动其中的一个人物,而人物活动却没有性格的推使,只是体现一种捉摸不定的心绪和如梦如幻的意识,虽然保持了欧·亨利小说的某些技巧,如人物遭遇的偶然巧合,小说结局的出人意外,但它突出的却是一种朦胧心态与环境的感应,一种贯穿小说始终的情绪的扩大或凝聚,意识的波涌与起伏,以此架设小说的主体结构。人物的意识流程和心绪轨迹成了审美意象的主体系列,构成小说的整体形象,让失落的爱情和迷惘的人生,通过人物心理屏幕的折射,映现出魔幻世界的景观。整篇小说,洞明了内心世界而模糊了性格特征,突出了环境气氛而冲淡了故事情节,但不经由刻划人物性格和经营故事情节的途径却能直接进入小说灵魂的深处,揭示出爱情的木犀花香因何消失于魔幻世界的严峻主题。
“供应家具的房间”,是用意识结构建造起来的。“房间”有环境的展现,“房间”有主题的隐藏——小说中有一个比喻是最好的提示:“肮脏的地席上有一块杂色斑驳的毯子,仿佛波涛汹涌的海洋中一个长方形的,鲜花盛开的热带岛屿。”欧·亨利暗示我们“肮脏的地席”,肮脏的社会,罪恶的潮流正汇成“波涛汹涌的海洋”,这就是环境的展现;人性“鲜花盛开的热带岛屿”被淹没在非人性的“波涛汹涌的海洋”,这就是主题的隐藏。小说的主题,就隐藏于环境之中,环境的展现,就是主题的揭示。而小说对环境的展现,即是对结构的显示,以人物的意识流动和情绪波动为轴心,既“由内向外”,又“由外向内”,则有不同诠次的交错和多层画面的转换。这种环境的展现,着重表现人物心理意识对外界生活场景的反应与对人物动作行为的影响。所抒发的情绪,有意念的飘溢,有情韵的流淌;所描绘的场景,有画面的剪辑与组合,有主观意绪与客观氛围的融贯如一;所飞扬的旋律,有思情的荡漾,有韵味的回旋;所跳荡的节奏,有时梦时醒的交替,有若得若失的变换。小说即以此意象系列展现意识环境,刻划心理形象,揭示悲剧主题。
世态素描式环境。年轻人是带着找不到情人踪影的失望心情来到纽约的——“他对她一往情深,千方百计要找到她。”在进入“房间”之前,小说一开始就为年轻人的出场勾勒出一个纽约下层社会的现实图景,通过外界一系列相关或不相关的客观画面的随意连接,反衬出流浪的年轻人的身份遭遇和意识心态,布满红砖建筑的贫民区公寓,是社会底层小人物的“几十、几百个家”,他们进进出出,“像时间那样动荡不安,难以捉摸”——这是流浪汉世界中的一个角落:“他们从一个供应家具的房间搬到另一个供应空具的房间,永远是短暂的过客——在住家方面如此,在思想意识方面也是如此。他们用快拍子唱着《甜蜜的家庭》;他们把门神装在帽盒里随身携带;他们的葡萄藤是攀绕在阔边帽上的装饰;他们的无花果树只是一株橡皮盆景。”有成千的不幸房客,就有成千辛酸的传奇故事,甚至在“这许多飘零人的身后”还经常可以见到一两个惨死的幽灵,因为整个纽约城就是如此变化无常,就“像是一片无底的大流沙,不断地移动着它的沙粒,今天还在上层的沙粒,明天就沉沦到粘土污泥里去了”。流浪的年轻人就是沉沦到粘土污泥里去的沙粒,如今就在大流沙世界中出现,正在“摇摇欲坠的红砖房屋中间徘徊,”挨家挨户拉门铃,到处查访他的埃洛伊丝·瓦许纳小姐——五个月来他不断地打听,他知道“准是这个滨水的大城市留住了她,把她藏在什么地方”。到底把她藏在什么地方呢?欧·亨利的着眼点是“房间”。因而作家的“视点”镜头,又从外界的环境画面推向“房间”的环境画面:第十二家的门铃“在冷静空洞的深处”显得又“微弱”又“遥远”,虚幻得很,阴森得很,仿佛来自地狱的音响。那女房东的模样,又“使他联想到一条不健康的,吃得太饱的蠕虫;蠕虫吃空了果仁,只留下一层空壳,现在想找一些可以充饥的房客来填满这个空间”;“她的声音来自喉头,而喉头也仿佛长遍了舌苔”,发出的是魔鬼嘶哑的声调,正在为她的“房间”编造骗人的鬼话……魔鬼一般的人,地狱一般的景象;公寓里面一片黑暗,只有“一道微弱的光线冲淡了过道里的阴影”;楼梯的“毡毯已经完全走了样,就连原先制造它的织机也认不出它了”。“仿佛变成了植物,在那腐臭阴暗的空气里化为一块块腻滑的地衣或是蔓延的苔藓,附着在楼梯上,踩在脚下活像是粘乎乎的有机体”;楼梯拐角的墙上只有空着的壁龛,以前在这里搁过的“那些花草”已经“在污浊腐臭的空气中枯萎死去了”;而曾经在这里供奉过的“圣徒的塑像”,却早已在黑暗中被“妖魔鬼怪”拖到底下的地窖里,“让它们待在邪恶的深渊里了”……黑暗,污浊,阴森,恐怖,构成一个典型的魔幻世界,充塞着地狱的氛围和死亡的气息。小说对外界世态的观照,仅用极为简洁的几笔素描,即透视了其中某些社会形态,从物象画面的象征意象中揭示了造成美国一代青年男女爱情悲剧的根源。这种环境的展现,是由公寓的外界而进入人物的内心感受与联想的,是由社会客观场景画面来反衬人物的主观意识和心理活动的。恶劣的环境,惶乱的心情,在两相照映间,年轻人又于失望中抱有一线希望,那带在舌尖问了千百次的“你的房客中间有没有一个年轻的姑娘……”的话题,就是他心灵深处爱情秘密在矛盾环境中的泄露;而得到的答话,则从侧面暴露了寄生虫女房东工于心计、善于行骗的鬼蜮伎俩,见出金钱社会钱魔的狰狞可恶!由地狱氛围和死亡气息呈现出来的魔幻现实场景的群体形象,成了年轻人意识心态和感官印象所依附的客体,强烈地映衬了人物的内心世界,使构成环境画面的一事一人一物,都是对心事意态的衬托,由此而引起人物心理意识的辐射。
意识辐射式环境。带着破碎、沉痛的心情住进了“供应家具的房间”的年轻人,在地狱氛围和死亡气息的感受中,有较多的心理流动和意识波涌,有较大的幻觉时空和主观随意性,因而能任其飞腾跳跃,变幻闪烁,显得荒诞怪异,光怪陆离。这是展示心理形象的意识环境,充溢于整个“房间”的心绪意象,始终闪映了年轻人对情人的焦急寻找和强烈思念的心理波动,形成一种“由内向外”与“由外向内”往返回复的意识流程。因而其表达方式无不呈圆圈交错状态,即如海外华人作家聂华苓所言喻:“小说的线索不是直线进行的。重点在中央,线索是圆圈,许多圆圈错落地围绕着那个重点……”①这里的“重点”就是年轻人的心绪情思,而“圆圈”则是“房间”诸意象系列所构成的几组形象画面,许多“圆圈”就错落地围绕着“重点”旋转,滚动,把年轻人失落、颓丧、绝望的意识波澜和心绪轨迹显出来。年轻人急于找到出走的人,那双到处观察、搜寻的眼睛,就显得特别敏感,特别锐利,周围场景的任何事物,都会由他的视线得到心灵的沟通,产生心理印象,发射出内心感应的辐线。这个“房间”,“肮脏”,“破烂”,对年轻人的“迎接”,是“带着初次见面的假客气”和“强颜为欢、虚与委蛇”的“妓女的假笑”,以给人“一种似是而非的慰藉”,一开始就让给年轻人感觉到一种可怕的虚伪和无情的嘲弄。而不见情人的倩影,却见“花花绿绿的墙纸上”贴着的“法国新教徒的情侣”、“第一次口角”、“新娘的早餐”、“泉边的普赛克”等有关爱情的画片以及“几张女艺人的相片”,则又引起他特定情景中对景伤情的回忆与联想,加深他对情人思恋的痛苦。他已经“有气无力”,就跟先前住户留下的“冷冷清清的零碎东西”一样——那些住户“有如船只失事后被困在孤岛上的旅客,侥幸遇到别的船而被搭救上来带往另一个港口”,便把他和“这些漂货给扔下了”。他有说不尽的内心的孤寂与失落。但在失落与孤寂中,“房间”却又“像通天塔里的一个房间似的,讷讷地想把以前各式各样住户的情况告诉他”,使他“如一篇密码被逐一破译”一般渐趋明朗:这里住过女人——“梳妆台前地毯上那块磨秃的地方说明有许多漂亮女人在上面踩过”;这里就是牢房——“墙上的小手印表示小囚徒们曾经摸索着寻求阳光与空气”;这里有过打斗——“一块像开花弹影子似的四散迸射的痕迹,证实有过玻璃杯,或瓶子连同它所盛的东西给扔在了墙上”;这里也有过情人的思恋——“壁镜上被人用金刚钻歪歪扭扭地刻出了‘玛丽’这个名字”……历来房客,一住进这个“房间”,“总是怨气冲天”,被它的死气沉沉的阴森冷漠和令人窒息的气氛“激惹得忍无可忍”。因而“家具给搞得支离破碎,伤痕累累”;“弹簧已经脱颖而出的睡榻,活像一只在极度的痉挛中被杀死的可怕的怪物”;“大理石的壁炉架,由于某种猛烈得多的骚动,被砍落了一大块”;“地板上的每一块凹痕和每一条裂纹,都是一次特殊的痛苦的后果”……发生在这个“房间”里的丑剧、闹剧、悲剧、惨剧,正“恍恍惚惚地”掠过年轻人的心头,别的“房间”又飘来了类似的“声音和气息”:一个“房间”正“传来淫荡无力的吃吃笑声”;另外的“房间”则“传来独自的咒骂,掷骰子声,催眠曲和啜泣抽噎”.…“房间”里的气息,他呼吸着,是那样的“潮湿”,那样的“污浊”,那样的“腐臭”,就“仿佛地窖里”所“蒸发出来的那种冷冰冰的,发霉的气味”。到处笼罩着浓重阴郁的地狱氛围和死亡气息,缠绕在年轻人的周围,好比是这一组意象系列和形象画面中不断旋转的一个又一个“圆圈”,紧紧地围绕着“重点”,正在“房间”凝聚着一种“情绪的结晶”。
情绪结晶式环境。在地狱氛围和死亡气息的缠绕中,年轻人受窒息的人性和受创伤的心灵有更深入的展示,疯狂寻觅情人的痴情和执著追求爱情的坚贞有更突出的显示,因而能为我们洞开一个生死不渝的感情世界,让我们窥视一个鲜明生动的心理形象。由于寻找情人的焦急与迫切,失望与痛苦,年轻人沉入了下意识,经常出现心理幻象,产生感官错觉。刚刚才呼吸着“腐烂”的“冷冰冰的、发霉的气味”;却突然又神奇般地飘来了“一阵浓烈、甜蜜的木犀花香味”,洋溢了整个“房间”,是“那样确切、浓郁和强烈,以至像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来客”。而“有血有肉的来客”又一下子幻化为情人瓦许纳小姐,似乎“在招呼他”,不仅使他“脱口嚷道”——“什么事,亲爱的?”还同时“跳了起来,四面张望着”。情感幻觉中心理的变异,情绪的奔涌,竟使“那浓郁的香味依附在他身上,把他团团包围起来”;竟使“他所有的感觉都混杂紊乱”而只顾“伸手去摸索”,摸索“刚才触摸他的、抚摩他的”以至“招呼他”的木犀花香味——“缭绕不散的木犀花香味”——他的瓦许纳小姐,情人感官之灵,是一种爱情的奇迹,年轻人竟能一下子辨识出情人独有的、瓦许纳小姐“所偏爱并已成为她个人特征”的那种木犀花香味。然而,“这股缭绕不散的木犀花香味”,“究竟是从哪儿来的呢”?这里有着他爱情心理的凝聚。他断定她就住过这个“房间”,立刻就想找出一个证据,因为他知道,“凡是属于她的或者经她触摸过的东西,无论怎样细小,他一看就认识”。木犀香味,使他感觉,使他呼唤,使他回应,使他行动。因而他在逐一“搜寻梳妆台的抽屉”而一无所获之后,有一种意识的流漫,情绪的结晶——
接着,他像猎狗追踪臭迹似的在房间里巡逡徘徊,扫视着墙壁,趴在地上察看角落里地席拱起的地方,搜索着壁炉架,桌子,窗帘,帷幔和房角那只东倒西歪的柜子,他想找一个明显的迹象,却不理解她就在他身边,在他周围,在他心头,在他上空,偎依着他,追求着他,并且通过微妙的感觉在辛酸地呼唤他,以至他那迟钝的感觉也觉察到了这种呼唤。他又一次高声回答:“哎,亲爱的!”同时回过头来,干瞪着眼,凝视着空间。因为到目前为止,他还不能从木犀花香味中辨明形象、色彩、爱情和伸出来迎接他的胳臂。啊,老天哪!那股香味是从哪里来的呢?从什么时候开始,气味竟能发出声音呼唤呢?因此,他继续摸索着。
然而,除了许多飘零的住户的“凄凉的微细痕迹”,关于他所要搜寻的“可能在这儿住过的、灵魂仿佛在这儿徘徊不散的她”,却毫无端倪。而年轻人“激动”的打听和“恳求”的问话引来女房东的再次胡诌,谎骗,则使他的一线希望彻底幻灭。他,“垂头丧气”;“房间”,“死气沉沉”。因为彻底失望了,生命的要素消失了,所以木犀花香味也消失了。希望的幻灭,耗尽了他的信心,判处了他的死刑——他自杀了。在这里,人物的主观意识乃至潜意识和人物情绪的扩大或凝聚,与周围的气息氛围融合为一片交密之气,以年轻人对木犀花香的追逐摸索为焦点,时而放射开来,时而投射出去,对环境形成一种由内向外的展示。但在随意灵活连接“房间”诸多意象系列形象画面的同时,又有世态素描式客观场景的由外向内的展示,以此反衬人物的主观意识、心理和情绪。这种“由内向外”与“由外向内”相兼的展示,在“房间”呈现出许多梦觉,幻象,心影,气味,声响,显影在诗意浓郁的视象画面与感觉意象相交叠的意境之中,虚幻缥缈,朦胧闪烁,因而表现出一种比形象本身更为感人的诗美魔力。
年轻人思念、搜寻情人的恍惚、迷乱、忧郁、绝望的心灵历程,是一条主线,贯串于现实时空与心理时空错杂多变的环境之中,组成意识结构的三部曲。它有如一首恋歌在浅唱,凄美,哀艳;又好比一曲挽歌在低吟,忧伤,悲凉。三部曲,演奏了年轻人在“房间”的悲剧,演奏了欧·亨利对纽约的忿懑。欧·亨利笔下的纽约,是罪恶金钱社会的象征,是资本主义美国的缩影,也是魔幻世界“公寓”的一个“房间”。纽约在欧·亨利的笔下,“却没有什么闪耀的街景,而只有阴暗的小公寓,闷气的小房间,油腻的小饭店……虽然熙熙攘攘,但是充塞在每个人心头的却是无边无际的寂寞之感”——“它是无数搁浅在资本主义钢铁都市里的小职员的寂寞,它枯燥无比,它摧残一切生机,它杀人。”②《供应家具的房间》所演奏的,也正是“杀人”三部曲。那始终弥漫在“房间”里的令人窒息的地狱氛围和死亡气息,是如此浓重,如此强烈,这种悲剧气氛的烘托,绝望情绪的渲染,是欧·亨利,小说中所鲜见的——它“几乎可以同早期美国短篇小说大家爱伦·坡的作品乱真——所不同的,是爱伦·坡着重神经质的变态心理,竭力制造恐怖,而欧·亨利,这种氛围只是更有感染力地衬托出一个绝望的处境:在无情的纽约城,贫穷的青年永远在做疲倦的旅客,永远从一个破旧的公寓转到另一个破旧的公寓,脆弱的爱情只不过点染了同一悲惨的命运”③。尽管欧·亨利表现了小人物生死不渝的爱情,那曾经缭绕不散的一股浓烈的甜蜜的木犀花香,就是这种爱情的象征,然而爱情却逃不脱幻灭的命运,缭绕不散的木犀花香,最终还是在魔幻世界消失了,就像“鲜花盛开的热带岛屿”被淹没在“波涛汹涌的海洋”一样。这一喻中主题,在欧·亨利的小说中,很典型,很有代表性。歌颂“合乎人性”与抨击“违反人性”,以及控诉“违反人性”扼杀“合乎人性”,是欧·亨利小说创作的总主题。可以说,《供应家具的房间》的主题是这一总主题的凝缩,因而这里的“缭绕不散的木犀花香”的“消失”与“鲜花盛开的热带岛屿”被淹没在“波涛汹涌的海洋”的比喻,可以看作是欧·亨利创作总纲领的形象化诠释。这里所展现的“房间”,实际上是被微缩在小说里的一幅美国式的“地狱”全景图,通过对“房间”的放大,即可看到一个典型的欧·亨利创作背景,一个欧·亨利整体小说的总的典型环境,而从展现环境与揭示主题看,《供应家具的房间》则又是欧·亨利整体小说的一个“微型”,一件“微雕”,有它的独特地位和特殊价值。
小说对悲剧主题的揭示,得力于环境的展现,因为环境更宜表现心理,而爱情,则是一个心理的世界,只有减弱故事情节而突出环境气氛,使性格模糊而心理清晰,才能充分表现人物的内心活动,深入到主观意识乃至潜意识的领域,窥探人物秘隐幽深的感情。何况心理也属于性格范畴,可以内在的、隐现的丰富性格内容,可以深刻揭示主题。由此,即可看出,为什么以讲故事见长的欧·亨利,会在创作中,从最常见的以编织情节为结构中心的宏观形象结构,变异为以人物心绪轨迹为结构脉络的微观意识结构,改观了人物形象构成及其表现形式,更新了小说形象结构的艺术形式,这就是所谓内容决定形式,也可以说是欧·亨利创作风格变异的依据,意识心态和心理情绪,人人皆有,随处可感,表现于小说形象,也表现于作家自身,两者相互交流融会,在作品泛漫一团朦胧之意,蒸腾一种氤氲之美,读者因而能在情绪氛围的感染中引起心灵的呼应与震荡,产生诗趣盎然的审美情致。人的内心活动有广阔的“真实”的领域,是作家自由驰骋的无穷的天地。“世间有一种比海洋更大的景象,那就是天空;还有一种比天空更大的景象,那便是内心的活动”。④这是雨果的名言。“人类情绪的种种表现,都是写小说的材料。”⑤这是欧·亨利的信念,扩散于《供应家具的房间》里的种种情绪,也是通过作家自己的爱情经历和痛苦感受表现出来的。在小说主人公的心灵屏幕上,也反射出作家过去的恋情心理和感伤情绪。欧·亨利是一位感情丰富而又深沉的作家,他的爱妻阿索尔·埃斯蒂斯,也是“一个漂亮姑娘,个子不高不矮,细腰身,金红色的头发”,她勤劳淳朴,温柔善良,很有文学才华,在办《滚石》周刊和创作活动中曾经是欧·亨利同甘共苦的伴侣和忠诚得力的助手,有过一段美好的爱情生活,就像缭绕不散的木犀花香,浓烈,甜蜜。但不幸的是木犀花的过早凋谢,就在欧·亨利人生经历最惨痛时,心身交瘁的埃斯蒂斯永远离开了他,如木犀花香一般消失于魔幻世界!从此,永远消失的这一股爱情的木犀花香,就一直凝聚在作家的心头,缭绕不散,不管是关进牢狱内,还是走出牢狱外,他都在灵魂里苦苦寻找他的埃斯蒂斯。到了定居纽约,欧·亨利在文学上成名了,但曾经患难与共的爱妻,哪里去了呢?回忆,怀恋,思念,无休无止的哀伤,却使心中那爱情的木犀花香更为“确切”,“浓郁”,“强烈”,从中郁结着一种“此恨绵绵无尽期”的心意情绪,这就是欧·亨利的“情绪的结晶”,把它投放到小说里,就是年轻人思恋、寻找瓦许纳小姐的意识流动,心绪轨迹,情绪的扩大与凝聚。欧·亨利在这个时候把他的“情绪的种种表现”化为“写小说的材料”的,还有诸如《麦琪的礼物》(1905)、《爱的牺牲》(1904)等名篇,都是相隔不久而跟随《供应家具的房间》写出来的,其中德拉和德丽雅都是阿索尔·埃斯蒂斯的化身,都有欧·亨利爱情心理的闪映,又都寄托了作家“追寻”与“再现”的情愫和愿望。触景生情,应物斯感。欧·亨利有不少小说是对他自己不幸人生的写照。欧·亨利的命运之路充满了灾难,所以他的小说经常反映的也都是小人物心灵痛伤的一面。不少小说的主人公有他的影子,有许多题材来自他亲自经历的生活,出现在小说人物身上的种种遭遇,都有他的情绪意象的外射。因而,《命运之路》有他自传意识的渗透,《华而不实》与《汽车等待的时候》有他纽约观感的反馈,《最后的常春藤叶》有他人性感应的闪光,《重新做人》有他监狱见闻的心理印象……而尤其难得的是与此同时,欧·亨利又能在自己的小说艺术上变“异”求“新”,如《命运之路》的超现实主义⑥《华而不实》与《汽车等待的时候》的“隐蔽的”心理描写手法⑦,《最后的常春藤叶》的创作风格的变异⑧……这都是对欧·亨利小说的创新,都是对欧·亨利风格的突破,因此都显得有点欧·亨利的“陌生”。但“陌生”,才有新鲜感,才有生命力。
在小说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意识结构,以及所谓的时空交错结构,心理反应式结构,心理印象小说,心态小说,无性格小说,等等,它们同属于“陌生化”文学家族。它们脱胎于性格小说,冲破传统的为人所熟知的以故事情节见长的“封闭式结构”模式,建立以心理形象为主体的开放性“新小说结构”,在本世纪前以至本世纪初,即开始出现并崛起于世界文坛。许多世界名家名著中,它们都榜上有名,如契诃夫的《吻》、《苦恼》、《万卡》,安徒生的《卖火柴的小女孩》,显克微支的《音乐迷杨科》,鲁迅的《幸福的家庭》、《示众》,还有美国女作家尤多拉·韦尔蒂的《一条新闻》,孙犁的《荷花淀》……都是脍炙人口的。随着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兴起和渗透,在我国繁荣发展的新时期小说创作中,这一“陌生化”家族才为许多小说家所探索所借鉴,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如王蒙创作的《春之声》等六篇系列小说,这曾引极大反响,激发了不少中青年作家追求“陌生化”的热情,给中国文坛带来了勃勃生机,这说明“陌生”家族是有自己的生命力的,因为这里有广阔的“真实”的领域,可以扩大作家的审美视野。现在我们研究欧·亨利的意识结构,正是为了深入这一广阔的“真实”的领域,去作审美视野的扩大。虽然我们对著名的“欧·亨利手法”并不陌生,但是还有一些陌生的“欧·亨利手法”,正有待我们进一步发掘,做认真研究,以让陌生的“欧·亨利手法”,不为我们所陌生。
1995年2月上旬写于华侨大学西苑
注释:
①聂华苓:《亨利·詹姆士及其现实主义》,《上海文学》1980年第10期。
②王佐良:《照澜集》,外国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21页。
③王佐良:《照澜集》,外国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21页。
④雨果:《悲惨世界》,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273页。
⑤转引自张易博《木犀花·译序》,台湾金枫出版社1987年版,第4页。
⑥《名作欣赏》1994年第6期,“欧·亨利小说名篇探赏系列之一”。
⑦《名作欣赏》1995年第1期,“欧·亨利小说名篇探赏系列之二”。
⑧《名作欣赏》1995年第2期,“欧·亨利小说名篇探赏系列之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