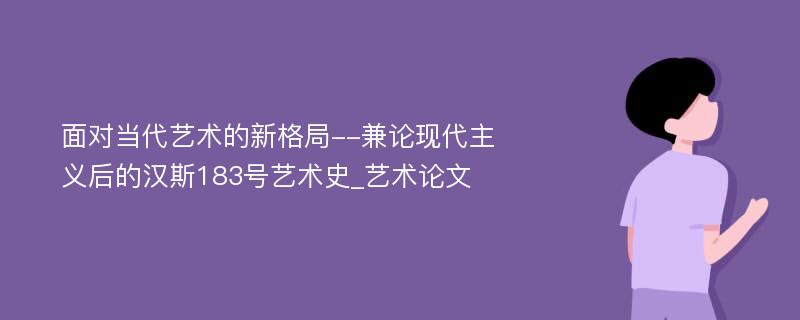
面对当代艺术的新版图——评汉斯#183;贝尔廷《现代主义之后的艺术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贝尔论文,现代主义论文,版图论文,汉斯论文,当代艺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汉斯·贝尔廷(Hans Belting,1935-)是德国著名艺术史家,其研究领域主要涉及欧洲中世纪和文艺复兴艺术以及图像史、西方当代艺术和新媒体艺术等。迄今为止,贝尔廷已经出版了三十多部著作,其中一些被翻译成多种语言。作为近二十年来在西方艺术理论界影响力颇大的德语艺术史家,他不仅接受过严格的艺术史传统训练,还敢于面对艺术实践与艺术史研究的新情况和新状态,不断调整自己的视角、立场和观点,力图使艺术史的书写更具有当代性和生命力。眼下,贝尔廷教授在中国艺术史界和艺术学理论界声名渐起,其学术观点正在引起刚刚经过学科重新划分的中国艺术理论界的极大兴趣。 《现代主义之后的艺术史》初版于1995年,主要内容是对1983年出版的《艺术史终结了吗?》所提出的问题的继续探讨。该书2002年的第二版纳入了从贝尔廷提出“艺术史终结”这一话题之后艺术理论界的一些新发展和他的新思考。2014年,该书同时出了两个中译本:一为南京大学出版社的洪天富译本,该译本据2002年的德文版译出;二为金城出版社的苏伟译本,该译本据2003年的英文版译出,并附有卢迎华和苏伟的相关评论。贝尔廷指出,当代西方艺术的内涵已经发生了诸多变化,这些变化深刻地影响到叙述艺术史的话语体系,甚至预示着艺术史话语发展的新方向。在《现代主义之后的艺术史》(本文引用的是洪天富译本,引文凡出自该著者均只随文标注页码)中,贝尔廷紧紧围绕着“艺术史书写”这个中心议题,提出了一些富有启发性和思考性的相互关联的论题。 一、艺术史何以会终结 首先需要确认的是,贝尔廷最早在西方学界提出了“艺术史的终结”,这在当时的欧洲艺术理论界引起了轩然大波。此后,在《艺术史终结了吗?》、《现代主义之后的艺术史》等著述中,他不断地阐发这一命题。扩大来看,西方艺术理论界的“终结”论肇始于德国哲学家黑格尔。黑格尔在《美学》中提出:“就它的最高的职能来说,艺术对于我们现代人已是过去的事了。因此,它也已丧失了真正的真实和生命,已不复能维持它从前的在现实中的必需和崇高地位,毋宁说,它已转移到我们的观念世界里去了。”①这里所说的“艺术”,既指实践方面的,也指精神气质上的。他认为,当艺术再也无法满足人们心灵需要时,其地位就会逐渐被宗教和哲学所取代。在黑格尔之后,美国学者阿瑟·丹托在20世纪80年代也提出过“艺术的终结”。他指出,“艺术的终结”并不是“艺术死了或绘画不再被人们画了,而是叙事结构的艺术史已经结束了”②。现代主义艺术有着与传统艺术全然不同的经验,前者总是试图探寻艺术的“本质”,试图进行哲学思考。“当艺术的哲学本质获得某种程度的意识后,那种叙事便终结了。”③丹托的观点影响了不少当代西方的艺术批评家,他们“对维护传统艺术观念的理论家进行了批判,站在丹托等具有颠覆性特点的理论家一边”④,并且还具有相当的影响力。 然而,贝尔廷却认为自己所说的“艺术史的终结”与丹托所说的“艺术的终结”不是一回事。“丹托指出,自从艺术本身提出有关艺术的本质的哲学问题以来,艺术正在变成‘艺术的媒体中的哲学’,从而背离了它的历史。早在以前发表的《寻常物的变形》……一文里,丹托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自从艺术从现象学的角度看不再区别于日常生活里的日用礼节,更多地让一种哲学的行为给自己下定义以来,艺术意味着什么……他现在解释:‘当艺术变成另外一种东西,即变成哲学的时候,艺术已经走到尽头了。’”(第24-25页)丹托的意思非常明白:艺术是艺术,对艺术的哲学思考则是艺术哲学;把艺术等同于哲学就是艺术的“终结”。“丹托的‘艺术的终结’指的是传统艺术的终结,因为艺术已失去了使其自身区别于其他事物的形式,意味着将出现新的艺术定义,由此艺术获得更大的开放性,丹托的观点是哲学取代艺术,也有匈牙利艺术史家宣称‘艺术取代哲学’,但这两者都与贝尔廷的主题完全不同。”⑤因此他声称从来都不赞同“艺术终结”这种观点。 那么,贝尔廷所说的“艺术史的终结”到底意指什么呢?我认为可以从以下方面来思考。 首先,该问题涉及对“终结”这个词语的理解。“终结”一词在西语中的含义与汉语的意思并不完全对等。黑格尔的“终结”使用的是德语“der Ausgang”一词,其含义除了汉语的“终结”之外,还有“入口”、“出口”、“出路”等。在他那里,艺术在“终结”之后还会继续存在,只不过最终要归于哲学。丹托使用的英语“end”一词,除“终结”的含义外,还有“边缘”、“范围”、“目标”、“目的”等。因此,贝尔廷一语道破:“关于‘终结’的传言并不意味着‘一切都完了’,而意味着‘改变话语’,因为事情发生了变化,不再和它原来的框架相适应。”(“序言”) 其次,还涉及对“艺术史”内涵的理解。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理解:其一,指艺术发展的历史;其二,指对于艺术发展历史所进行的学术研究,包括对艺术作品的鉴赏和对艺术史的梳理。这两种含义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正如贝尔廷所说:“艺术,在最狭窄的意义上只是艺术作品中可确认的一种品质;同样,历史也只存在于各种不同的历史事件之中。一个‘艺术的历史’将艺术作品中培育出来的艺术的概念转化成一种历史性陈述的专题学科,它独立于作品之外,又反映在作品之中。艺术的历史化就这样成为艺术研究的一种普遍模式。”⑥实际上,在欧洲,“艺术”和“历史”这两个词语的现代含义直到19世纪才得到确立,即“美的艺术”和“历史叙事”,而这两个词语结合成“艺术史”,也是19世纪才出现的事情。 第三,该问题还进一步涉及艺术与艺术史的关系,这成为理解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贝尔廷打了一个形象的、易于理解的比方。他把艺术比作图画,把艺术史比作画框:画框始终都要和图画相匹配。“在艺术的历史这一概念中既包含一幅图画的意义,也包含对一种框架的理解:图画意味着艺术事件,框架意味着被书写的艺术史。艺术一直和艺术史的框架相适应,就像艺术史的框架始终跟艺术相配一样。所以,我们今天不会说终结,而会说破框,破框造成的后果是,图画解体了,因为图画不再被关在它的框架里。”(“序言”)这样,“艺术事件”(图画)与“艺术史”(框架)的关系就意味着:一旦艺术事件出现新的变化,书写艺术史的框架就应当随之改变,目的在于更为有效地叙述新的艺术事件。否则,框架就会失去其有效性。 这就是“艺术史的终结”问题最重要的意涵:它实际上宣称的是一种艺术史传统的终结,一种艺术史叙事模式的终结,或者说是叙事模式在发生变化,而非人类的全部艺术史的终结。“艺术史的终结并不意味着艺术或艺术科学已经寿终正寝,而是记录下这样一个事实,即在艺术或艺术史的思维图像(Denkbilder)中,呈现出一种从现代派以来以我们所熟悉的形象变成为法规的传统的终结。”(第12-13页)在贝尔廷看来,这种必须终结的艺术史叙事模式和传统,是从欧洲“艺术史之父”瓦萨里开始,经过黑格尔的理论强化,到19世纪被固定下来,并一直延续到现代主义艺术泛滥之时的欧洲艺术史传统。其特点在于把各种丰富多彩的艺术事件框定在一种线性的、单一的和进步主义的历史叙述框架之中,以彰显这种叙述模式的普世性价值观。在《现代主义之后的艺术史》中,贝尔廷考察了19世纪出现的这种线性的、进步主义的艺术史观是如何生成的:瓦萨里首先完成了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叙事,把艺术史看作是一个不断进步的历史进程。在西方文化史上,瓦萨里的《意大利艺苑名人传》是影响深远的开山之作。在书中,他把艺术发展看作是类似生物的诞生、成长、衰老和死亡的阶段,当然这不完全是瓦萨里发明的。在当时,几乎所有的人文主义者都或多或少具有这样的历史观。在作品第一部分的“序言”中,他说:“我想让他们(按:指同时代的艺术家)知道,艺术是如何从毫不起眼的开端达到了辉煌的顶峰,又如何从辉煌的顶峰走向彻底的毁灭。明白这一点,艺术家就会懂得艺术的性质,如同人的身体和其他事物,艺术也有一个诞生、成长、衰老和死亡的过程。我希望以此途径使他们更好地认识到艺术复兴以来的进步以及它在我们时代所达到的完美。”⑦瓦萨里对西方早期艺术史的总结从框架上讲是比较传统的,他提出的“艺术再生”概念具有隐喻性和象征意义,这是对其时代文化发展的一种新认识。这种观点对后世艺术史的书写具有深远影响。黑格尔则把艺术看作是人类精神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认为艺术的终结和艺术史的终结都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19世纪以来的整个欧洲艺术史遵循瓦萨里的逻辑,全然变成了佛罗伦萨艺术史的翻版。正因此,贝尔廷对这种艺术史传统提出了强烈的质疑,他告诉我们经典艺术史的规范失效了,19世纪末以前的艺术史家们建构的艺术史书写原则已经无法对当代艺术进行有效判断。 艺术作为人类的特殊表达方式,要传达人类自身的体验与观念。每个人、每代人、每种文化,都要在创造艺术和诠释艺术中寻求意义。而艺术史是对艺术之历史发展的某种叙述。“一种包罗万象的艺术史的观念,在较为亲密的艺术家圈子之外,只是在19世纪才被普遍接受的,而包罗万象的艺术史逐渐地掌握的材料则源出过去的几百年和几千年。换句话说,艺术早就被人们生产了,但是尚无满足艺术的需要的一种特殊的艺术史的观念。”(第15页)“看起来好像在艺术的‘破框’之后,随之而来的是开放性和不确定性,甚至是无把握性的一个新的时代,这种无把握性是从艺术史传染给艺术本身的。”(第15页)贝尔廷敏锐地感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洲艺术的发展出现了众多新变化,这促使艺术史研究和书写面临着扩大研究对象、拓展研究视野、突破旧的研究方式、理论学科范式转型等迫切需要。因此,传统艺术史的叙述模式遭受质疑和挑战就势在必然。 二、如何书写艺术史 艺术史的书写借助特定的叙述模式和观念,旨在说明艺术家、艺术作品和欣赏者之间的关系在历史中的变化和走向。从理论上讲,只要人类社会存在,艺术创造和对艺术的阐释就会继续存在。只要艺术不会终结,对艺术进行的历史叙述亦不会终结。艺术史的书写,始终要面对艺术发展的新情况和新趋势,而不是固守某种观念,或者是用艺术来诠释和演绎固有的观念。贝尔廷认为,瓦萨里书写的艺术史,实际上是在某种观念支撑下的历史,因而成为一种观念的历史。瓦萨里所确定的观念框架对他来说非常方便和实用,但后来者却会受困于这种框架,难以对艺术发展的新情况和新趋势做出具有说服力的阐释。 如何书写艺术史,首先涉及到谁有权对艺术进行阐释的问题。从历史上看,最初是“诗人们能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众所周知,诗人们曾经是艺术的最初解释者。又好又古老的艺格敷词(die gute alte Ekphrasis)一直流传到今天。早在古希腊罗马文化时期,诗人们为了描述一部艺术作品,运用艺格敷词,以自己绘声绘色的语言再度创作这部艺术作品。当然,在今天,这方面的发言人是作家或哲学家,而不是历史性的艺术的专家”(第40页)。在古代希腊和罗马时期,诗歌是最为重要的艺术门类。由于诗歌担负着颂神的任务,因此诗歌和诗人们往往享有崇高的地位,诗人们自然就享有对艺术作品的解释权,诗歌常常高踞于艺术殿堂之上。 我们今天称之为“艺术”的东西,在古代希腊和罗马不过是技艺的一个方面而已,如木工、铁工、外科手术之类的技艺或专门培训的技能,它们都不专指现代意义上的“美的艺术”(fine arts)。今天人们所说的首字母大写的“艺术”(Art)的意涵,在18世纪中叶以后才逐渐被确立起来,并且最终与技术、手工艺等概念区别开来。雷蒙德·威廉斯认为,这种变化“记录了艺术的性质与目的、艺术与人类活动的关系、艺术与整个社会的关系等观念上的一个显著的变化”⑧。18世纪中叶以后,“从法国神父巴托开始,经过法国学者狄德罗、达朗贝尔、英国学者夏夫兹博里、哈奇生、德国学者鲍姆加登、迈尔,一直到康德,现代美学体系在这些并非艺术家的理论家的手中逐渐被建构起来”⑨。“这样一种人为建构起来的‘美的艺术’的美学理论体系,充其量是哲学家或理论家们自身观点和理论的一种演绎。”⑩自此往后,对艺术的解释权转移到了贝尔廷所说的作家或哲学家手中。他们将自己的观点和理论延伸到各个艺术领域。但遗憾的是,他们对艺术做出的解释,有时与艺术的实际情况相背离,难以具有真正的说服力。 20世纪以来,作家和理论家对艺术的介入,在现代主义艺术中集中表现为艺术评论与艺术作品的关系。在贝尔廷看来,这种情况对艺术来说并非福音,而是试图以评论来取代作品。他直言道:“艺术评论总是希望消除与作品的分歧,进而取代作品,也就是说,艺术评论与作品的关系是一种模仿的关系,前者力争作为艺术。随着艺术作品失去其作为作品的自成一体的形态,只借助于与艺术本身竞争的评论介绍自己,这方面的诱惑就增大。自从哲学家和作家撰写艺术家联合会的宣言以来,艺术批评就承担了艺术理论的任务。”(第41页)马里内蒂写了《未来主义宣言》,布勒东写了《超现实主义宣言》,这使他们成了“主义”的“代言人”和“工头”,由此造成的景观是:“新的理论接二连三的增多把每一种理论都压缩到一句口号,在这句口号后面,聚集着一批共同奋斗的艺术家……新的理论持续不断的增加迫使每一部作品都兑现一种共同的理论。所以,作品原则上受理论的约束,而后来的解释者不得不尊重理论。”(第42页)这里揭示的情形实际上是艺术理论借助于艺术评论先行并且泛滥。艺术史家受此影响,也试图以艺术作品来服务于自己的专业和学术实践。尽管贝尔廷表面上没有对理论先行和理论泛滥的情况进行褒贬,但其言下之意显然不赞成作家和哲学家用自己的理论为艺术设立围墙。他对艺术作品和批评文本“同义反复”的现象进行了尖锐批评,认为“从这样一种处境中传统的艺术科学很少能够获益,因为它似乎不得不局限于报道作品的产生(和完成)”(第43-44页)。如此看来,艺术史的书写不仅有瓦萨里模式的禁锢,更有现代艺术中作家和哲学家们所设置的种种围墙,艺术史的书写最终都变成了“实用艺术理论”。 那么,艺术史书写是否需要理论,或者说是否需要接受某种艺术观念的指引呢?通过对艺术史书写的历史回顾,他得出了这样的看法:“任何艺术的历史性描述历来都同某种艺术观念联系在一起,这种艺术观念恰恰是借助于艺术的历史性描述而证明自己是有效的。”(第245页)对此,我认为应当一分为二地看待。一方面,如果仅仅是用艺术史的材料来证明自身理论的正确或有效,或许可以认为是凭借一种理论的暴力来人为地确立某种价值规范和准则。倘若再把这种人为的而不是从艺术事实中概括出来的价值规范和准则说成是普世性的或永恒的,那么这正是贝尔廷坚决反对的。另一方面,任何艺术史的书写始终都会从某种立场或视角出发,总要受到书写者的艺术观念、美学观念、价值准则的引导、约束和影响。我们无法想象、也无法赞同艺术史的书写不需要理论,不受艺术观念的制约和影响。事实上,迄今为止,我们找不到任何一部已经写就的艺术史是没有理论立场、艺术观念和价值准则指引的。 贝尔廷并不反对艺术史的书写需要理论和艺术观念,他反对的是试图把某种艺术观念或理论指引下叙述艺术史的模式固定化,把对艺术史的某种特定阐释看作是普世性的。比如欧洲艺术史上曾出现的典型个案:古代修辞学发展出的风格理论规定了阐明艺术的某种标准或某种理想,其周期性的固定模式最终因不再有效而终结。在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历史编撰学建立了一种坚定不移的价值规范,用这种价值规范仿佛可以复测总是作为一种历史现象的艺术中的理想美”(第246页)。这种价值规范体现在瓦萨里的“生长、成熟和日渐衰老的生物模式”之中,它对欧洲古典主义艺术观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实际上,这是一种观念的历史,也因为不切实际而告终。瓦萨里最重要的后继者是温克尔曼,他沿用了瓦萨里的周期性生物学循环模式,以此来理解“真正的古代艺术”,只不过他在叙述方面采用了新形式。对于这种艺术史书写的方式,贝尔廷是这样总结的:“以前,人们向一种包罗万象的艺术学说的价值观念看齐,以便历史地描述艺术,现在,人们依靠多余的历史研究的陌生模式,或者依靠哲学的美学的陌生准则,而哲学的美学总是把艺术理解为一种独立于历史和经验语境的纯粹原则。”(第248页) 上述所有艺术史书写的方法和模式都可以追溯到黑格尔哲学。它所造成的后果标志着旧艺术史与新艺术史之间的转折点,即为艺术的历史发展提供一种哲学依据,把艺术当作与思想史的“过去状态”相联系的一种文化产品,而不是一种在艺术家生动的实践中展示出来的本质。这样一来,艺术就只有在“过去”或者博物馆之中感受自身的存在,其审美的自主权在理论、观念、历史回顾和博物馆的围墙之中丧失殆尽。针对黑格尔哲学对现代主义艺术之影响的弊端,贝尔廷指出:“黑格尔的错误在于:在历史之外能够对历史作出评价。”(第253页) 不同艺术史家对欧洲艺术史书写历史的回顾和评判,旨在表达他们对艺术史书写之未来的看法。艺术史作为欧洲现代性的产物,与现代主义艺术及其观念相关。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内部再也无法维持一种统一的、普世性的艺术观念。与此同时,当代艺术在媒介与观念上不断突破现代主义以来的种种规范和模式,使得当代艺术难以被纳入旧有的艺术史书写的模式之中。所以,贝尔廷一方面提出“艺术史的终结”,力图解构传统的艺术史书写的模式,另一方面也明确指出书写当代艺术史的可能性,希望艺术史书写的延续要重视以下维度:重视不同学科之间的对话与交融;延续传统的风格史研究;把过去对艺术受众的经验主义研究推向更深层面;关注大众传媒、语言符号和图像符号的研究;寻求艺术、艺术家与其所处的文化语境的关联;回到艺术史研究的学科存在价值的研究上来。 三、现代主义之后的艺术版图 现代主义之后的西方艺术史的统一图景逐渐瓦解,艺术史版图的基本特征是关注艺术实践的当代性、艺术批评与艺术市场的强势介入、西方与东方的分裂以及艺术追求的多元性。 我们会发现,在这种分裂的图景之中,“虽然各个理论家所关注的问题大体相同,但他们的立场、出发点、依据的理论资源、论述的方式和得出的结论都极为不同。换言之,他们对同样问题的看法是极为‘多元化’的,几乎找不到任何主调……我将其命名为‘马赛克主义’。这个词语的基本含义是指:各种理论观点和批判方法杂陈,彼此之间没有多少内在的联系,各自的视角和关注点极为不同,形成了一种看似‘众声喧哗’的局面”(11)。这种情形的出现,与20世纪初以来现代主义产生的语境有密切关系。艺术上的现代主义,在诸多方面体现出欧洲现代性进程的影响与后果。它寻根于传统,却又打破传统,面向未来。正如有西方学者所言:“现代主义之所以引人注目,因为它常常被描写成是对工具理性和市场文化大行其道的反抗。它试图为个性、独创和美学价值在一个愈发单一的资产阶级世界里保留或创造一片空间。”(12)早在19世纪末,经典现代主义就已经显露出深刻的内在危机,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逐渐造成了西方内部的分化,围绕着殖民话语的论争在世界各地蔓延。这种语境导致现代主义在自我神化中不断消耗能量,导致现代主义艺术史的书写面临着危机。因此,现代主义艺术家们在一个日渐分裂的世界中寻求灵感,创造出表达现代社会新奇和快速发展的各种形式、媒介和符号。这种语境促使人们开始对艺术史的书写进行自我反思。 那么,艺术史书写如何面对艺术的当代性,这是一个非常迫切的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经典现代主义试图按线性发展的模式继续书写艺术史,继续引导艺术的发展。但战后的艺术实践却在不断地挑战这种艺术史书写的模式,艺术的意义日渐在与日常生活的对话中形成,人们像感知日常生活一样去感知艺术。这种情形多少蕴含着对抗艺术史的意味。贝尔廷注意到,在现代主义艺术向当代艺术过渡的过程中,大众文化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最终导致了传统艺术史书写模式的转变和终结。消费社会和大众文化塑造着新的艺术表达方式,艺术反而因此具备了自我反思与自我批判的能力。正如他所说,面对大众文化的裹挟,“艺术用双重的游戏作出回答:要么对自己表示怀疑,要么在这种情况下保住自己”(第147页)。与此同时,艺术批评在艺术机制中逐渐成为艺术世界的日常话语,成为艺术生产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艺术批评的存在,让现代艺术史成为现代艺术历史的历史,可以说,艺术批评在某种意义上把艺术系统中的诸种要素融合起来了。 在此基础上,我们也需要关注艺术史和艺术批评对待艺术品的不同方式。艺术史学者运用人类学、图像学、符号学、文化研究等专业知识对艺术品进行跨学科研究,探讨艺术批评在对艺术品的阐释中扮演的角色。有时,艺术批评试图消除自身与艺术品之间的区别,用评论指代艺术。有时,艺术史和艺术批评感兴趣的东西超越了艺术品本身,将目光更多地投放到其他与艺术相关联的话题之上。艺术家与批评家之间似乎也存在着对作品阐释权的争夺。两者时而共谋,建立一种具有时效性和历史意义的价值标杆;时而成为话语权的竞争对手,以求为自己的价值观争得一席之地。艺术批评与艺术实践相辅相成,艺术批评的转向大多取决于艺术实践的发展。在当代,批评深刻地介入到艺术实践中,介入到艺术理论的生产中,但艺术的本性或许是抗拒理论阐释的。在批评与艺术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张力。艺术批评的目的是对艺术品的解读,离开这个中心,它也将失去意义。作为一种意义的存在,艺术作品的价值是在具体情境中、在意义的传递中体现出来的,而这种意义的阐发有赖于艺术批评。不过,批评也会受到时代语境的局限。当然,也正因此,它才能够更准确地反映出时代的精神气质。 在现代主义之后的艺术版图中,还必须提及一个事实,即艺术批评在当下看起来似乎非常兴盛。批评家们炮制出大量批评之后又迅速被淹没,导致批评无所不在,但又缺乏生命力。那么,到底是什么力量在背后支撑着这种现象?在贝尔廷看来,这种力量就是艺术市场。当代艺术市场的力量在消除批评的需求、占据市场主导权的拍卖价格方面已经超越了批评家的价值判断。正如鲍德里亚所说:“艺术批评原本是一种制造权威的方式。但在以消费文化占主导地位的后现代社会中,即便是打着‘前卫’名义的当代艺术也成了商品,现代主义推崇的权威消逝了,社会的中心和本质意义都不存在了,艺术批评只能与商业体制勾结,共同制造‘艺术的阴谋’。”(13)在当代资本全球化的冲击之下,艺术批评不可避免地会丧失权威性,但也有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即便背后的支撑是市场,艺术也需要体现出独有的价值判断。如果说传统艺术批评更多的是一种外在判断的话,当代艺术批评则更多地体现为一种与艺术史和艺术创作血肉相连的内在判断。所以,当代艺术和艺术批评并不会像鲍德里亚预言的那样死亡,它们只不过是变换了存在的方式和面目而已。 当代欧洲艺术版图分裂的图景,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东欧剧变之后,西方与东方的对立这一古老话题再次被推向艺术史舞台的中心。在古代,有亚历山大大帝东征、罗马帝国和基督教分裂所造成的东西方文化碰撞与冲突,近代以来有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扩张带来的东西方文化碰撞与冲突。这种历史上的对立状态也在当代延续:“一种文化靠牺牲另一种文化以及也许借助于另一种文化为生。随着这种对峙状态的消失,这两种文化很难在迄今为止的自我观照中活下来。它们各自的艺术处在一种历史的传统中,而两者的历史传统是互不相容的。”(第101页)在“冷战”时代,欧洲艺术版图的分裂呈现出的特点是:在俄罗斯,先锋派艺术家长期在西方引起议论,以致人们误以为现代主义只产生于西方,而在东方一再遭受打压。在东欧地区,现代主义属于地下的非官方文化,各国的艺术通过现代主义寻找到了与西方艺术联系的通道,而本土艺术则成了西方殖民化的产物。在东德和西德,由于意识形态的对立,出现了两种德意志艺术,造成了至今都难以弥合的对立与反抗。东欧剧变虽然结束了以意识形态对立为主要色调的东西方分裂局面,但在贝尔廷看来,情况并不令人乐观:“西方文化标榜自由的思想价值和资本的物质价值,今天似乎正在变成历史的全权继承人,它恨不得一口吞下其他的、多方面遭到诋毁的文化……恰恰是在东方,西方文化的魅力暂时还是不可抗拒的,因为东方长期被隔断同西方文化之间的联系。”(第106页)然而,在这种貌似统一的外表之下,依然存在着不同价值观、艺术体制、艺术风格等方面或明或暗的突出与对立,以至于很多人认为,实际上存在着两个欧洲:一个是罗马的欧洲,另一个则是拜占庭的欧洲。 面对这种外表统一、内在分裂的当代欧洲艺术的版图,我们不应当再刻意回避东方和西方的问题,应当允许在艺术史中存在两种不同的声音,应该有一种“世界艺术”。艺术史不应仅仅是欧洲的艺术史。艺术史书写的眼光应当超越欧洲,着眼于全世界,把东西方的问题置于世界范围内考察:“东方和西方这个题目是一个欧洲的题目,这个题目似乎逐渐取代西方艺术(Western Art)这个迄今为止的题目,而在世界艺术这个题目内,东西方这个题目压根儿没有找到自己的位置。但是,欧洲早与自己的历史失去联系,而且在西部这一半(指西欧)里长期陶醉于关于理想的西方的赎罪梦,在这个赎罪梦里,东欧完全被排除在外。”(第113页)世界艺术是贝尔廷思考艺术史书写的另一个重要切入点。全球性文化要求限制欧洲文化产物的艺术史,世界艺术是艺术史书写的一种新地理学。“全球层面的艺术并不意味着可以在其中辨识出一种内在的审美特质,也不意味着对于那些被看作是艺术的东西有一个全球性的概念。它不代表一种新的语境,反而表明了语境或者焦点的丧失,它通过暗示在国家、文化或宗教诸层面都存在的地区主义和部落化的反向运动,来表明自身也包含着矛盾。”(14)所以,这种世界艺术的新版图不是统一的、同质化的、普世性的艺术史图景,而是多元并存和跨文化对话的;不遵循一种普遍有效的艺术标准,而是所有国家或地区共同参与。“世界艺术的规模越来越大,它也提出了跨文化的论点,非西方的艺术家们用西方的媒体和艺术类别发表自己的意见,借此将家乡的传统继续进行下去,同时用对话的方式对西方文化表态,甚至对之作批判性的评论。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产生一些不寻常的作品和作品理念,但这并非西方文化的功劳,只有当西方的艺术能够对此作出创造性的反应时,西方文化才能在其中扮演一定的角色。”(第127页)多元文化平等对话,异质传统并存,或许就是他所期望的“现代主义之后的艺术史”的愿景。这种愿景固然美好,但在实际的实现过程中还存在许多矛盾与冲突,其道路依然漫长。 作为当代西方著名的艺术史家,贝尔廷最重要的贡献是力图跳出西方传统的艺术史书写模式和欧洲中心主义的窠臼,面向艺术实践的当代性,面向新媒体、艺术市场和艺术批评等不断变动着的领域,质疑固定不变的艺术史话语体系。他试图以艺术创作实践本身为基础来展开艺术史的研究,建立艺术史与创作者之间的真切联系。当我们面对不断变化的艺术史书写之时,当我们面对不断被质疑的艺术史学科、艺术史书写、艺术批评、艺术的文化身份等问题之时,贝尔廷的思考足以让我们对中国当代的艺术实践和艺术面貌进行自我反思。 每个时代的艺术创作和艺术史书写,都是一种创造性实践,需要变化的是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描述和评判它。艺术史本身也是在被不断书写的。艺术的危机也好,艺术史的危机也好,它们所隐含的意义都是双重的,或许在这之中也包含着人们对艺术和艺术批评的更大期待。 注释: ①黑格尔:《美学》第一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5页。 ②③阿瑟·丹托:《艺术终结之后:当代艺术与历史的界限》,王春辰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37页,第152页。 ④阎嘉:《艺术的边界、高雅艺术与艺术的功用——评约翰·凯里〈艺术有什么用?〉》,载《文艺研究》2012年第11期。 ⑤Cf.http://www.cafa.com.cn/2013.3.26. ⑥汉斯·贝尔廷等:《艺术史终结了吗?——当代西方艺术史哲学文选》,常宁生编译,湖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第294-295页。 ⑦乔尔乔·瓦萨里:《意大利艺苑名人传·中世纪的反叛》,刘耀春译,湖北美术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37页。 ⑧雷蒙德·威廉斯:《文化与社会》,吴松江、张文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8页。 ⑨⑩阎嘉:《对“美学”与“艺术”若干问题的反思:以克里斯特勒的观点为例》,载《励耘学刊》2014年第2期。 (11)阎嘉:《马赛克主义:后现代文学与文化理论研究》,巴蜀书社2013年版,第4页。 (12)蒂姆·阿姆斯特朗:《现代主义:一部文化史》,孙生茂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页。 (13)邵亦杨:《穿越后现代:当代西方视觉艺术》,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23页。 (14)Hans Belting,"Contemporary Art as Global Art:A Critical Estimate",in Hans Belting & Andrea Buddensieg(eds.),The Global Art World:Audiences,Markets,and Museum,Ostfildern:Hatje Cantz,2009,p.40.标签:艺术论文; 当代艺术论文; 现代主义论文; 艺术批评论文; 艺术价值论文; 欧洲历史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传统观念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