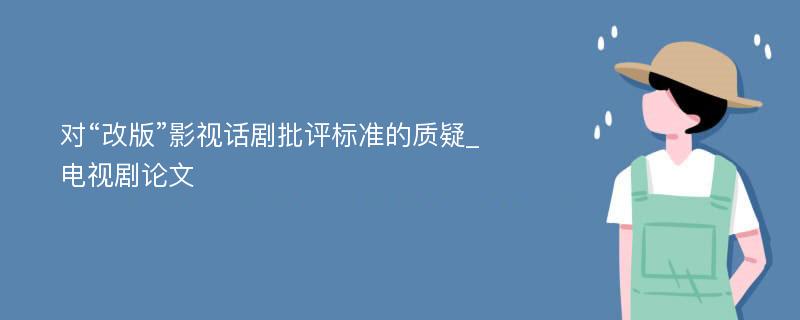
“改编型”影视剧的批评标准质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影视剧论文,批评论文,标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当代影视剧创作中,改编创作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对文学作品及历史题材的大量改编,不仅丰富了当代银屏,而且赋予影视剧较高的文化品位和艺术价值。但从大量的对具体作品的鉴赏批评和片断的理论阐述中,稍加留心我们便会发现,对于改编型影视剧展开的批评,其着眼点和批评尺度往往集中于“忠实”二字,即是否“忠实原著”或是否“忠实历史”。这一批评标准几乎贯穿改编创作的始终,成为一个最具普遍意义的传统评价标准。
这种评价标准的渊源何在,我们没有必要去细细追究,但当一部改编型影视剧问世后,人们几成定势地会首先用挑剔的眼光看它是否“忠实于原著”和“是否反映了历史真实”,然后再论其他,那么这种批评标准是否具有合理性、科学性?是否仍适用于今天多元化的改编观念和改编创作?它是否会一劳永逸地发挥批评应有的效用?是否会有效地指导创作?
对“忠实原著”及“忠实历史”的一一剖析中,也许不用争辩,其作为评价标准的合理与否便会“其义自现”。
一、“忠实原著”说
在“创作型”和“改编型”的影视剧评论中,存在两种明显不同的评论方式,前者多以自身得失论成败,而后者,特别是根据名著改编的影视剧,除了自身成就之外,往往还要究其是否忠实原著及忠实的程度如何。这似乎已成为批评的某种“思维定势”。“是否忠实原著,成为衡量评价一部影视剧是非成败首要的、甚至是惟一的尺度。
这种批评现象在当今影视评论中屡见不鲜。在我国,由于传统文化势力和古典文化的影响非常强大,对于代表古典文化精粹的名著,人们更是带着毕恭毕敬的态度去看待。由于这种民族文化心理的作用,人们往往将再现古典文化精粹、发扬民族文化传统视为己任,并以此来要求影视改编者,“忠实原著”不仅仅是创作者的改编态度问题,而且还将其上升为对古典文化传统的态度问题。仿佛“忠实原著”便意味着创作态度的严谨认真和对传统文化的尊重,而“不忠实原著”则是创作态度的不严肃及对传统文化的不尊重,甚至是亵渎传统文化。
尽管“是否忠实原著”作为一个批评标准,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随着近年来影视创作实践和创作观念的多元化,影视剧改编更是蔚为大观,在银屏上掀起一浪高过一浪的热潮,多元化的改编实践和改编观念造成了丰富多彩的影视剧类别,在丰富银屏的同时,不断冲击着传统的批评观念和批评标准。“忠实原著”这个首要的批评标准在实践创作的冲击之中,其不合理性及理论上存在的问题和尴尬鲜明地凸显出来。
其不合理性和尴尬首先体现在,当代大量在社会上“叫好又叫座”的改编电影并不是按照“忠实原著”的观念改编的,标准是一个灰色的理论框框,但影视改编者和创作者并不按照这个框框走,这从当代多样化的改编观念和样式上可以略见一斑。
改编样式之一:以点敷面,铺陈成剧
在我国当代影视剧创作中,这种“撷取原著之点,敷衍铺陈成剧”的改编方式非常普遍,最典型的莫过于被褒贬不一的电视连续剧《雷雨》,作品播出之后,引来批评界一片哗然——指责者大叫:改编得太离谱,糟蹋文化遗产!褒扬者高呼:这才是符合电视剧创作规律的改编之作,吸引人!
面对着批评界反差如此之大的评论之声,导演李少红说:“任何一部经典作品,真正经典的部分是原著,这是无可非议的。我们后人只能用我们的思想去演绎它,这种演绎在很大程度上带有我们的主观性,基于我们对原著的理解,名著之所以成为名著,就是经得起世世代代人去解释它。所以我们不追求改编得特别像话剧《雷雨》,而是追求我们的解释,去演绎我们心目中这些人之间的故事,这是我们的出发点。”
电视剧《雷雨》不忠实原著是显而易见的。尽管批评界褒贬参半,但电视剧可观的收视率和销售量,可见它在观众中的受欢迎程度,从收视效果的角度来看,《雷雨》的成功改编是不言自明的。
改编样式之二:浓缩提炼、为我所用
这种改编样式在今天也较为常见,当影视改编者面对一部作品及几部作品时,他可以将作品中令他感兴趣的人物情节提炼出来,再按照自己的某些主观意图重新加工。在电视荧屏上,引起轰动效应的比如根据王朔三部小说改编而成的电视连续剧《过把瘾》,其改编方式就是“杂取种种人,以合成一个”。
《过把瘾》的主要蓝本是小说《过把瘾就死》,改编者为了更好地编织自己的故事,借鉴了王朔其他小说的某些情节和思想,将方言和杜梅这一对青年男女的恋爱、结婚、离异、重圆乃至永别的过程,演绎得精致朴实,耐人寻味,在大江南北狠狠地煽了一把情,甚至一时间崇尚“过把瘾就死”的大有人在,言情剧能拍到这份上也实属不易。让观众发乎情,止乎情,痛快酣畅,社会上反响强烈。
《雷雨》和《过把瘾》尽管是改编中的个案,但它们的改编方式代表了一个普遍的改编观念和改编倾向——用当代的审美观念和需求对原作进行重新演绎。这种演绎体现在或是为了表达改编者的一种理解和认识,或是为了增强电视剧的可视性,而改编者所代表的当代人的某种意识融入改编的电视剧后,恰恰又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观众对电视剧的认同感,当有人问起第23次将《悲惨世界》搬上荧屏的导演,他此次改编与以往有何不同时,他明确地说,此次改编是为了表现当代人普遍关注的人权问题、人的尊严问题。在越来越注重个性体验的今天,对于诸多并不追求亦步亦趋跟着名著走的影视剧改编创作,“是否忠实原著”这一衡量、批评标准的效用何在?
“忠实原著”是个难以量化的标准。文学作品是印刷媒介承载的艺术品,而影视剧是电子媒介传播的艺术品,基于二者媒介本性的差异,文学作品同影视剧在塑造艺术形象、表达感情、传达思想的方式和手段上各有不同。同时也形成了二者在叙事表现上的优势和劣势。文学作品运用的文字语言,可以将人的精神世界、心理活动描绘得复杂而细腻,但影视剧运用的镜头语言,就很难将复杂的心理活动淋漓尽致地展现,文学语言可以很模糊地描绘形象,但影视剧的镜头语言却无法做到这一点,原著中有许多东西是影视剧根本无法再现的,一些抽象性的语言表述,描写也罢,议论也罢,感慨也罢,影视剧即使借助某些手段,如旁白、画外音等,可以有表现的可能,但是完全“忠实原著”既不可能、也做不到,在这种情况和事实面前,如果还将“是否忠实原著”作为评价的首要标准,岂不是有些“文不对路”或“隔靴搔痒”?其权威性要大打折扣的。
也许有人会反驳说,所谓“忠实原著”是忠实原著的精神即可,而不是要求亦步亦趋地去展现原著的情节、细节。这话固然没错,但是如果按照忠实原著的精神来衡量,首先要搞清楚原著的精神是什么。任何一部名著诞生时所负载的精神内涵,永远不会等同于今天它拥有的精神内涵,在它被传诸后世的同时,后人对它的理解认识和接受会不断丰富它的意义,甚至挖掘出原作者并不曾料想到的精神内涵。由于时代的距离,人们对古典名著或是有更为清醒的认识,能够揭示出原作者的本意或寓意;或是由于时代不同产生隔膜,不仅不能认同原作者的本意,可能还会背道而驰,从原著中挖掘出更新的精神实质。每个人对一部名著的内涵都有自己独到的理解,这是智者见智、仁者见仁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忠实于原著的精神,那么究竟忠实哪种精神才算是“忠实”?
因此,无论是忠实于原著的情节内容也好,精神内涵也好,由于从名著到影视剧是一种艺术门类的转换,到底转换到什么程度才算是“忠实原著”的转换,这是一个无法进行具体量化分析的标准,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批评指向性的混乱,甚至使批评话语自相矛盾。“忠实原著”似乎人人都明白,但只要涉及到如何忠实,马上就会惹来无数纷争。在纷争中,作为首要批评标准的“忠实原著”说立刻呈现出其作为一种理论依据的不确定性和混乱性,这种不确定性和混乱性又使批评在创作和鉴赏那里失去了权威,他们不再信奉批评家嘴里的一串串褒贬之词,而是我行我素。改编者只要觉得这样改编合理,符合创作观念和创作规律,我就这样改;观众认为只要影视剧好看,能吸引住我,我就看。如果一个批评标准被搁置在一个熟视无睹、置若罔闻的位置上,那么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二、“忠实历史”说
在当代影视剧改编创作中,除了对古典及现当代名著的改编外,对散见于历史长河中的人、事、物、象的改编创作形成了当代银屏上的又一热点,特别是对历史上重要的人物和事件的改编。改编者往往是从史书、杂记、甚至是野史轶闻中选取他们所需要的情节故事,来编织影视剧的主题和情节框架,用今人的眼光和头脑去述说历史。中华民族浩浩荡荡五千年的历史长河,改编者可谓“溯洄从之”,没有一个朝代不曾涉猎。于是在当代银屏上,出现了一浪高过一浪的历史题材的改编热。
由于“改编”的对象不是一本有着完整形态的文学著作,所以“改编”者似乎拥有了更为自由的处理权,可以不受原著的束缚而纵横驰骋,但是从大量历史题材影视剧的评论中,经常会出现这种现象:许多批评家围绕是否“再现历史真实”抑或“违背历史真实”而争论不休,《火烧圆明园》、《唐明皇》等影视剧因“再现历史真实”而倍受批评家的推崇,褒扬之语满天飞;而像《戏说乾隆》、《包青天》等在社会上影响较强、收视率很高的影视剧,却因“违背历史真实”而屡遭批评家的挑剔,贬抑之声不乏听。甚至有人曾写过一篇长长的文章,来论证《唐明皇》比《戏说乾隆》更有价值,主要原因就是前者再现了“历史真实”。
“历史真实”也堂而皇之地成为历史题材影视剧的首要标准。
“忠实历史”比较符合我国传统以来的“正史”思想,对历史题材的影视剧,要求在符合“历史真实”的前提下来论及其艺术性,将“是否反映历史真实”作为评判一部影视剧优劣的标准,不仅批评家这样认为,许多创作者也自觉地将反映历史真实作为创作历史题材影视剧的首要原则,力求展现真实的历史文化风貌。而且从接受者的角度看,将历史剧当成形象生动的“历史教科书”的观众也大有人在。
中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曾经辉煌的古代文明,又使今人在接受传统文化的同时,表现出一种对历史由衷的崇敬感。善于“以史为镜”,从凝结着先人智慧的史书材料及口耳相传的传说轶闻中,汲取营养和智慧,来观照今天的生活,服务于今天的生活,这是当代人仍然对古代文化津津乐道的重要原因,基于此,影视剧理所当然地肩负起反映真实历史的重任,在剧中通过艺术创作,为观众提供一个形象生动的参照体,使观众能够“温故而知新”,或者是“借古人之杯酒,浇心中之块垒”,因此,历史题材的电视剧当然要将“忠实历史”摆在首要位置,甚至有些批评家将“真实再现历史”视为历史题材影视剧的生命力和价值所在。
这种“忠实历史”的批评标准固然受到史学维护者的极力拥护,但是也不难发现,随着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的繁盛,包括港台地区创作的历史剧通过电视传媒迅速走入千家万户,对历史题材改编创作的观念和样式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多种多样、让人眼花缭乱的改编创作直接冲击着传统的批评标准,一味以“忠实历史”来衡量历史题材影视剧的批评标准,在多元化的改编实践面前,其不合理性也不可避免地显现出来。
1、历史剧创作中的“重构”
不难发现,当代的历史剧创作,大体出现这样一种趋势:即对历史生活进行富有个性的重构。对历史生活题材改编创作的同时,影视改编者表现出一种换个角度重新观照历史、理解历史、述说历史的欲望,突出体现在叙事过程中,淡化政治评介,浓化人情、人性、伦理等因素,强化故事性和趣味性。这种类型的影视剧往往在收视上颇为可观,叫好又叫座。
在一股港台的戏说风过后,《宰相刘罗锅》先发制人,片头就开宗明义“不是历史”,浓浓的戏说味道充斥着荧屏,观众又一次被吸引住了,电视剧让皇帝老儿与刘罗锅为一个女人争风吃醋,让一只狗扮麒麟戏弄乾隆,老百姓从这部“不是历史”,只讲“民间故事”的“罗锅戏”里,会心地笑了一把,体味出了乐子中的酸甜苦辣,《宰相刘罗锅》不仅在观众中好评如云,而且也得到了评论界的赞许和褒奖。紧接着《铁齿铜牙纪晓岚》在屏幕上火得一塌糊涂,第一部、第二部之后的第三部,编导者投观众所好,枝枝蔓蔓的情节都不编了,就让皇上、纪晓岚、和珅三个人斗嘴,收视率依然居高不下。
再说在中央一套热播的58集电视连续剧《汉武大帝》,该剧在收视上创央视一套黄金时段电视剧广告收入之最。片头声明“根据《史记》、《汉书》改编”,是一部历史正剧。胡玫在其导演阐述中声称:“我更明确地在艺术上尝试探索一种新的历史表现形式和表现风格。这种风格,我称之为‘新古典主义’。所谓‘新’,就是以现代的审美眼光,重新估价和表现古典与历史。我认为我的追求也可以称之为‘历史现实主义’,我以历史现实主义来区别于目前在历史剧中广为流行的历史戏说类闹剧。”
《汉》剧力求再现汉代人的经济、政治、文化、风俗及情感生活,超越今人与古人的距离,全景式地再现汉朝人民的生活风貌。
即使《汉武大帝》的这种尝试带来了广泛的赞誉和很好的收视率,但开播不过十多天该剧就被挑出了若干硬伤,甚至有文章列出《汉武大帝》的“七宗罪”,罗列了诸多细节,史学家们轮番上阵,认真挑刺,以至于围绕《汉武大帝》的讨论重点已经不再是有关剧情或者表演,居然是史学!这可能是包括导演胡玫在内的所有主创人员万万没有想到的。
长期以来,“以史为镜”、“重教化重正史”的思想,使得许多对历史题材的改编一味追求翔实、严谨的态度。这虽然无可厚非,但事实证明,也许当创作者在严肃拘谨的态度下忙于查询史实、再现历史真实时,观众已在一片乏味之中扭转了频道,何谈真实与教化!
在这个意义上,改编者何不换个角度,以新的视角、新的观念、新的方法去重新观照历史,述说历史。记得英国历史学家卡尔在《历史是什么》一书中曾指出:“历史是现在和过去的对话”。因此,在这说历史的同时,改编者不要忘记,应该时时给予当代观众一种现实生活状态的关照,这也许是让逝去的历史重焕生机的一个途径。对于这种并不追求真实再现历史的戏说之作,批评家如果用“忠实历史真实”的批评标准去衡量,显然又是“文不对题”,改编实践已经大大超出了批评标准所适用的范围,滞后的批评标准必然会对创作产生误导和束缚。
2、“历史真实”难以考究
“历史真实”作为一个批评标准,是一个模糊而考究不清的东西,真实的历史是何种面貌?什么样的历史属于真实的历史?有人说真实的历史就是教科书上的历史,有人说真实的历史是历史典籍中著述的历史,还有人说真实的历史是谁也看不见摸不着已经逝去的无踪影的东西……
诚然,对历史的阐释有多种多样,但人们面对的历史无非有两种:一种是纯客观的、己逝去的原生态的历史,它在自然消逝后是无法重现的;另一种是一些历史学家根据某些历史遗留下来的残骸、符号等考察得来的历史,它虽然也是客观存在,但却打上了历史学家主观印记的历史,(这种带有结论性的历史往往存在历史典籍书章之中)而恰恰是这一部分,形成了我们对历史的印象和看法。
因此,原生态的真实的历史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存于历史典籍中的结论和描述,都是对原生态历史某一点或是某一侧面的阐述,随着历史不断发展到今天,我们所接触到的历史真实,在实际意义上,往往就是历史典籍书章之中的,带有结论性、评判性的历史话语,而这种历史话语本身打上了历史典籍书章撰写者的主观印记。历史撰写者本人主观因素的参与,往往要使历史“真实性”打下几分折扣。
当然,追根究底去探究“历史真实”,并不是以此宣扬历史虚无主义和不可知论,目的在于澄清一些对“历史真实”不正确的看法,以树立艺术创作的正确原则,有人说,历史真实是非常靠不住的东西,有时,或者以为自己把握了历史真实,而恰恰是在这一瞬间,历史真实又从手指缝中溜走了。这话不无道理。由于“正史”思想的长久影响,使许多历史剧的创作被一些外显性的“历史真实”所迷惑,在“写真”上大下功夫,似乎要努力再现历史真貌,如在近年来银屏上掀起的“帝王皇妃”热,满眼皇袍翻飞,黄龙满天,满耳“吾皇万岁万万岁”的声浪。在声画的共同冲击下,我们看到创作者毕恭毕敬,热情洋溢地歌颂着帝王将相的业绩,太后的权术,皇妃的善良美貌……似乎“五·四”以来到今天,对封建社会的认识就仅限于此。创作者自以为是再现了历史的“真实”,而这种“真实”恰恰在实际上是陷入了历史认识的误区。
克罗齐有句名言:“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第2页,商务印书馆)。历史之真,实质在于现实对历史的需要和认知,在于用当代意识和认知高度去把握历史,展示历史。更确切地说,去把握和阐释历史的文本的话语。这应该是艺术创作追求“历史真实”的意义和本质所在。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可以说《雍正王朝》有真实性,也可以说《戏说乾隆》有真实性,它们不过是在当代意识指导下基于现实的不同需要,对历史所做出的不同阐释罢了。
澄清“历史真实”的观念有助于正确认识和把握历史的真实,然而对于历史题材的影视剧的创作而言,对历史真实的追求和反映,必须借助艺术的手段、以艺术的方式来体现。“史”和“剧”的区别就在于前者钟情于把握历史,后者侧重于艺术的表现;前者有很强的艺术性,而后者有很强的虚构性。只有将历史真实转化为艺术真实,才能充分发挥影视剧本身的审美效应,使观众在特定的审美氛围中,去洞悉世情、体察历史、感悟人生。历史剧不同于历史教科书,它要求创作者充分发挥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在将历史真实转化为艺术真实的过程中,首先要求创作者不拘泥于历史,从影视剧的创作需要出发,大胆虚构,驰骋想象,以历史事件为凭藉,构架自己的情节,将事件性的历史真实转化为情节性的艺术真实。过去,由于对“历史真实”的误解,对真实的无休止的追求似乎成为历史剧创作的首要任务,“事事须有出处,事事务求其真”,以史笔写史剧,往往使创作者拘泥于对历史事件及细节的觅求和摹写,却将艺术表现搁置一边,使创作出来的影视剧只见事不见人,只见“史”不见“剧”,正如梁启超所说“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能因袭而不能创作”,梁启超对旧史学病症的分析同样歪打正着,揭示出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在创作上的弊病所在。
归根结底,影视剧是为社会大众提供审美娱乐的,历史题材的影视剧也不例外,“历史真实”只是创造艺术真实的凭借,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更不能将其作为评判一部历史剧的首要标准。如果说影视剧不能以艺术真实来打动人,那么,其苦苦追求、苦心经营的历史真实往往也会流于空洞,甚至引起观众的怀疑和不满,何谈再现历史的恢宏与壮美!
鉴于以上种种分析,对于这种传统的批评标准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和思考。基于对影视剧传媒本性的认识,基于对改编过程创造性的理解,无论对原著或历史进行何种程度的借鉴、参考,最终目的都是创作出一部优秀的影视剧。评价一部改编型影视剧的首要标准,应该是看改编后的影视剧本身是否能称得上是一个独立完整的艺术品,具有独立的艺术审美价值,其量化体现在是否取得好的社会效益、高的收视率。因此,对于改编创作的影视剧,重点仍应该放在影视剧本身的效果上,而且这种标准的确立必定会在影视剧改编创作及鉴赏中充分发挥其指导作用,也必定会促使影视剧创作沿着一个更为科学合理的方向,不断完善自身的创作实践,为观众提供更多、更好、更受欢迎的精神食粮!
标签:电视剧论文; 艺术批评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雷雨论文; 过把瘾论文; 汉武帝论文; 戏说乾隆论文; 爱情电视剧论文; 古装剧论文; 武侠剧论文; 中国电视剧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