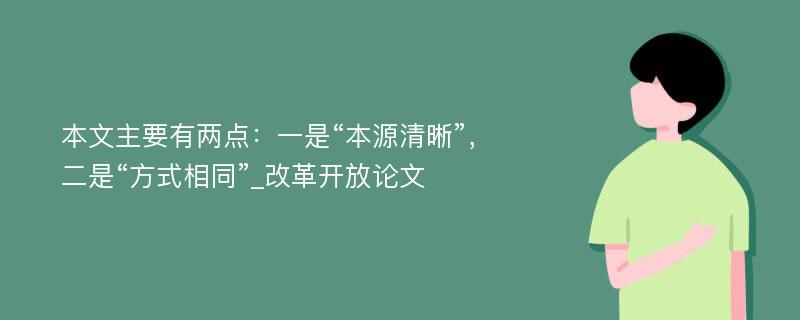
文谈两则:“正本清源”,“殊途同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正本清源论文,殊途同归论文,两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拨乱反正”以来,文艺理论研究随着改革开放形势的确立与发展,也有了不少进展。进展并非突然而至,有其必然性,但一般人没有料到会来得这样快。物极必反。“拨乱反正”就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热潮了。
在文艺界历次首当其冲的批判以至残酷斗争中,反反复复,早就存在着理论观点的各种分歧于其间,如:规律与反规律,学术与反学术,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共性与个性,文艺的特性与一味政治传声筒,人性、民族性与阶级性,民主、自由、独立思考与文化专制,真善美与独断的“正确”,为艺术而艺术、无用之用的作用,特别是,文艺工作是否都应按照诸如“以阶级斗争为纲”、“为现实阶级斗争服务”,“三突出原则”,“文艺从属于政治”这些要求来进行,文艺工作者是否一味做“驯服工具”、“啦啦队”才能“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才真能起到推动社会进步,增强综合国力,凝聚人民的作用?还要不要反映和表现生活的真相、人民的真情?还要不要批判社会生活中的不公和腐败?革命初告胜利后还要不要保持过去曾有的那种不断探索奋进的精神?诸如这些问题实际就是意见分歧中的症结。现在事隔数十年,已可清楚证明意见分歧不过都是学术研究范围里的事,而且提出不同意见者不但动机很好,如经充分讨论,必能改善领导,加强团结,有利于文艺事业的繁荣,会产生很好的效果。仅仅因为极“左”成了主宰一切的潮流,“一言堂”所称“群众路线”、“民主集中”,所提“百家争鸣”从未实行,却把学术问题看成了严重的阶级斗争政治问题,给五十多万真诚好心的知识分子雷霆万钧地扣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之类帽子,好端端一个喜人的黎明之世就开始下滑,终于陷入十年“文革”黑暗悲惨的谷底。“文革”中出现的许多丑事,诸如“请宝像”、“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最高指示不过夜”,“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知识越多越反动”等等,造神运动的权术层出不穷,成为风行一时,不可违抗的“真理”,实足是“封建主义大山”又回来了且还更严酷的表现。不容分说,空前严密的罗网,不要谈普通老百姓,连不少“开国元勋”都未能逃脱长期监禁或惨死的厄运。“四人帮”不过是一些“拉大旗作虎皮”的小丑而已。已经混乱、败坏到“民怨沸腾”的地步,一旦神像倒了,群众怎么不会万众一呼,积极奋起,一道来“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形势的确立,无疑是全国上下一切积极力量共同配合努力的结果。新时期才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新的希望与曙光。
并不是生活在本世纪中后期的中国学者特别低能。梁启超、王国维、鲁迅、胡适、陈寅恪们也历经忧患,不是完人,思想倾向也不一,尽管如此,他们以其不凡的学绩仍被公认为学术、文化界的大师,他们都在文艺理论研究方面留有重要的论著。而郭沫若、茅盾、老舍、曹禺们,五十年代以前都有著称的成绩,而此后的他们几乎都未有超过以前的大作,政治上很受重视,创作、研究上却令人感觉失重,他们当年的锋芒、勇气、才能为何反见衰减了呢?他们遵命办事,在历次文艺界的批判斗争运动中,虽未必心甘情愿,毕竟也曾冲在前面,伤害过同志,增加了运动的声势。同时,一时的重名,对曾作出过不少贡献的他们自己,究竟得到的是什么,失掉的又是什么?谈不到荣华富贵,这是他们与封建高官滑吏迥然不同之点,但不能自持已成习惯。现在许多人已知道,茅盾内心苦痛,忧虑很多;曹禺随俗浮沉,悟到“听吩咐”太多,不少写作计划无力完成;郭沫若死后仍要魂归大寨,知己之恩未舍,“文革”开始时不能不带头表态,声称自己所写的一切都应烧掉,不可能是由衷之言,他变化太快,随时太多,或者也有他的苦恼。在那疯狂的时代,他们的性格同被扭曲,不惜伤害同类,“江郎才尽”,身不由己。他们失掉的最重要的东西是,都未得尽抒其才。陈寅恪过去只在部分年长的文史研究工作者中深受敬重,他在“文革”中也饱受批评打击而逝。他现在终获大名于文化学术界中,且也不是由于他的观念全被首肯,而是由于他始终坚持住了学者应有的信念、风骨。岁寒,始知松柏之后凋乎?
在现代文学理论研究方面,冯雪峰、胡风、周扬三位素为大家所熟知。都是要求革命、以阶级斗争思想为理论核心、五十年代初为进步理论研究者尊为前锋的理论家。或以为既然都坚信马列主义,就不会有什么严重分歧,成为主流之后,更不可能有什么大的矛盾,犯什么大错。事实上他们之间理论上大方向、大原则并无多少出入,只在某些问题的具体理解、办法上不尽一致。冯、胡都是鲁迅的熟友。谁也也想不到五十年代中期胡风先成为“反革命集团”的主脑,冯在“反右”中也突然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鲁迅时“左联”领导之一周扬执行了对胡、冯两位的批判,最后竟也被打成文艺界的反动黑帮、黑线主要人物,在秦城蹲了多年监狱。现在他们三位都去世了,可说直接间接都是受害以死,未得善终。都要革命,都很咬文嚼字,想积极负起点应有的责任,可又在同一方向、原则下争执不休,又都始终未能争出什么新的究竟,搞出个大师辈出、精品纷呈的光景来。但见他们都曾有过自信,掌握着真理的年代,却一个接一个杀伐未休,最后连似乎多年掌有文艺界领导实权的周扬也给打倒了。以周扬署名发表的一些大文章中,实际含有一些最高权力者的语言在内,所有文章也不是他想发表就能发表的,周扬可说身在庙堂,而同样并不是能掌握自己命运的人。无怪他在知道了即可放他出狱的讯息后,还不敢相信这是真事,而不敢贸然便出来。胡、冯、周三位早已平反昭雪,都有他们的一些历史功绩。最晚逝世的周扬幸还得于痛苦的实践基础上撰文发表悟出了一些新的思想,可又几乎再惹祸殃。他们的遗著可以存备后人研究这一历史时期文艺理论研究是多么曲折、复杂,竟会充满着偏狭、过激与杀伐,仿佛一切矛盾、异议都非用极端机械的办法你死我活地来处理不可。不革命便是反革命,不是胖子就是瘦子。“和而不同”也不行。今后真要能闯出一条繁荣新世纪文艺理论批评研究工作的道路,显然还得依靠坚持不断改革开放的今天的仁人志士们自己从实际出发来努力。
五十年代之初我们这里就严格规定了要向苏联一边倒。文艺理论涌进了大量苏联文艺理论家极为肤泛的小册子。所谓“经典”的各种片断摘录大量流行,立刻成为大家学习的根据。那些“经典”摘录的产生背景人们并不清楚,也不可能清楚,在他们文艺界的实践成果以及社会效益总听说是一派大好。苏联是“老大哥”;作品总说都真实、感人得不得了。译供我们学习的指导写作“科学”论文的诀巧就是必须大量引用马恩列斯的话,这样才最正确,最深刻,而实际这也是最容易、最保险。为何会形成这种学风?这种学风文风果即成为我们这里的风尚。这种风气直在关系变化后仍深留在我们这里,且还变本加厉,只教条内容改为自己的罢了。长期我们只能知道一些让知道的外界东西。例如对我们这里向来很宣扬的《毁灭》作者法捷耶夫之死就在数十年后的今天才略知真相。苏联从1934年成立“作协”起,到1953年3月6日斯大林死时为止,在这段时期中,斯大林在清除“人民敌人”和“间谍”的名义下,仅在作家中就有两千名被处决、关押和被流放。身在“作协”领导岗位上的法捷耶夫1956年5月中旬忽然自杀了。记得当时听到这新闻时大家极为惊讶,他是已享誉多年的革命作家,得斯大林重用,好端端怎会自杀?一段时期后才听到解释乃出于酗酒,可这样一位革命作家又怎可能酗酒而至自杀呢?现才知道法捷耶夫1946年后还升任“作协”总书记,曾忠实执行斯大林的残酷高压政策,两千多名苏联作家受到镇压,他是有不小责任的。他良知未泯,故在斯大林死后,曾主动向内务部请予赦免留在劳改营中的一些作家,还活着的人才得幸免于死。苏醒的良知未能使他因此心安理得,终以一枪自己结束了灵魂上的极端痛苦。这一枪再次为后人戳穿了苏联斯大林时代无数历史谎言中重要的一个。无疑这一澄清对人们更有说服力和深刻的警示意义。这不能不使人联想到我们这里文艺界在历次批判斗争运动中都是重灾区的事实、许多同志备受残酷迫害的事实,也会是缺乏明智“向苏联一边倒”,向“老大哥学习”的结果。而在“拨乱反正”中,似乎至今仍远未得到足够的探究。
二十年来,我们在“拨乱反正”中已做了不少工作,“改革开放”就是对过去“闭关锁国”、“向苏联一边倒”“文化专制”“两个凡是”之类的最重要的“拨乱反正”。在这方面人们都已有些切身体会,且也开始使大家有了希望。理论研究需要一定的超越和自由,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的发展创新。这是一种重要的改进。在教育、文化、学术各专业方面,存在于深层的若干思想、观念方法中的问题,需要“拨乱反正”的东西多还需要深入努力。“左”的思维定势,很不容易转变。还须“正本清源”,转变思想观念,真正实行“双百”方针,自由讨论,使学术研究能在改革开放中起重大作用。正像要发展经济,同国际接轨,在重视科技、管理方法近于应用,比较直捷的学识之外,还要进而同时重视学习现代各门科学内比较根本的基础理论。近代时期开始只知道“船坚炮利”的厉害,逐渐知道还得学习所有西学的精髓,其中包括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等在内对我们一切有用的知识。现在我们开始悟到发展经济要凭各方面更多的新知识,那就比单重技术管理办法又进了一步。单靠技术进步,不一定就能使经济得到持续发展的深厚基础。这中间还存在许多深层的社会问题有待研究解决。所以,改革开放还必须在体制方面不断深入,大方向一致下加强学术民主与自由讨论,这才能逐步解决理论研究中的缺失和弱点,预防未来可能出现的问题。
在奋斗前进中人类肯定会愈来愈聪明,社会肯定会愈来愈进步。一时被认为清醒的,更加聪明、进步之后,不能过分满足于已有的成绩,否则可能成为新的蒙昧,而仍需要不断进行启蒙。发展无穷尽,进步无穷尽,因此“启蒙”的需要也无穷尽,“拨乱反正”总是各时代志士仁人们不断要负起责任来的天职和事业。
* * * *
谈文学问题,“社会主义”与“现实主义”问题是大家关注的焦点。正因大都是在各说各的,各是其是,各非其非,故虽同用这两个“主义”之名,其实内涵并不相同,甚至相距极远。纳粹德国的文学艺术,是以现实主义为正宗的,希特勒把一切不符合法西斯主义教条的文艺都认为对德国有莫大的损害,他把所有游离于独裁体制的作家、艺术家都视为不共戴天的仇敌,要求大家无条件地歌颂他的党,他自己这唯一的领袖,德国这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总之他勒令必须服从于他自己最夸口的残暴的法西斯专制,认为任何怀疑、反叛、逃离都是绝不允许、罪大恶极的。“法西斯主义”的现实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就是这样一种货色。它在纳粹德国盛行一时。在日本军国主义盛极一世时,类似的做法也不少。在苏联,先称现实主义,后来也称“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苏联的文艺理论与作品也曾在我们这里盛行许久,当成典范,中间宣传了那里人民的幸福生活,一切都那样无比正确,美满、自豪、英雄辈出,为全世界提供了“最先进”的“最革命”榜样。这都是现在我国中年以上读者们记忆犹新的。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苏联当时的一大套宣传,多年的个人迷信,残酷杀戮无辜,它的许多专制做法,虽在能击败希特勒的大举进攻后,它那种极权体制终于还是出乎不明真相者的意料,如此迅速地解体了。希特勒称雄一代,斯大林卫国有功,可都终归未能逃脱失败的命运。他们名义相同,说法不同,但是极权文化专制则一样。他们所讲的“社会主义”不但未能使德国和苏联的社会和广大人民得福,反而造成了极大的灾难。他们所讲“现实主义”理论与创作多很虚假,不真实,说得上艺术品的极少,更不必说有多少“大师”、“精品”。并不是当时德国、苏联的文艺工作者特别愚蠢,而是在他们当时所处的统治环境中,可能有的被镇压、监禁或外逃而销声匿迹了,有潜力原可发挥的,被压抑、扭曲才尽了,另有些则变为拜倒在权力者的脚下,异化成唾面自甘的恶仆或奴才了。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都不是难听,定该令人皱眉的名词,问题在纳粹德国和苏联权力者的手里,变成了如此专制,粗暴,简单,反进步,反艺术规律的东西。脱离实际,违背人类的发展趋势,假借革命的名义实行独裁,而没有民主和自由,只需要服膺其主观唯心的或过时的思想而不容学术、真理的追求,认为是非真伪只要凭权力者一言可决。历史上哪曾有过这样可能长治久安的成功例子?纳粹德国和苏联在文艺事业上各种“理论”和做法上的失败,是否也可作为我们总结过去历史教训的殷鉴?
关于文艺理论上的形形色色“主义”,几已烦琐得许多人不想理会。“现实主义”在我看来乃指一种非常关注现实社会问题的创作精神、要求。非常关注,有积极要求社会进步,关心老百姓疾苦,提供真善美的精品以丰富、提高人类自己的精神境界的;也有像希特勒、苏联独裁者这样的野心家、大领袖,实际起的是把历史拉向滞后甚至倒退的作用。“浪漫主义”文艺难道与现实社会无关?没有人能与现实社会无关。关注的目的有异,表现方式不同,客观上所起作用不一而已。我赞赏积极改进人生、推动社会不断改革,有志创造出真善美文艺佳作来,为绝大多数老百姓所喜爱的这种现实精神,不管它是怎样表达出来的。对“社会主义”我赞赏的不是过去那些豪言壮语、大言不实、天马行空的标语口号,觉得现在提出的目标如增加综合国力,发展生产、经济,提高老百姓的生活质量,如能认真向此方向努力,确有实绩,庶几就可说是走上社会主义之路了。综合国力自然包括物质、精神文明两方面的力量,而精神文明力量的增强,少不了“五四”时期就已提出的“科学”与“民主”两者的不断加强与扩大。过去空话太多,又成了套话,言行不一,对国计民生,太少实惠。仅靠宣传、学习这些老办法,难于解决实际问题。我们现在已很少谈“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了,这样合理,因为不必要对现实主义再加上什么限制词,文艺创作只能从有血有肉的生活实际和人物出发,写出生活的真相,先进人物的行动、真情,与人格力量来影响人,而不能从未经生活验证的思想、观念出发,进行说教,把文艺变成图解、政治传声筒、公式化概念化的虚假物。抽象灌输出来的东西不能产生感人的效果,这正是纳粹德国和苏联文学作品自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所以不能成功而失败的原因。一味的歌功颂德、粉饰太平,自欺欺人,只是表扬与自我表扬,而非更多批评与自我批评,以致走向社会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反面,完全违反了文艺创作的规律。文艺工作同样不能“以论带史”,只能“论从史出”,“论在史中”,理论必须是已经植根于生活中的深刻真理。从外加的思想、观念出发,并作为唯一依据的,从来不可能成为艺术品。文艺工作者自应学习古今中外一切有价值的理论资料,吸取营养,但再不应迷信、盲从,要自己思考、努力探索出解决新问题的办法。马克思主义需要随着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创新与发展,这一真谛永不能忘。发展因是从实际生活中得到启发,探寻出来的,所以有实际意义。学术研究、文艺创作与理论宣传有别,作用不同,却可互补。正因有区别,所以学术研究与文艺创作才有存在的价值,而且不可缺少。如果全讲一样的话,古代就不会设置采诗官了。学者的不同意见与艺术家对生活的形象表现,正可补理论宣传的不足,更能有助于某些政策及时得到必要的调整。“和而不同”,正是在我国古代已被认为非常有益于治世的持论态度。我看是深刻、合理的思想。
我认为,现在的“和”,就是对改革开放以及改革开放还需要继续深入下去这个大前提与总道理的基本“一致”,而“不同”,则是对如何做法方面真正实行“双百”方针,充分发扬学术民主,保障创作自由,鼓励大家共同进行不懈的探索,创新,多提积极的建议,博采众长,共同负起建设的责任来。如能做到这一点,相信无论文艺理论研究和文艺创作,都能出现新局面。积极的“社会主义”就蕴蓄其中,真正发生潜移默化的作用。归根到底,关键不在名义上,而在其实质的内容,实践后对社会产生何种客观效果上。
二十年来,文艺理论研究在已宽松了的文化环境中,确已有所“拨乱”,有所“反正”,开始了转折与现代化“接轨”的新时代,自然还须进一步总结,正本清源。有些过去不可质疑的诸如“以阶级斗争为纲”之类的禁区已经破除,横加干预的现象少了。学术文化领域的多元化探索已得共识。“社”、“资”、“唯物”、“唯心”、“个性”、“共性”、“人道主义”、“人性”之类都非一言可决的问题,尽可各抒所见,而不必太顾虑动辄得咎,会被问是什么政治动机、背景等的吓人追究了。文艺理论研究领域的新观念、新资料、新方法不断出现,虽然可观的成果尚少,毕竟有了生气,有了转机。所缺的是知识结构还不够深广,古今中外之间大多还各拘一隅,极少沟通,以致相互“转化”、“融通”、“兼收并蓄”的呼声虽多,实际进展仍极小。有志于此的通人尚少,这是历史的局限,总有个成长的过程。大前提确定了,总道理基本一致了,坚持努力就好。“和而不同”,古人已感悟到能够“万虑一致,殊途同归”。过去那种仅仅观点不同就会“党同伐异”,非此即彼,咬牙切齿,视同不共戴天,便互相杀伐,而同受损害,甚至内耗得同归于尽的时代该已消逝,开放的时世应当欢迎出现一个星光灿烂的学术文化繁荣发展的时代。过去“大破大立”,破的多未必该破,立的多未能站住,俱往矣。今后当然仍应有破有立,破立都要有理,符合科学,有说服力,不是只凭官大、权大,就可为凭。要重在具体分析,复杂情况决不是非此即彼,便可简单机械妄下断语。破易立难,终究还是要重视建设,吸收古今中外的一切优良有用的遗产,斟酌损益去取。返视百年,我们的文艺理论先辈中梁启超、鲁迅、胡适、王国维、陈寅恪诸位尽管各仍有其不可避免的某些局限,而非全美,可他们实绩具在,也经过时间考验,总体讲不愧为本世纪文艺理论研究的大师。较后如朱光潜,虽并无振聋发聩的思想,但他的《文艺心理学》《诗学》《西方美学史》以及所译黑格尔的《美学》《歌德谈话录》等等,都会有传世价值。他学殖深厚,建国后多次运动中受到干扰,仍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学到些新知,曾力求融化。只是馀悸之下,小心翼翼,唯恐有违,对经典作者几于一字不敢置喙,即在译文中也唯恐有失。此情可悯,也可以理解,有时他却还是禁不住说了些委婉的己见。他是几十年来屈指可数的有学术成绩的大学者之一。学术业绩的生命会比单纯急功近利的宣传长久得多。偏激加空洞怎能持久有用。
但愿我们这里将能生长出更多的大师与学者。
八月三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