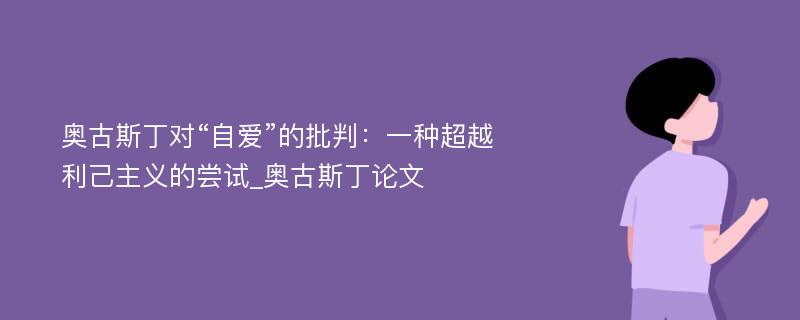
奥古斯丁对“自爱”的批判——超越利己主义的一个尝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奥古斯丁论文,利己主义论文,自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利己主义”是当今社会一个热门话题,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开展,日益受到人们广泛的关注和批判。然而,讨论仅局限于从伦理道德层面,单向度地给予利己主义以负面的定位,而忽视了利己主义这一社会思潮的多维性,尤其是其知识论意义上的历史渊源。
利己主义属于人学的范畴,或者说,它与人类中心论同源,肇始于人对自身的反思。从这个意义上说,以苏格拉底为代表的古希腊哲学家们,当他们试图“认识人自己”时,一方面开辟出一个与宇宙论哲学不同的人类学(Anthropologie)视域,同时也开启了利己主义的先河。 从苏格拉底时代到文艺复兴,从笛卡尔、边沁、穆勒、康德到黑格尔,整个西方古典哲学都坚持了这种“利人主义”或“利己主义”(个体本位)的原则。从族类本质上看,柏拉图和黑格尔坚持的是“利人主义”(或人类中心主义);从个体本质上看,苏格拉底、边沁、穆勒等人坚持的是“利己主义”。不过,他们都具有强理智主义的知识论特征,坚持logos中心论立场。
纵观人类自我认识的历史,这种强理智主义和logos 中心论立场对人类文明的发展、社会历史的进步和人自身的精神力量的发展,无疑起到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西方资本主义及其现代化过程就贯穿着这种利己主义,所以我们必须正视利己主义对人自己与人类社会的推动作用。
如果说利己主义因重视对人自身的研究而在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话,那么,由于利己主义执着于对人的主体性的单向性反思,而忽视了人与自然(神)、人与社会、个人与他人关系的交互性这一双向性反思,最终导致了利己主义的负面后果,即执着于对外在利益的追逐,而忽视了人的内在超越,在强调个人权利与利益的同时,淡漠了个人对社会的责任与义务。因此,当现代西方种种思潮开始超越主体性哲学,超越个体本位和个人主义的同时,我国市场经济的改革一方面培育出个体本位原则和中国式的个人主义精神,另一方面又与世界发达国家期望超越利己主义(个人主义)的呼吁接轨,超越利己主义而非反对利己主义便成了中国当代道德文化建设中的题中之义。超越而非反对,这是适合中国实际的一种选择。我国正在推进的市场经济改革,其目的便是实现全面现代化,这就要求我们包容个体本位、个人主义。对利己主义要有辩证的认识,不能简单地否定和反对,但也不能对利己主义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现代化赘生物)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利己与利他是一对矛盾,是对立统一关系。
“超越利己主义”是一个现时性命题,然而,在历史上也绝非无人提及,中国传统哲学关于道德超越、“天人合一”的思想之所以在今天获得某种世界性意义,原因即在于中国先哲们以独特的视角预见了人性既有自然性(即利己主义),又有道德超越的一面。在西方认识史上,基督教哲学也是较早预见这点的。奥古斯丁从原罪论出发,凸现了爱上帝与爱自己的矛盾,指出人类因执着于自爱,导致了道德的堕落。他对自爱的批判,旨在批判人类中心论和logos中心论、强理智主义。 他的这种批判可以说是对利己主义的一种“根式”(原创性)批判,他将自爱看成是利己主义的根源,他的批判不失为一种独具匠心的尝试。
二、自爱的来源
在奥古斯丁看来,自爱作为人类对自己的爱,由于漠视上帝,不爱上帝,因而是一种恶,它是对上帝的背叛,与原罪相关。
他认为,自爱来源于人的自由意志。人作为上帝的受造物,本有良好意志,应当能够过正直的道德生活。他说:“好意志就是追求过正直道德的生活,并达到最高智慧的意志”。(注:《论自由意志》〔M 〕Ⅰ.12.25。 )人只要有好意志,借好意志,爱好意志,轻视其他可以诱惑人的世物,就是有福之人了。不过,人的灵魂有一种移动,它“要么为占有或获得而趋于一种善,或者为了避免或远离而背离一种恶”。(注:《上帝之城》〔M〕ⅩⅣ.6。)因为“意志本身是灵魂的一种获得或保持某物的自由活动。灵魂的一切活动取决于意志”。(注:《论两种灵魂》〔M〕Ⅹ.14,转引自S ·吉尔松:《奥古斯丁引论》第226页,1930年德文版。)正当的爱就是遵循好的意志爱他所当爱的,行他所当行的,从而过有福生活。然而,人的灵魂总会发生“偏离”的情形。无福的人往往误用了自由意志,使意志变坏。所以,自爱源于坏的意志,因此又叫“错爱”。奥古斯丁这样解释:“爱永恒律的人就是有好意志的人,也是有福的人,而无福的人爱许多东西,即属世的东西”。“永恒律要求我们的爱离弃属世的事而朝向永恒之事。”(注:《论自由意志》〔M〕Ⅰ.15.31~31。)这就是说,正当的爱是爱永恒之律,自爱则以属世之事为对象,人自以为属世的东西如健康、敏锐的感官、力量、美丽等,还有诸如父母、妻室、儿女、亲友,以及一切与我们有关的人,还有国家、尊荣、显要、威望、金钱等等都是人所愿追求的,并视为有价值的,其实,这价值很有限,除了为生存所必需的以外,其余均属身外之物,是可以舍弃的。至于人们所谓求得从主子那里解放的自由,更是虚假的,因为依附属世之律的人不可能自由,只有“有福而依附永恒律的人才有真自由。”(注:《论自由意志》〔M〕Ⅰ.15.32。)奥古斯丁指出,该视为恶的不是那些东西,如金钱、肉体等,而是错爱它们的人。他说:“错用它们的人,恋慕它们,那就是说,为物所制而不能制物。……那善用它们的人,是把它们的价值表现出来,但价值不在它们本身里面。”(注:《论自由意志》〔M〕Ⅰ.15.33。)他还说:“堕落之所以为恶,是因为它违背本性的秩序而从较高的存在转向较低的存在。因为贪婪不是金钱的错,而是人的过失,人错爱金钱并偏离了公义,人本应该爱那无与伦比的公义胜于爱金钱的。”(注:《上帝之城》〔M〕ⅩⅡ.8。)爱永恒律的人拥有智慧、勇敢、节制、公正等美德,而爱属世之律的人则不配有这些德性,相反,他们要遭到错爱的惩罚,不得不忍受贪婪、快乐、恐惧、悲愁这些情感的折磨。贪婪(cupiditas)意味着对意志这种移动的赞赏;快乐(laetitia )意味着喜欢这一已获得的对象;而恐惧(metus )则意味着向每一次移动的让步,意志在每一次让步中,不得不对那对象产生畏惧且唯恐避之不及;悲愁(tristitia,mistria)意味着对自己已受到的惩罚不满。奥古斯丁认为,这些既是自爱的来源,也是它应得的惩罚。他说:“因为那种背弃和转向是自由的而非强迫的,所以,随之而来的痛苦刑罚,也是恰当而公道的。”(注:《论自由意志》〔M〕Ⅱ.19.53。)既然自爱源于自由意志的一种移动,而这种从存在向非存在,从永恒之律向属世之律的移动是一种有缺陷的移动,由那坏的意志而起,那么,人就必须为此移动付出痛苦的代价。奥古斯丁把自爱视为“恶”的原因加以批判,并强调了人作为道德主体应为此承担责任,应当说,这是一种颇为深刻的体认。黑格尔继承了原罪论,认为恶是人的自由意志自主选择的结果。不过,当黑格尔把这种出于自由意志的恶行看作社会发展和人类精神的动力时,奥古斯丁却把它看成是人类道德堕落的根源,是人之不幸。这不仅体现了基督教与理性主义的原则性分野,也是伴随人类认识发展史的两种不同观点。
三、自爱的表现
错爱一旦发生,人类就陷于“无能”而不得自拔。这无能首先表现为人要受欲望的折磨。在《忏悔录》中,奥古斯丁非常细致地描述了人陷入肉欲而无以自拔的痛苦。他写道:“我并不为别人的意志所束缚,而我自己的意志却如铁链般地结束着我。……意志朽坏,遂生情欲,顺从情欲,渐成习惯,习惯不除,便成自然了。……我开始萌发新的意志,即无条件为你服务,享受天主,享受唯一可靠的乐趣的意志,可是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压伏根深蒂固的积习。这样,我便有了一新一旧的双重意志,一属于肉体,一属于精神,相互交战,这种内战撕裂了我的灵魂。”(注:《忏悔录》〔M〕ⅤⅢ.5.10。 )一个具有双重意志的人是自我分裂的。如果说,人仅有肉体生命,满足于欲望,倒也不会感到不安宁,可是,人有理性,精神的自我常会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惧,他不会因为这低级的贪欲和愚蠢的快乐而自娱,他的悲愁会缠绕他的灵魂,这就是理性与生命的对抗。从这里,我们可以剥离出自爱的两个要素,即来自肉体的和来自精神的。如果说,贪欲与快乐属于前者,那么,恐惧和悲愁属于后者。
在肉体的自爱方面,首当其冲的要数“性爱”了。在《论自由意志》中,奥古斯丁列举了三种主要的恶:奸淫、杀人和渎神(注:《论自由意志》〔M〕Ⅰ.3.6。)。而万恶淫为首,奸淫居三者之先。 在《忏悔录》中,他又把人的欲望分为三种:即淫欲、口腹之欲和求知欲,淫欲仍列首位。
值得注意的是,奥古斯丁为何要如此强调“性爱”,并将它列为万恶之首呢?弄清这个问题是十分重要的。在《创世纪》中记载着上帝给亚当配妻的故事。女人是用男人的肋骨造成的,男女合二为一是自然、合乎天性的。《圣经》里也讲到人要离开父母与女人合一,上帝并没有禁止人为了生育的目的而缔结婚姻。但是,亚当被逐出乐园,与夏娃一起繁衍人类这一事件本身就已是罪的惩罚。亚伯和该隐作为上帝城和人间城的鼻祖,他们本是亚当和夏娃的两个儿子,彼此的交战揭开了人类历史中善恶势力斗争的序幕。因此,凡是从情欲出的都是罪之罚。然而,情欲对于人的诱惑实在是太大了!正如奥古斯丁自述的那样:“我冲向爱,甘愿成为爱的奴隶。……我得到了爱,我神秘地带上了享受的桎梏,高兴地带上了苦难的枷锁,以致于承受猜忌、怀疑、恐惧、愤恨、争吵等烧红的铁鞭的鞭挞。”(注:《忏悔录》〔M〕Ⅲ.1.1。)渴求女色,实质上就是自爱。奥古斯丁之所以如此强调性爱之恶,一方面源于他独特的“内在经验”,另一方面,是因为性爱极易掠去人对上帝的爱。他说:“在性行为中人最易不顾一切地把注意力由造物主转向受造物。”(注:《基督的恩典与原罪》〔M〕2:34,转引自唐逸:《西方文化与中世纪神学思想》,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2年。)上帝允许婚姻存在,本是他的仁慈。如果仅指出“性爱”的罪恶性,尚不足以说明性爱何以具有强大的诱惑力,那么,人究竟为什么会置上帝的警示于不顾,疯狂贪求性爱呢?《约翰》一书中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象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你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惟独遵行神的旨意,是永存的。”(注:《新约·约翰一书》〔M〕2:15~17。)人类自有原罪之后,其生存便处于匮乏状态,人类完全陷入了恐惧、不安、孤立无援的境地,因为他已是上帝的罪人,与上帝疏离了。人为了求生存,证明自己不仅存在着,而且活着,为了克服自己的匮乏处境,就会去追逐女人的肉体,用自己的生殖力(Libido)战胜恐惧,用创造填补空虚。然而,情欲毕竟与原罪同根,又与惩罚相关,是人无法摆脱的命运。情欲注定无法使人的灵魂得到持久的安宁,相反,短暂的满足之后是更大的空虚,更深刻的恐惧和哀愁,人一旦陷入情欲的罗网,就无能为力,难以自救了。所以,性爱从表面上看,是占有、掠夺,实质上是付出,是失去。它不仅不能弥合因原罪而来的缺失,反而会造成更大的分裂,使灵魂再次分有死亡的痛苦。
至于“杀人”,则是自爱的极端表现。《马太福音》中说:“爱上帝,爱人如己。”这是上帝的戒律。可是,人出于极端利己主义的动机,不仅违背了戒命,而且走上了杀人的罪途。这不仅没能“利己”,反倒是加剧了自己的罪。在原罪之上,使本罪更加深重。
“求知欲”被奥古斯丁视为人类自爱的一种主要表现方式。它与前面的淫欲、口腹之欲不同,因为它不以肉体的快感为目的,而以求知为目标,意欲超出自己的有限范围,知道人之外和人之上的事,因而具有渎神的动机。对这种精神性的自爱,奥古斯丁有时又用视觉外感(目欲)和好奇来称呼。他说:“好奇心驱使我们追究外界的秘密,这些秘密知道了一无用处,而人们不过为好奇而想知道,别无其他目的。”(注:《忏悔录》〔M〕Ⅹ.35.55。)人们常以此来说明奥古斯丁对自然研究不感兴趣,其实是对理智认识的拒斥。人类始祖亚当之所以违背禁令,就是受好奇心的驱使,以身试法,去试验上帝命令的权威性,偷食知识之树的果实,从而犯下原罪。殊不知,上帝的圣言绝非理解的对象,只能是信仰的目标。人类出于好奇,竟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窥探上帝的秘密。因此,求知欲比其他形式的自爱更加“罪大恶极”,这是对上帝命令和权威的公然违逆和冒犯,上帝将犯罪后的亚当逐出伊甸园,以防他再吃生命之树的果实。要真是那样,神人之间的界限就会荡然无存,上帝的权威就会丧失殆尽,一切信仰都要扫地以尽。在奥古斯丁对自爱的批判中,这是最实质的部分,自爱即是上帝对人的惩罚,同时也是人担当罪过的一种方式,直面这种不幸,是人唯一的生存选择。
四、自爱的本质
奥古斯丁在论述了自爱的来源、表现之后又概括了自爱的本质。他首先将人类的自爱和对上帝的爱进行了比较。“上帝之爱”是指人类对上帝的完全拥有,或者说,是人全心全意热爱上帝,不为外物所累,保持自己的本性。“自爱”则相反,是对上帝之爱的一种减损,丧失了自己的本性。他在《上帝之城》一书中说:“两种爱造成两座城,自爱以致轻蔑上帝,造成人间城,爱上帝以致轻蔑自己,形成上帝城。”(注:《上帝之城》〔M〕ⅩⅣ.28。 )自爱是罪后人类的一种现实生活方式。与罪前亚当是“按照上帝生活”不同,原罪后的人类是“按照人自己生活”。这种生活方式其实就是一种人类利己主义(或自我中心)。奥古斯丁在解释人为何会产生轻视上帝而爱自己的现象时指出,人的灵魂中有一种东西,像物体中的重量一样,不停地牵拉着它,不间断地驱使它,寻求安息之所。他说“我的重量就是我的爱,是它驱使我到我所属之处。”(注:《上帝之城》〔M〕ⅩⅠ.28。 )自爱正是自由意志受到误用的内在原因。对此,一位研究奥古斯丁的权威学者指出:“意志对于整个人而言,其作用是通过对表象和人所拥有的观念的调和而体现出来的。在奥古斯丁的心理学中,意志并不产生表象,而是联结表象。换句话说,意志将感觉、想象和思想的能力转到行动上去或从行动上移开。由此可见,意志对人的一切活动具有支配作用,是因为意志使人的全部活动被吸引到占主导地位的爱上面去的缘故。”(注:S ·吉尔松:《奥古斯丁引论》〔M〕第507页。)“爱是一种强烈的意志”(注:《论三位一体》〔M〕ⅩⅤ.21.41,参见S·吉尔松:《奥古斯丁引论》第507页。),这种强烈的意志即人类对自己的爱, 这是“灵魂的病态”,因为它会“令出而不行”,或“不能执行”(即“无能”)。奥古斯丁说:“意志的转移,并非怪事,而是灵魂的病态,虽则有真理扶持,然而它还是被积习重重压迫,不能昂首而立。由此可见,我们有双重意志,双方都不完整,一个有余,另一个不足。 ”(注:《忏悔录》〔M〕ⅩⅢ.9.21。)在另一处,他又说:“幸福在上提携我们,而尘世的享受在下引诱我们,一个灵魂具有两个爱好,但二者都不能占有整个意志,因此灵魂被巨大的忧苦所割裂:真理使它更爱前者,而习惯又使它舍不下后者。”(注:《忏悔录》〔M〕ⅤⅢ.10.24。)人的自爱是意志活动的内驱力。“合法的意志是善的爱,错误的意志就是恶的爱。”(注:《上帝之城》〔M〕ⅩⅣ.7。)自爱导致了意志的朽坏,从而也导致了对上帝之爱的减损。
奥古斯丁还认为:“爱就其本质而言是对一种有限的善的自然倾向。”(注:《论三位一体》〔M〕ⅩⅠ.7.12.,参见S·吉尔松:《奥古斯丁引论》第229~230页。)问题在于:人对待这一“自然倾向”的态度,态度不同,结果就不同。若态度是合乎道德的,那么爱就是正义的,否则就是不义的,是错爱。人的德性在于“决意要我们必须想要的东西,这意味着我们必须爱的东西。”(注:《论三位一体》〔M〕ⅩⅠ.7.12.,转引自S·吉尔松:《奥古斯丁引论》第230页。 )从道德角度看自爱是不符合德性的,原因又何在呢?奥古斯丁再次以贪婪为例,认为贪婪之所以为恶,是因为人以错误的态度看待(爱)金钱,把物质置于其无法比拟的更高的公义之上,从而损害了“爱的秩序”。“不义不在于对某种善的爱,而在于因我们没有喜欢比它更善的东西,进而损害了秩序。”(注:《驳学园派》〔M〕Ⅲ.16.35。)
奥古斯丁把人们对待他所爱的东西的态度分为两种:即使用(utimur)和享用(frui)。而爱的对象又分为正当和有用(honestum,utile)。正当是为自身的缘故而欲求的东西, 有用是为其他事物而欲求的东西,正确对待正当的态度,应该是享用,对待有用的方式是使用,前者指心灵的渴求,后者指肉体的欲望。可是,人错误地运用了爱,使用了该享用的,享用了该使用的,即爱错了,行了不当行的。因此,从道德的层面看,自爱的本质在于:驻足于有限可变的东西,忘却了人高贵的本性,人的灵魂不去爱那高于自己的创造主,而爱那低于自己的肉体,破坏了爱的秩序。
奥古斯丁还把“自爱”设定为“骄傲”,因为它渴望自我的荣誉。“骄傲”揭示了人类不甘心于上帝的仆从这一秘密。人通过背叛上帝,试图自己作主。从神人关系的角度看,人背叛上帝的行为在宗教上是渎神的,是遭奥古斯丁谴责的;从哲学理性上看,这种背叛富有人文主义的进步特征,然而这并非奥古斯丁的本意。不过,透过人类历史发展我们不难发现,人类中心主义极易发展为极端的自私、自利的利己主义。奥古斯丁对“人类骄傲”、自爱的批判恰恰构成了人类历史上反对人类中心论、利己主义的一道古老而奇特的风景。
在奥古斯丁看来,人本来是上帝的形象,因为他有理性,能够严守上帝的禁令。可是,“这一命令越是易于遵守,那么,损害它的不义就越严重。”(注:《上帝之城》〔M〕ⅩⅣ.12。 )他还指出:“骄傲不是别的,就是追求那虚假的荣耀。它之所以是虚假的,因为它使人从理应是精神之源的始基那里摆脱,试图自己作自己的始基,这就是精神过分喜爱自己时发生的情形。”(注:《上帝之城》〔M 〕ⅩⅣ.13。)人类从爱上帝转而爱自己这一背弃由于是人自愿发生的,所以与人的原初本质相左。换句话说,这种自爱是反人性的。奥古斯丁说:“背弃上帝存在于自身中或喜爱自身并不是虚无,但接近虚无。因此,圣经上也称骄傲为自我喜爱。”(注:《上帝之城》〔M〕ⅩⅣ.13。 )与骄傲相对的是谦卑,骄傲因其不听从而成为恶,谦卑是善,因为它就是听从。谦卑荣耀其心,骄傲则毁灭其心,骄傲是灵魂的下降,谦卑才是灵魂的提升,因为谦卑因其对上帝的恭顺而提升。而骄傲正是因为它的自我提升而堕入深渊的。由此可见,奥古斯丁从根本上反对人的自我意识、自我决定和自救。因为“自我提升和下降是一回事。”(注:《上帝之城》〔 M〕ⅩⅣ.13。)他反复区分谦卑与骄傲,说明上帝城是由谦卑之人、热爱上帝的子民组成,而人间城是由骄傲的人、热爱自我的子民组成。对于骄傲者,身陷一种明显的不可否认的罪恶中是有益的,以便使他们厌恶自己曾出于自爱而喜爱的东西,这是人得救的前提。他坚决反对罪人为自己的罪过开脱,认为这是罪加一等。“自我责罚是应该的,自我原谅是不妥的。”(注:《上帝之城》〔M〕ⅩⅣ.14。 )罪恶感的产生,已预示着人类悔罪的开始,正如黑格尔所言,恶不仅是历史进步的动力,也是促使道德完善的动力。奥古斯丁与其他大多数基督教思想家一样,强调人自我超越的必要性,尽管他坚持人的得救是上帝预定的这一立场。
五、批评与启示
人类的自爱是人类有限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它表现了人对上帝的背叛,因而必然受到惩罚,人类陷入这一处境是咎由自取。从哲学上看,奥古斯丁宣扬人对上帝的谦卑与服从,反对骄傲及不服从,似乎是纯粹为基督教辩护,削弱了哲学。其实不然,首先,他对自爱的批判揭示了生命底蕴的一种现象:即人类需要爱,因为他处于匮乏状态,需要拥有对象。人不仅期望着肉体快乐,更需要灵魂的安宁。其次,奥古斯丁对人类的原罪及自爱持批判否定态度,因为这极易使人走向自我中心主义。他无疑揭示了一个事实:人敢于与上帝作对,做出神不允许的事。自爱便是导致人类这一意志行为的内在动力,这便是自爱的深刻内涵。然而,自爱确也给人类提出了新的问题。人一方面获得了某种自由,可以获取自己想要的东西,但是他在拥有了这些世间之物之后,仍饱受着欲望的折磨,他不但没能因追求这些东西填补原有的匮乏与空虚,反而感受到了更大的不满足,灵魂的安宁并未就此而实现。奥古斯丁认为,人类愈是追求有限之物,就愈加剧其自身的受限处境。这又说明,人在执着于自身的同时,有超越有限自我回归无限的更大愿望,人需要一种终极关怀,这关怀不是任何一种有限物所能提供,它必须是全知全能全善的上帝,因为只有上帝才是真正的无限者。第三,奥古斯丁对自爱的批判旨在警示世人,人的本质在于其精神性,执迷于肉体等有形之物,是人本质的异化。他强调人的灵魂具有超越的本性,恐惧和悲愁就是这一超越倾向的反映。人渴望内心的和平与一致,自从与上帝疏离之后,深刻体验了内心分裂的痛苦,经过反思,在上帝的光照之下,终于走向内心的和平。人类从盲目信仰,经历不信仰的痛苦之后,复归信仰之路,这是人自我放逐与自我回归之路,这也是奥古斯丁对自爱的批判所寄予的愿望。
然而,奥古斯丁对自爱的批判,存在先天不足:他坚持基督教的原罪论,对人类生存处境的分析,是一种虚幻的认识,是信仰主义的,而且由于他对自爱持绝对否定态度,他对利己主义的超越方法也是反理性的,他对人类理智主义和人类中心论的批判视野充其量是一种参照系,而非现实途径,他抽象地分析人的自爱,尽管不失深刻之处,但总的说来是一种“负面”理论。在我们现当代讨论利己主义及其克服的途径时,我们缅怀历史理论固然重要而且必须,但不可以企图以历史理论解决现实问题,历史可以借鉴,真正的途径要深入到现实社会生活中去,分析、概括现实问题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和方法。所以,奥古斯丁对自爱的批判只是超越利己主义的一个尝试,而且仅仅是一种历史的尝试而已。
尽管如此,奥古斯丁对自爱的批判,对人的有限性的分析,他关于人们应当超越世俗、跃入神圣的呼吁等等,在今日这个特殊的时代处境中,仍然会引起我们一定程度上的共鸣。我们结合今天市场经济改革中的现实问题,不难看到:人既有追求物质利益的正当权利,又肩负着对社会的责任与义务。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利己”是一种普遍性欲求,与市场经济一致,个体本位逐渐成为现阶段社会中普遍的伦理观念和价值原则,对此我们简单地反对是没有用的。不过,市场经济要求效率与公平的结合,就必须遵循利己与利他的交互性原则,在自我实现的过程中,人人都是目的,人人也都有充当手段的必要性和现实可能性。在历史上,康德尽管在谈道义论、道德超越问题时,并未超出主体形而上学的范围,但他关于人是目的的思想仍然对我们有启示。在现代西方哲学思潮中,“主体间性”(Intersubjektivitaet )概念的推广旨在要求改造传统的个体主义原则。反对个体主体,而以交互主体取而代之,坚持主客融合,天人合一。我们今天所进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超越利己主义仍然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总之,我们要辩证地看问题:当奥古斯丁片面地反对人追求物质利益,并视之为恶时,我们要坚决予以批判;当他强调对物质利益应有正确的态度,即利用而非享受时,则应当借鉴之。当然,“超越利己主义”不仅是一个历史性问题,而且也是当代中国人面临的现实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除了投身到现实生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别无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