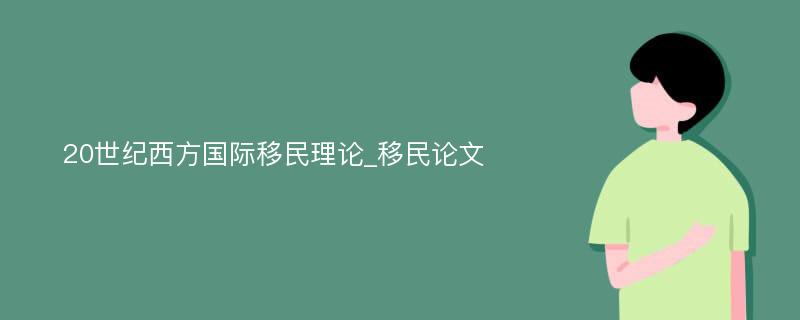
20世纪西方国际移民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移民论文,理论论文,世纪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口迁移的历史与人类社会本身的发展同样久远,然而,人口的“跨境迁移”则是国家形成并强化后的产物。进入20世纪,一方面是国家疆界、国家主权、国家利益空前明晰化,另一方面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全球性拓展以空前规模将数十亿人口裹挟入其发展轨道,与此同时,科技进步以空间距离的“缩短”与“消失”改变着人们的地域观念并加速着人口的跨境迁移。当今全球跨境移民已逾1亿,世界人口中大约1.7%生活于非出生国。
如果说,近代殖民扩张所催生的人口规模性跨境迁移的主要流向是从宗主国、较发达地区流向殖民地、不发达地区及新开发地区,那么,20世纪下半叶世界人口的跨境流动,呈现出从较不发达地区人口“奔向西方”的趋势。源于对自身国家利益的关怀,源于白色人种可能被淹没于有色人种之汪洋大海的恐惧,西方从政界到学界都对跨境移民问题投以密切关注。
20世纪西方关于移民问题的著述汗牛充栋,展现了多学科、多方位相互借鉴、共同探讨的丰富内涵与多元构架。虽然,这种“丰富”与“多元”仍然是西方话语模式下的延伸,但是,“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纵观20世纪在西方产生过一定影响的国际移民理论,将有助于我们在了解西方相关学术动态的基础上,更准确有效地加入国际移民研究对话。
一、国际移民的启始动因
移民为什么离乡背井?早在19世纪末,美国社会学家莱文斯坦(E.G.Ravenstein)就试图对移民的迁移规律进行总结。他认为:人口迁移并非完全盲目无序流动,而是遵循一定的规律。左右人口迁移的动力,是推动因素作用的结果。在“推拉模型”中,“推力”指原居地不利于生存、发展的种种排斥力,它可以是战争、动乱、天灾、生态环境恶化等对某一地区具有普遍性影响的因素,也可以是某一小群体遭遇的意外或不幸。“拉力”则是移入地所具有的吸引力,它可以是大量呈现的新机会,也可以是仅仅对于某一小群体的特殊机遇。纵观20世纪70年代以前发表的诸多研究移民问题的著述,虽然推拉因素孰重孰轻也见仁见智,但是,无论是以美国的古巴移民,还是以东南亚的中国移民为研究对象,研究者都在不同程度上注意从他们的原居地寻找将他们“推”往异国他乡的排斥力,同时剖析将他们“拉”往异国他乡的吸引力。在笔者看来,“推拉模型”之所以“常盛不衰”并“放之四海”,主要在于它只是设计了一个简易灵巧的大框架,往里进行实质性“填充”的学者们享有相当自由的想象空间。
伴随着一些研究者不断细化深化对“推拉”因素之罗列与剖析,该模型也受到来自不同方面的批评。主要意见可归纳如下。其一,“推拉模型”将“迁移”描述成某一群体被动地被“推”、被“拉”的过程,无视移民主体在这一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其二,“推拉模型”无法回答当原先存在的“推拉”因素发生变化之后,为什么移民行为并不一定立刻终止;反之,在另外的个案中,某些“推拉”因素并未发生明显变化,移民行为却减少或下降了。其三,在相似的“推拉”因素的作用下,同一群体中有的人走上了移民道路,有的人却依然故我,安于现状,原因何在?其四,移民行为完全是推拉因素作用下的“理性选择”吗?其中难道不存在偶然的恣意行为吗?
总之,20世纪后期西方出版的移民著述中,学者们已不再简单地去寻找、罗列不同的或特殊的“推拉因素”,而更多地着眼于分析究竟是哪些因素、在什么情况下形成产生移民行为的“推力”或“拉力”,而相似的“推力”或“拉力”又如何在不同的对象身上发生不同的效应。除了因严重天灾人祸而引起的突发性移民潮外,“主动移民”的动因问题尤其吸引学者的关注。近年来在西方学术界中较有影响的相关学说,可以撮要归纳如下。
第一,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以拉里·萨斯塔(Larry Sjaastad)、迈克尔·托达洛(Michael Todaro)等为主要代表。该理论着重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移民行为产生的动因。萨斯塔等学者以定量分析移出国与移入国之间的工资差距为基础,认为:国际移民取决于当事人对于付出与回报的估算,如果移民后的预期所得明显高于为移民而付出的代价时,移民行为就会发生。由此推导,移民将往收入最高的地方去;而移出地与移入地之间的收入差距将因移民行为而缩减直至弥合。该理论由于建立在比较具体的数据统计上而引起人们的兴趣。但批评者指出:收入差距是引发移民的原因之一,但决不是唯一的原因,甚至不是最主要的原因。而且,事实上并没有多少移民能够对于迁移的付出与回报做出准确的计算从而追求最高收益。
第二,新经济移民理论,主要代表是奥迪·斯塔克(Oded Stark)、爱德华·泰勒(J.Edward Taylor)等。斯塔克以自己在墨西哥的经验研究论证:同一收入差距对于不同人具有不同意义,因此,引发移民的动因不是两地“绝对收入”的差距,而是基于同参照群体比较后可能产生的“相对失落感”。如同是100美元的收入差距,在同一地区,生活于收入底层的家庭比生活于高层的家庭更可能因此而移民;对不同地区而言,生活于收入不均地区者比生活于收入均等地区者更可能移民。进一步说,在社会发展相对迟缓时,人们比较容易安于现状,当社会发生急剧变动时,人们习惯于在自己熟悉的人中选择那些原先自身条件不如己、可现在处境却比“我”好的人作为参照系,强烈的“失落感”油然而生,成为出走他乡、寻求社会地位提升的动力。
第三,劳力市场分割理论。迈克尔·皮奥雷(Michael Piore)从分析发达国家的市场结构中探讨国际移民的起源问题。他认为,现代发达国家业已形成了双重劳动力需求市场,上层市场提供的是高收益、高保障、环境舒适的工作,而下层市场则相反。由于发达国家本地劳力不愿意进入下层市场,故而需要外国移民填补其空缺。在“双重市场理论”的基础上,艾勒占德罗·波特斯(Alejandro Portes)和罗伯特·巴赫(Robert Bach)进一步提出了“三重市场需求理论”,即再加上一个“族群聚集区”。他们认为,这一在移民族群自身发展基础上形成的经济圈对其原居地人群有特殊的吸引力:一方面,该经济圈的运作需要引进新的低廉劳力以增强其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另一方面,由于族群经济圈的形成,移民企业家的地位更显突出,原居地人群往往从这些成功者身上汲取移民的动力。
第四,世界体系理论。随着谈论“全球化”成为一种时尚,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将人口的跨境迁移与“全球化”态势相结合。其主要观点是:商品、资本、信息的国际流动,必然推动国际人口迁移,因此,国际移民潮是市场经济全球化的直接结果。例如,埃罗·理克特斯(Erol Ricketts)在对18个加勒比海国家人民移居美国的数据进行研究后发现:1970至1979年间从上述国家移居美国的人口曲线,竟然与1966至1977年美国往这些国家的投资曲线大致吻合。莎里·E·芬德利(Salley E.Findley)则从考察菲律宾农产品商品化进程的社会效应中发现:农业商品化进程对当地人口外移起了明显的推动作用,因为产品进入国际流通网络后,促使当地人民对外部世界从无知到了解,进而因被吸引而移民。萨斯凯·萨森(Saskia Sassen)将海地、墨西哥、东南亚国家流向美国的移民潮,置于这些国家与美国的国家关系中加以考察,指出:贫穷、失业、经济发展滞后等因素并不一定直接引发跨国移民潮,更不左右移民去往哪一个国家,上述国家流向美国之移民潮,与美国在这些国家设立军事基地、增加资本投入、扩大文化影响密切相关,是美国大力加强在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影响的直接后果之一。
二、国际移民的延续衍伸
跨境移民潮一旦在某一地区出现后,是否会持续发展?如何发展?这也是移民问题研究者十分关注的问题。有关理论可归纳为以下三方面。
第一,网络说。移民网络是一系列人际关系的组合,其纽带可以是血缘、乡缘、情缘等。移民网络形成后,一方面,移民信息可能更准确、更广泛传播,移民成本可能因此而降低,从而不断推动移民潮;另一方面,随着时间推移,向外,甚至向国外特定地区定向移民可能融入某地的乡俗民风,从而不再与经济、政治条件直接相关。学者们还注意到,20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国家实行的为“家庭团聚”开绿灯的移民政策,促进了网络的延伸,产生了“移民增殖效应”。弗雷德·阿诺尔德(Fred Arnold)等人曾以美国的菲律宾和韩国移民为例,提出连锁移民的比例是:平均每个来自菲律宾的移民将带入一个家庭成员;每个韩国移民将带入0.5个家庭成员。格勒米那·亚瑟(Guillermina Jasso)和马克·罗森茨维格(Mark Rosenzweig)的研究结论则是:每个新移民在移居十年后平均带入1.2个“劳工类”新移民。(注:如果这几位学者的估算是正确的,那么,根据笔者的调查,中国人海外移民的亲缘纽带显然比上述民族要广泛得多。)
其二,连锁因果说或称“惯习”说。该理论基于如下假设:第一,某人认识的人群中移民的人越多,此人移民的倾向就越大;有过一次移民经历的人,再度移民的可能性相对更大,并可能带动其亲朋好友移民。第二,移民汇回家乡的钱款,将增加原居地的收入不均,从而使那些没有移民汇款收入的家庭增强“相对失落感”进而引发新的移民,因此,移民行为有其自身内在的延续性。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惯习说”也被用于作为剖析移民之“理性”或“非理性”选择的连接点:在某一社会群体中,当“移民行为”内化为超越意识控制的、具有衍生性的“惯习”时,即使诱发初始移民行为的客观环境发生变化,被局外人断定为非理性的移民行为在该群体内仍会获得认可而得以延续。
其三,“移民文化”说。按照“移民文化”的基本观点,在某些地区、人群中,伴随着人口跨境迁移而逐渐演绎出一种新的文化,这种文化在综合移出国与移入国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人生态度的基础上,创造出一个新的、相当自主的、跨越国境的虚拟空间,并展示出如下主要特征:那些在物质上获得成功的移民被尊为样板;他们的行为方式在原生活圈内被奉为圭臬;成长中的年轻人从就业取向到人生目标均与移民国外融为一体,“移民”成为该群体共享的社会文化资源。在此特殊文化的潜移默化之下,成长中的一代代新人往往在不由自主中、或在群体及个人均认为理所当然中追随其前辈走上移民道路。移民行为因而生生不息。(注:笔者以为,西方学者的“移民文化说”,与中国传统的“侨乡文化”、“侨乡意识”有相似之处。近年来西方研究中国移民问题的学者,同样注意中国“侨乡”研究。而且,随着“侨乡”(qiaoxiang)一词的拼音越来越多地被直接用于西方的相关研究著述,可以说,该词已在一定程度上被接纳为一个国际性词汇。)
三、国际移民的社会适应
跨境移民移居异文化社会后自身会发生什么变化?外来移民是否必须、是否能够融入主流社会?允许跨文化移民保持其文化自决的“多元文化主义”,是社会进步的标志还是可能导致社会分裂的隐患?这是贯穿20世纪始终的社会现实问题,也是西方移民学界孜孜探讨的重要理论问题。西方围绕外来移民与主流社会关系问题的理论研讨,虽然众说纷纭,论述浩繁,但按其基本取向,则可以梳理出“同化论”与“多元文化论”两大流派。
“熔炉论”是以美国为实证基础的同化模式的形象表述。众所周知,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如何协调族群关系,一直困扰着美国社会。1782年,法国裔美国学者埃克托·圣约翰·克雷夫科尔(Hector St.John Crevecoeur)形象地提出了“熔炉论”,他认为:美国已经并且仍然继续将来自不同民族的个人熔化成一个新的人种——“美国人”。该理论不断被衍伸、发展,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于19世纪中叶提出的“边疆熔炉论”,即各移民族群伴随着美国西部边疆的发展而被“美国化”;社会学家鲁比·乔·里维斯·肯尼(Ruby Jo Reeves Kennedy)于20世纪40年代提出的“三重熔炉论”,即美国存在新教、天主教、犹太教三座熔炉;乔治·斯图尔特(George R.Stuart)提出的“变形炉论”,即认为各民族文化在美国熔炉中被变形为美国文化,等等。这些理论都认为:各外来民族应当、而且必然会在美国这个“上帝的伟大的熔炉”中熔化为具有同一性的“美国人”。
“同化论”是“熔炉论”的普遍性表述。按照美国芝加哥学派的著名学者罗伯特·E帕克(Robert E.Park)为《社会科学百科全书》(1930年版)“社会同化”所下的定义:“社会同化指的是生活在同一区域内的一些具有不同种族源流、不同文化传统的群体之间形成一种共同文化的过程,这种文化的共性至少应当达到足以使国家得以延续的程度。”主张“同化模式”的学者大多认为,跨境移民在接受国一般要经历定居、适应和同化三个阶段。移民进入接受国时,由于大多不懂、或不能熟练掌握当地语言,缺乏进入主流社会的渠道,因此只能先在边缘地区设法落脚立足,以廉价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求生。由于存在与主流社会的隔阂,移民靠群体内部的互助互帮克服困难,由此可能进而形成移民小社区。在定居、适应的过程中,有的移民可能较先获得“成功”而得以提升自己在移入国的社会地位,其表现往往是:他们在居住地点上离开原先的移民社区而进入当地社会的中上层住宅区;在社会交往中力图进入主流社会的交往网络;在行为举止上以主流社会的上层人士为样板,最终褪尽自己的“异性”而被主流社会接纳为“自己人”。这些“先进者”作为同源移民族群的榜样,将为其同伴积极仿效。于是,越来越多的移民将接受主流社会的文化,认同于主流族群,进而实现完全同化。
然而,美国真的是能够锻铁铸钢的“民族熔炉”吗?“同化模式”真的如此顺畅美妙和谐吗?1915年,犹太裔美国学者霍勒斯·卡伦(Horace Kallen)已开始发表系列文章批评“熔炉论”,他认为,个人与族群的关系取决于祖先、血缘和家族关系,是不可分割、不可改变的。美国不仅在地理和行政上是一个联邦,而且也应该是各民族文化的联邦,美国的个人民主也应该意味着各族群的民主。1924年,卡伦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文化多元论”,他认为,在民主社会的框架内保持各族群的文化,将使美国文化更加丰富多彩。卡伦的理论提出后,很快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支持者认为,“文化多元”承认不同种族或社会集团之间享有保持“差别”的权利精神,与美国独立宣言和宪法序言中的平等思想是相互吻合的。批评者则认为:文化一致性是历史的必然,在美国的“大熔炉”中,各族群文化是无法长期保持其特性的。
60年代欧美民权运动兴起,关于“文化多元”的争论迅速走出书斋,成为引人注目的政治问题。1971年,“多元文化”作为解决国内种族、民族矛盾的理论基础,率先在加拿大被纳入国策,随后又相继被瑞典、澳大利亚等多个西方国家正式采纳。进入80年代,在70年代因经济高涨而引入了大量外籍劳工的西欧国家普遍面临如何缓解“外劳”与本国人矛盾的问题,由此,英、法、荷、比、丹等国相继在不同程度上实施允许外来移民保持其文化的“多元文化政策”。在不曾正式宣布实施“多元文化政策”的美国,不少学校也纷纷开设“多元文化课程”。作为对“同化论”的反叛,20世纪七八十年代,探讨“多元文化论”在移民学界成为一时之时尚。
提倡“多元文化论”者主要从以下三方面论证其积极的社会意义。首先,支持者普遍认为,在实施多元文化政策的国家,反映不同民族特色的文化活动丰富多彩,展示了该政策最普遍、最显著的社会效果。其次,推行“多元文化政策”,有助于形成宽容、理解“异”文化的社会氛围,有利于不同民族和睦相处。第三,推行“多元文化政策”有利于缓和错综复杂的宗教矛盾。在当今世界上,不同教派之间势不两立,乃至兵戎相见,时有所闻。美国哈佛大学奥林战略研究所所长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的“文明冲突论”就明确将“宗教差别”列为比“种族差别”更具有排他性的冲突基因。可是,按照“多元文化论”所描绘的理想,宗教也是一种文化,基督教堂、清真寺、佛庙尽可比邻而设,和平共处。总之,多元文化论者十分乐观地认为,只要真正、全面实施多元文化政策,当今世界上诸多民族、种族、宗教矛盾都可迎刃而解。
然而,“多元文化”真的是解决伴随移民而产生的民族矛盾的灵丹妙药吗?进入90年代之后,对于“多元文化论”的批评明显上升,而且各种意见针锋相对。
批评之一:“多元文化”是新种族主义。美国学者迈克尔·S·伯林纳(Michael S.Berliner)和加里·赫尔(Gary Hull)尖锐指出:按照“多元文化论”的逻辑,一个人的种族或民族属性与生俱来,不可改变,它左右着一个人的认同、思维与价值观,这是将民族隔阂固定化、合法化,实际上无异于在不同种族之间构筑起不可跨越的鸿沟。“多元文化”在为弱势族群提供特别关照的漂亮口号下,造成的结果却是同一国家内多个相互对立的族群彼此不断争权夺利。
批评之二,“多元文化论”将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简单地化为“文化问题”,进而幻想通过“文化展示”(而且仅仅限于外在文化景观的展示)消除根源于生存竞争的族群矛盾,结果只能是乌托邦。德国学者冈瑟·舒尔茨(Gunther Schultze)指出:当德国需要大量外劳时,外来劳力被当成“客人”而受到主流社会的欢迎。然而,当德国的失业率上升,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发生变化之后,“客人”就被描绘成了“从第三世界到发达国家瓜分我们现有社会福利的入侵者”,排斥外来移民的社会舆论随即占了上风。因而,移民的社会适应问题,决不仅仅是“文化问题”。
批评之三:“多元文化”否认文化有先进性和落后性之分,为一切反科学、伪科学披上了合法的外衣。1989年在法国巴黎发生的“头巾事件”所引发的争论,令人深思。是年,巴黎北部一所公立学校因三位来自北非的女学生拒绝在上学时去掉穆斯林妇女的头巾而不允许她们上学,此事经舆论披露后在法国各地引起强烈反响。支持者认为按照多元文化的理念,“头巾”是一种民俗文化,学生有按本民族习俗着装的自由;反对者则认为学生理应服从校规,“头巾”不允许女性展示其容貌,是对女性的歧视,“多元文化”认可这一习俗就是屈从于落后。
批评之四:“多元文化”所反映的是一种静止的(或曰僵死的)文化观。“多元文化”以“允许各民族保持自己的传统文化”为历史的进步,然而,“传统”并非一成不变,文化是生生不息的绵延过程,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伴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吐故纳新,并与其他文化相互交流,相互渗透。尤其对移民族群而言,其文化伴随迁移而变化,是适应生存需求的必然反映。
总之,百年来西方理论界对于外来移民的社会文化适应问题,仍然在“同化”与“多元”之间左右尝试,上下求索。两极冷战格局终结后民族矛盾的提升,使外来移民族群的社会适应问题更加尖锐,但经得起社会实践检验的济世良方仍然千呼万唤出不来。
四、国际移民发展趋势
当世界走向21世纪时,面对奔涌于全球的移民潮,西方表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世界各地人口以史无前例的规模离乡背井,如此大规模的迁移有压倒我们的应付能力的危险,迁移可能成为我们时代的人类危险。(注: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年度报告(1993年),转引自[香港]《文汇报》1993年7月7日。)
斯蒂芬·卡斯特(Stephen Castles)和马克·米勒(Mark J.Miller)对于移民趋势的分析颇具代表性。他们认为: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叶是“国际移民的时代”,其主要趋势将表现为国际移民的全球化、加速化、多样化和女性化。纵观移民历史之演进,民间自发的移民行为明显受到移出及移入国双方政府的制约,然而,两相比较,来自移民潜在目的国政府对于移民入境是鼓励、允许、限制还是严禁,对移民流向的影响较之移出国政府要重要得多。两位学者强调指出:移民是多种因素作用下的综合性的现象,是日益强化的全球经济政治体系下的一个次级体系,由于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只对信息、商品、资本开放而对人口流动实行封闭。因此,不论相关政府如何堵截,移民潮流都不可能在近期内下降。全世界从政界到民间的当务之急是:必须学会认识、理解、接受大批人口流动的社会现实。
在此还值得一提的是,对于中国学者而言,西方对于当代中国移民趋势的关注,尤其具有特殊意义。尽管当代中国人口跨境流动的数量在世界人口流动总量中所占比例有限,(注:前引联合国基金会的报告指出:90年代的国际迁移者达一亿人。据有关资料统计,20世纪70后代以后从中国大陆移居国外的总人口大约在70万至100万人之间。因此,与中国人口总数相比,跨境流动的中国人所占比例是十分有限的。)但是,由于中国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所具有的巨大的潜在流动人口资源,由于中华文化在异质文化环境中表现出的特性与韧性,对于中国跨境移民趋势的人文关怀,也是西方移民学界关注的一大热点。有人不无忧虑地提出:中国经济政治改革的发展,势必进一步打开中国人口向外流动的大门;然而,一旦中国的改革倒退,则会引发巨大的难民潮。言下之意,当代中国人大量跨境流动的趋势无法避免。如何对此未雨绸缪,已引起西方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
综上所述,国际移民学界的理论动向,值得我们追踪探讨。而且,在此基础上,从中国移民是世界移民潮组成部分的基点出发,结合中国移民的特点加入国际移民研究对话,增进国际移民学界对于中国移民问题的正确认识与合理关注,回应国际上某些人在中国移民问题上带有攻击性的偏见与挑衅,是我们国内移民学研究者应当大力加强研究的课题。
标签:移民论文; 多元文化论文; 美国社会论文; 移民潮论文; 移民澳洲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社会因素论文; 群体行为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人口问题论文; 国际文化论文; 中国人口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