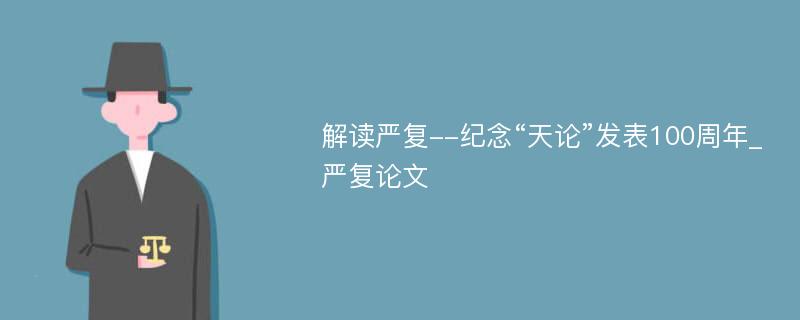
理解严复——纪念《天演论》发表100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天演论论文,周年论文,严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00年前,一本题为《天演论》的译著出版发表,标志着现代中国思想的开始。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部著作对于中国思想和中国现代化的意义,将会越来越深切地被人感受到。然而,它的译者严复,却无这般幸运。
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严复的命运颇为独特。这种独特的命运,很大程度上与他是《天演论》的译者有关。因为他翻译了《天演论》,他的名字将永远留在中国思想史上;也因为他是《天演论》的译者,他自己独特的思想及其对中国现代思想史的贡献往往被人忘却。人们谈论严复,不是因为他的思想,而是因为他的翻译。对许多人来说,严复只是一个翻译家,而不是一个思想家,他对中国现代思想史的贡献,只是翻译了几部西方学术经典。例如,1990年出版的《严复研究资料》(注:《严复研究资料》,牛仰山、孙鸿霓编,海峡出版社,1990年。),一个部分是“严复生平及文学活动”;另一部分是“严复翻译研究文章”,却没有一个部分是关于他的思想和思想活动的。这种情况表明,钱钟书的下述观点可能代表了不少人的想法:“几道本乏深湛之思,治西学亦求卑之无甚高论者,……所译之书,理不胜词,斯乃识趣所囿也。”(注:钱钟书:《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年,第24页。)
即使研究严复思想的人,对他的评价也不高。“早年先进,晚年保守”成为流行的定论。所指无非是他早年引进西方思想,主张变革,而晚年则赞成帝制,提倡读经。连汪荣祖这样的海外学者,也未能免俗。他于1994年发表的《严复新论》一文,尽管也指出“早年先进,晚年保守”这样的两分法似乎过于简单,(注:汪荣祖:“严复新论”,《上海文化》,1995年,第5期。)实际上却仍认同上述评价,并未有太多新意。具有反讽意味的是,上述评价的哲学根据,恰恰是与严复有极大关系的进化史观。严复成名以此,严复被贬低亦以此。
严译西藉不止一种,但最有影响者,当推赫胥黎的《天演论》。该书一面世,便一纸风行,使无数人血脉贲张,如梦方醒。这倒不是由于严氏文字典雅古奥,“骎骎与晚周诸子相上下”,而实在是因为它使我们这个民族看到了自己真实的生活条件和境地。胡适后来回忆说:“数年之间,许多进化名词在当时报章杂志的文字上,就成了口头禅。无数的人,都采来做自己和儿辈的名号,由是提醒他们国家与个人在生存竞争中消灭的祸害。”(注:胡适:“我的信仰”,《胡适自传》,黄山书社,1992年,第90页。)《天演论》宣传的进化论观念,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直到现在,它仍是许多中国人基本的思想预设之一。如果说,中国人接受进化史观最初与民族危亡的刺激有关,那么后来更主要是由于它以现代科学的成果出现,以及进化隐含的进步的必然性。科学既是真理和公理的象征,又是现代化的利器;而进步的必然性则满足了我们对于自己前途的美好期望。因此,进化论迅速成为现代中国世界观的基本成分。这大概是严复在翻译《天演论》时所想不到的。
但严复更不会想到的是,受到他所介绍的西方思想,尤其是进化论影响的中国知识分子,恰恰是依据进化史观来看待他和他的思想的。对于他们来说,严复主张只有渐变而无突变,赞成帝制,提倡尊孔读经,凡此种种已足以将他定为保守与反动,是完全过时的人物,根本不值得去认真研究他所留下的思想遗产。即使是他的翻译,也一直受到简单、甚至是粗暴的批评。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严复翻译的虽然都是名著,但“半属旧籍,去时势颇远”。(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80页。)而胡适一方面承认严译《天演论》的巨大影响;另一方面却批评严复用古文译书让人“不可猝解”。(注: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言》,香港文学研究社,1972年,第1卷,第5页。)张君劢则批评严复用了过去与现在的日常观念去翻译西方科学的意思,词章虽美,意思却走样了。总之,用中国旧有的概念去译西方思想,失去了其精确的精神。他甚至认为传统思维方式的影响,损害了严复的翻译。(注:转述自贺麟:“严复的翻译”,《严复研究资料》,第238页。)傅斯年干脆说严复翻译的书中《天演论》和《法意》最差,因为他不对原作者负责,译书是为了沽名钓誉。(注:傅斯年:“译书感言”,《新潮》,第1卷,第3期,1919年3月,第532页。)
这些批评严复翻译的人无不受过严译的很大影响,这样近乎苛刻的批评可说是忘恩负义。但这种忘恩负义却有其内在的理论根据,这就是严译传播的进化史观。既然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那么近代中国屡战屡败,濒于亡国;而西方各国则既富且强,为所欲为,足见我们落后,西方先进。再者,如果进化公理是普适的,进化的方向是一致和唯一的,那么当然是今胜于昔,新胜于旧。既然我们落后,当然是昔是旧,而西方自然是新是今。西方的今天是我们的明天或后天。在这种逻辑之下,才会有中西文化的差别是新旧古今之别之说。因此,严译与原作有出入,不是翻译技术上的不足,更不是创造性的理解与诠释,而是证明了严复自己思想的局限和保守。严复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贡献,似乎只是译了几本西书,引进和宣传了新思想;但即使是这个工作,他也没做好,即使在他最先进的文章和翻译里,也是“进步的和反动的思想同时并存。”(周振甫语)在这种思路下,严复及其思想怎么可能得到足够的重视与评价?
当然,也有例外。同样是深受严译影响的鲁迅,对严复却赞佩不已,说:“严又陵究竟是‘做’过赫胥黎的《天演论》的,的确与众不同:是一个十九世纪末年中国感觉敏锐的人。”(注:鲁迅:“随感录二十五”,《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第295页。)毕竟是鲁迅,他能觉察到严复思想的深度和独特价值。对于严复“做”赫胥黎的《天演论》,不仅没有丝毫批评,反而给予最高的评价。另外,吕思勉对严复也有独到的看法:“严几道学问的规模,比康长素、梁任公、章太炎都小。然其头脑确是很冷静的,其思想亦极深刻。”(注:吕思勉:“从章太炎说到康长、梁任公”,《章太炎生平与思想研究文选》,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76页。)陈宝琛在给严复写的墓志铭中说他:“于学无所不窥,举中外治术学理,靡不究极原委,抉其得失,证明而会通之。六十年来治西学者,无其比也。”(注:陈宝琛:“清故资政大夫海军协统严君墓志铭”,《严复集》,第5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1542页。)这决非过誉之词。细检现代中国思想史,何止是“六十年来治西学者”,六十年后治西学者也少有其比。
严复作为一个重要思想家的地位,在西方学者对他的评价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印证。美国学者路易斯·哈茨给严复对西方思想的阐述与评论以极高的评价。他认为严复在一些方面对西方思想与社会的误解甚至歪曲“是为了获得一种新的洞察力而付出的无害的代价。”(注:史华慈:《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叶凤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页。)他认为严复站在尚未经历近代化变化的中国文化立场上,一下子就抓住了近代欧洲思想中体现了欧洲走向近代化运动的“集体能力”这一主题,并将其与阿累维对英国思想文化和托克维尔对美国社会文化的研究相提并论,认为他们母国文化提供的对照恰恰使异国社会生活中蕴涵着的思想清晰可见。(注:史华慈:《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叶凤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页。)“西方思想的西方评论家告诉我们较多的是我们已知的事情;而严复进一步告诉了我们一些我们所不知道的事情。”(注:史华慈:《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叶凤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页。)因此,“严复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最终会成为我们的看法。”(注:史华慈:《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叶凤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页。)但问题还不止于此。严复的价值还不仅仅在于帮助西方发现“西方”和了解自己,真正重要的是:“西方本身已卷入了严复阐述的世界,因此西方根据它自己的经历不可能回避严复提出的看法。”(注:史华慈:《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叶凤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页。)
《寻求富强:严复和西方》的作者史华慈教授则认为:“严复的思想非常值得注意。在我看来,严复所关注的事是很重大的,他设法解决这些事情的努力颇有意义,他所提出的问题,无论对于中国还是对于西方都意味深长。”(注:史华慈:《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叶凤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页。)很显然,在哈茨和史华慈看来,严复的重要性决不只是在对西方的理解上,而更在于他的思想和他所提出的问题具有超越东西方文化畛域的普遍意义。果真如此,我们自己又怎能回避严复和严复提出的问题呢?而要重新认识严复,必须象哈茨和史华慈那样,抛弃近代以来的成见和公式,将他放在一个更为广阔的视域中来考察。
迄今为止,中外学者一般都是将严复放在现代化和中西文化交流冲突这个语境中来考察。这种做法当然有其合理性,但却容易流于简单化,往往只是根据严复对待中西文化和政体的态度来断定严复的“激进”或“保守”;、“进步”或“反动”。这种判断诚然也可在严复留下的文字中找到若干证据,但却使人难以进一步理解和认识严复思想的深刻内含和独特价值,更无法令人满意和信服地解释一些严复理解上的明显困难。
首先出现的问题就是,是否有两个不同的严复,“进步的”严复和“反动的”严复?也就是说,严复的思想是否有根本的转变?在很多人看来,答案似乎是肯定的。严复晚年完全背离了其早年的立场。但严复留下的全部文字告诉我们,他的思想的确前后有变化,但这种变化不是根本立场的变化,而只是关注焦点的变化。早年他关心较多的是通过学习西方来克服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的种种弊病,促使中国通过自身的改良走上西方同样的富强之路。而晚年在中国显示状况的刺激下,他更多地注重和鼓吹传统在维系民族生存与统一,培养和提高国民道德,以及在社会稳定发展中的作用。但他主张渐进改良,主张学习西方,不遗余力地批判中国传统社会和文化的种种弊病这些基本立场,却是始终一贯的。无论是戊戍后还是辛亥后,上述基本立场都无实质改变。事实上,正如史华慈所指出的,严复被认为是最革命的那些论文,即在1895年所写的《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等,与他后来在翻译赫胥黎、亚当·斯密、孟德斯鸠、穆勒等人著作时所写的按语(大部分在本世纪初)观念基本上是“一脉相承的”。(注:史华慈:《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叶凤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9页。)因此,有人说他从戊戍(1898),也就是上述那几篇论文发表三年后就开始走向反动,(注:周振甫:《严复诗文选》后记,《严复思想旨探》,香港大东图书公司,1980年,第275页。)未免有点过甚其词。
值得注意的是,持这种观点的人主要并非依据文本或其它历史材料,而是根据进化史观。主要的理由是时代变了,即使保持原来的观点,进步也变成了反动。康有为和章太炎也因为同样的理由而得到相同的结论。可是,且不说判断时代转变需要有力的证据和周密的论证,以思想与时代合拍与否来判断思想的价值,实际上是取消了思想自身独立的真理性,而将它等同于趋时应世的意识形态宣传。这样,思想本身就名存实亡了。这种做法的典范,文革期间的评法批儒的闹剧,从反面证明了这种做法的荒唐。思想的价值永远在于它是否包含真理,而不在于它属于什么时代,更不在于它是否符合人为的所谓时代要求。
说严复“晚年反动”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是他所谓“反对共和,主张恢复帝制”。其实,严复始终认为,民主是最好的制度:“民主者,治制之极盛也。使五洲而有郅治之一日,其民主乎?”(注:《严复集》,第4册,第975页。)严复不象各个时代都会有的赶潮流的人,他对民主制度的精义与实质:平等和自由有深切的体认,因而甚至认为希腊、罗马的民主都不是真正的民主。同时,他也相信,“由君主转为民主可,由民主转为君主不可。”(注:《严复集》,第4册,第891页。)因此,尽管他知道辛亥以后的中国号为民主,但专制之政阴行其中,当袁世凯欲称帝要他支持,他却认为“此时欲复旧制,直如三峡之水,已滔滔流为荆扬之江,今欲挽之,使之在山,为事实上所不可能。”(注: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严复集》,第5册,第1551页。)以此来规劝和婉拒袁世凯。后袁世凯派人请他写一篇劝进文字,他更以“顾吾生平不能作违心之言”相拒。(注: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严复集》,第5册,第1551页。)列名筹安会六君子显然是杨度先斩后奏,而他又因与袁世凯私交素厚,而勉强默认了。(注:参看王蘧常:《严几道年谱》第96页;《严复集》,第3册,第631页。)
但另一方面,严复的确始终赞成帝制,但却并不反对共和。严复是注重事实的经验论者,而不是注重意识形态的教条主义者。进化论使他相信:“制无美恶,期于适时;变无迟速,要在当可。”(注:《严复集》第2册,第240页。)“法制必不可徇名而不求实。”(注:《严复集》第2册,第241页。)民国初年中国政治的腐败,社会的落后,并不因帝制改共和而有丝毫改善这一事实更坚定了他的这一信念。号为共和,可以阴行专制;但另一方面,帝制也不就好。“夫民德不蒸,虽有尧舜为之君,其治亦苟且耳。”(注:《严复集》,第4册,第969页。)关键在于民德民智,尤其国民的道德素质,是民主共和能否名符其实的根本条件。基于他对中国社会和国民道德素质的悲观估计,他认为中国在当时仍以帝制为宜。而民国以后政坛的混乱局面和分裂,更使他相信帝制是维系国家统一和凝聚人心(这两者乃是中国能否成为现代意义的民族国家的关键)的适当工具。他主张尊孔读经也是从凝聚人心和培养民德的目标出发,“必凝道德为国性,乃有以系国其于苞桑”。(注:《严复集》第2册,第342页。)政体对严复而言只有手段和工具的意义,他的目标是国家富强和人民自由平等。这个目标他始终如一,生死不渝。
作为一个进化论者,严复当然会抽象同意共和比帝制进步;但也因为他的进化论,他认为进化发展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水到渠成,不能强求。所以他“但以政府权界广狭为天演自然之事,视其国所处天时地势民质何如。”(注:《严复集》,第5册,第1290页。)他相信,倘若国民民智未开,“则虽有善政,迁地弗良。淮橘成枳。一也;人存政举,人亡政息,极其能事,不过成一治一乱之局。二也。”(注:《严复集》,第5册,第1340页。)严复的这个思想,已在现代政治史中得到充分证实。
当然,历史也证明,严复认为中国的一线生机在于复辟,中国若要存在亦恃数千年旧有之教化,(注:《严复集》,第3册,第662页。)是彻底错了。数千年旧有之教化早已荡然无存,中国却并未与之偕亡。因此,人们当然有理由说严复“保守”甚至“反动”,就象以前说孔丘“保守”和“反动”一样。但是,严复上述预言的失败,却证明了任何制度都必须适合一国的历史和现实的状况与条件这个严复的根本信念。而现代中国未依仗旧有之教化而存在,则证明了严复晚年的另一个观点:“古不能以徒存也,使古而徒存,则其效将至于不存。”(注:《严复集》第2册,第276页。)严复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但严复为之奋斗的目标和理想,仍是今天中国人民的目标与理想。因此,严复留下的问题,也仍然是我们今天的问题。这些问题用“革命”与“反动”;或“激进”与“保守”之类意识形态色彩极浓的术语是无法解决的。对于今天和未来的历史来说,重要的不是显示我们在政治上比严复正确,而是以他同样的热情与执着来继续思考他留下的问题。否则,我们是没有资格批判严复的。
如果说中国学者更多地是以革命的话语来评判严复,那么西方学者大多是用“冲击—回应”的模式,将严复放在中西文化冲突的语境中来考察。他们一般都把严复看成是一个全盘西化派,将严复对传统文化的肯定与强调解释为明知西方思想文化优越,为了一种民族自尊心或民族自豪感,硬要给予传统正面的评价。这种说法当然带有西方文化中心论的色彩,尤其是用在严复身上。说这种话的人完全忽略了严复对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都有严厉的批评这一事实。当然,也有西方学者对此有不同看法。例如,史华慈就指出,严复认为中国古人在许多方面有与近代西方思想相近的思想,主要动机并不是要“拯救民族自豪感”。(注:史华慈:《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叶凤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91页。)但他却因而认定严复实际上是一个全盘西化论者。他一方面正确地指出严复内在的思想实质是前后一致的;另一方面却将这种一致理解为“丝毫未偏离西方思想”。(注:史华慈:《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叶凤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76页。)史华慈这个信念异常坚定,以致于他认为严复晚年对一些近代西方价值观念的批判并不表明他真正背离了西方。(注:史华慈:《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叶凤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1页。)在他眼里,严复始终是个全盘西化论者。尽管史华慈的《寻求富强:严复和西方》是一部相当精彩的研究严复的著作,但却在对严复思想倾向的基本判断上令人遗憾地错了。
无论说严复“向传统倒退”,还是说他“丝毫未偏离西方思想”,实际上都是用“传统—现代”的思想模式来解释严复及其思想。而这种“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的思想模式的理论前提之一,正是近代的单线进化论。可是,基于这种思想模式的任何一种观点实际上对严复来说都不合适。
的确,严复这代中国知识分子是在西方列强强行闯入中国的条件下,才得以系统接触西方思想文化的。近代中国与西方交往的痛苦经验,和中西社会文化的对比,使他们充分认识到,西方文化在许多方面的确有优越性。中华民族若想兴盛富强,自立于世,非学西方不可。但是,决不能因此认为,象严复这样主张全面向西方学习的人,就完全没有自己独立的思想,而为西方思想所支配。
事实上,中国人对自己文化传统种种弊病的批判,并非由西方在近代大规模进入中国所促成。明末以来,中国士大夫对自己传统文化和现状的批判不绝如缕。严复对中国传统的种种批判,大都可以在前人那里找到同道。他在《辟韩》中批判君主专制的言词:“秦以来之为君,正所谓大盗窃国者耳”,(注:《严复集》第1册,第35页。)其激烈程度未必超过唐甄的“自秦以来,凡为帝者,皆贼也”,而意思完全一样。当然,严复这代人在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和现状时,往往以西方文化和现状为参照,并且有了以此为改造中国的目标的信念。但决不能因此说,不与西方接触,中国人就会一直陶醉在虚幻的太平盛世的美梦中,而看不到传统与现实的问题。
上述看法还导致另外一个严重误解,就是既然严复们是从中国与西方的实力较量中一再遭受挫败,而认识到西方的优越和厉害,那么他们当然对西方文化必然是持一种彻底的功利主义态度,而不可能有一种超越的欣赏乃至认同。史华慈教授就是这样来理解的。在他看来,“在严复的关注中,占突出地位的仍然是对国家存亡的极大忧虑。如果假定普遍性的最终希望比这个眼前目标在决定严复的思想方面更重要,将是一个可悲的误解。相反,严复的所有信奉必须放在国家危亡造成的背景中来看。假如在严复看来,科学、自由、平等和民主与他所关注的事没有直接关系,那么人们大可怀疑,他对‘自由主义’的信仰是否会如此热诚。”(注:史华慈:《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叶凤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2页。)然而,这样一来他就无法解释:“为什么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中国鼓吹者强烈地感到需要那个躲在进化长河背后的最终的、不变的、最高的实在呢?假如他已是一个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深深地思索着怎样使中国摆脱耻辱而成为富强之国;假如他除此以外,还信奉一个坚定的信念,即把某种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念作为达到富强目标的唯一手段;那么,为什么这些新的信仰不足以成为他生命的意义所在呢?”(注:史华慈:《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叶凤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99页。)其实不仅史华慈,许多持“冲击—回应”思想模式的中国人也同样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毫无疑问,严复接受西方文化是有使中国富强等功利的考虑,但决不仅仅如此。西方文化使他震撼和心仪的不仅是事功方面的优越,更有其超越的内在价值方面的东西,譬如史华慈最关注的自由问题。严复决不仅仅把自由理解为达到富强的手段。相反,他早看出,西方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注:《严复集》第1册,第4页。)凡对中国传统的“体”“用”概念有所了解的人,都不难得出与史华慈不同的结论。严复还在《法意》按语中写道:“且夫自由,心德之事也”。(注:《严复集》,第4册,第986页。)他从未从单纯形而下的功利手段意义上去理解自由,而是始终坚持将自由视为一种超越的终极价值,尽管他对自由的理解与西方传统的自由主义的理解未必尽同。而他之所以被斯宾塞所吸引,也并非因为斯宾塞思想中有什么经世致用的良方,而是由于其能满足他对于真理的理解和对学问的追求:“窃以为其书实兼《大学》、《中庸》精义,而出之以翔实,以格致诚正为治平根本矣……斯宾塞氏此书,正不仅为群学导先路也。”(注:《严复集》第1册,第126页。)凡此种种,都足以表明,严复对西方思想和文化,决非持纯粹功利主义态度;相反,他对西方思想和文化从一开始就不乏形而上的,超越的欣赏和认同。
应该指出,严复不象他的众多研究者,喜欢区分古今中西。他是一个真正的普遍主义者,而不是象许多人那样,虽以普遍主义者自居,但却是以某种文化或文明为普遍的伪普遍主义者。在严复看来,“夫公理者,人类之所同也。至于其时,所谓学者,但有邪正真妄之分耳,中西新旧之名,将皆无有,……”(注:《严复集》第1册,第157页。)人类共同的真理,决无始作俑者,而是由不同文化、不同时代和不同民族的人来共同阐发;而它们之间的互文(intertext)互释,则是这种共同阐发的基本方式。他从英国哲学家约翰·穆勒的“欲考一国之文字语言,而能见其理极,非谙晓数国之语言文学者不能也”中悟出,不仅语言文字是这样,人类公理也是这样:“使其理诚精,其事诚信,则年代国俗,无以隔之。是故不传于兹,或见于彼,事不相谋而各有合。考道之士,以其所得于彼者,反以证诸吾古人之所转,用澄湛精莹,如寐初觉。”(注:《严复集》,第5册,第1319页。)所以在他看来,中国的传统文化非但不会因输入西学而消亡,相反,却会中西互补,相得益彰。因此,严复始终对西方思想持一种积极开放的态度。
也因为上述认识,严复不象后来许多人那样,对西方思想崇拜得五体投地,亦步亦趋,毫无批评。他虽然早年深受斯宾塞的影响,却并不象史华慈说的那样,让“斯宾塞的思想支配了严复以后整个思想的发展。(注:史华慈:《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叶凤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0页。)事实上,严复和斯宾塞在许多问题上并不一致。严复并非不了解斯宾塞的真实思想,但往往根据自己的需要,加以在熟悉斯宾塞思想的西方人看来是“曲解”的阐释,一方面固然可以是“实际上揭示了这位大师教导中一些他的西方门徒还并不清楚的异常特征;”(注:史华慈:《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叶凤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4页。)另一方面也说明从一开始,严复就是以自己的眼光去读解斯宾塞的。斯宾塞思想与严复思想的关系恐怕不是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而是一种互文关系。否则,严复对斯宾塞思想的释义学阐释是不可思议的。
严复思想的发展,不是证明了斯宾塞对他思想的控制,而是刚好相反。在翻译《天演论》时,他对斯宾塞进步主义的进化论似乎深信不疑:“夫斯宾塞所谓民群任天演之自然,则必日进善,不日趋恶,而郅治必有时而臻者,其竖义至坚,殆难破也。”(注:《严复集》,第5册,第1392页。)然而,到翻译《法意》时,他的这种信念已经开始有所变化,一方面他认为古人向往的所谓三代不过是一种虚构的宗教迷信;(注:《严复集》,第4册,第940页。)另一方面却又说,三代之治必远过秦,“此其说诚有不可尽信者;顾以一二事之确证,知古人之说,不可诬也,则有如吾古人之重乐。试取《乐记》诸书读之,其造论之精深,科学之高邃,不独非未化者之所能窥,而其学识方术,亦实非秦以后人之所能。”(注:《严复集》,第4册,第945页。)在同一时期写的《论教育与国家之关系》中,他将目光转向西方,指出西方的进步大都在物质方面,“其属于器者九,而进于道者一。且此一分之道,尚必待高明超绝之士而后见之,余人不能见也。”并且,“独至于道,至于德育,凡所以为教化风俗者,其进于古者几何,虽彼中夸诞之夫,不敢以是自许也。”(注:《严复集》第1册,第167页。)严复的这种判断,也是近代以来不少西方人的判断。
即使我们承认进化过程是一个历史事实,并且承认进化是朝向某种类型人类生活的出现,也不能得出它是道德上最可赞扬的。正如赫胥黎看到的,适于生存与道德上完美并不必然是一回事。其实,即使在严复大力鼓吹西方文明优越性的早期,他已有了类似的思想。他一开始对西方近代文明就不象后来很多人那样,持毫无保留的赞美态度。相反,他认为近代西方文明远称不上“至治极盛”。不仅如此,他甚至认为近代西方不仅算不上“至治极盛”,而且与之“相背而驰,去之滋远也。”西方物质文明的发展使得少数人有可能控制对国计民生至关重要的能力和手段,使得贫富贵贱之间的距离日益拉大。现代文明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技术手段,使得一些人的作奸犯科,危害社会与人类的可能性和程度也大大增加。(注:参看《严复集》第1册,第24页;第4册,第986、1122、1286页。)因此,严复对于现代性的负面效应始终持警惕态度。到了晚年,他更将这些负面效应归之于进化学说:“自物竞天择之说兴,大地种族,各以持保发舒为生民莫大之天职。则由是积其二三百年所得于形数质力者,悉注之以杀人要利之机。”(注:《严复集》第2册,第348页。)值得指出的是,严复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通过对维多利亚鼎盛时代的英国社会的亲身观察和体验发现现代性所包含的严重问题的。严复对于现代性一以贯之的批判性,足以证明他的思想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也证明鲁迅说他是十九世纪一个感觉敏锐的人,是何等的正确。
严复的过人之处不仅在于他对西方思想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而且还在于他几乎一开始就对现代性有异乎寻常的认识。他并不仅仅把近代中国的命运视为一个只与中国有关的特殊事件,而是已觉察到了它从属于全球现代性的性质:“存亡之机,间不容发,视乎天心之所向,亦深系四万万人心民智之何如也。后此之变,将不徒为中国洪荒以来所未有。其大且异,实合五洲全地而为之。”(注:《严复集》,第4册,第896页。)中国要想自存,没有其它选择,只有努力去适应这种形势及其要求。这就是为什么他要极力鼓吹向西方学习,并身体力行。但另一方面,他又不愿意任天为治,满足于指出所谓的历史必然性,以强调历史必然性来取消价值判断和道德批判,因为这等于是取消了自由。严复无法象后来的进化—历史论者那样,以历史必然性自慰,而对现代的种种苦难和弊病视而不见,因为他决不认为现代就是历史的终结,或人类理想的完美境地。作为一个真正的经验主义者和怀疑论者,他无法以现在为代价来换取一个虚幻的未来。
当然,在进步—历史主义者看来,严复对现代化负面效应的批判正好证明了他的“落伍”与“倒退”。在他们看来,既然中国的首要问题是实现现代化,那么在现代化实现之前,一切对现代性的批评只会阻碍现代化的实现,助长反现代化的气焰,所以不是“保守的”,就是“反动的”。西方社会由于已经先于我们而现代化了,批判现代性在西方也许有积极的或正面的意义,但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只有消极和负面的作用。毋庸赘言,这种思路的理论预设,正是线性单向进化论。然而,这种赢得许多人赞同的看法也象线性单向进化论一样独断、片面与简单。
持线性单向进化论的人大多是进步主义者,相信人类历史发展只有一条“共同的道路”,走在前者为优,走在后者为劣。发展本身就是进步。却未能进一步思考,历史发展的目的是什么?什么是进步?近代以来,人们惯于将历史发展和自然发展混为一谈,实际上它们是有极大不同的。这不同就在于,自然发展没有目的,而历史发展是有目的的。历史总是人的历史,目的是人的本质特征。人是自身的目的,也是历史的目的。虽然由于自身的历史性,这个目的本身并不完全确定,但它却使历史有了一种意义,我们可以据此来对历史本身作出判断;而这判断又构成我们自我理解的主要内容。进步与否,只有在此目的前提下,才能谈论。
进步—历史主义者由于对历史发展的目的没有过多的考虑,他们的进步概念往往十分抽象。既然道德进步和其它精神方面的进步无从谈起,他们所谓的“进步”实际所指只是物质方面的进步。这在中国尤其如此。任何对现代性的批评都被视为不利于物质文明的发展。人们喜欢用汽车飞机比马车跑得快,大炮原子弹比大刀长矛利害来证明现代性批判在中国不合时宜,正是这种心态的反映。然而,作出这种极不象样论证的人似乎忘了,有害气体或污染的环境对人类健康的伤害是到处一样的;现代科层制或权力结构对人性的压抑和摧残也是举世皆然;核泄漏不只对拥有汽车洋房的人有威胁。难道我们只有饮鸠止渴一条路,到了那一天再说?
其实,只要我们放弃对进步概念单纯物质主义的规定,而采取一种多元论的进步观,那么结论就会非常不同。我们会发现,在现代化过程的任何一个阶段,对现代性的批评都是一种促进社会健康全面发展的积极因素,而不是阻碍现代化的消极因素。现代化应该是人类全面发展的契机,而不应该是人向单面人转变的原因。人类需要发展,自然需要保护,正义要得到维护,缺乏这三者的任何一个,人类能真正幸福吗?缺乏这三者的任何一个的世界,能称得上进步吗?它们难道不应该是进步的基本衡准,如果有进步的话?也许进步—历史主义者在这些问题上和我们有相同的答案。分歧在于:我们认为,这些目标要通过人类种种艰苦的努力,包括不懈的批判来达到;而他们认为历史必然会向这些目标前进,尽管历史至今还没有提供任何这方面的证据。
毋庸讳言,严复的名字是与中国现代进化史观联系在一起的。在一定程度上他本人也可说是进化论的信徒。他对进化论的理解与解释的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后来中国的进步—历史主义的基本思路。在严复看来,“天演”首先指的是纯粹自然发展过程,“一气之转,物自为变。此近世学者所谓天演也。”(注:《严复集》,第4册,第1106页。)这种纯粹的自然中没有任何价值意味的。所以严复认为《老子》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两句话“括尽达尔文新理。”其中第一句话是“天演开宗语。”(注:《严复集》,第4册,第1077页。)然而,人也是“天演中一境,且演且进”。(注:《严复集》,第5册,第1325页。)这个“进”字,就含有价值意味了。本来是把人纳入自然界,从而将自然原理顺理成章地引入人类社会领域;现在却又反过来,价值进入自然过程,所以“且天演者,时进之义也。”(注:《严复集》,第5册,第1241页。)进者,当然是进步。这样原来是自然的,没有价值意味的发展过程,人为地成了一个同时也是进步的过程。本无价值意味的自然过程如何同时又是一个进步过程,这其中的过渡颇不自然,也是问题多多的。但在严复看来,既然是一个自然过程,那么即使是进步,也只能听之自然,非人力所能强求:“其演进也,有迟速之异,而无超跃之时。”(注:《严复集》,第5册,第1265页。)不但自然是这样,人类社会也是这样:“宗法之入军国社会,当循途渐进,任天演之自然,不宜以人力强为迁变,……”(注:《严复集》,第3册,第615页。)因此,他毕生主张改良,反对革命。进化论的世界观,决定了他保守主义的政治立场。而后世主张革命的进步—历史主义者,则将进化论修改为发展是不平衡的,进化是一个演进和突变交织的过程。他们更注重后者,这就给他们的革命立场提供了“科学的基础”。
既然进化是一个进步的过程,那么当然是“世道必进,后胜于今”。(注:《严复集》,第5册,第1390页。)一旦进化,就不可能再倒退回去。这就是说,历史是一个单向的进步过程。各国的发展,“虽时有迟速,期有长短,而其所经历者,固未尝不同也。”(注:《严复集》,第5册,第1268页。)也就是说,各国历史发展必经相同的阶段,不同的只是时间早晚而已。显然,这种思想是“XX的今天是我们的明天”之类的美梦与口号的理论基础。最后,进化是一个因果必然的过程,偶然性没有地位:“盖自达尔文、斯宾塞提证天演之说,于是言人群者,知世变之来,不独自其相承之纵者言之,必后先因果,倚优召从,无一事为偶也。”(注:《严复集》第2册,第270页。)至此,近代进化论世界观已轮廓初具。
然而,令人感兴趣的是,作为近代进化论世界观的始作俑者,严复对进化论的态度却是暖昧的。仔细阅读他留下的文字,很容易发现另外一种因素,这就是传统的循环论因素。他在读《老子》时写下这样的评语:“万化无往而不复”,(注:《严复集》,第4册,第1084页。)“不反则改,不反则殆,此化所以无往不复也。”(注:《严复集》,第4册,第1085页。)这显然与进化史观是格格不入的。但却由于这样的思想,中西古今在严复那里始终不是处于一种先进与落后,进步与反动的二元对立格局中,而是处于一种互补共进的关系中。即使在象《论世变之亟》这样早期文章中,将中西文化的不同特点对照比较,严复也决不是象后来承袭这种做法的人那样,心目中早已有了扬彼抑此的先定意图。严复更多地是采用一种经验主义列举事实,避免价值判断的做法。他在这里列举的是不同文化与民族在不同历史条件下长期形成的社会心理与风俗习惯,以及不同传统固有的教化。它们各有千秋,从不同角度体现了人类的公理。所以即使在批判中国传统种种弊端最激烈,鼓吹西方文化最积极的时候,他仍然认为“至于今日,若仅以教化而论,则欧洲中国,优劣尚未易言。”(注:《严复集》,第5册,第1390页。)
这决不是为了敷衍顽固派,避免给他们以口舌的策略之举,而是出于他内心深刻的信念。由于他思想中根深蒂固的循环论思想,他不可能将传统与过去视为完全消极的因素,将过去与现在,新与旧完全对立起来。相反,过去与现在,新与旧是健康发展不可或缺的,互补的因素。“非新无以为进,非旧无以为守;且进且守,此其国之所以骏发而又治安也。”(注:《严复集》第1册,第119页。)一方面,“文明进步,群治日新,必借鉴于古先,乃可求其幸福;”(注:《严复集》第2册,第271页。)另一方面,“古不能以徒存,使古而徒存,则其效将至于不存。”(注:《严复集》第2册,第276页。)古今互补互进,方能给人类带来最大幸福。他不象后来的进化论者那样,只注重变,而忽略恒常的东西。在他看来,“开国世殊,质文递变,天演之事,进化日新,然其中亦自有其不变者。”(注:《严复集》第2册,第332页。)这个不变者才是目的,其余都是手段。所以他认为“制无美恶,期于适时;变无迟速,要在当可。”(注:《严复集》第2册,第240页。)“法制必不可循名而不求实。”(注:《严复集》第2册,第241页。)而后来的进化论者却往往因只注重变革,而忽略恒常,一味追求新的名称和形式,结果却是有名无实,名实相背。严复的话在后来的进化论者看来可能是迂腐不堪,然而历史证明了他的睿智。
应该指出的是,本来在斯宾塞的进化论思想中就有循环论的因素。斯宾塞认为宇宙中并不是只有进化,而是进化与消亡的交替。在宇宙的任何部分都存在着进化与消亡有规律的循环运动,从个人生老病死,到物种的产生消亡。总之,斯宾塞的进化论在这点上有点象早期希腊循环论的宇宙论。但严复的循环论却很可能不是来自斯宾塞,而是来自老庄。证据之一是他在表述循环论思想时从未提及斯宾塞。并且,斯宾塞的进化论是从进化消亡交替运动中间接得出的,而严复则认为运动或进化本身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循环往复是进化的动力。这种思想显然是从《道德经》中化出来的。
但严复思想中的确还有一个来自斯宾塞的因素,使得他对进化的理解与后来的进步—历史主义者的理解有重要的不同。这就是斯宾塞的不可知论思想。斯宾塞和赫胥黎都认为,宇宙中有神秘的不可认识的东西,这就是万物的本体和终极原因。认识止于感觉经验。严复完全接受了这种不可知论的思想。正是出于这种不可知论,他认为虽然一般而言,进化是一个由因果必然性支配的过程,但具体是怎样的因果必然性我们不能尽知,因此,进化本身究竟如何都很难说:“天演之事,其因果非旦夕可尽,安知从此无所谓反动力者乎?”(注:《严复集》,第4册,第1004页。)进化到最后,究竟是个什么局面,谁也不知道。而后来的进化论者一个个似乎都不但知道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和必然阶段,也知道进化发展的最终景象。也就是说,严复知道不但自己的能力有限,而且人类的能力也有限,永远无法穷尽真理;而后来的进化论者和历史主义者则往往以为自己真理在握,或是真理的代表,说话以真理自居,必不许反对意见有反驳的余地,从而无形地限制了自由思想的空间,给专制主义预备了必要的精神土壤。
承认人精神能力的有限性,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种难得的思想品性。我们总是希望自己能知道一切,总想给出最终的结论。我们过于重视断言和肯定,却未必能够理解问题和怀疑的意义,更不愿象苏格拉底那样说:“我知我之不知。”其实,承认这一点并不意味着放弃真理与知识的追求,而只是让终极秘密永远作为不可思议者存在。这样,知识和真理就永远有发展的空间和余地。相反,一旦人们认为绝对或终极真理可致,就很容易会宣称自己已经达到,那么,剩下可做的事当然不会是对真理的探索与追求,而是对异己的讨伐了。也许英国经验论最值得我们宝贵和最能弥补我们精神气质上缺陷的,不是象有些人庸俗地从汉译的字面意义,想当然地理解的那样,以别人的经验为真理的尺度,而是它的怀疑论和不可知论。怀疑论和不可知论作为认识论立场问题不少,但作为一种思想态度却是对独断论必不可少的疗救。
严复思想中的不可知论因素使他对进化论远没有象后来的人们那样独断和绝对。正是对于进化论的复杂理解,使他的许多思想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历史助成了进化论的流行与接受,历史也越来越多地揭示着进化论的错误。严复和《天演论》宣传的进化论观念将会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和质疑,但严复进化的不可知论的态度,将会与他伟大的名字一起,越来越多地被人们记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