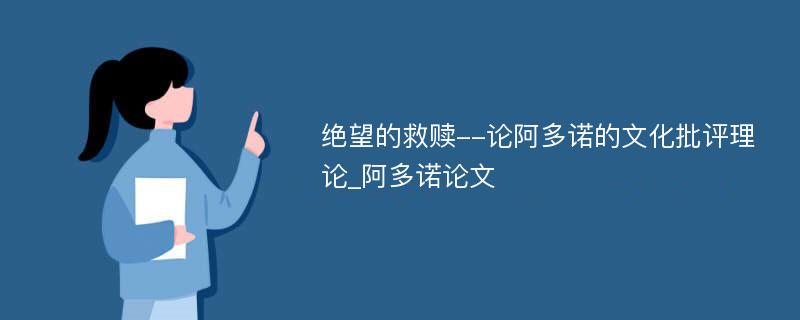
无望的救赎:评阿多诺的文化批判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论文,文化论文,评阿多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文化批判是阿多诺哲学、美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大众文化(文化工业)带来的艺术堕落、音乐衰退,特别是其强有力而又无所不在的文化控制,使阿多诺原有的文化启蒙、文化救赎的理想破灭,故而他对大众文化继始至终怀抱一种敌视的态度,并对其进行了激烈的批判。阿多诺的文化批判理论是深刻的、独特的,同时也是系统的,它不仅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就是在今天也仍然对我们具有启发性。
阿多诺是法兰克福学派中最早关注大众文化的人,是他“最先把大众文化和高等文化同时纳入到现代文化的理论研究视野”〔1〕。 早在1938年,阿多诺就写了《论音乐的偶像性和欣赏的退化》等论文,开始把大众文化纳入学术领域,在其影响下,1941年的法兰克福学派会刊《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特辟一期研究大众传媒和大众文化的专刊,在多维度上探讨了大众文化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运行机制和特征。1947年,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出版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经典著作——《启蒙辩证法》,它标志着法兰克福学派创立了具有自己特色的社会哲学理论,而其中的《文化工业:作为欺骗群众的启蒙》一文则被奉为研究当代大众文化的开山之作,它奠定了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的基调。此外,阿多诺还著有《现代音乐哲学》(1949年)等大量论文,对大众文化进行了更为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和影响。
阿多诺对大众文化所持的态度是极其明确的,马丁·杰用“无情的敌视”〔2〕来形容, 并且说他的这种思想“具有压倒一切的连续性”〔3〕。确实,阿多诺继始至终对大众文化进行着激烈的批判。 他甚至觉得“大众文化”(Mass Culture)这个词模糊而不准确,容易混淆视听,于是新造了“文化工业”(Cultural Industry )这一术语来说明事情的实质。阿多诺一开始就站在了大众文化的对立面。
一
阿多诺首先指出大众文化下的艺术堕落了。他坚持用“文化工业”来为“大众文化”正名,就说明了他对大众文化的“文化品质”的怀疑。阿多诺十分强调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区别,精英文化独一无二的精神自由和思想价值,成为他衡量和抨击大众文化的最有力武器,另外,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经典分析也是他文化批判的重要支柱,特别是“商品拜物教”更是他的论点的根据。在阿多诺看来,大众文化已偏离了正常的文化轨道,它以文化工业生产为标志,以市民大众为消费对象,以现代传播媒介为手段,一步步地趋向物化,直至沦为纯粹的商品,并不可避免地具有了商品拜物教的特性。同时,它自身的文化韵味也消失殆尽。基于这种认识,阿多诺拒绝承认文化工业的产品是艺术品。因为这时的艺术已成为纯粹的商品,文化工业的产品从生产到流通到消费,都是严格地按照商品的操作程序运转的,其所以被创造出来,只是为了交换,而不是为满足任何真正的需要,它意味着文化的人文意义和价值的全面覆灭,这是站在精英文化立场的阿多诺无论如何也不能容忍的。
阿多诺有着自己独特的艺术思想和艺术原则,他认为艺术乃是这个管理化世界的否定的潜在源泉,为此他提出一个重要命题:艺术对于社会是社会的反题。阿多诺还用社会批判理论来规定艺术,并赋予艺术以社会批判职能。他坚持,真正的艺术必须拒绝逢迎现存社会的规范,不使自己具备对“社会有益”的品格,艺术应对现存社会具有一种否定、颠覆的能力。同时,艺术还应具有乌托邦的功能,“在它拒绝社会的同一程度上反映社会并且是历史性的,它代表着个人主体性回避可能粉碎它的历史力量的最后避难所”〔4〕。 艺术“否定”和“乌托邦”的功能,就犹如一枚钱币的两面。总之,阿多诺认为,艺术是“一种救赎”〔5〕,艺术要表现由社会不公正造成的人类的痛苦, 要反思人类粗暴控制自然所带来的灾难。
可是在大众文化空间下,艺术想要逃避堕落的命运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艺术面临着一个商品交换社会。在商品关系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艺术不蜕化为商品,不蜕化为为实用目的服务,艺术家们不被整合到社会中,不丧失掉自律,将是十分困难的”〔6〕。 难怪“阿多诺尤其不赞同被当作大众文化的东西”〔7〕。他一针见血地指出, “文化工业只承认效益,它破坏了文艺作品的反叛性”〔8〕。 在这种情况下,艺术的产生变为艺术的生产,而且这种艺术生产是预先计划好的,是迎合市场竞争的。文化工业关心的不是艺术的审美价值和批判职能,而是作品的经济效益或“上座率”。于是,艺术家成了顾主的奴隶,艺术的创造纳入了按照固定框框设计出来的生产过程,“电影和广播不再需要作为艺术,……它们的结构都是由工厂生产出来的框架结构”〔9〕 。商品化了的艺术自然无法保持自身的独立品性,它拜伏在交换关系下,作为娱乐而像物质一样被消费,它与艺术王国日益疏远,却成了商品世界的一部分。以音乐为例,阿多诺指出,由于创作和消费受利润动机和交换价值的商品化趋势影响,从而出现了以下三种后果:其一,音乐不再区分为“轻音乐”和“严肃音乐”,而是区分为“受市场导向的音乐”和“不受市场导向的音乐”。其二,音乐的创作者孜孜以求的已不是艺术完美的审美价值,而是上座率和经济效益,他们一味迎合顾主的需要,成了消费者的奴隶。其三,绝大多数作品的价值已取决于是否可变为要销售的和可交换的,价值的实现依存于欣赏者肯否为之付钱,以投资效果作尺度。
既然艺术已沦为商品,那么它就必然按照商品的逻辑来运行,其显著特征就是艺术生产的标准化和艺术产品的齐一化,紧接而来的,则是艺术个性和艺术风格的彻底覆灭。“文化工业”按照一定的标准、程序大规模地生产各种复制品,它促进和反复宣传某个成功的作品,使风靡一时的歌曲和连续广播剧可周而复始出现,这造成艺术创作中作家的才能与个性被消除得一干二净。艺术与广告之间的差别消失了,“广告成了唯一的艺术品,戈培尔曾狡黠地把广告算作纯粹的艺术,实际上广告本身纯粹是社会权力的展示,……广告与文化工业在技术上和经济上都融为一体了”〔10〕。在阿多诺的心目中,真正的艺术是排斥商品性的,同时也是自尊的,为此他由衷地赞赏贝多芬,“贝多芬在病危时曾把瓦尔特·斯科特所写的一本小说掷之于地并气愤地说‘这个家伙写作就是为了赚钱’,同时他却以娴熟的技巧和执着的精神创作市场上拒不接受的最后一部四重奏,这就是市场与资产阶级艺术独立性对立面统一的一个极好的例子”〔11〕。贝多芬在证明,真正的艺术总是与无个性、无独立性的倾向进行着殊死斗争,它坚持自己的艺术本性,反对把自己变为商品和消费品。当好莱坞影片和爵士音乐作为美式文化商品出现在欧洲市场上的时候,它们立即与欧洲传统的古典艺术形成鲜明对照,而它们的缺乏“艺术风格”成为阿多诺批判大众文化的一个重要依据。他否认它们存在风格的可能,“文化工业的风格不再需要经过难对付的材料和验证,是反风格的风格”。在阿多诺看来,一切按配方程序制作的产品,都是没有风格的,无论这种产品是电影、电视节目,还是汽车、衣服,都只不过是某种单质整体的样品和复制品。面对这一切,阿多诺悲叹道:“艺术可能已进入它的没落时代,就像黑格尔在150 年前估计的那样。”〔12〕
二
在看到艺术堕落的同时,阿多诺更清醒地意识到,现代社会对个人的控制程度已远远地超过了以往时代,并且这种控制不是通过暴力和恐怖实现的,而是由意识形态进行的,这就是由“工具理性”和消费至上原则结合起来的大众文化。大众文化在无声无息中施行着一种全面的文化控制,“它一方面具有现代文化虚假解放的特性和反民主的性质,与独裁主义潜在地联系在一起,是滋生它的温床;另一方面构成对个人的欺骗与对快乐的否定”〔13〕。
在阿多诺看来,文化应该从根本上具有对现实的批判性和否定性,应该体现否定现实、超越现实的价值理想,应该提供种种与现实根本不同的抉择。可大众文化却是一种牢固的管辖与控制,它实质上充当了资产阶级统治的主要支撑物。在这里,文化即意识形态即操纵性工具。其逻辑是文化工业通过对大众心理进行操纵而发生作用,在操纵性文化的催眠和压抑下,大众丧失了批判和否定现实的能力。其结果是:文化中心成了商业中心或市政中心的适当场所,文化不再是现存制度的批判性力量,而只是维持现存制度的一种意识形态。一句话,大众文化是意识形态与社会物质基础的融合,是资本主义商品制度的组成部分。
大众文化说到底是虚假的和带欺骗性的,它无所不在地操纵着大众的思想和心理,培植着支持统治和维护现状的顺从意识,成为巩固现行秩序的“社会水泥”。阿多诺指出:“与自由时代不同,工业化的文化可以像民族文化一样,对资本主义制度发泄不满,但不能从根本上威胁资本主义制度,这就是工业化文化的全部实质。”〔14〕事实上,大众文化不仅不能丝毫动摇资本主义制度,反而加强了它的意识形态控制。由于“整个世界都得通过文化工业这个过滤器”,所以社会中的每个人都难以逃脱它的操纵和控制,他们貌似自由却是不自由的,貌似主动却是被动的,“每一个自发地收听公共广播节目的公众,都会受到麦克风、以及各式各样的电台设备中传播出来的有才干的人、竞赛者和选拔出来的专业人员的控制和受他们的影响”〔15〕。久而久之,大众就会自动放弃思想,变得麻木平庸,成为文化中的被奴役者。拿电影来说,它“总是用它的内容教育观众,促使观众直接用它去衡量现实”,这就必然会“抑制观众的主观创造能力”,从而导致“文化消费者的想象力和自发性的渐渐萎缩”。这在流行音乐那里也同样得到了表现,虽然阿多诺坚持,音乐应超越大众的流行意识,可流行音乐却彻底地堕落了。流行音乐结构简单,旋律反复,机械敲打,像刻板的公式一样,听众独立的思维、丰富的想象力瓦解了,听力退化了,处于被动的依附状态。“人们在听轻音乐时,从听到的流行歌曲的第一个音节,就可以猜出后来的续曲,往往因为乐曲果然如所猜想的,也就自得其乐。”〔16〕阿多诺认为,这表明流行音乐作为大众文化的一支,已沦落为受上面操纵和利用的傀儡,它剥夺了个人使音乐带有自己感情的能力,解除了听众必须赋予听的活动以任何精力或意义的负担,“使听者对社会现实不加批评,简言之,它对于社会意识具有催眠效果”〔17〕。现代社会,音乐最终被电台退化为一种日常生活的装饰品,成为一种社会的粘合剂。阿多诺由此得出结论,大众文化对国家权力失去了对抗的能力。“那种对抗集中控制的需要,已经先被对个体意识的控制扼杀了”〔18〕。大众在文化工业的五彩斑斓中沉醉,没有了思想,没有了反抗,这与法西斯的统治在本质上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却与法兰克福学派所坚持的“社会批判”立场尖锐对立。
文化工业对文化的控制本质上是对人的控制。一方面,文化活动失去了给人以精神享受的作用,而成为劳作的延长,旨在恢复精力,以能再次应付机械的工作;另一方面,文化工业决定着娱乐商品的生产,控制和规范着文化消费者的需要,成了一种支配人的闲暇时间与幸福的力量。在现代工业社会,“没有一个人能不看有声电影,没有一个人能不收听无线电广播,社会上所有的人都接受文化工业品的影响。文化工业的每一个运动,都不可避免地把人们再现为整个社会所需要塑造的那个样子”。更为甚者,“文化工业使精神生产的所有部门,都以同样的方式影响人们傍晚从工厂出来,直到第二天早晨为了维持生存必须上班为止的思想。”〔19〕大众失去了自己的判断力,他们一方面“不得不容忍一再生产出来的总是相同的产品”,另一方面又“对一切未经证明是畅销品的产品不予信任”,陷入一种极其尴尬的境地。阿多诺就此指出,文化工业生产出的文化商品剥夺了大众对艺术的超越性价值的追求和大众个人的感情与主动性,使其只作机械的条件反射;而且大众意识由于不断地受到这种丧失了否定性、超越性的文化商品的催眠和灌输,也就逐步习惯于对社会现实不加批评。所以他坚持认为,文化工业的产品骗走了人们从事更有价值和更为充实的活动的潜力,“文化工业通过不断地向消费者许愿来欺骗消费者,它不断地改变享乐的活动和装璜,但种种许诺并没有得到实际的兑现,仅仅是让顾客画饼充饥而已”〔20〕。也就是说,文化工业总试图用表面的华丽与热闹来掩饰它的阴谋,“用令人兴高采烈的预购,来代替现实中禁欲的痛苦”〔21〕。人最终被文化工业异化和同质化了,成了一个个原子。“如今已贬值的深层心理学所规定的内在生命,它整个儿都向我们显示人正在把自己变成无所不能的机器,甚至在感情上也与文化工业所提供的模式别无二致,人类最内在的反应也已经被彻底僵化,任何特殊个性都完全成了抽象的概念:个性只不过是表现为闪亮的皓齿,清爽的身味和情绪,这就是文化工业的彻底胜利。”〔22〕
三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阿多诺的文化批判理论笼罩着浓厚的悲观主义色彩,“阿多诺是迄今为止对当代文化最彻底和最悲观的批判者”〔23〕。文化的控制、艺术的堕落、音乐的衰退,使解放无望、救赎无望,在阿多诺的眼里,文化工业的世界已完全没有了希望,他的工作只能是对大众文化的极力贬损。他叹息道:“除了绝望能拯救我们之外就毫无希望了。”
阿多诺的悲观主义不是偶然的,这与他的文化经历和对文化的独特理解分不开,马丁·杰对此有详细考察,“作为一个在异国环境中流亡的人,他有时扮演着专心于理解他的所在国的陌生习俗的文化人类学家的角色”,但“对于在离乡背井中所碰到的各种土生土长的艺术形式,他都只有轻蔑。……阿多诺对美国从未有过任何真正的同情,更不用说处于西方范围之外的各种较为原始的文化样式了。……他对无产阶级失望,阿多诺认为无产阶级创造一种相反的工业阶级文化的努力是完全失败了。……他很少赞同在使用现代技术手段的大众艺术中所进行的试验。……对民族主义文化中被扭曲的反抗性要素、乌托邦的痕迹,他也不甚乐观”〔24〕。就个人来说,阿多诺对德国法西斯利用宣传工具操纵大众意识有痛切的感受,因此它对文化工业对大众意识的操纵特别敏感。这一切决定了阿多诺对大众文化不可能作任何辩护,他也无法预见现代文化的最终走向。正如怀森指出的那样,“阿多诺的理论盲点,必须同时理解为理论的和历史的盲点。的确,他的理论在我们今天看来也许就如同历史的废墟,被它的表述和产生条件所破坏和残损:德国工人阶级的失败、现代派艺术在中欧的先盛后衰、法西斯主义、斯大林主义和冷战。……无论是试图复活或埋葬阿多诺……都必然不能为他在我们不断变化的认识现代性文化的努力中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25〕
由于阿多诺的文化批判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大众文化的部分本质特征,暴露了晚期资本主义的矛盾与危机,故而引起了社会各界特别是知识界的广泛关注,并一度为60年代的欧美青年的“反文化”运动提供了思想武器,表达了他们对大众文化成为反人性的意识形态的抗议和对文化商业化的不满。但另一方面,由于阿多诺对大众文化的无情敌视,也常引起争议,并招致下述指控,说他是精英主义的势利眼,傲慢的上流人物,甚至还是一个隐藏的种族主义者(由于他憎恨爵士乐)。杰姆森讥之为得了“前资本主义怀旧病”,伯因斯坦斥之为固守精英贵族立场,甘斯认为他犯了“文化自主论”的错误〔26〕。后起的一些大众文化批评者也对他悲观的文化批评从多方面作了彻底的检讨和批判。
站在今天的立场上,一方面我们应该意识到,阿多诺的文化批判理论“在今天毕竟已经是一个成为过去的历史产物”〔27〕,另一方面,作为当代杰出的思想大师、20世纪最有影响的文化批评家之一,阿多诺的思想无疑又是具有启发性的,“阿多诺的文化理论至今仍有着极重要的意义……事实上,现今任何对大众文化的讨论都无可避免地要包括对阿多诺群众文化理论的某种评估”〔28〕。总之,阿多诺文化批判理论的历史意义是不可抹杀的,但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他的理论限度。
注释:
〔1〕〔27〕〔28〕徐贲:《走向后现代与后殖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91、297、291页。
〔2〕〔3〕〔7〕〔24〕马丁·杰:《阿多诺》, (台湾)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版,第126、135、126、128页。
〔4〕阿多诺:《论抒情作品与社会》, 转引自弗雷德里克·詹姆逊:《马克思主义与形式》,李自修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27页。
〔5〕阿多诺:《现代音乐的老化》,载《乐谱》1965年第18期, 第22页。
〔6〕李小兵:《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与危机》,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63页。
〔8〕〔9〕〔10〕〔11〕〔14〕〔15〕〔16〕〔18〕〔19〕〔20〕〔21〕〔22〕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洪佩郁、蔺月峰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117、113、154、148、132、114、117、 118、123、131、132、125页。
〔12〕阿多诺:《美学理论》,美因法兰克福1970年版,第13页。
〔13〕欧力同、张伟:《法兰克福学派研究》,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286页。
〔17〕阿多诺:《广播音乐的社会批判》,载《凯尼恩评论》, 1945年第8卷,第2期,第212页。
〔23〕弗雷德里克·詹姆逊:《马克思主义与形式》,李自修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30页。
〔25〕艾屈司·怀森:《阿多诺的另一面:从好莱坞到理查德·瓦格纳》,载《新德意志批判》,1983年第29期,第12页。
〔27〕见吴迪:《文化工业、品位文化与文化阶层》,载《电影艺术》1995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