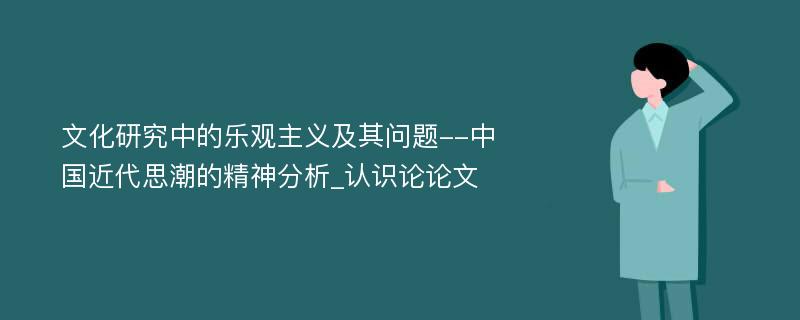
文化研究 乐观主义及其问题——对中国现代思潮的一种精神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乐观主义论文,思潮论文,中国论文,精神分析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伊始,中国就面临着极其严峻的社会危机和民族存亡的抉择。事实上,从19世纪后期起,中国知识精英的困境远远超出了传统意义上的内忧外患,它凸现为民族实体及其文化孰存孰亡的危机。现实操作层面的屡屡受挫和浸淫日深的价值迷失,更指示出一种社会解体的前景。因此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何近代的志士仁人总是心怀忧患,挥之不去。
历史常常呈现出吊诡之面貌。任何稍稍检视过近现代文献的人,都会发现,与忧患意识并列的却是高昂的乐观主义精神。1900年,才华横溢的梁任公写了一篇20世纪的开场白:“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吸张。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天载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美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这篇《少年中国说》鼓舞了多少热血青年!20世纪中国文化精神的主流无疑是相当乐观的。它超越了政见和思潮的对立,成为知识界普遍的观念倾向;而且已经积淀为社会心理。“乐观主义”成为值得贞定的价值,而它的对立面悲观主义则常常被现代中国人所鄙弃。是什么造成了忧患与乐观双峰对峙的现象?从社会效用的角度说,本世纪中国人获得的民族独立和巨大的社会进步,固然证实了乐观主义的合理性,但是它同时又是若干民族祸乱的精神之源(至少是其中之一),这就提示我们本世纪中国精神的“乐观主义”特征,实在是一个值得检讨的问题。
一
怀特海说过:“我认为,时代思潮是由社会的有教养阶层中实际占统治地位的宇宙观所产生的。”[①a]那么,20世纪中国“有教养阶层”的宇宙观是什么?我们知道,中国古代有辩证宇宙观的悠久传统,它特别体现在《易》学之中。从龚自珍、魏源开始,为了摆脱民族的和社会的双重危机,变易的理论就成为主流宇宙观。它相信“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相信“否极泰来”,“日新、日新、日日新”,宇宙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在永恒的变动中有望解决人类的一切困境。它不是从彼岸世界去寻求解脱,而是认定生活的意义就在生活世界之中,这本身就包含着乐观的倾向。
至19世纪末,变易史观成为中国人移植西方进化论的土壤。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是从“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类《易》理出发来接纳和理解进化论的。进化论对中国人有双重的意义:从工具的意义说,它确实激发起了人们挽救民族危亡的巨大热情;从价值的角度说,它建构起一个带目的论色彩的宇宙图景,无论自然还是人类,都处于一个上行的通道上。正是根据这种宇宙观,20世纪的中国人告别了古代的循环论和倒退史观,建立起“进步”的信仰。最早系统地介绍西方进化理论的是严复,最早独立地阐发历史进化论的却是康有为,这就是著名的“三世”说:人类社会遵循着普遍的进步规律,沿着“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上升通道向前进化。其最终目标是一个具有普遍人道的太平世界。“每变一世,则愈进于仁。仁必去其抑压之力,令人人自立而平等,故曰升平。至太平则人人平等,人人自立,远近大小若一,仁之至也”[①b]。那是一个大同世界。我们知道,戊戌年间的维新志士,包括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人,几乎无例外的都是进化论者。20世纪的诸多思潮,如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等等,几乎都和它有割不断的干系。不过,最重要的是,它的宇宙观的遗产已经成为20世纪中国思潮的基本精神背景。一部《天演论》哺育了几代中国知识分子。
由此确立了20世纪中国精神的乐观主义基调,形成了进步主义的现代传统。事实上,这在20世纪是一种世界性的现象。正如希尔斯(Edward Shils)说的那样,“它作为现代西方文化的必然构成要素,现在正在西方以外的当代社会日益扩大传播。这是一种认为人类能够从其世俗的不完善中救赎出来的传统。但是尽管上帝的王国不会在世上建立起来,然而使人类走向完善的社会进步则必将实现。进步思想以一种世俗化的翻版接受了关于人类堕落以及通过上帝恩典加以救赎的思想传统;以后这个传统中又增加了人类精神日益自我实现进化的思想。人类精神进化的思想逐渐变成了社会进化的思想,其目标是在更为完善的人类世俗生活中实现精神的潜力。”[②b]
这样一种乐观主义的宇宙观,不但为民族主义的崛起提供了令人向往的前景,而且普遍地导致社会向善论和人类向善论。不用说,自由主义者几乎无例外的都是进化论者,他们崇拜理性、崇拜一种有秩序的逐渐累积的进步。甚至原则上理应同进步主义相对立的文化保守主义,也大多分享了这一精神气质。以梁漱溟、熊十力为例,他们顶多只是批评生物进化论过于强调“竞争”,没有注意“互助”的重要性[③b];而对进步主义本身并无批评。梁氏的“文化三期重演”说完全符合进化论的基本模式。熊十力甚至用循环与进化的交参互涵来解释“相反相成”之道,得出了进化过程表现为螺旋形上升运动的辩证法结论。他们都受到柏格森“创造进化论”(Creative Evolution)强烈影响,主张创造的价值,其社会理论和人格理论都有着浓厚的道德理想主义色彩。
进化论有渐变论和突变论的区别,突变论在社会领域即转变为社会革命论,是进化论更激进的一翼。不过,生物进化论本身不能指示社会革命的方略;以进化论为其理论前提的唯物史观,水到渠成地成为指导革命(激进主义)的理论工具。而且在50年代以后,很快就成为主导意识形态。它不是一般地肯定“进步”,而是具体地规定了历史进程的明确阶段和最终结果,努力揭示普遍适用的社会发展规律。通过客观的决定论的公式,唯物史观比一般进化论显示出更多的乐观主义色彩,它预言人类经过不断的社会革命,不但可以达到高度的富裕,而且将消灭一切不平等与非正义,从而进入“自由人的自由联合体”的理想境界。
以进化论为背景与基调,本世纪中国人占主流地位的宇宙论—历史观的乐观主义,派生出近现代理想主义的Utopia[④b]传统。20世纪中国各种社会思潮,出于回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大多有一套理想社会的模式,作为自己的终极目标。康有为的《大同书》、世纪初广泛流布的无政府主义和新村运动、孙中山的“突驾”说[①c]、40年代自由主义者“人人有饭吃,各自选路走”(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②c]的社会蓝图、当代新儒家“内圣外王”的道德理想国,以及毛泽东农业社会主义式的“五·七公社”,几乎形成了20世纪Utopia史。从现实的层面说,所有这些“理想国”没有一个真正转变为现实;但是它们中的相当一部分,在历史上曾经起过很重要的范导作用。同时,它们中有的也曾经产生了巨大的破坏性。对此人们尚需要作深入系统的具体研究。本文不赞成一提“Utopia”就一笔抹煞的简单武断态度,只是注意到两点:一是激进主义思潮的“Utopia”确实给中国的现代化带来了极大的祸害,今天人们一提“Utopia”,就容易想到激进主义,但是并非只有激进主义才有“Utopia”倾向,它是一个世纪性的现象;二是乐观主义成为20世纪一系列“Utopia”共同的心理气质。认识到这两条,可能对我们比较正确地看待现代史上的一系列“Utopia”,会有所帮助。
二
20世纪社会思潮的乐观主义,同时还表现在认识论的领域,表现为一种认识论的乐观主义。按照卡尔·波普尔的说法,“这种乐观主义对人察明真理和获致知识的能力持一种十分乐观的态度”,其本质在于主张“真理是显现的”,相信人们有能力区别真理和谬误[③c]。
围绕着“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认识论成为20世纪中国哲学的热点之一。这主要展开为心物、知行的讨论。同时由于意识到中国古代形式逻辑被冷落的局限,逻辑学的研究也有长足的进展。既然本世纪(特别是上半个世纪)认识论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服从于中国道路的探索,那么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它们总体上都显示出强烈的乐观主义态度。
参与认识论问题讨论的有卷入各种社会思潮的人物。我们可以以两个极端的类型——非理性主义者和实证论者——来透视这一现象。认识论可以分为狭义和广义的两种:前者主要讨论“感觉能否给予客观实在”和“普遍必然的科学知识何以可能”两个问题,基本上是知识论的论域;后者则还要讨论获得具体真理——“道”——何以可能[④c]。在20世纪中国,几乎很少有人怀疑人们能够获得科学知识,非理性主义者对科学的批评,不是说我们不能获得科学知识,而是说科学不能解决价值问题。要解决价值问题,解决安身立命的难题,必须求“道”,即诉诸形而上学。20世纪的中国人,依然很大程度地保存了追寻“道”的热情。在西方,对认识论(广义)的乐观主义持批评态度的,是像卡尔·波普尔那样的实证主义者,他们的一大特征是拒斥形而上学。但是中国的实证论者,很少像他们的西方同行那样,完全拒斥形而上学。冯友兰和金岳霖是两位最著名的新实在论者,但是冯氏的“新理学”是“最哲学的形上学”,他不但以一套“理”、“气”、“道体”、“大全”范畴,来导引人进入他所谓的“天地境界”;而且认定,在逻辑分析的方法之外,我们可以用“负的方法”——直觉或禅宗的“顿悟”——来把握形上之道。金岳霖在《知识论》中以“所与是客观的呈现”和“概念有摹写和规范的双重作用”,肯定了感觉能够给予客观实在,回答了普遍必然的知识之所以可能。另外,他的《论道》指向“至真、至善、至美、至如”的理想境界,表示他对这些“超名言之域”有强烈的兴趣[①d]。另一个著名的实证论者胡适则坚决认为,科学知识完全可以负责指导人生对价值的探寻。任何一个知悉著名的“科玄论战”的人都会知道,中国的实证论者,对我们能够把握人生大道,很少有认真的怀疑。
对20世纪认识论的乐观主义,我们可以分三种情况来清理其思路。
自由主义思潮中人(其哲学背景通常是英美实证主义),他们在认识论上的乐观主义还表现在理性崇拜。他们认为,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每个人都有理性,只要不盲从权威,敢于运用自己的理性,就能够达到真理。这种乐观主义为他们的政治信仰提供了认识论的依据:“人能够认识,因而他就是自由的。这就是解释认识论乐观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观念之间的联系的公式。”[②d]西方古典自由主义有“上帝”作为“自由”之信仰上的依据,而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更多的是依赖人人皆有理性的推理。
文化保守主义者(其哲学背景常为宋明理学和欧洲大陆哲学,包括非理性主义),他们在认识论上的乐观主义,大多表现在直觉崇拜。他们认为科学所凭借的工具理性——逻辑——不能达到形上的真理,要想达到玄学的真理,只有直觉可以完成这一任务。梁漱溟是这样,熊十力也是这样。他们认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一旦觉悟到本心,就达到“天人合一”——自由——的境界。“人能涵养其本有之智而不放失,则后起之理智作用与一切知识,亦皆是智之发用”[③d]。牟宗三依据这一思路,用“良知的自我坎陷”,来解释如何从道德本人体开出知性本体。不管他们的理论架构是否成功,其理论预设是一致的:人类具有获取知识、达到真理的能力。与此相联系,应当以传统的中国文化为本位。
激进主义者(20、30年代以后还包括陈独秀、瞿秋白那样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在认识论上的乐观主义,常常表现为对“客观规律”这一范畴作机械论的理解。受前苏联哲学教科书的影响,他们通常把客观规律解释为纯粹的单线决定论,盲目地强调它的普遍有效性;并且毫不怀疑人类能够把握这种客观规律。一旦有人(常常是领袖)认识到这一规律,他就有权指导人们的行动。我们已经看到,教条主义(也就是机械论)地理解规律范畴,导致了独断论,在60-70年代则导致了严重的个人崇拜、个人独裁。这种对规律的独断论的理解,在它的另一极,由于过分强调实践的能动性,事实上又常常走向唯意志论。从进化论盛行的时代,直到70年代,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两极相通的情况[④d]。换言之,认识论的乐观主义还同唯意志主义思潮相关联。
20世纪认识论的乐观主义,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和近代以来西方科学的传播有关。
在中国传统哲学中间,除了道家有某种程度的反智论倾向外,从理论上说人们很少怀疑自己认识世界、认识自己的能力。儒家(如宋明理学)认为通过“道问学”和“尊德性”两个途径,可以直达大道。中国佛教(特别如禅宗)认为人人能成佛,也就是人人能够觉悟、达到智慧的境界。不过,中国古代认识论的乐观主义较为有限。认识大道并非轻而易举。儒学认为它要经过天理与人欲的斗争,佛教认为要经过去染成净的修炼。宋以后的儒家,一直为一种困境意识所纠缠。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说,王安石变法这一操作层面的严重受挫,促使宋明儒学在实际事务中转向温和的现实主义,在形而上的世界里却更多地指向两个相关的目标:一是寻找一种圣人的力量来引导世界走向善,二是通过个人的道德净化来完成人的伦理关切。但是基本上由于“道心惟微,人心惟危”的原因,真理似乎显得可望而不可即[⑤d]。
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家严厉地批评宋明理学的“空谈心性”,一批知识精英转向“经世致用”、转向“实学”,包括大批学者献身于考据学的研究。与此同时,西方的科学技术开始在中国传播,19世纪中叶起,中国人对西方近代科学技术表现出越来越高的热情,到本世纪初,科学技术已经变得十分崇高。新文化运动把“科学”与“民主”并列为两大价值。其前提不仅在于科学的有用性,而且在于科学的真理性。凭借现代科学,中国人不但能够获得知识、解除现实操作层面的困境,而且能够洞察真理——对于这一点,除了少数敏锐的思想家以外,大多数中国人没有怀疑。这就是唯科学主义在20世纪中国十分流行的重要原因。因为,正如有的研究者指出的那样,“唯科学主义认为宇宙万物的所有方面都可以通过科学方法来认识。”[①e]唯科学主义思潮成为认识论的乐观主义的一种新的极端形式,乐观主义也由于科学主义思潮而前所未有地强化起来。
三
相信人类理性的力量,相信人有察明真理的能力,实际上还同信任人本身有关。因此,认识论的乐观主义就同人性论、伦理学联系起来。
由于犹太教—基督教的“原罪”说,更往前推,希腊神话中还有人性中杂有“Titan”的故事,西方文化关于人类堕落的学说可谓源远流长。中国文化中没有这种幽暗意识的传统。相反,关于人性的理论,中国古代儒家有悠久的“性善”论的传统,至少是它的变形,即承认人是可以改善的。中国人很少会相信如新教加尔文宗那样不可更改的“预定论”。佛教中国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在佛性论上向儒家性善说转变——中国佛教各宗纷纷宣传人人能成佛,就是用佛教的语言在说人皆有善性。
中国哲学—文化中的这种性善论的传统,成为20世纪中国精神中乐观主义的另一重要根源。性善论使得教育人、改造人、提升人的前景变得十分光明,它是所有道德理想主义的基本前提,换言之,它也使得种种社会改造的蓝图能够取信于人。我们知道现代新儒家如梁漱溟、熊十力等都是性善论者。熊氏更提出著名的“性修不二”说,把《易传》富于乐观意味的“成性”说发挥得更具积极进取性。他认为一方面根据并发展天性,一方面发挥人力修行,由此“变染成净”,造成理想人格。在20世纪中国,信奉“大同”理想的,有康有为式的改良主义者,有孙中山那样的民主主义者,还有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其间当然有细节的区别,但是他们都相信可以达成“人皆为尧舜”的理想境界。换言之,这种乐观主义,不光有宇宙论的原因,而且有人性论的根据。
既然“性善”说古已有之,何以到本世纪才导致强烈的乐观意向?在古代正统儒家的学说里,肯定人的本性善的同时,又承认在经验的世界中人不断为恶。他们通常把它区别为“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前者常常指理性(天理),后者常常指感情、欲望(人欲)等等。如程朱理学就主张通过“存天理灭人欲”的功夫,培养出理想人格——圣人。所以我们可以说,中国古代性善说虽然对人为善的前景较为乐观,但是其中仍然保留着对人性中非理性因素的恐惧和压抑,有相当的禁欲主义倾向。
近代以来,中国人的观念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龚自珍、俞理初开始,不断有人批评禁欲主义,主张满足人的合理的欲望。《病梅馆记》一类呼吁人道主义的文学作品,大量涌现。从哲学上说,功利主义代替德性论,成为近现代伦理学的主流。这构成了20世纪的精神背景之一。维新思潮、民族主义思潮、启蒙主义思潮,甚至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都有功利主义的背景。现代新儒家尽管对功利主义大张挞伐,但是并不公开主张禁欲主义。
这种变化在20世纪中国人的生活世界里也有相应的根据。从19世纪中叶开始,中国缓慢地进入了现代化的进程。尽管在相当长的历史中,中国的经济困难重重,但是现代化在逐渐实现也是事实,其间还数度出现过高速增长的时期。一方面,工业化、现代化的前景描绘了高度满足人们生活需求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本来需要刺激人们的消费欲望。换言之,在中国这样的后起的外生型现代化过程中,功利主义和消费主义几乎是题中应有之义。
这两个世界的变化导致了互相矛盾的双重结果:它使得人道主义思潮成为难以扼杀的潮流,它为人性的全面自由发展提供了新的条件。在20世纪,我们仍然能够期望人类走向真、善、美统一的理想境界。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对我们自己的发展前景更加乐观。与此同时,负面的结果也随之而来,功利主义和消费主义在销蚀着德性的价值,现有的价值迷失更为加重了。也就是说,乐观主义正在酝酿着它的对立面。
四
我们说乐观主义已经融化为中国近现代精神的传统,并不是说可以用它来概括近现代精神的全部。在把握一个时代的共同点时,不应该忽略它所包含的差异。其实,乐观主义的对立面——悲观主义——从来就有。不过这种在本世纪只占次要地位的倾向,在我们现在反思其对立面——乐观主义——的时候,却有了某种参照系的意义。
王国维是本世纪中国一位著名的悲观主义者,在他的青年时代,认定“生活不过是痛苦与无聊间的钟摆”的叔本华,可谓深契他心。这种对生活意义的悲观主义理解,几乎贯穿了他的一生,并且出于对现代世界性精神分裂之感悟,而越发深刻浓重。这使他说出了一句名言:“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①f]他从根深的哲理上发现,人类古老的真善美统一的理想,其实是无法达成的。科学与人生、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理智与情意,都有难以消解的紧张。
章太炎从进化论到“俱分进化论”,也使他走向了悲观主义。《旭书》时代的章太炎是个进化论者,但到《民报》时期,他转而对人类生活普遍进化的观念提出了深刻的质疑:从经验中可以获得证实的,只有科学知识能够不断进步。至于人类社会,善进化、恶也进化;幸福进化、痛苦也进化。像王国维一样,章太炎也认定人性是善恶搏杀的永恒战场,人的意志本质上是不可弥合地自我分裂的。因此章太炎不仅认为善恶是一起发展的,而且认为“进化惟在知识,而道德乃日见其反”。甚至认定“人为万物之元恶”,又是无法根本改善的,以致于对人类抱极端悲观与虚无的态度。
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些别的个案,但是王国维和章太炎的悲观主义是最典型的。在20世纪大气磅礴的乐观主义主流下,王、章完全是个异数,他们的观点不但没有被多少人真正接受,而且简直就没有被认真注意。特别是章太炎的《俱分进化论》发表以后,很长时期都处于寂寞之中。但是今天我们认识到,他们对我们重新审视乐观主义却并非毫无意义。实际上,王氏以后,真正深刻有创见的乐观主义哲学家,大多没有消极地绕过王国维的问题,而是在试图用不同的途径去消弭这种世界性的分裂。我们可以看到,熊十力——牟宗三一脉的哲学家试图从“德性主体”到“知性主体”,来打通善和真;金岳霖——冯契一脉的哲学家则在努力从知识而德性,贯通科学与人生。他们的共同目标,都是一个真善美统一的理想世界。在进化论的家乡,西方思想界自60年代开始,也对进步主义提出了批评。毋庸多言,乐观主义几乎永远不可能从根本上被推翻,更不能被取消。一般意义上的“乐观”和“悲观”,只是一种心理趋向或气质之差异,不存在认识上之是非。但是“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可能都有偏颇,我们需要的是在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之间建立起对话与沟通,使之能够形成一种审慎和清醒的乐观心态。这大概是我们反思20世纪中国乐观主义的一点结论。
注释:
①a 怀特海:《科学和近代世界·序》,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
①b 康有为:《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卷一,万木草堂丛书本,1917年。
②b Edward Shils,Tradition,chapter five,Faber and Fabers,London,1981.
③b “互助”在20世纪中国思潮中也是一个重要的观念,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是其主要来源,它同时也是无政府主义思潮的主要经典,但是《互助论》并未脱离进化论的基本理论范式。
④b 本文使用“乌托邦”这个概念的时候,基本上取价值中立的态度,考虑到现代汉语中的“乌托邦”一词主要被负面理解(尤以80年代以来为甚),可能用Utopia更加合宜。
①c 孙中山认为中国革命可以民族革命和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然后中国可以取得西方发达的经济,同时避免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这就是他的“突驾”说。
②c 参见胡伟希、高瑞泉、张利民《十字街头与塔》第六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③c 据笔者所知,卡尔·波普尔最早提出用optimism和pessimism作为研究认识论的分析架构,参见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6页。Thomas Metzger也用它们作为思想史研究之分析架构的一部分。笔者认为,把它们作为理想类型来使用,对于“客观描述”思想史是有帮助的。但是,他们都没有说明,在认识论上它们的“绝对值”不相等:我们可以有绝对的(或极端的)乐观主义的认识论,但不能有绝对的悲观主义认识论,因为断言“我们绝对无法认识真理”,立刻就陷入逻辑悖论。
④c 冯契先生更是把“理想人格如何培养”也纳入认识论的范围,这成为他的“智慧说”的一大特征。可参见冯著《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①d 参见冯契《忆金岳霖先生以及他对超名言之域的探讨》,载《智慧的探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②d 卡尔·波普尔:《猜想和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第7页。
③d 熊十力:《新唯识论》,中华书局1989年版。
④d 参见拙著《天命的没落——中国近代唯意志论思潮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⑤d 这里我采用了墨子刻教授对宋明理学研究的结论。参见 ThomasMetzger,Escape from Predicament,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7,NewYork.
①e 郭颖颐:《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雷颐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
①f 王国维:《静安文集续编·自序二》。
标签:认识论论文; 精神分析理论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乐观论文; 社会思潮论文; 现代主义论文; 理想社会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读书论文; 进化论论文; 科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