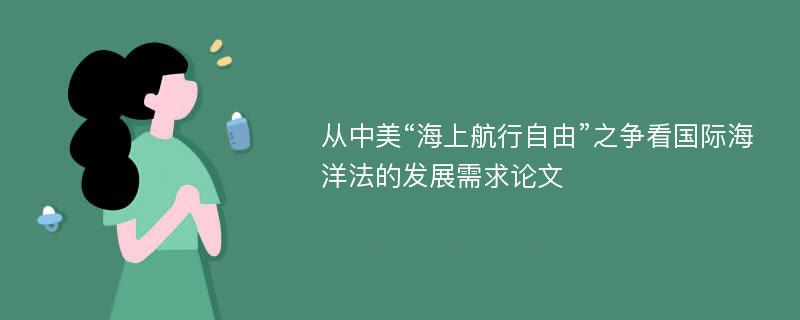
从中美“海上航行自由”之争看国际海洋法的发展需求
张 炜
[内容提要] 2015年以来,“海上航行自由”之争成为中美军事摩擦并可能引发冲突危机的焦点问题。中美各自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相关条款做了不同解读。二战结束迄今,国际形势、战争形态、武器装备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带来了诸多新问题。但缺乏相关国际专法,现行国际法及海洋法对海上军事行动适用的明确规定很少,一些应运而生的双边或多边军事条约、规则的法律强制性不够,都是导致海上军事摩擦、冲突乃至可能的战争之重要原因。它从一个侧面深度反映了当代国际海洋法的发展需求,其中既包括战争法和武装冲突法的发展、国际海洋法对海上军事活动适用的发展,也包括直接建立相关的双边和多边海上军事行动法。在这一领域,中美两个大国和国际社会都应当有所作为。
[关 键 词] 中美关系 海上航行自由 航行自由行动 国际海洋法
2015年,美国军用舰机开始进入中国南海岛礁附近海域实施巡航行动。四年过去了,美国南海“航行自由行动”成为常态,中美军事关系持续恶化。“新冷战”抑或“热战”会否打响?二战以来的世界格局会否崩盘?中美“海上航行自由”引发的对峙僵局如何打破?举世瞩目。
前期获得关注度后,则需要研究用户群体属于哪一类,什么样的文章会获得较多的浏览和点赞,什么时间推文最适合。后期则需要不断改进。但是笔者认为无论关注度如何,微信公众号该做的最重要的事是持续输出高质量的内容。
一、“海上航行自由”之争是中美军事摩擦乃至引发危机的焦点问题
2015年5月,美国军方发言人爆出“美国军方考虑派军舰和军机进入中国近期填海造地的南海岛礁12海里海域”以宣示航行自由的消息,随即“沃思堡”号濒海战斗舰抵近南沙群岛中国驻守岛礁的12海里外邻近海域。同年10月27日,“拉森”号导弹驱逐舰进入渚碧礁附近海域,开启公开进行“航行自由行动”巡航的序幕。这一年,美P-8A反潜侦察机和B-52战略轰炸机也抵近了中国南沙驻守岛礁12海里外的邻近空域。(1) 参见刘晓博:《研究|中美南海海上军事互动的危险前景及形势评判》,国观智库,2018年10月29日,http://www.grandviewcn.com/archives/5280 [2019-08-10]。
随着科学技术的创新发展和社会生产力的极大提高,传统的市场营销模式已经无法适应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快速变化,生产的规模化和生产流程的标准化,极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因此各行各业的内部竞争日益激烈,市场上的产品都处于“供大于求”的局面。在这种状况下,“卖方市场”为主的传统市场营销模式逐渐向“买家市场”为主的现代市场营销模式变化。
2016年,美国“威尔伯”号驱逐舰和“迪凯特”号驱逐舰两次进入中国西沙群岛领海基线以内。美国长期以来非议中国西沙群岛的领海基线主张,公开派军舰进入西沙群岛海域挑战中国这一主张,反映了双方南海矛盾斗争的升级。这一年,美海军“劳伦斯”号驱逐舰也进入南沙群岛永暑礁的12海里内实施“航行自由行动”。
抽象域[10]是指通过一组由计算机可以表示的元素命名为域元素以及基于该元素定义的一系列的操作,称为域操作,来对具体的程序所进行的抽象刻画。在抽象解释的理论基础上的分析验证过程都是在程序的抽象域中展开的。作为抽象解释的理论中的一个核心概念,抽象域的描述要从抽象域的表示(即域元素的描述)和抽象域中的操作,两方面来考虑。
中美“海上航行自由”之争发生在危险的军事领域,显然不是纯粹的法律问题。然而,二战以来,以《联合国宪章》为引领,国际社会形成了以相关国际法,特别是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为代表的国际海洋秩序。美国奉行“国内法优先于国际法”的基本政策,在1988年推出“航行自由计划”(6) 美国“航行自由计划”始于1979年。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通过后的1983年,里根总统有针对性地发表了《美国的海洋政策》声明,重申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航海和航空自由等权利,1988年12月正式推出“航行自由计划”,明确指出要以军事行动“表明美国保护航行自由的决心”。此后,美国海军在世界100多个国家实行“航行自由计划”,每年用“航行自由计划报告”记录这些军事行动。 ,且迄今没有加入《公约》,但也始终宣称遵守包括《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并据法与中国辩争。中国则是《公约》的成员国,根据包括《公约》在内的相关国际法建立了中国的涉海法律体系。由是,中美“海上航行自由”之争经年(7) 参见张炜:《中美海上航行自由之争——回顾与展望》,载王缉思主编:《中国国际战略评论2016》,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6年,第93页。 ,涉及的主要法律分歧是:
2018年,有统计显示,美国在南海先后派出六艘军舰进行了五次“航行自由行动”,B-52战略轰炸机进入南海空域活动创纪录的达到了28次, P-8A巡逻机还曾搭载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记者在南沙群岛中国岛礁航拍现场报道。其他相关活动也很频繁,如:美国海军海洋调查船“托马斯·汤普森”号停靠了台湾,巡洋舰“安提塔姆”号和驱逐舰“威尔伯”号航行通过了台湾海峡,“里根”号航母编队与日本“加贺”号准航母编队在南海进行了联合军事演习,“黄蜂”号两栖攻击舰在被拒绝进入香港后也在南海进行了示威性军事演习。(4) 参见刘晓博:《研究|中美南海海上军事互动的危险前景及形势评判》,国观智库,2018年10月29日,http://www.grandviewcn.com/archives/5280 [2019-08-10]。 此外,更为先进的B-1B战略轰炸机也加入了在南海上空的飞越自由行动。(5) 转引自《吴士存:如何使“航行自由行动”远离南海》,环球网,2018年10月2日,http://opinion.huanqiu.com/opinion_world/2018-10/13164019.html?agt=15438 [2019-08-01]。
美国对此反应迅速,坚决反对中国“限制无意进入中国领空的外国航空器飞越东海防空识别区”,公开声明不予承认,三天后即派遣两架B-52战略轰炸机穿越中国东海防空识别区。美国还与日本签署发表要求中国取消东海防空识别区的共同文件,此后不断派遣飞机穿越,以显示其在中国领空以外航行和飞越自由的基本立场。
这至少是临近危机。如果真的是41米的海上航行距离,发生撞船事故就在一分钟之内;如果是在空中,就是一瞬间!美苏1988年黑海撞船事件和中美2001年撞机事件都是前车之鉴。如果撞上就是危机发生,而其后也只有冲突或不冲突两种选择,概率各是50%。到那时候,规则是一回事,现场指挥员的决定是另一回事。设问:中美在南海可不可能发生冲突?答:完全可能。于是,两国外交上的声辩、交涉、抗议不断见诸报端,中美双方似乎已接近了“准对抗”,或者说正“纠结”在对抗与合作的边缘上。
进入2019年,这种状况继续:1月7日,美“麦坎贝尔”号导弹驱逐舰进入中国西沙12海里领海海域;2月11日,美“斯普鲁恩斯”号和“普雷贝尔”号两艘导弹驱逐舰进入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和美济礁邻近海域。之后,在5月6日、20日和8月28日,美海军导弹驱逐舰又有三次擅闯中国南海岛礁邻近海域的行动,包括进入黄岩岛12海里以内海域。又据9月26日中国国防部例行记者会披露,美国“里根”号航母编队“正在南海航行”,炫耀武力。此外,还有美国B-52H战略轰炸机飞入南海空域和美海军舰艇穿越台湾海峡等相关报道。面对中国的严正反应,美国仍以行使“国际水域”航行自由权为说辞。
中美军事关系进入了新的紧张期,美国的南海“航行自由行动”成为中美海上安全的焦点问题。尽管双方目前的海上接触行动都很克制,又有两个“海空相遇安全准则”的行为规范,但由此带来的中美军事摩擦是现实的,引发意外事件乃至危机冲突的可能性亦不可低估。这当然是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
二、中美“海上航行自由”之争中的法律分歧
2017年4月,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将派军舰和战机在南海实施“航行自由行动”、挑战中国海洋权益主张的一揽子年度计划送交白宫,并建立了展开行动的标准程序,特朗普随后批准了这份要求美军“例行、规律地”在南海开展“航行自由行动”的年度计划。(2) 参见萧强、杜海川、王会聪:《美国批准“航行自由”年度计划南海航行将更频》,《环球时报》2017年7月24日;《美军制定南海“航行自由”计划表 每月2至3次》,人民日报海外版-海外网,2017年9月2日, http://news.haiwainet.cn/n/2017/0902/c3541093-31099344.html [2019-08-01]。 这标志美国在南海的“航行自由行动”改变了“一事一请”的方式而进入有计划的常态,也意味着美国海军的相关航行请求“更快得到批准”。 同年5月24日,美国“杜威”号驱逐舰进行了计划批准后的第一次“航行自由行动”。这一年,美国实现了四次公开的南海“航行自由行动”,两次进入美济礁12海里内,两次进入中国西沙群岛领海,并在美济礁临近海域进行了搜救演练。还有消息人士说,这一年还有两次未对外公开的“航行自由行动”,并首次进入中沙群岛的黄岩岛附近海域。(3) 转引自《吴士存:如何使“航行自由行动”远离南海》,环球网,2018年10月2日, http://opinion.huanqiu.com/opinion_world/2018-10/13164019.html?agt=15438 [2019-08-01]。
(一)关于中国的领海基线制度
2014年12月,美国国务院公开发表从法律角度评述中国南海权利主张的官方研究报告,核心观点是中国南海断续线及其历史性权利主张不具有合法性。报告认为,中国没有按照国际法方式清晰解释与南海断续线地图有关的海洋权利主张,而无论是以“岛屿归属线”、“国界线”还是“历史性主张线”来解释南海断续线,都不符合国际法;中国以南海断续线为依据对其中的低潮高地和暗礁等“水下地貌”主张主权,并主张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超出了《公约》赋予沿海国的权利。(14)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Bureau of Oceans and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and Scientific Affairs:Limits in the Seas No.143 China’s Maritime Claims in the South China Sea,December 5, 2014,http://www. state. gov/e/oes/ocns/opa/c16065.htm[2019-08-15]. 美国还强调,中国南沙群岛岛礁建设属于“人工岛屿”,亦不应享有领海主权及海域管辖权。据此,2015年以后美国一再派舰机赴南沙群岛实施“航行自由行动”,以宣示上述立场。
1958年9月4日,中国《关于领海的声明》宣布,中国的领海宽度为12海里,领海基线为直线基线。1992年2月25日,中国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正式确立了直线领海基线制度。1996年5月15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决定”,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发布了《关于领海基线的声明》,对外正式公布了从“山东高脚”至“海南峻壁角”和环绕西沙群岛的两组领海基点及其基线,从而明确了中国这部分领海海域的起算线。
美国反对中国的领海基线制度。1996年7月,美国国务院海洋事务办公室海洋国际环境和科学事务局发表了署名罗伯特·W.史密斯的《中国的直线领海基线主张》研究报告,详细评判了中国上述两组领海基点和基线。报告认为,中国大陆海岸不具备选择直线基线法的“法定自然条件”,基线内的部分内水应为领海或公海,部分领海应为公海,西沙群岛用直线基线法划定领海基线没有法律依据。报告提出:“中国合理的领海基线应是沿大陆海岸、近岸岛屿的低潮线和合法的海湾封闭线。”自此,美国基本否定了中国的领海基线制度(8)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Bureau of Oceans and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and Scientific Affairs:Limits in the Seas No.117 Straight Baselines Claim: China,July 9,1996, http://www.state.gov/e/oes/ocns/opa/c16065.htm[2019-08-15]. ,并使双方的主张在中国领海的划定上出现了一个“分歧海域”,关于美国军舰是否进入了中国领海的争议由此产生。
(二)关于中国的领海无害通过制度
1958年联合国《领海与毗连区公约》和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都没有对“军舰无害通过权”给予明确规定,但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三节“领海的无害通过”的C分节里,定义了军舰,规定沿海国有权要求不遵守其国内法律法规的外国军舰离开领海等。此既说明“领海无害通过”适用于军舰,也说明沿海国对外国军舰通过领海具有管辖权。国际实践显示,各国对“军舰无害通过领海”的处理方式多元,分歧集中于是否需要沿海国批准或事先通知。
经过1978—1985年的反贫困努力,我国的贫困因子发生了变化,由过去的制度约束性贫困转变为区域性条件约束性与贫困户能力约束性贫困。基于此,1986年,中国政府启动了大规模的农村专项扶贫计划,旨在通过专项政策,提升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主要措施有:成立了专门的扶贫机构——“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1994年后改为“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确定了开发式扶贫方针;开始以贫困县为重点瞄准扶贫对象;安排了专项扶贫资金等。
中国政府采取了“限制”政策,认为《公约》赋予了沿海国对专属经济区的专属管辖权,并建立了“海洋和平利用”的基本原则。(10) 《公约》序言指出,“为海洋建立一种法律秩序,以便利国际交通和促进海洋的和平用途”的目标;第88条规定,“公海应只用于和平目的”;第58条规定,“第88条至第115条以及其他国际法有关规则,只要与本部分不相抵触,均适用于专属经济区”;第301条设置了“海洋的和平使用”条款。 中国政府据此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1998年)等一系列法律和规章。在对外国军用舰机军事活动的实际管辖中,既给予其在中国专属经济区及其上空航行和飞越的权利,但同时要求其活动必须基于“和平目的”并遵守中国相关国内法。中国坚决反对美国军用舰机在中国专属经济区及其上空进行危害国家安全的军事侦察和挑衅性巡航活动;对于其进入管辖海域的海洋军事测量等活动,要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海洋科学研究管理规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进行事先申请并得到批准。
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领海的声明》指出:“一切外国飞机和军用船舶,未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许可,不得进入中国的领海和领海上空。”199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第6条规定,“外国军用船舶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须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批准”。
美国一方面认为军舰无害通过领海无需事先通知或事先征得沿海国的同意,这一观点在其《海上军事行动指挥官手册》中被一再强调,并将秉持这一观点和做法的国家列入“过分权利主张”的行列,在实践上,美国则对这类国家根据需要采取“航行自由行动”以彰显其“反对”的立场和主张。美国对于中国要求外国军舰进入领海需要事先批准的主张是公开反对的,也将其列入中国“过分权利主张”的内容之一。
(三)关于中国对专属经济区及其上空军事利用的管辖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建立了专属经济区制度(9) 《公约》第56条规定,沿海国在其专属经济区有勘探和开发、养护和管理自然资源,从事经济性开发和勘探等活动的主权权利;有对人工岛屿、设施和结构的建造和使用,海洋科学研究,海洋环境保护和保全管辖权。第58条规定,沿海国有给予其他国家权利的义务,即航行和飞越自由,铺设海底电缆和管道的自由等。在规定沿海国和其他国家权利和义务的同时,又分别规定了相互“适当顾及”的原则。 ,其第56、57、58条规定了所有国家在专属经济区内的权利和义务,其中包括各国都享有“在公约有关规定限制下的”航行和飞越自由,同时也规定了应当“适当顾及沿海国的权利和义务”和必须“遵守沿海国按照本公约的规定和其他国际法规则所制定的与本部分不相抵触的法律和规章”的原则。由于专属经济区制度争议颇大,相互妥协而成的条款表述模糊,形成一些“灰色地带”和弹性解释空间,导致沿海国对外国军用舰机在专属经济区海域军事活动的处理大致分“限制”和“不限制”两类做法。
我国大陆海岸线蜿蜒深远,18000公里的长度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渤海湾、胶州湾、杭州湾、珠三角湾等湾区星落其上,也让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有了重要的前期经济积淀。占据九市二区,在惠州、深圳、香港、东莞、广州、肇庆、佛山、江门、中山、珠海、澳门围绕下的粤港澳大湾区,不同区域内,不同生产要素的优势互补,可以为粤港澳大湾区乃至整个泛珠三角区域提供广阔的经济腹地,同时也将为泛珠区域合作注入新的发展动力。作为“一带一路”桥头堡,粤港澳大湾区得天独厚。
根据文章的表述可知,青少年自身具备的价值观与道德判断能力越强,出现攻击行为的频率将会大大降低。在此过程中,群体观作为一种集中体现社会取向的价值观,其个体价值发挥的越高,人际价值存在感将会越高。针对于此,笔者建议学校方面应该加强青少年价值观与道德判断方面的教学工作,教师应该起到正确的舆论引导作用,及时纠正个别学生行为上的偏差,有效约束与规范个体行为,确保青少年个体可以得到全面性发展、茁壮成长。
本文在精确测定金门花岗闪长岩SHRIMP锆石U-Pb年龄的基础上,探讨其成岩与成矿作用的关系,分析其与钦杭成矿带及旁侧与花岗闪长(斑)岩有关的Cu-Au-Pb-Zn-Ag多金属成矿带成因联系,为矿区及区域下一步找矿工作提供年代学依据。
对于什么是智慧校园,有各种不同的定义。笔者理解的智慧校园是一个复杂、智能的系统,是在数字校园基础上的进一步提升,通过综合运用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新兴信息技术,全面感知校园物理环境,有效识别学生学习特征和教师工作场景,将学校物理空间和数字空间有机融合,构建开放的教育教学环境,改变师生与校园的交互方式,最终实现以人为本的个性化创新服务
我公祖因生活困苦留下太婆和爷爷在乡下,带亚祖漂洋过海到马来西亚割胶谋生。公祖勤奋、又孝顺,想方设法做工赚钱又省吃俭用寄回来给太婆盖房子。花了公祖他们六七年辛苦赚的钱盖起的大房子惹来伯公祖一家的贪婪,伯公祖一家欺负我太婆爷爷两婆孙,耍起野蛮,以分家的名义将太婆和爷爷赶到了放杂物的烂瓦屋住。村民与亲戚觉得欺人太甚,要为我太婆讨回公道。我太婆心善,不愿吵架,怕伤了兄弟的情分,也不肯告诉公祖。两年后来自同镇的村民的家信里提到,公祖才知道此事,他听从太婆的劝告,没有和伯公祖吵,又辛勤赚钱重新盖房子。
美国反对中国的上述限制政策,认为沿海国在其专属经济区除对自然资源可行使主权之外,管辖权是很有限的;专属经济区是“国际水域”,美国军用舰机享有与公海同样的航行和飞越自由,以及和这些自由相关的合法使用海洋的其他自由。美国承认沿海国有权对其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内的海洋科学研究实施管辖,但认为对海洋地貌、水文气象、海峡水道等的军事测量是军事活动,不是海洋科学研究,不需要得到沿海国批准。
(四)关于中国防空识别区的设立
在国家领空以外建立防空识别区以保障飞行安全,是为当今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国际惯例。20世纪50年代后,美国、加拿大、日本等许多国家都根据各自国情建立了防空识别区。
在数学课堂教学中,往往有许多效率低下、无效的而且是分散的、琐碎的、不相关的问题。这些问题使学生的思维变得肤浅。学生在教师的推动下,被动地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2013年11月23日,中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飞行基本规则》,宣布划设中华人民共和国东海防空识别区,要求“位于东海防空识别区飞行的航空器”,必须提供飞行计划、无线电、应答机和标志四种识别方式,并服从中国防空识别区管理机构的指令。(11) 参见《中国政府宣布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人民网,2013年11月24日, http://politics. people. com.cn/n/2013/1124/c70731-23636082.html[2019-08-15]。
针对美国在南海频繁的海空军事行动,中国照例派出舰艇和飞机进行查证、监视、驱离的维权行动,双方海空相遇明显增多,危险接近不断发生。据报道,2018年9月30日,美海军“迪凯特”号驱逐舰进入南沙群岛并逼近南薰礁,受到中国海军“兰州”号导弹驱逐舰的拦截驱离,双方发生了据说最近距离41米的危险接近。
(五)关于中国对南沙群岛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主张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家无视中国的反对,在南沙群岛争相抢占、建设岛礁,在中国南海断续线内海域捕鱼、开采石油天然气,并通过国内立法宣示对所占岛礁及海域拥有主权和管辖权。对于中国与周边国家在南海的主权和海洋权益争议,美国一直采取“不持立场”“不选边站”态度。但在2010年以后,随着中国崛起进程加快,美国改变了其南海政策。尤其是2015年中国南沙岛礁建设工程被媒体报道后,中美在南沙群岛及相关海域的权利归属问题上形成尖锐对立。
中国政府根据《开罗宣言》《波兹坦公告》等二战后国际秩序安排的权威文件,于1945年收复了南海诸岛。自1951年中国政府正式发表“西沙群岛和南威岛正如整个南沙群岛、东沙群岛一样,向为中国领土”(12)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长周恩来关于美英对日和约草案及旧金山会议的声明》,《人民日报》1951年8月16日。 的声明后,一直持续宣示同一立场。2016年,中国政府再次发表声明,准确阐述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1)中国对南海诸岛包括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拥有主权;(2)中国南海诸岛拥有内水、领海和毗连区;(3)中国南海诸岛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4)中国在南海拥有历史性权利。(13)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声明》,人民网,2016年7月13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6/0713/c1001-28548649.html[2019-08-15]。 南沙群岛作为中国领土,中国进行岛礁建设自然是中国的权利。
领海基线是沿海国确定其领海和其他管辖海域的起算线。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确定领海基线的方法有正常基线法、直线基线法和混合基线法。沿海国可根据其海岸实际情势,决定其领海基线的确定方法。
三、从中美“海上航行自由”之争管窥国际海洋法的发展需求
就国际法的发展而言,总是实践在先、成法在后,而矛盾和分歧就是各种不同国际实践的反映。中美“海上航行自由”之争发生在军事领域,并对此有诸多对国际法、海洋法的不同理解,其重要原因之一在于:统一规范当代海上军事行动的相关国际公法还没有产生,现有相关国际法、海洋法对海上军事行动适用的明确规定少之又少(15) 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例,直接涉及军舰的条款有:第29条“军舰的定义”;第30条“军舰对沿海国的法律和规章的不遵守”,“沿海国可以要求该军舰立即离开”;第31条“船旗国对军舰……造成损害的责任”;第32条军舰的豁免权;第95条规定“军舰在公海上”的“完全豁免权”;第102条对军舰和军用飞机由于其船员或机组成员发生叛变而从事海盗行为的规定;第107条规定军舰和军用飞机对由于发生海盗行为的扣押权利;第110、111条对军舰及军用飞机的“登临权”和“紧追权”的规定。 ,而一些应运而生的军事双边和多边的条约、规则的法律强制性不够,这反映了当前相关国际法、海洋法亟须发展。这是一个很大的或者说是全人类的共同课题。本文仅从中美“海上航行自由”之争略加引申,管中窥豹,以引起各方关注和讨论。
(一)关于战争法和武装冲突法的发展问题
在国际法领域,战争和武装冲突有质的区别,战争受战争法调整,武装冲突则主要受平时国际法的调整。从以“大炮射程”为基准确立领海开始,规范海上战争和平时军事行动就进入了国际法议程。19世纪末20世纪初,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战争的残酷性使人类对规范战争行动的需求空前强烈,出现了以海牙体系为代表的战争法和以日内瓦体系为代表的武装冲突法(亦称人道主义法),其中包括了对海上战争和武装冲突的规范,这是国际法建设的重大成就并延续至今。二战以后,以《联合国宪章》为代表的世界和平秩序和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代表的海洋秩序建立,但这并不意味世界范围内的海上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就此停止。1977年《日内瓦公约》两项附加议定书、1994年《圣雷莫海战法手册》等,是国际社会为战后武装冲突法发展的新贡献,美苏限制核武器及运载工具的“条约”也为冷战背景下保持世界和平做出了贡献。
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现代战争概念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核武器、生化武器、远程导弹等武器装备的发展,信息时代引发战争形态的改变,太空军事竞争的加剧,国际海底开发纷争可能的发展,甚至以无人机横空出世为代表的机器人技术的广泛使用,都带来新的国际法问题。进入21世纪,大国经济政治博弈尖锐化,由反恐怖主义带来的国际干涉主义战争行动不断发展。近年美俄在叙利亚的干涉战争、俄罗斯突袭攻占克里米亚、俄美在委内瑞拉的军事行动、美国退出“中导条约”、土耳其对叙利亚发动军事打击行动,还有其他非传统威胁、非战争军事行动以及国际军事合作的大量需求等,都呈现出当今国际变局中战争、武装冲突及国际军事行动的新特点、新趋势,对二战以来的国际秩序产生前所未有的挑战。
从法律的角度看,这些不断发展的国际实践,使现行的传统战争法、武装冲突法的法理及规则日显缺失和苍白。中美“海上航行自由”之争,是国际法和海洋法中的古老问题在当今国际社会的发展,它会否引发军事冲突甚至战争,谁都不敢断然否认。因而,无论是从国际大环境来看,还是从中美海上纷争的局部问题来看,发展适应当代新特点的相关国际法规的需求是显而易见的,包括战争法和武装冲突法(平时法)。
(二)关于国际海洋法的发展及对海上军事活动的适用问题
1494年葡萄牙和西班牙在大西洋上划定“教皇子午线”,成为最早的海洋瓜分实践。1609年,荷兰法学家格劳秀斯提出“海洋自由论”,反对国家瓜分和垄断海洋;1702年,荷兰法学家宾刻舒克的《海上主权论》(也译《海洋领有论》),主张沿海国依其陆上武器所及之处领有海洋。从此,“海洋自由”和“海洋领有”两派立场相悖、争论不休——从3海里领海制度将海洋区分为公海和领海,到美国1945年“大陆架声明”将国家海洋权利延伸;从第三世界国家纷纷声索200海里领海和群岛国权利,到联合国召开三次海洋法会议讨论海洋管辖权问题;直至1982年签署《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将全球大约1/3的海洋赋予沿海国专属管辖权。矛盾似乎缓和了,却不可能根本解决。
由于这份当代“海洋宪章”是世界各国利益平衡和相互妥协的成果,各国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加以解释和引证,带来了纷争不断。中美“海上航行自由”之争的内容,大多源于此。并且,迄今为止的各种国际法以及国内法,都基本排除了对军事活动的适用,而《公约》如上所述直接涉及军舰和军用飞机的规则很少,其他有关军事活动的问题则更属于参照。
然而,在实践中,参照的弹性是相当大的,这对于限制军事摩擦、武装冲突乃至向战争升级极为不利,尤其是像中美这样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双方由此走上对抗乃至军事冲突不啻现代社会的悲剧。但是,反过来说,如果中美两个大国就此出发,进入争议海域军事航行自由、专属经济区海洋军事利用规则等问题的细化讨论,意义无疑是重大的,至少是正视问题、合作前进,开启补充发展国际法及海洋法对海上军事活动适用的规范、细则之门。当然,这并非只是秉持中国立场要求美国妥协,妥协从来都是互相的。如果中美能够携手推动军事领域国际海洋法适用的发展,应当是世界海洋的和平福音。
(三)关于海上军事行动法
二战以后,随着美苏冷战的发生,根据国际法的基本规则和国际惯例,通过双边或多边军事条约规范相关军事行动成为国际社会普遍的做法。如冷战时期北约、华约两大军事集团的多边军事条约,以及数个与美国的双边军事同盟条约。这些条约解决了包括盟国和伙伴国之间的海外驻军、司法、访问、海空军事行动、联合军演和作战行动等诸多基本问题。与此同时,以美国与苏联在1972年签署的《美利坚合众国政府与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政府关于防止公海及其上空意外事件的协定》(简称《美苏关于防止海上意外事件的协定》)为代表,借助《1972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国际民用航空公约》和《国际信号规则》等相关国际法规,用附件形式规定了美苏双方军舰飞机在海上相遇时的行为规范,开互为敌手国家之间建立海上军事行动法规之先河。(16) 参见张炜:《冷战时期美苏预防海上突发事件的双边协定》,《外国军事学术》2013年第6期,第41页。 之后,这一做法被许多国家效仿,甚至作为建立海上相互信任措施的重要内容。
此外,近年来一些地区性的军事信任措施和安全规则也在发展。2014年,西太平洋海军论坛通过了《海上意外相遇规则》,将海上军事行动规则成功扩大到多边军事领域。(17) 参见《西太平洋海军论坛年会通过〈海上意外相遇规则〉》,中央政府门户网站,2014年4月23日,http://www.gov.cn/xinwen/2014-04/23/content_2665423.htm[2019-08-11]。 2014年12月,根据中美高层达成的共识,两国国防部签署了《中美关于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谅解备忘录》,中美两军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签署军用舰艇和军用飞机之间海空相遇的两个安全准则。(18) 参见《中美关于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谅解备忘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网站,2014年12月6日, http://www.mod.gov.cn/affair/2014-12/06/content_4555927.htm [2019-08-14]。 由于两国的大国地位及两国关系的重要性,相信这两个安全准则的示范性将超过以往。但也要看到,以上这些规则的细节和法律约束力还不够,双方在法律依据方面的分歧还有待寻求弥合途径,海空交战规则、海空遇险进入领土等规则还未明确纳入其中。
目前,随着中美在南海军事行动对抗性加强,双方都在为不可预测的军事摩擦和冲突担忧。可见,在战争与和平之间,在双方决心诉诸武力之前,国际性海上军事行动法的发展需求是多元的,且其发展的本身就是对相关国际法、海洋法在军事领域的细化和深化。
四、结 语
对中美而言,尽管“海上航行自由”博弈本质上是政治问题,但诉诸国际法及海洋法的发展平衡权利和义务,推进国际法及海洋法对海上军事活动适用的进程,致力于国际通用的海上军事行动法律法规的发展,仍是缓解两国间海上矛盾冲突乃至战争风险的重要和安全的途径,也是一个负责任大国应有的担当。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则更应当从当今世界变局、武装冲突风险增加的角度,统筹和引导战争法、武装冲突法以及国际海洋法的发展,在这一领域有所作为。这既是当今人类社会对和平与安全的期待,也将对完善国际海洋秩序、推动世界文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作者简介] 张炜,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特邀研究员、中国南海研究院客座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 D8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484(2019)06-0069-10
[责任编辑:李聆群]
标签:中美关系论文; 海上航行自由论文; 航行自由行动论文; 国际海洋法论文; 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论文; 中国南海研究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