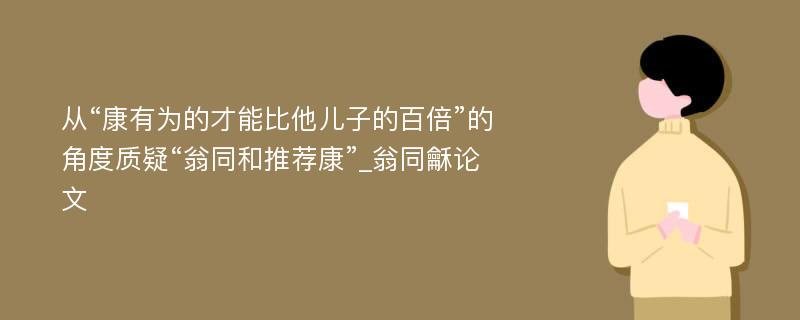
“翁同龢荐康”说质疑——从“康有为之才胜臣百倍”说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才论文,康有为论文,龢荐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戊戌维新中翁同龢向光绪帝“举荐”过康有为的说法在近代以来颇为盛行,得到了世人广泛认同。然而,这种说法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历史实情,似应予以更深入的分析和探讨。
一
1898年12月4 日(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十月二十一日)清廷颁布明发上谕,宣布将开缺在籍的翁同龢“即行革职”。该谕云:
翁同龢授读以来,辅导无方,从未将经史大义剀切敷陈,但以怡情适性之书画古玩等物不时陈说。往往巧借事端,刺探朕意。至甲午中东一役,主将主和,甚至议及迁避,信口侈陈,任意怂恿,办理诸务,种种乖谬,至不可收拾。今春力陈变法,密保康有为,谓其才胜伊百倍、意在举国以听。朕以时局艰难,亟图自强,于变法一事,不惮屈己以从。乃康有为乘变法之际,阴行其悖逆之谋,是翁同龢滥保匪人,已属罪无可逭,其余陈奏重大事件,朕间有驳诘,翁同龢辄怫然不悦,恫喝要挟,无所不至,词气甚为狂悖,其任性跋扈情形,事后追忆,殊堪痛恨。前令其开缺回籍,实不足以蔽辜。翁同龢著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不准滋生事端,以为大臣居心险诈者戒。(注:《清德宗实录》,卷432。)
这是最早提到翁同龢曾“举荐”康有为的官方文书,同时也首次披露翁氏“荐康”时说过“其才胜臣百倍”一语。此谕对近百年来“翁同龢荐康”说的盛行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然而,对于清廷做出的上述结论,当时即有异议。两江总督刘坤一在致友人函中称:“康有为案中诖误,内则有翁中堂(同龢),外则陈右帅(定箴),是皆四海九州所共尊为山斗,倚为柱石者,何以贤愚杂糅至此?若为保康有为以至波及,闻翁中堂造膝陈词,亦是抑扬之语。”(注:《戊戌变法》丛刊,(二),633页。)看得出, 刘氏对翁“荐康”是表示怀疑的。据张謇当时所闻,翁氏之案系“刚毅、许应骙承太后之意旨,周内翁尚书于康、梁狱,故重有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县官编管之谕旨。”(注:《戊戌变法》丛刊,(四),201页。)就连军机大臣王文韶亦为翁鸣冤, 认为“翁某罪在‘莫须有’之间”(注:《戊戌变法》丛刊,(四),252页。)。 这些迹象表明,翁氏革职别有隐情。
事实上,这道谕旨系由军机大臣刚毅拟稿,并体现了刚毅等人的意愿。1914年翁同龢侄孙翁斌孙撰《翁同龢列传》记云:“戊戌十月旨出大学士刚毅手,先一日,刚毅独对,褫职编管皆其所请。尚书王文韶于述旨时争之曰:‘朝廷进退大臣以礼,编管奚为?’刚毅谬其说,曰:‘慈圣意也’。文韶叹曰:‘吾曹他日免官可以此为例矣’。”(注:转引自谢俊美《有关翁同龢开缺革职的三件史料》,见《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3期,278页。)荣禄门人陈夔龙《梦蕉亭杂记》亦记云:“迨八月政变,康、梁获罪,刚相时在枢府,首先奏言:翁同龢曾经面保康有为,谓其才胜臣百倍,此而不获严惩,何以服牵连获咎诸臣?”(注:见该书(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63页。)以情理推之,刚毅奏此言当在十月革黜翁氏之前,而非八月政变发生时,此处应为陈氏忆误。从这些记述看,翁同龢革职似与刚毅的蓄意倾陷有很大关系。不过,刚毅是怎样以“滥保匪人”的罪名将翁罗织在康、梁案中,这还需要我们进一步分析和考证,特别是谕旨中“康有为之才胜臣百倍”这句话是否可视为“荐康”的铁证,则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二
据翁同龢门生称,翁从未说过“其才胜臣十(百)倍”之类的话,谕旨中此语实乃“刚毅辈不惬于公,设词以倾公,且以倾德宗也”(注:孙雄:《故清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翁文恭公别传》,见《旧京文存》,卷一。)。此论明显是为翁氏辩解。一般说来,刚毅拟旨,对翁氏上奏之言恐怕不敢凭空捏造,多少必有所据。从实际情况看,翁氏确实佩服康氏的才华,1895年7月1日(乙未闰五月初九)首次与康晤谈后,即视其为“策士”(注:参见孔祥吉《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133—134页。),并称康为“天下奇才”(注:王庆保、曹景郕:《驿舍探幽录》,见《戊戌变法》丛刊,(一), 492页。),照此看来,说句“其才胜臣百倍”的话也不奇怪;况且,据一些比较可靠的材料,翁同龢并未否认自己说过“其才胜臣百倍”之类的话。
近人丁国钧《荷香馆琐言》记云:“世皆谓翁相国保荐康某,相国得罪后,上谕中亦及之。赵次丈侯,相国老友也,曾面质以此事。相国谓皇上一日问及康某,我对以才胜臣十倍,然其心叵测,恐皇上不解叵字,又申言叵测者,不可测也,余未及康某一字云。”(注:《戊戌变法》丛刊,(四),253页。)。 从赵次侯转述翁同龢的话中可知,翁氏否认“荐康”,但并不否认自己说过赞誉康氏之才的话,只是有“十倍”与“百倍”之别而已。王崇烈《〈翁文恭公传〉书后》亦记云:
康有为成进士后,感愤时事,急于致用,每作危言论天下事,康实具有世界知识者,造次上书常熟不报后,以所著《日本变政考》乞为奏进御览。夫此岂常熟肯为者乎?康固不知也。忽一日,德宗于常熟独对后,示以《日本变政考》,意甚愠常熟不为奏进,并谕以试论康有为之才如何,常熟见天颜不霁,惶悚对曰:‘康有为才具胜臣十倍,其他非臣愚所能知也。’当刚、翁同值时,自亲王外,满臣以刚居首,圣眷亦隆,自刚衔怨之后,其于常熟早蓄排挤之计,至是得其间矣。(注:转引自谢俊美《有关翁同龢开缺革职的三件史料》,见《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3期,278页。)
王崇烈(字汉甫)系清季国子监祭酒王懿荣之子,民国初年开设清史馆,王氏受聘为协修。《翁文恭公传》即是王崇烈在翁斌孙所拟《翁同龢列传》基础上,又参阅清廷档案资料后写成的。据王称,一些情况因“事属琐屑,例不应引入正传”,故“用述颠末,作为书后,以存纪实”,以便“后人窥知当时政局之真迹”(注:见《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3期,279页。)。由于撰拟翁同龢传时,王崇烈曾向翁斌孙征求过意见,故上述说法有可能得之于翁氏后人之口,或者至少经过了他们的证实。因此,在原始材料缺乏的情况下,这段经过演绎、流传下来的口碑材料与《荷香馆锁言》所记情况均是有源史料,它同样证实了翁同龢说过“康有为之才胜臣十倍”这句话。
不过,将丁国钧、王崇烈的记述比较后会发现,翁同龢虽说过“康有为之才胜臣十倍”之言,但这只是半句话,“其才胜臣十倍,然其心叵测(其他非臣愚所能知也)”才是语意完整的一句话,这句话与协办大学士孙家鼐当时对康的评价极为相似。1898年7月17 日(五月二十九日)孙在《议陈宝箴〈厘正学术造就人才说帖〉》中称:“康有为之为人不端,而才华尚富……愿皇上采择其言,而徐察其人品心术”(注:苏舆:《翼教丛编》,卷2,19页。)。看来, 肯定康氏才识同时贬斥其人品心术并非翁一人的看法,这种褒贬各半的评价,恐无一般意义上的“举荐”之意。
三
进一步而言,翁氏奏言的具体时间亦可考证出来。王崇烈言“其才胜臣十(百)倍”之语是在奏进《日本变政考》时所说,其时间当在戊戌年三、四月间,这与刚毅所拟谕旨“今春力陈变法,密保康有为,有其才胜伊百倍之语”相吻合。以此为线索查证戊戌年春季的翁氏日记,可以发现,四月初七、初八(5月26日、27 日)两日的日记非常值得分析。
初七日记云:“上命臣索康有为所进书,令再写一份递进。臣对:与康不往来。上问:何也?对以此人居心叵测,曰:前此何以不说?对:臣近见其《孔子改制考》知之。”
初八日记云:“上又问康书,臣对如昨,上发怒诘责。臣对:传总署令进,上不允,必欲臣诣张荫桓传知,臣曰:张某日日进见,何不面谕?上仍不允,退乃传知张君,张正在园寓也。”(注:《翁同龢日记》(排印本),台北中文研究资料中心,1970,2175页。)
这里所言“康书”,正是《日本变政考》。康氏首次递进的《日本变政考》于4月13日(三月二十三)已由翁代呈御前, 但很快被转呈慈禧,故光绪帝令翁传旨让康再抄一份进呈。翁因抗奉旨,遭到皇帝训斥。笔者以为,“康有为之才胜臣十倍,然其心叵测”一语应该是君臣二人论辩时所讲。当时是枢臣见起,刚毅得以亲闻翁氏此言。戊戌十月在向慈禧进言并草拟谕旨时,刚毅断章取义,将“其才胜臣十倍”改为“百倍”,作为翁氏“荐康”的证据,同时将“其心叵测”一句隐去不言,此举不可不谓阴巧。翁氏自知是遭受诬陷却无法申辩,只好将日记中“其才胜臣十倍”半句删去,仅留下“其心叵测”半句。这正是我们今天在翁氏日记中看不到“其才胜臣十(百)倍”之语的原因。以前曾有人怀疑“其心叵测”一句是翁氏后来删改日记时添加用以饰人耳目者,现在看来,这种推论似乎并不准确。
戊戌年四月初七日(5月26 日)翁氏向光绪帝奏言“康有为之才胜臣十倍,然其心叵测”一事,从翁氏日记的另一处记载中也能得到映证。1899年12月20日(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十八日)清廷再下谕旨,重申悬赏缉拿康、梁,其中再次提及“翁同龢极荐康有为,并有‘其才胜臣百倍’之语”(注:《清德宗实录》,卷455。)。12月23 日(十一月二十一)翁氏日记云:
《新闻报》纪十八日谕旨,严拿康、梁二逆,并及康逆为翁同龢极荐,有‘其才百倍于臣’之语。伏读悚惕!窃念康逆进身之日,已在微臣去国之后,且屡陈此人居心叵测,不敢与往来。上索其书至再至三,卒传旨由张荫桓转索,送至军机处同僚公封递上,不知书中所言如何也。厥后臣若在列,必不任此逆猖狂至此!而转因此获罪,唯有自艾而已。”(注:《翁同龢日记》(排印本),2253页。)
此记充满了申辩的意味,这里提到戊戌年四月初七、初八之事恐非偶然,恰恰证实“其才胜臣十(百)倍”一语确在皇帝索取《日本变政考》时所说,否则翁同龢在读谕旨时不会再无端涉及此事。而且可以肯定,最迟此时他已将四月初七日记删改过。“因此获罪,惟有自艾而已”,流露出翁氏遭刚毅陷害而有口难辩的无奈。
四
戊戌年春翁同龢与刚毅同值枢垣,在处理政务时意见屡有不和,二人关系未洽确为实情,翁氏四月之开缺即与刚毅排挤有关(注:叶昌炽《缘督庐日记》戊戌四月二十九日云:“佩鹤来云,虞山(翁)之去,木讷令兄(刚毅)实挤之。七月十二日又记:“至别墅,适弢甫(翁斌孙)在允之座,谈极久,瓶师(翁)之归,木讷令兄有力焉。”见《戊戌变法》丛刊,(一),528—529页。)。作为慈禧在军机处的耳目,刚毅对翁同龢与康有为及其变法活动的关系再清楚不过了,翁如果“荐康”,无论如何是瞒不过刚毅的。然而,从革黜翁氏的谕旨看,除了“其才胜臣百(十)倍”这句话外,刚毅并未拿出更为有力的“荐康”证据,因此,王文韶对刚毅强加给翁氏“莫须有”的罪名持有异议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如果翁曾有“荐康”行为,为何政变发生时没有立即受到朝廷的惩处而要迟至十月才有此谕?这个问题本身就值得思考。戊戌八月礼部尚书李端棻、内阁学士张百熙均因公开举荐康有为而遭到“革职流放新疆”(注:《戊戌变法》丛刊,(二),105页。 )和“革职留任”(注:《戊戌变法》丛刊,(二),108—109页。)的处分。就连大学士荣禄也因保荐维新人士陈宝箴而被予以“降二级留任”(注:《戊戌变法》丛刊,(二),108页。)的薄惩。试想,这种氛围下, 慈禧如何会对曾经“荐康”的翁同龢网开一面?
再者,翁若“荐康”,无论以何种形式,总会留下一些蛛丝马迹的。如果是具折“保荐”,似应有奏疏存世。然而,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及台北故宫博物院迄今尚未发现有翁氏“荐康”的奏疏。若是“面保”,则有两种情况:一是“造膝密荐”,即除了翁同龢与光绪帝外,没有第三者在场;二是军机大臣召见时当众“面荐”。前者只有翁同龢在毓庆宫授读时才有可能,但是,从1896年2月25 日(光绪二十二年正月十三日)慈禧下令撤去汉书房后,翁氏已无法在毓庆宫“造膝独对”。同时,按照清代规制,军机大臣无单独召见之例,枢臣只能在入值时一起被召见(注:清代军机大臣一同进见之例始于乾隆年间,详见梁章钜《枢垣记略》卷27。甲午年翁同龢入军机之初,因在毓庆宫行走,枢臣入值前,得以与光绪帝独对。此事与常例不符,翁同龢曾深为忧惧。据《翁同龢自订年谱》(载《近代史资料》总86号)甲午年十二月记:“自念以菲才而当枢要,外患日迫,内政未修,每中夜彷徨,憾不自毙。讲帷职事,仅有数刻。最难处者,于枢臣见起之先,往往使中官笼烛宣召,及见则闲话数语而出。由是同官侧目,臣亦无路可以释疑。”后慈禧下令撤去汉书房即与翁氏“独对”招致奕訢等枢臣不满有关。)。从汉书房被撤到戊戌四月翁氏开缺为止,光绪帝从未单独召见过担任军机大臣的翁同龢,《谕折汇存》和翁氏日记均可证实此事。如果翁是入值时当众“面荐”康有为,当时必然会有传闻,而事实上在戊戌年四月翁氏被开缺前乃至是年八月政变爆发前,似未有人闻及翁同龢“荐康”之事。这一情况在史料学上的反映是,迄今我们见到的涉及翁氏“荐康”的全部文献,无论是官方档案还是私家著述,没有任何一件被证实形成于戊戌政变前。因此,翁氏“荐康”作为一种历史事实存在过的说法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五
刚毅在戊戌十月罗织“荐康”罪名对翁进行政治打击并非偶然,这与康有为政变后的第一次公开谈话直接相关。
1898年10月6 日(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一日)康有为在香港接受了英文报纸《中国邮报》(《China Mail》,又称《德臣报》)记者的采访,这是康逃离北京后第一次就时局发表公开谈话。作为当事人,他把整个维新变法过程和政变原委作了简要的阐明,经过一位买办翻译,记者将康氏谈话用英文记录下来。当时离政变发生仅隔半月,世人方苦于传说纷纭,是非真相扑朔迷离之际,康氏的谈话立刻引起中外媒体的极大关注。第二天,上海英文报纸《字林西报周刊》全文刊载了这篇采访记(注:《戊戌变法》丛刊(二)收录的《中国的危机》一文,即是根据《字林西报周刊》转载的康氏访谈记重新翻译的。),随后,上海《申报》、《新闻报》、天津《国闻报》等纷纷将康氏谈话译成中文以飨读者,其反响之大,以至于慈禧也得以目睹(注:戊戌年九年改归知县庶吉士缪润绂曾将《国闻报》转载的康氏谈话内容抄录进呈。见《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9年版)487页。)。 翁同龢“举荐”过康有为的说法正是康氏在这次谈话中首次提出的。时隔两月,刚毅即以“其才胜臣百倍”为据,治翁氏“滥保匪人”之罪,恐与康氏谈话所造成的舆论氛围有直接关系。
康氏为何政变前对翁“举荐”之事守口如瓶,政变发生后却公然将此“秘密”扬之报端?这令人疑惑不解。翁同龢从报纸上看到康氏谈话内容后,于10月18日(九月初四日)日记中写到:“《新闻报》等本皆荒谬,今日所刊康逆语,谓余论荐,尤奇,想我拒绝,欲计倾我耶?!”(注:《翁同龢日记》(排印本),2201页。)这里,翁否认曾“举荐”过康氏,并断言这是康有为对自己曾“拒绝”他而进行的倾陷。由于翁氏日记在政变后曾经删改,此论或不易为人们所相信。不过,通常而言,康氏散布“荐康”说时是不会不考虑对翁氏安危影响的。既然他置自保不暇的翁同龢于不顾,公开宣扬对翁不利的言论,显然对“荐主”没有保护之意,反倒有恩将仇报之嫌。如此而言,翁氏日记所云则更近情理。何况,据张荫桓称,翁同龢确实拒绝过前去求见的康有为(注:《戊戌变法》丛刊,(一),492页。)。
从康氏后来的著述看,他自己对翁“举荐”时间的说法也前后不一。在1910年(宣统二年)刊布的《怀翁常熟去国》诗序中,康氏称丁酉年十一月十九日前“常熟已力荐(康)于上”(注:《戊戌变法》丛刊,(四),342页。);而1920 年(民国九年)所写《翁文恭书〈易林〉书后》一文中则云,“(翁)公忧中国,进呈吾所著《日本明治变法考》、《俄大彼得变法考》,因荐言:‘康有为之才,过臣百倍’,遂被德宗特达知。 ”(注:康有为:《万木草堂遗稿》, 台北成文出版社,1978,192页。)从这里看,“举荐”又在戊戌年三、四月间。 《康南海自编年谱》则没有明确提到翁“举荐”之事,只是称翁在光绪帝前对“高燮曾奏荐请召见”之议“力称之”、“再持之”而已。(注:《戊戌变法》丛刊,(四),137—138页。)如果这也算作一种“举荐”的话,其时间应在丁酉十一月十九日(高氏上折)之后。对康来说,翁氏“举荐”绝非一般小事,可他的记载却彼此矛盾,这恐怕不能简单归结为记忆上的失误。更为有趣的是,1899年5 月梁启超于日本横滨印行的九卷本《戊戌政变记》在叙述翁氏“荐康”一事时,竟将刚毅所拟谕旨中翁氏“密保康有为,谓其才胜伊百倍之语,意在举国以听”之句,删改为“翁同龢复面荐于上,谓康有为之才,过臣百倍,请皇上举国以听”,添作翁氏“荐康”的细节,翁奏言“康有为之才胜臣十(百)倍”一语的时间也被说成是戊戌正月初三至初八之间(注:《戊戌变法》丛刊,(一),250—251页。)。这说明,康、梁在政变前并不知道翁氏说此话的具体情况,更不知道这是被刚毅歪曲了的“荐康”证据。显然,康、梁著述中有关翁氏“荐康”的说法并不可靠。
六
50年代《光明日报》曾披露出一封所谓翁氏自认“举荐”康、梁的佚札,人们多视其为出自翁氏本人之手的“荐康”力证,不过,此札的真实性同样受到了怀疑(注:参见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台北,1970年版)149—150页。)。笔者以为,政变后兴起的“翁同龢荐康”说,无论是源于康、梁的倡说,还是刚毅的指认,均缺乏确凿的事实依据。在戊戌年春康有为进用过程中,翁同龢并未“荐康”,翁、康关系也不像政变后康、梁著述中所描述的那么密切。当时于幕后积极支持康有为并直接向皇帝密荐康氏的,应是户部左侍郎、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号樵野)。如果说翁对康之进用也起过一定作用的话,这种作用也是间接性的。作为深受皇帝信赖的重臣,他在初期曾对张积极援引康有为的活动予以了默认和支持,这是不可否认的,尽管这种谨慎的支持与翁、张之间的私谊不无关系,而且是以履行公务(如奉旨索取康书或以总署名义代奏康氏条陈)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关于翁、康关系以及翁同龢与戊戌变法的关系,史学家何炳棣先生曾分析说:“当此之时,同龢所处地位最难,南北之争,英俄之争,满汉之争,以至帝后之争,同龢无不身当其冲。同龢非不知中国需改革之切,而不敢同尽废旧章之改革;非不知中国需才之殷,而不敢用驰突不羁之才;非不原有所建树,而不敢以首领禄位为孤注。故于变法之论,未尝执意力主,亦未尝昌言反对。”(注:何炳棣:《张荫桓事迹》,见《清华学报》第13卷,第1期,1941年昆明出版,206页。)此论可谓中肯。
政变后康、梁公开宣扬“翁氏荐康”说的原因,大约有两点:其一是为了借以掩盖张荫桓通过非正常途径推动康有为进用的内情(注:详见拙文《张荫桓与戊戌维新》(收入王晓秋、尚小明主编《戊戌维新与清末新政——晚清改革史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其二是刻意攀附翁同龢以自高身价,以便利用翁氏的清望,唤起士林对“保皇”活动的同情和支持,其用意与伪造光绪帝密诏可谓同出一辙。从实际情况看,“翁同龢荐康”说是通过康氏谈话、革黜翁氏上谕、《戊戌政变记》等文献的传播散布开来的。在此过程中,康、梁与刚毅各怀目的,存在着事实上的相互利用,这一点也是昭然可见的。
标签:翁同龢论文; 康有为论文; 戊戌变法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翁同龢日记论文; 清朝论文; 近代史研究论文; 新闻报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