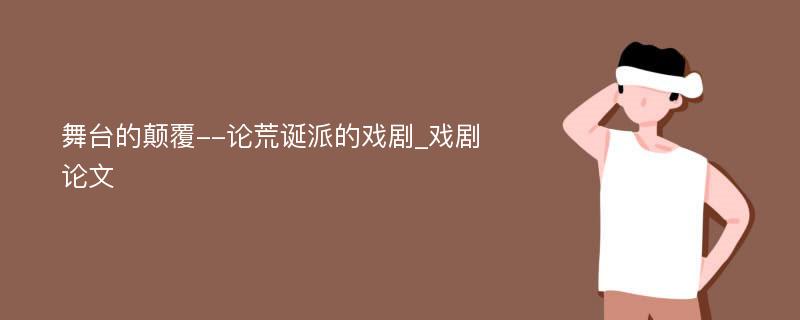
舞台的倾覆——论“荒诞派”戏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荒诞派论文,戏剧论文,舞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古希腊一直到20世纪初期在西方戏剧舞台上不知演过多少让世代观众魂牵梦绕、莫能忘怀的悲欢离合的故事,舞台上也曾出现过灿若群星的戏剧天才,但是,舞台上虽然出事更迭、英雄辈出、翻江倒海、热闹非凡,舞台自身却一直稳固安然,大抵遵循着亚里斯多德的戏剧理论发展着、完善着,不曾有过大的震动。然而,自本世纪西方荒诞派戏剧崛起后,这一稳固的舞台便开始倾斜,最后几至于被彻底颠覆。
“荒诞”原本是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总体特征之一。但是,作为西方战后最为重要的一种戏剧流派——荒诞派戏剧,同这一总体特征有何联系?又有何区别?为何独有荒诞派戏剧以“荒诞”命名,并获得了广泛而又持久的“轰动效应”呢?探索这一原因不仅使我们很快便捕捉到荒诞派戏剧的主要特征,同时我们对荒诞派戏剧难以逾越的困难也一目了然。荒诞派戏剧的独特之处也正是它的困难之处;它要求两种全然不同的认识世界和调和矛盾的方法协调一致,而这两种方法本身又是根本对立的。它一方面通过一种形而上的理性主义认为世界是荒诞的,另一方面又想借助于一种荒诞的形式来证实这一理性主义的结果;它一方面彻底地、疯狂地攻击理性,但它的思维方式却仍然是理性主义的;逻辑说理的胜利将证明生活并非完全没有意义,而理性的失败将会取消荒诞派戏剧自身的价值和意义。总之,荒诞派戏剧所追求的是一种从内容到形式的彻底的荒诞,而非理性的象征、表现却永远无法实现其明确性、清晰和可信性,它更多的只是告诉我们:不仅世界上的一切都是荒诞的,而且表现荒诞也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一结果或许是荒诞派剧作家们所始料不及的,但这抑或不又是一种更高意义上的荒诞?
一、荒诞的本体化
“荒诞”(absurd)一词由拉丁文surdus(耳聋)演变而来,用来指音乐中的不谐调音。后来引申为“不合道理和常规,含有不调和的、不可理喻的、不合逻辑的”意思。固然,人类荒诞的经验与感受源远流长。但是,长期以来,由于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种荒诞,于是,文学对这种经验与感受的反映与表现便只是零星的、局部的、不自觉的,并且,这种荒诞往往被一种强大的外部力量消除殆尽。在古希腊,荒诞由命运或宙斯得以解释;中世纪它便被上帝玩弄于股掌之间;文艺复兴以后,它又在理性光辉照耀下,悄然冰释;在易卜生那里,荒诞就等于社会“问题”。只有到了现代,在尼采宣布上帝已死之后,人们才开始认识到、体味到这种荒诞。存在主义哲学被称为荒诞哲学。萨特说,荒诞就在于偶然性。加缪说得很具体:“一个哪怕可以用极不象样的理由解释的世界也是人们感到熟悉的世界。然而,一旦世界失去了幻想与光明,人就会觉得自己是陌路人。他就成为无所依托的流放者,因为他被剥夺了对失去的家乡的记忆,而且失去了对未来世界的希望。这种人与生活之间的距离,演员和舞台之间的分离,真正构成荒诞感。”①但是,存在主义的意义并不只在于发现了人生状态的荒诞,更主要的是因为他们试图用理性的最后一线光辉慑住荒诞,并且超越荒诞。他们依靠高度清晰、逻辑严谨的说理以及丰富多彩的、生动活泼的语言含蓄地向人们宣告了一种公认的信念:合乎逻辑的言论能提供正确的答案,语言的剖析可以揭示出基本的概念。存在主义者在揭示出荒诞之后又将它扬弃,以恢复理性的权威。尽管前途未必光明,但是存在主义者从来就不放弃努力和追求。这正象西西弗的苦役一样,虽然石头是注定要从山上滚下来,但他仍然一步一步将石头推上山去。此后,荒诞派戏剧作家又向荒诞跨了一大步。这时,存在主义那点理性的微光也被荒诞派全然遮蔽。人类与生俱来就处在荒诞中,而且还将永远处在荒诞中,在劫难逃。尤奈斯库说:“不是任何社会制度使我感到荒诞,而是人本身。”“任何社会制度也不能把我们从生的痛苦和死的恐惧中拯救出来。”②贝克特在《论普鲁斯特》一文中指出:“呼吸是习惯,生活是习惯,或者说,生活是一连串的习惯,”忙碌而无意义,最终走向死亡。③生活是荒诞,生命也是荒诞,语言是荒诞,一切都是荒诞。尤奈斯库曾说:“他之所以喜欢写剧本,就因为他讨厌戏剧。”④他的戏剧创作的“出发点”就是“语言支离破碎,面目全非,文字落地如石块或如死尸。”⑤让·日奈进一步将荒诞推向极端,他在《女仆》一剧中对语言的解构,不仅彻底颠覆了一切由语言和文字记载的事物,一切人类赖以认识自己、说明自己的文明,而且,连同语言自身也被还原为幻像、虚构和欺骗。在这出戏中,语言不再是透明的、清晰的、合乎逻辑的,而是模糊的、混乱的、矛盾的。它表意不清,既欺骗了观众,又欺骗了语言的使用者,并且,最终将语言的主人推向死亡的绝境。这样,荒诞派戏剧在将一切都推向荒诞后,它自己也落入了自己苦心设计的陷井。而在这无时无处不有的荒诞面前,人们只好放弃任何形式的努力与追求,束手待毙。于是,荒诞成了一种普遍意义的经验,被赋予了一种本体论的涵义。
然而,真正使我们感到荒诞的是荒诞派戏剧的这一结论,又是剧作家们长期理性思索的结果,虽然他们认为理性本身也是一种荒诞。这究竟是他们的失败呢,抑或是他们的成功?这正如尤奈斯库在他的名剧《秃头歌女》中借剧中的女佣玛丽朗诵的一首诗:
火
灰土五光又十色哟
丛林中闪闪又烁烁
石头一块着了火
城堡跟着就着火
树林着了火
男人着了火
女人着了火
鸟儿着了火
鱼儿也着火
水着火来
天着火
灰也着了火
火着火
通通着了火
着火又着火。
诗是荒诞的,正如其戏剧一样,但是,在这“着火又着火”的荒诞中,不也有着对现代西方人的生存状态极为形象的真实的比况吗?
荒诞派戏剧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在巴黎戏剧舞台上的一种新的戏剧流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们的观念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它意识到历代那些实在的事物和不可动摇的基本概念已被一扫而光;经过检验,它们被视为虚无;它们被贬得一钱不值,甚至被看成是童稚的幻想。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宗教信仰的衰退一直没有被人觉察,因为它在暗中被进步、国家主义和名目众多的极权主义谬论的宗教信仰取代了。所有这一切都被战争所毁灭。”⑥因此,尤奈斯库说:“在这样一个现在看起来是幻觉和虚假的世界里,一切历史存在的事实使我们惊讶,那里,一切人类的行为都表明荒谬,一切历史都表明绝对无用,一切现实和语言都似乎失去了彼此之间的联系,解体了,崩溃了。世界使人感到沉重,宇宙在压榨着我。一道帷幕,或者说一道并不存在的墙矗立在我和世界之间;物质填满各个角落,充塞所有的空间,世界变成了令人窒息的土牢。”⑦另一位荒诞派戏剧大师贝克特,是位创作十分严谨而又十分孤独的作家,他为了躲避世人的纷扰和荒谬,长年过着隐士般的生活。1969年,若不是担心成为继萨特之后第二个拒绝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他会拒绝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因为比较而言,拒绝领奖更容易使他成为世界注目的中心。因此,对于这样一位作家,我们便只好借助他的作品来分析他对世界和人生的看法了。他的“作品发自近乎绝灭的心情,似已标举了全人类的不幸。”⑧而他的“等待戈多”被誉为“触礁的世界中心灵疏离的最佳写照。”⑨
这种本体的荒诞,表现在剧本中,譬如尤奈斯库的《椅子》。该剧写一对年过90的老人坚信已经从上帝那里获得了真理,老头儿要把这个信息传达给人类。但是,在听众到齐之后,他却先投海自尽了。而把传达信息的重任委托一位天才的演说家。待演说家登台后,人们竟发现他既聋且哑。他决定开始演说了,但竭尽全力也只能是咳嗽、叹息,以及发出一阵和哑巴一样的喉音:“嘿,姆,姆,姆,姆。居,咕,呼,呼。嚯,嚯,居咕,勾。”接着,他又在黑板上写下,“神训:嗯嗯啊啊 嗯嗯姆 嗯呜嗯呜嗯 呜弗”。最后他又开口解释他在黑板上揭示的真理,“姆姆,姆姆,咯咯咕。姆姆,姆姆,姆姆。”这里,尤奈斯库所要表明的思想非常明确:真理是荒谬的,或世上原本就不存在什么真理,一切都是荒诞。然而,当尤奈斯库将这一荒诞理论一步步推向绝对时,他将自身也否定了。既然一切均是荒诞,最好是保持沉默,但是沉默仍然是荒诞。
二、悲剧的喜剧化
荒诞派剧作家所表现的主题及思想大体都属于悲剧的范畴,但他们从来不用悲剧的形式来完成内容与形式的和谐与统一,而总是采取一种戏谑虚无的态度将这一切喜剧化。
有些学者认为,荒诞派戏剧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悲剧与喜剧的巧妙融合:“荒诞派戏剧,实际上是萨提洛斯剧的发展。荒诞派剧作家一直把悲喜剧的融合作为自己的艺术追求。”⑩指出这一点是不错的,但我认为又是不够的。因为追求悲喜剧的融合并不单单只是荒诞派戏剧的特征。在古希腊,除了正统的悲剧和喜剧之外,还有一种摹拟剧,它以现实生活和风俗习惯为题材,其中既有喜剧意味,又有悲剧气氛。这种新型戏剧更加贴近现实,贴近生活(萨提洛斯剧是一种在演出悲剧后演的笑剧,恐怕与悲剧无缘)。以后,以莎士比亚为代表的戏剧创作进一步突破了悲剧与喜剧的藩篱,悲剧与喜剧互相渗透、互相融合,以致莫能分辨了,譬如《罗密欧与朱丽叶》。启蒙主义时期,杰出的理论家和戏剧家席勒、莱辛、狄德罗不仅致力于戏剧创作实践,还初步建立了一套新戏剧(市民剧、正剧、悲喜剧)的美学理论。循此发展,至易卜生和肖伯纳的社会问题剧,这种悲喜剧的界限就越发不易觉察了。这里,生活本身就是悲喜并存、悲中有喜,喜中有悲。因此,戏剧作为现实生活的反映,也就决无悲剧和喜剧之分了。这显然是植根于现实主义美学基础的。
荒诞派戏剧不是现实主义戏剧。它的哲学基础是存在主义哲学和非理性主义,文化传统就是反传统。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用现实主义的美学原理和传统的戏剧理论来衡量荒诞派戏剧。荒诞派剧作家关注的是人类生存状态这一严峻的问题,他们试图“将现代人的困乏转变成亢奋”,(11)其作品深处往往迷漫着浓郁的悲凉之雾。但是表现在舞台上,却是一种喜剧的形式,有时甚至是闹剧的形式。贝克特笔下的一个人物就说,“再没有什么比不幸更可笑了。”荒诞派剧作家在经历了一幕幕人间悲剧后,终于明白了尼采的这段绝妙的沉思:“何以人是唯一能笑的动物,恐怕这个道理要算我顶明白了。因为只有在他受苦受得如此恶毒时,才无可奈何地发明了笑。”(12)这便是荒诞派戏剧的主要特征,它决非一般意义的悲喜剧融合所能概括。
贝克特的戏剧旨在揭示生活的毫无意义和存在的极为荒诞。他笔下的主人公往往都生活在死亡与疯狂的阴影中,受尽了痛苦与折磨,却得不到丝毫的报偿。而这一悲剧主题便是通过荒诞变形的喜剧性情节与语言表现出来的。在他的名剧《等待戈多》中,作者表现的是这样一个悲剧性主题:人生活在盲目的希望中。人们在遥遥无期地等待着一个模糊的万难实现的希望。然而,人们并不因为屡次失望而不希望,反倒是失望愈多,希望愈烈,最终在等待中耗尽了生命。希望等于无望,绝望中又不放弃等待,时间也由此而变得毫无意义。这一思想在剧中是通过这样的剧情表现出来:黄昏,在一条乡间小路上,两个流浪汉在等待戈多。一天过去了,戈多没有来;第二天他们又来等戈多,戈多仍未出现;第三天他们还将等待……而通过剧中人物幸运儿的演讲展现在观众面前的,却是这样一个世界:
在平原在山地在海洋在烈火沸腾的河里天空是一样的随后是大地换句话说天空随后是大地在一片寒冷中哎哟哟在我们的主诞生六百年左右天空大地海洋大地石头的住所在汪洋中一片寒冷中在海上在陆地在空中我接下去讲不知什么原因尽管有网球事实俱在但时间将会揭示我接下去讲哎哟……网球……石头……那么平静……丘那德…未完成的……(13)
贝克特将人生的这种荒诞的处境在他的小说《不可名状者》中说得更加明白无误:
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是。走进世界而又并未出生,住在那里而又不是活着,毫无死去的希望……我们,所有我们漫长而又徒劳的终生,过去最终总是那种处于生活之外的人……那种对自己一无所知而又沉默的人,那种对他自己的沉默一无所知而沉默的人,这种人不可能去尝试什么,但又不会放弃尝试。(14)
在尤奈斯库看来,“喜剧的东西就是悲剧的东西,而人的悲剧都是带有嘲弄性的。对于近代批评思想来说,没有什么东西是能够完全加以认真对待的,也没有什么东西是能够完全加以轻松对待的。”(15)在这里,悲剧和喜剧化而为一了。悲剧便是喜剧,并用喜剧的眼光看待一切。他“试图以喜剧手法处理既荒唐又痛苦的人生戏剧”。(16)这较之将悲剧喜剧化又向荒诞迈了一大步。他的名剧《秃头歌女》,就因为一个演员念错了台词而得名。剧本主要写一对共同生活了多年的夫妻竟素昧平生,互不认识;一对恋人互相辨认良久,才知道对方是谁。剧中人物“一个接一个地说出的基本而又清楚的真理变成了胡言乱语。”(17)而剧本表现的却是这样一个严肃的主题:世界是一场漫无边际的恶梦;人生充满了琐屑、乏味、平庸和空虚,没有生气,毫无理解,也根绝了希望。而人们面对这一切却习以为常,熟视无睹。这便是真正的悲剧!然而,这种悲剧却通过这样的台词来表现:
马丁夫人:我能买把小折刀给我兄弟,而您没法把爱尔兰买下来给您祖父。
史密斯先生:人固然用脚走路,可用电,用煤取暖。
马丁先生:今天卖条牛,明天就有个蛋。
史密斯夫人:日子无聊就望大街。(18)
这种对话真令观众莫名其妙,无所适从。剧本作者抽掉了语言的意义,让人物不断重复罗嗦的就是这样一些颠三倒四、支离破碎、文不对题、词不达意、自相矛盾、胡言乱语的梦呓和废话,而观众在笑过之后,体味到语言背后的空虚与荒诞,又不得不黯然深思。这便是喜剧效果所包蕴的悲剧内容。
三、舞台的象征化
埃斯林说:“假如说:一部好戏应该具备构思巧妙的情节,这类戏则根本谈不上情节或结构;假如说,衡量一部好戏凭的是精确的人物刻划和动机,这类戏则常常缺乏能使人辩别的角色,奉献给观众的几乎是运动机械的木偶;假如说,一部好戏要具备清晰完整的主题,在剧中巧妙地展开并完善地结束,这类戏剧既没有头也没有尾;假如说,一部好戏要作为一面镜子照出人的本性,要通过精确的素描去刻划时代的习俗或怪癖,这类戏则往往使人感到是幻想与梦魇的反射;假如说,一部好戏靠的是机智的应答和犀利的对话,这类戏则往往只有语无伦次的梦呓。”(19)荒诞派戏剧舞台上没有了情节,没有了人物,没有了主题,甚至连正常的语言也没有了。它彻底掀翻了传统戏剧的舞台,那么它还剩下些什么呢?这主要便是象征的舞台。我们知道,传统的现实主义戏剧的灯光、布景、效果、服装、道具等等都服从于现实主义艺术的总的原则,旨在创造一种真实的、典型的环境和气氛。而荒诞派戏剧反对的就是这种真实的、典型的环境和气氛。他们认为,世界的本体就是荒诞,因此,作为戏剧舞台同样也是荒诞的。艺术家的任务就是要通过直喻把握世界。尤奈斯库说;“我试图通过物体把我的人物的局促不安加以外化,让舞台道具说话,把行动变成视觉形象……我就是这样试图伸延戏剧的语言。”(20)这样,荒诞派剧作家便十分重视布景、灯光、音响、道具、服装的直观象征作用,他们将无生命的道具赋予了生命,让观众在演员在台词之外,还能听到阵阵惊雷。为此,英国著名理论家马·埃斯林说:“我们只能用荒诞派戏剧的准则来衡量这些戏。”(21)
在尤奈斯库的《椅子》一剧中,一对年逾90的老人为了迎接宾客的到来,在舞台上摆满了椅子,最后,这对老夫妇连立足之地也失去了,只好从窗口投海自杀。这满台的椅子令人震惊地表明了剧本的主题:椅子。尤奈斯库说,“这出戏的主题不是老人的信息,不是人生的挫折,不是两个老人的道德混乱,而是椅子本身,也就是说,缺少了人,缺少了上帝,缺少了物质,是说世界的非现实性,形而上的空洞无物。戏的主题是虚无。”(着重号是本文作者所加)(22)在强大的物质洪流的挤压下,人已经失却了自己应有的位置,连上帝也不可能占有一席之地,世界最终是一片虚无。这样,椅子就不再是一种简单的道具,它成了剧中的主角,成了世界的象征。
在贝克特的名剧《等待戈多》中,背景是一片虚无的荒郊野岭,那里只有一颗枯树,象个十字架,又象个绞刑架。到了第二幕,这棵枯树竟然长出了四、五片叶子。这真是荒诞概念的绝好的象征。另外,剧本为了说明生活的卑屑、乏味、无聊、空虚这一主题,便让主人公反复地穿靴戴帽。这样,靴子和帽子也成了生活的象征。
荒诞派戏剧的另一位大师让·日奈认为,戏剧就是象征性的弥撒祭。他的代表作《女仆》写的是两位女仆每逢女主人外出,就轮流扮演主仆游戏,借以发泄对主人的强烈仇恨。最后,饰主人的女仆假戏真做,竟饮鸩自尽,代主人服毒。这里,剧中人物的设置原本就是一种象征,而人物之间互相替代的游戏,仍然是一种象征,至于剧中的道具,譬如路易十五式的家具、鲜花、闹钟、手套、大衣等等无不是某种象征。
总之,观众在荒诞派戏剧舞台上看到的无不是象征。满台的犀牛——象征着法西斯可怕的传染病;遍地的鸡蛋——象征物质不断的生产对人的压迫;禁闭在垃圾桶里的人,半截子入土的人,脱离肉体的一张巨大的嘴——象征着现代人既不能认识世界也不能行动,只是依靠一张嘴无限地重复着空话和谎言;无限增多的家具——是人被物化的象征;不断膨胀的尸体——象征着这个世界没有生命,只有死亡在扩展,在吞噬着一切……荒诞派戏剧并不反映具体的事件、人的具体的经历和命运,而旨在揭示人类的生存状态。因此,舞台上就失去了具体真实的布景,代替它的是建立起一个和现实平行的隐喻性图景。而这种象征性的舞台便延伸了戏剧语言,扩大戏剧效果,给观众以十分强烈的震动和深刻的印象。所以,马·埃斯林说:“最真实地代表了我们自己的时代的贡献的,看来还是荒诞派戏剧所反映的观念。”(23)
以上所论及的荒诞派戏剧的主要特征,第一点是核心,是内容;第二点是关键,是中介;第三点是补充,是形式。当然,它们又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荒诞的本体化不仅没有彻底否定荒诞派戏剧,反倒构成了荒诞派戏剧的意义与价值,这是其荒诞的合理性;荒诞派宣告一切理解和表现都是不可能的,而这又引起世人普遍的关注与共鸣,以致贝克特196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70年尤奈斯库进了法兰西学院,这便是不可理解的理解;荒诞派戏剧从反传统开始发展到成为传统的一部分,它所认定的“一切均无意义”又引起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和效应,这即是无意义的意义。荒诞派戏剧倾覆了传统戏剧的舞台,而在这倒悬的舞台上荒诞派戏剧家们却仍有其恣意驰骋与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
前一个时期,我国也出现过一些近似荒诞派戏剧的创作,例如高行健的《车站》,魏明伦的荒诞川剧《潘金莲》等等。《车站》象贝克特的《等待戈多》一样的确有许多荒诞之处。一帮人在城郊一公共汽车站上等车二十年,可就是没有一辆车靠站停下,他们那一点小小的心愿就是无法得到满足。老大爷要去赶一局棋,姑娘要去同男朋友约会,愣小伙想吃杯酸奶,母亲想去给城里的丈夫、女儿做顿晚饭,戴眼镜的要去考大学……,但是,我们与其说这部戏的主题是“等待”,不如说它是宣告“等待是毫无意义的”。这便是《车站》与《等待戈多》的最大区别。《等待戈多》里只有等待没有行动,剧中的等待实际上等于绝望,因为这是无望的等待;《车站》中的等待最后却导致了行动,而众人还在等待时早有“沉默的人”大踏步的先行一步了。“车站”只是人生中的一站,人们虽然可能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错过这一站,但这并不决定他的人生意义和价值;而“戈多”本身则可能便是生命的目的或意义,缺少了“戈多”生活将毫无意义,但“戈多”却永远也不会来临。当有人问贝克特,戈多是指什么人时,他说:“我要知道,早他妈的说出来了。”高行健却明确地提出,他的“车站”有种象征意味:“表示的也许是一个十字路口,也许是人生道路上的一个交叉点,或是各个人物生命途中的一站。”因此,我们说《等待戈多》是拒绝理性之后的荒诞,而《车站》则是在理性基础上的荒诞。
魏明伦的《潘金莲》虽然被称作荒诞戏,但荒诞的也只是形式与方法,其内容却有着浓烈的理性思辩色彩。剧作者将施耐庵、贾宝玉、安娜·卡列尼娜、武则天、七品芝麻官、红娘、吕莎莎、人民法庭庭长、现代阿飞等古今中外人物和其他艺术形式中的形象云集在同一舞台,对潘金莲的命运遭遇进行评说,这看上去好似荒诞无稽,其实却是作者对妇女问题进行深刻的反思的结果。剧本结尾处女庭长的台词颇能说明问题。“一部沉沦史——千年封建根。想救难挽救,同情不容情。覆辙不可蹈,野史教训深!”
通过对以上两剧的分析,我认为,中国不可能有真正意义的荒诞派戏剧,因为我国不存在本体论的荒诞,其荒诞都只是局部的、暂时的和偶然的。我们的荒诞是理性中的荒诞,而不是荒诞中的理性。我们虽然要加强理性的形象,但我们并未走向理性的贫困;同样,我们在提倡创新与开拓的同时,并未忘却继承和发扬传统。因此,我们借鉴荒诞派戏剧的表现形式及舞台手段是必要的,是有益的,但全盘照搬荒诞派戏剧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意义的。
注释:
①加缪《西西弗的神话》,杜小真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6页。
②(20)(22)朱虹《荒诞派戏剧述评》。《英美文学散论》,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82页、190页、163页。
③贝克特《论普鲁斯特》,《文艺学和新历史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86页。
④⑥(14)(15)(21)(23)《现代主义文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11、674、648、623、673、674页。
⑤⑦(16)《外国现代剧作家论剧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69、169、303页。
⑧⑨(11)《诺贝尔文学奖全集》第42卷,陈映真主编,台远景出版事业公司1981年版,第5、162、42页。
⑩杨国华《现代派文学概说》,华东师大出版社1989年版,第211页。
(12)转引自威尔·杜兰《西方哲学史话》,杨荫鸿、杨荫谓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447页。
(13)(18)《荒诞派戏剧选》,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4、222页。
(17)尤内斯库《秃头歌女——语言的悲剧》,《外国文学报导》1981年第5期,第65页。
(19)《现代西方文论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356页。
标签:戏剧论文; 荒诞派论文; 贝克特论文; 世界语言论文; 荒诞论文; 等待戈多论文; 车站论文; 象征手法论文; 喜剧片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