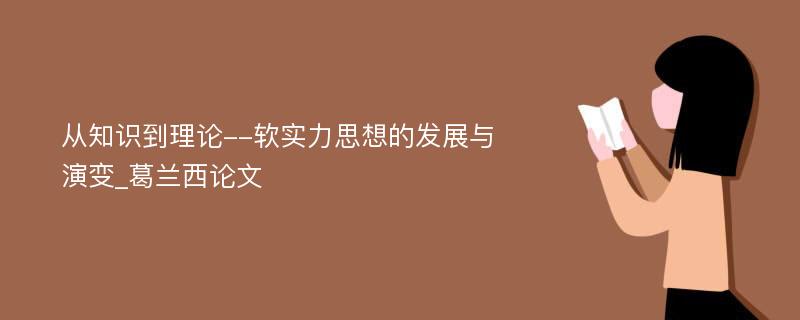
从智识到理论化——软权力思想的发展演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权力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8)2-0088-07
“软权力”(soft power)①作为一个明确的概念,是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美国原助理国防部长小约瑟夫·S.奈(Joseph S.Nye,Jr.)在其1990年出版的《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一书中首次明确提出的,并在20世纪末得以逐渐发展和丰富。就国际关系学界而言,“软权力”概念的提出虽然丰富了权力论的内涵,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新的生长点,但作为一个新出现的国际关系分支理论,仍显单薄,甚至可以说尚不成熟。所以,尽管软权力研究已经成为学术界的一种时尚,但如同国际关系研究必须基于历史理解一样,任何一种“现代政治思想和国际关系思想的肇始同样出自历史考察和历史理解”②。因此,对软权力的考察并不能仅仅关注其最近十几年的演进和发展,而应从国际关系史、尤其是理论史的演进中去挖掘。而就国际关系理论史来说,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鼻祖修昔底德在其传世巨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借助于一场场精彩的演说和辩论,已经隐约提到了“观念”的重要性以及雅典作为“全希腊的学校”③101所拥有的政体、民族精神等软权力方面的重要优势。相比于2000多年前尚处于“智识”(intellectual)阶段的软权力思想而言,19世纪末20世纪初意大利思想家安东尼奥: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思想已经论及了软权力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文化。及至现代,就连古典现实主义大师汉斯·摩根索也认为,“文化帝国主义的东西,是最巧妙”的以“征服和控制人心”为目的的权力手段,④74并且“在影响国家权力的具有定性的三项人的因素中,民族性格和国民士气是突出的因素”。毫无疑问,民族性格和国民士气并不属于一国传统意义上的权力范畴。⑤146-158不仅如此,软权力思想的痕迹在国际机制理论、国际社会学派的著述以及建构主义理论中也有比较明显的体现和折射。到了冷战濒临结束的1990年,在前人的基础上,小约瑟夫·奈将以上这些“权力第二张面孔”(the second face of power)或“权力的第二层面”结合起来,并将之正式命名为“软权力”。所以,在软权力思想的发展演进过程中,至少有三个具有典型意义的思想理论阶梯,即修昔底德的启示、葛兰西主义的思想传统和小约瑟夫奈的理论化贡献。
观念的力量——修昔底德的启示
在国际关系理论界,尽管人们公认修昔底德是现实主义的鼻祖,但在其经典名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修昔底德在展示雅典和斯巴达的权势政治的同时,也给人们清晰地揭示了权力要素的另一个重要层面——观念的力量,并通过一场场著名的演说或辩论来说明这一点。
在古希腊,及至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雅典已由阿提卡半岛的小邦邦一跃成为囊括爱琴海的“泱泱大国”,于是雅典城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东地中海地区政治、经济、海陆交通和文化中心,成了“希腊的学校”③译序。对此,雅典最著名的领袖伯里克利认为,“我们之所以日渐壮大,是在一种雅典独有的政体——民主制下实现的”,“我们的宪法没有搬照任何毗邻城邦的法律,相反的,我们的宪法却成为其他城邦模仿的范例。”他进而认为,“我们所依赖的主要不是制度和政策,而是我们公民的民族精神”。雅典的势力“就是靠这些品质获得的”③98-101。
然而,雅典霸权的建立和护持不仅仅有赖于伯里克利所炫耀的“品质”⑤,更在于雅典提出的国际关系信条,即“米罗斯人的辩论”中雅典所鼓吹的“强者做其权力所能,弱者受其所不得不受”③313,这一信条尽管受到了米罗斯人道德至上主义的质疑,但显然在修昔底德的笔下,它实际上是当时希腊城邦的“共有观念”。早在第一次拉栖代梦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大会上,雅典代表就表示过:“……我们也不是首创这个先例的。因为弱者应当臣服于强者,这一直就是一条普遍的法则。同时,我们也相信我们自己是无愧于这种地位的,而且迄今为止你们也是这样认为的。”③40在雅典人与弥罗斯人的辩论中,面对弥罗斯人“以正义之师抗击不义之师”的说辞,雅典代表回应道:“……自然界的必然法则就是将其统治扩展到任何可能的地方。这个法则并不是我们的首创,也不是我们首先将它付诸行动;我们发现它由来已久,并将与世长存。我们现在的所作所为只是运用了这个法则,你们以及其他任何人如果有了我们现在的实力,也会做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③316
正是借助于这些精彩的演说词,我们可以从中明了,“任何国家只要有可能都会进行扩张”的原则,被雅典提升到了“自然界的普遍和必要的规律”的地位。尽管雅典这一“强权即公理”的说法多少显得有些“蛮横”,但事实上,正如雅典人所说的,当时的希腊城邦对于雅典的这一提法并没有提出底气十足的挑战,就连当时雅典在希腊最大的竞争对手斯巴达也相信:“……弱者,放到天平上,指针只会朝一个方向转动。”③315
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说的,“雅典人对弥罗斯人的回答彰显了权力的主观性,即别人在观念上认为你是强大的,你就是强大的。反之亦然。”⑥所以,当这一信条上升为当时希腊城邦制国家的“共有观念”后,当然也就成为雅典帝国的“软权力”之一,于是雅典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这一观念的最大受益者。
随着时代的发展,今天的国际政治体系已经不再允许这类“强权即公理”的信条上升为人类社会的共有观念。但是,从修昔底德的启示中,我们窥见了观念的重要性,而修昔底德的见解也在国际关系理论流派中得到了很好的传承。可以说,在经典的国际关系理论中,观念一直是国际关系理论家们关注的焦点之一。
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奠基者爱德华·卡尔就指出,权力有三种形式,第一种是军事实力,第二种是经济实力,第三种是支配舆论的力量。⑦120-130而“支配舆论的力量”是观念范畴的事情,是维护或是改变人们观念和意愿的能力。卡尔明确指出:“政治学领域的研究是与人的行为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不存在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客观事实”,“如果研究人员在思维中已经存在改变事实的愿望,并通过他的研究使其他人也接受这种愿望,那么,一旦接受的人达到足够的数目,事实就会得到改变。”⑦3尽管结构现实主义将观念的作用“抽象”到了微乎其微的地步,⑧但在古典现实主义者看来,观念因素在国际政治中却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摩根索便认为,“对于国际道德的讨论,必须防止两种极端观点,一是过高地估计道德对于国际政治的影响,二是低估这种影响,认为政治家和外交家采取行动的时候,除了物质性权力之外不会考虑其他因素”④248。在这里,摩根索清晰地指出了观念的重要性。
新自由主义同样重视观念的作用。在新自由主义者看来:“观念常常是政府政策的重要决定性因素……观念以下述方式影响政策:观念所体现出的原则化和因果性的信念为行为者提供了路线图,使其对目标或目的——手段关系更加明确。”⑨
而将观念在国际关系中运用得最为纯粹的,当属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建构主义认同新自由主义关于观念的看法,即在一个行为体身份已经确定的情况下,观念起到引导行为体选择何种政策、采取何种行动的作用。但是,建构主义同时认为,观念不仅是指导行动的路线图,它还具有建构功能,可以建构国际关系行为体的身份,从而确定行为体自身的利益。在建构主义者看来,观念才是国际关系中的首要因素。而“正因为物质性原因是由观念建构的,所以,如果把观念视为与其他原因并列的变量,就不能充分理解观念的作用。⑩。需要注意的是,建构主义强调的观念是共有观念,也就是建构主义学者所说的“文化”。当一种观念成为共有观念的时候,它的力量就是巨大的。(11)
文化霸权——葛兰西主义的思想传统
如果说修昔底德对雅典“软权力”的描述尚处于“智识”阶段,那么葛兰西的文化霸权(Cultural Hegemony)思想则看到了文化——这一软权力的重要因素——的独特作用。
学术界翻译的葛兰西著作并未包含对文化霸权的精确定义,(12)但文化霸权被广泛地认为是“对于主要统治集团强加于社会生活的总方向,人民大众所给予的‘自发的’首肯;这种首肯是由统治阶级因其在生产界的地位和职能而享有的威望(以及由此带来的信任)‘历史地’(historically)所引发的。”(13)
葛兰西是在对教条式机械决定论的反驳中、在其革命实践以及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阐明文化霸权理论的。(14)他认为,国家上层建筑可以分为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政治社会由议会、法庭、警察和选举机关等机构组成,起到有限领导权的作用。市民社会则指民间社会组织的集合体。政治社会对市民社会的意识形态上的统治,是在市民社会“同意”的基础上,国家政权机关通过制订与传播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从而对市民社会进行“精神和道德的领导”,构筑起统治阶级对从属阶级的领导权。
由此,葛兰西认为知识分子和领导集团在文化霸权中起着重要作用,他们是整个社会结构和上层建筑的中介。一方面,他们在市民社会中充任文化霸权的主要行使者,从而在普遍民众自觉自愿的基础上传播统治阶级的世界观,维护统治集团对全社会的统治;另一方面,他们又在政治社会中强制行使直接的文化统治职能,并通过合法政府对对立或消极服从集团给予合法制裁。
在此基础上,葛兰西借用西方军事术语,提出了政治上的“运动战”和“阵地战”。前者是指对国家机器的直接进攻,后者则指在市民社会里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进行长期的进攻。葛兰西认为,与十月革命时俄国的情形不同的是,在当时的西方发达国家,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已占据了市民社会的坚固堡垒,公民中的大多数已经被统治阶级的世界观、生活方式、愿望、道德、习惯所高度内在化。这时,再去用“运动战”方式直接攻击资本主义国家,结果只能是摧毁了资本主义防御线的“外表”,最后还是将以失败告终。这也是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如德国、匈牙利、奥地利无产阶级革命昙花一现的原因。因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必须转入“阵地战”,针对的应不仅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暴力功能,而且有它的同意基础,即市民社会的文化霸权。(15)葛兰西认为,对西方发达国家来说,其政权的维系“表现在两种形式中——在‘统治’的形式中和‘精神和道德领导’的形式中。”(16)
葛兰西看到,统治阶级除了依赖暴力来维持社会的政治经济秩序之外,还必须具有意识形态中的领导权,以使被统治者在心理—观念上顺从和满足于现状。显然,政权越稳固,它得到的同意就越多。所以,无产阶级要在夺取国家政权以前,在市民社会里发动一场“精神革命”。而当无产阶级在市民社会中建立起文化霸权之后,资产阶级国家政权自然就会崩溃,无产阶级国家也最终会建立起来。(17)
葛兰西之所以要着重强调文化上的领导权,是想强调这样一种重要思想:经济斗争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具有相对局限性,而意识形态有时却是具有物质、政治力量的。意识形态并非只是一个脱离日常生活的抽象的思想领域,作为一种媒介物,它通过不同的社会形式可以体现为一种道德和哲学的领导权力,并转化为像物质力量那样大的能量(18)。
20世纪晚期,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思想在西欧、北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亦称葛兰西学派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得到了回应和发展,他们的有关学说被学术界称为“新葛兰西主义”。(19)新葛兰西主义复杂的理论体系结构是以霸权这个基本概念为基础而构建的。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罗伯特·考克斯认为,霸权是一种基于同意基础上的统治,因为“霸权还意味着支配性大国创造出以观念意识的广泛共识为基础的统治秩序,它以确保主导国家的主导阶级的至上地位,同时让其他弱国满意的原则和措施来发挥领导作用”(20),“霸权体现着物质力量、观念和制度的和谐与适应,它形成思想并约束行为”(21)。在考克斯看来,“当主导国家和主导社会阶级通过捍卫众多从属国及从属阶级接受或默许的普遍原则来维护自身的地位时,全球霸权就存在了”(22)。由此可见,新葛兰西主义继承了葛兰西对观念、文化、制度以及意识形态等“同意”基础的强调,虽然对观念的作用有所夸大,但总的来说,对葛兰西主义仍有一定的发展。
在新葛兰西主义更早以前,古典现实主义大师汉斯·摩根索提出了一个与文化霸权相似的概念——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 Imperialism)(23)。摩根索认为:“我们姑且称作文化帝国主义的,是最微妙的,而且,如果它单凭自己的力量而能获得成功的话,则也是最成功的帝国主义政策。它的目的不在于攻占他国的领土,或控制其经济生活,而在于征服和控制人的头脑,作为改变两国权力关系的工具。”④4摩根索从历史的视角认为,自古以来,“征服者不仅会以经济和文化渗透为军事征服做准备,也会把他的帝国主要建立在控制被征服者的生计和统治其心灵的基础上,而不是只依赖武力。”④76他认为亚历山大、拿破仑和希特勒都没有完成对人心的征服,所以尽管他们已经征服了其他方面,仍然不能避免失败的命运。相比之下,罗马则较为成功地做到了这点。
由此可见,不论是新葛兰西主义,还是文化帝国主义,其基本思想都来源于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思想。不可否认,它们对于“文化”(意识形态)因素的强调是“软权力”思想演进和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标志。正是在这些思想的引导下,“文化”这一软权力的关键因素开始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以至于“对国际关系的定义越来越从文化角度出发”。(24)
国际关系中的软权力——小约瑟夫·奈的理论化贡献
“软权力”这一提法之所以在今天如此风靡全球,与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美国原助理国防部长小约瑟夫·奈的贡献是密不可分的。尽管前人对于软权力思想已有论及,也出现了“权力的第二张面孔”(25)的提法,但“软权力”概念确实是奈的创造物,也正是他非常系统和清晰地表述了软权力的思想,并使之风行世界。(26)
“软权力”概念提出的背景是20世纪80年代末掀起的“美国霸权衰落论”(27)。为了驳斥这一论点,奈在其1990年出版的《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一书中首次提出了“软权力”的概念。他认为美国在当时的世界上不仅拥有经济和军事等“硬权力”优势,而且还具有一些无形的权力资源,包括文化、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他认为控制其他国家意志的能力与这些无形的权力资源有关,这种能力便是“软权力”。软权力是通过吸引而非强迫得到想要的结果的能力,这种吸引力包括思想、文化、通过影响其他国家偏爱的标准或制度设定日程的能力。如果一个国家能使它的权力在其他国家的眼中是合法的,并建立激励其他国家以一致的方式界定它们的利益的国际机制,它可以不必花费过多昂贵的传统经济或军事资源。(28)软硬权力都是有效的,但在信息时代,软权力变得比以前更加引人注目。(29)
虽然奈对于软权力的定义一直不断变化,但最完整、最系统的定义无疑是:“软权力是一个国家的文化与意识形态所产生的吸引力,它通过吸引力而非强制力影响他人的行为,并获得理想的结果,比如能够让他人信服地跟随你、遵循你所制定的行为标准或制度,并按照你的设想行事。软权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信息的说服力。如果一个国家可以使它的立场在其他人的眼里具有吸引力,并且鼓励其他国家依照寻求共存的方式加强界定它们利益的国际制度,那么它无需扩展那些传统的经济和军事实力。”(30)“9·11”事件以后,奈又有针对性地出版了两本著作——《美国霸权的悖论——为什么美国不能独断专行》和《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集中分析了软权力问题以及美国对软权力的运用。
奈认为,随着国际政治性质的变化,那种“对大国的检验……就是对战争实力的检验”(31)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权力的定义不再强调昔日及其突出的军事力量和征服。随着现代技术的进步,落后国家在军事和经济方面的能力得到了加强,而大国所拥有的令人敬畏的传统权力资源却随着世界政治问题性质的变化而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削弱,传统的权力工具已经不足以应对世界政治的新困境,从而使得“任何大国控制其环境、实现其预想目标的能力,常常不像传统硬权力指标所预示的那样强大”(32)75。尤其是信息革命最终改变了世界政治的进程,使得“在软、硬权力的关系中,软权力比过去更为重要”(33)。对现代国家而言,权力正从“拥有雄厚的资本”转向“拥有丰富的信息”——即更多“看不见的权力”。
奈认为,软权力来源包括文化(普世性文化)、政治价值观(包括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等)和外交政策(国际战略、制定国际规范、设定国际政治日程和创立国际制度的能力等)。他认为文化是“为社会创造意义的一系列价值观和实践的总和”,当一个国家的文化涵盖普世价值观,其政策亦推行他国认同的价值观和利益时,它就很可能“如愿以偿”。美国霸权的形成和护持正是受益于其普世性的文化。
尽管奈对软权力推崇备至,但他同样认识到了软权力具有自身的局限性。第一,国际政治环境对软权力作用的发挥起到了牵制作用;第二,软权力较之硬权力更有赖于诠释者及接受者的意愿;第三,软权力作为一种吸引力,通常具有扩散漫效应,产生的是一般性的影响,而非某种具体的、易于测量的行为。同时,奈尽管十分重视软权力在当今国际政治领域的作用,但他并没有轻视硬权力或物质性权力的重要性。他一再强调,聪明地运用权力的方式是“将硬、软权力结合起来使用”(34)。因此,软权力思想的提出,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那种过于关注物质性权力的简单化和物质主义思维方式的回击,也是对传统的、同时关注物质与非物质因素的权力思想的回归。(26)
综上所述可见,“软权力”概念虽出现不久,但其所要表达的事物或内容其实早已存在,并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不断得到体现。其中,小约瑟夫·奈的贡献在于正式给了软权力一个“名分”并将之理论化,这样,在历经上千年的发展和演变后,软权力终于从“智识”阶段慢慢向理论方向演进,并对当前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正因为“同化权力(让他人随你所愿)和软权力资源(文化吸引力、意识形态和国际制度)并无全新之处”(32)77,而且“软权力”这一概念所要表达的事物或内容早已存在,所以,其他的国际关系理论流派,如国际机制理论、国际社会理论以及建构主义理论,自然也会对软权力思想多有涉及,或者说,对“软权力思想”从智识到理论化这一过程进行完善和补充,尽管这些理论对于软权力思想的论述在理论指向和视角上明显不同于约瑟夫·奈。可见预想,在国际关系理论谱系中,软权力理论论说还将不断地得到升华和完善,并对治国谋略继续产生深远影响。
收稿日期:2008.03.05
注释:
①“Soft Power”一词在国内学术界被译为“软权力”、“软实力”、“软力量”、“软国力”等等,本文统一取“软权力”。
②时殷弘.关于国际关系的历史理解.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10):20
③[古希腊]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徐松岩,黄贤全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④Hans J.Morgenthau.Politics Among Nations: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6th ed.Beij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05:74
⑤事实上,有学者认为雅典的民主制“臭名昭著”。参见:Jennifer Tolbert Roberts.Athens on Trial:The Antidemocratic Traditional in Western Thought.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4:1; Thomas Hobbes,"On the Life and History of Thucydides",该文1628年11月15日发表于伦敦,为其《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英译本的序言,转引自:惠黎文,时殷弘.雅典为何终告惨败?——关于民主、内争、文化特质和战争效应的辨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3):21
⑥Richard Ned Lebow.The Paranoia of the Powerful:Thucydides on World War III.PS,Winter 1984,17(1):10
⑦[英]爱德华·卡尔.二十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秦亚青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
⑧詹奕嘉.观念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国际政治科学,2006(4):115
⑨[美]朱迪斯·戈尔茨坦,罗伯特·基欧汉主编.观念与外交政策.刘东国,于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3; Daniel Drezner.Values,Interests,and American Grand Strategy.Diplomatic History,June 2005,29(3):429-432;同时,朱迪斯·戈尔茨坦和罗伯特·基欧汉将观念分为三种类型,即:世界观(value)、原则化信念(principle belief)和因果信念(cansal belief),并认为这三种观念对人的行为有着重大的影响,尤其是在不存在唯一可能的政策选择时,观念能够决定人们的最终选择,这就是“观念是路线图”的论点。
⑩[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38
(11)秦亚青.文化与国际社会: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序言部分
(12)T.J.Jackson Lears.The Concept of Cultural Hegemony:Problems and Possibilities.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June 1985,90(3):568
(13)Quentin Hoare,Geoffrey Nowell Smith.ed.and trans.Gramsci,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1971:12;转引自:T.J.Jackson Lears.The Concept of Cultural Hegemony:Problems and Possibilities.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June 1985,90(3):568;亦见:[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姜丽,张跣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7
(14)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思想并非建于空中楼阁之上,其理论形成有多种思想渊源。意大利的知识传统,如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学说、拉布里奥拉的实践哲学、克罗齐的文化—历史哲学理论、卢卡奇的著作都对葛兰西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马列主义的一些理论也与文化霸权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参见:孙晶.文化霸权理论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3-20
(15)于文秀.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与“文化研究”思潮.求实,2002(4):24
(16)[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葆煦译.人民出版社,1983:316;亦参见:[英]吉姆·麦克盖根.文化民粹主义.桂万先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72
(17)孙晶.文化霸权理论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27
(18)孙晶.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及其质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1(1):83
(19)其实新葛兰西主义并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名称,其代表人物之一斯蒂芬·吉尔将其称为“跨国历史唯物主义”,另一代表人物吉斯·冯·佩吉奥称之为“新自由主义”。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和著作有:Stephen Gill,David Law.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Perspectives,Problems and Policies.London:Simons and Shutter,1988; Stephen Gill.American Hegemony and the Trilateral Commiss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Robert W.Cox.Production,Power and World Order:Social Forces in the Making of History.New York,Guildford: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7; Kees van der Pijl.The Making of an Atlantic Ruling Class.London:Verso,1997; Stephen Gill ed.Gramsci,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Cambridge,1993; Enrico Augelli,Craig Murphy,America's Quest for Supremacy and the Third World.London,1988
(20)Robert·Cox.Production,Power and World Order:Social Forces in the Making of History.New York,Guildford: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7:7;转引自:王铁军.新葛兰西主义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欧洲,2000(1):17
(21)Stephen Gill.American Hegemony and Trilateral Commiss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49;转引自:王铁军.新葛兰西主义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欧洲,2000(1):17
(22)王铁军.新葛兰西主义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欧洲,2000(1):17
(23)Hans J.Morgenthau.Politics Among Nations.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6th ed.Beij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05:74;文化帝国主义概念的系统诠释,则是由美国传播学研究巨擎、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名誉教授赫伯特·席勒于1976年的《传播与文化支配》一书中首次完成的。文化帝国主义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现代帝国主义总过程的一部分。“文化帝国主义”作为政府间文化政策的主张,是法国文化部长的雅克·郎于1982年在联合国所作的题为《美国文化帝国主义》演讲中提出来的。
(24)Akira Iriye.Cultural Internationalism and World Order.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7:177-187
(25)这一提法是由20世纪60年代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彼得·巴克莱奇(Peter Bachrach)和摩尔顿·拜拉茨(Morton Baratz)在其1962年发表的文章《权力的两张面孔》(Two Faces of Power)提出来的。参见:Peter Bachrach,Morton Baratz.Two Faces of Power.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Dec.1962,56(4)947-952;有学者认为小约瑟夫·奈的“软权力”概念受他们二人的影响。
(26)张小明.约瑟夫·奈的“软权力”思想分析.美国研究,2005(1)
(27)包括保罗·肯尼迪和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在内的大家们在这一时期纷纷发表著作,指明美国正因“帝国过度扩张”而处于衰落状态,而且大国兴衰更替也是一个必然的循环过程和周期现象。参见:[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陈景彪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三卷).尤来寅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2000; Immanuel Wallerstein.The United States and World Crisis//Terry Boswell,Albert Bergesen.eds.American's Challenging Role in the World System.New York:Praeger,1987:14-17
(28)Robert O.Keohane,Joseph S.Nye,Jr.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in the Information Age.Foreign Affairs,Fall 1998:86
(29)Joseph S.Nye,Jr.Redefin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Foreign Affairs,July/August 1999:25
(30)Joseph S.Nye,Jr.The Challenge of Soft Power.Time Magazine,Feb.22,1999:21
(31)A.J.P.Taylor.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Europe,1848-1918.Oxford,Eng.: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4:xxix;转引自:[美]约瑟夫·奈.硬权力与软权力.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14
(32)Joseph S.Nye,Power in the Global Information Age:From Realism to Globalization.London:Routledge,2004
(33)Robert O.Keohane,Joseph S.Nye.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3rd edition.Beijing:Beijing University Press,2004:227
(34)[美]约瑟夫·奈著.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吴晓辉,钱程译.东方出版社,2005:31
标签:葛兰西论文; 修昔底德论文; 国际关系论文; 领导行为理论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美国政治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论文; 政治学论文; 经济学论文; 市民社会论文; 国际政治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