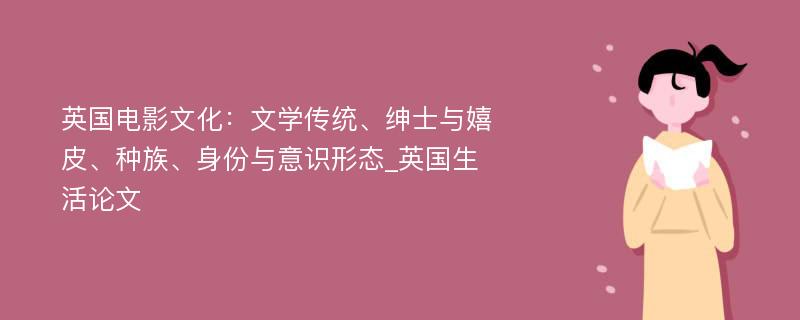
英国电影文化:文学传统、绅士与嬉皮、种族、身份和意识形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英国论文,意识形态论文,绅士论文,种族论文,身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英国电影的百年发展,一直是在与好莱坞电影的纠结难分中度过的。甚至在很多时候,英国电影的国族身份都很成问题。这也许是英国电影常常表现出对身份认同问题执着乃至焦虑的“身份情结”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英美操持同一语言的特点,也因为历史上他们那种近乎兄弟的关系,更因为在演员、导演、资金和制片上,英国电影与美国电影彼此之间交流流通的畅通无阻(它们之间没有语言上、文化上的天然屏障)。英国的很多电影用的是来自美国的资金,很多演员、导演在好莱坞和英国之间来回移动拍片。英国电影除了遭受美国电影的巨大冲击之外,英国民族构成的复杂(如北爱尔兰民族情绪的高涨)更使得一个统一的英国电影的称谓变得有点可疑起来。当然,这些越来越复杂的情况,并不妨碍在世界电影史中有自己独特位置的一部英国电影史或一种英国电影文化的存在。
一 英国电影的百年沉浮
我们结合在英国电影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几个流派或现象来大致梳理整合一下英国百年电影的发展概貌。
(一)布莱顿学派
布莱顿学派是电影诞生的早期,在19、20世纪之交出现的第一个具有一定流派性质的电影群体。
近几年,世界电影史学界对英国的布赖顿学派评价很高,不但被认为是世界电影史上最早的一个电影流派,甚至把最早的蒙太奇手法的使用归之于布赖顿学派。然后才是美国的鲍特和格里菲斯等。而且,鲍特和格里菲斯的电影实践的确受到英国布赖顿学派一定程度的影响。
布赖顿学派源于英国海滨城市布赖顿,主要代表人物有史密斯、威廉逊等。史密斯和詹姆士·威廉逊原来都是静态摄影家,后涉足电影摄制领域。他们对于电影特技效果和剪辑技巧的探索影响了其他国家的许多电影工作者。其作品如《汽车中的婚礼》(1903)等,初步综合了卢米埃尔与梅里爱的探索:他们继承了卢米埃尔真实地记录现实生活的纪实美学原则,但又不再局限于对生活的简单再现和复制,而是吸取了梅里爱对生活进行艺术加工和虚构的戏剧主义或表现主义美学思想。他们的创作原则是“通俗化”,即大多取材于普通日常现实生活,但又不是照相式的纯客观记录,而是触及并发掘一些社会问题,有一定的社会批判性。可以说,这些原则很大程度上奠定了英国电影的诸多传统。在电影语言方面,他们较早试验了诸如两次曝光、移动摄影、叠印、停拍、特写镜头与全景镜头、移动镜头拍摄以及电影蒙太奇手法等。如史密斯1903年的怪异喜剧《玛丽·珍妮的灾难》就使用了相当复杂的剪辑手法。
布莱顿学派对美国电影,尤其是鲍特和格里菲斯早期的创作都有很大的影响,甚至能找出很重的模仿的痕迹。大卫·波德维尔在与他人合著的《世界电影史》中曾指出:“人们一般把1908年以前几乎所有的电影创新都归功于鲍特,包括第一部故事片《救火员的一生》(1903)的拍摄,以及众所周知的电影剪辑的发明。而事实上,鲍特常常从梅里叶、史密斯和威廉逊等人已经使用过的技巧中汲取借鉴。”[1](P15-16)因此不妨说,布莱顿学派是电影从欧洲大陆“文化漂移”到美洲大陆的中介和桥梁。
(二)纪录电影运动
20世纪20、30年代,英国电影有一个初步繁盛的局面。随着电影声音问题的解决,希区柯克的《讹诈》(1929)成为英国第一部有声电影。
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纪录电影的拍制主要仍被限定在新闻影片与风景短片的拍制范围之内,虽偶尔也会有一些具有剧情长度的纪录片出现,但却并没有建立起这一电影类型的重要意义。故至此还不能说真正的、具有独立片种意义的纪录片。虽然如此,20年代期间,随着纪录电影逐渐被定位为艺术性的电影,它在电影大家庭中也逐渐获取了新的地位。在这一过程中,英国的纪录电影运动曾经起有重要的历史作用。
英国的纪录电影运动是以J·格里尔逊为核心的。格里尔逊作为电影导演,只拍出一部《飘网渔船》(1929)。这部影片明显表现出格里尔逊受苏联蒙太奇手法的影响。他快速地剪辑鱼船的各个部位,微微仰拍的影像效果使得片中的一般工人显得形象高大。但格里尔逊却独自举起了英国纪录电影运动的大旗,组建了一个永久性的电影团体并在他身边团结起一大批自由派纪录电影工作者。如巴锡尔·瑞特保罗·洛撒巴西尔·瑞特与哈莱·瓦特等。他们拍制了《纪录影片》《夜邮》《锡兰之歌》等。以格里尔逊为领袖的英国纪录电影运动,创立了一种纪录电影的创作样态。这些作品关注现实生活中的普通人,以公共利益为目的,参与到各种服务性事业中去,发挥了纪录电影记录现实、服务公众的效用。
(三)伊林喜剧
英国资深导演M·巴尔康于1938年主政伊林电影制片厂。巴尔康通过非常民主的经营决策方式,给予了一些电影工作者以极强的独立自主性,在此基础上生产了一些风格比较一致的作品,这些作品往往对生活中的种种落后、可笑的现象进行温和的讽刺,在电影史上被称作“伊林喜剧”。伊林喜剧的电影生产一直持续到50年代,更为重要的是,伊林喜剧典型地代表了英国式喜剧风格与传统。这一传统对英国电影影响深远。
1949年的《好心与王冠》(又译《慈悲心肠》)由英国著名喜剧演员亚力·坚尼斯一人饰演八个不同的角色,这使他一夜成名。与大多数好莱坞风格的喜剧片往往是通过插科打诨的逗趣或嬉皮笑脸的搞笑而营造喜剧效果不同,伊林喜剧的幽默大多建立在普通的生活情境中,更为日常生活化。但是英国喜剧常常在普通生活中加入一个大胆的假想的前提或假设。例如,《通往平利可的护照》的故事发生在单调的伦敦劳工街区平利可,而全片也大多以写实的手法实景拍摄。然而影片的情节却建立在一个大胆妄为的假设之上:研究者发现这个街区根本不是英国的一部分,而是法国的某一地区。英国人必须持护照才能进入此区。这一胆大妄为的假设却有当时英国的现实生活依据。这一居民区居民的粮食供应不受伦敦的粮食配备限制。这折射了战后英国人民希望摆脱艰难生活的愿望。
另一部典型的伊林喜剧,是由查尔斯·克莱顿执导的《雷文坡的匪徒》(1951)。这部影片混合了写实主义与风格化表现。开场的几个片段以近乎纪录片的风格,展示了主角的日常生活惯例。英国电影的这种喜剧风格其实我们在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等著名小说中也似曾相识。克莱顿在几十年后的1989年,又以《一条叫旺达的鱼》引人注目。这部影片充满了古怪刁钻的英国式的黑色幽默风格,可以说这部影片是对伊林喜剧传统的现代提升,或者也可以说是传统的伊林喜剧风格的后现代变调。
(四)自由电影运动和新电影
英国的“自由电影运动”是英国纪录电影传统与现实主义传统的重叠。它又被称为“厨房水槽电影”,这是因为这些电影的题材往往取自卑微琐碎的日常生活。但从某种角度看(如发生的年代,其艺术革新意味,其“愤怒青年”特征等)却相当于英国的法国“新浪潮”。其主要导演有林赛·安德森、卡莱尔·雷兹、瓦尔特·拉萨利等。
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英国的戏剧与小说中,因为以具有叛逆性的普通劳动阶级为主要表现对象,从而形成了一个“愤怒的青年”的浪潮。这一文学浪潮也波及到电影。先是林赛等人组织的一系列纪录电影的拍摄和播映,继而他们成立了一个非正式的团体组织,后来人们习惯称之为“自由电影委员会”。其纲领是“强调电影制作者的自由”;电影工作者应当成为当代社会的评论家”,“公正地探索当代英国社会”。这一运动继而发展到剧情片创作领域。此类电影也被称作新电影。代表性作品有托尼·里查森的《愤怒的回顾》《蜜的滋味》《一个长跑运动员的孤独》、卡莱尔·雷兹的《星期六晚上与星期天早上》等。与其他“愤怒的青年”影片相似,《一个长跑运动员的孤独》运用了若干可能借鉴自法国新浪潮的技巧,如以快动作镜头表现主人公犯罪时的狂躁不安心绪,以摇晃不定的手持摄影机拍摄他在户外慢跑并进而表现他此时的精神状态。与特吕弗的《四百下》结尾时那个著名的定格镜头很像,《一个长跑运动员的孤独》的结尾也是那个男孩戴着防毒面具的定格画面。[1](P473-474)
与法国新浪潮导演们的从影经历有点相似,林赛·安德森原是影评人,一向不满于当时英国电影对于当代生活的拒绝。他的《如果——》就是以电影的方式对英国社会提出了强烈的批评。影片讲述了四个在男校就读的叛逆学生对学校当局进行反抗的故事,这可以视作当时席卷欧洲的“左倾”社会革命的一个缩影。在艺术革新上,《如果——》采用了哥达尔式的通过切入银幕的字幕介绍重要片段的技法,有时还使用彩色与黑白片段交替的做法,这些都营造了一种布莱希特式的间离效果。毫无疑问,《如果——》把一种英国式的现实主义精神与法国新浪潮式的艺术革新意向较好地融合在了一起。
(五)青年电影
英国电影在20世纪70年代,进入一个明显的衰落期。票房与电影产量都急剧下降。有时甚至年产量下降到三十几部。英国本土成为了美国电影的生产工地和放映场所。
直到进入80年代,英国电影才出现了明显的转机。1982年,《火的战车》的编剧科林·韦兰在获得奥斯卡原创剧本奖时甚至宣称:“英国人的时代来了。”
一批被称为“撒切尔时代电影”如《富足》《丑闻》等,一批对英国殖民历史进行反思的文化反思电影,如《甘地》《印度之行》,以及试图重整英国民族精神的《火的战车》《希望与光荣》《我的左脚》等,一向长于从文学改编电影(其电影因而被称为“文学电影”)的著名导演詹姆斯·艾弗里的《四重奏》《看得见风景的房间》《莫里斯》《霍华德庄园》等,均是80年代英国电影业复苏以后的重要作品,代表了英国电影发展的一个高峰。
此间英国电影的导演队伍组成也更为复杂化、年轻化,如导演《杀戮之地》《使命》(也译《传道》)的罗兰·乔菲、导演《蒙娜丽莎》《精神亢奋》《哭泣的游戏》的乔丹、导演《画师的合同》《厨师、窃贼、他的妻子和她的情人》的格林纳威、导演《四个婚礼与一个葬礼》的麦克·纽威尔等,都是一批出生于战后40年代的影坛新秀。这批电影导演也就是被称作“青年电影”的导演群体。他们的创作使得英国电影的风格、题材和主题意向等更为多元复杂而摇曳多姿。按照斯蒂芬·奇布诺尔在《英国心灵怪异的兄弟们》一文的概括则是:“80年代的英国电影极大地忽略过去观众的传统,而偏向寻求另类的身份关系、多元文化,以及多重性别的市场定位。”[2]
二 影像的英国:英国电影文化素描
(一)文学改编传统和文学性
英国是文学大国,或者更直接地说是小说大国。莎士比亚、狄更斯、托马斯·哈代、E·福斯特等文学大师星光灿烂。丰蕴的文学宝藏为英国电影提供了源源不绝的源泉,也影响了英国电影的风貌。
从文学名著改编,这奠定了英国电影具有深厚内涵的特点,也延续了一种基本可以称之为现实主义的传统。只要我们不纠结于这一术语的原始含义,英国电影的现实主义特色非常明显。比之于美国电影的娱乐性、画面感和奇观化,英国电影对现实的关注,其人文色彩和教化特色尤为明显。而比之于欧洲艺术电影或作者电影传统,英国电影又少了那种超现实风格、宗教的神秘气息和经院哲学的玄思色彩。也许可以说,正是这种现实主义精神使得英国电影成为美国电影与欧洲电影之外的“第三种存在”。
电影自文学原著改编,这使得英国电影具有一种文学性非常强的传统和特色。诚如有论者指出:“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又给予英国电影十分深刻的影响,即使不是根据文学作品改编的影片,其中的人物也时常透现出文学的影子。”[3]这一传统自然也延伸到其它非改编电影。在我看来,这也是英国电影向来厚重、坚实,常常渗透着纪实精神,并表现出一种类乎西方古典油画那样的凝重风格的一个原因。
(二)绅士与嬉皮的两极
英国是一个价值观比较保守、君主制有着很大影响的国家。因而英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或传统是保守主义,这也表现在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生产”的电影中。
大卫·里恩的《相见恨晚》呈现了英国中产阶级的典型精神特点,即“自我克制”、绅士风度等。影片描述了一对各自婚姻都陷于单调乏味境地并因而坠入婚外恋情网的中年男女的故事。两人经常会面,但是克制着不逾越规矩。大卫·里恩对这种传统保守主义精神是微温嘲讽而非剑拔弩张,呈现出一种内敛含蓄的浪漫温情风格。
《红菱艳》中的红舞鞋对人的感性本能(爱情、世俗生活)的如同孙猴子的紧箍咒般的压抑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在我看来,《红舞鞋》隐喻的不仅仅是事业与爱情的矛盾,而有着更为深刻的人生哲理意蕴和文化象征意义。那双有着魔力的红舞鞋、歌剧舞剧团老板莱蒙托夫、芭蕾舞剧中的精灵——鞋匠都是现实中人无法逾越、不可战胜的规范、禁忌、宿命等的象征,这些规范和禁忌对英国人(尤其是中产阶级)的压抑、控制,成为英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成为英国电影具有沉稳、剧本扎实、文学性强、现实主义精神等特点的重要原因,同时此类规范、教条或禁忌又常常成为英国电影文化反思的矛头所指。
《火的战车》《希望与光荣》《我的左脚》等影片通过对英国历史的重述和对现实生活的观照,以其深沉、严峻的现实主义风格,充实、乐观的精神风貌,呈现了英国的民族精神和清教徒传统。
也许是压抑过深,反弹也越不常规,越会扭曲变形。英国电影在保守甚至不免迂腐的电影风格之外,却几乎并行不悖地存在着一种近乎嬉皮的风格形态,这种嬉皮,简直可让观众瞠目结舌。就像我们知道英国有文化标志性的燕尾服、文明棍和绅士风度,但也有赫赫有名的摇滚乐、披头士乐队等等。
英国评论家斯蒂芬奇·布诺尔曾指出,英国电影有一种过去的传统,这种传统“更多的是像众所周知的《相见恨晚》那样将情感表达得保守、压抑……”,他认为以《猜火车》《光猪六壮士》《人类交通》等电影为代表,出现了“英国电影的一种新风格——狂躁喧嚣、低成本、玩世不恭,具有颠覆性;定位于青年,而且具有先锋实验性。”[2]
风格怪异、特立独行,不见容于好莱坞,也不屑于好莱坞的电影大师斯坦利·库布里克的一批电影,就堪称这种新风格的先导。他的《巴里·林登》(又译《乱世儿女》)中,弥漫着一种光怪陆离而又超然冷漠的气息。这种通过独特的镜像风格传达的冷漠幽玄气息在悬疑惊悚片《闪灵》中更是达到极致。
艾伦·帕克的《墙》也具有相当的文化前沿性和艺术探索性。《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剧情片,而是一种音乐电影,甚至被认为是MTV即音乐电视这种现今流行于电视媒体上的“后现代符号”的典型代表的先驱。影片的主题是繁复多层的,反战、反传统、反社会、反文化、自由与压抑、父与子,社会与青年……重重的矛盾和主题交织在一起。而最为令人震惊的是影片在影像和音响上的不同于常规的处理。影像通常是碎片式的,不具有明确的意义和叙事结构,而只是光影的切换,用来表达情绪或形成纯粹视觉上的快感。画面构图多样化、不平衡,主观化的色彩处理、唯美化的光线处理、运动镜头、场景变化、快速多变的剪辑风格、交替交错的叙事结构(倒叙、插叙非常随意),主观化的多变的音乐,大量片段而随意的象征、写意、比喻、夸张,这一切,形成了强大的“视听觉冲击流”。
及至20世纪80、90年代,《猜火车》《浅坟》《洛克,斯多克和两杆大烟枪》《光猪六壮士》等进一步集中呈现出这种新风格,一种“酷英国”(Cool·Britannia)①或“怪异英国”。
《猜火车》具有强烈的反传统、反文化的边缘文化性。影片充满了后现代文化的一些重要表达策略如滑稽模仿、拼贴与挪用、反讽与叙述游戏、颠覆和解构、开放不定的结尾、自相矛盾的叙述、“摇滚化”的影像或声音风格、假定性的突出和有意暴露、超现实的影像,等等。
《厨师、大盗、他的妻子和她的情人》也是一部惊世骇俗的怪异乖戾之作,但又有异于《猜火车》《墙》等带有青年边缘文化特征的风格。影片中表现的以尸体为烹饪大餐等丑陋粗野的场景,充满了东拼西凑的杂烩、模仿和幽默等手法。其大胆夸张离奇的想象和表现令人瞠目结舌。导演格林纳威本人曾说《厨师》一片表达了他对英国政治的不满,而且他认为自己的作品与18世纪英国讽喻小品、英国作家斯威夫特的作品有很深的关系。他认为自己作品中的反讽性是一种很“英国化”的态度,即一种对周围事物抱有深刻怀疑的态度。当然,作为现代视觉传达和影像表现的电影艺术,对传统的借用肯定不是简单的回归,在这部影片中,则毋宁说是后现代式的挪用、戏拟、拼贴、杂糅和隐喻。所以,《厨师》从根本上而言还是一种后现代黑色幽默的风格的政治讽喻电影。
(三)文化反思、身份认同和政治意识形态
英国学者勒兹·库克认为,“电影是阶级、社会、种族、地域和身份的再现”。英国的社会文化政治有自己的特点:它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悠久的封建君主制中发生的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使得封建等级社会传统与近代自由民主国家体制长期并置,曾经辉煌的殖民地宗主国历史以及这种“日不落”帝国地位的日渐衰弱的现状也常不和谐,这些现实和历史因素,使得作为意识形态之独特表象的英国电影一向关注种族问题、自我身份定位、第一世界/第三世界文化对比等,跨文化、跨国家、跨种族、跨社会阶级阶层政治团体乃至跨性别等题材的影像化思考与表述。这种题材选择与主题意向尤其在80年代以来更趋明显,这也表现为英国电影文化传统的不断丰富和开放,正如论者所言,“80年代的英国电影极大地忽略过去观众的传统,而偏向寻求另类的身份关系、多元文化,以及多重性别的市场定位”。
文化对比与文化反思一直是英国电影的一个重要文化意向。大卫·里恩的一批跨国电影堪称代表。
大卫·里恩曾自述《桂河大桥》这部影片是“令人痛苦而雄辩地阐述了战争的荒谬性及破坏力”,就像他借助片尾军医说的那句话“疯了,全都疯了”所画龙点睛般地点题那样。影片探讨了英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一些特点,着重对英国民族精神中墨守成规、刻板守旧的保守性、“死要面子”的绅士风度等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和批判。
影片对这些深沉凝重的文化问题的思考是通过所塑造的三个鲜活生动、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英、日、美三个军官——而完成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这三个人就分别是三种文化类型的文化符号——当然,是影像化、艺术化了的文化符号。另一方面,影片又不是为讲故事而讲故事,而是始终贯穿着文化反思与文化重建的现代主题,因而又极富现代性。
《阿拉伯的劳伦斯》则把劳伦斯置于作为宗主国的英国与作为被殖民的附属国的夹缝中,塑造出了一个能够一定程度上超越狭隘的国家利益,尊重第三世界国家的,因而被自己国家排斥冷落的独特形象,进而表现出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深刻反思。与此相似,《印度之行》也通过表现英国殖民主义的历史,从不同民族文化隔阂和文化冲突的角度,反思历史与文化。
阿顿巴罗的《甘地》也难能可贵地超越了民族偏见和前殖民地宗主国心态,塑造了甘地这样一个致力于为本民族摆脱英国殖民统治的民族英雄。
另一种文化反思意向则是从英国文化和民族内部进行的。一批具有后现代文化意向和青年、边缘文化特性的电影如《墙》《猜火车》等,均不乏深刻尖锐的文化反思意向。《猜火车》一开场,就是男主人公瑞特在街上狂奔,伴随着风格狂放的运动拍摄和快速剪辑而形成的几乎令人眼花缭乱的视听冲击力,一个画外独白愤愤地否定了各种循规蹈矩、按部就班的生活方式,宣称自己“选择不要生活”。这种对社会生活方式的反思和叛逆还常常上升到文化和民族。英国,虽然是最早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现代工业革命的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但到20世纪已渐趋衰落。英国人曾经引以为豪的灿烂文化和悠久历史在现代社会中逐渐失去活力。瑞特甚至喊叫着:“我以身为苏格兰人为耻,我们是下等的,地球的垃圾,是他妈的烂文化、混蛋,我们一切都过时了……”
再如《光猪六壮士》属于以男性为叙事中心的“小伙子电影”,它通过生动活泼而略显夸张的情节喜剧的方式,描写了一群英国北方失业工人对社会的适应与反抗,影片以男性视点进行叙事,男性成为被女性观看的客体,在这种戏剧性张力中,流露出成熟男性不无机智的幽默自嘲。同样,被称为代表了英国电影新风格的《人类交通》“生动形象地再现了属于年轻人的文化,但不是为了提供一个逃避现实的虚幻梦想,而是用自己的奇思妙想构建了另一种真实”。[2]
客观而言,早期英国电影,民族问题的表现并不明显,表现的主要还是英国南部以英格兰民族为主体的民族性(忽略了全英国范围内的其他民族如苏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也难免具有一种大一统的民族优越感。随着民族危机的逐渐加剧,素有现实主义传统的英国电影开始关注多民族问题并加以表现(尽管在潜意识中还是有着英格兰民族优越性的主导意识形态)。英国影评家约翰·希尔曾论述过这一趋向并对此趋向表达了由衷的赞许:“有人哀叹英国民族电影的消失,不再表达和反映统一的民族身份或者文化,但是关于这些表现应该换一个角度和方式更好地看待,那就是越来越多的英国电影准备展现英国全境的更为丰富、更为复杂的民族的、区域的、种族的、社会的和生理性别的身份和特点。”[3]
有的电影如乔丹的《迈克尔·柯林斯》是正面展现了爱尔兰独立运动,塑造了一个机智、勇敢、大义凛然的爱尔兰民族英雄形象。
但更多的影片则不无歧义、困惑和矛盾。《哭泣的游戏》是一部涉及民族、政治和性等复杂旨意的电影。在结构上,《哭泣的游戏》巧妙地并置了两个互相渗透的故事,也即主人公弗格斯同时陷入的两个困境——一是种族身份的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困境,一是性别身份上的困境。一方面,爱尔兰人的民族身份使他加入爱尔兰共和军领导的独立运动,但领略了独立运动的血腥恐怖之后,善良的本性又使他陷入困惑和同情,他背叛组织,为共和军绑架的人质实现生前愿望。另一方面,他找到人质的女朋友黛尔并坠入情网之时,却发现黛尔是一个男性易装癖者。这两个结构或两种困境无疑具有一种互为隐喻的关系。实际上传达了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意识形态困惑和质疑。客观上对势不两立的民族纷争表达了困惑和解构的意向。
作为意识形态之表象的电影,我们还是不难发现,导演们虽然在民族意识、价值取向上更为平等、自由、开放,但在潜意识深处还是表达出一种大一统的英国国家意识形态,他们虽然同情爱尔兰独立运动,但其实颇为隔膜,而且无一例外地极力谴责共和军的恐怖行径,表明了骨子里正统的官方意识形态立场。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执政的英国工党政府比较重视电影工业,并采取多种措施极力推动电影业。英国电影在政府的鼓励和支持下,逐渐呈现出良好的势头。在第50届戛纳电影节上,英国文化部长曾满怀信心地说,“我希望今后‘英国出品’的标记在全世界成为成功的同义语。”英国电影在新世纪的发展无疑是引人关注的。
注释:
①英国影评家克莱尔·蒙克在《影现“新英国”》(《世界电影》,2004年第4期)中写道:“英国记者安迪·贝克特在1998年的一篇文章里追溯了‘酷英国’这个概念是怎样在媒体中偶然出现而变成了政府的方针政策的。‘到了1997年’,贝克特分析说,‘酷英国’意味着摇滚乐队、饭厅餐馆、足球教练、时尚设计师,以及具有英国特点的一切事情;1998年初,它就是英国政府对待艺术的全部方针政策的简称,甚至是英国政府的简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