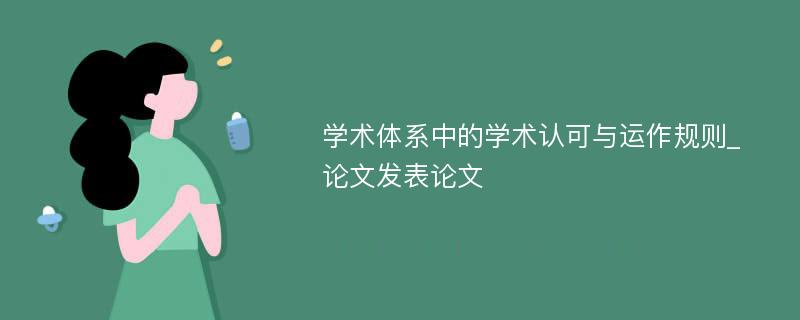
学术认可与学术系统内部的运行规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术论文,可与论文,规则论文,系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203(2007)04-0021-08
学术系统或者说学术共同体是一个抽象的“社区”,不是一个具体的组织和机构,如大学和研究所。共同体成员的日常职业活动实际上是在特定的组织中进行的,诸如收入、福利以及工作条件等都是由其被雇佣的机构承担。因此,共同体对于个体而言并不具有直接的约束力。既然不存在直接的利益关系,个体如何甘愿遵从共同体约定俗成的规范,甚至在组织与共同体之间,个体为何对后者表现出更强烈的归属感和认同感?笔者认为,学术机构内部特定的制度安排的确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这还远远不能解释全部。任何特定机构对个体而言具有可替代性,而学科乃至整个学术共同体却是学者的职业生涯得以终身维系和持续的安身立命之所。正如加斯顿( Jerry Gaston)所言,在共同体内部的奖励体制中,收入和金钱对个体而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共同体基于个体对知识的贡献所给予的认可(recognition)和荣誉(honor)。[1] 只有得到共同体的认可,并被纳入共同体内部的学术等级之中,个体无论是求知的精神需要还是职业的生存需要,才能够得到满足。在一些国家,这种来自共同体内部的认可,甚至可以保障个体无惧于外部道德和政治的压力以及所服务机构的行政干预。
一、学术共同体内部认可的内涵
认可(recognition)是学术共同体内部最有价值的无形资源,它不仅决定了个体在整个学术系统中的等级、权力和地位,而且影响了个体在其组织中对各种有形和无形资源的占有。正因为认可涉及一系列个体潜在或显在的“收益”问题,涉及个体之间、组织之间竞争与合作的不同互动形式以及互动双方的优劣势作用和影响,所以,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它就一直作为一个核心的社会学议题,被英美学者如默顿(Robert K.Merton)、克兰(Diana Crane)、科尔兄弟(Stephan Cole,Cole Jonathan)和加斯顿(Jerry Gaston)等人广泛研究。
对于究竟什么是认可,加斯顿认为:“科学家并不拥有他们的研究成果,他们所拥有的惟一智力财富就是其对科学发展所贡献的知识受到承认……,认可由两部分构成,前半部分是贡献,后半部分是在利用他的知识贡献过程中其他科学家对其表示的赏识。”[2] 然而,其他科学家究竟在什么情境中、以什么方式对其成果表示“赏识”(appreciation)?“赏识”是一个多少带有情感色彩的字眼,它在一定程度上很可能模糊了科学组织内部认可的客观性标准。这对于一向追求客观、精确的科学共同体内部成员而言,显然还远远不能令其满意。因此,如何将“赏识”量化,并将其分解为具体可测量的指标,就成为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科学社会学领域的焦点问题,直至今日,人们的研究热情依然未减。
就总体而言,英美学者的基本共识是,衡量学者的被认可程度最为基本的指标是研究产出。研究产出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产出的数量,另一个是产出的质量。产出数量是一个比较好把握的指标,然而问题在于产出虽然是必要条件,即加斯顿所指的前半部分,但产出的多寡是否是决定认可或知名度的决定因素?科尔兄弟对物理学家的研究表明,通过控制质量因素,数量与知名度之间几乎不相关(相关系数为0.06),而在控制数量的情况下,质量与知名度之间存在相关,相关系数达到0.47。[3] 科尔兄弟的实证结论基本符合我们的常识性判断,但似乎不能绝对化。因为同样有众多实证研究得出相反的结论,如加斯顿对高能物理领域的学者研究表明,高产出的学者的知名度也很高[4]。
另外,因为学科差异,情形也不尽相同。例如,摩根(David R.Morgan)等人就认为,在自然科学中,少而精的完美主义者(perfectionists)更容易得到认可,但是在社会科学中,高产者(prolific)的影响则相对显著。[5] 有趣的是尽管科尔兄弟的结论是认可与数量不相关,但问题是质量与数量竟然高度相关,两者的相关系数高达0.72。[6] 在扎克曼(Harriet Zuckerman)1963年对美国5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研究中发现,这些知名科学家几乎无一例外地是高产者,平均每年的论文数量是3.9篇,而其他非获奖科学家样本只有1.4篇。[7]
因此,这给我们的一个启发是,产出即发表的数量很可能是一个伪问题,真问题可能在于究竟什么是有“质量”的数量。而且,什么是能够得到认可的“质量”恐怕才是最为核心的问题。基于已有的英美学者的研究,一个比较普遍且易操作和可量化的质量指标是学者发表成果的引用率。科尔、克兰等著名学者都比较认同这种观点。如赫默麦什(Daniel S.Hamermesh)等人提出,所谓学术质量其实意味着学者成果对其他学者的影响程度,它可以通过成果引用(排除批判性的引用)频次来测量。[8] 但是,通过SCI、SSCI等索引出的引用率来测量质量,也并不是无懈可击的,它同样广受争议。如桑尼特(Gerhard Sonnert)就认为,引用长期以来始终为人们所批评,重要的原因在于引用者的动机和引用情境实在过于宽泛和复杂,例如,有时候研究者也可能故意引用很糟糕的论文以与自己的观点构成反差,所以引用数量不能直接转换为质量。[9] 另外,引用频次的计算也存在一些技术问题,如作者的排序、名次重复等。[10]
正因为使用单一引用指标可能会带来偏差,所以许多学者往往在计算引文数量时,也综合了更多的其他指标来衡量一个科学家的认可程度或知名度。因为认可反映了他人对个体研究水平的评价,因此它也可以表现为其他尽管与产出有些游离,但可能非常有价值的指标。如贝叶(Alan E.Bayer)等人指出,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测量指标是个人著述数量、同行投票以及引用频数等。[11] 这种测量是把数量和质量相结合,同时也引入了同行评议的定性评价。但是,除此之外,人们还引入了一些其他评价指标,如是否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是否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是否是主要学术期刊的编委、各种学术荣誉是否被列入《科学美国人》条目等等,甚至还有人把个人的专业收入、在专业学会中的职位、所指导的研究生数量和质量、每年空中旅行距离等等,都视为衡量认可程度的依据。
在简单的数量和可量化的质量指标之外,又综合更多的其他定性指标,不可否认,这样它们可能更全面、更真实地反映学者学术认可的程度,然而,这也同样存在一系列值得深究的问题。首先这种认可的测量因为定性指标的介入,必定带来操作意义上的复杂性和模糊性。然而,更为关键的是,无论是以上量化指标还是定性指标,它充其量只能够反映一位学者被认可的程度和知名度,即在静态的学术阶梯结构中的地位和等级,对于这种认可和知名度背后更为复杂深层的内涵及其动态运作,却实在提供不了多少更有价值的洞见。也就是说,简单的实证分析,至多说明了两个或多个变量间的相关与否的联系,但是,对于变量间的孰因孰果却往往无法辨识和定位。甚至,这其中还有一个更为本质性的问题,即假定数量、质量特别是由引用率反映出来的质量以及各种学术声誉等是学者获得认可的决定性因素,那么,这种数量、质量的界定是否就反映了真实的学术水平和水准?换言之,数量、质量以及各种其他学术声誉资源究竟反映的是个体纯粹的智力贡献,还是其他包括非学术性因素在内起作用的结果?显然,回答这一问题才真正触及学术认可背后有关学术共同体内部的运作机制。
二、学术共同体内部的运作机制
一般而言,一位学者的学术认可过程实际上也是他一生的学术职业发展的过程。大多数英美学者的研究生涯是以其研究生阶段为起点,个别的会以本科生阶段为起点。所有学者获得认可的过程都无一例外地经过如下环节:获得博士学位——选择学术机构从事学术研究和教学——发表论文——被评价、被引用或获得学术奖励——向上流动步入学术更高等级——成为知名学者。有关学术认可最为传统和经典的观点来自默顿的“普遍主义”(universalism)观。默顿认为,科学家对待科学或者学者对待学术不仅来自一种精神上的好奇和对求知的热诚,而且也来自一种获得他人尊重的精神需要。如达尔文所言:“我对自然科学的热爱……在很大程度上获益于要赢得其他博物学家尊重的雄心。”因此,对于科学家个人而言,科学是一种纯属为科学家提供精神层面愉悦的活动或者事业,是非功利的。正因为科学的无功利性以及它的求真取向,所以科学家的工作是跨国界的、超越个人私利的利他主义,它的认可只在于科学本身,即科学内部所谓真理的普适性标准。用这种普适性标准衡量评价科学家的工作,就是所谓的普遍主义。即评价一位学者的研究贡献 (或者是否能够为共同体认可)的标准只在于它是否合乎构成真理的技术性和学术性要求以及新知识的重要性,而与研究者的出身、种族、国别、性别、宗教、年龄等等一概无关。[12] 如果结合学者的成长过程来分析,学者的认可过程其实只与其个人的聪慧程度、努力程度、所受到的良好学术训练等自致性因素相关。借用科尔兄弟的说法,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者的心理学人格特征、动机以及“神圣的火花” (sacred-spark)效应①。[13]
显然,如果默顿的普遍主义成立,那么学术认可就仅仅体现为学者的能力以及学者的研究成果本身,与学者其他先赋性和结构性的社会条件无关。然而,正如人们所看到的,在学术系统内部为什么会存在一个等级分布不平等的结构布局?具体而言,为何付出同样努力的学者可能会拥有不同的学术地位?为何在学者群体中,有的人发表文章数量很多,有的人发表文章数量很少?普赖斯(Derek John De Solla Price)的研究指出,在科学家中,有50%的科学家可能终身只发表1篇文章,而有10%的科学家贡献了30%的发表成果,真正的高产者只有3%。即使在大量已发表的科学论文中,为何只有少数论文被频繁关注和引用,高达50%的论文几乎被忽视?加斯汀(Bernard H.Gustin)对这一现象的评价是:与社会其他领域一样,科学界中既有百万富翁,也有一贫如洗的乞丐。如果所谓普遍主义的学者的求知纯粹是追求被他人尊重和获得精神愉悦的假设成立,那么,就意味着绝大多数得不到认可的科学家将陷入无法容忍的绝望状态,这几乎是不可思议的。[14] 另外,人们还提出疑问,诸如为何大多数论文和学术地位较高的学者集中于少数研究型大学或机构,为何从名牌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者要比其他人更容易得到认可等等问题。
其实,也正是由于上述一系列问题的出现,20世纪70年代后关于“科学的科学”的研究才偏离了关注个体的研究方向,转向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科学社会学。英美特别是美国的主流社会学、科学政策研究等期刊刊载了大量与之相关的实证研究文献,这些文献几乎深入到了学者职业成长的所有环节和细节,包括博士学位授予机构、工作单位的等级声誉与学术认可之间的关联,学者所拥有的各种学术身份与产出间的关联,期刊图书出版运行方式与产出间的关联,年龄、性别甚至种族、阶级在学术认可中的影响,学者的早期学术贡献与后期地位间的关联,论文性质和文本特征与引用率之间的关联等等。所有这些研究的基本旨趣在于探索学术认可背后的社会化、结构、程序以及组织背景等的影响,而这些因素的作用特征在笔者看来,毋宁说它反映了科学共同体或者学术界内部的“潜规则”,用加斯顿的说法是“不成文的规则”(no codified law and no book of rules)[15]。当然,这里的“潜规则”未必带有贬义和负面的色彩,而是指涉作为非组织化的松散的学术共同体内部所特有的运行机制,它对于我们理解宏观的学术制度有着极为特殊的意义和价值。因为大多数研究的样本往往具体于某一学科,且定量工具使用不同,所以在结论上也必定存在众多差异。在此,本文仅仅将有关研究的一般性结论概括如下。
1.学术出身和身份
一般而言,博士毕业于或工作于排名越靠前的高校或者院系的学者,其产出通常越高。克兰·克拉克(Kenneth E.Clark)的研究表明,从知名的研究型大学毕业的博士的产出明显高于其他学校的毕业生。[16] 摩根等人则通过对政治科学专业的学者的产出研究表明,产出与学者所在研究机构间存在适度相关,但并非绝对一一对应;对该学科几家权威性刊物的论文统计表明,21%的论文来自美国排名前10位的院系,55%的论文来自前20名的院系。[17] 而基思(Bruce Keith)等人的研究则表明,大学的地位声誉比院系的业绩本身影响更为显著。[18] 我们不妨进而推之,学者所在大学的排名对学者的产出和认可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另外,科尔兄弟、莱斯金(Barbara Reskin)、朗(J.Scott Long)等众多学者对工作于不同组织背景中的科学家进行了广泛研究,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学术界的科学家比政府和工业界的科学家发表更多的成果,并更容易得到认可。[19]
2.期刊与专著的运作程序
关于期刊和图书出版运作与学者认可、声誉间的关系,克莱门斯(Elisabeth S.Clemens)等人对此进行了非常独到和翔实的研究。首先,他们认为,著作与论文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学者知名度的影响是不同的,自然科学领域的论文被引用得更为广泛,而社会科学领域则往往是著作更有影响。其原因可能与社会科学的一致性、可编码程度(codification)水平低,绝对学术权威缺乏以及学派林立有关。由于运作程序不同,论文发表和著作出版对学者的认可和知名度的影响也不同。期刊论文存在高度程序化的审稿过程。如布兰克对不同领域的38家权威期刊抽样调查发现,有11家采用双盲评审。在经济学领域的38家刊物中,有16家采用双盲评审,其他则多为单盲评审。不过有趣的是,真正的双盲稿件采用率只有5.5%,而假盲(双盲评审中有45%的通过参考文献可以辨别出作者)采用率为16.4%,单盲评审用稿率达到15%。值得注意的是,物理、化学和心理学等许多理科期刊基本采取单盲评审,由此不难发现,作者的身份依旧在其中发生某种影响。但是,著作特别是社会科学专著的出版却完全不同,编者因为考虑到市场和回报的问题,极少采取盲审的程序,更看重作者的身份以及已经建立起来相互间稳定的信任关系,结果是专著出版往往趋向于对精英开放。[20]
出版系统的程序或者说潜规则,往往也影响到学者的投稿行为。如戈登(Michael D.Gordon)认为,作者选择刊物虽然基于回报最大化的原则,但是往往首先考虑的是被拒绝的概率。[21] 刊物系统内部的等级结构以及专著出版的精英倾向,一方面体现出学术系统内部存在等级结构,另一方面,它们的运作似乎更倾向于强化既存等级结构而不是推动平等,即使存在一个比较严格的同行评审过程。
3.同行评议
同行评议(peer review)是学术界中最流行的一种方式。刊物稿件的评审、研究项目和课题的申请报告、有关奖励项目的评审乃至学者的职业晋升材料评审等等,往往都由同行权威承担。就总体而言,英美学术界普遍认可程序严格的同行评议。例如在对美国基础科学最大资助机构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的基金申请者的调查研究中,在申请参与专家邮件评议的学者中,45%的人认为同行评审可靠,50%的人认为可以接受但存在一些弱点,只有4%的人认为有问题;而参与同行小组评议的评审者中,64%的人认为同行评议可靠,34%的人认为同行评议可接受,5%的人认为有问题。但是,当调查问及在申请书旗鼓相当的前提下,不同机构间的申请者是否机会均等时,52%的评审者和61%的申请者认为,来自知名大学的申请比其他大学的更容易获得通过,只有29%的评审者和16%的申请者认为两者机会均等。[22] 显然,从公平的角度而言,同行评议恐怕并非是完美的,甚至在效率上它也受到部分人的质疑。如罗伊(Rustum Roy)就认为,没有经验和理论证据表明NSF基于对申请书的同行评议就能够使好的研究获得支持;评议者存在自我偏好,新的或不符合主流的理念往往被排斥;同行评议体制存在惊人的资源浪费,导致众多科学家耗掉其1/4乃至一半的时间去争取资金,而不是去从事分内的研究工作;评议导致科学共同体内部的竞争和紧张等等。[23] 卡普纳里奥(Juan Miguel Campanario)则在对ISI(建立SCI和SSCI索引的机构)所提供的引用率最高的学术论文的案例分析发现,很多经典论文最初被所谓遵守严格同行评审程序的期刊拒绝或被迫作不适当的修改。而最为经典和最有影响的事件莫过于皮特斯(D.P.Peters)和西塞(S.J.Ceci)所做的一个“欺骗性”实验。他们把12篇已经发表过的、由知名大学权威学者撰写的心理学论文,在换掉名字和所属机构后,重新投稿给已发表这些论文的权威杂志,结果,只有3篇被发现作假,而8篇被拒用,只有1篇被通过。[24] 这一事件不仅引起人们对同行评议程序可靠性的怀疑,更让人不安的是作者身份而不是质量在评审过程中很可能被赋予不太恰当的权重,因而存在严重的公平性问题。
4.性别、种族及其他
性别也一直是科学社会学研究关注的重要因素。朗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仅从数据来分析,妇女和少数族裔本身跻身科学研究领域的人数比例较低,女性的学术声誉也确实无法与男性相比,产出少且很少得到学术认可。所以,在他看来,也许一个值得去深入研究的真问题是:什么因素导致女性和少数族裔低程度的科学参与。[25] 然而,尼娜·托尔(Nina Toren)等人则认为,在学术的障碍赛中,女性很少有机会去显示她们的能力,即使处于同等水平,她们往往需要付出更多去证明自己的能力,并发表更多的成果,才有可能被认可或得到晋升。[26] 最激烈的批评来自玛格丽特·罗塞特(Margaret W.Rossiter),她认为学术声誉是社会建构性的,女性的科学贡献往往被科学内部潜规则所埋没。她详细列举了在科学史上包括诺贝尔奖评选在内的众多对女性不公平的事件:1890年德国妇女艾格尼丝·伯基丝(Agnes Pockels)的“表面张力”理论被英国的雷利(Lord Rayleigh)“剽取”;1905年,遗传学家内蒂 (Nettie Stevens)与哥伦比亚大学的威尔逊(Edwin B.Wilson)同时发现了性别决定论的性质,但最终后者得到荣誉;1934年病理学家惠普尔(George Hoyt Whipple)获诺贝尔奖,而其贡献相当程度上来自他多年的女助手弗丽达·罗宾斯(Frieda Robscheit Robbins);20世纪50年代我们所熟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和李政道,提出了宇称不守恒理论,但是该理论却是由吴健雄通过实验得到证明的;丽丝·米娜(Lise Meitner)为哈恩(Otto Hahn)工作十几年,发现了核子分裂,但后者却独享荣誉;鲁丝(Ruth Hubbard)作为瓦尔德(George Wald)的妻子几乎承担了所有的研究工作,但最终是丈夫独享殊荣,如此等等。[27] 另外,还有许多学者对年龄、合作方式与学术认可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包括发表论文的年龄、入职年龄、独立作者还是合作者、合作论文的排序等等对学术认可的影响。总体上,这些研究没有得到比较一致的结论。
三、关于学术共同体内部规则的理论解释
从20世纪70年代到现在,众多的实证研究虽然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启发,但就总体而言,它们与其说让我们对学术界内部的潜规则有个清晰的把握,不如说更多的是困惑和问题。众多结论虽然揭示了学术认可与一系列变量间存在的不同程度的相关性,但因为在抽样策略和工具使用上存在众多差异,许多结论依旧存在一致性不足的问题,而且,由于总体结论并没有背离我们常识意义上的理解,故而很难说这些实证研究就一定揭示了学术界内部运作的规律和本质。正因为如此,笔者认为,这些内部规则是潜在的、模糊的,它反映了某种大致趋向而不是刚性的原则,这也是加斯顿为何把它们称为“不成文规则”的重要原因。也正是因为这些规则的潜在性和模糊性,关于这些规则的理论解释也存在复杂性和多样性。
关于学术认可的内部规则或者说趋向的解释概括起来,涉及以下两个维度:个人层面与社会组织环境层面,或者说自致性层面与先赋性层面;积累优势和强化效应与社会建构效应。所谓个人层面或者自致性层面,更多地强调学术认可来自个人的人格特征、动机(包括“神圣火花”效应)、认知水平、工作习惯或工作努力和勤奋程度等,它与学者的社会化过程没有关联。[28] 换言之,个体的学术声誉和学术认可主要是个人因素作用的结果。学术界的规则就是一个优胜劣汰的筛选过程,在这个筛选过程中,优秀者被吸纳到高排名的研究型大学或院系中,并获得这些机构的博士学位或教职。由于这些机构具有重视研究、教学负担轻、图书和工作设备条件好、高水平同行间交流频繁、学生和研究助手资质良好、研究假期长等条件,强化了优秀者的竞争优势,因而他们产出高、质量好,所以更容易被认可。这种理论解释应该说也符合默顿的科学的普遍主义观和社会学的功能主义特征。在默顿看来,在学术界,个体优势有时候往往会转化为社会优势,一旦个人成就被认可,它就慢慢形成一种累积优势(cumulative advantage)效应,这种效应又被称之为马太效应,从而导致一种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现象。正如扎克曼认为的,累积优势的马太效应是普遍主义的必然结果,它是基于对个人能力和成就(achievement)的认可,而不是外在于个人的社会因素。[29] 所谓社会学的功能主义特征,即承认学术界内部精英主义的价值取向和不平等结构的合理性,因为这种结构特征的形成是自致性而非先赋性因素作用的结果。
然而,另有一些学者认为,默顿的马太效应其实违背了科学的普遍主义观,因为累积优势效应已偏离了业绩(achievement)本位的准则,它毋宁说是符合默顿对帕森斯进行修正后的功能主义,即马太效应是一种负功能,是先赋性因素作用(ascriptive process)的结果。[30] 这种观点我们不妨称之为学术认可的社会建构观。20世纪70年代后,英国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在该方面提供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如布鲁尔(David Bloor)等人认为,科学知识与其说是反映客观性的真理,不如说它是政治和财力资源运作,以及特殊的语言风格系统作用的结果。而引用就是为科学家的论文提供支持并让读者对其所谓宣称的可靠性深信不疑。引用率塑造了学术系统内部的等级结构,反过来,这种等级结构又进一步影响个体成果的引用率。故而,影响引用即学术认可的因素更多地与被引作者在学术系统内部等级结构中的地位有关,而不是论文内容本身。[31]
关于学术认可的社会建构观的第二种解释是,学术认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者在学术系统内部的网络关系资源,即所谓的社会资本。图赖(Palonen Tuire)等人认为,学术系统内部的网络结构包括两个部分,无形学院(invisible college)和引用网络(citation networks)。前者主要表现为学者间的一种私人联系,进一步可区分为两个维度:信息网 (information matrix)和合作网(collaboration matrix)。信息网主要表现为学者间经常的会议、电话、信函以及电子邮件等方面的联系,合作网则主要指学者间的研究合作、稿件交流、相互发表评论如书评,以及众多其他正式或非正式的合作。[32] 个体与网络中行动者的联系越多,密度就越大,因而被认可的可能性就越大。而那些拥有系统中高等级地位的人,往往也占据网络的中心位置,不仅能够决定选题以及研究方向,而且能够获得更多的信息资源,进而表现出典型的马太效应。在引用网络的分析中,图赖等人发现,学术系统中的高级成员往往更局限于相对狭窄的权威文献,即一些权威性的著述和期刊。[33] 另外,巴尔迪(Stephane Baldi)认为,学术界的强关系如导师与学生间的关系、在同一机构获得博士学位的研究者间的关系以及同事关系,都有可能比其他关系对引用率带来潜在的影响,从而影响不同个体的学术认可。[34]
除了上述观点外,还有人从其他角度进行了一系列的解释。如有人认为,马太效应与第一印象(first impression)效应有关,如果学者早期的研究工作相当出色,那么,他就会更容易得到认可,反之,如果新来者初期的研究成果平庸,则带来相反的效果。[35] 加斯汀则援引库恩的观点指出,科学共同体是完全由精英把持的相对封闭的系统,它与宗教共同体相仿,其共同点都在于推崇内部的查理斯玛(Charisma)权威,即信奉权威的人格魅力。宗教内部存在一系列确立权威的仪式,科学共同体内部也存在这种现象,如每个学科领域的创立者如同宗教的领导者,出版、奖励、职位选拔、大型学术会议如同一系列程序化的仪式,这些仪式赋予少数精英及其话语以合法性和特殊的象征性权力,进而确立和巩固其在系统中的精神领袖地位并强化其影响,这一过程就是查理斯玛效应。[36]
总之,以上理论解释都以马太效应作为一个客观现象为前提,然而,也有个别研究对马太效应本身提出质疑。如有人认为,马太效应过于强调研究者的特征,事实上如果从引用率来看,文章特征可能在其中更具有显著影响。如斯图亚特通过实证研究证明,文章的长度、文献引用数量、表格、图片以及方程式等特点是影响引用率的重要因素,此外,研究领域的差异、论文内容的理论性与经验性取向,也对引用率产生不同的影响。[37] 斯蒂芬·科尔(Stephen Cole)对物理学学者的实证研究则表明,无论作者的地位高低,高质量的论文都会被认可,但是,马太效应也发生作用,只不过它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成果被传播和认可的速度上,学术地位高的学者的成果传播速度明显快,而学术地位低的作者的成果往往在短时间内被忽视。[38] 而更多的学者则认为,学术认可中的马太效应或者累积优势效应的确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它绝不是该过程中惟一具有显著影响的潜规则,学术认可应是各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如福克斯(Mary Frank Fox)在她的综述性研究中指出:影响学术认可的因素存在个体、组织环境和学术界三个层次。在个体层次上,心理、智力等人格特征、工作习惯、精神驱动力以及年龄等是影响认可的重要因素;在组织环境层次上,毕业于排名靠前的学术机构或者在有声望的学术机构任职非常有利于个体的学术产出,并对其学术认可有积极影响;在学术共同体层次上,累积优势和强化效应发生作用。[39] 麦卓夫(Ian I.Mitroff)则在同行评议的研究中区分了三种模式:累积优势模式(accumulative advantage model)、政治模式(political model)和实力模式(merit model)。在他看来,前两种模式都反映学术界中的特殊主义(particularism)而不是普遍主义取向,累积优势模式即马太效应,使得资源分配更趋向于向已获得声誉的学者集中,这是一个看似自然实际上是不平等的分配模式。而政治模式则反映了学术界的权力关系,少数精英学术机构中的精英科学家,不仅依靠在学术界与其他精英科学家的人脉关系获取更多的稀缺资源和信息,而且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众多特殊机构如权威期刊、NSF和各种其他政府研究资助机构的掌门人(gatekeeper)、顾问以及同行评议者,所以,他们往往比其他人更易获取资源甚至影响政府的科技政策。以上两种模式在麦卓夫看来都受到学术界权力、关系和声誉的“污染”,并产生负面效应的潜规则,只有第三种实力模式才是真正体现了普遍主义取向、根据个人的能力按照竞争原则分配资源的模式。[40]
总体而言,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关于科学共同体的研究基本是由英美学者完成的,并且几乎所有的研究都采取了实证量化的研究线路。纵观这些研究,其基本的理论假设虽然是把科学共同体视为一个存在结构、等级和流动特征的社会系统,但从严格意义上讲,它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小社会系统。因而,在确定变量关系时极少会考虑到来自共同体外部环境的干扰因素甚至是显著性因素的影响。毫无疑问,这些研究无论是在方法上还是在理论解释上,尤其对于我们理解英美学术系统内部运作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发。但是,由于不同的国家文化、政治制度存在差异,科研体制、出版制度和学术系统的内部运作也有所不同,因此,在考虑影响学术认可的潜在变量关系时,我们固然可以对上述研究框架有所借鉴,但不能简单照搬,否则就很难洞察学者的学术认可在中国特定背景下的真实内涵,并误读学术共同体内部运作的真实状态。因此,基于这一认识,本文与其说是一个阶段性的研究成果,不如说仅仅是一个启发我们对中国学术系统内部的运作规则展开研究的引子。下一步,我们将以此为基点,在充分考虑中国学术传统特殊性的前提下,适当借鉴英美上述研究的方法、工具和理论,建立一系列假设并予以实证检验。相信这种基于社会学的研究,对于我们理解中国学术界的学术认可以及学术制度,规范和完善我国的学术制度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注释:
①“神圣的火花”效应是指一种出自对职业的热爱而形成的内部驱动力和自觉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