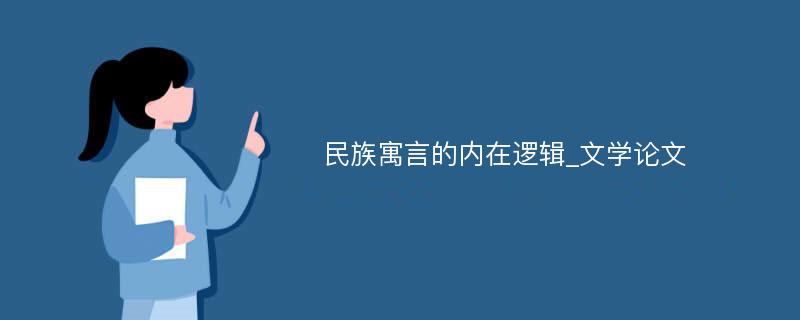
民族寓言的内在逻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寓言论文,逻辑论文,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批评界,詹明信(Fredric Jameson)像是一条章鱼,他的理论触角几乎无所不及。他自称是法国文学专家,对德国法兰克福学派也颇有研究;他擅长分析叙事文学,但他对形象文化,特别是对电影的研究,又使他跻身于一流理论家的行列;从中国的鲁迅到塞内加尔的奥斯曼尼塞姆班涅,他无所不读、无所不评,而且立论无不掷地有声。然而,他广博的论述也引起了广泛的批评[①],其中的焦点之一就是他的“第三世界文学与民族寓言”论。
詹明信为什么要建构一种关于第三世界文学或文化的理论?这跟他研究后期资本主义或后现代主义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众所周知,詹明信对第三世界的非洲、古巴、中国始终牵挂有加,很想“每隔二三年去一次中国”,并声称“他寄希望于伟大的中国”[②]。作为西方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他对第三世界文学或文化的研究到底有什么意义呢?难道仅仅是为了其学院式书写的需要,或是在现实中重温他理论中的乌托邦?
甚至早在60年代,詹明信就开始关注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第三世界之间某种内在的文化逻辑。在他的成名作《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一书中,他就引用过当时我们的报刊上一个很流行的观点:“从整个世界范围看,如果北美和西欧可以被称为世界的城市,那么,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则构成了世界的农村。从某种意义上讲,当代世界革命也显示出一幅农村包围城市的图景。”[③]很明显,这种所谓世界范围内的“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在某种意义上启迪了詹明信。作为“农村”的第三世界具有一种边缘性,落后的第三世界如何“包围”发达的第一世界,这一课题本身对詹明信来说就极富辩证意味。也就是说,詹明信看重第三世界文化的边缘性,并不仅仅因为他的某些分析方法颇受解构主义的影响,习惯于从边缘切入中心,而更重要的是,深谙辩证法的詹明信要想彻底深入地剖析后期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他很难不面对第三世界文化。否则,在单一文化系统内谈文化,辩证思维只会流于空疏。所以,詹明信提出第三世界文化这一命题是其辩证思维发展的必然。当然,从文化转向文学,对詹明信来说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因为“雷蒙·威廉斯曾说:文学教师必须把他的学习对象当作一种文化的产物,这样才有可能认识作品的意义和本质。”[④]
出于辩证思维发展的必然,詹明信提出了第三世界文化或文学这一概念。这一点可以从他最喜欢援引的一段黑格尔关于“奴隶与奴隶主”的神话得到佐证。按照黑格尔的叙述,人类历史源于两个人的相遇。他们彼此都渴望得到承认,因此,你死我活地搏斗起来。一种情况是,一方被打死了,矛盾得到暂缓。但更大的可能是,一方宁愿承认失败,也不愿接受肉体的死亡;而另一方则更不愿意让对方死亡,因为一旦对方死亡,即使成功了,仍然是一种没有得到承认的成功。其结果,忍气吞声、苟且偷生的一方则接受失败而成为奴隶,为价值、理想而宁死不屈的一方则成了征服者,即奴隶主。表面上看,奴隶主成功了,奴隶失败了。但具有辩证意味的是,由于奴隶被迫为奴隶主干活,因此,他们所接触到的是真正的现实,而且也只有他们最了解现实,并产生唯物主义意识。而奴隶主则被高高悬置,渐渐远离现实,享受着所谓荣誉、自由,却丧失了认识真理的土壤。按照詹明信的观点,上述情形基本能印证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之间的关系。因此,认识第三世界文化才能从根本上了解世界文化的格局,从而更好地揭示出资本主义文化的特征和矛盾。
其次,詹明信提出“第三世界文学”最直接的启发应该来自歌德。“在今天的美国重新建立文化研究需要在新的环境里重温歌德很早以前提出的世界文学。任何世界文学的概念都必须特别注重第三世界文学,这是我今天要讲的广泛的题目。”[⑤]如果我们再深入地考察一下詹明信的理论背景的话,我们就不难看出,他提出“第三世界文化或文学”这一论题更深刻的影响应该说来源于卢卡契。歌德关于“世界文学”的概念其实是一个相当开放的术语,文学理论家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从民族文学、个体文学、国别文学等角度来丰富“世界文学”这一概念的内涵。而歌德在提出这一概念时,也不是从政治的角度出发的,而是强调一种文学的共时性。具体说来,他是指在故乡魏玛可以同时接受世界各地的文学信息,因此,他认为世界文学的时代到来了。詹明信从“世界文学”这一概念引发出“第三世界文学”这一命题,完全是他创造性阐释的结果。而这创造性阐发的背后多多少少隐含了卢卡契的“总体论”。不难看出,在詹明信评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中,从阿多尔诺、本雅明到阿尔都塞、马尔库塞,詹明信对卢卡契可谓推崇备至,并认为他的代表作《历史与阶级意识》“奠定了新马克思主义知识论的基础”[⑥],因而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为“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⑦]。众所周知,这部著作的真正贡献在于“恢复了总体论范畴在马克思著作中的中心地位”[⑧],至此,总体论成为马克思认识论中的一个核心概念。而这一核心概念对詹明信来说至为关键,特别是在理解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关系时,因为“对第三世界文化的研究必须包括从外部对我们自己(指第一世界)重新进行评估(也许我们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们是世界资本主义总体制度里旧文化基础上强有力地工作的势力的一部分。”[⑨]在此,詹明信强调的是一种外部与内部,特别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所以,可以说詹明信独辟蹊径着手第三世界文学和文化的研究,其理论是建基在“总体论”之上的。
对詹明信来说,提出一个关键性命题固然重要,但如何丰富这一命题的内涵而使其在理论上有所建树才是他的真正目的。詹明信的突破点是第三世界知识分子(当然包括作家)。从探讨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作用中,詹明信发现,就使命感而言,第三世界知识分子迥异于第一世界知识分子。与第一世界知识分子仅仅充当一种纯技术性的社会功能不同,第三世界知识分子“永远是政治知识分子”。这些“文化知识分子同时也是政治斗士,是既写诗歌又参加实践的知识分子”[⑩]。因此,研究这些知识分子的意识也就在某种程度上了解了第三世界的集体意识。那么,第三世界知识分子最关心、讨论最多的,也即是占据了他们意识中心的究竟是什么呢?詹明信认为是民族主义。一种在第一世界看来早已过时的经验为什么会成为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政治情结呢?对此,詹明信并没有提供直接的答案。但我们从其论述中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第三世界的生存意识迫使它把民族主义放在压倒一切的位置上。当然,如果我们正确地理解民族主义这一概念的话,我们就不能纯粹从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的生存对抗上来认识。这仅仅是这一概念内涵的一部分,而且是外在的一部分。民族主义的核心内容应该包括对自身“民族性”的反思。只有对自身的“民族性”进行深刻的反思之后,第三世界才不至于陷入站起来之后又站不住的境地。事实上,真正有深邃思想的第三世界作家往往在后者上倾注了更多的心力。
既然民族主义成了第三世界知识分子身上普遍存在的政治情结,那么它又通过何种形式表现在文学上的呢?
詹明信的回答是,“所有第三世界的文本均带有寓言性和特殊性;我们应该把这些文本当作民族寓言来阅读……”,“第三世界的文本,甚至那些看起来好象是关于力比多趋力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投射于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11)詹明信之所以把所有的第三世界的文学文本都视为单一的民族寓言加以解读,这跟他对“寓言性”的理解是分不开的。我们不妨先来看一下他是如何阐释寓言性的:“在西方早已丧失名誉的寓言形式曾是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的浪漫主义反叛的特别目标,然而当前的文学理论却对寓言的语言结构发生了复苏的兴趣。寓言精神具有极度的断续性,充满了分裂与异质,带有与梦幻一样的多种解释,而不是对符号的单一表述。它的形式超越了老牌现代主义的象征主义,甚至超越了现实主义。”(12)这段论述基本上高度浓缩了寓言的主要内涵,即与象征的某种对立性、断裂性和复义性。下面我们分别就上述三个方面进行一些还原性的工作,看一看詹明信为什么选择寓言性来解释第三世界文本,或者更确切地说,寓言性与他所要建立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学有什么关系。
必须指出的是,詹明信对民族寓言这一概念的使用决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他几十年如一日思考马克思主义与形式问题的结晶。从他的早期作品《侵略的寓言》(1979)明确提出“民族寓言”这一概念起,詹明信在他的《马克思主义与形式》(1979)、《政治无意识》(1981)、《政治地理美学》(1992)等几部重要作品中,都论述了寓言问题,对浪漫主义以来一向受到贬斥的寓言作了新的阐说。
究竟什么是寓言?尽管寓言研究专家艾德文·霍尼格认为对之很难下一个满意的定义(13),但我们仍可以有足够的选择余地。譬如,当代著名的批评家M.H.艾伯拉姆斯界定说,“寓言是一种叙事,它的行为者和行为,有时包括背景经过作家刻意的创作,其目的不但使它们本身有意义,而且更重要的是揭示出一种相关的、第二层面的人物、事物、概念或事件。”(14)浪漫派文学代言人柯勒律治的定义非常冗长,但影响更大:“我们可以慎重地把寓言性作品定义为运用一套行为者和形象及其相应的行为和随应物以伪装的形式来表达道德品质,或本身并非感知客体的理性概念,或别的形象、行为者、行为、命运或环境,其结果差异性随处可见,而相似性也被隐隐约约地暗示出来。这样,各部分就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15)。实际上,普卢塔克是最先使用这一术语的古典作家,他的定义简洁并抓住了事物的本质,体现了哲人的睿智:“叙述的是一件事,而理解的却是另一件事”(16)。对寓言进行过系统研究的学者安格尼斯·佛莱切的定义更为言简意赅:“简言之,寓言就是言此意彼。”(17)至此,我们可以较为明确地的得出结论,寓言的本质特征在于言意的分裂,即所指与能指的漂移。
然而,寓言作为一种文学体式(mode)长期以来却备受欺凌。这是其他文学体式,如讽刺、幽默等所不曾有过的现象。推崇象征的人把寓言视为死敌;研究神话的人也极力贬低寓言。浪漫派挞伐寓言,新批评更是弃之如敝屣。人们不禁要问,寓言怎么啦?它为什么受到如此灾难性的攻击而在文学史上名声不佳。但与此同时,寓言并未一蹶不振,相反,寓言型作家代不乏人,而且几乎都是超一流大师,如庄子、但丁、斯宾塞、卡夫卡、托马斯·曼、鲁迅等?要回答上述问题,我们首先必须了解谁抨击过寓言,他们的理由是什么。
其著作被怀特海誉为“西方哲学之源”的柏拉图首先在《理想国》中流露出对寓言的厌恶,尽管就在他的这部代表性著作中,他本人也使用了家喻户晓的“洞穴”寓言。但他坚持认为,“它跟反映现实本质的思维方式相反,也就是说,它反映的不是,或者说基本上对立于感觉和理性所确认的论据。”(18)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布莱克对寓言似乎更不友好:“寓言故事或寓言(fable or alle gory)是一种截然不同的、劣等的诗。幻想或想象则再现了永恒的、真实的和不变的存在。寓言故事或寓言是由记忆之女孕育的,而想象的翅膀是由灵感之女托起的。”(19)大诗人歌德对寓言的偏见可谓根深蒂固。他的观点影响了一大批浪漫派诗人,因为他论述得极为精辟、独到:“诗人是为一般而搜求个别,还是从个别中看出一般,这之间有着天壤之别。从第一个过程中诞生了寓言,它把个别只当作服务于一般的例子;而第二个过程才真正是诗歌的本质:它表现了个别的事物,并没有想到一般或指向一般。”(20)歌德的这一观点被柯勒律治发挥得淋漓尽致:“关于这一话题最重要的一点是,寓言不得不有意识地叙说;而象征表明,真理无意识地存在于运用象征的作家心里。与寓言相比,象征性作品的优势在于,它要求的不是各种能力的分离,而是纯粹的驾驭。”因为“寓言把现象变为概念,再把概念变为形象。然而,这样的结果是概念仍然是有限的,并完全包含在形象中,为形象所表现;而象征把现象变为观念,再把观念转化为形象,其结果,观念就会永远无限地活跃在形象中,并且不可捉摸,尽管言有迹却意无穷。”(21)
不难看出,上述几段富有代表性的评述都有一个共同点,即把寓言作为提倡者宣传物(如理性、灵感、个别、无意识等)的对立面而加以抨击,而且有意思的是,观点相左者在攻击寓言上却成了盟友:鼓吹理性的柏拉图视寓言为恶瘤,而推崇无意识的柯勒律治更以抨击寓言为能事。这说明寓言的身上肯定存在着某种相反而相成的品质,否则它不至于如此腹背受敌。这种相反而相成的品质就是寓言的双重性:一方面,它追求“言”,即文学性的表述;另一方面,它的指归却在“意”,一种观念性内容。直观地说,就是“设言托意,或咏桑寓柳”(22)。其结果,寓言的这种双重性是两头不讨好:道德者流如柏拉图嫌其一叶障目,以文害理;艺术信徒如柯勒律治鄙其曲隐其意,大伤性灵。事实上,我们只要略加分析就能发现,批评者们对寓言所采取的共同策略是:击其一端而无视其余。他们对寓言的论述并非建立在全面考察之的基础上,因为他们有着强烈的目的,就是要宣传各自的艺术观或哲学观。这样,他们对寓言的复杂性就自然不会详加细究,而只能偏执于一解了。
然而,真正给寓言以全新阐释的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理论家W.本雅明。他不但把寓言从浪漫派单纯的二元对立式理解中解放出来,而且还赋予它以新的内涵。本雅明认为,从本质上讲,寓言是一种“底本”。不同于象征所强调的个别与普遍的有机统一,寓言只是以自身为底本形成一个理解的多样性,以便产生各种可能的理解副本。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寓言体现了一种从象征的和谐、统一走向无序、多元的过程。从时间的角度看,象征是“瞬间的、抒情的、非延续的”(23),而寓言则试图把残存在时间碎片里的意义艰难地复位。由于工业文明的无情摧残,人与自然、精神与物质之间的和谐关系早已荡然无存,一切似乎变得支离破碎、残缺不全。在这样一个处处残垣断壁、呈现颓势的现代社会中,再提倡表现和谐统一关系的象征就难免不合时宜,相比之下,寓言则更能捕捉社会衰败期的特征。在此,本雅明表面上客观的描述并没有掩盖他对寓言的偏爱。我们在其作品中经常可以看到他一往深情地使用“葬礼”、“尸体”、“废墟”这类词,并把它们与寓言联系在一起。例如,他说,“思想领域的寓言就等于物质世界的废墟”(24)。当我们读到他的“只有在痛苦和衰败时,历史才有意义”,“历史的意义跟死亡率和衰败力正好成正比”(25)这些话时,我们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对寓言情有独钟。
把一种文学形式放在历史的纬度上来考察,并以其折射出历史意蕴的厚度来判断艺术作品的质量,这是本雅明理论的高瞻远瞩之处,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作品的深度所在。深谙法兰克福学派著作的詹明信对此早已心领神会,并把这种分析方法自如地运用到了他的作品里。然而,詹明信不同于他所景仰并论述过的几位大师的是,他在历史的这一纬上,添上了政治性之经。这样,在历时性上,詹明信以历史性为纬;在共时性上,使用政治性作经。特别是对后者的强调,可以使我们毫不迟疑地得出结论,詹明信的美学是一种政治阐释学。关于这一点,詹明信用他那雄辩得令人难以置疑的论述为我们提供了例证:“本书(指《政治无意识》)将论证文学文本政治性阐释的优先权。它认为政治性透视不是某种补充性方法,也不是当今流行的其它阐释方法的附庸——如精神分析、神话批评、风格分析、道德阐释或结构分析——而是所有阅读与理解的绝对基点”(26)“……事实上,所有一切归根到底都是政治性的”(27)。在他的这部代表性作品中,詹明信用无懈可击的叙事分析阐述了文学性文本政治性阐释的第一性,从而为马克思主义阐释学增加了一个新的理解维度。同时,由于这部作品在美国的经典性地位(28),它的“典型性”(乔纳森·卡勒语)(29)影响波及整个西方,甚至中国。然而,我们不禁要问,提倡文本的政治性理解的詹明信为什么在形式上如此推崇寓言呢?换言之,寓言跟政治到底有什么关系?或者更进一步说,寓言与马克思主义批评有什么内在联系呢?
就后一个问题而言,西方文论界似乎认定,任何马克思主义式阅读从根本上讲是寓言式的。因为马克思主义从来就不把文学性文本视为纯粹的文化产物,马克思主义批评毫不掩饰它是带着目的去发掘作品的意义的。恩格斯在谈论巴尔扎克时所说的一段话颇具有代表性。他认为,巴尔扎克的作品提供了“关于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从中我得到的知识比从所有自封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所提供知识的总和还要多,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也是如此。”(30)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进而明确地提出了“文艺为工农服务”的方针。因此,无论从作品到读者的接受上讲,还是由作者为读者而创作这一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文艺观都要求毫无条件地凸现一种目的性:即要求作品有意义,而寓言的设言托意正好满足了这一要求。当然,如果我们按照柯勒律治的划分,把所有的批评家都分为两类:一类是注重客观形式分析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者;一类是宣传道德教化的柏拉图主义者。那么,我们就不难理解“兰色姆用柏拉图主义一词来指道德批评,这种批评把形式与内容分离,如新人文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作品。”(31)同样,法国理论家托多洛夫在《散文诗学》一书中指出,存在着三种阅读方式:投射型(读者把一种理论强加给文本,如马克思主义或弗洛伊德主义者);评述型(阐发、细读)和诗学型(研究那些体现在文本中的普遍规律)(32)。很明显,投射型阅读基本上属于一种主观的、内容的、六经注我式阅读,也即柯勒律治意义上的柏拉图主义者;而评述型、诗学型大致可归为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因为他们注重修辞、风格、范式等形式的因素。事实上,无论是19世纪的柯勒律治,还是当代的新批评干将兰色姆和结构主义大家托多洛夫都在他们貌似客观的划分背后,隐藏者明显的个人倾向。他们一致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阅读方式是外在的、主观的、武断的,因而也就是非审美的、反艺术的。在詹明信看来,这种观点自然不堪一击,因为任何形式主义的分析如果不跟历史、政治、文化等嫁接起来,都只不过是无源之水、无根之花,表面上的精致并不能掩饰衰竭的归宿。但是,无论是兰色姆说马克思主义看重形式与内容的分离也好;还是托多洛夫说马克思主义把理论强加给文本也好,他们有一点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这两个特点正好与寓言的两个特征不谋而合,即与“分离”相一致的寓言的“断裂性”和与“投射”相关的寓言的“复义性”。这样,我们就比较好理解为什么马克思主义批评与寓言有一种内在的契合。
詹明信看重寓言,主要因为他认为寓言的“断裂性”更能涵盖当今的文学特征,这方面他受阿尔都塞的影响至深。“显而易见,在黑格尔式的因果关系中,文学作品便会成为一个和谐的有机体,由一种精神结合在一起。而今天的观点受到了阿尔都塞的模式的影响,文学作品好像不是统一的,而是由相互矛盾的、相互区别的不同层次组成的。艺术品不再是一有机的整体,而是由分裂、距离、相异性和间隙组成的游戏”,因此,詹明信断言,“当代理论中的一个趋势是放弃传统的关于象征的概念,而认为寓言性是文学的特征。”(33)
此外,法国理论家米歇尔·福柯的观点也有助于我们理解詹明信为什么始终不渝地坚持其寓言性阐释方式,而不管对象是第三世界文本,还是后现代文本。在评论尼采的《道德的谱系》时,福柯写道:“只有当历史在我们本身的存在中引入断裂性,它才变得有效,因为它使我们的感情分离,使我们的天性戏剧化,使我们的身体多样化并使其与自身对立。……有效史(effective history)把传统的根基连根拔起,并且无情地摧毁它那虚假的连续性。这是因为知识并不是用来理解的,而且用来切割的。”(34)福柯的论述非常准确地描述了詹明信寓言式阅读的特征。无论是对鲁迅的《阿Q正传》的分析,还是对蒲松龄的《画马》的阐述,他事实上都是用他的知识在“切割”文本。从《画马》中,他得出结论,“这个故事可以说是对货币这一现象的艺术思考”(35),他提出,“阿Q是寓言式的中国本身(36),这些都表明,他的分析非常精辟,而且也极为“有效”。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詹明信的这种断裂式切割往往容易导致断章取义的理解,这也是他的阐释学遭到非议最多的地方。对此,詹明信本人可能不以为然,因为他认为寓言的另一个基本特征确保了他阐释的合法性。
这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寓言的另一特征,即它的“复义性”。自从威廉·燕卜孙系统地阐释了诗歌的复义性之后,人们普遍地认识到,文学作品的意义不是单一的、绝对的。其实,对文学作品多重理解的看法,在中国古典文论中也相当普遍,如当谈到对屈原作品的理解时,刘勰就指出:“故才高者菀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辞,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37)而寓言性作品正好为这种多样性理解提供了基础,因为寓言的本质是“暗示性”的,是一种“转换”,一种“翻译”(38)。对詹明信来说,寓言的这一特征无疑至关重要。他之所以置象征于一旁而不顾,是因为象征的那种——对应关系根本束缚了理解的翅膀,而寓言的多义性为批评家提供了更为开阔的阐释空间。尤其当阐释者把政治、文化、经济、历史等因素熔于一炉而运思立论之时,寓言的多义性就更为关键了。因为政治、文化、经济、历史等因素与表现为形式的文学性成分并不“兼容”,如何使它们“同构”,这就需要“翻译”,而“翻译”的首要前提是该作品必须具有可译性。毫无疑问,对詹明信来说,寓言性作品的可译性最强。因此,这类作品自然成了他分析的重点。然而,这不啻又是詹明信的致命弱点,因为他把他分析得最有效的作品普遍化了。换言之,寓言性作品虽然有着多重的意义底蕴,并更具有审美价值,但在每个时代,寓言型作家毕竟是鹤立鸡群、凤毛鳞角。而且寓言型作家本身所要求的素质根本限定了他们的数量。在《叙事的本质》一书中,罗伯特·斯科勒思和罗伯特·凯罗格总结了寓言型作家应有的素质。他们认为:“他们(指寓言型作家)的共同之处是文学知识精深渊博、语言能力卓然不群;他们对白话诗文娴熟自如,一则得益于自然天赋,一则来源于苦学强练。对他们来说,思想观念与叙事艺术双峰并峙,互为映托,交相生辉。”(39)尽管他们的结论来源于叙事诗人斯宾塞和但丁,但综观庄子、卡夫卡、托马斯·曼、鲁迅等文坛巨匠,我们认为,真正的寓言型作家非旷世奇才莫属,因为寓言性的本质要求思想与审美的珠联璧合、理性与感性的水乳交融,而真正能臻于这一境界的作家确实微乎其微。多数作家审美有余而思想贫弱,思想家则观念余裕却美感枯竭,大多数寓言或病于骨多于肉,或弊在枝不胜叶。这就造成了对寓言的众多攻讦。而詹明信的问题在于,他撇下众多劣等寓言型作家不顾,而把最优秀的几位寓言型作家,如鲁迅、托马斯·曼等的创作经验加以泛化,这就造成了他立论的偏颇之处。
综上所述,詹明信提出第三世界文本的表现形式是民族寓言的论断一方面是出于他辩证思维和“整体论”的需要,但更重要的是,他试图从文学形式中探讨出孕育其后的政治性内涵。他的尝试虽然不尽如人意,但他探索的转迹为我们标志了一个新的方向,即如何把形式分析与意识形态分析熔于一炉,从而揭示出文学中更为本质、内在的东西。
注释:
[①] Jameson,Fredric,The Geopolitical Aesthetic,Bloomington,Indeana UP,1995,p.xiv.
[②] 王逢振《今日西方文学批评理论》,漓江出版社,1988年,第11页。
[③][⑥](23)(24)(25) Jameson,Fredric,Marxism and Form,New jersey,Princeton UP,1971,p.399,p.182,p.72,p.71,p.73.
[④][⑦](33)(35) 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2、96、77、114页。
[⑤][⑨][⑩](11)(12)(36) 杰姆逊《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见《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张京媛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第233、234、240、235、239、239页。
[⑧] 卢卡契《历史与阶级意识》,张西平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23页。
(13)(18) Honig,Edwin,Dark Conceit:The Making of Allegory,Oxford UP,1966,p.6,p.8.
(14) Abrams,M H,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Holt,Rinehart and Winston,Inc,1957,p.4.
(15)(21) Coleridge,S.T.Miscellaneous Criticism,ed,T.M Raysor,London,1936,p.30,p.29.
(16)(17)(20)(38) Fletcher,Angus,Allegory:The Theory of a Symbolic Mode,Ithaca,Cornell UP,1964,p.237,p.2,p.13,p.2.
(19)(31) Adams,Hazard,ed.,Critical Theory Since Plato,HBJ,Inc.1971,p.415,p.8.
(22) 曹雪芹、高鄂《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138页。
(26)(27)(29) Jameson,Fredric,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Narrative as a Socially Symbolic Act,Ithaca,Cornell UP,1981,p.26,p.27,on the cover.
(28) Kronic,John,PMLA 1991:vol.106,No.2,p.203.
(30) 《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美学》,杨柄编,文化艺术出版社,1982年,第556页。
(32) Todorov,World Authors 1980—1985,p.847.
(34) Foucault,Michel,"Nietzche,Genealogy,History",Language,Counter Memory,Practice:Selected Essays and Interviews,ed.,Bouchard,Ithaca,Cornell UP,1977,P.154.
(37) 刘勰《文心雕龙校注》,杨明照校注,中华书局,1962年,第27页。
(39) Scholes,Robert & KelloJJ,Robert,The Nature of Narrative,Oxford UP,1966,p.108.
标签:文学论文; 世界文学论文; 寓言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文化论文; 艺术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读书论文; 作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