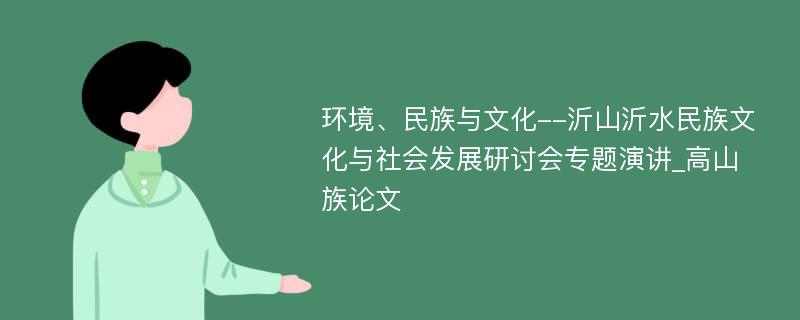
环境、族群与文化——依山依水族群文化与社会发展研讨会主题讲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水族论文,讲演论文,族群论文,文化与论文,研讨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887(2003)02-0002-05
乔教授、黄校长、林委员、童院长,各位同仁、各位女士、先生,很高兴又有机会来东华大学参加这个学术会议,也很荣幸被邀作主题演讲,更高兴能在东华见到从大陆来的几位我很熟悉的人类学同仁。依山依水族群文化与社会发展的题目立意很好,只是我个人对依山依水族群这样的题目并没有很深刻地去思考,而且这几年我年纪大了,身体不好,做田野也非常少了,也没有什么新的材料可以提供出来。因此,今天我只能从我自己以前做田野的资料作一点综合,并配合一些旧理论做架构,提出一个看法,勉强把它当作这个会议的一个引言吧!
一
这次会议的主题“依山依水族群”是一个非常好的比较研究切入点,一个作不同民族文化比较研究的切入点。从我自己的田野经验来说,我想引用两个架构模型来谈一点看法:一个是小区域的模型,另一个是比较宽广的大区域模型。小区域的模型是就台湾岛内的族群资料所建构而成。我在台湾前二十年做的田野是以台湾南岛民族(高山族)为主(注:在台湾目前已将高山族改称为“原住民”,这是一种政治上的名称,学术界并不完全赞同,从考古学的发现而言,在高山族移入台湾之前,已另有居民,而高山族并非最早居于台湾之族群,所以称之为原住民是不对的。而从族群平等的立场上来说,有“原住民”一词,就相对的会出现“非原住民”(指汉族而言)的想法,将来就易于产生土地主权之争,这是在美洲各地常见的现象,所以学术界较倾向于采用较合适于作为族群专有名称的“台湾南岛民族”一词,以取代“原住民”,以及族人不甚喜欢的“高山族”一词。)。那时我正是年轻的时候,可以随意跑山地,所以台湾南岛民族十族我都跑过,但真正只做过五个族的田野,时间长短不一样。这五族是阿美、泰雅、排湾和雅美,另外一个是大家都不注意的,也就是日月潭的邵族。[1]~[5]大家都知道这五个族中,阿美族当然也可以说它是靠海的,但未必都在海边,可以说它是比较近水的民族。雅美族是最典型的依水民族了,是一个居于小岛—兰屿的族群。泰雅族则是最典型的依山民族,他们居住的山比较高。排湾族也是依山的,但他们居住的山不如泰雅族那样高。邵族是最特别的一族,它不是依海边,而是依日月潭,可以说是一个湖居的民族,因此也可说是依水的族群。所以我做过田野的这五个族,假如用今天的主题来分的话,是三个依水,两个依山。阿美族靠着海边,打鱼没有问题,即使不靠海边的部落,打鱼也是他们很重要生活的基础。雅美族是个小岛民族,它不但打鱼,而且整个生活、宇宙观、时间观都跟海和鱼连在一起。邵族最特别,它原来跟布农族或邹族差不多,是一个依山民族。后来因为迁到日月潭附近,在1938年的时候,由于日月潭的水位升高,他们更加依赖日月潭,变成一个打鱼的民族。邵族对水的适应非常特别,1954年我在日月潭进行经济问题调查时,发现他们除开正常的打鱼以外,还有一种跟水有关的很少见的、很特别的设计,那就是台湾旧方志中常有记载的“浮屿”。所谓“浮屿”就是用竹子编绑成的竹排放于潭边。根据多种方志的记载,邵族人的祖先把泥土铺在竹排上,并在上面种植水稻,这可以说是一种很巧妙地利用湖边生态的生产设计,所以称为“浮屿”。但是也有一些方志不认为“浮屿”可以种稻。我自己做调查的时候,“浮屿”仍然常见,但只是捕鱼的另一种工具,那就是族人在竹排上种了水草,并放置鱼篓,等鱼跳上来产卵时,就可以捕捉到鱼。我在做田野时,有些报导人说古时候确曾在“浮屿”上种稻,有些人则说那只用来捕鱼。不过根据判断,水稻的传入很晚,在方志记载的康熙年间,应该尚未有水稻的种植,相信其实也只是一种捕鱼的设计而已,不过,不管是否种水稻,这种“浮屿”总是邵族人的一种特别依水生活的巧妙适应方式。邵族人目前也因住在日月潭边,所以靠观光的收入维生很重要,可以说是另一种依水的生计方式。[5](P59~61)
就上述我所做过调查的五个台湾南岛民族的生态环境而言,可以做成如下的分类:
一、依水族群:阿美族(居住海岸)、雅美(岛居)、邵族(依湖)。
二、依山族群:泰雅(深山)、排湾(浅山)。
其它我未做过田野的五族,则有布农、邹、赛夏和鲁凯等四族是依山族群,只有卑南一族是依水的。这样把十个台湾南岛民族的生计环境介绍之后,大家也许就要问他们的社会组织与宗教信仰又是怎样呢,是否也与他们的依山依水情况有所配合?换而言之,就是要问这种依山依水的背景影响其它文化面向的情形如何,这也就是本次研讨会最根本的主题所在。
要回答上面的问题,请让我就我早期的一篇讨论台湾南岛民族的社会宗教形态的论文说起。1962年我在出席一次学术研讨会时撰写了《台湾土著民族的两种社会宗教结构系统》一文,[6][7]在该论文中我以阿美族与泰雅族为例,分析台湾南岛民族中有两种社会宗教结构范式,一种是阿美族所代表的在社会结构及宗教信仰与组织上都具明显的阶梯系列的观念形态;另一种则是以泰雅族为代表,其社会组织与宗教系统都属较平等而无阶梯观念的型态。我的这一分类理念其后又为现任中研院民族所所长黄应贵先生加以扩大延伸,黄先生不但把九个台湾南岛民族都包含进去。而且借用美国芝加哥大学人类学家Marshall Sahlins有关大洋洲各群岛民族的社会组织分类名称予以套用。下面是黄先生的分类方式:[8]
(A型)酋长型chief societies(阶梯组织形态):阿美、卑南、鲁凯、排湾、邹族。
(B型)大人物型big-man societies(平等组织形态):泰雅、布农、雅美。
(赛夏族属中间型;黄文中未列邵族,惟邵族应属A型)
假如我们把黄应贵的这一个社会组织分类与上面以依山依水的环境生态分类做比较,大家也许期望两者配合得很好,也就是说依山依水与阶梯平等两组形态扣连得很对称,那么我们这个讨论会就会很有意思了,可是事实上并非如此,我们可以看出,依水的主要两族阿美和雅美分别具有A型与B型社会,而依山的泰雅与布农属B型,而排湾、鲁凯及邹族则属A型,真是不凑巧!
不过大家不要泄气,情况不是那么简单,而且假如是这样凑巧的话,我们人类学家也许就没有饭吃了,而只要地理学家就行了。地理学家是研究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而人类学家与地理学家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那就是我们在人与自然之间加入了文化。人类学家之所以被称为人类学家就是因为他们不仅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还研究人与文化的关系。上述的两个系统,不能够完全百分之百地或者非常漂亮地把环境跟文化完全扣连对称,应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人与环境之间不是这么简单的关系,假如是这么简单,人就不是人而是动物了。这是因为我们有文化,所以影响生计的虽然与依山或依水有密切关系,但是社会组织、宗教信仰就不一定有那么密切的关联,这是人类学家最根本的一个认识。我做过田野的台湾南岛五族,每一个族都有它的文化来作为跟环境之间的缓冲,进而适应或改变环境。这是因为文化跟环境之间以及跟人之间是互动的,是一种辩证的关系。文化是以人为主,人可以适应环境(adapt to environment),但是也可以改变环境,更可以用自己的文化来创建新的环境。所以我们在谈依山依水这个题目时,不要很快地就陷入环境决定论的胡同,我们必须要体会人类学的研究,文化才是我们思考的关键。最重要的一点,作为人类学家我们要研究文化怎样在环境跟人之间互动,造成人的适应,不需要像动物那样改变身体的器官来适应环境,而是用文化来改变并创造环境。总之我的立场跟大家一样,虽然以依山依水为题,但是要探讨的不单单是环境与人群的关系,而是环境、族群与文化之间的互动、辩证关系。
二
我今天要谈的第二部分就是所谓较大架构的模型。我自己平常以台湾为最主要的研究对象,不管研究南岛民族还是汉族,都以台湾为主。但是我的视野经常受到其它有关的人,我的老师、我的朋友的影响。我的老师已故的凌纯声教授是一位太平洋专家,所以我的视野也远及于太平洋,今天我所说的大架构模型,也就是以整个太平洋为背景。
其实在太平洋这样大的范围里,我并没有能够真正做很多田野,只在马来西亚、婆罗洲、菲律宾做过田野。所以较不容易有我自己的田野资料提出来讨论,也许可以利用前面提到过的Sahlins教授的酋长与大人物分类为例来作再一次的说明。按照Sahlins的说法,所谓有阶梯型态的酋长社会多见于玻利尼西亚群岛(Polynesia),而平等的大人物社会则在美拉尼西亚群岛(Melanesia)较多见。如以我们的依山依水观念来说,前者多属于小型的珊瑚岛,应该是近于依水;后者属大岛(如新几内亚岛),应是近于依山。依山的大岛应该较易于发展成阶梯的酋长型社会,可是情形却是相反的,可见问题并不是可以简单解释的,而是要更有系统地去把握才对。[9]假如要更深入地去了解文化如何在人与环境之间发生作用,也许可以从东太平洋诸群岛转到西太平洋诸岛及半岛区的例子来看。西太平洋包括印度尼西亚群岛、婆罗洲、菲律宾及马来半岛等地区。这一带是经过不同宗教的影响、也经过不同殖民地的影响,但是这一带有很多共同的地理跟气候的因素,所以假如把这些因素加起来,比东太平洋岛上的分类要更适合于我们作为一个模型来看待依山依水跟族群文化之间的关系。今天因时间不多,我不能引太多的例子,只是引用一个我较熟悉的婆罗洲的例子。我自己在1963年曾去婆罗洲做过调查,我调查的地方在婆罗洲的第二区,叫拉让河(Rajang R.)的一个流域。[10]但是我今天要用的例子却是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同事蒋斌先生做的一个调查。
蒋先生在砂劳越第四区的Baram河流域做调查,他提出的一个架构,跟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依山依水观念有非常的相似性,可以用来作例子说明在依山依水的生态环境下,族群关系的文化展现模式。蒋先生研究的砂劳越Baram河流域居住的不只是一个民族,而是有一系列的民族。在Baram河最上游的高山上,住的是Punan族,他们是山田烧垦的民族,同时也是擅长上山打猎的民族,所以是典型的依山民族;在中下游居住的则有Kayan和Kenyah两族,他们可以说是半依山半依水的民族;最下游则是典型的马来人(Malays),他们是依河边或海岸而居;最后是居住于市镇内,大都业商的华侨。这一系列的民族构成一个很有趣的谋生与商业交换关系,因此也打破了他们原有的依山依水单纯的生计方式。原来自明代中期以后,华人来到砂劳越,他们最喜欢砂劳越河流上游山洞中的燕窝。大家都知道,燕窝是我们中国人食物中的珍品,价格很昂贵。但是燕窝要在山洞的顶壁上采集,所以只有靠惯于攀爬山壁的Punan人去采集。中国的燕窝市场很大,所以Punan的男人就把采燕窝变成他们主要的生计,当然这也可说是依山而成的。但是Punan人采了燕窝却不是直接卖给华侨,而是经由中游的Keyan和Kenyah作为中间人才卖出去的,而这两族人也因作为燕窝的贸易,一方面与上游的Punan人建立主雇关系,另一方面又与下游的马来人建立亲戚伙伴关系,并藉此把燕窝交易出去,以取得瓷器、钱器及珍贵金银珠玉饰品回来。而马来人才是最后把燕窝转卖给城市里视之如珍品的华侨商人,从而完成了这个长系列的交换系统[11]。从这一例子看,我们可以很明白地说,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不仅有文化来作为适应的工具,而人又是成群而居构成系列的关系,这种系列互补有无的关系,也是人类适应、转换或改变环境对自己束缚的重要机制,这也就是我要对本次研讨会提出来的第二个论点。
总之,依山依水这一论题不是一种简单地理环境决定论,而是要把它看成是文化与环境之间互动所构成的一个系统来讨论;而且人类学家也不把依山依水看成是单独的或两个对立的环境体系,实际上,山与水之间也可以形成互补的因素,端赖族群之间如何加以巧妙地运用。
三
前面两部分我提出在这个依山依水的讨论会中,不应该机械式地看环境与人的关系,而应该把握人的文化如何作用,以及人类社群如何构成互动互补的系统两种观点,但是这样的观点其实也不是我自己的创新,文化的概念固然是每一位人类学家都了然于胸的,即使是社群或族群系统的观念,也不是我或蒋斌先生最先提出的。在东南亚区域中,提出族群系统观念的,大家都知道是英国人类学前辈Edmund Leach先生,他是在研究缅甸北部克钦人(就是我们中国的景颇族)时提出来的。克钦人跟掸人、跟缅甸人之间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系统,民族不同,但是互相交易,不但互相交易,也互相通婚。在这区域系统里,娶妻一定要从地位高的族群来,嫁女儿一定要往下嫁。这也就是著名的联姻理论中,所谓不对称婚姻交换制度的源起之处,这也就是使Leach先生的那一本《缅甸高原的政治系统》(Political System in Highland Burma)的书成为经典名著的原因。[12]这就是说我们做研究的时候,不要把它当作单一的一个民族来看,而要把它当作一个系统或者一个区域来考察。我们回过头来再看依山依水的论题,假如从单个民族来看,台湾的分类实际上谈不出什么特别的意义,但是把它看成一个系统则依山依水互补构成一个民族与其它民族的关系网,就会使我们能从整体的文化脉络中理解出人群与环境的真实关系。
其实,最后的这一节中,我不仅是要说出像Leach先生的缅甸克钦人研究的这种国外经典著作,而是要对与我们讨论会主题密切相关的所谓“文化生态学”(culture ecology)的发展做一简单的介绍,以为大家讨论的参考。人类学的重要理论所谓文化生态学(culture ecology)是整个人类学主流理论的一部分。所谓文化生态学是美国学者Julian Steward首先提出的观念,他在1955年有一本著名的书《文化变迁理论》(Theory of Culture Change),[13]即是文化生态学的古典名著,其着重点在于探讨一个特定的族群如何在一定的地理区域内有意无意地调适、改变其居住的环境,并进而影响其文化与其经济、社会及宗教生活的过程。其后研究环境与文化关系的学者虽对文化生态愈有更精细的推进,但其主要目标大致总在这一范围之中。在20世纪60年代~70年代,生态研究的人类学者引进生物学的观念模式并注重于量的计算方式,对热带地方的山田烧垦生计与环境及人类不同文化行为的互动综合研究至为兴盛,因此有许多新观点的提出,包括生态系统(eco-system)、民族科学(ethno-science)、族群生态学(ethno-ecology)、人类生态学(human ecology)、行为生态学(Behavioral ecology),以至于生态人类学(ecological anthropology)等等。[14](P25~53)后一名词是美国密西根大学教授Roy Rappaport所提出的,他以研究新几内亚高地土著的烧垦农业、猪只畜养与定期性祭仪以及战争之间平衡关系而著名,[15]影响所谓生态人类学式的研究风行一时。这些生态人类学或文化生态学的理论以及其相关的民族志研究的参考,对我们依山依水族群文化探讨都有相当程度的裨益。然而前此人类学家都较偏于小型社群的研究,近年来则渐转变趋向于较复杂、甚至于国家社会的研究,因此又有“历史生态学”(historical ecology)或“政治生态学”(political ecology)的出现[16],更近年且有以全球系统的观点而探讨全球性生态均衡的“全球生态学”(global ecology),或以土著文化的观点要求以当地文化为发展的“旅游生态学”(Touristic ecology)之出现,也是值得注意的现象[17]。在这一次依山依水研讨会中我看到广州中山大学的邓启耀教授关于摩梭族文化与泸沽湖生态保护的论文,十分高兴,因为这就是属于当代生态人类学最新发展的一种研究[18],很值得大家注意,这也是本研讨会题目中显示的所谓“社会发展”的意义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