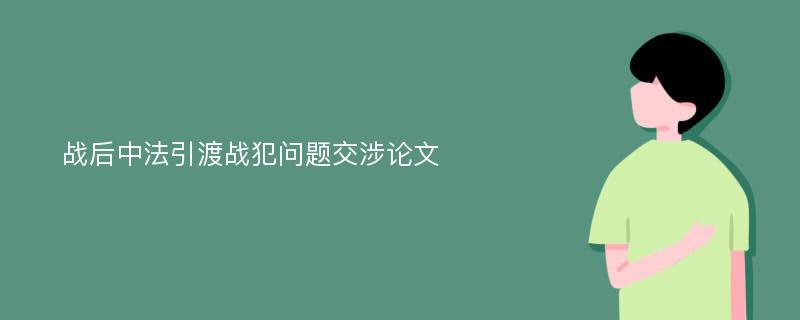
历史学研究
战后中法引渡战犯问题交涉
刘 萍
[摘 要] 1944年1月,联合国战争罪行委员会成立后,制定了近代以来国际社会第一份战犯引渡公约——《解递战事罪犯及其他战事违法人犯公约》,公约剔除了传统引渡制度中“政治犯不引渡”的条款,以保证对战犯的彻底追究和惩治。二战结束后,中法两国达成以该公约为相互引渡战犯依据的协议,在处置战犯问题上从冲突走向司法合作,保证了战犯审判的顺利进行。中法两国在引渡战犯上的初步实践,较为全面地诠释了公约的主要原则和精神,也开启了现代国际社会通过司法合作惩处战争犯罪的先例。同时也是废除治外法权后,中国政府处理外交事务的一次成功案例,对于当今社会处理国际事务富有启迪。
[关键词] 战犯;引渡;审判;中国;法国;联合国战争罪行委员会
引渡战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处置战犯的重要环节,也是近代以来国际社会对重大国际犯罪进行彻底惩处的初步实践。二战期间,为在战后对法西斯战争暴行进行彻底惩处,中、英、美等17个同盟国家组成联合国战争罪行委员会(United Nations War Crimes Commission)① 此处联合国与1945年后成立的联合国并不同义,应为联合国家。 ,起草了《解递战事罪犯及其他战事违法人犯公约》,成为近代以来国际社会制定的第一份战犯引渡公约。《公约》明确规定战争罪犯不属于政治犯,不得援用“政治犯不引渡”的原则,从而保证了战后审判的顺利进行,在国际法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虽然因种种原因,该《公约》未能在联合国战争罪行委员会通过,但仍然成为战后盟国间引渡战犯的重要依据。战后引渡战犯的实践,开启了现代国际社会通过司法合作惩处战争犯罪的先例。战后中国和法国间引渡战犯的过程,较为全面地诠释了《公约》的主要原则和精神,在引渡战犯中具有典型意义,对于全面认识和理解《公约》及战后处置战犯问题的多面性及复杂性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中法两国在处置战犯问题上从冲突走向司法协助的过程,是废除治外法权以后,中国政府在恢复外交主权过程中处理外交事务的一次成功案例,对于当今社会处置国际事务也富有启迪。
一、 引渡战犯公约
国际间引渡罪犯,系国家之间刑事司法互助的一种形式。引渡活动古已有之,公元前1280年,古埃及与赫梯帝国签署的和平条约中,曾经引入引渡逃犯的条款。但直至近代,引渡制度才逐步发展成熟。1625年,国际法的鼻祖格老秀斯认为,违反自然法的犯罪是对整个人类的犯罪,各国对惩处这类犯罪均负有普遍义务。从这一观点出发,他提出了著名的“或起诉或引渡”的原则。1794年,美国和英国签订《杰伊条约》,明确规定相互间将遣送一切被指控在各自管辖范围内犯有杀人或伪造罪的罪犯,被认为是现代引渡制度的滥觞。随后,欧美各国为打击犯罪的需要,相互间签订了一系列双边和多边引渡条约。随着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发展,特别是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爆发后,大批革命党人流亡国外寻求庇护,各国在引渡法或引渡条约中逐渐增添了保护政治犯的条款,避免将引渡作为政府迫害政治犯罪的工具。1783年法国宪法第120条规定,法国给予为了争取自由而从本国流亡到法国的外国人以庇护。1833年,比利时制定的《引渡法》中,明确禁止引渡政治犯,成为近代第一部明文规定禁止引渡外国政治犯的国内立法。1843年,法国与比利时签订引渡条约,第一次引入“政治犯不引渡”条款。① [英]劳特派特修订:《奥本海国际法》(上卷,第1分册),王铁崖、陈体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185—186页。 此后,各国在立法和实践中都明确肯定了“政治犯罪不引渡”的原则。但这一原则在保护人权的同时,也给予罪犯以“政治庇护”为由逃避罪责之机,造成国际犯罪不能得到惩处。这一弊端在第一次大战后对战犯的审判中暴露无遗。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同盟国拟组织战犯法庭对战争罪犯进行审判,但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元凶、德皇威廉二世逃避荷兰,荷兰以政治犯不得引渡为由拒绝引渡,从而使战后审判最终成为一场闹剧,不了了之,也埋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祸因。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对战犯的惩处再次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一些国际组织开始从法律上探讨战犯的引渡问题。
1942年初,伦敦国际大会上,清算战争问题委员会向大会提交了一份由比利时代表起草的报告,提出为了避免战犯以各种方式寻求庇护,建议缔结一项关于盟国(军)间交出战争罪犯的特别公约,最终由中立国签署或加入;或者与中立国签署一项单独的临时协议。如果有必要,联合国家应采取一致行动,施加压力,以促使中立国交出战犯。② UN War Crimes Commission,The History of the United Nations War Crimes Commiss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aws of War,London: H. M. Stationery Office,1948,p. 394.
1943年9月,意大利投降后,处置战犯问题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为了避免战犯逃往中立国寻求庇护,美、英、苏三国磋商后认为,应向中立国发出照会,禁止庇护战犯。随后英国向葡萄牙、瑞士、巴西、西班牙、瑞典和梵蒂冈发出了如下照会:“鉴于意大利的形势发展,墨索里尼及其他重要法西斯头目,以及犯有战争罪的人,可能向中立地区寻求庇护。英国政府认为,有义务呼吁中立国拒绝向上述任何人提供庇护请求,并呼吁他们发表声明,表示凡为战犯提供避难所、任何协助和保护的行为,皆违背联合国家竭力实现的原则。”紧随英国之后,美国、苏联也向中立国发出了相同内容的照会。③ Extract from a Debate in the House of Lords on the Subject of the Treatment of German War Criminals( 7th December,1943 ),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惩处德国、日本战犯问题》, 020/010117/0055,台北“国史馆”藏。
1943年12月7日,英国上议院讨论处置德国战犯问题,上议院议长西门代表政府发言指出,允准避难者进入国境是任何主权国家的权利,没有绝对的条约要求这些国家必须驱逐避难者,除非签署引渡条约。④ Extract from a Debate in the House of Lords on the Subject of the Treatment of German War Criminals( 7th December,1943 ),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惩处德国、日本战犯问题》, 020/010117/0055。
越北日军战犯被押解到广州后,法国政府又向中国政府提出:将战犯引渡至越南,由法国自行审判,或由法国派人参与中方审判。8月12日,法国大使馆在致中国政府外交部节略中声称,在越北“被逮捕之日本战犯,其犯罪地点既系在越南境内,彼等似应于审判之前或至少亦应于审判之后,移交法国当局”。并进一步提出,“如中国当局于终审时拟自行判决此等罪犯,至少亦应准许法国代表列席法庭参与审判,以便提示被告之罪行”。⑤ 《法国大使馆致中国外交部313号节略译文》(1946年8月12日),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战俘审判与惩治》, 020/010117/0040。
Department of Cardiac Surgery,Bangabandhu Sheikh Mujib Medical University,Shahbag,Dhaka 1000,Bangladesh.
《公约》共13条,当中最重要的内容,是明确了战争罪犯非政治犯,不得援用“政治犯不引渡”的保护性条款。《公约》说明书明确说明:“本公约之用意,系在确保联合国家在其权力范围内相互解递被控之战事罪犯或‘基斯林’(叛国者),或已在此等罪状下被判处之人犯,同时以求以最便捷之方法获此结果,避免平时引渡程序所引起之繁复手续及延误。”特别强调,“尤其是去除任何一方可能借口此类罪行具有政治罪行之性质而拒绝解递。”从上述目的出发,《公约》第三款明文规定:对战犯的引渡“应不顾任何借口此类罪行具有政治上之违法性质,而予以执行”。第四款规定:“请求解递之人犯,无论在任何状况之下,不得援用被请求国之引渡条约、法律或条例中所规定之司法程序。”其目的,即是彻底剔除对战争罪犯任何的保护性条款和司法保护程序,同时也避免因当事国所持的法律依据不同而使引渡搁置,以保障对战犯的审判顺利进行。
由于国际间引渡罪犯是一较为复杂的问题,不仅牵涉法律问题,某种程度也会牵涉政治问题,以及国际关系,而国际社会尚未制定统一的具有法律意义的国际引渡条约,故《公约》说明书强调,引渡战犯与引渡普通罪犯不同:“本约草规定之解递,系一种行政程序之结果,并非一法律程序之结果。”公约尊重各国之间签署的引渡条约,强调:“本公约乃系一种非常措置,除非本公约特有规定者外,并不影响各缔约国之间所订有之任何引渡条款之运用。”
五国司法部长起草的草案中,条款的适用范围不仅包括同盟国,也包括中立国及敌国。对于中立国而言,因牵涉复杂的国家主权问题,争议较大,英、美、苏发出对中立国的照会后,中立各国虽赞同其建议,但对其做法也提出了抗议,故公约取消了中立国。而对于敌国,由于同盟国已经开始酝酿在停战协定中插入交出战犯的条款,故均认为,敌国交出战犯的义务,应该按照各自在战后签署停战协定或和平条约来解决。最后公约的适用范围,只适用在同盟国家之间。从身份看,只适用于犯有违反战事法规或战事习惯的罪犯,包括叛国者和附敌者。同时受欧洲大陆法系的影响,基于刑事管辖中的属人原则,公约并规定,“各缔约国得拒绝彼此解递本国国民或以往之国民。”
公约第四款至第九款,详尽地规定了对战犯的引渡原则和规则,构建了较为完善的引渡机制和规范体系。主要内容为:1.缔约国相互引渡对于违反战争法规及习惯法之战犯,包括叛国者和资敌者。2.引渡之请求,应经外交途径提出,并须由被请求国适当执行或行政当局实行解递。3.要求引渡时,必须提供违法人员之姓名、国籍、外貌及被控罪状之说明,及该罪状可能处以的最高处罚;被控罪状之一切文件、相片及其他证物。4.缔约国对于要求解递之人犯,如其罪行系在该缔约国裁判权权限内所犯者,该缔约国得拒绝引渡。5.当两国以上缔约国请求解递同一人犯时,该人犯应先被解递至对其判刑最重之国家;当罪刑相同时,应先解递至最先请求之国家。6.被控违法人员可能判处之罪刑较请求解递之罪刑高时,在审判程序未终结前,被请求国可拒绝解递。7.死刑宣判应予执行,虽有缔约国请求引渡,亦不受影响;违法人员已为请求国之一判处死刑,则应由该国执行。上述条款,体现了对各国司法管辖权的尊重,但又不失灵活性。
该《公约》为保护被引渡者权益,又制订了相应的条款,要求请求引渡之国家,须以书面形式提出如下保证:1.审判将依司法程序举行;2.判决或预审判决及处罚,将在公开法庭宣告;3.被控违法人员在审判以前或审判之中应得到律师之援助。
在引渡程序上,公约摒弃了传统引渡中的繁文琐节,特别是影响引渡顺利执行的“双重犯罪原则”(principle of identity)。所谓双重犯罪原则,系指被请求引渡者的行为,依请求国与被请求国的法律,均构成犯罪的,方准许被引渡,有其中一国认为被请求引渡所指向的行为不构成犯罪的,则不能引渡。公约在基于战争犯罪是对人类的侵害,必须加以彻底惩处的原则下,将引渡程序简化,公约第一款即明确规定:“各缔约国互相同意按照以下规定程序,彼此解递在彼等裁判权范围内被控或被判犯有战事罪行之人犯,为俾予审判或执行判决之目的。此类违法行为,包括违反战事法规或战事习惯之行为,无论系在请求国裁判权范围而所犯,或系对请求国本身或其国民或武装部队所犯者。”① 以上所引均参见《联合国引渡战犯公约》,“中华民国外交问题研究会”编:《中日外交史料丛编(七)日本投降与我国对日态度及对俄交涉》,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66年,第503—510页。 即只要一方认为有罪,即可以引渡,不仅表明国际社会对战争犯罪予以彻底惩处的政治意愿,也保证了在战后的实践中,战犯审判的顺利进行。
战后,同盟国扩大了战争罪的概念,除普通战争罪行外,将违反和平罪和反人类罪也定义为战争罪行,盟国关于审判战犯的声明中宣布,施于平民的罪行,与文明国家理解的战争行为或政治罪概念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将战争罪、反和平罪与反人类罪均排除在政治罪之外。
鉴于同一战犯可能会被多个国家引渡,公约虽然规定了引渡的次序条款,即先引渡给处罚刑度最高的国家;如刑度相同,则以引渡的先后为序,但却没有规定具体的仲裁机构,在实际执行中难免引起冲突。1945年5月底至6月初,在伦敦举行的战争罪行委员会各国代表大会上,比利时代表提出了赋予委员会仲裁员权力的建议:“当一名被告人应联合国若干国家要求被列入战犯名单时,战争罪行委员会应当作为仲裁员,决定他将被移交给哪个政府”。该建议在大会上通过,并被纳入向大会提交的正式声明中。提案于1945年6月13日由总会审议,并得到了普遍赞同。随后通过了一项建议:如果一些国家要求交付战争罪犯,成员国政府应指定战争罪行委员会有责任作为仲裁员,决定战犯审判的顺序,或由委员会将其任务委托给其他机构。② UN War Crimes Commission,The History of the United Nations War Crimes Commiss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aws of War,p.409.
美、英虽力主制定交出战犯的条款,并也主张签署引渡条约,但《解递战事罪犯及其他战事违法人犯公约》制定后,两国却以各种原因拒绝签署。美国以条约第四款,要求引渡之战犯,“无论在任何状况下,不得援用被请求国之引渡条约、法律或条例中所规定之司法程序”,与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五条规定的“任何人之生命自由及财产非经法律程序不得剥夺”明显抵触为由,声明持保留意见。③ 《王化成杨云竹致吴国桢签呈》(1944年11月8日),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战俘审判与惩治》,020/010117/0002,台北“国史馆”藏。 英国则认为,其政府拥有足以通过行政手段交出战犯的权力,即根据现行的英国法律,政府有权通过将任何不受欢迎的外国人驱逐出境的方式遣返战犯,只要有初步证据表明其是战争罪犯,或犯有背叛罪,或是资敌者。④ UN War Crimes Commission, The History of the United Nations War Crimes Commiss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aws of War,p.399. 再加上部分国家由于法律条款的限制,以及种种因素,使得该《公约》一直未能正式签署。这是诸多国际公约在签署过程中历来面临的尴尬,即约束他国易,约束自己难,至今仍是难题。
《解递战事罪犯及其他战事违法人犯公约》中,国际社会第一次将战争犯罪从国际保护条款中剔除,不仅避免了给战争罪犯以可乘之机,保证了对战犯的惩治,一定程度上也遏制了国际犯罪。该公约促进了对国际性犯罪的认识,战后战争犯罪是国际性犯罪已经成为共识,这在国际法的发展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Yang:My master,we haven’t cooked for several days because of the big snowfall.
对于该公约第四款是否有违中华民国宪法一事,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也曾呈请国防最高委员会核实,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审查,行政院于 1945年9月5日发布指令:该公约第四款“与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尚无抵触,”实际承认了该公约。⑤ 《行政院指令》(1945年9月5日),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引渡战犯法规》, 020/010117/0002,台北“国史馆”藏。 这为战后中国政府与盟国之间引渡战犯提供了条件。
虽然该公约仅为草案,但在联合国战罪委员会秘书长致各国政府的说帖中,也明确说明:“本公约即使不为若干联合国家所接受,或认为需要,亦可在其他联合国家间运用”。战后基于彻底惩处战争犯罪的共识,盟国间跨越种种障碍,仍然以《公约》为原则,相互之间对战犯进行了引渡,使《公约》的法律意义及思想意义最终得以呈现。
二、 中法处置战犯问题交涉
近代以来,中法间已有相互引渡罪犯的活动。1886年4月25日,中法签署的《中法越南边界通商章程》(又称《滇粤陆路通商章程》)第17款规定:“中国边界某某通商处所,倘有中国人民照中国律例无论犯何罪名,逃入法国人或法国所保护人民寓所或商船隐匿者,地方官照会领事官,查明理由,即设法拘送中国官审办;至中国人民因犯法逃亡越南,由中国官照会法国官,访查严拿,查明实系罪犯交出,照法国与别国所订互交逃犯之约最优之章办理”;同样 “其法国人民及法国保护之人犯法,被告逃往中国者,法国官照会中国官,查明实系罪犯,设法拘送交出法国官审办”,并规定“彼此不得稍有庇匿”。① 陈帼培主编:《中外旧约章大全》(第1分卷),北京:中国海关出版社,2004年,第1135页。 “互交逃犯”即为早期中法间的引渡条款,但引渡对象是各自国家犯有刑事罪行的罪犯,与二战结束后引渡的对象迥然不同。
利用远程移动AR系统、虚实融合的视觉创新技术,飞跃性地提升远程溶栓取栓远程指导工作的效率和精准度,真正实现全年365天24小时的60分钟黄金静脉溶栓判定服务,开展以急性脑梗塞的溶栓治疗为代表的先进治疗服务,提高脑血管患者的救治率,降低脑血管危急重症的致残率和死亡率。
在上海地区,日本投降后,中方在逮捕日本战犯的同时,对于战时与日军和汪伪政权合作,出卖中方利益的法侨也实施了逮捕。而法国戴高乐政府驻沪领事馆警察以法国在华继续拥有治外法权为由,逮捕了部分法奸。中法双方相互要求释放或引渡被对方逮捕的法籍嫌疑犯,围绕处置战犯问题产生了司法管辖权之争。由于中国政府拒绝了法国政府要求引渡战犯的要求,法国政府驻上海总领事费礼浩在未获中方允准的情况下,擅自将领事馆警察逮捕的法籍战犯卡尔平诺转移至停泊在上海的法国军舰白尔丁号上,并移解法国,导致“白尔丁号事件”的发生,从而引发了战后中法之间第一次外交危机。③ 参见刘萍:《“白尔丁号事件”与法国在华治外法权的废除》,《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2期。
由于二战期间,日军对盟国均犯有不同程度的战争罪行,战后受降又涉及多个国家和地区,各国对战犯拥有不同的司法管辖权,在接受日军投降的同时,中国政府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迅速制定了《处理战犯纲要》,对于涉及不同司法管辖权的战争罪犯提出了基本的处理原则:“在我国境内逮捕之战犯,如其罪行在侵害我国法益之外,并侵害其他联合国法益者,应经我国审判后,得依法请求移送被害国家审判;在我国境内逮捕之战犯,经侦讯后,如其罪行仅侵害其他联合国之法益者,得依法请求移送被害国家审判。”并规定,“前二项移送被害国家审判案件,均须依外交途径办理之。”② 《处理战犯纲要》(1945年),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相关方案》, 020/010117/0041,台北“国史馆”藏。 这一处理原则,系根据《莫斯科宣言》和联合国战争罪行委员会引渡战犯公约的精神而制定。
在引渡日本战犯的同时,中法之间又对引渡法籍罪犯展开了交涉。“白尔丁号事件”解决后,中法两国迅速签订了中法新约,彻底废除了法国在华治外法权。淞沪警备司令部开列了52名法籍嫌疑犯名单,拟向法国引渡。经调查,52名嫌疑犯中,有6名正在接受中方审查。其余46名人中,有30人已于1945年底返回法国,5人返回越南,1人在西贡受审,1人离沪,2人已死亡,其余7人是否在沪尚待调查。① 《上海高等法院检察处呈司法行政部长谢冠生》(1946年4月6日),上海高等法院检察处档案:《上海高等法院检察处关于琪培萨尔礼汉奸案》, Q188/2/428,上海市档案馆藏。
二战结束后,同盟国开始设置各级战犯法庭审判战犯,各国也就战犯引渡问题展开交涉。中国政府与法国政府关于战犯问题的交涉,从地区看,主要涉及两个地区,一是战后由中国政府接收的原法国在中国的租界地,尤集中在上海租界。二是由中国军队负责接收的越南北部地区,这一地区原属法国殖民地。从身份上看,涉及两类人员。一是在战争期间犯有战争罪行的日本战犯,二是在战争期间投敌、附敌,出卖中国政府或法国政府利益的法籍和越籍“准战犯”。双方围绕上述战犯分别展开交涉,而又互相牵涉。
而在广州,因美军葛雷中将检举前法国维希政府驻广州领事西门为战犯,国民政府广州行营多次向法国政府驻广州领事馆提出交涉,要求引渡西门,但均遭拒绝。迫不得已,广州行营除陈请中国外交部照会法大使馆训令法国领事迅速将西门交出外,并决定俟西门外出时,乘机将其逮捕归案。这一决定,获得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第19次常会通过。④ 《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第19次常会记录》(1946年3月19日),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会议记录(一)》, 020/010117/0042,台北“国史馆”藏。 如果付诸行动,势必再次引起中法之间的外交冲突。
由于相互之间引渡战犯的需要,同时为避免再次为引渡战犯发生冲突,“白尔丁号事件”解决后,中法两国通过外交谈判,于1946年3月,同意以互惠的方式,以联合国战争罪行委员会起草的《解递战事罪犯及其他战事违法人犯公约》为引渡战犯的条款。① 《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第19次常会记录》(1946年3月19日),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会议记录(一)》, 020/010117/0042。 这是战后,在亚洲战场上针对处置日本战犯问题而达成的第一个引渡协议,从而为解决战犯问题提供了一条路径。“白尔丁号事件”解决后,中法之间战犯引渡的焦点转向了越北地区。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8月1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任命远东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为驻日盟军总司令,同时下达第1 号总命令,对同盟国各自的受降区域作了严格划分,规定“在中国(除满洲外)、台湾和北纬16 度线以北之法属越南境内之日本高级将领及所有陆海空军及附属部队,应向蒋委员长投降”。② “中华民国外交问题研究会”编印:《中日外交史料丛编》(七)《日本投降与我国对日态度及对俄交涉》,第54页。 根据这一命令, 越南境内北纬16 度线以北地区属中国受降地区,由中国军队受降。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将中国战区划分为16个受降区,其中北越地区由第一方面军司令官卢汉为受降主官,日军第38军司令官土桥勇逸中将为日军签降代表,受降地点在河内;广州地区由第二方面军司令官张发奎为受降主官,日军第23军司令官田中久一为日军签降代表,受降地点在广州。
根据麦克阿瑟的指令,在接受日军投降的同时,各受降区对列入战犯名单的日军迅速实施逮捕。遵照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电令及国民政府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颁布的《战犯处理条例》,第一方面军成立了战争罪犯调查委员会,由司令部第五处副处长陈修负责,对越北日军犯罪事实展开调查。经越南华侨检举,并根据陆军总部颁发的战犯名册,第一方面军在越北共逮捕了189名战犯,当中包括由美军提出的7名战犯。1946年5月,卢汉指令将上述战犯押解到广州,交广州行辕拘押,并由广州行营军事法庭进行审判。由于在路上溺毙病故4名,实际移解到广州行营的战犯共185名。③ 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印:《续云南通志长编》(上册),1985年(内部版),第275—277页。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越南原为法国殖民地,日军占领越南后,不仅残酷屠杀越南人民,且对法国战俘及侨民也进行虐杀和迫害。第一方面军受命赴越北受降后,法国驻越北高级专员,公署专员圣德尼多次函请卢汉总司令对越南及法国军民犯有罪行之日本军人予以拘捕,并向中国军队提交了93份敌人罪行调查表和23份有关战犯之备忘录。④ 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印:《续云南通志长编》(上册),第277页。
就协商内容而言,它是人民内部各方面就社会公众共同关心的、利益相关的议题进行广泛而自由的讨论、商量,从而实现民主管理、民主的决策。在现实层面,社会公众能够就改革发展稳定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进行自由、深入的讨论,从而达成广泛的共识,形成科学、民主决策,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协商民主将统一战线作为党联系群众的纽带、作为执政党进行利益表达、利益协调、利益整合的有效机制,并上升到民主政治制度的层次。这不仅有利于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而且体现“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3],使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具有深厚的基础。
1944年1月,为了在战后立即对战犯进行惩处,美、英、中、法等17个同盟国家在伦敦成立了联合国战争罪行委员会,以指导各国调查搜集战争罪行证据,并提出战争罪行案件,制定战犯名单。战争罪行委员会成立后,吸取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审判战犯的教训,并听取各方意见,制定了《解递战事罪犯及其他战事违法人犯公约》草案。该草案系依据比利时、卢森堡、挪威、荷兰、波兰五国司法部长所拟定之约草案修订而成。
法国驻越北高级专员公署虽向中国军队提交了93份敌人罪行调查表和23份有关战犯的备忘录,但93份敌人罪行调查表中,多无罪行人姓名;23份备忘录中,所列犯罪人多为宪兵,已被中方列为战犯。按照联合国战争罪行委员会《解递战事罪犯及其他战事违法人犯公约》的原则,要求引渡方必须提供能够证明罪犯犯罪事实的证据。9月,经广州军事法庭审查,从越北转来的185名被押战犯中,26名有罪,交广州行辕继续拘押候审,其余159名无罪行案卷,由于法方一直未能提出罪行证据,因此广州行辕呈请国防部,拟将其全部遣返回国,并希望在遣返之前,法方能够迅速将拟引渡战犯的“全部罪行事实抄寄来穗,以便侦讯”。国防部讨论后认为,无罪行案件的159名日俘,均为日本宪兵队官兵,而遣返工作刻不容缓,故同意广州行辕将其遣返,并电外交部,将中方的决定转知法国。① 《国防部致外交部快邮代电》(1946年9月30日),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战俘审判与惩治》, 020/010117/0040。
随后,中法双方按照联合国战争罪行委员会制定的《解递战事罪犯及其他战事违法人犯公约》原则,对引渡战犯进行交涉。
三、 中法引渡战犯经过
中法之间引渡日本战犯的交涉,主要涉及以下类型:
第一,对于未对中国犯有罪行或暂时查无罪证的战犯。
针对法方提出的引渡战犯的要求,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讨论决定:“(一)凡经调查确实仅对法越有罪行而对我国无罪行之战犯,准依照外交途径引渡;(二)仅对我国有罪行者,由我方审理;(三)对我国及在法越同有罪行者,由我方审理,法方可将罪证资料送交我国法庭参考;如认我方所判罪刑不满意时,并可循外交途径请求引渡。”但国防部强调,引渡以不影响战俘遣送为前提。而法方提出的派代表列席审判的要求,无疑是会审公廨制度的延续及扩大,对此,司法行政部认为,“此举与我国司法主权不无妨碍”,因而断然拒绝。⑥ 《国防部至外交部电》 (1946年9月5日)、《司法行政部致外交部快邮代电》(1946年9月11日),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战俘审判与惩治》, 020/010117/0040。
1.2.2 不同风送状态解吸湿特性研究 风送设备选择要考虑到风送对成品烟丝含水率影响较大的工序和设备,根据生产工艺流程特点和环境温湿度的影响,选择烘梗丝风选机、叶丝就地风选机和混合丝风送喂料机。选择一种在制品,在其风送设备前后取样进行含水率测定,同时记录试验时环境温湿度条件、风送风速以及物料流量和物料温度。
法国方面接到中方节略后,强烈表示不满,一方面认为中方出尔反尔,另一方面又表示已转请法国驻越北高级专员公署迅速提供战犯的罪行资料,请求中方将战犯“暂行扣留广东省内,勿予遣送回国”。② 《法国大使馆致外交部第396号节略》(1946年10月14日),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战俘审判与惩治》, 020/010117/0040。 10月12日,驻广州法国领事署领事并致函外交部驻广东广西特派员公署,要求设法延缓遣送战犯,并强硬提出,如果该批日兵已被遣送回国,法国政府如须逮捕战犯时,仍由中国政府设法交回。针对法方的无理要求,广州行辕表示,遣送船只11月1日将到达广州,要求法方务必于10月27日以前提出罪行证据,以便查办,否则届时将战俘全部遣送。但法方坚持保留“如被遣送,将来由中国政府交回”的意见。鉴于法方的强硬态度,中方作出让步,表示法方逾期未将罪犯证据提出,该批战俘本可依照原定日期遣送,但“惟本友好合作精神”,同意将已经押送致虎门的日俘暂时扣留,并解返广州。③ 《外交部驻广东广西特派员公署致外交部快邮代电》(1947年1月6日),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战俘审判与惩治》, 020/010117/0040。
为了解决中法间引渡战犯问题上的纠纷,10月25日,法国驻越北高级专员公署外交顾问格拉克、法国大使馆首席参事戴立堂,与中国外交部派出代表凌其翰、陈泽溎进行谈判。在谈判中,法方提出8位据称是“罪行凿实者”之战犯名单,要求迅速将之引渡至越南,交给法国当局。对于其他未列名之战犯,法方虽声称因对上述战犯之调查尚未完竣,未能提供各项罪行之全部案卷,但又强调,“法当局所持之证据,颇为重要,足以认为此项战犯有重大违犯国际公法之嫌疑”,故请求中方“在其命运得以正式判定之前,一律暂行扣留广州”,否则如果将这些“嫌疑犯遣送返日,则以其远离犯罪地点之故,不免终于逃避其应得之惩处”。④ 《法国大使馆致外交部第413号节略》(1946年10月28日),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战俘审判与惩治》, 020/010117/0040。
法方提出的8位战犯的名单及罪行如下:大岛亲光,河内日本宪兵司令;平井春二,河内日本宪兵班长。此二人的罪名均为“虐待法俘虏、人民”。坂口俊夫,海防日本宪兵司令;原贤二郎,海防日本宪兵中尉排长;今井明保,海防日本宪兵翻译官。此三人罪名为“虐待、拷打与苦刑”。荒田诚三,地方日本宪兵班长,罪名为“拷打并对法宪兵苦刑”。木村英男,地方日本宪兵副官;太田,宪兵。此二人罪名为“拷打、苦刑”。⑤ 《中国当局拘押在广东日本战犯名单》(1946年10月28日),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战俘审判与惩治》, 020/010117/0040。
虽然法方提交的8名战犯的罪行事实极为简略,但中方仍然同意了法方的引渡要求,国防部随即致电广州行辕对上述8名罪犯予以扣留,并电外交部转知法方派员持文前往引渡。经广州行辕审查,情况如下:法方要求引渡之日宪兵8名中,其中大岛亲光1名,亦系中方战犯;太田1名,查无此人;今井明保1人,系日本联络班人员。其余151名战俘中,死亡1名。国防部指示:大岛亲光押送广州军事法庭侦讯审查,今井明保等准由法方引渡,其他日宪兵,“并入粤琼待遣俘侨内送上海东部战犯管理处接收遣送”。① 《国防部致外交部代电》(1946年11月23日)、《国防部致外交部快邮代电》(1946年11月28日),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战俘审判与惩治》, 020/010117/0040。
但不久国防部又接到“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部长官”冈村宁次呈文,称今井明保系由南京日本官兵善后联络班派往广州任华文翻译,帮助中方接收工作,因与日本前21师团法语翻译官今井一夫同姓,故误为战犯,“请予开释遣送”。国防部同意其暂缓引渡,并请法方重新查核。② 《国防部致外交部快邮代电》(1946年12月5日收电),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战俘审判与惩治》, 020/010117/0040。 其他5名战犯,中方同意由法方引渡。
12月7日,外交部以节略的形式将上述决定通知法国大使馆。12月19日上午10时,广州行辕将平井春二、坂口俊夫、原贤二郎、荒田诚三、木村英男等5名战犯移交法国驻广州领事馆秘书鲁伟罗(Ruve Youx)接收。
至于其余的150名战俘,国防部认为因中方和法方均未提出罪证,而遣俘船全部由美军供应,故仍然坚持“未便缓遣”。1946年12月9日,这批战俘搭乘轮船至沪集中,等待遣返。③ 关于遣返的该批日俘的人数,国防部1947年3月21日致外交部代电说是152名,但在该电中又提及后藤则吉经越南华侨指认为罪犯,再除去大岛亲光、今井明保2人,以及引渡的5名,死亡1名外,综合统计应为150名。
日军第38军司令官土桥勇逸是唯一一名在越北受降区内被中国陆军总部列入战犯名单的战犯,因地位特殊,恐逮捕后会影响整个战俘管理,故直到日本战俘遣送时才将其逮捕,④ 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续云南通志长编》(上册),第275页。 被关押在南京小营战犯拘留所。法国政府以土桥勇逸在越南总督任内,曾犯有杀害当地人民及俘虏之罪行嫌疑,向中国政府提出引渡请求。同时,荷兰大使馆也以土桥勇逸在战争期间犯有纵容士兵将300余名荷兰人及盟军装入猪笼中投入海中溺毙等罪行,希望其在南京受审后进行引渡。⑤ 《荷兰大使馆节略》(1947年1月17日),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战犯个案(三)》, 020/010117/0035,台北“国史馆”藏。 经国防部战犯军事法庭审判,土桥勇逸在安徽怀宁杀人放火案,因犯罪嫌疑证据不足,决定不予起诉⑥ 《国防部致外交部代电》(1947年7月31日),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战犯个案(三)》, 020/010117/0035。 ,故国民政府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同意两国的引渡请求,希望两国尽快提出罪状证据。法国大使馆于1947年5月7日,检送土桥勇逸罪证、罪行纪要给外交部,共列罪状10项。而荷兰大使馆直到10月1日才将土桥勇逸的罪状检送,并提出因荷印当局将在年底完成战犯之检举工作,未便将土桥勇逸送往荷印受审,希望中国军事法庭审判时,就荷兰政府提出的罪状进行审判。⑦ 《荷兰大使馆节略》(1947年10月1日),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战犯个案(三)》, 020/010117/0035。 但因中国政府对土桥勇逸的审判已经结束,故未接受荷兰政府的请求。1948年1月9日,土桥勇逸由上海军事法庭移交法国驻沪领事馆。翌日,被押解越南受审。⑧ 《申报》1948年1月10日第4版。
第二,对中法双方均犯有罪行并被中方处以最高刑罚的战犯。
1947年7月7日,河内日本宪兵司令大岛亲光经广州军事法庭审判,以犯虐待及残杀华人罪名,被判处死刑。得知这一消息,法国驻广州领事馆领事卫映章致函广州行营主任张发奎,要求引渡,称:“查该犯是贵国政府答允移交法国审讯之8名战犯之一者,……现该大岛亲光因犯虐待及残杀华人既被判刑罪,则事已决定矣。兹依照同盟国协定及根据田中久一先例,本领事应请贵主任饬将该战犯大岛亲光移交本国审讯,以为虐待法国军民人等之惩戒。”⑨ 《国防部第二厅致外交部快邮代电》(1947年8月20日收)附件“广州行辕代电”,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战俘审判与惩治》, 020/010117/0040。一说大岛亲光被判为无期徒刑,参见《国民政府主席广州行辕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战犯审判录》,张中华主编:《日军侵略广东档案史料选编 》,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5年,第156页。
函中所称之“田中久一先例”,系指1946年5月18日广州军事法庭开庭审判日军华南派遣军第23军司令田中久一,驻华美军总部以该犯在1944年底兼任香港总督期间,犯有杀害美国飞行员的罪行,要求将田中移交到美军设在上海的军事法庭受审。虽然美军在华擅自设立军事法庭审判战犯,严重侵害了中国主权,而在中方审判期间要求提审田中久一,也不符合联合国战争罪行委员会引渡战犯公约的原则,但迫于美方的压力,中方同意了美方的要求。9月3日,美军上海军事法庭判处田中久一死刑,并呈报驻华美军总部核准执行。此举遭到中方的坚决反对,中方提出,鉴于田中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的严重性,必须再交回中国军事法庭审判。1946年10月17日,广州军事法庭以14项战争罪名判处田中久一死刑。1947年3月,经蒋介石核准执行。
百合在培养过程中部分材料会呈半透明状,组织结构发育畸形,称为玻璃化,又称“过度水化”。玻璃化苗是导致组培苗繁殖效率低的最常见的原因。由于其生理功能不健全,分化能力低,继代和移栽多难成活。百合试管苗在不适宜的培养基中玻璃化比例最高可达82.4%,明显影响生产效率[10]。
法国想仿照美军的方式引渡大岛亲光的要求,遭到张发奎的拒绝。张发奎在致法国领事函中称:“查田中久一并非由美国引渡,乃系在本国法庭尚未判决前,美方循外交途径要求在本国境内提审该犯。关于屠杀美国空军人员案件,经本国政府同意,暂交美军在华军事法庭审问,而至该犯审判权则仍由本国保留。”故不同意法方的引渡请求。① 《张发奎致法国驻广州领事卫映章函》(1947年7月30日),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战俘审判与惩治》, 020/010117/0040。 对于美军在华提审战犯一事,张发奎的解释并不准确,而其拒绝法方的引渡请求,也违背了引渡战犯《公约》的原则。
法国大使馆转向中国外交部请求引渡。1947年11月6日,法国大使馆致中国外交部节略,再次申诉引渡大岛亲光的理由,称:第一,大岛亲光作为前河内日宪兵队指挥官,是该宪兵队在越北被控各项战争罪行之主犯,理应出庭受审;第二,如果该犯缺席审判,难免造成其他罪犯“企图将其本身罪责一律诿诸该犯”,因此,坚请 “中国当局对法国法庭此项维护正义之工作,给以必要之协助”。鉴于该犯已经被中方判处死刑,故根据引渡公约第九款规定,违法人员已为请求国之一判处死刑,则应由该国执行,法方表示,该犯与其部属在越审讯终结后,立即将其移交中国政府执行死刑,② 《法国大使馆致外交部节略》(1947年11月6日),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战俘审判与惩治》, 020/010117/0040。 法方的请求,应该说合情合理。11月15日,国民政府战犯处理委员会第78次会议议决:“以该犯在越审讯终结后,由法方移回我国执行该犯在华所判死刑之条件引渡”,同意了法方的引渡请求。③ 《骆人骏签注》(1947年11月17日),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战俘审判与惩治》, 020/010117/0040。
第三,对中法双方均犯有罪行并经中方判决的战犯。
引渡大岛亲光的同时,法国驻越南高级专员公署以“非法监禁普通人民、虐待普通人民及战俘,并滥施酷刑” 等罪名,又向中国政府提出了12名战犯的名单,包括:春日馨、浅井庄次、麻生亘理、阿部久次郎、后藤则吉、片山宗助、松本武、山崎阙男、妻刈悟、高木传。该名单于10月14日、11月24日提出,后又做了修订。④ 《法国大使馆致外交部第346号节略》(1947年11月24日)、《法国大使馆致外交部第374号节略》(1947年12月26日),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战俘审判与惩治》,020/010117/0040。
2.1四组患者心脏结构相关指标比较:OSAHS患者组中,中度组与重度组患者的LVDD、LVDS、LA、IVS、LVPWD指标与健康对照组比较明显升高,差意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3]
经广州行辕查证,法国所列12名战犯名单中,经中方法庭判刑者4名,分别是:春日馨,判处徒刑12年;麻生亘理,判处徒刑15年;妻刈悟,判处死刑;高木传,判处徒刑15年,均关押在上海战犯监狱。无罪遣送回国者4名,分别是浅井庄次、后藤则吉、松本武、东兼德。由越解送广州时死亡2名,分别是山崎阙男、片山宗助。查无其人者2名,分别是阿部久次郎、稻木寿台。⑤ 《国防部致外交部代电》(1948年3月23日),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战俘审判与惩治》, 020/010117/0040。 因春日馨等4名战犯已经被中方判刑,外交部指示广州行辕,根据联合国战争罪行委员会制定的引渡公约第四款的规定,对两国犯有战罪的战犯,引渡时需要提供“被控罪状之说明及该罪状之最高可能处罚之记载”,如将春日馨、麻生亘理、妻刈悟及高不传等战犯引渡赴越,应先请法方将这四名战犯之罪证及可能处以之最高刑罚送到后再行核办。⑥ 《外交部致国防部代电》(1948年3月30日),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战俘审判与惩治》, 020/010117/0040。
由于法方不能提供罪状材料及可能处以的最高刑罚,这4名战犯最后未能被引渡。1948年4月20日,妻刈悟被上海军事法庭执行死刑。
在E-Navigation战略的支持下,人类的航海活动将从有限岸基支持下的单船行为转变为岸基、它船海量信息支持的船船协同行为,GMDSS现代化将是这一变化中最有力的技术支撑。GMDSS现代化与E-Navigation战略协调发展是大势所向。发展GMDSS现代化就需要经历3个阶段:初级阶段的现代化是应对当今海上局势并进一步发展海上通信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准现代化将为E-Navigation战略发展提供真正意义的通信支撑;终级现代化则是完全融合现代通信技术的海上通信现代化的终极目标。
联合国战争罪行委员会制定的引渡战犯公约明确规定:“各缔约国得拒绝彼此解递本国国民或以往之国民”。对于淞沪警备司令部拟引渡法籍嫌疑犯一事,司法行政部核准引渡战犯公约后认为:“查我国与法方并无引渡条约,而与敌人合作之罪行又属于准战事犯之类,前此联合国拟订之《解递战争罪犯及其他战事人犯公约》草案,虽经外交部与法国大使馆同意引用该草约之原则,以解决两国间处理战犯之解递事项,但该草案第五条第一项规定,各国得拒绝解递本国之国民,故大部法犯,如已回国,欲使法方同意,解递至华,颇为不易。”随后司法行政部指令上海高等法院先调查各嫌疑犯所犯罪行及证据,并开列呈报,然后转交外交部,由外交部尝试洽商法国政府。② 《司法行政部部长谢冠生令上海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杜保祺》(1946年5月16日),上海高等法院检察处档案:《上海高等法院检察处关于琪培萨尔礼汉奸案》, Q188/2/428。 而事实上,囿于联合国战争罪行委员会引渡条约的限制,引渡法籍嫌疑犯最后不了了之。
结语
中法间引渡战犯,具有两个特点:
一是提出引渡的战犯名单多,但最终成功引渡的少,这一点与中国向盟国引渡战犯的案例相似。法国向中国提出引渡的日本战犯近200人,但最终成功引渡的仅有7名,而中方拒绝引渡的理由,自始至终是因法方缺乏罪状证据。而检讨战后中国向盟国引渡战犯的工作,成功引渡的案件也很低。截止到1948年7月底,经外交部成功引渡来华之日本战犯只有15名。③ 骆人骏:《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工作报告》(1949年),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战犯处理政策》 (二), 020/010117/0039,台北“国史馆”藏。 重要的原因是缺乏证据。而揆诸美军在越北向中国第一方面军提出的7名战犯名单,包括详细的姓名、职级、部队番号、罪状,这与美军自战争爆发伊始就注重罪行证据的搜集有关。故能否成功引渡战犯,最为关键的一点是能否提供罪状证据。
位于贵州的开磷集团、瓮福集团是国内外具有较强影响力和竞争力的龙头骨干企业,技术装备、研发能力和磷石膏资源综合利用水平均走在全国前列。何光亮介绍说:“开磷集团和瓮福集团的磷矿资源集中度很高,两家企业合起来的磷资源工业储量大概在15亿吨,从开采利用能力上讲,占了贵州省80%-90%的份额。”由此可见,对这两家企业的管理是实现贵州磷石膏综合利用的重要环节。
检视父母教养范式的适切性,就是检视其合理性和有效性。“鞋子合不合脚,脚知道”。与孩子的个性和成长需求契合的家庭教育,对孩子成长产生积极的正向影响,反之亦然。检视家庭教育范式的适切性,要检视家长的家庭教育动机、教育目标,检视日常生活中亲子双方的情绪体验和行为反应等。如果消极的劣性的情感体验多,就要对家庭教育多加注意,及早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
二是严格恪守联合国战争罪行委员会制定的引渡公约的原则。中方在引渡中坚持“无罪状不引渡”的原则,以及公约中对于被引渡人的保护性条款,无疑都努力希望把审判纳入法律的轨道,避免单纯的报复性行为,也反映了现代法律制度向公平、正义发展的方向。中法引渡战犯的实践,对于全面理解战后审判,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The actuating torque of the passive joint in Eq.(14)can be transformed into
二战结束后对战犯的处置,是列强在华治外法权废除、中国成为主权国家后首先面临的问题,涉及棘手的司法管辖权纠纷,对中国政府行使主权能力是一次考验。中法间引渡战犯的实践,无疑是中国政府处理司法管辖权纠纷的一次较为成功的案例。在与法国政府交涉过程中,政府相关部门主权意识不断加强,在中法双方共同达成以联合国战争罪行委员会《解递战事罪犯及其他战事违法人犯公约》为引渡战犯的原则后,相关部门并严格遵守公约条款,坚持证据优先,虽在具体环节上略显刻板,但较为完善地诠释了公约条款,使公约有了实际意义;同时中国政府在引渡战犯中对国际性公约的严格遵守,对融入国际社会,树立国家形象也具有积极意义。
战后审判是近代以来国际社会惩治国际犯罪的重要举措,也是国际刑法发展的重要阶段。而战后以引渡为主的国际司法互助方式,保证了对战争罪犯的惩处,故从国际法的角度分析、评判中法间引渡战犯的实践,对于全面认识战后审判的经验和教训,以及对现代国际法的促进作用,具有重要的意义。
对于符合成立蔬菜合作社的地区和村社成立合作社,收集市场供求信息,指导种植户种植不同品种蔬菜,组织农民统一采摘、统一包装,采用“打捆”销售的方式,使农产品从“田间地头”通过合作组织这个桥梁走到“城市卖场”,实现即摘即运,确保产品品质,改变农民单家独户自产自销这种销路不畅、收益低下的方式。通过抓活市场、理顺供求关系,在遇到特殊时期、产品滞销情况下,及时将农产品收进冷藏室或者进行深加工,确保收益。
首先从国际法看,《解递战事罪犯及其他战事违法人犯公约》系近代以来国际间首次制定的引渡战犯的国际法规,第一次确立了战争犯罪行为不属于政治犯罪,各国不得拒绝引渡的原则,对于审判战犯,彻底清除战争犯罪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随着国际法的发展,当前“恐怖犯罪非政治化”的观点逐渐为国际社会所接受,并在国家间签署的引渡条约及国际性条约中采用,形成了国际社会共同打击国际犯罪的局面,禁止任何国家对其行使庇护权,对于有效防止犯罪或消灭犯罪具有积极作用。中法引渡战犯过程中对于公约条款的诠释,一定程度上也证明了公约的合理性和可行性,为战后国际间引渡条约的制定提供了思路和借鉴。
(2)拓展话语空间。成为“人物符号”的专家尚属少数,但在互联网时代,更多的非官方专家学者通过微博、博客、微信等自媒体平台,自发主动地宣传自身政策主张,极大拓展了话语空间。如吉林独立人口研究者杨子实,其微博粉丝数达13 878人,共发布13 945条微博,有一定的转赞评量;关注人口问题的专栏作家何亚福从2010年末开始在微博上探讨人口问题,始终支持放开生育,现微博粉丝近4万。[注]数据截至2017年4月6日。 这些“草根”学者尽管无法直接向决策者提交政策议案,但通过新媒体平台产生了不可忽视的社会影响力。
第二,中法之间对于战犯的引渡,一定程度上为目前中国的司法引渡制度提供了借鉴。由于引渡涉及国家司法管辖权及国家主权等复杂问题,不同国家间又秉持不同的司法制度传统,国际社会尚未形成统一的国际引渡法,国际法中没有关于引渡的统一规定,但国际引渡制度作为一种司法互助在当代已经发展得较为成熟,引渡的主要依据是国家间双边的或多边的引渡条约,同时也形成了相互间遵循的原则,如“互惠制度”、“条约前置”、“或引渡或起诉”等等。战后中法间出于对战争犯罪进行彻底惩处的目的,达成以联合国战争罪行委员会《解递战事罪犯及其他战事违法人犯公约》为准则引渡战犯的实践,贯穿了现代引渡中的“互惠原则”及“条约前置”原则,使得引渡工作顺利进行。目前中国除与部分国家签署有引渡条约外,与欧美一些国家尚未签署引渡条约,而这当中一些国家又秉持“条约前置”主义,必须签署条约才能引渡。中国在引渡中,在不损害主权的基础上,如何利用引渡原则,以避免某些国家成为庇护中国罪犯的温床,尚需要作进一步的探讨和努力。
Negotiations on the Extradition of War Criminals between China and France after World War II
LIU Ping
Abstract: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United Nations War Crimes Commission in January 1944, the first convention of international war criminals’ extradition was set up in modern times. The Convention eliminated the clause of “political offenders” in the traditional extradition system to ensure thorough investigation and punishment of war criminals. After the end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China and France reached a consensus on extraditing the war criminals based on the provisions of the Convention, which marked the turning point from conflicts to cooperation on the handling of war criminals, and also guaranteed the smooth trial of war criminals. The preliminary practice of the extradition of war criminals between China and France comprehensively interpreted the main principles and spirit of the Convention. It also became the precedent in the modern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punishing the war crimes through judicial cooperation. Furthermore, it was also a successful case of Chinese government’s dealing with foreign affairs in the process of restoring its diplomatic sovereignty after the abolition of extraterritoriality. The case is instructive in today’s society for how to successfully handle international affairs.
Key words: war criminals; trial; China; France; UN War Crimes Commission
刘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审(北京100006)。
About the author: LIU Ping is Professor of Editorship at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 Beijing 100006 ).
(责任编辑:蒋永华)
标签:战犯论文; 引渡论文; 审判论文; 中国论文; 法国论文; 联合国战争罪行委员会论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