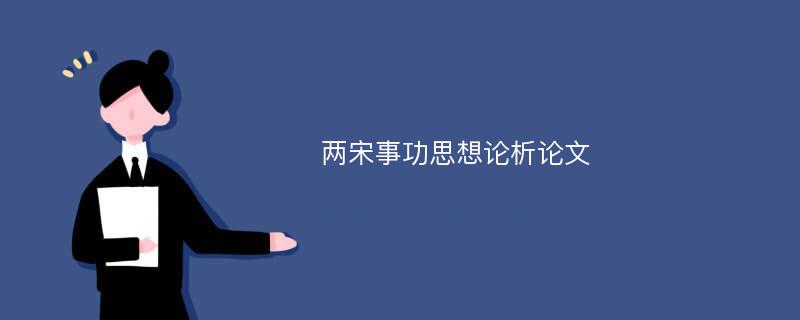
·学者专论·
两宋事功思想论析 〔*〕
赵 滕1, 王浦劬2
(1.北京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124;2.北京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 北京 100871)
〔摘 要〕 两宋时期,是儒家改变魏晋隋唐的相对弱势地位,重新主导官方意识形态的关键时期。沿着战国时期孟荀之间规范主义与现实主义辩争的理路,两宋儒家形成了性理之学与事功思想的对立。两宋事功思想从现实与功利的视角阐释儒家的世界观、伦理观与政治观,已萌发人本思想,其发展了儒家“入世”的文化传统,强调“经世致用”的君子人格意象。从这个意义上说,两宋事功思想是儒家内生的由传统向现代转进的文化基因。
〔关键词〕 性理之学;事功思想;文化意义
大一统中央集权的相对削弱与商品经济的积极发展,催生了两宋儒家哲学、伦理以及政治思想的繁荣。从儒家文化来看,两宋既是儒家性理之学吸收道、佛精华,建立道德色彩的本体论的时期,也是儒家道德功利并用的事功思想系统展开论证的时期。从现实政治来看,两宋时期儒学内部的性理之学与事功思想的对立,实际上是儒家解决王朝积贫积弱问题的不同思想和政治主张之争。从儒学传承来看,两宋时期儒学内部的性理之学与事功思想之争,延续了孟子的理想主义与荀子的现实主义的文化争鸣。两宋事功思想的文化意义在于,在与性理之学的辩争中,突出功利的合理性,体现了人本的关怀,其哲学、伦理与政治思想已经具备了初步启蒙性质。从儒家文化传统来看,两宋事功思想强调与“醇儒”对立的“成人”君子人格,推崇改革与担当的文化品格,继承并发扬了孔子“入世”的精神,并且以事功思想的形式积极光大,应时而进地推进了中华文化优秀要素的发展。
一、两宋儒家事功思想的演进脉络
从时间上看,两宋事功思想可以分为北宋与南宋两个阶段。而北宋又可以划分为前中期与后期两个阶段。从地域上看,其又经历了从汴梁到浙东的地域中心转移。
有一些译者在翻译的过程当中不是很考虑电影字幕的瞬时性,觉得把英文翻译成英文就可以完成任务了,但是句子过长会导致观众没办法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把字幕看完。所以,这个问题我建议对一些长一点的句子进行简化和删减。达到既不影响原文的意思,又言简意赅地表达出来。
北宋阶段,与“宋初三先生”〔1〕同期的李觏的事功思想堪称最为全面。其唯物倾向的哲学、公共利益的“礼”论以及政治主张,确定了其两宋事功思想奠基人的地位。紧随李觏的是王安石,在性理之学保守路线与事功之学改革路线的大交锋中,与政治上司马光、苏轼等人相呼应,作为“北宋五子”〔2〕的二程、邵雍批评了王安石的思想。王安石进行了反驳,他以事功为原则在道器、人性、义利、王霸等方面进行了论证。其学说一度成为官学,史称“荆公新学”。在儒学的广泛传播下,永嘉地区诸君子也开始了事功的思考。皇祐年间,“皇祐三先生”即王开祖、林石与丁昌期在该地传播儒学。与温州地域务实、开拓的文化相统一,三人的思想有鲜明的事功特征。实际上,当时李与二王之间已有了深度的交流。王安石在给王开祖的《答王景山书》中强调自己曾吸取李觏的思想,李觏的学生邓润甫则是王安石变法的主力干将。对王开祖的思想,王安石也在《答王景山书》《答王该秘校书》等书信中进行了高度评价。三人生徒动辄数百,这使得事功思想传播更为广泛。
启示:这句谚语告诉我们,人生的道路并不是畅通无阻的,要坦然面对阻碍和困境,事到临头,必定会有解决的办法。但办法不会自己出现,还需要我们开动脑筋,主动思考:遇到山,要会迂回前进,寻找出路;遇到水,要会积极应变,寻找渡水的手段,这样才能达到既定的目标。
而对于IV类润滑剂而言,由于其主要成分为合成油聚α烯烃,其对橡胶材料各类性能参数的影响略有不同。当被浸泡在IV润滑油中时,丁腈橡胶吸入润滑油的量小于溶解在润滑油中的橡胶添加剂的量,内部的网状结构被压缩,橡胶试样内部分子链的自由度变小,导致其体积减小、硬度增大、拉断伸长率减小;而体积增大使得内部的网状结构被压缩,增大了网状链结构中的相互作用力,使得其抗拉伸能力有所增强,所以其断裂拉伸强度增大。
南宋阶段,事功思想进入了集大成时期。实际上,南宋也是性理之学走向巅峰,最终夺得意识形态统治地位的历史时期。由于高宗赵构将北宋灭亡的原因归咎于“荆公新学”,所以南宋时期事功思想已经完全脱离了官方意识形态。这个时期的事功思想,主要形成两个学派,一个是继承北宋渊源的永嘉学派;另一个是异军突起的永康学派。南宋永嘉学派的思想家有薛季宣、郑伯熊兄弟、陈傅良、叶适等人;永康学派的代表人物是陈亮。创新是两宋事功思想的灵魂,上述诸子在多方面达到了两宋事功思想的高峰。从理论的深度上看,薛季宣是南宋永嘉学派的核心人物,他推动了郑氏兄弟由性理之学转向了事功之学,同时对陈傅良、叶适等人也影响颇深。陈亮以其与朱熹的“义利王霸之辩”而闻名古今。
二、两宋儒家事功思想的理论逻辑
两宋事功思想的逻辑,是从儒家性理之学的理论逻辑中衍生形成的。因此,欲明了两宋的事功思想逻辑,必先清晰掌握两宋性理之学的理论逻辑。就其理论逻辑而言,两宋性理之学在形而上世界的道德化“天理”论证,具有三个层面的“理论主线”。
围绕着儒家性理之学在世界观、伦理观和政治观层面的理论逻辑和主线,两宋事功学者展开了深刻质疑,在此基础上,论证了自己的思想主张。
在世界观方面,性理之学借鉴佛、道思想,将形而上的“理”概念引入儒学,形成了“理”支配、统御“气”的基本哲学格局。一般而言,佛家的“理”,强调空净虚无,是一种“空理”;道家魏晋玄学中的“理”,强调高深玄妙,是一种“玄理”。而儒学的“理”不是“空”“玄”的“虚无”,而是具备“实有”特点的“天理”。这集中体现为“天理”支配世间万物,而不是如“玄理”“空理”一般与世无碍。儒家的形而上的规律——“理”与形而下的物质——“气”之间,存在着“体”与“用”、“本”与“末”的关系。在理学中,“体”与“用”、“本”与“末”并不指具体事物,它们是用来表示范畴之间关系的概念。“体”即是“本”,是终极的、原则的、本源的;“用”即是“末”,是表象的、具体的、衍生的。“理”之于“气”,就是“体”之于“用”,“天理”是支配物质世界产生、发展的根本大道。理学“天理”的终极支配性有几个特点:第一个是静止性。因为其根本的终极性,所以“天理”是永恒不变的,这实际上是否认运动与发展、坚持僵化的世界观;第二个是超验性。因为“天理”在形而上世界,所以其不存在于具体的物质之中,超出人们自然感官的感知范围;第三个是决定性。“天理”生发、推动着物质世界的生成与变化。总之,性理之学的理论主线在于“理”作为“体”与“本”对于“气”的根本支配性作用,这种思辨结构是性理之学伦理观与政治观的逻辑基础。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学生娱乐的方式也越来越多,小学生的自制力较差,容易被各种游戏、视频所占据,再加上许多小学足球教学本身缺乏足够的吸引力,导致学生对足球学习的兴趣不高,多是以消极应付的心态来面对足球课堂,而在失去了学生的主动参与后,无论教师怎样努力,也无法开展有效的足球教学。当然,在小学中也有一部分学生是喜欢足球的,但从数量上说还是太少,并且绝大部分都是男生,对于其他学生尤其是女生来说,难以感受到学习足球的乐趣,反而认为足球课是一种负担。
在伦理观方面,理学家们将道德与价值赋予“理”,给予其实在意义,将“天理”深化为“性理”。在性理之学中,“理”是终极的价值评判标准,其与人间的“性”,即人性是同一的。这样,形而上的终极道德标准“理”,就形成了对人间社会规范性的支配。这样,道德就无所不在地统治了世界。从内部看,人性的本质具备天理的道德内容;从外部看,天理又形成自然、社会的各种价值性的规范。道德在性理之学中,变成了普遍和绝对的规律。体现在人性论及“义”与“利”的关系问题之中,就是人性善与“义”为“本”、“利”为“末”。孟子的性善论在性理之学的思辨结构中获得了逻辑上的依据,即“天理”同一于人性,而“天理”又是至善,所以人性纯善。当然,这种善性也同“天理”一样,是绝对的、静止不变的人性。在性理学家眼中,有一丝事功的动机和行动,都玷污了人性的纯正。所以,“义”代表的道德是根本的、绝对的、永恒的、必然的;而“利”代表的事功则是微末的、相对的、短暂的、偶然的。这样,人们就有了坚持道德动机与行动的根本义务,即所谓的“存天理、灭人欲”。性理之学之所以能在伦理上得出这种结论。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理学家们在其“理本气末”的根本理论红线基础之上,将“理”同价值统一起来。而这就是性理之学第二层次的理论主线。
使用SPSS19.0软件对灌浆过程进行拟合及相关统计分析,利用Richard方程对灌浆过程进行拟合,并得方程参数[7]。
在政治观方面,性理之学坚持“王道”至上的第三道理论主线。“王道”与“霸道”是儒家治国理念的两大范式。“王道”强调以道德的动机和道德的规范进行统治。惟其如此,权力才合乎天理从而具备合法性;“霸道”则是以事功进行政治统治。性理学家认为,只要统治者有了事功的动机,或者功利性的行为,那么其统治就失去了全部的合法性。因为道德的动机与规范,从“天理”和“性理”的两条红线看,是绝对的、刚性的、不容有丝毫松动的。所以,政治合法性也必然是纯粹的道德统治,不能有丝毫的“霸道”。体现在政策中,性理之学主张保守的政治路线,其根本的政治方法论就是“安坐感动”。既然“天理”是终极支配的,“性理”是道德纯善的,那么,统治者的任务就应当是安坐感悟道德的动机,并遵守既有的道德规范。而政策效果和现实的情形,统治者是不能以“事功”动机进行干预的,必须交给“天理”支配。这种政治路线的本质就是静止化、绝对化地处理问题,不是从现实出发积极、动态、发展地进行政治治理,而是从信仰出发消极、僵化、教条地进行政治治理。具体而言,其人才观认为,用人应当以经义教条取材,重用“醇儒”。即选用饱受理学理论熏陶,具备神秘高深的“气象”,能闲静醇厚地感悟“天理”的君子。如果才华突出,精明干练,那就是“气象”不良,具有被事功污染的危险,不是最优的人才了;在经济上,性理之学反对理财,对财政之策与货币政策漠不关心,认为道德君子是不能够经手事功的污染的。对两宋时期土地兼并、私盐私茶等社会经济问题,理学家们拿不出实用的方案;在政治上,对于两宋根深蒂固的“冗兵”“冗员”等问题,理学也缺乏有力的主张;在军事上,理学家们普遍认为“天理”自然会帮助两宋政府收复失地,故而不必认真进行军事建设。
从专名的角度看,这个新的标准或许可以暂时被称为无屈折变化标准。它至少对描述性谓词有效,因为通常被用作描述性谓词的形容词和动词是有屈折变化的。在某种意义上,它也对种类谓词如“Pferd”有效。例如,如果我们给出三个质料“赤兔”、“的卢”和“马”,那么至少可以构成两个质料部分相同的断定句:1、Chitu ist ein Pferd und Dilu ist ein Pferd;2、Chitu und Dilu sind Pferde。其中,Pferd经历了单复数的变化。
在世界观层面,从北宋初年的“道不离器”到北宋中期“道在器中”,再到南宋的“道无本末”,事功思想逐步突破了性理之学的根本红线,将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推向了新的高度。李觏认为:“天有常,故四时行;地有常,故万物生;人有常,故德行成。”〔4〕“道”的运行是客观的,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这继承了儒家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具有明显的唯物倾向。王安石的“器者道之散,时者命之运”〔5〕的思想,认为“道”“理”是不能脱离具体的物质世界而存在的,这就打破了性理之学认为“理”独立于并先于物质世界而存在的论调,将形而上世界的“道”与现实世界的“器”(气)紧密联系一处。“永嘉九先生”中的刘安节,在“道不离器”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顺则通,逆则塞,物之常性也”〔6〕,即“道在器中”。这就将“道”或“理”从神秘的形而上世界引入了形而下世界,使之具备了经验性的现实功能。进展至此,事功学者的思想不可谓不精彩,但是仍然没有脱离性理之学“道本器末”“理体气用”的总体哲学框架。因为承认“道不离器”与“道在器中”,都没有否认“道”“理”对于“器”“气”的根本性支配作用。“道不离器”只是承认“器”对“道”的必要性,但是其地位仍然是辅助的;所谓“道在器中”,不过是将“道”的支配作用延伸至现实世界,强调其支配作用可以是“经验性的支配”,从而能被人类的感官所认知。而不是如性理之学所主张的只能是神秘的、依靠直觉才能悟知的“超验性的支配”。但无论何种支配,“道”与“理”的“体”与“本”的支配性地位并没有被动摇。无论是周行己,还是南宋的郑伯熊、叶适、陈傅良等人,都没有超越“道在器中”的范畴。在这其中,唯一例外的是,薛季宣跳出了性理之学的圈子来论证世界的本质,具有激进的革新性。薛季宣提出了“道无本末之辨”〔7〕的思想,从根本上推翻了性理之学的世界观。“道无本末”于“道在器中”的基础之上,更进一步地否定了形而上天理的“体”“本”的支配地位,实际上也否定了形而上超验世界的优越地位,推动朴素的唯物主义进入了新的境界。
在伦理观层面,围绕人性论与道德属性两个问题,两宋事功思想家对性理之学的第二条理论主线提出了有力的挑战。在人性论的问题上,李觏借鉴孟荀之争、杨雄、韩愈、荀悦的性三品说,提出了以作为绝大多数普通人的“中人”为分析对象的“性三品”〔8〕说,从人性角度对道德进行了相对化的论证。其中,王安石的人性论最为彻底,其认为“性不可以善恶言也”〔9〕,主张从祛价值化的角度来分析人性,实际上跳出了儒家传统“性善”与“性恶”论争的窠臼,将人性论向前推动了一大步。刘安节在王安石去价值化的人性论基础上,提出:“大抵人性靡常,惟君所尚”〔10〕,即运动、发展的人性观。两人的观点突破了性理之学关于人性纯善并且永恒不变的教条,事实上形成新的人性论范式——即祛价值化的人性分析。人性论之外,两宋事功思想家们还围绕道德的性质进行了论证。周行己认为“无不善,则亦无善之可称”,〔11〕即不存在绝对的道德。更为激进的是,周行己提出“仁……知不为道”〔12〕的观点,即“道”“理”是不具备价值特征的,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性理之学的第二条理论主线。可见,无论是祛价值化的人性论,还是将“道”“理”进行祛价值化,都否定了性理之学的第二道论证防线。从字面上看,周行己的“仁、知不为道”相比于王安石的人性“不可以善恶言”还是较为深刻的,因为其上升到了形而上世界,直接批判了性理之学的世界观与伦理观。而祛价值化的人性论只是在经验层次论“性”,没有直接对形而上世界进行批判。不过,既然性理之学中的“性”与“理”是同一的,那么对“性”进行祛价值化,与对“理”进行祛价值化实质上也是一致的。
在唯物倾向的世界观与相对主义的伦理观之下,两宋事功思想家提出了以事功为核心原则的政治理论。在政治原则层面,两宋事功思想家们反对性理之学将“王道”作为刚性而不可撼动的教条原则,认为“王道”与“霸道”并不是截然对立、不能共生的。王安石认为无论是“王道”,还是“霸道”,在实践中都得运用道德规范进行治理,否则政治统治就没有合法性,也就不能长久存在。〔13〕王安石并没有从动机出发专门分析两者的区别,但是,他认为,“王道”与“霸道”只是动机上有区别,而且这种区别并不如性理学家们说的那样严重(有一丝人欲动机即是邪恶),而是无足轻重于现实政治与治理。陈亮在与朱熹的“义利王霸之辩”中,提出了“义利双行,王霸并用”〔14〕的主张。无论在动机上,还是在行动上,陈亮都认为道德与事功可以并行不悖。这实际上是将“道德”与“事功”置于同一位阶,事实上,这不仅仅承认了“王道”与“霸道”的统一性与相容性,还打破了“理本器末”“义本利末”的形而上思辨结构。所以,朱熹视陈亮的观点为洪水猛兽,因为其论证同时突破了性理之学的三条主线。与陈亮同时,叶适提出了“王霸统一”的“实德”〔15〕论,即以事物、事功为基础的道德治理。叶适的观点比陈亮的观点更进一步,其重心在于强调“事功”是“道德”的现实依托,两者是内在统一的。总体上来看,陈亮与朱熹的辩论实际上还是在“王道”高于“霸道”的理学基本框架之下进行的,陈亮作为挑战者,其观点虽然犀利,但并没有进展到叶适的“王霸统一”的境界。在具体政策层面,两宋事功思想家们提出了经世致用的政策主张。针对两宋政府的“冗员”问题、财政问题、土地兼并问题、盐茶市场化经营、货币政策以及军事政策等方面,都提出了真知灼见。
三、两宋事功思想评析
(一)两宋事功思想与传统政治功利思想
两宋事功思想承上启下,联系春秋战国时期的功利思想与明清事功思想。其从功利视角解读道德,将儒家思想范式与功利的逻辑结合起来,在这种融合中实现了创新。
北宋中期后,改革派与顽固派发生激烈斗争,“荆公新学”地位受到动摇,事功思想的重心开始由朝廷转移到永嘉地区。此时“永嘉九先生”的儒家事功学说,开始形成体系化的永嘉学派。“永嘉九先生”是元丰年间永嘉九位就学于太学的士子,他们坚持唯物倾向的世界观、强调事功的伦理观以及推行务实的治理主张,在实践与理论中发展了事功思想。从留存的许景衡、周行己及“二刘”〔3〕的文献来看,“九先生”的事功思想已经发展到了新的阶段。如果说李觏、王安石与“皇祐三先生”是两宋事功思想的初创时期,那么“永嘉九先生”时期就是两宋事功思想批判发展的时期。两宋事功思想具有兼容并包的特色,这正是其推陈出新的动因。“永嘉九先生”的学术背景是较为综合的,除了继承前人思想如荀子学说、“荆公新学”、法家思想资源等,还有“正统”的二程“洛学”痕迹,也深具张载“关学”朴素唯物主义的烙印。这使他们能在批判“性理之学”的同时,汲取先进的思想,进行学术创新。另外,徐、周与“二刘”都曾经做过宋朝政府的重要官职。现实的政治实践,也给理论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养料。
第一,两宋事功思想借鉴道家以及同时期的理学思想,发展了具有儒家底色的唯物主义世界观。春秋战国之前,“五行”的朴素唯物学说就广泛流行,战国时期的儒家荀子也具有鲜明的唯物倾向。东汉王充以道家的“自然”为最高本体,以“无为”作为实践宗旨,将本体之“天”与物质之“气”统一起来,与董仲舒以来天人感应论的“人格神”之“天”形成了对立之势,较为系统地发展了朴素的唯物主义。南朝范缜在与佛教神学唯心主义的论争中,在“形神”、经验论、物质规律等方面着手,有针对性地发展了唯物论。北宋时期,理学家张载吸收前代唯物思想之大成,将物质之气作为宇宙本原的“气本论”,并将“气”进行辩证阐释,为宇宙的发展变化提供了动力。两宋功利思想家积极吸收了上述唯物思想的精髓,从北宋永嘉诸子的“理不离器”“道不离器”上升为“道在器中”,到南宋薛季宣的“道无本末”,本质上将“道”“理”的最高本体从形而上世界中解脱出来,回归经验世界,且已暗含对唯物论实在“本体”的发问。
如果个案需要继续接受服务,则在半年或一年后继续对个案进行专业评估,讨论制定个别化支持计划,继续进行专业服务。如果个案因为其他原因不宜继续接受该服务,则进行结案并展开定期追踪。
温衡发现半年不见,陶小西长高了,嗓音也变粗了,女生还坐在他的自行车后座上,陶小西顺着温衡的目光,才恍然大悟似的介绍了女生。
儒家功利思想与法家功利思想不同:第一,两宋儒家功利思想以善治作为功利激励的目标。与法家单纯强调功利不同,两宋儒家功利思想中的功利论证是以道德的规范为前提的。另外,儒家功利思想强调功利激励中人的实现。如果说法家是以人为工具达成利益秩序,那么,儒家的功利激励则是为了达成君子主导的善治;第二,两宋儒家功利思想主张君臣、君民利益共同体。这种观点主要体现于陈亮、叶适等人的著作中,主要认为君臣、君民之间根本上具有共同利益,而不是如法家所言的利益冲突。两宋儒家功利思想坚持儒家德治的政治传统,认为德治不是形而上学的空谈,而是切实解决和发展臣民的基本利益,建立君臣、君民之间的利益共同体。在“义利双行”“义利统一”的逻辑下,善治体现为君臣、君民之间和谐利益关系;第三,两宋儒家功利思想阐述了“权变”的学说。许景衡、叶适等人专门探讨了这个问题。当道德规范与功利发生冲突时,是否能以功利对道德规范进行权变,既是儒家功利思想对法家的借鉴,也是其与性理之学的重大分歧。两宋功利思想认为,在极端情况下允许功利对道德进行权变,但这只是特殊规则,是不得已才能使用的。
第三,在与性理之学道德神圣化观点的论争中,两宋功利思想主张将道德与超验“本体”——“天理”区分开来。这种思想主张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将“理”与“道”在形而上世界与“仁”“义”“礼”“智”等道德区分开来,主要体现为周行己等人的观点;第二是将经验世界的“性”与道德进行区分,形成经验世界对人性的“祛魅”,集中体现于王安石的观点;第三是继承荀子将道德客观化的思维,以客观化的“礼”来概括道德,主要体现于李觏的观点。当然,两宋功利学者只是从形而上学的本体论中解放道德,并没有放弃道德高于功利的观点,这也是其功利思想区别于法家思想的根本特点。
(二)两宋事功思想与传统政治哲学
〔1〕“宋初三先生”,指北宋时期性理之学的三大奠基人,即“安定先生”胡瑗、“徂徕先生”石介、“泰山先生”孙复。
值得注意的是,两派王霸思想的对立是在儒家对比三代,反思汉唐政治的讨论中出现的。在儒家传统中,尧、舜、禹三代是道德政治的理想范式。但是,汉、唐以来,封建统治者在争权夺利中灭绝天理人伦的事实,震撼了儒家学者。汉唐政治是否具备合法性,成为了王霸争论的焦点。事功思想从三个方面对汉唐政治进行了肯定:第一,政治革新的合法性。性理之学以永恒、静止、绝对的“天理”为论据,认为道德的政治是不容忍革新的,尤其是因功利而进行的革新,更是大逆不道。而事功思想则针锋相对,认为汉唐的政治革新不仅现实必要,而且合理合法;第二,道德与法之间的关系。性理之学认为道德决定法律,道德不变,法律亦不变。功利思想认为不然,法是可以根据具体时势的变化而变化的。这主要体现在郑伯熊的思想及其与朱熹的讨论之中;第三,是否承认汉、唐君主进行“权变”的合法性。叶适用很大篇幅论述“时”“势”的问题,陈亮更是在“义利王霸之辩”中为汉唐君主鸣不平。“霸道”之所以在汉、唐得以运用,是因为时势变化所致,汉唐君主不得已采取部分“权变”的办法,无损于其整体上施行的“王道”。
另外,重视“民利”是两宋功利思想家们的普遍主张。他们吸收了孟子“无恒产则无恒心”的思想,认为统治者保障人民基本的生存利益,是其政治合法性的必要条件。这里的“民利”虽然还不是尊重个体的利益,但是作为全体人民的“民利”既然能够成为政治合法性的基础,那么实际上就提出了政治合法性“绩效”基础的初步观念。与此相关,两宋功利思想承认利益的普遍性和必然性,主张尊重利益的规律,事实上回归了经验的人性,已经初步具备了反封建的启蒙意义。两宋功利思想重视民利的主张,为后来的明清事功思想所继承,并且成为明末清初反封建思潮的重要理论来源。
(三)两宋事功政治哲学的理论特色
第一,两宋事功政治哲学建基于专制主义政治哲学。虽然其强调普遍的、以家庭为单位的民利,但是,它们是建立在君利的基础上的,更谈不上个体权利。在儒家传统中,民利只是君主统治合法性的一个指标,即不能兼顾民利,政治统治就不正当。显然,其重心不是在于民利,而是君主的利益。此外,性理之学与功利之学的重要区别在于是否允许以功利对道德进行权变。这种权变,既可以民利为由,也可以君主的利益为由。显然,事功思想的权变主要指前者,但对于后者却并未明确否定。在个别思想中,甚至主张应当保障君主的特殊利益。而性理之学则严守孟子范式,对两者都坚决否定。〔16〕从这个意义上说,两宋事功思想虽然整体上承认民利,具备启蒙意义,但却没有完全脱离专制主义的逻辑。而性理之学虽然根本上否认民利,典型地体现了专制的色彩,但对君主也有一定的限制。〔17〕
第二,具有现实主义政治哲学的思想色彩。在两宋性理之学流行,人们思想僵化的背景下,事功思想重视实践、经验与发展的观点,无疑具有鲜明的思想解放意义。两宋功利思想继承了孔子的事功传统与荀子的现实主义范式,认为君子只要坚持道德的主导作用,重视现实的功利并不为过。不仅如此,所有的道德政治,最终都离不开利益的考量。另外,两宋功利思想是同当时政治军事的弱势密切相关的,与性理之学坐议论道的夫子们不同,两宋功利学者关注现实的国计民生、在理论和实践上都积极努力以统一国家,这无疑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
第三,构建了“王霸”统一的德治观。两宋功利思想既不同于性理之学僵化地坚持“王道”,也不同于法家思想一味地强调“霸道”,其政治思想是王霸统一的治国理论。与西方政治思想史中马基雅维利与中世纪封建神学的斗争相似,两宋功利思想也是在与占据主流地位的意识形态——性理之学进行论争中发展的。两者都体现了某种现实主义的“统一”特质。马基雅维利认为,君主应当是“狮子”与“狐狸”的统一体,威力与智慧并重。而两宋功利思想则认为君主应当兼用“王道”与“霸道”,道德与功利并重。虽然马基雅维利的“狮子”与“狐狸”都属于现实主义功利政治层面,但是,其具有彻底的工具主义色彩。考虑到两宋功利思想家先于马基雅维利400多年,因此,其思想的进步性与超前性是不容置疑的。从这种对比中,也可以看出东方利益政治思想的特质,即道德与功利相统一,物质需要与精神超越相统一,体现在政治层面,就是既承认利益,又注重通过规范消弭冲突、形成和谐利益关系,最终实现利益全面发展的“王霸”统一的政治思想。
第六,具有鲜明的功利主张与初步的启蒙意义。两宋事功思想以功利为标准实现善治,承认普遍人性中的功利内容,鲜明地论证功利的正当性,这是其历史特色,具有现代性的初步启蒙意义。两宋时期的功利思想家在研讨中之所以直言功利,主要原因在于:首先,在理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之前,功利之学一度成为北宋政府的官学。王安石变法是荆公新学的重要推手,面对国土分裂的形势,两宋政府中始终存在着主张事功的改革派,其指导思想正是功利主张,因此,两宋时期的功利思想十分鲜明地主张功利的正当性;其次,魏晋南北朝到唐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思想活跃期。这一时期的政治特点在于,要么中央集权较为薄弱,无法对思想界进行强力控制,要么中央政府(唐)对思想界十分开明,由此使得各种思想一定程度上能够得以发展,形成了佛、道、儒以及诸多外来文化的交流碰撞。在两宋时期,儒家内部还发展为理学、心学、事功三大学派相互鼎立的格局。显然,相对宽松的思想环境,无疑为当时功利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条件;第三,儒家发展至明清,“功利”的提法逐渐被“事功”全面代替。居于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理学的压制,导致儒家学者不愿轻言“功利”的提法,逐渐以“事功”替代“功利”,形成较为稳妥的,可以为其它儒家学者接受的表达。
第二,在唯物论的基础上,两宋事功思想继承了荀子的现实主义传统,在功利、事物的基础上分析道德,与同时期性理之学从“天理”绝对本体来理解道德形成截然区别,从而在儒家内部形成了两种不同的道德论证范式。两宋功利思想家以儒家孔子开创的事功传统为根基,吸取法家思想精华,在与性理之学的辩争中形成了“义不离利”“义利双行”“义利统一”等道德观念。
第五,功利思想的阐述与治理天下的具体方略和政策紧密联系。两宋功利思想家对于功利思想的阐述,除了纯粹的规范性思辩论证之外,更多地是以对于治理天下的实际战略、方略、原则和政策的方式呈现的。或者说,他们的功利思想大都是在对于治理天下的实际问题的分析和阐述中得以表现和展开的,因此,其功利思想更多体现在对于具体的国是政务的现实主义阐述,体现为对于所处时代国家治理实际任务的见解和阐发,体现为处理和对待国家治理事务的功利性主张。因此,两宋功利思想,许多时候看起来并不是政治哲学的阐述,而是对于现实治理事务的分析和主张。但是,这种与现实的国家治理事务紧密联系,并且在对于这些事务的实际看法和见解中展开,恰恰是两宋功利思想的重要特点。
第四,形成了“中庸”政治思想解读的新范式。在儒家政治思想中,“中庸”心法是核心的行为准则。“中”即标准或准绳,“庸”则指日常和运用。《尚书》强调“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只有遵循了“道”,统治才能无偏正当。这种思想被性理之学所发挥,形成了在政治活动中对“天理”的崇拜。而事功思想则以事实为准绳,以致用为依据来解读“中庸”。事实上,孔子十分重视事物与功利,如“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荀子则进一步形成儒家学说的现实主义范式。两宋事功思想将“中”的标准从形而上的境界中解放出来,认为“中庸”的运用应当是实践导向,而不是以神秘直觉坐议论道。与性理之学相比,功利思想的王霸并用也是一种真正的“折中”,并没有走偏执于“天理”与德治的极端。
注释:
“王道”与“霸道”的争论,是中国古代政治哲学发展的主要线索。两者的关键区别在于是否强调以道德规范进行政治统治。两宋时期,儒家将王霸争论与政治合法性问题统一起来。性理之学以儒家“道统”自居,认为只有以纯粹的、绝对的道德规范进行统治的“王道”,才能证成政治合法性。事功思想则弘扬了孔子的某些观点和荀子的范式,认为主导地位的“王道”并不是唯一的合法性来源,以功利为基础的“霸道”也应当有其空间。王安石、王开祖、叶适与陈亮等人对此展开讨论。王安石主要从动机区别入手分析两者,认为“王道”与“霸道”在客观上是一致的,两者的关键区别在于统治者是否有美德的动机;王开祖则认为统治者可以运用“霸道”,但是其动机必须符合道德的要求;陈亮在与朱熹的辩论中,提出了“义利双行、王霸并用”的政治理论,动摇了性理之学的哲学与政治逻辑;叶适则着眼于“王道”与“霸道”的共同点,认为两者本质上具有一致性。
针对一些有天生残疾或者后天有缺陷的学生来说,心理健康教育是非常重要的,在一定程度上,这些学生更易产生心理问题,而且周围的学生的冷眼目光会有意无意的刺激到这些学生。所以学校要定期举行一些可以让这些同学参加进来的活动,在活动中展现自己,在掌声中更加自信。齐齐哈尔大学图书馆在近两年年的世界读书节都会举行经典美文诵读比赛,每年的比赛都有个别身体有缺陷的同学参加,但是每次比赛他们都是靠自己的实力取得很好的名次,而且也得到了学生和老师们的广泛关注,在一定程度上对这些学生的心理产生的积极向上的影响。
〔2〕“北宋五子”,指“宋初三先生”之后,将性理之学概念进一步体系化的周敦颐、程颐、程颢、邵雍以及张载五位思想家。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的高校是社会主义的高校。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判断,不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也必将产生深远影响。从根本上讲,这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21世纪的伟大宣言: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不动摇,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动摇。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也是我国大学最鲜亮的底色[3]。因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新的历史方位中,高等学校责任重大,必须继续坚持办好社会主义大学的原则,坚持办学的正确政治方向,承担起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人才的历史使命。
〔3〕时人称作为兄长的刘安节为“大刘先生”,刘安上为“小刘先生”,二人合称“二刘”。
〔4〕〔8〕〔宋〕李觏:《李觏集》,王国轩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1、12页。
〔5〕〔9〕〔13〕〔宋〕王安石:《王安石集》,张富祥、李玉诚注说,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75、224、213页。
〔6〕〔10〕〔宋〕刘安节:《刘左史集》,《钦定四库全书》(卷二),北京:中国书店,2014年,第23、11页。
1.2.3 人格测定 采用艾森克个性问卷(幼年)(EPQ)[8],该量表是由英国心理学家艾森克教授于1975年编制,其中国版由龚耀先教授主持修订。由E、P、N、L四个量表组成,E、P、N 三个量表包括了艾森克个性理论的三个要素,E量表表示内-外倾向,P量表表示心理变态倾向(精神质),N量表表示情绪的稳定性(神经质),L量表表示受试者的掩饰程度。
〔7〕〔宋〕薛季宣:《薛季宣集》,张良权点校,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332页。
〔11〕〔12〕〔宋〕周行己:《周行己集》,陈小平点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3-14、14页。
〔14〕〔宋〕陈亮:《陈亮集》,邓广铭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81页。
〔15〕〔宋〕叶适:《叶适集》,刘公纯、王孝鱼、李哲夫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635页。
〔16〕对孟子“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等“大逆”言论,明太祖朱元璋曾经对其进行删减,试图推行《孟子节文》,但因坚持儒家“道统”纯粹性的知识界的联合抵制而未能成功。
〔17〕韩愈提出“道统”(儒家正统思想的合法性)论,二程自称是“道统”的继承人,而朱熹又自称是二程的继承人。其思想定位本身就具备某种同“政统”(政治合法性)分庭抗礼的意图。在实践中,程颐、朱熹都曾经对皇帝的人身自由大加进言,令哲宗十分害怕程颐,宁宗十分讨厌朱熹。
DOI: 10.3969/j.issn.1002-1698.2019.09.011
作者简介: 赵滕,北京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王浦劬(1956—),《学术界》本期封面人物,江苏盐城人。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至1988年先后获北京大学法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1991年任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副教授,1995年破格晋升为教授。现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位分委员会主席,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主任),“国家治理协同创新中心”联合主任。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政治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政治学科评议组召集人、教育部高等学校政治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第一批领军人才。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政治学组首席专家。主要研究领域为政治学理论与方法,当代中国政治与治理。编撰出版《政治学基础》《选举的理论与制度》《以治理的民主实现社会民生》《政道与治道》等作品;主编《当代中国治理丛书》《西方政治学经典著作译丛》《西方政治学经典教材》等作品;在《求是》《北京大学学报》《政治学研究》《中国行政管理》等刊物上发表六十余篇学术论文,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转载;曾经或正在主持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教育部跨世纪人才项目等二十余项科研项目。
〔*〕本文系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项目“利益政治学”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汪家耀〕
标签:性理之学论文; 事功思想论文; 文化意义论文; 北京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