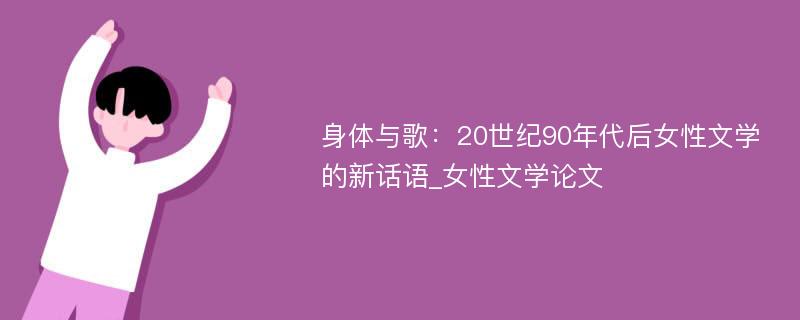
身体与歌——20世纪90年代后女性文学新话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话语论文,身体论文,年代论文,女性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新时期女性文学的发轫并没有女权解放运动在前面开路,而是以思想解放的大潮为前 导。当禁止自由思想的紧箍咒一旦去掉,女作家们首先意识到的是女性的存在,就像伊 甸园中的夏娃发现自己是个女人一样,恢复了女性的性别意识。她们开始把女性作为一 个生存群体去考察,以女性的亲身体验去描写女性的气质、女性的命运、女性的追求、 女性的烦恼、女性的痛苦,去描写妇女因性别而引起的一切幸与不幸。
女性文学在风起云涌的发展路上,渐渐地受到了西方女性写作和阅读理论、女性主义 批评理论的影响,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直到新世纪之初,不断地出现女性文学的新话 语,其中,最重要的是女性对身体的自我发现、觉醒和思考。向来只见衣服不见身体, 只描画灵魂不描画身体的女性文学有了直面身体、正视身体、表达身体的变化,从文学 的立场阐述身体,为身体命名,为身体定义,出现了一批具有严肃的正面建设意义的作 品。从王安忆的《岗上的世纪》和《小城之恋》、铁凝的《玫瑰门》,到林白的《一个 人的战争》、《空心岁月》、《致命的飞翔》,再到张抗抗的《情爱画廊》、《作女》 ,直到黄蓓佳的《没有名字的身体》,完成了女性文学向身体回归的历程。在这些作品 中,女作家们把身体和身体欲望作为审美对象来表达,通过诗意的抒写,呈现出以前未 曾揭示过的美感。同时,又通过身体去表达女性独有的欲望体验、情感体验、生存体验 ,从而填补了文学的空缺。而在价值取向上,则依然遵循灵魂高于身体的人文理想,并 未坠入身体至上的陷阱,失却精神的气息。
法国女性主义作家埃莱娜·西苏在《美杜莎的笑声》中曾经指出:“通过写她自己, 妇女将回到自己的身体。”(注:《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 版,第193、191、196、195、196页。)中国女性文学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发展正合此 道。女性文学的本体就是女性的性别写作,从女性生命的感觉、感受、感悟出发,去寻 求与人们、与社会、与世界的对话,女性生命的幽暗隐秘之处,只有通过女性的性别写 作才能获得表达,其中很重要的一环是身体表达。而多少年来,女性对自己的身体是不 可言说的,正如埃莱娜·西苏所说的那样:“身体被幽禁、被妥善保存着,完整如初地 珍藏于她自己的镜中。”(注:《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第193、191、196、195、196页。)林白的长篇小说《空心岁月》中也有同样的话语: “有一些女人就要从镜子里出来了,她们最英勇最活泼,因此最美丽,她们的身体触碰 到镜子冰冷的表面,我听见发出了咝咝的声音,这种声音灼伤着她们的皮肤,灼痛着她 们的眼睛,但我们最后听见乒的一声,镜子在空中舞蹈着,碎破在地上。”女性身体破 镜而出,作为破镜者的女作家们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而打破镜子的力量则来之于女性 写作的使命感,来之于文化的突围,来之于深刻的生命感受,她们聆听到了女性身体的 各种音响,聆听到了“我的身体,充满了一连串的歌”(注:《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93、191、196、195、196页。)。是这种女性集体的 身体记忆,把女作家们推向了表达身体的前沿,要把被驱离的身体写进文本,要把被幽 禁的身体释放出来,要把身体中的一连串的歌表达出来。
然而,身体之歌的表达并不容易,埃莱娜·西苏说过:“肉体不比上帝、灵魂或他人 更容易描写,你的那一部分在你自身中留下一片空间,并且鼓励你用语言去刻画你的妇 女风格。”(注:《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93、191 、196、195、196页。)难度、空间、风格,这就是女性文学进入身体叙事所面临的审美 课题,中国严肃的女作家们对此作出了许多成功的艺术探索,她们在身体与歌之间所建 立起的各种审美联系值得赞许,弥补了文学叙事中的历史性缺失。
二
首先,她们开始追寻女性身体的自然的美丽,把女性身体之美放进了审美空间。在20 世纪80年代女性文学的发轫期,“一个崭新的、可爱的、美好的,因而也富有魅力的精 神世界”是女作家们观察和描写女性的主要观点,她们尚未去欣赏、描画美丽的女性身 体。只有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女作家的笔下,才出现美妙、和谐、高雅的女性身体 的画面。
这些女作家对身体的审美注视和审美表达有着很强的精神性,出于文化的突围动机, 正如张抗抗在《情爱画廊》中借主人公画家之口所传达的那样:“当中国人能坦然而纯 真地欣赏自家客厅墙上悬挂的人体油画艺术作品时,这个民族大概才能真正面对精神的 解放和自由。”纯粹地去欣赏人体美,将真正的人体美表达出来,这就是女作家们对身 体命名的一种方式,让身体回归到审美对象使之成为歌的一种方式。美国乔治·桑塔耶 纳在《美感》中指出:“生理快感与审美快感之间有着十分明显的区别;审美快感的器 官必须是无障碍的,它们必须不隔断我们的注意,而直接把注意引向外在的事物。”( 注:乔治·桑塔耶纳:《美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4~25页。)欣赏 人体美的障碍就在于欲望,无论是出于欲望去描写身体,还是为了欲望去描写身体,都 不属于真正的纯粹的人体的审美表达。“在别的快感中,我们满足我们的感官和情欲; 在审美观照中,我们却能神驰身体,使情欲平静下来,我们认识了一种我们并不想占有 的善而感到快乐。”(注:乔治·桑塔耶纳:《美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第24~25页。)这样一种人体审美的精神境界正是女作家们所肯定、所追求和所表达 的。这种境界在华夏美学和华夏文化中历来缺少,女作家们的补缺意义也在于此。
为了实现对身体的全新表达,女作家们采取了新的视角。在林白那儿,是女性欣赏女 性身体的叙述,叙述人“我”是女性,无论在叙述自己的故事还是别的女性的故事,都 以女性身体的崇拜者和窥视者的面貌出现,形成同性欣赏的情景,但又极力避免性别角 色的暧昧不清,努力与同性恋划清界限。她的中篇小说《致命的飞翔》的女主人公李莴 认为这样才能找到“女性的真正的美”:“我想我应当做一名摄影家。不是摄影者,而 是摄影家。后者意味着更高的技能和对美的发现,这样才能配得上北诺。我将以一个女 人的目光(我的摄影机也将是一部女性的机器)对着另一个优美而完美的女性,从我手上 出现的人体照片一定去尽了男性的欲望,从而散发出来自女性的真正的美。我想起另一 个女人拍摄的以陈冲为模特儿的人体摄影,那种美丽十分接近我的理想,我有时沉浸在 这种美丽之中,就像月亮悬浮在冰山之上,清凉、空彻,一切无关的东西都远离。”女 性的视角、女性的立场在这里表露无遗,是剥离了男性欲望看女性身体后产生的新话语 ,追寻一种冰清玉洁的女性身体的审美境界,冰清则是无欲的“清凉、空彻”,玉洁则 是如玉的美丽的女性胴体,只有冰清才能玉洁。
实际上,林白提供了女性身体审美的双重前提,一是无欲,二是艺术,所需要的是浑 然忘欲唯有艺术的欣赏目光。无独有偶,张抗抗的长篇小说《情爱画廊》亦表现了同样 的审美理想,叙述策略采取的是画家的视角,“画家并不带着渴而思欲的眼光来看一池 清水,也不带着荒淫好色的眼光来看一个美人。”(注:乔治·桑塔耶纳:《美感》,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4~25页。)尽管张抗抗笔下的画家周由是位男性, 然而专攻人体油画的画家专业身份却使得他有可能对女性的身体作排除欲望的艺术欣赏 。当周由初遇苏州美女水虹时,就只是以画家的眼光去审视她,在给她作画的过程中, 美感与欲念不断地在他心中相争和较量,他为了画出真正的人体美而努力压制时常冒出 来的欲望。周由内心经历了“对美从惊叹到感慨、由崇拜而赞美、然后是追索、是记忆 、是体察、是思辨的全部的心路历程”,“最后他甚至已忘了她的存在,他面对的似乎 只是一个美的幻影和美的精灵”,“忽然觉得自己多年来对美的追求,今天才走到了最 高境界,一种他想都不曾想到的境界。他心里一片纯净一片圣洁,无爱无欲,唯有对美 的膜拜。”登上这样的审美境界,他才画出了能够真正表现出水虹身体美丽的画像。
因此,在《情爱画廊》中,通过画家和美女邂逅的故事,张抗抗表达的是对女性身体 审美的期待和想像,在审美的层面为身体命名,为身体的审美性正名。更为深刻的是, 张抗抗对女性身体的审美表达,融入了民族审美意识,进入到民族文化的层面,将吴地 女子的美丽与水文化、玉文化、丝文化联系在一起,阐释女子肌肤如水般晶莹、如玉般 温润、如丝般柔滑的美感,而有别于西方女子的美感,属于华夏美学对女性身体的审美 观念和审美方式。
三
女作家们对女性身体的自我表达有着双重的笔墨,当她们以剥离欲望的叙述策略让身 体回归纯粹的审美时,并不意味着否认身体的本能欲望,恰恰相反,她们表达身体的另 一重笔墨就在于确认身体是性的负载体,既表达身体之美,亦表达身体之欲,通过确认 性在情爱中的位置发现身体的另一支歌,来进一步为身体命名。王安忆曾经如此来注解 自己的作品:“我尝试着将爱情分为精神和物质两部分:写情书、打电话、言语都是精 神方面的,而物质部分就是指性了。……《岗上的世纪》可以和《小城之恋》一块看, 它显示了性力量的巨大;可以将精神扑灭掉,光剩下性也能维持男女之爱。”(注:《 王安忆说》,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39页。)黄蓓佳的长篇小说《没有名字的身 体》叙述身体法则,直接抒写女主人公在四次恋情中身体的不同反应,从身体的真实体 验中获得了对爱情的完整感悟:“我开始醒悟到,男女之间相爱到了一定程度,是必须 要用身体作许诺的,如果彼此的肉体没有撞击、交汇和渗透,没有大汗淋漓的缠绕、筋 疲力尽的付出、淘空一切的给予,没有喘息、吟哦和战栗,爱情就是空中楼阁,是水中 月镜中花,虚伪到爱恋的双方都不辨真假。”“有性之爱和无性之爱完全不一样,爱情 落实到身体,就像种子落回了大地,有了水,有了养分,有了温度,是一种死心塌地的 归附。”这无疑是一篇身体的宣言,宣告身体是不能忘记的。当然,这更是一支身体之 歌,曾经被压抑、被歧视、被轻视、被忽视的身体之歌。这是一支更为隐蔽的身体之歌 ,隐藏在女性生命的深处,只有女性自己才有深切真实的体验,正如林白在长篇小说《 空心岁月》中告白的那样:
我总是看到我自己、我的女友们、报纸上披露的素不相识的女人,所有这些另一种性 别的人们被爱情所伤害,她们在半夜里哭泣和自杀,或者暗中憔悴。有一种东西,只有 她们才能感觉到,她们的眼睛、皮肤、心和触角在她们青春的岁月里经过性别的浸泡, 变得高度敏感和脆弱,她们即使闭着眼睛把手放在空气里,也能感觉到那种东西是否在 流动,它轻微的流动像水一样明确,并立刻涨满她们的全身。
倘若我们回顾一下女性文学20年来的历程,那么在文学记忆中首先浮起的是张洁的经 典短篇《爱是不能忘记的》,由此出发到达黄蓓佳的《没有名字的身体》,走了一条从 柏拉图之爱到身体之爱的路线。从爱的觉醒到身体的觉醒,的确是前进了一大步,个中 意义可用张抗抗的一段话来说明:“我想‘女性文学’有一个重要内涵,就是不能忽略 或无视女性的性心理。如果女性文学不敢正视或涉及这点,就说明社会尚未具备‘女性 文学’产生的客观条件,女作家亦未认识到女性性心理在美学和人文意义上的价值。假 若女作家不能彻底抛弃封建伦理观念残留于意识中的‘性 = 丑’说,我们便永远无法 走出女人在高喊解放的同时又紧闭闺门,追求爱情却否认性的怪圈。”(注:《关于女 性文学的对话》,《香港文学》第72期。)
正因为如此,严肃的女作家们在表达身体之欲时亦坚持审美注视,用审美观照去展现 其美好的一面,用诗意的描述去捕捉其美好的境界,从而再一次在身体与歌之间建立了 审美关系,将女性身体的快乐上升到精神的快乐,前者是性快感,后者是性愉悦——两 性相悦的境地。基于这样的追求,她们对性爱中的女性身体的表达,远离了粗俗、色情 与低级。请看林白的描写:“她感到男人到达了她的上方,她张开她的身体等待得救, 她摊开两条胳臂,像一只鸟儿,即将随着一股气流飞上蓝天。”(《致命的飞翔》)用审 美的语言和象征化的手法,将身体的欲望阐释为飞翔的感觉,完成了肉体到精神的转换 、快感到美感的转换。在《情爱画廊》中,这种转换是凭借一幅幅绘画来完成的:“那 些画面传递出远古人类性图腾素朴和虔诚的精神。在那个绝对自我而隐秘的角落,依然 探索着尝试着某种高位回归。”
很显然,女作家们把身体作为性的负载体来确认和肯定,去歌唱身体的快乐之歌,是 有着“高位回归”的审美理想的。如何才能“高位回归”?如何区分丑陋或者美丽?如何 区分粗俗或者高雅?这些女作家们交出的答案仍然是“爱”,仍然是“爱是不能忘记的 ”,从爱出发,经过身体的洗礼,再回归到爱,她们在爱情的框架中言说身体,她们的 身体之歌充满了美与爱。
四
身体觉醒以后,不仅仅成为表达的对象,也成为表达的手段,女性文学几乎在表达身 体的同时,也开始了身体表达。所谓身体表达,埃莱娜·西苏解释道:“她是在用自己 的血肉之躯拼命地支持着她演说中的‘逻辑’。她的肉体在讲真话,她在表白自己的内 心。事实上,她通过身体将自己的想法物质化了;她用自己的肉体表达自己的思想。” (注:《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93、191、196、195 、196页。)女性的身体一旦被打开,一旦被表达,那么将可以重新思考女人,重新认识 女人,重新表达女人,用身体来思考,用身体来表达,在身体与歌之间找到另一种审美 关系,形成有独特风格的女性性别语境。
于是,对女性人物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的一种新的诠释产生了,不仅仅挖掘其心理 基础,还挖掘其生理基础,从精神和身体两个方面进行叙述。张抗抗的长篇小说《作女 》就是如此,作品刻画了一个永远在生活中寻求变化的“作女”卓尔的形象,卓尔的“ 作”,从根本上来说,是出于寻找自我的价值观。除此之外,张抗抗还将她的“作”与 身体的行经感觉联系起来,专门写了一章“‘作’的欲望从哪里来?”叙述了月经对卓 尔性格的影响:
如今的卓尔已深信不疑,她身上所有的变化,都是从14岁之后那月月的“井喷”开始 的。那些发源于她体内、颜色时浓时淡的石油,一滴一滴地送走了她安静乖巧的童年。 它们不邀自来地在她的身体里拱动,一次比一次剧烈,一次比一次澎湃;每一次疼痛过 后,她会觉得自己全身的毛孔都在扩张,细弱的肌肉和单薄的皮肤,包括她平坦的胸脯 ,都在一寸寸膨胀,像是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了。即使是在它们悄然蛰伏的那些日子, 她也能感觉到血管中蠕涌的那种燥热和冲动,正在一日日积攒着喷发的力量,常常搅得 她心神不定。
女主人公卓尔就是如此时常能够强烈地感觉到身体内有一股翻腾激荡的物质在寻找出 口,使她产生“作”的欲望,这是精神力量的物质根源,女性生命经验的自我袒露和空 前展示。在张抗抗的笔下,卓尔的身体感觉与精神感觉合而为一,一次新的折腾变化, 就会让她获得类似行经后的感觉:“她的身体都会获得一种飘飘然的轻盈和轻松”,“ 都带给她一种大江凫游和温泉沐浴的感觉。”这是女性的身体与精神的自我组接,开辟 了身体与歌的又一片空间。
女性文学中的身体表达也并不只用于女性的自我阐释,它的审美的功能正在女性写作 中不断地被扩大。试看散文《母性的草原》(阿拉旦·淖尔)的开头:
从我躺在阿扎睡了四十年的青羊皮褥上被自己鲜红的初潮吓哭的那个早晨起,我就固 执地认为:
草原——是母性的。
女性的生命体验被用来描绘自然,对自然的审美感受不是来之于精神素养,而是来之 于身体的内驱力,应该说,这是一种崭新的审美关系,同样属于女性文学独特的性别语 境。再看这篇散文的结尾:
我的感情注定了我是一个属于草原的女人,我的身体打开就是一片柔软的青草地。山 山水水满坡牛羊游走在我的身体上,游过我高高的乳房和辽阔的胸脯,游过我左腿右腿 细长而粗壮的山梁,游过我宽大的额头和鼻梁很白的雪峰和我脚下的柔软的草地。
这是一种全新的表达,同时表达身体和草原,身体和草原互为表达,身体和草原合为 一体,既是表达身体,又是身体表达。身体内的歌已在身体外的自然之中得到了回应、 反响和融合,这也许就是身体与歌的更为广阔的空间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