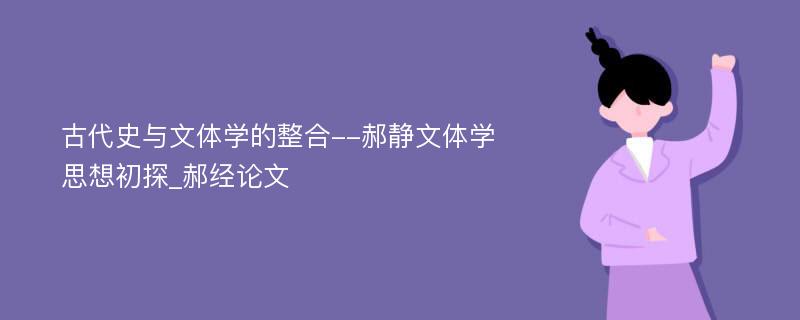
经史一体与文体谱系——郝经文体学思想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谱系论文,经文论文,文体论文,思想论文,经史一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7)08-0140-05
郝经是元初有重要影响的理学家和文学家。四库馆臣在《陵川集》提要中说:“其生平大节,炳耀古今,而学问文章,亦具有根柢,如《太极先天诸图说》、《辨微论》数十篇,及论学诸书,皆深切著明,洞见阃奥。《周易》、《春秋》诸传,于经术尤深。故其文雅健雄深,无宋末肤廓之习;其诗亦神思深秀,天骨挺拔,与其师元好问可以雁行,不但以忠义著者也。”[1](P1422)高度评价郝经的人品、学问,并以其诗文与元好问相提并论,足见推重之意。可是,在此后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郝经极少引起学界的关注。直到近30年来,才开始出现一些关于郝经的专题论文,论题则主要集中在其理学思想、文学观念及文学创作成就上,而对其文体学成就,几乎无人涉及。①实际上,郝经有《原古录》、《文章总叙》等重要文体学论著,其中蕴含着丰富而独特的文体学思想,理应得到文学与文体学研究者更广泛的关注。
一、经史一体说
郝经家世儒业,是元初最早接受程朱学说的北方儒者之一,又是一位积极有为的政治活动家。因此,其读书治学重视实用,力图把儒家理论与治国安邦结合起来。早年作《志箴》曰:“不学无用学,不读非圣书。不为忧患移,不为利欲拘。不务边幅事,不作章句儒。达必先天下之忧,穷必全一己之愚。贤则颜孟,圣则周孔,臣则伊吕,君则唐虞。毙而后已,谁毁谁誉?讵如韦如脂,趑趄嗫嚅,为碌碌之徒欤?” [2](卷21《箴》)足见其经世致用的儒学旨趣与理想抱负。
郝经一生信奉儒道,推崇六经。在他看来,道是具体可感的,存在于天地万物中,而总萃于人,尤其是圣人。六经则是道的形器,是圣人载道、传道的工具,“故《易》即道之理也,《书》道之辞也,《诗》道之情也,《春秋》道之政也,《礼》、《乐》道之用也。至中而不过,至正而不偏,愚夫愚妇可以与知,可以能行,非有太高远以惑世者”,“谓夫虚无恍惚而不可稽极者,非道也。谓夫艰深幽阻高远而难行者,非道也。谓夫寂灭空阔而恣为诞妄者,非道也”,“至易者乾,至简者坤。圣人所教,六经所载者,多人事而罕天道,谓尽人之道,则可以尽天地万物之道”。[2](卷17《论八首·道》)可见,郝经的道,不同于天道、性理、象数等抽象、玄虚、高远的观念,而是以人事为归依,明而易见,近而易行的。六经则从不同方面反映了道的内容和精神,是客观世界与现实生活的表现,而非至高无上的神圣教条。
六经既是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生活的反映,自然在某种意义上具备史的性质。《春秋制作本原序》:“《春秋》以一字为义,一句为法,杂于数十国之众,绵历数百年之远,而其所书虽加笔削,不离乎史氏纪事之策,而无他辞说。”[2](卷28《序》)明确指出《春秋》纪事的史体特征。又《一王雅序》:“六经具述王道,而《诗》、《书》、《春秋》皆本乎史。王者之迹备乎《诗》,而兴废之端明;王者之事备乎《书》,而善恶之理著;王者之政备乎《春秋》,而褒贬之义见。圣人皆因其国史之旧而加修之,为之删定笔削,创法立制,而王道尽矣。”[2](卷28《序》)这里把经与史更密切地联系起来。首先,在起源上,六经中的《诗》、《书》、《春秋》是圣人“因其国史之旧”修订而成的,可谓经、史同源;其次,在内容上,三部经典分别反映了王者之迹、王者之事、王者之政,换言之,即王者之史。六经所传王道,是通过王者之史体现出来的。合此二端,则经、史本为一体,分疆划界,实出后世。《经史》曰:
古无经史之分。孔子定六经,而经之名始立,未始有史之分也。六经自有史耳。故《易》即史之理也,《书》史之辞也,《诗》史之政也,《春秋》史之断也,礼乐经纬于其间矣,何有于异哉!至马迁父子为《史记》,而经史始分矣。其后遂有经学,有史学,学者始二矣。经者,万世常行之典,非圣人莫能作。史即记人君言动之一书耳,经恶可并?虽然,经史而既分矣,圣人不作,不可复合。第以昔之经而律今之史可也,以今之史而正于经可也。若乃治经而不治史,则知理而不知迹;治史而不治经,则知迹而不知理。苟能一之,则无害于分也。[2](卷19《论》)
从学术发展史的角度,指出“古无经史之分”,明确倡言并具体论证“六经自有史”。汉代以后,经史由同源而分流,已不可逆转,经主阐发义理,史主记载事迹。尽管如此,两者依然互相渗透,互为依存,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这不仅因为二者同源,更因为经和史,义理和事迹,与天地万物一样,都是道的形器,是道在不同内容与性质上的不同表现形式。
郝经的经史一体说在宋元时期并非空谷足音。南宋末叶适《徐德操春秋解序》曰:“盖笺传之学,惟《春秋》为难工。经,理也;史,事也。《春秋》名经而实史也,专于经则理虚而无证,专于史则事碍而不通,所以难工也。”[3](P221)虽仅就《春秋》一经而论,对郝氏的影响则显而易见。叶适为南宋“事功派”的代表,主张功利之学,反对空谈天理性命,这与郝经也是声气相通的,由此不难窥见经史一体说的深层动因。又元延枯戊午(1318年),集贤殿大学士奏郝氏《续后汉书》于朝廷,仁宗诏江西行省付梓,江西学正冯良佐董其役,且为此书作《后序》曰:“人有恒言,曰经史,史所以载兴亡,而经亦史也。《书》纪帝王之政治,《春秋》笔十二公之行事,谓之非史,可乎?盖定于圣人之手,则后世以经尊之,而止及乎兴亡,则谓之史也。”[4](卷首)这里的“经亦史也”,自是对郝经“六经自有史”的发挥;而以学正身份推衍此论,足见这种观点在当时绝非惊俗之论,而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近现代学者多注意到“六经皆史”说并非章学诚首创,隋代王通,明代王守仁、王世贞、胡应麟、李贽,清代顾炎武、袁枚等,都曾直接或间接提出类似观点。元初郝经的“六经自有史”说,无疑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它提醒我们,至少在宋元时期,人们已开始较多关注经史性质异同、源流分合以及经书文体与史书文体的联系和区别等问题。其中郝经的研究,内容比较丰富,论述也颇系统,与章学诚“六经皆史也”,“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5](卷1《内篇一·易教上》)等论断最为接近,贡献也最大。可是,长期以来,这种贡献却有意无意被忽略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当然,笔者更关注的则是这种学说对郝经文学观念以及文体学思想的影响。
二、对“文本于经”说的丰富和发展
由于以史观经,把经作为社会历史生活的反映,郝经在论述经书的不同内容与性质时,已涉及经书的文体分类,如“《易》即道之理也,《书》道之辞也,《诗》道之情也,《春秋》道之政也”等。在《续后汉书》卷六十六上上《文艺·文章总叙》中,郝经进一步发挥这种观点,把历代文体归入《易》、《书》、《诗》、《春秋》四部,《易》部有序、论、说、评、辨、解、问、难、语、言10体,《书》部有书、国书、诏、册、制、制策、赦、令、教、下记、檄、疏、表、封事、奏、议、笺、启、状、奏记、弹章、露布、连珠 23体,《诗》部有骚、赋、古诗、乐府、歌、行、吟、谣、篇、引、辞、曲、琴操、长句杂言14体;《春秋》部有国史、碑、墓碑、诔、铭、符命、颂、箴、赞、记、杂文11体,总计古今文章58体。②每部之前有总序,论述其分类依据。如《易》部序曰:“昊天有四时,圣人有四经,为天地人物无穷之用,后世辞章皆其波流余裔也。夫繇、彖、象、言、辞、说、序、杂,皆《易经》之固有,序、论、说、评、辨、解、问、对、难、语、言,以意言明义理,申之以辞章者,皆其余也。”[4](卷66上上《文艺·文章总叙》)《诗》部序:“《诗经》三百篇,《雅》亡于幽、厉,《风》亡于桓、庄。历战国先秦,只有诗之名而非先王之诗矣。本然之声音,郁湮喷薄,变而为杂体,为骚赋,为古诗,为乐府、歌、行、吟、谣、篇、引、辞、曲、琴操、长句杂言,其体制不可胜穷矣。”[4](卷66上上《文艺·文章总叙》)分别论述各类文章的功用、性质、发展流变以及与儒家经典的关系,集中反映了郝经的文体分类思想。
从表面看,郝经把各体文章归入四部经书,是受了“文本于经”传统的影响,从儒家经典追溯文体的源流。然而,细究各部总序,则可发现,郝经的观点,并非传统的照搬,而是融进了经、史一体的学术理念,极大地丰富了“文本于经”的思想内涵。如以《易》言义理,“即史之理也”,《书》载王言,即“史之辞也”,“《春秋》、《诗》、《书》,皆王者之迹,唐虞三代之史也”等,都贯穿着经、史相通的思想。既然如此,那么,由经书衍生出来的各体文章,自然也有史的性质。这在《一王雅序》中有明确的表述。序文在提出“六经具述王道,而《诗》、《书》、《春秋》皆本乎史”之后,论述战国以来的文章流变说:“战国而下,逮乎汉魏,国史犹存。其见于词章者,如《离骚》之经传,词赋之绪余。至于郊庙乐章,民谣歌曲,莫不浑厚高古,有三代遗音,而当世之政不备,王者之事不完,不能纂续正变大小风雅之后。汉魏而下,曹刘陶谢之诗,豪赡丽缛,壮峻冲澹,状物态,寓兴感激,音节固亦不减前世骚人词客,而述政治者亦鲜。齐梁之间,日趋浮伪,又恶知所谓王道者哉?隋大业中,文中子依放六经,续为诗书,骋骥騄而追绝轨,甚有意于先王之道,乃今坠灭而不传。李唐一代,诗文最盛,而杜少陵、李太白、韩吏部、柳柳州、白太傅等为之冠冕。如子美诸《怀古》及《北征》、《潼关》、《石壕》、《洗兵马》等篇,发秦州,入成都,下巴峡,客湖湘,《八哀》九首,伤时咏物等作;太白之《古风》篇什,子厚之《平淮雅》,退之之《圣德诗》,乐天之讽谏集,皆有风人之托物,二雅之正言,中声盛烈,止乎礼义,抉去汙剥,备述王道,驰鹜于月露风云花鸟之外,直与三百五篇相上下。惜乎著当世之事而及前代者略也。”[2](卷28《序》)把“《离骚》之经传,词赋之绪余”作为“国史犹存”的体现,正是以史家眼光来看待词章;而他对历代文章的评价,也确实是从史家标准出发,推崇表现“当世之政”、“王者之事”、“先王之道”的作品,认为只有这样的作品,才体现了经书的精神。这些内涵,是传统的“文本于经”说所不具备,因而也无法比拟的。
郝经以史观经,是为了强调六经并非章句训诂之学,更非空谈义理之文,而是社会历史的生动反映,是王者之道与王者之迹的统一,是圣人经世致用的产物。在《文章总叙》中,郝经已对此再三致意,如《易》部序称“吴天有四时,圣人有四经,为天地人物无穷之用”,《书》部序称《书》类文体“皆代典国程,是服是行,是信是使,非空言比,尤官样体制之文也”,《春秋》部序称“凡后世述事功,纪政绩,载竹帛,刊金石,皆《春秋》之余”。这种将文章与政事紧密联系,强调文章济世功用的观点,使郝经反对一切无用之末学和无用之虚文。《上紫阳先生论学书》曰:“经生今二十有八年矣,自十有六始知问学。世有科举之学,学之无自而入焉,蜡乎其无味也。有文章之学,学之无自而入焉,蜡乎其无味也。退而叹曰:‘利禄其心,组绣其辞,质日斲,伪日翔,何区区尔也!’而狃于俗,陷于世,有不能已焉者。如是者有年,始取六经而读之,虽亦无自而入,而知圣之学,道之用,二帝三王致治之具在而不亡也,真有用之学也。”[2](卷24《书》)自述求学经历,天性不喜科举之学、文章之学,故“学之无自而入”,而于圣人之学,则心领神会,并由衷赞美六经使“二帝三王致治之具在而不亡”,“真有用之学也”。又《文弊解》曰:“事虚文而弃实用,弊亦久矣。自为己之学不明,天下之人狃于习而陷于利,是以背而驰之,力炫而为之譟,援笔为辞,缀辞为书,藉藉纷纷,不过夫记诵辞章之末,卒无用于世,而谓之文人,果何文耶?俾佛老二氏蠹于其间,文武之道坠于地,而天下沦于非类也,宜矣。其不幸而不观于大庭氏之先,而不见夫文之质也;不幸而不游于孔氏之门,而不见夫文之用也;不幸而不穷夫六经之理,而不见夫文之实也。……天人之道以实为用,有实则有文,未有文而无其实者也。 《易》之文实理也,《书》之文实辞也,《诗》之文实情也,《春秋》之文实政也,《礼》文实法而《乐》文实音也。故六经无虚文,三代无文人。夫惟无文人,故所以为三代;无虚文,所以为六经,后世莫能及也。”[2](卷20《杂著》)提倡为文要追求“文之质”、“文之实”、“文之用”,严厉抨击“事虚文而弃实用”的风气,斥之为“文之大弊”。在郝经看来,六经之所以不可企及,是因为务于实,周于用。而他之所以把诸体文章归入经书各部,正是为了强调各体文章不同的实用、济世功能,在立论宗旨上,与“六经自有史”是完全一致的。这种宗旨,与刘勰、颜之推等仅从五经追溯文体源流,或为推尊文体而倡言“文本于经”,自不可同日而语。
三、文体分类谱系
在《续后汉书》成书前六年,郝经已编纂成文章总集《原古录》,惜后世失传。从《原古录序》看,此书分体编排,也将古今各体文章归入《易》、《诗》、《书》、《春秋》四部之下。[2](卷29《序》)由此可见,这是郝经成熟、稳定的文体学思想。在序文中,郝经介绍自己的分类依据,大旨同于《文章总叙》,而更为明确地概括出各部文体的功能特征,如称《易》部为“义理之文”,《书》部为“辞命之文”,《诗》部为“篇什之文”,《春秋》部为“纪事之文”。在此之前,北宋真德秀《文章正宗》首次把纷繁复杂的文章分为辞命、议论、叙事、诗赋四类。郝经的分类当受此影响,表现了文体学研究开始重视综合归类,执简驭繁以起纲举目张之效的新风气。所不同的是,郝经把四部文章,分别纳入经书体系中,初步构建了一个“文本于经”的文体分类谱系。明代黄佐《六艺流别》在此基础上加以丰富和发展,把古今150多种文体分系于《诗》、《书》、《礼》、《乐》、《易》、《春秋》之下,形成六大文体系列,完备、充实了郝经的谱系,可谓实践“文本于经”文体学理念的集大成者。
在《原古录序》中,郝经介绍《原古录》编纂体例说:“凡四部,七十有二类,若干篇,若干卷。部为总论,类为序论,目为断论。凡立说之异同,命意之得失,造道之浅深,致理之醇疵,遣辞之工拙,用字之当否,制作之规模,祖述之宗趣,机杼之疏密,关键之开阖,音韵之疾徐,气格之高下,章句之声病,麤凿巨细,远近鄙雅,皆为论次。”可见这部文章总集根据文体类聚区分,以部统类,以类系目,部有总论,类有序论,目有论断,共同构成一个集文选与文论为一体的,层次分明、结构严密的文体学研究体系。这样严密的体系,此前大概只有晋代挚虞的《文章流别集》才具备,可惜挚书久佚。郝经之后,尤其是明清以来的不少著名文章总集,如吴讷《文章辨体》、徐师曾《文体明辨》、储欣《唐宋八大家类选》、姚鼐《古文辞类纂》、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等,多采用了类似的体系,其接受郝经的影响,应比早于郝经近千年的挚虞更直接、更具体。
由于《原古录》失传,今天已无法见到此书各类文体的序论,所幸六年之后成书的《续后汉书》至今保存完好。此书所载《文章总叙》的文体分类方法与《原古录》完全一致,所涉文体名目及排列秩序也大致相当。也许《文章总叙》本身就是总结甚至摘录《原古录》总论和序论而成。因此,这篇总叙应可大致反映郝经的文体论内容及特征。
《文章总叙》对源于经书的58种文体一一论其体性,内容相当丰富。如《书》部“檄”类序曰:“檄者,传布告召之文。自丞相、尚书令、大将军、藩府、州郡皆用之。或以征兵,或以召吏,或以命官,或以谕不庭,或以讨叛逆,或以诱降附,或以诛僣伪,或以告人民。皆指陈事端罪状,开说利害,晓以逆顺,明其去就。其文峻,其辞切,必警动震竦,撼摇鼓荡,使畏威服罪,然后为至已。其制以木简为之,长一尺二寸。若有急则插以鸟羽,谓之羽檄,取其疾速也,故亦谓之羽书。初汉高帝谓吾以羽檄征天下兵,又谓可传檄而定,则三代先秦已自有之,而其文未见也。至孝武遣司马相如责唐蒙等,始见《喻巴蜀》一篇。首曰:‘告巴蜀太守。’终曰:‘咸谕陛下意,毋忽。’盖古制然也。至三国之际,益尚事辞,其制愈备矣。”详细介绍檄的起源、性质、作用、使用场合、体貌特征、书写工具、递送情况等,在阐述角度与研究方法上,大体继承了刘勰“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文心雕龙》卷十《序志》)的文体学研究传统。在刘勰之后至明代以前的漫长历史时期中,体系严密、内容丰富的文体论专著寥寥可数,因此,《文章总叙》的序论便显得弥足珍贵。
郝经论文体体性,注意揭示相关文体的共同特征。这在四部总论中概述每部文体特征时已有所表现,而在具体的文体分析时,更是时时关注这一点。如《易》部“评”类序曰:“先秦二汉所未有。桓灵之季,宦戚专朝,学士大夫激扬清议,题拂品核,相与为目,如曰:‘天下模楷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许劭在汝南而为月旦评,评之名昉此。至陈寿作《三国志》,更史赞曰评,而始名篇。然特论之异名也”。“辩”类序曰:“辩者,别嫌疑,定犹豫,指陈是非之文也”,“故凡论说之文,皆辩也。先秦二汉犹未以名篇,后世始与论别而为题矣”。指出评、论、辩三种文体都有议论曲直,辨别是非的功用。又如《书》部“疏”类序曰:“疏者,疏通其意,达之于上也。凡政有所未便,事有所未当,宛枉有所未信,壅蔽有所未达,臣下为之论列奏上,则用之,亦三代先秦之故有。至汉高帝五年诛项羽东城,诸侯王皆上疏请尊汉王为皇帝,疏之名始见。其后臣下往往上疏,同夫书矣。”“封事”类序曰:“汉制,表、书皆启封。其言密事,则皂囊重封,谓之封事。其文亦书疏也。”“奏”类序曰:“凡进言于君,皆曰奏书,谓敷奏以言是也。汉世,凡劾验政事,特有奏请,乃特作奏。其文亦书疏也。”指出疏、奏、封事诸文体,都是臣子向君主陈政言事的文体。这些共同特征,是文体分类得以实现的基础。郝经以经书四部统帅众多文体,必须具备这种提纲挈领、敷理举统的功夫。
除了善于把握共同特征外,郝经还善于区分相关或相近文体的细微差别。如《诗》部“吟”类序曰:“吟,亦歌类也。歌者,发扬其声而咏其辞也。吟者,掩抑其声而味其言也。歌浅而吟深,故曰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论吟与歌的区别,切中肯綮,发人之所未发。又《书》部“书”类序曰:“至战国秦汉,不可胜载,而体制多矣。臣子之于君父,小臣之与大臣,布衣之于达官,弟子之于师长,小国之于大国,皆谓之上书。名位相埒,则谓之遗书。平交往反,则谓之复书。上之于下,则谓之谕书。告戒论列,则谓之移书。躬亲裁制,则谓之手书。天子下书,则谓之赐书。用玺封题,则谓之玺书。敌国讲信,则谓之国书。吉庆相贺,则谓之贺书。胜敌报多,则谓之捷书。丧师败绩,则谓之败书。无礼相陵,则谓之嫚书。叛君指斥,则谓之反书。死丧凶讣,则谓之哀书。”论述“书”这种文体,因使用场合、对象、目的不同,而发生的种种衍变,可谓细致入微。这些区别,是各种文体具有独立存在价值的前提,也是文体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文章总叙》在这方面的成就,也颇为引人注目。
宋元时期,文体学研究的核心内容是辨体批评。这种批评,在理论形态上多以诗话、序跋、书信等形式表现出来,显得零散、随意,缺乏系统性。这实际上也是整个中国文论与文体论普遍存在的问题。郝经从经世致用的宗旨出发,倡言“六经自有史”,对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形成有重要贡献。以这种学术理念为指导,郝经撰成《原古录》、《文章总叙》等文体学研究专著,初步构建了一个以经为本的文体学谱系,并以详尽、系统的文体论充实了这一谱系。郝经文体学研究的内容、方法及体系,上承六朝的挚虞、刘勰,下启明清的黄佐、吴讷、徐师曾、姚鼐、曾国藩等,不仅在宋元时期别树一帜,在整个文体学发展史上,也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和影响。
注释:
①据笔者所见,目前只有吴承学、陈赟《对“文本于经”说的文体学考察》一文提及郝经《文章总叙》的文体分类。文载《学术研究》2006年第1期。
②在郝经的文体谱系中,没有《礼》、《乐》的地位。这一方面由于《乐》经自古无传,更重要的是,郝经以《礼》、《乐》为“道之用”,即儒家伦理道德的实践,而非以文载道,故不能成为后世文章的文体渊源。详参《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十七《论八首·道》、卷十九《论·礼乐》。
标签:郝经论文; 历史论文; 中国历史论文; 续后汉书论文; 春秋论文; 汉书论文; 后汉书论文; 元史论文; 东周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