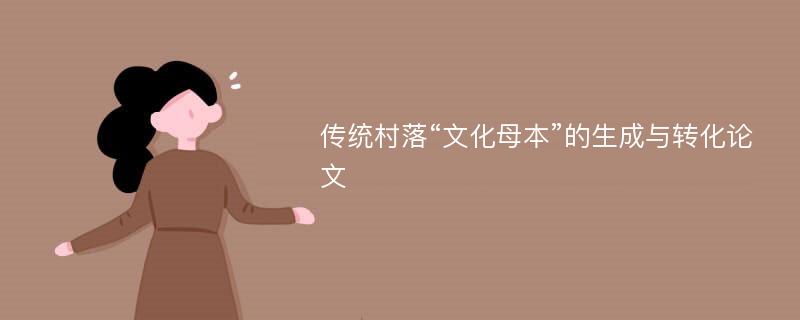
传统村落“文化母本”的生成与转化 *
谢旭斌,李雪娇
(中南大学 建筑与艺术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3)
[摘 要] 研究立足传统村落文化的“母体”特质,把其作为“文化母本”的概念。分析传统村落“文化母本”所具的母体意蕴与文化系统特性,探讨其文化生成的特质及现代转化的方法。从生成论与系统论角度,将传统村落文化视为文化生发的起点和“冶炼场”,为人类的繁衍与文化的生发提供孕育场和滋养力,是民族文化的孕育之源。传承和发展村落文化,是实现乡土文化资源的共生与转化利用的新路径,是促进和培育现代乡村家园社区文化建设的新方法。
[关键词] 传统村落;文化母本;文化生成;乡村社区培育
传统村落是人类农耕文明与乡村聚落文化的艺术表征形式,是我国悠久农耕文明留下的一笔巨大而独特的文化遗产资源。从2012年起,国家开始采取名录制保护方式保护传统村落,至2019年,先后五批共计6819个传统村落入选《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名录》。村落(聚落)文化是世界范围内一种重要的文明形式,是构成各民族文化特性与塑造各民族文化心理的重要基础,对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形态和民族文化形式具有重要作用。村落作为农耕文明的典型聚集形式,是形成秦陇文化、齐鲁文化、燕赵文化、湖湘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岭南文化等地域文化特性的重要基础,这些文化类型的地域文化特征与民族文化特性的形成都离不开村落文化的浸染。建立在农耕文明上的世界各民族文化均受村落文明的影响,追寻中华文明的源起,离不开村落文明的考古发掘与发现。冯骥才认为中华民族最久远绵长的根不在城市中,而是深深扎根在这些村落中。我国拥有独特的民风、民俗、民艺、礼乐等,从其映射出的审美取向和价值观念来看,村落文化奠定了华夏文明中文化历史与民族精神的丰厚基础。传统村落作为文化景观的空间载体和文化“母体”形式,不仅具有“以家园为主题的聚落空间‘共栖地’和文明汇集的文化共同体”[1]的家国意义,而且蕴含着丰厚的文化母境,是孕育生成乡土文学、艺术、宗教、伦理等“子文本”的“文化母本”,也是传承和转化民族文化精神发祥的母体。
一 传统村落“文化母本”的母体意蕴
传统村落是基于沃土的文化种子和以农为本的经济结构上生发出来的,是灿烂农耕文明与悠久聚居历史交织集合的“母体”结构形式,是集堪舆、建筑、艺术、文学、伦理、审美、礼乐制度、经济价值等网状结构的“文化母本”形式。在人类漫长的农耕时代,传统村落如同人类“子宫体”,为人类的繁衍与文化的生发提供孕育场和滋养力,具有富饶、丰满、包容、稳定的母体意蕴。
(一)传统村落在农业社会是孕育文化的“母体”
传统村落是孕育生成文化的母体,其形成源于人类长期生产实践、聚落空间、审美经验、礼乐文化等交织的聚集形式。20世纪50年代,著名的英国史前考古学家柴尔德在《远古文化史》一书中,提出农业文明的兴起促进了人类聚居及耕作方式的转变,从而开始了聚族而居、邻里守望的新的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为了生活、生产和安全的需要,出现了房舍、仓储、墓地、防卫设施等人工物。在此基础上,文化也逐渐产生和演化。这种聚居与聚集的村落方式在世界范围的人类考古中得到验证。这种传统村落“文化母本”形式的雏形在人类聚族而居的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这是一种创造劳动生产工具、适应自然地理环境的结果,是人们不断在劳动过程中发现、创造、审美的过程,也是人类思维观念及精神信仰形成演化的过程,更是人类历史与文化科技等多种综合因素影响的体现与映射。传统村落的产生和发展伴随着文化历史与生产科技等的生发、进步与变迁,二者为共融、共生关系。村落是人类生息的温床、孕育文明的沃地,为人类文明的丰富发展提供滋养;文化是村落得以延续的纽带与灵魂。
从已发现的文化遗址和遗存中可以窥探到古代聚居文明及族群社会的生存环境、生产结构与劳作方式。这些生产创造、工具发明、艺术审美、宗教信仰、礼乐制度等文化形态与艺术样式都是基于乡土环境的社会关系及生产力条件下产生的。如在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发掘出的榫卯结构、杆栏式住房建筑遗存,是依据南方沼泽地区多雨水、地面潮湿等特点因地制宜构思设计的产物,是古代先民经过长期实践、不断积累经验后的精心发明与创造。遗址中还出土了数量众多且制作精致的骨耜农具,证明在河姆渡文化时期,生产力水平的发展已达到耜耕农业的阶段。“人类也主要是在造物的过程中实现着自己的目的,开发着自身精神世界的无量的潜力。”[2]20原始农具中传递着先民的精神信息,人类对形式美感的认识也在工具制造的过程中逐渐孕育成熟。遗址中发现了我国早期的凤鸟朝阳图案雕刻。凤、太阳作为图腾和崇拜符号,体现出先民的艺术创造力和审美感悟力,除具有吉祥喜庆之意外,更是一种宗族文化、审美文化的体现,也是一个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文化圈。此外,我国还有良渚文化、仰韶文化、磁山文化、屈家岭文化等拥有“母体文化”意蕴的聚落文化形态。
阿袁小说的知识女性也是如此,对女性的性别价值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判断:年轻、漂亮永远是最有力的利器。她认为男人在美色面前,从来都是势利的。所以,在阿袁的笔下,“色”依然是女人最锋利的“鱼肠剑”。剑指处,所向披靡,男人缴械,女人落马。聪明漂亮的女人,挥舞自己的这把利剑攻城掠地,完成自我的实现。
(二)传统村落“文化母本”的审美意蕴
多年以来,我国高校场馆软件信息开发意识普遍滞后,不利于新业态开发和构建新盈利模式,但近年来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场馆体验掀起新一轮重构,无论从教学管理还是开放经营的角度来看,高校场馆增设智能化设备,朝智慧场馆转变成为提高运营能力的重要机遇。在智慧场馆运营模式下,场馆的运营管理更加数字化、智能化,能够加强活动信息发布促进人员引流,及时传达和共享馆内情况,使运营机构做到内外实时管理,进一步完善场馆信息服务体系;学生和消费者的个性化体验能够得到全方位满足,场馆不再是冰冷的建筑物,累积的大数据可成为赞助商评估的重要依据,进而为广告招商、无形资产开发带来可能,能迅速确立场馆的竞争优势,促进场馆转型升级。
传统村落“文化母本”具有富饶、丰满、活力、智慧的“母体”表征。传统村落文化是一个民族或地域集体无意识的体现,蕴含丰富的母体文化基因。一方面,富饶、丰满的“母性”审美特征表现在传统村落文化样态的艺术审美上;另一方面,充满活力、智慧的“母体”表征体现于传统村落建筑及艺术装饰、家具器皿、宗教信仰、道德等“母性意蕴”的文本与图像的描述中。以湖湘传统村落为例,在湖湘传统建筑、村落老屋的石础、梁柱、横联、门簪、门窗木雕等建筑构件与装饰上存有大量 “母性主题”“母性崇拜”“追源溯本”“母性空间”的雕刻装饰与空间布局,这是丰富多彩的村落现实生活的映射,同时深刻融入了“母性意蕴”的审美意象。怀化市沅陵县依山而建的金花殿村,在现存老屋的隔扇门上,栩栩如生地刻着五六只母鸡与小鸡啄米的场景,母鸡对小鸡的嬉戏、爱护,在其形态、场景的细节刻画中流露出浓浓的母爱意蕴,母爱情感呼之欲出,令人感动!老屋虽已摇摇欲坠,但这块门扇木雕活化了饱经沧桑的老屋,赋予其情感和温度,富饶、丰满的“母体”表征也被活生生地再现出来。福建客家圆形土楼、湘西南窨子屋、民居四合院等围合空间都体现了浓浓的母体意蕴。
传统村落“文化母本”具备安定、稳定、淳厚、无垠的“母性”审美特质。以农业为基础业态的传统村落具有稳定、祥和的审美特征,具有安定、平和的“母性”审美特质。分析我国传统建筑形式与审美意象,一是造型飞扬、形态活泼、空间尺度平实,给人灵动、向上的审美意象;二是建筑体量稳重、空间造型敦厚朴实,给人平稳、安定的审美意蕴。由于民居具有栖身住居、繁衍生息等功能需求,村落老屋的建筑结构、空间形态、围合样式、材质装饰多离不开稳固、安全、保暖、隔热及适合生存的“母体意象”。随着历史进步与发展,在村落形成与文化发展的过程中,不断融合、涵化着地缘、血缘、业缘、物缘等先天母体文化的生态环境因素,渗透并表现出浓厚而鲜明的母性色彩,具有强烈的生命延续性、母爱包容性和文化滋养性。
在我国,传统村落文化的生发多依水系、高地丘陵或高原平地而生。一方面,以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两大流域为基础,发源并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形态。“黄河上游地区的马家窑文化、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中原龙山文化,以及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证明了黄河是中国文化重要的发祥地。”[7]现代考古资料证明,长江流域的三星堆文化、屈家岭文化、河姆渡文化和良渚文化等,同样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源起。另一方面,大量随支流小溪纵深流布并择高地丘陵而建的村落文化同样构筑了中国文化源起的摇篮,形成了各具鲜明地域色彩的民族文化。距今约7000多年、依沅水支流而生的高庙文化,其中凤鸟纹、獠牙兽面与八角星、三角纹等神像图案,成为湘、黔、桂相邻地区具有母题意义的纹饰符号。“逐步向长江中下游、黄河流域以至更辽远的辽河流域‘流布和辐射’,由此发展成为日后多源一体的中国古代文明的共同精神支柱——龙凤信仰和肇始于观象授时的八卦宇宙观。”[8]28
当然,前两名模仿者即使演得再像卓别林,也只是模仿了他的表情和动作,而发自他内心的原创能力是谁也模仿不出来的。卓别林曾在回忆录中说:“逗人乐没有什么秘密。我所做的就是睁大眼睛、保持警惕、留意任何可以用在电影里的事件和情形。”
二 传统村落“文化母本”的生成系统
传统村落“文化母本”观,是基于思维的系统性、文本的互文性、文化的生成论等理论基础提出的文化观,从“母文本”与“子文本”的交互、系统生成的角度,把孕育生成乡土建筑、乡土文学、民族艺术、伦理道德、宗教信仰、民族精神、民俗风情等物质载体和精神意向的传统村落作为“母体”而提出的理论观点。传统村落作为一个社会文化系统,犹如文化“冶炼场”,是现实、历史与实践经验反复锤炼、沉淀、创新发展的结晶。
B超引导下肝组织活检术在临床上越来越普遍开展,该术创伤小。安全性高,并发症少,为肝病患者及早明确诊断和合理治疗提供了科学依据,值得大力宣传普及和推广。但该术还是一有创术,还存在一定风险性,必须根据循证护理方法,对患者施以正确的术前术后护理干预、教育评估和指导,以提高穿刺术的安全性。
(一)“系统”与“整体”的文化生成观
“系统”与“整体”的思维结构深刻影响我国村落景观风貌、堪舆选址、空间布局、给排水与灌溉、宗法制度、社会关系等方面。“系统论”“观其会通”“阴阳相生”是《周易》提出的“整体论”思维方式,主张有机、系统、整体地看待事物间的关系,反对割裂事物的联系。“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3]这是整体观的一种精彩概括,它强调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从而奠定“天人一体”宇宙观的基础,深受《周易》和《黄帝内经》等经典著作的影响。在中医领域,以《黄帝内经》为代表,呈现了自然、生物、心理、社会相结合的“医学系统模式”;在村落选址方面,我国历来注重堪舆选址的整体和谐,注重“五行相协”“阴阳相生”的整体协调观、孕育生成观,注重“方位朝向、藏风聚气、去污纳财”等系统性要素的综合考虑。这种系统性和整体性的全局观、系统观,充分体现出我国古代先民的思维图式与卓越智慧。传统村落“文化母本”作为一个整体性的文化系统,是促进文化有机生成的场所。“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文化圈中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群落,内含丰富、宝贵的文化信息基因库藏。”[4]3如今,面对日渐分散和消失的传统村落文化,注重这种“系统性”和“整体性”的逻辑思维观,开展这种文化“母体”生成观的研究,并对其进行深入研究与论证,具有文化传承与唤醒的现实意义。
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伯内特·泰勒在《原始文化》中开宗明义对文化作出了这样的界定:“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5]1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将传统村落作为一个社会文化大系统的“文化母本”,包含了人类最原真、最初始的传统建筑、乡土文学、艺术、宗法、伦理、风俗等诸多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子系统”。各子系统之间相互影响、交织与映射,并且与传统村落母体文化密切关联。“母文本”中的文化基因信息通过互文、衍生、创造等方式在“子文本”中继续生发和传承,在该系统中丰富、发展着人类文化基因信息库。从文本的互文性来看,传统村落就如一本深厚的“书本”,其中的翻页与内容构成了村落文化景观的多样性,折射出村落文化历史的厚重性;也犹如一个网络,其中每一“子文本”,包括农耕文明与文化历史的产生发展都是建立在传统村落“文化母本”这样一个母体网络或场域的系统中,是不断滋养、生发的动态变化与生成过程,是在村落空间场域中的系统生成与互文互生的结果。“母文本”与“子文本”互为引证、吸收、生成与发展关系,通过“吸收—转化”,“子文本”延续了传统村落“母文本”中优秀文化基因,丰富了传统村落优秀文化内涵及文化价值,实现优秀传统村落文化传承化、多元化发展。从文化生成的角度看,传统村落“文化母本”观,是在充分把握主客体的相互作用及其内在的本质与规律的基础上,从认识论与方法论层面对传统村落文化的生发与建构进行的系统性、逻辑性研究。“母文本”为村落母体文化生发的起点,各“子文本”在母体场域中不断产生与演化,逐渐形成为一个地域的文化模式,体现着一个地域的民族意志和民族精神。正如露丝·本尼迪克所指出的:“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模式,每一个模式都是一个独立的文化世界,集中了该民族共同的文化性格和文化行为。”[6]56传统村落文化的模式既是构成和维持一个地域、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又是一个地域、民族集体无意识的体现。
2.交融性、灵活性的“文化母本”特质
(二)传统村落是文化生发的起点
传统村落作为人类聚居空间和精神慰藉的场所,是人类文化生发的一个重要起点。人们首先面临生存的需要,依据生存环境的特点而创造工具、建房造屋,从而设计出建筑结构与空间形态的原初样式,这从历代考古发掘及文化历史遗产中得到佐证;其次,为了获得生活生产资源而进行社会生产、物质生产,进行创造性生产,促进了手工业文明、社会关系生产的发展,从而催生了手工艺生产,促进了饮食、服饰、家具产品、车马交通等文明雏形的演变,同时也推动了礼乐文化、节日习俗、宗法民约、伦理道德等社会雏形的建立;再次,为了获得精神上的宣泄、愉悦,进而出现了文学诗歌、宗教信仰、艺术审美等精神文化的雏形。人们在自身的精神追求、文化创造、审美表达的过程中,出现了人类本体性、起源性、生命性等哲学的思考与追问。人在漫长的农耕历史上作为村落文化创造的主体,使得传统村落成为人类文明生发的一个重要起点,不仅是人类文化艺术、社会关系和精神意志的生发点,而且是人类农业文明的本真表现、精神文明的原初体现。
传统村落“母子空间”“母体意象”具有融合、包容的“母爱”情怀。传统村落文化包容、多样的“母爱”情怀主要体现在村落空间的布局与村落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既包括“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兼收并蓄空间,又注重母子空间形态的布局。分布于我国闽西地区的客家土楼用建筑实体围合,形成外闭内敞的“母性空间”形态。土楼不仅具有一定高度、厚度以及封闭的外墙,显示出极强的“母体防御”功能,同时突出体现客家人求安定、安稳的特点,既有利于家族团聚,又具有鲜明的公共艺术特征。一栋栋土楼犹如客家文化孕育、发展的“子宫体”,为客家人的繁衍生息、客家文化的延续传承提供着滋养和保障。位于永州市零陵区富家桥镇涧岩头村的周家大院,其整体由六个不同宅院按北斗七星状进行分布,注重母子空间的穿插与围合,既分散独立,又聚合成一整体而气势恢宏;同时,其中作为单体空间形式的“四大家院”又具有“母体形制”,该院由周氏子孙中一分支的四个孙子共同修建,由炮楼、书院、老院和正院四部分子空间围合成一个母体单元,步廊相连、院院相通,体现了母爱情怀。由此可见,传统村落是一定地域范围内人们共栖、共育、共息、共存的物质承载和精神中心,极具民族文化的“本源性”和“母体性”,同时具备安定、厚重、稳定的“母性”特质。
从人类社会的发展来看,传统村落文化具有哺育性、原发性、乡愁性、多元性的母性特质,这可以从村落文化母本的整体性、母题的多样性、文本的独特性中得以体现。乡土文学、民族艺术、宗教信仰的产生及发展尤其离不开传统村落的影响。
传统村落文化的生发,蕴含着人们丰富的审美感悟力与艺术创造力,这很大程度上源于自然环境、地理时空的启示。“人们关于地理、环境、季节、气候、时空、方位等自然规律的认识,对于自然万物相生相克的现象启示及自然万物枯荣的审美意识,逐渐生成生命存在、因果伦理的审美教化观念。”“在景观物象中体验生命的存在、感悟生命的本源,感知自然教化的意义。”[9]因地域环境、民族心理、审美习惯的不同,其景观形象、艺术语言、文化表征也各不相同。为了满足不同的审美表达和精神需求,由此也形成了民间美术、乡土文学、民间歌舞、宗教信仰等表现形式多种多样的“子文本”,共同交织生成了传统村落地域文化样态。传统村落“文化母本”的逻辑建构过程,正是将传统村落文化立体、系统、整合的过程。传统村落作为一类社会有机体,其“再生、更新和发展的内在机制是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人自身生产的三者统一”。[10]507
传统村落拥有孕育、生发、滋养、培育的“母体”意蕴,具有历史文化多样、生态文明鲜明、景观类型丰富、非物质遗产资源丰厚、民俗礼乐文化深厚以及地域民族特征鲜明的结构形式。传统村落作为文化生发的“文化母本”,具有富饶、丰满、安定、内秀、包容等文化审美意蕴。
(三)传统村落是文化生成的“冶炼场”
综合前两个实验已经收集的191个样本,我们选择样本数相对较少的网络视频情境随机再抽取60个样本,剔除不合格样本后,最终有效样本为228份。涉及到其他中介变量和结果变量的测量方法与上述实验相同,实验步骤也保持一致。
美国凯瑟琳·帕特里克在论述创造性思维时,提出创造性思维的产生经历“准备期、酝酿期、阐明期和验证期四个阶段”。[12]3传统村落文化的创造,是原始先民们历经问题存在、反复尝试、思考酝酿、明晰思路、反复验证等一系列思维过程后得出的结果,同时是激发新思维、进行新实践、得出新结论的过程。因此,文化的生成是一个反复锤炼的过程。传统村落“文化母本”是文化生成的“冶炼场”,各“子文本”在母本场域中相互交融,反复锤炼、成长、发展和演变,共同熔铸为独具地域特色与民族特征的“文化母本”系统。因此,在文化生成的“冶炼场”中,“子文本”是“母文本”的延伸,任何一种“子文本”的形态及样式都是母体文化的提升与转化。在传统村落这个“冶炼场”中,是对母体文化进行判断和明晰,将优秀的传统文化提炼、交融,而传承、创新及发展的过程。这样既有利于推动社会发展、文明进步,又有利于文化多样性的维护。腐朽、愚昧、落后的文化陋习在发展过程中被逐渐摒弃,并最终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褪去。
历经千百年历史和文化的发展,在传统村落“文化母本”的大熔炉中不断孕育和衍生着民族文学、建筑、艺术、伦理、宗教、审美等“子文本”,“母文本”所包含的语言符号、审美观照以及所承载的文化信息往往在“子文本”中被描绘、引用、编织和创新。在时代变迁下,村落文化的基因种子同样会开花并结出美丽的果实。“人们自古以来形成的思维方式、民族特性、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具有强烈的历史性、遗传性和鲜活的现实性,为我们开创新文化提供历史的根据和现实的基础。”[13]
皮亚杰认为:文化的发生是结构、解构到建构的过程,离不开生成的环境与场地,“每一个结构都是心理发生的结果,而心理的发生就是从一个较初级的结构过渡到一个不那么初级的(较复杂)的结构。”[11]传统村落“文化母本”中“子文本”的发展,就是建立在对原有的母体文化吸收和建构的基础之上,是运用母体文化符号来创新构成子文本的过程,正如卡西尔在《人论》中提出的“人——运用符号——创造文化”的哲学逻辑。
三 传统村落“文化母本”的特性及体现
分别选择注塑温度180℃、190℃、200℃、210℃、220℃、230℃、240℃、250℃,使用PP材料注塑100 mm×100 mm×3 mm的试验样板若干。将制作好的样板在标准实验室(湿度:53%,温度:23℃)中自然放置3天,然后测试气味、VOC。
(一)传统村落“文化母本”的特质
1.哺育性、原发性、乡愁性、多元性的“文化母本”特质
从历史的角度看,传统村落在人类历史上犹如一个代代生长在乡村原野土地的母亲,繁衍生息、薪火相传。从母性哺育的角度,犹如一位位母亲无私地养育着自己的孩子,哺育其茁壮成长,关注孩子的教育、智力、德育、情感、谋生等能力与品质;从社会结构与文化创造的角度,创造了社会结构与社会生产发展的模式,促进了人类社会生产的发展与经济的繁荣,深刻影响到社会关系与生产力的发展与变革。村落犹如海洋河流一样滋养、灌溉着人类社会的文明之花,犹如点亮人类各民族文化之灯,更是情系人类乡愁情感与文化记忆的“母体”;同时,犹如母亲张开臂弯的双手,极具文化的包容性,既包括其文化审美、宗教信仰、民俗礼仪等文化特色的多元性,也包括富有民族气质的音乐、舞蹈、戏曲、歌谣、手工艺等人类活动的多样性。从人类社会多样文化的来源及发展看,乡土文学、民族艺术、宗教信仰、民谣歌舞等各具特质的文化类型,几乎没有不受村落文化的影响,尤其在作品的形象、题材、情节、场面等艺术表现中,离不开人性关怀、母性慈爱、诗意乡愁、家国情怀等主题内容的表现。传统村落是民族文化精神的孕育之源,不仅蕴含本土的景观文化基因、承载了深厚的民族文化精神,而且孕育生成了人类多样原初文明与各具特质的文化类型。
首先,学院应建立院系两级校企合作理事会,将学院和相关企业人员纳入理事会成员。其次,整合校内职能,成立科研与校企合作部,并安排专职人员,设立固定场所。校企合作理事会主要负责为院系的重大发展问题提供咨询、建议和指导,加强院系与行业、企业的联系,促进产、学、研紧密合作,实质性推进合作办学、合作育人、合作就业、合作发展,增强办学活力,加强理事会成员单位之间的交流与合作等。科研与校企合作部主要负责研究学院校企合作方面的重大问题,推动校企合作体系建设、起草校企合作计划、制定校企合作制度,并组织和推动实施等。
在村落发展的过程中,随着生产工具及生活方式的不断变化,传统村落文化不仅是“交融”“变易”的文化,而且能灵活适应变化,以促进社会发展与进步。《周易》主张不仅顺应自然、察天观象,而且顺应时机、讲究心理、注重变通。文化生成论主张“交融”“灵活”“有容乃大”,不止是对待外来文化,应具有互为取长、吐故纳新的态度,而且对待不同民族、家族宗法,结合不同地域文化,应抱有交融、贯通、互长互生的理念。尤其在文化语言、建筑形制、宗教习俗、伦理教化等方面,传统村落文化表现出极强的交融性特质。以传统村落中常见的生殖与繁衍主题为例,其纹饰、图文形象及语义就体现了极大的通融性、灵活性。不仅鸟纹、蛙纹、瓜纹、花纹等纹样被民间广泛运用在窗牖、石础、廊坊、梁柱等建筑装饰中,而且麒麟送子、莲花生子、葫芦生子、观音送子等图文形象在雕刻、壁画中均以借喻手法来体现母性、母爱、生殖的主题,如湖南省祁东县沙井老屋窗楣上的麒麟送子彩绘,娄底涟源杨家滩老刘家架子床上刻有的花草、南瓜等寓意瓜瓞延绵的吉祥图案等。同时,在我国传统村落中,阴阳鱼形象、八卦图形等多体现阴阳相生、生命繁盛的哲学观念。这些图文符号和艺术形象成为村落“文化母本”中经典的民间艺术形式,也成为华夏各民族融合共用的文化符号和艺术语言。
(二)传统村落“文化母本”的体现
传统村落“文化母本”主要体现在“母本”的整体性、家园“母题”的多样性与各子文本的“母体”性三个方面。
传统村落“文化母本”是建立在文化系统基础上的整体性。传统村落“文化母本”不是单一产生的,是在社会文化大系统中不断生发和互文交织形成的。这一过程伴随着“子文本”从“母文本”中的衍生,以及各“子文本”间的互文引申、编织、转换、映射的过程,由此构成整体性的村落文化大系统。传统村落母体文化中蕴含的堪舆、建筑、艺术、宗教、伦理、审美等“子文本”,并非割裂和独立,而是彼此关联、互文体现。传统村落“文化母本”的整体性,犹如一个巨大场域,紧密交织成为一个网络整体,任何一个部分不可分隔抽离。
从“母题”的角度来看,传统村落所包含的自然环境、人文地理、民族心理、宗教信仰、装饰纹饰、文字语言、民风习俗、礼乐制度等,均可引申、转换、生成为其他文化艺术的题材形式与语言符号。不仅不同地域、民族、国家的传统村落均有自己独特而鲜明的文化系统,而且传统村落景观本身构筑成了世界民族艺术语言的审美符号。西安半坡村仰韶文化遗址中充满图案化、符号化意味的彩陶纹饰,不仅被赋予了人的“审美”“灵魂”“感觉”和“意志”,体现了人们审美文化的生发,其中三角形、圆形、鱼、蛙、鸟等彩陶纹饰构成了世界艺术“母题”形式,而且凝结着原始先民的卵生神话与生殖等意象,反映出人们对生命生发的大胆设想和对生殖文化的崇拜,成为华夏民族艺术语言的典型符号形式,并广泛应用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传统村落“文化母本”是孕育生成乡土文学艺术文本的“母体”。虽然每个村落文本的独特性,受其自然环境、经济结构、建筑空间、艺术形态、礼乐民俗、心理观念等各具文化肌理与地域特色的影响,但包括乡土文学、乡土建筑、民间美术、民族宗教信仰、民风习俗特性等各“子文本”都受村落文化“母体”的影响。纵观近现代乡土文学艺术史,村落文化影响了沈从文、赵树理、周立波、孙犁、路遥、古华、何立伟、贾平凹、莫言等乡土作家和齐白石、吴作人、易图境、黄永玉、罗中立、李自健等乡土画家。沈从文的《湘行散记》《边城》《菜园》等乡土文学作品,其题材与内容就根植于对家乡山水、人文景观的“母体”情怀与情感寄托,带有浓厚湘西村落景观的文化基因,流露出浓厚的湖湘乡土景观的“母题”性。“一个个生动的村落乡土景观被建构起来,沅水、村落、码头、河街、渡船、吊脚楼、封火墙、牌楼、浅滩、丘陵、芦苇、老人、女孩等景观要素与语言符号,作为文本描述的景象与表现对象,生动地构筑了一幅幅湘西村落画卷。”[14]
四 传统村落“文化母本”的转化利用
传统村落“文化母本”具有的母性意蕴、空间逻辑、文化价值、艺术智慧等,对当今乡村社区文化的系统建设与应用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艾森斯塔德认为,“现代性并未使传统解体,这些传统反而是现代性永远的建构与重构的源泉。”[15]20我们要以全球观来面对传统村落文化,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共筑人类家园共栖地,发展“文化母本”的多元现代性链接路径,延续传统村落优秀文化基因,在现代文化的发展当中充分发挥传统村落“文化母本”的价值。
数学课程是以理论为主的重视逻辑推导的一门课程,而数学建模课程是以数学方法为主来解决实际问题的一门课程。简单来说,数学课程是数学建模的基础课程,而数学建模课程是数学课程的理论应用。因此,在数学建模的培训、教学、竞赛等方面工作中,会用到大量数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牵涉到有如工程、经济、金融、统计、计算机等各个行业与专业方面的知识,有利于提升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因此,一次竞赛,终身受益。在解决实际问题中所用到的数学知识,可以让学生更好的理解数学理论;而数学理论在各个实际问题的应用,可以提高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有利于数学课程的教学。
(一)传统村落“文化母本”的传承利用
要传承利用传统村落“文化母本”,首先要注重艺术智慧的传承与转化。我国传统村落注重人与自然生态的和谐、注重人生价值的精神体验、重视礼乐文化、追求审美伦理及审美意境的营造,这些审美教化与价值取向对现代社区的空间营造与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在现代乡村社区培育与建设中,我们应该从文化的系统性、整体性视角,探索各“子文本”在现代乡村社区文化建设与空间形态的传承、培育、构建的路径与方法。重视村落空间科学布局、发展邻里互助关系、传承文化艺术智慧,把传统村落“文化母本”的母体性、稳定性、创造性、审美性、包容性、多样性、原发性等引入并转化到现代文化艺术的建设中;提倡继承优秀宗法社会的秩序,探讨从乡村景观空间形态、建筑结构形式、民族民间艺术培育等角度进行乡村社区营造及其社会关系的科学构建,培育乡风文明、助推乡村振兴。其次,注重乡土艺术遗产资源的转化利用。从村落社区的整体入手,进行艺术乡建、发展文化产业。重视乡村“文化母本”的历史、文化、宗教、艺术的社会价值、资源价值,可从公共建筑、住宅民居、雕刻艺术、刺绣艺术等物质文化遗产和歌舞艺术、文学艺术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汲取文化营养。从方法论角度,将乡土艺术遗存作为现代艺术转化的“元”与“源”。挖掘村落地域文化发展之“源”,进行文化科技产品的开发;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开展数字化文化展示及乡村文旅产业。不仅要促进传统村落文化“母体基因”的延续,保持村落文化的独特性,而且要保护传统村落“文化母本”的源头形式,保护民族的根性文化。最后,借鉴村落宗法治理、文化教育、社会生活等内生文化结构、教育机制、治理机制,借鉴民族精神、礼乐教化、审美伦理等乡村民族心理结构的内生机制,探寻构建村落社区和谐治理、传统与现代文化和谐共生、村规民约健康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得到彰显、先贤文化得到积极发展、良俗风貌得到展现的机制,引领人们对优秀民族文化的有效传承,进一步唤醒民众对村落老屋的保护意识和现代乡村文化的建设意识。
(二)家园社区与本土意识的多元链接
构筑家园社区、共建家园共栖地,主动发挥传统村落所具独特性、多样性、包容性的“文化母本”特质。吴良镛指出“文化的特性是社会内部的动力在进行不断探求创造的过程” 。[16]5文化的发展必须从多样性中汲取营养,是一个不断更新、充满活力、持续探索的过程。因此,将传统村落“文化母本”上升到家园共同体和地球村的概念,在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追求文化的多样性,尊重民族文化的特质性,以家国情怀和家园意识为基点,共筑家园共栖地,是打造民族话语体系、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心的重要路径。树立整体性保护发展的概念,加强不同地域和族群村落文化的相互连通,强化母体文化的生命力,提供母体造血功能,是避免文化僵化、封闭和同质化的重要举措。随着信息科技的发展,民族文化逐渐式微,应基于全球观与家园社区意识,建立“文化母本”各“子文本”间的互文链接,建立现代家园社区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17]文化之间的差异应该成为人类文明发展和进步的动力,是增进民族间交流与合作的桥梁。中国传统村落拥有整体性与系统性的“文化母本”思维观,拥有民族文化的艺术精神与人文智慧。以传统村落“文化母本”观创新性地认识并转化为现代文化的利用,强调以整体性、系统性、综合性的视角看待和保护村落文化,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拓宽文化复兴之路、建立乡村产业新业态、促进现代乡村社区培育、实现传统村落文化多维发展的关键。
五 总 结
传统村落作为人类具有“母体”文化特质的文化母本,是孕育人类文明的基础,是奠定人类社会发展所需衣食住行的源头。传统村落在农业社会是孕育文化的母体,是具有富饶、活力、丰满等生命力表征的“母亲”。从“母文本”与“子文本”的彼此交叉、叠合、渗透与引证的角度,将其视为农耕文明与乡村聚落的文化表征,来系统研究“文化母本”包含的独特文化与艺术审美智慧,破除了单一学科、片面化研究的局限性,是从文化生成及系统性角度探讨村落文化的新方法。传统村落文化生成系统犹如文化“冶炼场”,是现实、历史与实践经验反复锤炼、沉淀、创新发展的结晶。传统村落是我国具有悠久历史的家园共栖地形式,是人类的家园共同体。若“家园”这个生存的基点逐渐消亡,传统村落物质载体与样态消失,那么,其中的文化无疑也会慢慢遗失,人们便无法通过“历史的文化景观”来激起回忆、传承文化与文明,无法通过“民族的艺术智慧”激发人们爱乡土、爱家园社区的情感并更好地走向未来。由于时代变迁,乡村家园发展的立足点出现了晃动,中国几千年农耕文明结下的文化硕果被遗弃,传统文化基因传承的纽带被割裂,出现了中华民族智慧的独特思想与价值观念迷失的现象。民间手工艺生产、乡土建筑文化、传统审美伦理、礼乐民俗制度等具有区域特征、带有乡土文化与乡土资源特质的“母本文化”渐趋淡薄、消失之势。在现代的话语体系中,大量根植于传统村落的传统文化被忽视。“乡土往往被想象成为落后、蛮荒、萧瑟的‘前文明’状态。这种强势的话语体系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乡土的文化传统与民族特性。”[18]传统文化中的敦厚率真、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等优良的道德品质被人们忽视。而这些独特的地域文化、优良的道德品质,正是传统村落“文化母本”孕育、演化、传承、创新的结果。因此,拯救传统村落是重视民族文化精神的孕育之源,是保护现代乡村社区文化发展的文化基石。
[参 考 文 献]
[1] 谢旭斌.湖湘传统村落景观审美生成研究[D].长沙:中南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2019.
[2] 倪见林.装饰之源——原始装饰艺术研究[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
[3] 胡勇.中国哲学体用思想研究[D].南京:南京大学哲学系,2013.
[4] 方李莉.努力推进迈向人民的艺术人类学的发展——方李莉会长在2018年中国艺术人类学年会上的发言[J].内蒙古艺术学院学报,2018(4):5-10.
[5] 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6] [美]露丝·本尼迪克.文化模式[M].北京:京华出版社,2000.
[7] 候仁之.黄河文化[M].北京:华艺出版社,1994.
[8] 袁行霈.中国地域文化通览[M].北京:中华书局,2014.
[9] 谢旭斌,张鑫.湖湘传统村落景观教化特色探讨[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5):115-121.
[10] 王博.浅析社会系统论[C]//第二届世纪之星创新教育论坛文集,2015:507.
[11] 熊哲宏.皮亚杰理论与康德先天范畴体系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2.
[12] [美].凯瑟琳·帕特里克.创造性思维十一讲[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6.
[13] 彭岚嘉,杨华.文化自信的历史根基与当代价值[J],甘肃社会科学,2018(6):21-29.
[14] 谢旭斌,湖湘村落景观的互文性解读[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182-187.
[15] [德]多明尼克·萨赫森迈尔等.多元现代性的反思——欧洲、中国及其他的阐释[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16] 萧默,王贵祥.建筑意[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
[17] 邸乘光.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3):7-21.
[18] 吴翔宇.沈从文重构“乡土中国”的文化机制与话语实践[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9(6):115-122.
The Form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Cultural Matrix "in Traditional Villages
XIE Xu-bin, LI Xue-jiao
(College of Architecture and Art,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Changsha 410083,China)
Abstract :The research is based on the "maternal" characteristics of traditional village culture, which regards it as a concept of "Cultural Matrix".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maternal implication and cultural system characteristics of "Cultural Matrix" in traditional villages and discusses characteristics of cultural formation and methods of modern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ormation and system theories,the traditional village culture is regarded as the starting point and "smelting field" of cultural growth. It provides breeding field and nourishing force for human reproduction and cultural growth. It is the source of national culture. Inheriting and developing village culture is a new path to realize the symbiosis, transform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local cultural resources; it is also a new way to promote and cultivate the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culture in modern village homes.
Key words : traditional village;cultural matrix; cultural formation;cultivation of rural communities
*[收稿日期] 2019-06-11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于拯救老屋行动下传统村落景观“文化母本”的话语变迁及其社区培育研究(18BSH084)
[作者简介] 谢旭斌(1972—),男,湖南洞口人,中南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传统村落景观、乡村文化艺术遗产、艺术哲学。
[中图分类号] G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 1763( 2019) 05— 0126— 08
标签:传统村落论文; 文化母本论文; 文化生成论文; 乡村社区培育论文; 中南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