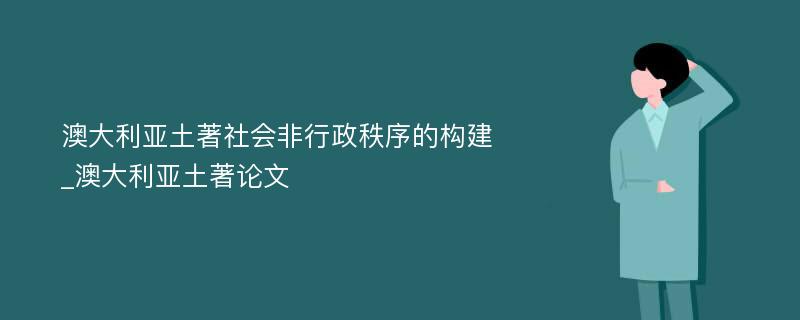
澳洲土著社会非行政性秩序的建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土著论文,澳洲论文,秩序论文,行政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澳大利亚土著是人类在现代社会所能直接观察到的最原始的人类种族之一,是研究人类童年时代生存状态的“活标本”。由于数千年的孤立隔绝,澳大利亚土著文明长期游离于世界各主要文明发展的进程之外,其文明发展的水平“在非洲黑人之下而接近于发展阶梯的底层”,因此,“他们的社会制度接近于原始形态的程度必不亚于现存的任何民族。”〔1 〕澳大利亚土著因其独特的原始性而具有很高的史学认识价值。对澳洲土著的研究,有助于探究史前时期人类的生存状态及其社会生活的基本面貌。
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将澳大利亚土著的社会组织作为一种特殊类型加以研究,原因在于澳大利亚土著“以性为基础的社会组织”极端落后,“这种以性为基础而不以亲属为基础的社会组织比氏族更早;……它比迄今所知的任何社会形态更为原始。”〔2 〕澳大利亚土著社会中并不存在类似美洲印第安人中发展起来的比较严密和发达的社会组织形式,他们的部落或氏族组织尚处于萌芽或不成熟状态,按照氏族组织的正规理论,澳大利亚土著社会尚未发展到成熟的“部落”或“氏族”组织阶段,但是氏族组织正在侵蚀和瓦解以性为基础的社会组织。
在原始初民的生活中,社会组织愈发达成熟,它所固有的对社群的管理职能也就愈突出。成熟的部落或氏族组织内部一般设有专职的政权管理者和政权机构,有一整套处理部落、氏族日常事务的代代相传的制度或惯例,整个社会的管理与控制是有组织的和强制的,如美洲印第安人易洛魁部落的情况。然而,在澳大利亚土著中,权威是极其有限的,既没有一个掌管政权的氏族酋长,也没有部落议事会这样的常设机构,似乎也不存在事实上的所谓“老人政治集团”。在墨累河低地曾有一个正式的氏族会议(Tendi), 氏族首领和长老通过这个会议对邻近部落的争议进行仲裁。〔3〕但这是极偶然的情况。总起来说, 澳大利亚土著社群缺乏相应的比较成熟的社会组织,它们没有任何专职的社会政权机构和管理者,因而澳大利亚土著社群的管理与控制是非行政性的、自觉的和非强制性的,至少从社会结构来看是如此。这使土著社会内部的控制机制变得复杂而微妙,实际上,澳大利亚土著社群正是通过一些隐含的因素对整个社会实施着控制,这些隐性因素通过“互渗”与“叠加”律共同作用于土著社会,从而在社群管理与社会控制中发挥重要作用,由此建立起一种非行政性的社会秩序。
就社会结构而言,澳大利亚土著的部落或氏族制度,在发展程度上是极不平衡的,譬如,澳洲大陆东部、西部和东南部大多数部落的传承世系从母系计,大陆西北各部落的传承世系从父系计。每个土著社群都有着自己的群体结构,一般分为部族、半族、氏族和宗族四个层级。其中宗族的划分是以性别为标志的,从卡米拉罗依人的群体结构来看,宗教的划分纯粹是为了实现群间的通婚规则。因此,氏族公社仍然是社会生产的基本单位。但是,应特别注意到,澳大利亚土著的氏族制度还保留着相当完整的原始形态,似乎还处于正在形成的阶段,只有在父系传承的部落里,才有了真正的氏族;更原始的部落,往往划分为20—25个游牧的地方性集团,而不是分为氏族,反映在图腾上,便是只有性别图腾,而没有氏族图腾。譬如,库奈部落就没有氏族图腾,而是将人口分为两个性别集团,一个是男性集团,以鸸鹋鸥鹪(Emu-Wren )为图腾,一个是女性集团,以一种善歌的莺科鸟为图腾,土著称为“D;ürgun”。
在社会组织不发达的情况下,澳大利亚土著的社会管理主要依靠其内部隐含的一整套社会控制系统。在土著社群中,社会控制并非意指那些限制不轨行为的正式法律和禁令,实际上,“这种控制是一个更微妙、更普遍的过程,它深扎根于社会生活之中。社会控制也是以非正式的和不成文的方式进行的,它有效地将绝大部分人口组织在社会规范之中。”〔4〕总起来看,澳洲土著社会控制的隐性因素很多, 它们分别从自然关系、社会关系、亲缘关系、婚姻关系、宗教以及秘传文化等方面对整个社会起着规范作用。
一、亲属制度是最基本的社会规范
亲属关系构成澳大利亚土著社群日常生活的底蕴。可以说,亲属关系和婚姻在一切社会中都是作为组织原则而发生作用的,在处于原始的“群队”状态的澳大利亚土著社会中,亲属关系和婚姻构成了整个社会的基本组织原则。所有土著社群的亲属关系基本上都是建立在分类上的(按社会身份分类而不是按生物关系分类)——这就是说,一组有限的称谓通常被加以延伸,用以称呼所有熟悉的人。譬如,直系的称谓,如父亲,适用于同一级别的所有亲属,这种集体称谓制与夏威夷土著相近,夏威夷土著将所有父母一辈的人统称为父亲或母亲。在澳大利亚原始民族中,同样用“父亲”来称呼与其生父同辈的所有男子,用“母亲”来称呼与其生母同辈的所有女子,“这并不意味着一个人可能不认识他实际上的父亲、母亲、儿子或其他亲属。称谓只是暗示着某种行为——后代的、兄弟的、姊妹的、父亲的或其他行为。”〔5 〕集体称谓有助于社群管理,这是因为亲属关系可被视为是一个结构社会群的基础,亲属称谓中隐含着一系列行为方式,譬如限制、回避、责任、权利和义务以及血亲复仇等等。由于实行严格的族外婚制度,土著称谓本身还隐含着可能的配偶和姻亲关系。在卡米拉罗依人八个亚族的婚级制中,全体玛塔都是全体孔博的妻子,而阿兰达人两个半族的婚级制度,在称谓上,A半族的全体女子都是B半族全体男子的妻子,假若A 半族的一名男子遇见B半族的任何一名女子,他都应称她为自己的“妻子”。 土著男子的“岳母”也通常是由一群妇女组成,而该土著男子同他称之为“岳母”的女性群体之间存在着严格的回避关系,这是一个类似于原始的伦理规范的行为规则。在澳大利亚的族外婚阶段,父—女之间、母—子之间以及兄弟姊妹之间的血缘婚已被严格排除,因此兄弟姊妹之间的关系也是社群中最紧张的关系之一,通常也是要严格回避的。这样,亲属称谓就不只是一种符号系统,它在划定个体在群体中的地位的同时,也参与了整个社群的内部管理,成为社会不可或缺的内在化控制因素之一,正如美国人类学家威廉·A·哈维兰所说, “亲属制度使个人精确地知道他或她与别人的关系如何,他们能够要求对方做些什么。这种亲属制度构成了其成员的义务与利益:它支配着人们共同担任经济与宗教任务,在危机时刻给人们提供心理支持,必要时给人们提供法律帮助与保护。”〔6〕
二、婚级制度维系着土著社会生态的平衡
在土著社会中,婚姻和亲属关系一样,在社会控制中起着隐性的作用。澳大利亚土著社群的婚姻形态,正处于从以性为基础的婚级制向以亲属为基础的族外婚制过渡的时期。澳大利亚土著虽然也普遍地实行族外婚,但其婚姻制度与典型的族外婚又是有区别的。这里通行的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有限制的族外婚”。按照氏族制度的正规理论,典型的族外婚,通常只是禁止氏族内部的血亲婚配关系,在此情况下,“每一个氏族中所有的成员应当可以与本氏族以外任何氏族的异性结婚。 ”〔7〕在澳大利亚,根据有限制的族外婚规则,某氏族中的全体男子却只能跟某一指定氏族中的女子通婚。虽然两者群间通婚的性质以及排斥血缘婚的目的相同,但通婚的模式却有一定差异。流行于世界各民族中的典型的族外婚,其群间通婚的规则一般是“族外无限制”,而流行于澳大利亚的“有限制的族外婚”,其群间通婚的规则却是“族外指定”。人类学家一般将后者称为“级别婚”或“婚级制”。
散布在悉尼以北达令河流域的卡米拉罗依部族是实行婚级制的典型代表。从婚配权的角度而言,卡米拉罗依人分为A、B两个半族,两半族内部各包括三个氏族,A半族包括鬣蜥氏、袋鼠氏和负鼠氏;B半族包括鸸鹋氏、袋狸氏和黑蛇氏。在卡米拉罗依人的部族中,“无论男女,都不得与氏族内的人通婚,这是绝对禁止的。”〔8〕同时, 在一个半族内的三个氏族(如A半族的鬣蜥氏、 袋鼠氏和负鼠氏)之间也是彼此禁婚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三个氏族是从一个母氏族中分化出来的,他们属于一个扩大化的血缘集团,并被假定起源于同一的祖先。B 半族的三个氏族也是一样。因而其群间通婚的一般规则也与正规的氏族制度有所不同,即通婚关系只能存在于两个半族之间而不能在其内部。
一般而言,卡米拉罗依人将其人口分为男女两大性别集团,每个性别集团再分为四个婚级。男性婚级分别是伊排、孔博、慕里和库比;女性婚级分为伊帕塔、布塔、玛塔和卡波塔;根据摩尔根的研究,八个婚级内在的通婚规则如下:
通婚关系 子女归属
男性婚级女性婚级 男性婚级女性婚级
伊 排 卡波塔慕 里 玛 塔
孔 博 玛 塔库 比 卡波塔
慕 里 布 塔伊 排 伊帕塔
库 比 伊帕塔孔 博 布 塔〔9〕
根据上述婚配权内的对应关系,卡米拉罗依部族的婚级制具有如下一些典型特征:(1)典型的群间通婚, 部族中四分之一的男子与四分之一的女子结为婚姻。显然,“通婚”是一个现代术语,按照澳大利亚的实际情况来看,所谓“群间通婚”系指部落中的一群男子与指定的一群女子之间的同居关系;(2)隔代通婚。虽然世系传承从母系计, 即子女总是归属于母亲所属氏族,并信奉母系图腾,但子女总是在同一氏族内转入与父母不同的婚级,这个规则显然表达了土著社群要求在其内部限制或取缔血亲婚配的朦胧意向,只不过所限制的仅仅是兄弟姊妹和亲子婚配关系而已。从上述通婚规则可以很明显地看出,第一代卡波塔的女儿归属玛塔,玛塔的女儿又转入卡波塔。换言之,祖母与孙女属于同一婚级,其通婚对象是伊排婚级中的所有男子。因而在卡米拉罗依部族,父女婚配关系禁止,祖孙婚配关系许可。“这种情况下,级别制度就是从杂乱性交关系的状态中直接产生的;或者是在级别发生的时候,父母和子女间的性交关系业已为习俗所禁止,……据我所知,在澳大利亚,父母和子女间的婚姻关系的例子还没有人提到过。”〔10〕级别婚的自然目的是“乱伦禁忌”,但隔代通婚的规则表明,在澳大利亚阶段,“乱伦禁忌”的实施是不彻底的。(3 )以性为基础的原始婚姻形态。
虽然人类的性行为完全出乎天性,但性行为的外在的法定形式——婚姻以及对人类性行为的法定形式的进一步规范(通常表现为一定地域内的群体对于代代相传的婚姻习俗系统的默认),却有着深厚的社会文化意蕴。从社会控制的角度而言,婚姻形态事实上标志着一种外在的可监控的社会秩序。作为社群中的个体,他往往被以各种形式灌输信守这一规范的理念。由于土著社群尚停留在前氏族阶段,未能建成正规的专职的行政管理体制,也不能产生专职的当权者,因而婚姻制度在社会控制中的作用是十分显著的,这是因为在所有的社会关系中,性关系是最活跃、最本质地反映个体欲求的社会范畴,性关系本身既隐含着加速社会分解、刺激社会动乱的因素,又隐含着维系社会稳定的因素。对性的控制,事实上是对人类社会生态的控制,因而性关系社会化所赖以表现的形式——婚姻及婚姻形态是一种人类用以维系社会生态平衡的基本方式,只不过同其他有形的政治制度相比,婚姻形态的演变基本上是依照所谓的“自然逻辑”进行的,这是本能地自发地进行的,并没有明确的目的意识。对性关系的控制,首先涉及的一个范畴,就是兄弟姐妹间、亲子间的性行为和婚配关系。在汉文化中,对这个范畴中的性行为的发生,称作“乱伦”,即扰乱社会秩序之意,这说明性关系的规范直接地涉及到社会秩序。马林诺夫斯基指出,“家庭成员之间的婚姻会使亲族上的地位发生错乱,从而不能实现孩子的社会化这一家庭所负担的义务。”〔11〕乱伦禁忌不仅是性的规则,而且也关系到婚姻的规则,同时也是社会秩序的规则。
三、层级划分与入族仪式是权利结构的原始形式
在澳大利亚土著社群中,权威的观念仍然十分淡薄,显然还没有出现专职的政权和政权管理者。在土著的采集狩猎社会,缺少形式上的领导权,也没有常设性的酋长职务。对于反社会的行为,并没有相应的常设性的机构来实施惩罚。个体对社群担负的责任、义务与权利的大小,由社群内部的层级结构加以规定与调节。一般而言,土著社群总是分为男女两类,男性社群内部再分为入族者和未入族者,对土著事务拥有发言权的主要是成年男子集团,其核心则是部落中的年长者,凡重大问题都由长老决策。虽然还没有形成一个真正的老人特权阶层,但是部落事务中处处可见到老人集团的不可或缺的影响力。老人集团是社群秘传文化的保存者,年龄愈长,对秘传文化的负载愈深厚。年长者知道在困难环境下如何应变,遵从年长者的建议对整个社群都是有利的;此外,年长男性对仪式的丰富知识,使他们在神圣的仪式筹划中具有不可替代性。由于这些原因,游牧群社会中年长的男性就占据着比他人更优越的地位。“老年男子享有的性特权,他们对秘传的文化的控制,以及凶残神秘的入族仪式,都是澳大利亚社群的一般特征。”〔12〕但是可以说,真正的政治性的领导权是根本不存在的,领导权只是社会性功能的分化,其本质是一种“基于性别和年龄的不同角色的活动。”〔13〕因此,在游猎群阶段的领导权,不是公共的职务,不是行政性手段的权威,其赖以领导社会的行政命令是建议性的。
与此相对应的是,女性则明显地处于社会的边缘。在权利结构的划分中,她们处于底层。在宗教生活中,她们被排除于神圣的宗教仪式之外。从族外婚的功能来看,列维一斯特劳斯曾指出,“在家庭内禁止结婚,就是把女性让渡给他人,作为补偿,则产生了从他人那里得到女性的权利,于此可以创造出基于交换女性的连带关系。”〔14〕女性是从某个游猎群到另外的游猎群的馈赠物,作为确保连带关系的一种形式而被互惠性地加以交换。交换女性具有政治连带的功能,这是家庭创造新的社会关系并扩大关系网络的契机。女人和男性老人组成了澳大利亚社会生活的两极,因而在实际生活中,仍然存在着一个权力结构,而且遵循着这样的规则,即“男人高于女人,入族者高于未入族者,神圣高于凡俗。”〔15〕
在澳大利亚社群的层级结构中,男性集团行使着主要的管理职能。为了使男子在社群事务中能够担负起真正的责任,他需要经历一系列残酷的入族仪式的考验,才被社群承认为合格成员,并参与社群的管理活动。这种入族仪式通常包括四个仪式段落:(1 )穿鼻礼(刺穿鼻膈);(2)割礼(即切割包皮);(3)下割;(4)接纳礼。 仪式通常从青年男子处于14—30岁期间继续举行,正好是一个人的身心成熟过程。澳大利亚入族仪式有其独特而神秘的宗教内涵,同时也具有一般的社会功能,即为社群塑造新的合格成员。这一塑造过程隐含着四个层次的内容:(1)划定个体在群体中的位置;(2)身心磨砺;(3 )文化灌输;(4)自我意识中新生过程的完成和群体对新生者的接纳。〔16〕
在文明社会,道德规范和法律秩序能够对社会中的个体产生一种普遍的和充分的控制力量。在原始社群中,仪式则隐含着某些公认的信息,“对于仪式的责任义务,仪式命令提供了服从并将其理性化的动力。”〔17〕正如拉德克利夫—布朗指出的,“原始人之消极的与积极的仪式之所以能够存在和延续,在于他们是秩序化社会赖以自我维系的部分机制,并用来建构某些根本的社会价值。”〔18〕仪式本身具有心理的和宗教的意义,但它的核心功能却在社会方面,即它具有教化作用。仪式是人们与某种社会地位相适应的诸多情感的规范化(秩序化)的表现形式,当人们参与仪式活动时,他们或者受到一种情操的熏染,或者被强制性地灌输了一种社会性的规范,而这正好是社会秩序赖以存在的基础。
四、图腾崇拜在自然和社会间建立起关联
澳大利亚土著最重要的宗教形式是图腾崇拜,“一个氏族常常把某种动物作为他的‘柯彭格’,他的朋友或保护者,作为人与其氏族动物之间的神秘联系的一种存在。”〔19〕图腾大多是动物。弗雷泽曾做过统计,在澳大利亚740个群体图腾中,有648个是动物图腾。”〔20〕常见的动物图腾是袋鼠、鸸鹋、渡鸟、蜥蜴等。除动物外,用作图腾的还有植物和非生物,豪伊特博士在澳大利亚西南部的部落中收集到500 多个图腾名字,其中有40个名字既不是植物也不是动物。
在澳大利亚,图腾制度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同时存在着母系图腾、父系图腾、族内婚图腾、族外婚图腾、两个半族的图腾和八个亚族的图腾。例如,瓦拉门加族和阿拉巴纳族内部并存着母系图腾和父系图腾,阿兰达族实行两个半族的图腾,卡米拉罗依人则实行典型的八个亚族的图腾制。根据杜尔凯姆的研究,澳大利亚图腾崇拜具有两个明显的特点:(1)澳大利亚图腾崇拜是迄今收集文献最为完善的一个种类; (2)澳大利亚的图腾崇拜虽然发展很不平衡,但却完全是同质性的。 这种同质性极为重要,它不仅造成社会组织的同一性,而且在诸多的部落中以同样或相等的名字为标志;图腾还标志着群体的划分,费森和豪伊特都曾指出,“澳大利亚的行政区划表明,图腾首先是一个群体的徽章。”
在澳大利亚图腾信仰中,图腾增殖仪式具有典型意义。图腾增殖仪式通常归结为三个主要的仪式段落:(1)以圣地以及圣地中的圣石、 圣树为直接媒介与祖灵及“拉塔帕”(非人非图腾、亦人亦图腾的二者死后的灵魂)的沟通过程;(2 )杀食图腾圣物——以图腾圣物为直接媒介与祖灵及“拉塔帕”的沟通过程;(3 )较长时间的仪式性歌舞——主观体验意义上的全身心沟通。〔21〕
图腾增殖仪式的宗教意义很复杂,要从根本上弄清楚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图腾增殖仪式的经济功能却很明显,即促使图腾动植物和图腾族人的双重增殖。这种增殖具有鲜明的利他性,在一般情况下,增殖并非是为了增加本氏族的食物来源,而恰恰是为了增加相邻氏族的食物来源。这与图腾信仰的一个普遍习俗——禁杀和禁食本部族图腾有关。土著深信祖先已化作某种动物或植物,进而规定了严格的食物禁律。在阿兰达神话中,“图腾祖先只靠自己特殊的食物为生。而今天情况正好相反:每一图腾集团都靠其他集团的图腾为生,而禁食自己的图腾。”〔22〕在这种情况下,相邻部族的图腾增殖仪式实际上是为对方增加食物来源。否则,禁食袋鼠的袋鼠族举行袋鼠增殖仪式就毫无意义。实际上,在族内禁食图腾的各社群间,图腾增殖仪式确实是互惠性的。根据列维—斯特劳斯的研究,每一图腾团体都有义务为其他团体提供自己专门负责其“生产”(意即通过图腾仪式增殖)的动植物。“于是鸸鹋族的成员在单独出猎时就不能碰一头鸸鹊”,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他是结伴出猎,就允许接触鸸鹋并应该射杀它,然后把它交给其他氏族的狩猎者。”〔23〕
由此可以看出,澳大利亚的图腾崇拜具有巫术——经济功能,作用于图腾的一整套仪式也是作用于土著社会的,图腾的增殖也意指族人的增殖,在这里,土著就在自然社会和人类社会之间建立起一种同态关系。“图腾代表着氏族,对土著居民来说,它实际就是社会本身。”在图腾仪式中出现的食物禁律,则隐含着道德规戒的作用,它构成了规定或禁止一些行为方式的某种道德的基础。
综上所述,在社会组织和行政性的领导权发育不成熟的澳大利亚土著社会,共同的秩序一般通过多层次的监控机制来加以维系。有形的社会组织的欠缺,使隐性的社会控制因素所起的作用更加突出。婚姻形式、入族仪式、层级结构、亲属制度、图腾崇拜与食物禁忌都成为社会的管理手段,共同维系着公共的社会秩序。正如马林诺夫斯基所说,“宗教需要整个的地方以使分子共同崇拜圣物与神祗,同时社会也需要宗教以维持精神上的律法与治安。”〔24〕这些隐性的控制因素并非单一性地发生作用,而是通过“互渗”与“叠加”律作用于社会。列维—斯特劳斯指出,“如果……一个种族把族外婚制与图腾制相结合,这是因为这个种族想加强已由图腾制建立起来的社会结合力,在图腾制上叠加另一个系统,这个系统是由于关系到血缘的和社会的亲属关系而与第一个系统结合起来……。”〔25〕入族仪式和生育年龄有内在的关联,其效果也体现了叠加原则,它与婚配权的取得是相一致的,实际上,不只是婚姻形态控制着性行为的规范,入族仪式由于控制着婚配权(通过规定结婚年龄)也参与了对社群内部性关系与性行为的管理。一般而言,叠加的层次越多,其管理功效也越强,对反社会行为的控制也更加严格。
注释:
〔1〕〔2〕〔7〕〔8〕〔9〕路易斯·享利·摩尔根,杨东莼、 马雍、马巨译《古代社会》(上),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49页、50页、51页、53页。
〔3〕〔5 〕《The New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WilliamBenton,Publisher,1943~1973年,第427页、425页。
〔4〕罗伯特·F·莫菲著,吴玫译《文化和社会人类学》,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第117页。
〔6〕威廉·A·哈维兰著,王铭铭等译《当代人类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89页。
〔10〕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39页。
〔11〕〔13〕〔14〕石川荣吉主编周星等译《现代文化人类学》,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年,第100页、120页、100页。
〔12〕〔15〕〔22〕〔23〕〔25〕列维—斯特劳斯著,李幼蒸译《野性的思维》,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109页、107页、117 页、129~130页、124页。
〔16〕〔21〕张岩《图腾信仰与原始文明》,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151页、147页。
〔17〕〔18〕史宗主编《20世纪西方宗教人类学文选》(上卷),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第118页、79页。
〔19〕爱德华·泰勒著,连树声译《原始文化》,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676页。
〔20〕岑家梧《图腾艺术史》,上海:学林出版社,1986年,第12页。
〔24〕马林诺夫斯基著,李安宅译《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37页。
